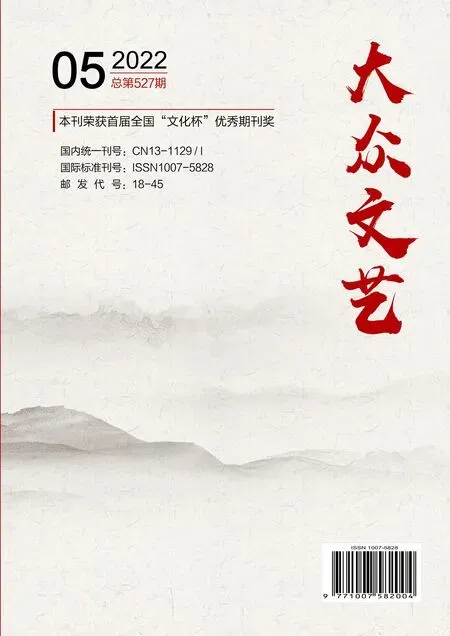论艺术正义在故事性艺术作品中的呈现
江 琳 (上海戏剧学院 硕士研究生 200040)
论艺术正义在故事性艺术作品中的呈现
江 琳 (上海戏剧学院 硕士研究生 200040)
《艺术正义及相关问题》一书中提出这样的命题:“一般来说,艺术正义只出现于故事性艺术作品。”原因在于艺术正义需要由善福恶殃的情节尤其是善福恶殃的结局彰显出来的,而善福恶殃的最终呈现是少不了必要的情节铺垫的。其中,艺术正义通过善恶有报的故事情节和故事的再造与结局的改编的方式,因为对对正义的迫切需要和爱与正义关系的原因,在故事性的艺术作品中呈现出来。
艺术正义;艺术作品
《艺术正义及相关问题》一书中提出这样的命题,即“一般来说,艺术正义只出现于故事性艺术作品。”其原因是艺术正义需要由善福恶殃的情节尤其是善福恶殃的结局彰显出来的,而善福恶殃的最终呈现是少不了必要的情节铺垫的,是少不了因与果之间多阶段的转换过程的。这种从恶行到恶报或者从善行到善报的情节链在故事性的艺术作品中才有可能呈现出来。那么,艺术正义在古而有之的故事性的艺术作品中是怎样呈现的呢,又为何会呈现出如此的概念呢?
一、如何呈现
(一)善恶有报的故事情节
艺术正义在故事性的艺术作品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作品本身是为了彰显善恶有报。正如博尔赫斯所说,故事的情节只有少数几种类型,或者说,这些故事有趣之处在于故事情节之间的转换与改写,而不在于故事情节本身。所有的故事情节其实都出自于少数的几个模式而已。而这种较为固定的善福恶殃的模式无论在东西方都最为常见。
卡尔维诺就曾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指出:在奥维德的作品里,神话是张力的场域,这些力量在其中冲撞或互相抵消。一切取决于神话被叙述的语调:有时众神会叙述他们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神话,以当做道德典范来警告凡人;其他时候,人类也会拿这些神话来与众神争论,或对他们提出挑战,就像庇厄里得斯或阿拉克尼。庇厄里得斯的女儿们知道一个关于提坦族攻击奥林匹斯山的版本,充满了被迫逃亡的众神的恐惧。她们在向缪斯挑战叙事艺术时,缪斯则以其他重建奥林匹斯众神权威的系列神话来回应;接着她们将庇厄里得斯变成喜鹊以示惩戒。
那么,善有善报呢?我们所认定的快乐是什么呢?我们又是如何看待失败与胜利的呢?现在当大家谈到圆满大结局的时候,想到的只是惑骗大家的结局,或者说比较商业手法的结局。博尔赫斯认为,“即使大家的心中总是感到一股挫败的尊严,不过几个世纪以来,仍然殷切期望快乐凯旋的结局”。例如,一旦有人写到金羊毛的故事,读者与听众会打从一开始就觉得羊毛最后一定可以找到。
(二)故事的再造与结局的改编
博尔赫斯曾谈到,人们对史诗的盼望相当热切。好莱坞能够把史诗般的题材粉饰一番,然后再推销给全世界在世界各地都一样,当人们在观赏西部片的时候,观众其实从这样的场面中还是得到了阅读史诗的感觉,追求到了正义在其中的声张。正如诗人除了会说故事之外,也会把故事吟唱出来。
无独有偶,这点在古代的中国也同样明显。消极补偿:中国特色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实践 一文中曾比较了四组具有源流关系的中国古代艺术作品,分别是:晋干宝的《韩凭夫妇》(《相思树》)与唐佚名的《韩朋赋》;唐元稹《莺莺传》(《会真记》)与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唐陈鸿的《长恨歌传》与清洪昇《长生殿》;明施耐庵《水浒传》与明李开元《宝剑记》。通过对这四组作品的比较,文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每一组中的第一个作品为第二个作品提供了素材,或者与第一个作品源自于同一个故事,而第二个作品总是改写了第一个作品的结局,或者改写了为第一个作品所承袭的源故事的结局。人们对圆满结局的殷切期望致使他们将作品无一例外地改编成善福恶殃的圆满结局。
当然,由于目标群体的不同,后一个作品较之前一个作品更为通俗。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曾谈到“18世纪英国剧场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都把它的悲惨结局完全改过,让Cordelia嫁了Edgar,带兵回来替李尔王报仇。这种翻悲剧为喜剧的玩艺,中外都很流行。我们尽管说它不是艺术,却不能不承认它有一般人的心理要求做后盾。”
二、为何会呈现
(一)对正义的迫切需要
上文提及的“一般人的心理要求”推动着人们将故事性文字作品的结局改编,从而让正义得以伸张。那这种心理要求会不会就是艺术正义呈现在艺术作品中的主要原因呢?
艺术正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充当了社会正义的代偿品?社会正义的不可得导致人们在艺术作品中寻求一种心理上的补偿。这点在《艺术正义及其相关问题》中已有相关阐述。如中国古代公案剧及公案小说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它们的结局几乎都是善恶有报。郑振铎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原因有如下解释,即平民们“实在也是去求快意,在舞台上求法律的公平与清白的。当这最黑暗的少数民族统治的年代,他们是聊且快意的过屠门而大嚼。”由于官府不能提供法律上的公平与清白,人们只能在舞台上去寻求安慰。
与此同时,宗教正义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社会正义的代偿品。当社会正义不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人们通过想象让它在宗教世界中的实现,来满足人们对正义的心理需求。当人间的统治者难以主持正义,人们选择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超自然之上,这是他们“期待恶人的没落的”的最大希望。
当然,迈克尔桑德尔提出“先有善,才能确定何谓正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取代“宽容公正”等德行,而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对什么是“善的社会”“善的生活”的理解,宽容公正等自由德行是否可能独立存在。
(二)爱与正义的关系
在艺术作品中,绕不开爱的永恒主题。在正义彰显的时刻,它与爱呈现出何种关系?对尼布尔来说,正义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而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所谓正义与爱相关是说正义从来没有自己独立的基础,它是爱在社会历史中的具体化。“爱和正义可以分别,但不能分开”“二者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等同”,尼布尔分别以“牺牲的”“超历史的”“不计利益得失的”等修饰语来限定和说明爱的特征。
历史中唯一完美的爱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通过放弃权力来实现的。与爱不同,正义含有历史性的因素,它必须把自私的顽固性考虑进来的,必须通过权力而不是放弃权力来实现自己。所以,正义是“审慎的”“分别的”,关注的利益和权力的协调和平衡。牺牲之爱和正义之间也是一种辩证关系:爱既是正义的实现又是正义的否定。尼布尔论述说:“爱是任何道德体系的极限概念。爱的要求实现同时也否定了所有的正义方案。爱实现了正义,因为生命对生命的责任在爱中比在任何平等和正义的方案中得到满足的可能性更大。爱否定了正义,因为爱消除了正义的制度对利益的审慎计较。爱不是在自我和他人的需要间的细致筹划,因为它只求满足他人的需要,从不顾及自身的利益。
[1]王云著.《艺术正义及相关问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9.
[2]刘时工著.《爱与正义(尼布尔基督教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
[3]伊塔洛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为什么读经典》[意大利]译林出版社,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