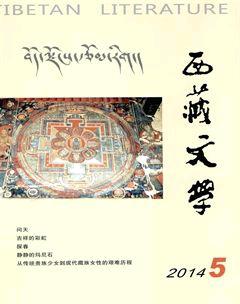从传统贵族少女到现代藏族女性的艰难历程
鞠晨
【摘要】本文以当代藏族女作家央珍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中主人公央吉卓玛的成长历程为线索,展现了她辗转于不同庄园的坎坷童年。通过对孤独的体验和爱的执着追求,她从传统的西藏贵族少女转变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现代藏族女性。
【关键词】藏族女作家现代女性人的觉醒独立意识
藏族女作家央珍于1994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目前研究这部小说的论文有徐琴《评藏族作家央珍的小说<无性别的神>》、栗军《时代巨变时期的不同书写方式文学多元化下的自觉审美追求——对小说<格桑梅朵>、<无性别的神>、<尘埃落定>的比较》、蒋敏华《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心理——兼评马原、央珍、阿来的西藏题材小说》、耿予方《央珍、梅卓和她们的长篇小说》等。《无性别的神》从贵族德康庄园二小姐央吉卓玛的视角,展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藏历史巨变的时代风貌。
小说描述了央吉卓玛孤独地辗转于德康庄园、帕鲁庄园、贝西庄园的童年生活和一步步脱离贵族的成长历程,塑造了一个勇于同封建势力划清界限,敢于追求理想的现代藏族女性形象。央吉卓玛从童年开始就被贵族圈子边缘化过程,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客观方面来说,变化无常的成长环境,制约了央吉卓玛对贵族礼仪的学习,使她没有机会接受西藏贵族家庭为后代进行的“限制性家庭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中,孩子们被有意识地培养成有贵族精神的人物。在礼仪方面,贵族家庭会利用一切机会给孩子进行言行规矩教育,包括“吃相”、“坐相”、“行相”等规矩。但是,对于颠沛流离的终日只有奶妈和女仆相伴的央吉卓玛来说,她受不到母亲的宠爱,也就得不到母亲的直接礼仪训练。因此,当她从贝西庄园被接回拉萨的时候,母亲嫌她吃饭像田里做活的农人、说话像街头的乞丐、完全缺乏教养,这让央吉卓玛感到“紧张和不习惯”。
从主观方面来说,一方面,央吉卓玛幼年时期就被动地远离贵族圈子,即使回到贵族圈里也找不到归属感。比如,当央吉卓玛重新回到拉萨自己的家时,却被家人嘲笑不会敬语、被训斥不懂礼节;家人外出赴宴时,母亲就让奶妈把她带到远处去玩,若不答应就用许多谎话来骗她,或者就干脆把她关到卧室等情景都让央吉卓玛感到和家人的隔阂。即使央吉卓玛逃亡到贝西庄园,有姑太太的悉心照料,她虽然感到“舒适、愉快”,但也感到“茫然和不习惯”。这说明央吉卓玛早已习惯被贵族冷落的生活,即使再次回到贵族圈子,她也不能适应被贵族法则约束、受人摆布的生活。另一方面,在与下层人民相处的过程中,央吉卓玛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因父母之爱的缺席,央吉卓玛只能与奶妈相依为命、与小女仆拉姆建立起超越等级的友谊。她通过拉姆了解了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看到了贵族阶层凶恶残忍的一面。经历了家族衰落的央吉卓玛看透了贵族社会的虚假,与参加上流社会的宴会相比,她更愿意和奶妈、拉姆在一起。她予以下层人民的温情和关怀,使她与把仆人当作牲口一样使唤的贵族群体有了本质区别。
由此可见,央吉卓玛在其辗转西藏各庄园的童年生活中远离了贵族社会,只有奶妈和女仆可以信任、依靠,反而逐渐具备了初步的独立意识,由被动地排除在贵族之外转变为主动寻找到心灵的容身之所,追求真性情的她在内心深处否定了她本应所属的贵族,将自己和“贵族”这个词剥离开来。
但是,与贵族社会的疏离又使央吉卓玛时时刻刻感到孤独,因此她比一般的孩子更渴望爱和尊重。出于对爱的焦虑和渴望,她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贵族以外的世界,寻找被爱的同时,她也给予爱,这一过程中她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因此,在央吉卓玛这一形象中蕴含着突出的特点:深刻的孤独体验、对爱的执着追求。
倘若我们重新回顾央吉卓玛的成长历程,会发现先后失去父母之爱、叔父之爱的央吉卓玛和后来深陷宗教困惑的央吉卓玛对爱表现出了特别的敏感和渴望。
母爱的缺失让央吉卓玛首次体验到孤独。央吉卓玛因为出生时的不祥不被母亲关注,从小就被贴上了“不吉利的人”、“命里没有造化的人”、“没有福分”等标签。后来父亲因病去世、继父到来、弟弟出生之后更是常被母亲遗忘。当母亲再次派人把她接回拉萨时,她竟认不出自己的母亲了,甚至在见到母亲时竟然“全身莫名的冷颤”。“冷颤”是人面对恐惧时做出的反应,对孩子来说,母亲本应是避风港,但央吉卓玛对母亲不是依恋或喜爱,却是恐惧。这说明央吉卓玛长期与母亲分离,并未深切地体验过母爱,母亲对她来说与陌生人没有区别。当奶妈的女儿达娃告诉她,母亲送自己去寺庙,并不是为了她能得到最终的幸福,而是为了省下一大笔置办嫁妆的钱。这时,消失已久的孤独、凄凉的感觉又回到了她的心中,从此她开始“怀疑一切,不再相信别人。”根据弗洛姆的理论,“我被人爱是因为我是我”,我不被人爱则是因为我没有成为别人期望的我。一般来说,母爱是无条件的,是对儿童的生活和需求做出的毫无保留的肯定。央吉卓玛作为贵族母亲的孩子,却因为她出生时的种种不祥以及后天养成的习惯、性格让她没有成为母亲理想中的样子,不合贵族礼仪的行为让她更像一个普通百姓家的孩子。“没有母爱,生活就会变得空虚”,所以央吉卓玛在家里仿佛掉进了一口大井底,感到说不出的憋闷和烦躁。
阿叔之爱让央吉卓玛体验到短暂的被宠爱的感觉。和阿叔在帕鲁庄园生活的那段日子是央吉卓玛最快乐的时光。在阿叔那里,央吉卓玛渐渐恢复了自己消失已久的任性、快乐、淘气。相比德康庄园的压抑和被人嫌弃,阿叔的一句“以后你天天都陪着阿叔好吗?”㈣让她感到了自己的被需要,这是她在德康庄园从未有过的体验。在阿叔家里她不顾小姐礼仪地跳上跳下、钻进全是灰的柜子、和仆人帕加在房里乱跑等行为在德康庄园都不被允许、甚至是会遭到训斥,却统统得到了阿叔的许可和包容。这久违的、来自亲人的关爱,使央吉卓玛想长久地留在帕鲁庄园不愿回去。
对宗教的失望促使央吉卓玛重新为自己的未来定位。央吉卓玛在母亲和姑妈的劝说下,渴望在宗教那里获得终极的爱和幸福。她以为从此能过上无忧无虑地受人尊敬的生活。可是进入寺庙后,她发现寺庙并不如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仍然存在着歧视,使她对宗教所说的平等产生怀疑。在她心目中最圣洁、最崇高的寺院也渐渐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她以为宗教能给她终极的安慰和爱,结果那份爱也不能成为她最终的精神依靠。
从以上的简单回顾中,我们可以在文本中处处感受到央吉卓玛对于孤独的深刻体验,尤其是她在帕鲁庄园体验到了家的感觉,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被爱、被尊重的感觉。但好景不长,阿叔也离世了。她常常孤零零地带着一双痴迷而探寻的目光在帕鲁庄园进进出出、四处游荡,阿叔的去世带走了央吉卓玛久违的温暖和宁静,也把她的心扯得空空落落。她感到时间变得从未有过的漫长,孤独和虚弱又重新萦绕在她心头,以至于每天早上醒来便感到一阵恐惧和颤栗。如果说不能被母亲所爱使央吉卓玛很小就尝到了孤独的滋味,那么爱得而复失之后的巨大心理落差更加深了她对孤独的体验。
弗洛姆说:“孤寂是引起强烈恐惧感的根源”。儿童时期的央吉卓玛一直处在孤独和寂寞中。在家里她不能唤起母爱,疼爱她的父亲和阿叔相继离世,宗教也让她失望。她的童年充斥着不被爱和爱的消失,在精神上她始终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人只有通过完全彻底地脱离周围世界,以至于不再感到与世隔绝,他对彻底孤独的恐惧感才会得到克服。”在贵族家庭里,央吉卓玛的行为与贵族的礼仪格格不入,现实的宗教生活与她想象中的状态也相去甚远,因此,她与周围的世界产生了强烈的隔绝感。央吉卓玛从贵族家庭走向寺庙,又从寺庙走向解放军,从心理学上分析,她的这一系列行为均是通过寻找爱从而摆脱孤独感的监禁。
首先,对爱的渴望让她从被动地获得爱转向主动地寻找爱。她不像姐姐或其他的贵族小姐什么都不做就能拥有来自家人和仆人的关爱,她拥有的每一份爱都必须通过努力获得。“爱人”是她获得爱的途径,只有去爱别人,才能争取到他人的温情。所以,她为受伤的身为仆人的拉姆偷清油,吃鱼时把大的鱼肉给拉姆,在姑太太用最恶毒、最轻蔑的语音大声训斥拉姆的时候为拉姆辩解。这是孩子对友情的渴望,同时也是对爱的焦虑的正常回应。在与下层人民的交往中,她分享爱的同时也感受被爱,在无意识层面使她和冰冷的贵族产生了本质上的区别。
其次,央吉卓玛的行为也符合马斯洛人的需求层次理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㈣。由于央吉卓玛感到自己在贵族家庭属于可有可无的状态,出于对被尊重的需要,她开始向往寺院。但是进人寺院后,她却开始思考:“既然铁匠和屠夫是底下的贱民,为什么不管是黑头俗人还是身披袈裟的僧尼都要吃屠夫杀的牛羊肉呢?又都使用铁匠打的刀和锅呢?所有的人不都是天天都必须吃肉的吗?所有的男人不是腰间都要佩带精美的装饰刀吗?我们没有沦为贱民是因为我们没有直接去杀牛去打铁吗?师傅过去不是总说佛教的灵光是众生变得平等吗?㈣”当央吉卓玛超越自己的贵族阶级,站在众生平等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时,表明央吉卓玛已经突破了当时西藏社会的某些既定思想,在她眼中没有职业的高贵与贫贱,平民和贵族也应该平等。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使她冲破了贵族视家族荣誉为最高美德的狭隘天地,在实践众生平等的同时也解放了自己。后来,央吉卓玛加入解放军、渴望学习汉语等举动都源自她对众生平等这一理想的追求。在最高层次需求的指引下,她勇于走出西藏,实现对真理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她实现了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觉醒。
她的成长之路一直伴随着对自己存在和价值的探寻。父亲去世的时候,她常常独自一人思考“运气到底是什么,自己真的是不吉利的人吗?”;阿叔死后,她曾想透过镜子看见自己的灵魂;因为装神弄鬼吓唬人被关进圣湖的时候,对她而言“命运”这个词仿佛是一个古老的符咒,让她感到敏感,因为这是“她耳边听到的最多在她心里琢磨最多的一个词”;她也渴望别人的肯定,所以在观圣湖的时候,她才会思考“为什么神灵不保佑我,让我成为一个吉利的人”这样的问题。前文提到,对于贵族家庭来讲,个人的感情仅仅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而央吉卓玛正是由于别人对她存在的否定和质疑才刺激她不断思考自身存在的意义,比起隐忍、牺牲个人感情的其他贵族少年来说,她的人格显得愈发独立。马克思曾说:“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央吉卓玛渴望别人的尊重不是出于自己的贵族身份。而是基于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与如同行尸走肉般被家族命运支配的贵族女孩相比,央吉卓玛在意识层面首先成为了“人”。
独立意识驱使央吉卓玛自主地选择人生道路。从德康庄园、帕鲁庄园、贝西庄园再到出家为尼、加入解放军青年联谊会,央吉卓玛先后在亲人、宗教和解放军那里寻求内心的寄托,但对爱的焦虑和对自我价值的渴求不断使她内心的寄托被推倒(失去对亲人的依赖)、重建(遁入佛门)、再推倒(离开寺庙)、再重建(加入解放军青年联谊会)。同时,她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也全权由母亲做主(被寄养到阿叔那里)、半自主(母亲把她送入寺庙的想法和她不谋而合)到完全自主(在没有征求父母的同意就毅然参加解放军)。马克思指出:“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央吉卓玛没有步入既定的贵族人生轨道,而是选择自由支配自己的生活,她主动解开了身上的贵族枷锁,在更广阔的世界里驰骋。
在贵族世界里不被喜爱,央吉卓玛感到孤立无援,这就形成了卡伦·霍尼所说的人的“基本焦虑”。被那些使她不安的状况所困扰,她自己摸索生活的道路,并在无意识中形成了相应的策略、发展了独立自主的性格倾向。
综上所述,央吉卓玛在她的成长历程中,颠沛流离的生活让她在渴望爱和不被爱的冲突中不得不为自己的生活做独立的决策:在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勇敢地投入时代的洪流,成为了自己的主人。因此,央吉卓玛是当代藏族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个由藏族女作家塑造出来的具有独立意识的现代藏族知识女性。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