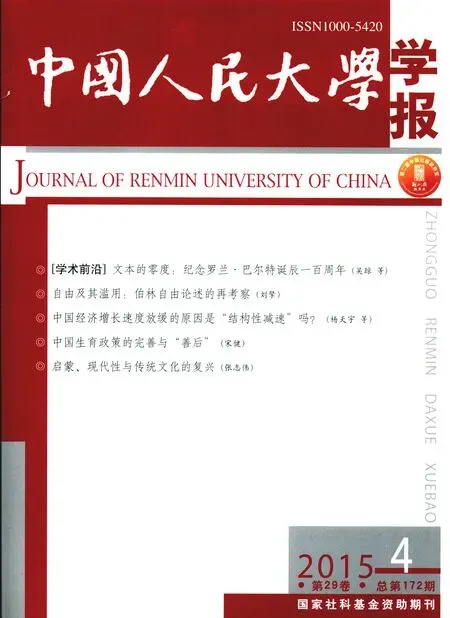中国生育政策的完善与“善后”
宋 健
中国生育政策的完善与“善后”
宋 健
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基础上,2013年年底启动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标志着中国的生育政策进入了其生命周期的转折点。生育政策的完善与“善后”是政策生命周期当前阶段的重要任务。生育服务证制度、社会抚养费制度和奖励扶助制度等配套政策的同步改革是生育政策完善过程中的必经之路,而构建国家层面的、保障计划生育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的社会安全网则既是奖励扶助制度改革的核心,也是计划生育政策“善后”的重要内容。
生育政策;生育服务证;社会抚养费;奖励扶助;计划生育家庭
2013年年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启动“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决策并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这一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的重大举措,牵动了千家万户,也标志着中国的生育政策进入了逐渐宽松化的历史进程。在历史的转折点回望来路,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全国普遍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经济和人口形势,更重塑了家庭结构、家庭伦理和家庭功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家庭、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家庭,以及作为“计生特困家庭”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笔者认为,中国的生育政策已经进入其生命周期的转折点,在不断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同时,应做好善后工作,协调配套政策,关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家庭尤其是特殊困难家庭,以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
一、中国的生育政策已进入其生命周期的转折点
(一)时代背景下的人口形势催生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是中国生育政策的主旋律,而且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力度和效果世所罕见。①例如,世界上最早施行计划生育政策(1952年)的、人口规模同样超过10亿人的印度,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为2.4,而同期中国的数据仅为1.6。参见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2014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P10,www.prb.org/Publications/Datasheets/2014/2014-world-population-data-sheet/data-sheet.aspx.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卫生事业的进步,我国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从1949年的20‰降至1965年的10‰以下且再未反弹;与之相对应的,是仍然高达30‰左右的出生率,在这个时期,绝大多数妇女处于生育不加控制的状态,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是衡量一定时期生育水平的指标,指假设一批育龄妇女按照某年各年龄段妇女的生育状况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人生育的孩子数量)除了个别年份之外,基本都维持在5以上。*1949—1965年期间总和生育率低于5的年份仅有3个:1959年4.30、1960年4.02、1961年3.29。数据来源: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与信息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11》,103页,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成就了持续近20年的快速的人口增长。分别于1953年和1964年开展的第一、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地区的总人口数分别接近6亿和超过7亿。庞大的人口规模和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呈现出人口压迫生产力*马克思在区分过剩人口时提出的观点。“人口压迫生产力”指同生活资料再生产条件相比,人口的发展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的窘况,就业和吃饭成为政府面临的两大难题。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不无忧虑地提到:“这样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1]。在这样的局面下,1955年3月中央首次发布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正式文件[2](P776),指出“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参见《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1955-03-01。,就此拉开了中国实施计划生育*1953年提出节制生育,在1956年毛泽东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之后,1957年开始叫计划生育,提法不同,内容相同。参见路遇、翟振武:《新中国人口60年》,772、780页,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9。的序幕。
从20世纪50年代以开展宣传教育、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供避孕节育技术服务为主,到60年代制定人口增长指标,再到70年代提出“晚、稀、少”的全国生育政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成形。20世纪80年代,随着实行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以及《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的发表,计划生育工作日益制度化。在严格的“一胎化”目标和严厉的惩罚措施导致的紧张与冲突之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育政策逐渐以“因地制宜多样化”[3]的形态稳定下来。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加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人口过快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到20世纪90年代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历史性转变,有效缓解了人口对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压力。目前虽然总人口仍在保持惯性增长,但内在自然增长率*内在自然增长率是稳定人口状态下的自然增长率,可以测度人口的真正发展趋势。当内在自然增长率为0时,反映了女儿一代恰好可以代替母亲一代的生育职能,代际间实现更替水平。内在自然增长率为负值,说明人口发展的内在趋势是缩减的。已远远小于零,净增人口数量不断下降,预计总人口将在2023—2025年左右达到高峰,实现人口零增长,然后进入人口快速负增长阶段。[4](P117)
(二)政策生命周期及其四阶段划分
生命周期通常指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这一理念往往被用于其他领域,如家庭生命周期等。政策生命周期是指一项政策从初始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开始,经过规划、决策、执行、评估乃至终结所经历的时间跨度和持续期限[5],反映在政策周期/循环理论中[6]。政策生命周期的开始和结束可以有清晰的边界,如以一项政策的颁布实施作为起点,以政策的废止作为终结;也可能是边界模糊的,如在政策颁布实施之前,对政策相关问题进行了较长时期的探讨和摸索,在政策结束之前,经过了耗时长久的调整完善,甚至与新的政策生命周期相重叠。政策所涉及的问题越复杂,其生命周期边界可能就越模糊。
虽然对于中国生育政策的阶段划分有多个版本*有四、五、六、七、九阶段等各种划分。参见王广州、胡耀岭、张丽萍:《中国生育政策调整》,21-2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但我们以政策目标的确定和完成作为标志点对政策生命周期进行四阶段划分。第一阶段是政策目标的确定阶段。从政策问题进入决策层视野,到统一思想认识,形成政策共识,最终确定适当的政策目标。第二阶段是政策目标的实现阶段。从建立机构、配备人员、制定配套制度,到通过各种手段宣传倡导、奖励惩罚、管理服务,最终实现政策目标。第三阶段是政策目标的稳定阶段。从多途径反复确认政策目标的实现,到继续统一认识、强化管理,同时探索新的政策目标。第四阶段是政策目标的转移阶段,在这一阶段,围绕新的政策目标逐渐达成政策共识,并确定下一步的政策走向。
(三)中国生育政策进入生命周期第四阶段
中国生育政策的生命周期始自20世纪50年代,从对中国人口是否过多的讨论开始,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
第一阶段为1953—1961年。震惊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受迫于人口状况与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央开始关注人口问题,并利用各种场合统一思想认识,在“反动的”马尔萨斯和新马尔萨斯观点与“作为榜样的”苏联鼓励生育的政策现实和“人口众多是极大好事”的主流舆论之间,努力探索既适合当时中国国情又能为时人接受的政策理念。经过激烈争论和多次反复,最终达成了“节制生育”的政策共识,并以缓解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减少新增人口数量,降低社会负担为目标。
第二阶段为1962—1990年。“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全国性生育高峰唤醒了被政治运动冷冻和耽搁了的“节育”共识与实践。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自1963年开始,地区性计划生育工作机构纷纷成立,1964年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1973年之后,人口增长指标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随后,陆续提出了“晚稀少”生育政策、“一孩”生育政策、“一孩半”生育政策等,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现了低生育水平。
第三阶段为1991—2012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达到2.31,在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背景下,这已非常接近更替水平。*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2.1为更替水平,但这是在出生性别比正常情况下的推算结果;当出生性别比偏高时,代表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指标也更高。事实上,反映代际更替水平的内在自然增长率指标在1990年时已经转为负值。[7]但政策惯性仍在继续,1991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体现了决策层对于人口发展趋势的不确定和对可能的生育反弹的忧虑。在持续的政策高压态势下,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1992年为2.05,1993年开始低于2;1998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1998年是自1949年以来正常年份中(1960年和1961年困难时期自然增长率分别降至-4.57‰和3.78‰)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10‰以下的水平。降到了10‰。经过近10年学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于中国生育率准确水平和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再三争论和辨识,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在肯定政策目标已经实现(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的同时,强调“计划生育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且“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工作要求更高,任务更艰巨”,“未来十年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时期”。之后,2001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2003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更名、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的出台等,表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一方面沿着法制化的道路继续前行,另一方面,工作重心慢慢从以计划生育为主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方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指“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等。转移。
2013年年初人口计生委和卫生部的机构合并,以及年末的生育政策调整,意味着中国的生育政策进入其生命周期的第四阶段,也是从原有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政策目标向新的政策目标转移的转折点。目前下一步渐趋宽松的政策取向已经确定,只在等待合适的时机逐步实施,而新的政策目标仍在讨论和斟酌中。
二、协调配套政策与完善生育政策应同步进行
在每一项核心政策的背后,都有若干配套政策作为其顺利实施的保障。伴随着生育政策生命周期的阶段转换,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的调整完善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本文主要讨论生育政策的“三驾马车”,即生育服务证制度、社会抚养费制度和奖励扶助制度这三项主要配套政策。
(一)生育服务证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
生育服务证又称“准生证”。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政策目标下,把握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态、引导其合法生育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因此,“准生证”制度几乎与计划生育政策同步实施,并体现在地区性《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对符合政策要求的育龄夫妇发放当年或下一年的生育许可,并标明胎次信息,既可以帮助政府通过事前申报和审批了解生育规模、进行生育规划,也可以区分甄别符合政策的与不符合政策的生育行为,进行相应的奖惩。
近年来,各地在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时逐渐将带有浓厚行政管制色彩的“准生证”更名为“生育服务证”或“计划生育服务证”,并制定了《(计划)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无论是生育第一个子女还是再生育子女,夫妻都需要在出示户籍所在地基层政府与计生部门核准的婚姻、生育情况证明之后,办理《生育服务证》,并作为合法生育的依据和依法接受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的凭证。“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由于夫妻的独生子女身份证明要涉及其父母的婚姻生育状况,使得办证程序格外麻烦,激发了公众要求改革生育服务证制度的呼声。目前有些省份开始进行生育服务证制度的改革探索,如湖北省于2014年取消了一孩生育审批*取消一孩生育审批并不意味着《生育服务证》的取消,只是群众不用再申请办理,改为由基层卫生计生部门在生育前主动发放,并依法提供计划生育各项技术服务。参见湖北省卫生计生委:《湖北省关于规范生育证件办理工作的通知》,2014-02-28。,但仅限于省内户籍人口。
生育服务证制度是原有政策目标下带有浓厚行政管理色彩的配套制度。夫妻在生育孩子之前,备齐各种证明文件先申请,再等待审批;持证生育者为合法,否则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在这一制度中,政府充当计划的制订者和生育的监管者角色,群众则处在被动的“请求生育被批准”的弱势地位,这不仅容易造成二者的对立,也是生育信息失真、部分人群为了躲避生育监管而宁肯放弃生育服务的原因之一。在群众多育观念已经转变、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形势下,这一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有待商榷。目前从政府方面来讲,生育服务证具有管理生育(规范群众按政策计划生育)、服务群众(对育龄人群提供从产前到产后一系列服务)和信息收集(获得育龄群众的孕产信息)三大功能。群众迫切希望简化办证手续并能方便获取所需要的各项服务。保留必要的功能,削减不必要的程序,为符合政策生育者提供尽量宽松的政策环境应该是生育服务证制度改革的出发点。
笔者认为,在生育政策逐渐调整完善的背景下,生育服务证制度的改革不仅应具有可行性,还要具有前瞻性,为生育政策完善之后的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留有余地。因此,提出如下建议:(1)变更“生育服务证制度”为“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即取消证件管理的形式,保留其提供服务和收集信息的功能,简化工作程序。(2)将事前审批(无论是一孩审批还是再生育审批)变更为事后登记(一孩或者二孩的孕检及活产登记)及核查。在登记时可特别区分一孩或二孩、“单独”夫妇或其他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妇等。(3)将由群众提供材料主动申报变更为政府部门对怀孕及出生登记信息的收集和审核,从而彻底减轻群众负担,突出政府行政功能。生育服务证制度的改革成败与否同部门间信息登记和共享制度的建立以及信息化建设紧密相关。机构改革实际上已经提供了建立出生登记系统的有利平台,通过将实时准确的住院分娩登记和出生医学证明等相结合,并增加孩次信息项,将有助于发挥机构整合优势,解决数据失真的顽疾。
(二)社会抚养费制度最终会消亡,但目前为时尚早
社会抚养费是由原“计划外生育罚款”演变而来的行政性收费,是对未按照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生育的公民进行的经济处罚。与生育服务证制度一样,社会抚养费制度也是保障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重要配套制度。2002年公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是与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相配套的政策。2002年8月2日公布,2002年9月1日起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对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目的、对象、标准、方式以及使用和监督等都做出了明文规定,“要求从2002年9月1日起,凡未按国家规定的法定条件生育的中国公民,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以补偿因多生育子女而增加的社会公共支出”。《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政府在处罚措施理念上的重大转变,主旨仍是借助惩罚性手段,引导群众的生育行为,尽可能减轻中国的人口压力。
由于存在征收标准不统一、征收程序规定混乱、缺乏监督和公开等问题,社会抚养费长期以来饱受诟病。2014年11月开启了对其进行改革的步伐*2014年11月2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向社会公布了卫生计生委报送国务院审查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及起草说明等,并公开征求意见。。新的《社会扶养费征收管理条例》较12年前的《征收管理办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主要体现在:(1)由“办法”上升为“条例”,法律地位得到明确;(2)征收标准进一步统一,设年实际收入最高三倍的上限,杜绝随意性征收;(3)征收对象缩窄为“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定多生育子女的公民”,将程序性违反生育的情形*程序性违反生育的情形如未及时办理《生育服务证》或未达到生育间隔等。排除在外,减少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群体;(4)从原来的15条扩充到30条,增加的部分主要强调了征收程序的合法性;(5)征收主体限定为县级政府,不再委托乡镇政府代收,避免了征收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
社会抚养费制度在新的人口形势下是否仍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笔者认为,由于计划生育仍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人口众多的国情也未改变,且计划外生育仍占一定比例,因此作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配套制度,针对“多孩生育”群体的社会抚养费制度仍有存在的必要性。对违反现行政策生育者,仍需要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但在征收对象(严格针对多孩生育)、程序(允许补登补报)、标准(动态按比例)和经费使用(公开透明)上要有法律依据并令人信服。社会抚养费制度最终会走向消亡,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宽,群众的生育意愿和行为与政策要求进一步吻合,计划外生育行为杜绝或减少到微不足道之日,应该就是社会抚养费制度寿终正寝之时。
(三)奖励扶助制度需顺应形势尽快改革
奖励扶助制度与社会抚养费制度分别是生育配套政策中的“胡萝卜”与“大棒”。中国的生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经历了从重“罚”到重“奖”的演变过程,即从主要依靠“计划外生育罚款/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来制约人们的生育行为,到重视依靠一系列奖励扶助措施来引导群众的生育行为。
在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对计划外生育采取了严厉惩罚的措施,包括超生罚款和行政处分等,这些措施促进了当时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成功推进,但也形成了严重对立的干群关系,计划生育被“污名化”不能说与此无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以惩罚为主的措施与计划生育在新时期的工作思路与工作方法背道而驰,因此,在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同时,为保护群众的基本权益,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国家到地方均积极探索以利益导向机制为主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主要是对独生子女家庭、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和晚婚晚育者给予各种奖励、照顾和优惠,以引导人们主动实行计划生育。[8]2000年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特别强调,要“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具体措施包括:“各级政府及涉农等部门要采取小额贷款、项目优先、科技扶持、政策优惠等措施,帮助计划生育农户增加经济收入,解决实际困难,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各级政府及扶贫开发部门应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户予以优先扶持,提高他们的生产自救和发展能力。各级政府及基层组织要建立激励机制,落实对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和优惠政策。对独生子女户发给一定数量的奖励费,城市独生子女父母退休时,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补助。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特别是只有女孩的家庭,在分配集体经济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承包土地、培训、就业、就医、住房及子女入托、入学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等。在中央的倡导下,2000年以来各地区奖励措施的分量逐渐超过了处罚措施,从以惩罚机制为主慢慢转向以利益导向机制为主。由于“奖”主要针对的是符合政策生育的对象,而“罚”主要针对的是违反政策生育的对象,因此奖励的面更大,对于计划生育家庭是一种经济和精神的补偿,但资金来源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的做法也限制了奖励的力度和效果。
在城镇化迅速发展且人口政策逐渐趋于宽松的现阶段,应适时梳理以往的奖励扶助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首先,需顺应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在奖励扶助措施上统筹考虑城乡计划生育家庭;其次,应区分新老对象,在依法奖励扶助以往计划生育家庭的同时,要鼓励群众按政策生育,取消对符合政策但自愿放弃生育指标者的奖励措施,以适应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形势,并减少新的不必要的独生子女家庭的产生;第三,应建立国家专项基金,为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弱势人群和家庭构建以国家作为后盾的社会保障安全网,这也是计划生育政策“善后”工作的核心。
三、建立国家层面的计划生育家庭 扶助制度是善后工作的核心
(一)生育政策并不完全遵循效果逐渐递减法则
按照“公共政策效果逐渐递减法则”[9](P155),“任何政策工具的运用都会在政策目标实现的同时带来一些有意或者无意的效果。随着政策的实施,那些有意识可预见的效果会逐渐缩小,而那些无意识不可预见的效果则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在研究中我们发现,生育政策并不完全遵循这一法则。
在政策目标实现层面,生育政策的效果的确呈现出逐渐弱化的态势。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在死亡水平不断下降的同时,必须降低生育率,这是生育政策的目标得以实现的唯一路径。人口学家认为,生育率降低的直接因素是结婚年龄、已婚比例、避孕比例及效率等,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等其他因素必须通过这些直接因素间接地发挥作用。[10]计划生育有助于推迟结婚年龄(提倡晚婚晚育)、增加避孕比例(免费提供避孕药具)、改进避孕效率(研发高质量避孕药具),因而为降低生育率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对中国生育率下降都有重要的影响[11],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生育的作用在减弱,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则不断增强[12]。
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意识可预见的效果包括可能导致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老人缺人照顾等问题,但这些效果并非都会随着政策实施而逐渐缩小,有些效果的严重性已经超出预期。研究发现,总体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家庭的影响正趋于式微。虽然中国家庭户规模变化的大趋势由出生率水平的变化所决定,因而计划生育是导致平均家庭户规模迅速缩小的主要原因,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生育水平已经降到很低,少儿人数的减少对家庭户规模的影响不断减弱,由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迁移流动及生活方式变化导致的家庭分化程度提高对家庭户规模缩小的影响则日益凸显。[13]人口老龄化本身受到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影响,死亡率下降增加了老年人口数量,生育率下降则因减少了少儿人口比重而相应地增加了老年人口比例。当放宽生育政策、新生人口不断增加时,老年人口比例(即老龄化水平)会随政策调整而降低,却并不能因此减少老年人口的存量。当然,我们可以仅就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率的影响所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认为其对于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效果是逐渐下降的。出生性别比失衡成为近30年来困扰中国的顽疾,因为这一现象的发生与生育政策的实施几乎同步而使生育政策遭受广泛质疑。然而,生育中的性别偏好尤其是男孩偏好才是性别失衡背后的根本原因,生育政策只不过是加速了人口转变,加剧了数量/性别选择的冲突,医疗技术的进步和便利又恰好提供了实施“两非”*“两非”指非法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的手段。不消除性别偏好,生育政策再宽松,“非男不止”的生育行为仍会大行其道。目前人们也正在观察“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趋势,有人认为偏高趋势会有所缓解,也有人认为反而会加剧二孩的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老人缺人照顾的问题虽然在政策实施初期就被预见,但因其混杂在老龄化、高龄化、城镇化等人口和社会转型一系列问题中,问题的严重程度和解决的困难程度都超乎预想。现在已经是当时认为有能力消减或避免这些负面影响的“将来”,生育政策的转折期也是实施生育政策善后工作的最后良机。
(二)构建国家层面的计划生育家庭社会保障安全网是生育政策“善后”的主旨
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过程也是国家利益与群众利益博弈的过程,是社会风险转嫁为家庭风险的过程,独生子女家庭尤其是“失独”家庭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尽管“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作为“普遍二孩”政策的前奏已然启动实施,然而过去几十年间所积累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人群和家庭,并未随着政策的调整完善退出历史舞台,相反,他们作为当时国家政策的积极响应者,有些人已经永远失去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机会,并遭遇了或面临着“失独”的风险。在“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基本国情下,生育政策仍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短时期内不太可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但通过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可以防止政策意义上的独生子女家庭继续累积,避免产生新的风险家庭;同时政府应积极关注、妥善对待那些为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做出贡献的家庭和成员,尽快构建替代其子女功能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并作为奖励扶助制度改革的重点内容。
以极端弱势家庭“失独家庭”为例,由于8%~9%的独生子女会在55岁以前因患病或非正常原因而死亡[14],随着独生子女规模的日益增加,“失独”家庭的数量也随之上升。虽然就全国整体而言,“失独”家庭的数量是有限的,占全部家庭的比例微乎其微,但在较早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且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较好的地区,独生子女家庭比例更高,“失独”家庭的数量不可小觑。例如,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0~30岁的独生子女为40 954人,占同龄人口比重的53.46%;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2010年终身独生子女母亲*界定“终身独生子女母亲”为年逾50岁且活产和现存子女数均为1的妇女。占独生子女母亲的比例为29.30%,占全部50~64岁妇女的比例为60.80%;而终身“失独”母亲*界定“终身失独母亲”为年龄在50岁以上的活产子女数为1而现存子女数为0的妇女。占全部“失独”母亲的比例为40.63%,占全部50~64岁妇女的比例为0.26%。这些人群正是在中国生育政策生命周期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度过了其育龄期,帮助国家的政策目标顺利实现却使自身的家庭陷入了巨大的风险。
“失独”父母尤其是丧失生育能力的终身“失独”父母在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重大精神打击之后,从此缺失了从子女处获得各种养老支持的可能性。2001年国家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先将帮扶的责任主体定位于地方政府;2007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规定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每人每月可领取不低于100 元/80元的扶助金,资金由各级财政负担。*其中西部、中部和东部试点地区的地方财政负担比例分别是20%、50%和100%。仍以北京市为例,2008年制定的《独生子女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实施方案》规定,“具有北京市户籍、独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由政府给予每人每月20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为止”。2014年北京市将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独生子女伤残扶助金、独生子女死亡特别扶助金分别由原来的每人每月100元、160元和20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120元、400元和500元。*参见北京市卫计委、市财政局:《关于提高本市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和特别扶助金标准的通知》,2014-11-17。其他各省也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不断上调扶助金标准。即使是这样,与不断上涨的物价相比较,扶助金仍是杯水车薪。除了经济补助外(包括一次性补助金、月度养老扶助金、商业保险金等),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是“失独”父母面临的更大难题,且更难获得满足。在入住医院、养老院等机构时,没有子女签字就成为这些“失独”老人过不去的一道坎。目前各地均在社区层次进行“失独”老人长期照护的探索,虽然区域差异明显,但总体而言,目前采取的政策措施的主要特点为:(1)扶助对象一般针对户籍人口;(2)经济扶助是主要手段;(3)根据夫妻的生育能力,分别采取措施(有生育能力的会帮助其再生育);(4)结合社区资源建立帮扶基地;(5)民间公益组织积极参与;等等。但适合全国的统一扶助模式和标准还未出台。
笔者认为,我国应结合生育政策调整完善过程中奖励扶助制度的改革,针对过去几十年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受影响的人群和家庭,特别是对“失独”家庭,尽快建立全覆盖(考虑到城乡一体化的未来发展趋势)、高标准(应该与生活成本和物价水平动态链接)、多层次(应包含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社会保障安全制度。最重要的是,这一制度应该是国家层面的,且应有相应的国家专项基金作为保障。还应注意与残联的合作协调(针对独生子女病残家庭)、与养老相关政策的衔接配套,以及达到老年年龄界限前后人群的扶助衔接等。如果说实行计划生育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那么,补偿扶助因计划生育政策而陷入困境的家庭也应该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这是生育政策调整完善过程中重要的善后工作。
[1] 周恩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1953年9月29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 路遇、翟振武:《新中国人口60年》,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9。
[3] 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载《人口研究》,2003(5)。
[4] 王广州、胡耀岭、张丽萍:《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 马海韵:《政策生命周期:决策中的前瞻性考量及其意义》,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
[6] 杜本峰、戚晶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回顾与展望——基于公共政策周期理论视角分析》,载《西北人口》,2011(3)。
[7] 王丰、郭志刚、茅倬彦:《21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载《人口研究》,2008(6)。
[8] 杨魁孚:《积极建立控制人口增长的社会制约机制和利益导向机制》,载《人口与经济》,1992(6)。
[9] R.J.英特威尔德:《政策工具动力学》,载B.盖伊·彼得斯、弗兰斯·K.M·冯尼斯潘编:《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0] Bongaarts,John.“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Proximate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78,4(1):105-132.
[11] 顾宝昌:《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载《中国人口科学》,1987(2)。
[12] 陈卫:《“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的动态关系:中国省级数据再考察》,载《人口研究》,2005(1)。
[13] 郭志刚:《关于中国家庭户变化的探讨与分析》,载《中国人口科学》,2008(3)。
[14] 《人口研究》编辑部:《对成年独生子女意外伤亡家庭问题的深层思考》,载《人口研究》,2004(1)。
(责任编辑 武京闽)
China’s Birth Policy: Adjustment and Compensation
SONG Jian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China’s newly revised birth policy in 2013 allows the couple either of whom is the “only child” to have the second kid. It indicates that,though family planning still holds the position of the basic policy of the country,birth policy that runs over the past decades in China has entered into a new stage in its life course. This stage expects urgently simultaneous reform of the supporting policies involving birth permission certificate,social compensation fee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under the new socio-demographic contexts. The central issue of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incentives system is to construct a special national-level social security network for birth- policy-affected families especially those who have only child and have lost the only child,which is also the compensatory obligation of the birth policy.
birth policy;birth permission certificate;social compensation fee;economic incentives;birth-policy-affected families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失独’家庭生存状况及相关政策研究”(13JDSHB007)
宋健: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