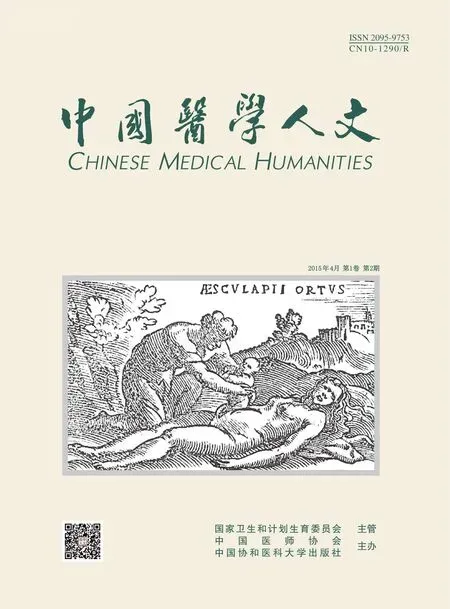灯下的夜
文/邹 垚 摄影/缪小燕
灯下的夜
文/邹 垚 摄影/缪小燕
医院是一个永远不会熄灯的地方。暖箱是医院里最温暖的小天地。
我来到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就要8个月了,夜班的次数也记不清楚了,平均每个月七八个吧。也许每个月的月圆之夜我都在值夜班,也许这个夜晚在世界某一处正有着对月咆哮的狼人。我和我的同事不会对月咆哮,因为我们看不见月亮在哪里,月光的皎洁势必会被医院内的灯火通明抢了风头。当然,我们也不是狼人。大概我们只能对着NICU里的灯光,内心咆哮着“别收孩子”。
别收孩子。这四个字不仅仅意味着这个夜班度过的平安,更重要的是证明在这里出生的娃娃都是足月的、健康的、不用承受收下来接受治疗的痛苦。医院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蔓延着病人的呻吟,空气里每一丝都是每个人不同的痛苦。而对于一个早产儿来说,他的啼哭、他的痛苦,全数被收在NICU病房里的一个小小的暖箱当中。
每个在NICU上班的人都经历过夜里收进小娃娃或者抢救的洗礼。称之为“洗礼”,大概是因为我要在月光和灯光的见证下挽救一个新生命,而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数量远不如白天,还有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在睡觉,我和我的同事则有可能忙一个通宵。
上学的时候偶尔会跟同学朋友约个时间玩儿个通宵,当时觉得夜晚的生活丰富多彩,大家兴致勃勃,精疲力尽后休息一个白天就立地“满血”复活了。而上班以后,通宵的频率就不是“偶尔”了,在这个灯火通明的地方,通宵是个常事。通宵做的事情内容的确是“丰富多彩”,到了天亮也确实是“精疲力尽”,却再也不是“兴致勃勃”。
回到主题。
一个600克的娃娃从妈妈肚子里出来了,迎接他的不是妈妈的亲吻,不是爸爸的怀抱,也不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笑脸。这些都是建立在他能够长到2000克以上、能够摘掉氧气、自己吃奶还不会危及生命的前提下。此时此刻,他被几道紧张的目光注视着,被一双陌生而温暖的大手检查着,一根帮助他维持供氧的管子会被这双手插入他的气管。他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就被抱起,放到人生中的第一所“房子”里,我们叫它转运暖箱。紧跟着,他就来到了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住进他的专属暖箱。
有一所“房子”是要有代价的。他的代价就是不仅仅有一根管子在他的气管里,还有一根胃管在食道直到胃里,一根留置针在血管里,以后还会有一根中心静脉导管从手臂经过血管到达他的上腔静脉,还会有一根管子从肛门放入到达他的肠子里。这些管子看起来比他的小胳膊没细多少似的,不是说管子太粗,而是他太小了。你能想象他的头像一个成人的拳头大小吗?能想象他的胳膊就是你的一根手指的长短粗细吗?把你的手伸出来,比划一下。
他躺在这所“房子”里,就好像你站在故宫广场里。但是,再夸张的比喻也没法让你理解这么一个具象的存在,因为见不到便无法想象,一旦见到则是难以想象。我们都已记不得他的本来面容了,那一眼只是被送进来的一瞬间。现在,他的脸上身上被贴上各种保护用的或者监测用的贴膜和胶布,每一块都比他的皮肤还厚。
NICU门外站着焦急的父亲,等待着我们把小人儿的生命维持住,等待着走出来一个人告诉他这个与他有着血缘关系的生命是否安好。他当然是要安好的,暂时。这个夜班的任务就是:把他的生命安好地交给下一班的同事。班班如此,他才能安好地出院回家。
NICU是这个医院里最温暖的地方。暖箱为小人儿提供温室般的环境,干净而温暖,安静又舒适。一个生命成长的距离是什么?是小人儿从骨瘦如柴到圆润丰满的距离,是由一只手的长度长到指尖至肘长度的距离,是“居住”时间一分一刻的距离,是没有血缘关系却产生爱意的距离。爱意钻进暖箱中,没日没夜地散发热量,温暖着小人儿的手足。爱意弥散在空气中、附着在呼吸机的湿化罐中,随着小人儿的每一次呼吸而游走。爱意居住在每一批营养液中,顺着泵管进入到小人儿的血液中。爱意驻足在我们的指尖,随着每次与小人儿的触碰而传递到他的全身。爱意起源于我们的心底。
NICU也是个“冰冷”的地方。当然,不是说我们上夜班的时候被冻得全身冰凉快要感冒。人类的成年被定义在18岁,才是被视为可以独立生活的年龄。而这里的小人儿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便远离了父母亲人。虽说不能独立生活,却是真真正正地独自面对生死存亡。
小人儿在带着气管插管的时候的痛苦谁也不能体会,他躺在暖箱里,被方巾固定在特定体位,眉头紧皱,闭着眼、张着嘴,躯体扭动,手脚挣扎,他在哭泣、张大嘴巴嚎叫,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这是生命的挣扎和呐喊,哑剧演员在台上所传递给人的情感和演技的震撼远远不及此。我们的爱意在此渺小得可怜,他已无暇感受我们的爱,他必须奋力拼搏,必须对所有有碍生命的威胁进行不懈地抗争。
在生命面前,我们即使充满爱意和坚持,却也只能看着他饱受治疗的痛苦。我们给予他生存的帮助和支持,而最终生命的坚持只有他自己才能做到。他虽然生后只有18小时或者18天,却比大部分18岁的人面对生死的次数多得太多。这里条件限制无法探视,虽然只有几十米的距离,却是父母无法跨越的难度。他们永远无法知道自己的孩子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无法想象他是怎样逐渐长大脱离了各种机器、奶量逐步增加、一切平稳直到出院的。
NICU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都是圣人。通常我们会感慨父母的爱是伟大的,不过在这里要在小人儿出院了才能更好地体现。我以为,对自我存在有所怀疑、对未来心灰意冷、对生命心存放弃的人,不用言语劝解,来到这里“一日游”就会有所触动,明白生命本身就在于抗争艰险和坚持不懈;对于那些情感冷漠的人,来到这里“一日游”,也会明白无论有无血缘,爱是无处不在的。就像我们工作在这里的人,与小人们都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却承担了抚养其成长的责任。
我们给他好的治疗和护理,用各种方法减轻他的痛苦,帮助他成长,陪他闯过发育不全、呼吸困难、肺炎、颅内出血、喂养不耐受等等一系列坎坷,最终把他送回到父母的怀抱。我们亲手养大的小人儿,看不见我们长得什么样子,看不见我们的“小花帽”是什么颜色和图案,不记得曾经被谁抱在怀里喂奶、哄他入睡,不记得曾经谁夸他长得漂亮、表现好。我们亲手把小人儿“交还”给他的父母,心里有着不舍,但这是最最令人欣慰的“成果”。我们的爱面对着这些刚出世便来到这里的小人儿,也面对所有即将出生的小人儿。他们的不到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福音,也是所有父母的福音。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一个夜班12小时,12小时的不熄灯是为了维护这里的生命,是为了点亮小人们的生存之路,让他们在看不见月亮的夜里不会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