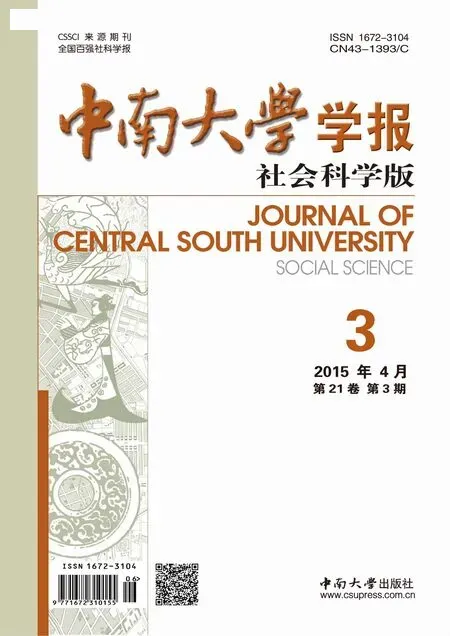《松花笺》“拆字法”的生成与审美诉求
——以“三犬之风”为中心
任增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海外汉学研究所,山东青岛,266555)
《松花笺》“拆字法”的生成与审美诉求
——以“三犬之风”为中心
任增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海外汉学研究所,山东青岛,266555)
“三犬之风”是洛威尔与艾斯珂汉诗译本《松花笺》对李白诗句中“飙”字的译法,此一译法便为“拆字法”,即将单个汉字加以拆解,厘析各组字偏旁的意象特质,进而赋予其以诗性言说。中外学界对《松花笺》的褒贬不一,“拆字法”是纷争之焦点。对“拆字法”的非难,是未曾考量彼时美国诗界向东方寻求创作资源的时代吁求,忽视了西方“语音中心主义”传统的置入。“拆字法”发明出汉诗中某些汉字的诗意潜流,彰显出汉诗的审美空间,但亦会引致一些翻译败笔。
三犬之风;《松花笺》;拆字法;语音中心主义
“三犬之风”是美国译家洛威尔(Amy Lowell)与艾斯珂(Florence Ayscough)对李白诗句中“飙”字的译法。20世纪上半叶,美国意象派诗人洛威尔与汉学家艾斯珂在合译的《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1921)中将李白《塞下曲》①中“骏马似风飙”一句译为“Horses! Horses! Swift as the three dog’s wind!”(马群!马群!急似三犬之风!)。在此,两位译家将“飙”字拆析为三个“犬”字与一个“风”字,并将“骏”加以拆解,将其中作为偏旁的“马”字与后一“马”字等量齐观。此种译法即体现了洛威尔与艾斯珂所力倡的“拆字法”(character-splitting),即将单个汉字加以拆解,厘析各组字偏旁的意象特质,进而赋予其以诗性言说。
细勘《松花笺》,其援用“拆字法”之译例不一而足。由此一方面遭到了诸如陶友白(Witter Bynner)、张歆海(Chang Hsin-hai)、张安尼(Annie Chang)、叶维廉(Wai-lim Yip)、葛瑞汉(A. C. Graham)、周发祥等诸学者的驳难;但另一方面《松花笺》却赢得了公众的欢迎,在1921年12月第一次出版后便一售而空,次年重印,其后又多次再版。有美国学者指出《松花笺》在公众中获得了“应有的成功”,并认为洛威尔是比英国著名汉学家与译者亚瑟·韦利(Arthur Waley)更强的诗人。[1](19)尤值一提的是,《松花笺》中关于“飙”的拆字译法,在中国现代诗人朱湘的散文《书》中得到了呼应与暗合。可以说,围绕《松花笺》的“拆字法”聚讼纷纭,贬斥之声颇大,但亦不乏褒扬或精神暗合者。本文尝试结合西方“语音中心主义”语境,对“拆字法”的审美价值加以探寻,并辩照其得失,对之做一较为公允评断。
一、《松花笺》中的“拆字法”
《松花笺》是洛威尔与艾斯珂两译家合译的一部汉诗诗集。所谓“松花笺”,原本为唐代女诗人薛涛自制的用以写诗的彩色笺。译家以此命名其诗集,显示出对中国诗歌的特殊情愫。正是出于对唐诗的酷爱,两位译者虽天各一方,但仍以鸿雁传书的方式进行翻译合作:身在中国上海的艾斯珂首先将每首诗的汉字及英文翻译、字形解析以及字面义、引申义写出后寄至远在美国波士顿的洛威尔,后者本人并不通晓汉语,只凭借对诗歌的灵感,对注释材料加以再创造。在将其翻译成英语后,复寄往艾斯珂处对照原文加以校阅润饰,如此往复,历时四年方付梓印行。
藉由汉字字貌以传达汉诗诗意,是洛威尔与艾斯珂在《松花笺》中所倡导并践行的翻译方法。在为译本所撰“序言”中,两位译家强调了汉字之于汉诗诗意表达的重要性。洛威尔指出,她们在研究之初便察觉到,汉字偏旁部首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远比通常所意识到的还要大。诗人之所以择选此一个汉字而非与其同义的另一个,无非是因为此一汉字间架中蕴蓄着某种描述性寓意(descriptive allusion);汉诗之意蕴正由于汉字结构中的意义潜流(undercurrent of meaning)而得以充盈。[2](vii)她同时强调,援用“拆字法”是助其更准确地释读原诗,并非孤立地对译某些偏旁部件。
作为汉学家的艾斯珂亦持此论。她以为,对汉诗的研治绝不可绕开汉语的语言学特质;汉字在汉诗创作中所起作用之大不容低估。汉语是表意的文字,换言之,是图像的语言。中国文化中有书法艺术,而西方没有,恰恰说明汉字是言述完整思维图像的单独个体。诗歌与书法在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中是互相依存的,此将诗歌与绘画艺术融为一体的文化现象,要求西人在解读汉诗时不仅要观瞩每一个汉字的表情达意功能,更则兼顾汉字偏旁互相组合之后的整体功效。[2](lxxxvii)
艾斯珂进一步解释说,汉字从结构上可以简单字符与复合字符两大类划分。具有独特意涵与用法的简单字符可作为偏旁,彼此有机结合进而构建出更为复杂的复合字符。各个偏旁作为独立之实体在组合中发挥它们或表音或表意的功能,表述复合字符不同层面的意义,最终完整地呈示出该字符的整体含义。汉字独特的组合方式,为中国诗人建立了通往“个性诗意”表达的途径。所以艾斯珂的结论是“若要充分把握诗人意图,就必须具备分析字符的知识”[2](xxxviii)。
可见,洛威尔与艾斯珂的“拆字法”着意偏旁组合对原诗整体诗意潜在的言述作用,为此细译每一汉字偏旁的意涵,将汉字结构分析所得有机融入译文中,从而呈现出汉诗原有之风貌与神采。在《松花笺》中援用“拆字法”的译例,除上述李白《塞下曲》中“骏马似风飙”一句外,尚有其他。
比如二位译家将李白《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中最后一句“白云堪卧君早归”中的“早”字加以拆解,将“早”译为“when the sun is as high As the head of a helmeted man),转译为汉语,即是说,“当太阳升至有戴头盔人头顶那么高的时候”。单看“早”字,其上有一“日”字,整体观来,则貌似一戴头盔者。
又将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中“犬吠水声中”的“吠”字拆析为“口”和“犬”,将该句译为“一只狗,一只狗在叫,还有水流激荡声”(A dog A dog barking And the sound of rushing water)。
再如将唐代诗人綦毋潜《春泛若耶溪》诗中“生事且弥漫”里的“弥”字加以拆解,衍生出“湍急的水域,涌动,绵延”(a swiftly moving space of water, a rushing, spreading water);将“原为持竿叟”一句里的“竿”析出“竹”字,将整句译为“手拿竹钓竿的老翁”(an old man holding a bamboo fishing-rod)。
二、学界对“拆字法”的批判
《松花笺》在1921年12月出版后,批判之声便不绝于耳,对此西方学者迈克尔·卡茨(Michael Katz)曾做过一番梳理。如美国诗人陶友白在1922年2月《诗刊》第19期撰文指出,《松花笺》的译法太繁琐,正如过分强调英语中daybreak、breakfast、nightfall、landscape等单词的组词含义那样,过分强调汉字组字偏旁亦失之谬误。此外,民国时期的外交官兼学者张歆海,曾在1922年7月出版的《爱丁堡评论》第236期撰写《中国诗歌的流行》一文,指出洛威尔的译文用词太多,颇显冗赘。张安妮在伦敦大学时所撰硕士论文(1959)中,亦批评洛威尔和艾斯珂的译文在描述性的细节上过于繁复。美国华裔汉学家叶维廉也曾评论说,《松花笺》使用了与庞德关于象形文字的看法相联系的、其谬误已为人所知的“拆字法”[1](193−197)。
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对《松花笺》的“拆字法”也颇有微词,“翻译汉诗,最必需的是简洁的才能,有人以为要把一切都传达出来就必须增加一些词,结果使得某些用字最为凝练的诗人被翻译成英文后,反而显得特别冗赘。”[3](19)
直至上世纪末,国内学者周发祥亦持否定态度,以为《松花笺》在使用“拆字法”的地方,“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以“三犬之风”译 “飙”字“令人陡生疑惑”[4](87)。
可见,正是因为强调翻译汉字时必须把隐喻和部首完全译出来,才给译文招致了“冗赘”的诬名。而事实上,中、英作为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在数、格、时态、人称等方面差异较大,即便将一首汉诗转译为形式同样凝练的英文诗歌,恐已是难能之事,遑论形式与内容均达及“简洁”。学界对“拆字法”的非难,是未曾考量《松花笺》出现的时代语境,更进一步言之,忽略了西方“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传统的置入与译家以英文传递以汉字为载体的汉诗诗意的良苦用意与审美诉求。可以说,“拆字法”远非一无是处,相反,其秉持的审美价值不容小觑。
三、“拆字法”成因及优势探析
一战的浩劫强烈地冲击了欧美传统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促使人们开始质疑长期以来奉为正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准则。一些知识分子试图在欧美传统文化之外,如悠久神秘的东方文化中去探寻出路,寻求新的思想和创作源泉,而具有突出审美特征的汉字意象无疑会引起英美诗人的关注,成为激发其诗歌创造灵感的新资源。汉字有高度的视觉可见性,因此不同于需要隔着一个层面去理解的、由拼音文字组成的欧洲诗歌。从直接的观感中,即可把握到汉诗意象的流动过程,这也使得汉诗成为了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所谓的一种记录自然运动的非常生动的速写图画,而汉诗的这种运动规则,也是与大自然或“事物”本身的律动规则是一致、相匹配的。在洛威尔与艾斯珂的“拆字”译中,我们注意到其所揭橥汉诗的几大特点,就是“自然”“感性”与“运动”。而这些又都是与对生命的具体性活力的强调密切系联的,由此而对理性主义的思维习惯与文化病疴做了尖锐的针砭,借“中国”之矛,攻“西方”之盾,也就是为解决西方本身的文化问题而援用中国文化资源。对此,已有学者对之做出详尽的论讨,似毋庸喋述。②当然,如做进一步考察,洛威尔与艾斯珂对汉字与汉诗之关系所表现出的极大兴趣,并由之而能发现汉字的审美特性,则都是因其将汉语置于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坐标系中加以审视之结果。
“语音中心主义”推崇言说,贬低文字。此种“中心主义”始自柏拉图,历经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卢梭直至索绪尔等,形成一个脉络清晰的传统。柏拉图将文字视为一种奇怪的东西,认为对文字的学习,会在灵魂中助长遗忘。亚里士多德认为:“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并不是有相同的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5](55)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实现那必须予以实现的东西,其所依靠的力量就在于说话。”[6](55)口说的语言表述着自我本身。卢梭更是强调言说对于文字的优越性,他强烈谴责描写性的、堕落的人工文字,认为文字削弱了言语,依据书写来判断天才,就如同根据尸体给人画像。结构主义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仍是将口说的言语凌驾于书写文字之上,认为文字是能指的能指,是不同于语言的内在本质的外在符号系统。然而,在中国古代非但不存在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传统,还似乎形成了一种以象形为本的“文字中心主义”,与西方传统对于口说的言语的推崇相对。显然,中国不存在“二元对立”的宇宙观,并不具有西方意义上的“中心论”,但确实存在一种与西方“语音中心主义”不同的重文字的传统。
这一点,早期的来华耶稣会士便曾意识到,并尝试在图画般的汉字符号中演绎深远的基督教义。如马若瑟神父以为汉字中的“十”“日”“东”“羊”“麒麟”“凤”均为基督教中的象征,最为奇妙的是“船”,表示“八口人乘舟”,与《创世纪》中的诺亚一家八口乘舟逃离大洪水的故事相吻合。[7](83)对汉字加以分解,以此证明中国人是诺亚的后裔,自是无稽之谈。但是,由审美角度而言,析出汉字的偏旁部首,进而构建出种种鲜明意象,并加以并置与叠加,此一方面确实可以引出无尽联想。这一点,英国汉学家德庇时(John Davis)已然察觉到,其在《汉文诗解》一书第一部分“汉诗作诗之法”中就曾指出,“长期以来似乎有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汉诗的全部优势来自于对汉字奇特而富于幻想的择选,以及对其偏旁部首的考量。”[8](5)虽然德庇时在这方面未及详述,然其关于汉字作为汉诗媒介重要意义的零星表述,却在费诺罗萨的汉字诗学理论,庞德、洛威尔、艾斯珂等的汉字结构分解实践中遽成气候。
20世纪初,美国学者费诺罗萨发表《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一文,突出强调汉字之于汉诗表达的独特媒介作用。费诺罗萨认为汉字的标记远不仅仅是武断的符号,其基础是“记录自然运动的一种生动的速记图画(shorthand picture)”[9](12)。“诗歌语言总是振荡着一层又一层的弦外之音(overtone),振荡着与大自然的相似性,而在汉语中,隐喻的可见性往往把这种品质提高到最强的力度。”[9](29)费氏认为,汉字所赋予隐喻的可见性是弦外之音强烈振响的原动力。如“日升东”三个字中,左边有太阳在闪着光,另一边,树木的枝杈遮蔽着太阳的圆脸;中间的日轮,则已升至地平线及附着物之上了。整个气氛通过“日”这个形象而浑然融合起来,恰似在主旋律之外响起了烘托作用的“弦外之音”。
费诺罗萨认为,通过解析汉字结构本身去挖掘汉字字面外之意涵,可以更为形象生动地表达诗歌的“言外之意”。由此,将汉字的意义从诗学、美学的维度展开,演绎出一整套汉字诗学的理论。其《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一文经由著名诗人庞德的鼓吹,成为上世纪初美国新诗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费诺罗萨着重探究汉字偏旁部首或基本笔画的意涵,再加上庞德在实践上的推波助澜,终于促成西方汉诗英译中的“拆字法”。而洛维尔与艾斯珂等便是此一理论的积极践行者。③
从另一方面来看,“拆字法”并非如先前几位学者众口一词的“冗赘”,而恰如韦勒克与沃伦所言:“诗歌不仅是写给耳朵听的,也是写给眼睛看的。”“中国诗歌中图画式的表意文字构成了诗的整个意义中的一部分。”[10](153−154)从而使汉诗的美感意蕴得以丰赡。而且“由于文字的象形性,很自然地容易唤起视觉上直接的参与,这就有利于语言上形象思维的更为活跃”[11](4),而“拆字法”对汉字之形体与偏旁部件意涵的厘析,便彰明了汉字的形象性,在某些情况下于开掘与言述诗歌整体潜在之诗意颇有助益。
无独有偶,朱湘曾在其散文名篇《书》中也将“飙”字拆解为“三条狗的风”,进而对汉字的诗性功能做过一番生动的描述:“一个个正方的形状,美丽的单字,每个字的构成,都是一首诗;每个字的沿革,都是一部历史。飙是三条狗的风:在秋高草枯的旷野上,天上是一片青,地上是一片赭,中疾的猎犬风一般快的驰过,嗅着受伤之兽在草中滴下的血腥,顺了方向追去,听到枯草飒索的响,有如秋风卷过去一般。”[12](35)
《书》作为朱湘的散文名篇,发表在其本人1927年创办的《新文》月刊上。我们虽难以考订朱湘是否览过《松花笺》,但其由“飙”字结构而构建出的诗意想象却与“拆字法”惊人暗合。④中西诗人所见略同,表明汉字是具有诗性的语言,在“这种在有形的文字后一些隐约存在的审美活动使得整个文本增加了不少感性的、丰富的主体性,正如一幅画因光、色的丰富而增加了不少美感”[13](58)。但英语作为表音文字,无法直接再现汉字的风貌,若如朱湘所解,“飙”字中蕴涵着猎犬疾如风般的飞奔,加之,战马风驰电掣,这无疑渲染出李白诗歌中拉枯摧朽、势不可挡的雄浑气势。故而洛威尔与艾斯珂诉诸于“拆字法”,通过解析汉字偏旁,释放了汉字结构中所潜隐的审美意义流,“Horses! Horses! Swift as the three dog’s wind!”在此“the three dog’s wind”同样可以引发英语读者的审美想象:辽阔的战场上骏马奔驰,卷起的狂风如猎犬在追逐猎物,而马嘶声,犬吠声,瞬间一起袭来……由此感知到李白诗歌描写鏖战与厮杀的激烈场面,非但弥合了英文感性不足的缺陷,而且传达出汉诗隐而未彰的独特风韵。
再如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首句“犬吠水声中”将“犬声”与“水声”两种声音并置,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以为其诗境营造效果在于“把来访者告诉隐士和把隐士居处之闭塞离群显示给来访者之外,流水声与犬吠声还构成一个突入结构,即给人以一个诗人的不速来访打破了隐士清净世界的类似感觉”[14](289)。而洛威尔与艾斯珂将“吠”字拆解为“口”和“犬”,将该句译为“A dog A dog barking And the sound of rushing water”(一只狗,一只狗在叫,还有水流激荡声)凸显了声音效果,可谓是对原诗意境的生动彰明与再现。
四、结语
汉字的笔画与结构可以直接诉诸读者的视觉,在给读者鲜明的形象刺激的同时,还可以唤起想象。闻一多指出:“我们的文字是象形的,我们中国人鉴赏文艺的时候,至少有一半的印象是要靠眼睛来传达的。原来文学本是占时间又占空间的一种艺术。既然占了空间,却又不能在视觉上引起一种具体的印象——这是欧洲文字的缺憾。我们的文字有了引起这种印象的可能,如果我们不去利用它,真是可惜了。”[15](415)而身处“语音中心主义”传统中的费诺罗萨、庞德、洛威尔与艾斯珂等国外汉学家及诗人以“他者”的视角,得见汉诗文字形态的独特性;难能可贵的是,他(她)们摆脱西方偏见,由汉字与汉诗关系角度入思,揭示汉字的审美与诗意价值。在他们看来,汉字作为象形表意的文字,其特性与西方拼音文字有别。在记载与传达事物方面,汉字重在视觉,拼音文字则侧重于听觉。拼音文字由抽象的字母符号组成,其只能唤起接受者对抽象概念的记忆,尔后联想到该事物的感性质地;而汉字的象形、指事和会意可以不经过抽象概念而直达对象的感性与知性,汉字自身的形象与“意”具有直接关联,它是“意”的直接符号,而非间接载体,“每一个汉字就是一首诗”[16](41)。洛威尔与艾斯珂的“拆字法”经由对汉字的分解,拆析出偏旁部首,进而构建出一个个鲜明的意象,将汉字的诗意充分释放出来,极大拓展了汉诗的诗性空间。
但我们在肯定“拆字法”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看到其毫无诗意之败笔。诸如将“原为持竿叟”一句里的“竿”析出“竹”字头,拆解为“竹”与“竿”,将整句译为“a bamboo fishing-rod”(竹子的钓鱼竿),确实有前文中评论者所指摘的“冗赘”之嫌。“拆字法”有其成功之处,但若逢字便拆,滥用之下也难免遭人诟病。
注释:
① 《塞下曲六首》为唐代诗人李白的组诗,共由六首诗构成。经由叙述汉武帝平定匈奴侵扰,以乐观高亢的基调和雄浑壮美的意境再现了盛唐气象。“骏马似风飙”一句出自该组诗的第三首。
②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钟玲,《中国诗与美国梦——美国现代诗中的中国文化模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瑞典汉学家林西莉在所撰《汉字王国》(该书于1989年在瑞典出版,获得瑞典最高文学奖——奥古斯特文学奖,后由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刊出中译本)一书中,亦有对汉字诗性的精彩解读。如其所言,“見”是一个站着或坐着的人和一只大眼;“谷”字,让人想起一个人走进黄土高原沟壑里的滋味,寒冷的春风刮着,晴空万里,细软的黄土像面粉一样。没有一棵树,连一根柴棍也没有,只有干涸的河底,歪歪扭扭的黄土墙和浓烈的艾草味儿。分别见该书2008年中译本之第31页,第67页。
④ 《说文解字·犬部》中云“猋,犬走貌。从三犬,甫遥切。”段玉裁注:“引申为凡走之称。”此“走”为“跑”义,疾跑,迅速。而“飙,扶摇风也。”朱湘似由此而获灵感。
[1] 迈克尔·卡茨. 艾米·洛威尔与东方[C]// 比较文学译文集.张隆溪选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2] Ayscough Florence, Lowell Amy. Fir-flower tablet: poe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M].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1.
[3] Graham A C. Poems of the late T’ang [M].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5.
[4] 周发祥. 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5] 亚里士多德.解释篇 16a[C]// 范畴篇/解释篇. 方书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6]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贺麟, 王玖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7] 周宁. 天朝遥远: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8] Sir John Francis Davis.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M]. London: Asher and Co., 1870.
[9] Ernest Fenollosa.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 [M]. London: Stanley Nott, 1936.
[10] 韦勒克, 沃伦. 文学理论[M]. 刘象愚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11] 林庚. 汉字与山水诗[J]. 文学遗产, 1995(6): 4.
[12] 朱湘. 书[C]// 朱湘散文选集.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13] 郑敏. 余波粼粼: “‘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研讨会”的追思[J]. 诗探索, 1997(1): 58.
[14] 宇文所安. 中国传统中的诗歌[C]// 美国学者论中国文化. 罗溥洛主编, 包伟民, 陈晓燕译.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4.
[15] 闻一多. 诗的格律[C]//《闻一多全集》第3卷. 北京: 三联书店, 1982.
[16] Purcell V W S.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etry [M]. Singapore and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1929.
The three dog’s wind: on the character-splitting of Fir-flower Tablets
REN Zengqiang
(Institute for Overseas Sin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66555, China)
The three dog’s wind as a translation of the character ‘飙’ in Li Po’s poem is a case in point of character-splitting, which as a technique of translation is adopted in Fir-flower Tablets, but dismissed as verbose by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critics. The dismissive critique on character-splitting is partial due to the neglect of the American context and western phonocentrism. As a translation device, character-splitting is instrumental in rendering the poetic meanings of some characters in Chinese poetry, though it does not work for all.
three dog’s wind; Fir-flower Tablet; character-splitting; phonocentrism
I207.2
A
1672-3104(2015)03−0262−05
[编辑: 胡兴华]
2015−02−02;
2015−04−29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D75107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51046);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J13WD6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4CX04059B)
任增强(1980−),男,山东泰安人,文学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海外汉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海外汉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