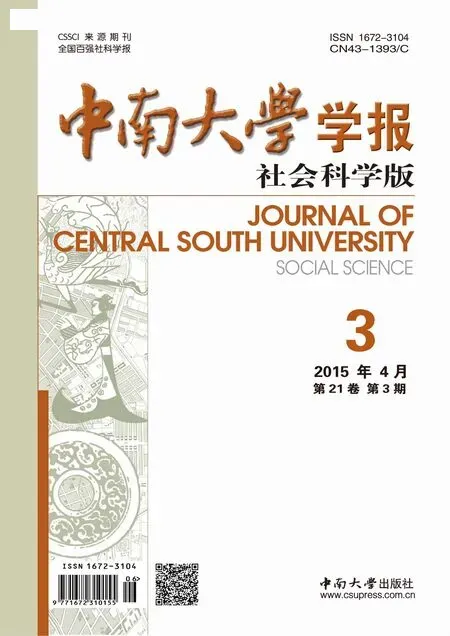《资本论》价值概念的“术语革命”
——经济范畴的存在论意涵
孙慧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资本论》价值概念的“术语革命”
——经济范畴的存在论意涵
孙慧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是以对商品的价值概念的分析作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起点的。其价值概念与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原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关的纯粹定量的经济范畴的价值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首先,马克思在对李嘉图的“价值唯实论”和贝利的“价值唯名论”的双重批判中,对价值的性质和内涵进行了重新考察,实现了价值概念的“术语革命”。其次,马克思将价值概念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范畴,通过揭示现代商品社会劳动取得社会形式的特殊方式,从而揭示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本质。第三,马克思将价值概念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对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人受资本统治的异化状态进行了揭示和批判,由此构成了《资本论》价值概念深刻的存在论意涵。
《资本论》;价值;术语革命;存在论意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以商品,准确地说,是以商品的价值形式分析作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起点的。人们常常容易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价值概念,因为在其他的经济学家那里已经有同名称的经济术语。这可能会导致对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的广泛误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并不是简单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是在对李嘉图的“价值唯实论”和贝利的“价值唯名论”的双重批判中,于商品交换关系中发现了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具有不同内涵的“价值”概念。事实上,马克思的经济术语都是围绕着生产关系展开的,他将经济术语视为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这揭示了其政治经济学的真正主题和理论关怀。《资本论》中的价值概念不是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形态的一般经济范畴,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建制及人的异化的概念化而呈现出来的社会历史范畴。马克思揭示了价值概念的“历史性”,打破了政治经济学将价值概念视为非历史的概念的“形而上学”,实现了价值概念的 “术语革命”。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1](33)马克思通过对价值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人受资本统治即人的异化过程的状态进行了揭示和批判,这构成了价值概念深刻的存在论意涵。
一、价值概念的“术语革命”:马克思对李嘉图和贝利的双重批判
众所周知,价值概念并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新鲜术语,它在马克思之前的诸多经济学家那里已经得到了较为完整的阐释。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对价值概念的性质和内涵进行重新界定的“术语革命”,主要在于对李嘉图的“价值唯实论”和贝利的“价值唯名论”之争的批判和超越。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看来,“一件商品的价值,或所能换得的他种商品的数量,乃定于生产所必要的相对劳动量。”[2]李嘉图的价值论是较早的劳动价值论,即认为商品的价值由其内部具有的劳动属性所决定,并具体由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量所决定。劳动作为价值的实体,无论商品是否完成交换,其价值已内在于商品之中。我们借用日本学者广松涉的称法,把这种价值论称为“价值唯实论”[3](77)。
而经济学家贝利对李嘉图将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量的主张进行了批判,指责李嘉图说,“价值本来是诸商品相互关系上一个相对的性质,但他把它转化为绝对物了。”[4](110)贝利通过对商品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商品的交换关系的考察发现,商品的价值只能通过和它进行交换的另一商品的量才能表现出来。因而,在贝利看来,价值就是商品的购买力,“价值不指示任何积极物,或商品固有的东西,只指示二物当作可交换的商品互相间保持的比例。”[4](124)也就是说,贝利将价值看作是商品的交换关系的表现,认为在相对的价值关系背后,并没有一个价值对象性的共同实体。我们仍借用广松涉的称法,将贝利的价值论称为“价值唯名论”。
可以说,克服“价值唯实论”和“价值唯名论”之争是马克思进行价值概念“术语革命”必须要面对的理论难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形成价值的原因。通常人们认为马克思价值概念的形成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有着重要的继承关系,这源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明确提出的,“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1](53)但若是仅仅据此来理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相等同,价值概念将被还原为一种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形态的“生理耗费说”,并得出一切劳动产品都是商品的结论。而这不仅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的“用来满足自己需要而生产的劳动产品不是商品”[1](54)的论断相冲突,并使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价值定位为“幽灵般的对象性”[1](51)的论断变得无法理解。
事实上,马克思高度重视贝利从价值形式的角度,从商品的交换关系中去考察商品的价值。关于贝利对李嘉图的价值论的批判,马克思评论道,“虽然他(指贝利)眼光短浅,但触及了李嘉图学说的弱点。”[1](78−79)李嘉图只关注构成价值的劳动时间的量的规定,而从未从形式的方面考察过价值。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一书中曾指出,贝利对李嘉图的批判之于马克思,犹如休谟对经验论的批判之于康德的重要性。正是贝利使马克思从李嘉图的价值唯实论的迷梦中惊醒,从而使得马克思开始从关系的视角去看待价值范畴。[5]马克思正是从商品交换活动的“关系”视角出发才发现了价值概念的内涵,并明确指出,“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1](61)
但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从李嘉图的“价值唯实论”走向了贝利的“价值唯名论”,而是对二者进行了双管齐下的批判。贝利指出同一数量商品的价值在与不同商品进行交换时具有种种不同的相对表现,即具有多种交换价值。如一件上衣与X量谷物、Y量呢绒相交换,将得到上衣的谷物价值和呢绒价值。因而,在贝利看来,商品的价值只是表示“该商品在交换中的关系,……因此,……有多少种商品,就有多少种价值,它们都同样是现实的,又都同样是名义的”[1](78)。由此,贝利将一切消解于关系,认为商品价值只是一种纯粹相对的东西,而彻底否定了规定价值概念的可能性。而马克思就此批判道,贝利“把价值形式和价值混为一谈”[1](64),将商品交换价值以商品的量呈现出来的表面现象当作了商品的价值,而忽视了商品等价的交换关系是以同质关系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交换活动本身并不能产生价值,“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1](61)贝利没有意识到,当上衣作为价值物与谷物、呢绒相等时,是将缝制上衣与种植谷物和织制呢绒的具体劳动化为了同一的抽象人类劳动。因而,在马克思看来,在商品的交换关系背后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实体,抽象人类劳动就是商品价值的“社会实体”。
那么,如何理解被马克思称为“幽灵般的对象性”的价值的“社会实体”的抽象人类劳动,是理解马克思构成超越“价值唯实论”和“价值唯名论”之争的价值概念“术语革命”的关键。
马克思在商品的交换关系中看到了李嘉图和贝利都没有觉察到的东西——构成价值的劳动的特殊性质——“劳动在人类劳动的抽象属性上形成自己的价值”[1](67)。马克思对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道,“至于价值一般,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的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1](98)李嘉图将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即具体劳动量的差别,而没有意识到,“各种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1](98)这意味着,价值并不是作为有用劳动的凝结而内在于商品中的天然属性,凝结为不同质的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只有转化为同质的、无差别的、一般的抽象人类劳动,才使得商品可以互相通约。
马克思价值概念的“术语革命”的关键在于提出价值的实体是劳动,但这种劳动是“社会的劳动”,是抽象人类劳动。这种抽象人类劳动不是去除掉有用劳动的具体性和特殊性,而是将其抽象为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能量上的耗费。因为这样抽象而来的一般劳动仍是表现为使用价值的一般有用劳动,而不是表现为价值的劳动。这种一般有用劳动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但适用于人类一切社会形态,甚至无法与牛、马等牲畜所进行的劳作区分开。在马克思看来,表现为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转化为表现为价值的抽象人类劳动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6](423),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商品交换过程中才能完成的“抽象”。并且这一过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1](58)。也正是因此,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间不是某种具体的、既定不变的时间量,而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1](52)再生产该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要再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动,那么即使生产商品的实际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也要发生变动。这便是被马克思称为是“幽灵般的对象性”的价值的“社会实体”的抽象人类劳动的真实内涵。正如广松涉在《资本论的哲学》中指出的,“在高层次上虽是与广泛的商品世界的社会关系的反思规定相关的das Arbeit(抽象人类劳动),但就价值形式而言,是作为实体的基础而存在。”[3](136)
我们看到,正是在对李嘉图和贝利的双重批判中,马克思重新探索了价值概念的性质和内涵,超越了“价值唯实论”和“价值唯名论”之争的地平,实现了价值概念的“术语革命”。正如美国学者麦卡锡所指出的,“在马克思看来,价值是一定性的社会关系,不能还原成定量的比价。事实上,商品具有价值仅仅因为社会关系,而非因为劳动本身。”[7](284−285)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分析的价值概念绝不是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一般经济范畴,而是人们在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生产活动中的关系的理论表现的“历史性”范畴。
二、作为“历史性”范畴的价值概念:揭示现代商品社会劳动的社会性的特殊形式
对于价值概念,马克思关注的重点是劳动的社会性在现代社会中取得“社会的形式”的特殊方式,是劳动表现为价值的背后的社会历史基础。社会分工使得社会成员彼此为对方劳动,因而劳动的社会性体现在一切人类社会形态中,只是劳动取得“社会的形式”的方式不同。在马克思看来,价值概念只是劳动在人类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现代商品社会中取得社会性的特殊方式的理论反映,它绝不是什么超历史的经济范畴,而只是商品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透过价值概念的棱镜,马克思要揭示的是现代商品社会“独特社会关系的定性确定”[7](290)。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价值概念揭示出了现代商品社会中蕴藏的三组对立关系。第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商品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个人以彼此独立的商品所有者的方式存在,其商品对他来说是非使用价值,他只有将其转化为交换价值才能获得其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商品对于它的所有者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才是使用价值。”[6](434−435)第二,具体劳动和抽象人类劳动的对立。具体劳动并不是由于其具有的不同形式和有用属性而可以彼此交换,恰恰相反,具体劳动只是由于被抽象掉了劳动的一切具体形式和特殊属性,即作为同一的、无差别的抽象人类劳动才彼此交换。第三,私人劳动和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相对立。在商品社会中,虽然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社会总劳动总是由各种私人劳动的总和构成。但在商品社会中,劳动的社会性并不是采取私人劳动的特殊形式,相反,劳动的一般性才表现为劳动的社会性。或者说,私人劳动“要通过采取与自身直接对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才变成社会劳动”[6](426)。
我们看到,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作为商品社会生产体系的客观基础,在自身中已经包含着社会对个体的强制和否定。使用价值、具体劳动、私人劳动,总之,一切体现为劳动的个性的特殊形式和目的的感性东西都被劳动的价值形式扬弃为了抽象的、同一的、无差别的存在。个体只有作为这种抽象劳动——价值的提供者,才成为社会的存在。对此,马克思指出,“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在于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方式才具有的这种特点,对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来说,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的。”[1](91−92)价值范畴对于商品社会的生产关系来说,是具有“社会效力”的“客观”的经济范畴。
然而,当我们考察其他社会生产方式时,就会发现蕴藏在价值概念中的种种对立关系消失了。例如在农村宗法式的社会中,或是作为生产前提的公社中,人们按照自然联系进行分工,而互相为彼此劳动。凝结为不同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并不以价值的形式存在。“个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机体的一个肢体的机能”[6](426),由此,劳动的特殊性直接构成了劳动的社会性,而无需转化为无差别的抽象人类劳动才能获得其社会有效形式。或者说,“成为社会纽带的,是个人一定的、自然形式的劳动,是劳动的特殊性,而不是劳动的一般性。”[6](425)因此,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揭示出的是在现代商品社会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与历史上以往劳动形式性质不同的劳动社会化组织形式。劳动的价值形式不过是“劳动借以获得社会性的那种特有形式”[6](425),绝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永恒的、超历史的经济范畴。
正如前文所述,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具体的、个别的、私人的、有用劳动转化为社会的、一般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的过程,是只有在商品交换事后才得以完成的“抽象”过程。作为价值的“社会实体”,“一般社会劳动不是现成的前提,而是变成的结果”。[6](438)也就是说,在商品生产的前提下,劳动的社会化性质,只有在不同种商品的等价形式中才能显示出来。因为商品社会的特征是,商品生产者作为商品所有者而彼此独立存在,他们除去商品交换不发生关系。
这里的关键在于,使劳动表现为价值的“抽象”过程得以实现的交换过程绝不是物物的直接交换,而是表现为必须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而前文所述的李嘉图和贝利的价值论虽表现不同,但其根本上都是只关注价值的量的规定性。在他们看来,仿佛商品可以不以货币为中介而直接物物交换。而社会事实是,当产品生产采取商品生产的形式,就意味着,物物交换的社会阶段的解体和终结。物物不能直接交换,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商品生产的前提中了。李嘉图和贝利都忽视了这一“抽象”过程中的关键——价值必然以交换价值的化身即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作为价值尺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是潜伏在商品中,并且只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才以货币的形式显露出来。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价值形式的考察指出,由价值概念所揭示出的商品社会的三组对立关系——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对立,私人劳动与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的对立,正是在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完成形式——货币形式中获得了和解。货币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具备以下三个特点:第一,货币以其自身的“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第二,凝结在货币中的“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第三,表现在生产货币身上的“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1](7)
这里马克思要强调的是,其他商品要想实现这三个方面的转化,只有通过转化为货币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表现或者说劳动表现为价值的过程,只有通过交换,转化为社会公认的等价物——货币,而以货币为媒介表现出来。这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的真实内涵。
我们看到,价值概念体现出的是个人对交换关系的依赖,“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8](95),并以以货币为化身的交换价值成为统治人们产品交换的支配性原则表现出来。由此,交换价值成为生产的直接对象,这意味着一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在马克思看来,使劳动表现为价值的,不是直接的生产活动,而是一个不由个体劳动者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对此,马克思指出,价值范畴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1](99)。价值范畴是人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同他们自己相异化”[8](110)的特定社会历史阶段——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而这是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当作非历史的、永恒的自然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无法看到的,即“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1](99)。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价值概念的“术语革命”通过揭示现代商品社会劳动社会化的特殊形式,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本质。
三、价值概念的存在论意涵:价值的生产过程与人受资本统治的异化状态
在马克思看来,内在于价值概念中的对立关系以及社会关系对人的统治,在商品社会尤其是产业资本主义阶段得以昭然,并以资本对人的统治的关系表现出来。产业资本主义与前产业资本主义阶段的商品社会的生产过程的关键区别在于,劳动力是否成为商品,因为劳动力这种商品拥有的使用价值能创造出比它的交换价值更多的交换价值。资本正是通过无偿占有这些多出的交换价值而实现自身的增殖的。由此,通过从一般的商品交换活动转向对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分析,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人受资本统治的异化状态的揭露和批判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资本增殖的过程,是资本作为一种强制性社会力量对人的统治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人同自身相异化,这种异化不仅表现在工人身上,也表现在资本家身上。这是将价值概念视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关的,可以还原为纯粹定量的价值量的经济范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无法察觉的存在论内涵。
首先,对于工人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实现过程是人同自身的类本质相异化的异化劳动过程,即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劳动本身不表现为对工人的类本质力量的确证,而是表现为“工人对立的、异己的、统治工人的权力”[1](659)——资本的积累。这一过程是活劳动与工人相分离的过程,是“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的倒置”[1](360)的过程,并不断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不断再生产出工人的异化条件本身。
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工人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这构成了产业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前提。劳动力对工人来说是非使用价值,它只有在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完成后转化为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才能进而转化为自身得以维持的生活资料。因而,对于工人来说,劳动这一被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确认为“人的类特性”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9](57)只有并入资本,成为资本的一种形式——可变资本时,才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在与资本发生关系之前,工人就无法进入劳动过程,工人和劳动的客观条件,以及工人彼此之间不发生关系。而一旦并入资本,工人的劳动便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控制生产过程的“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
价值的生产过程体现了工人对资本的隶属关系。这不仅意味着工人对象化劳动的直接结果——凝结为商品的价值不为工人所有,不能确证工人自身的力量,而是表现为工人以外的他人——资本家的力量的积累和强大。同时由于产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机器大生产特征,劳动资料转化为机器体系,作为过去了的、积累下来的对象化劳动,“对象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的形式或者以当作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10](186)这意味着,价值实现过程中由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带来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也不再表现为活劳动自身的发展和积累,而是表现为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的属性”。[10](186−187)因而,劳动资料一旦转化为固定资本,便同时产生了劳动资料作为资本同工人对立的形式。知识、技能的积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动”[10](187)。由此,“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10](187)而工人的活劳动上升为社会劳动的过程,即价值的生产过程“表现为单个劳动在资本所代表、所集中的共同性面前被贬低到无能为力的地步”[10](191)。工人的活劳动被贬低为体力劳动,贬低为转移和创造价值的“生产工具”和“活的机器”。
我们看到,在作为同一个过程的价值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增殖过程中,对象化劳动不再表现为人的类本质的实现,而是表现为“劳动的外化过程”,在资本的角度来看是表现为资本对社会劳动的占有过程。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价值生产过程的现实,是资本增殖的奥秘。包括工人个人的消费,也不过是用于工人再生产自身即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的资本增殖过程中的一个要素。我们知道,劳动力的平均价格是工人能够维持其生活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工资。也就是说,在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中,工人所占有的仅仅是勉强维持其生命再生产的极小部分。工人始终处于G-W-G(商品−货币−商品)的商品流通的循环中,而其余的价值则被资本家占有。工人是价值的“人身源泉”,但这些价值不断地以与工人相对立、控制工人的权力被生产出来。工人“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1](658)。构成价值的异化劳动使劳动仅仅变成维持工人自身生存的手段。
而资本家作为价值的占有者,则处在G-W-G`(货币-商品-增殖了的货币)的资本增殖的循环中。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同一个价值生产过程及再生产过程的结果就是不断再生产着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的工人与活劳动的分离,从而造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永久化。我们看到,通过对价值的生产过程的考察,马克思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实现方式是一种从结构上剥夺了人的类本质的自我实现的可能途径的特殊劳动形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9](59)因而,工人同自身的异化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现实地表现出来。由此,“异化不是作为一种哲学或人类学状态被感知到,而是作为一种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被感知到。”[7](300)价值的生产过程泄露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奥秘。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的对象化,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劳动者生活的手段。
其次,人受资本统治从而人同自身相异化的状况也体现在资本家身上。一方面,资本家对其他人的劳动、劳动过程、劳动产品的实际作用都漠不关心。生产过程的一切具体感性特殊形式只有被抽象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价值一般”才有意义。资本家只在乎一件事,即这一生产过程的结果——商品能否转化为货币,即将价值实现出来。资本家把他人的劳动仅仅当作手段,价值增殖的手段。在资本控制下的生产过程中,生产过程中的各种不同要素——生产工具、原材料、劳动力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结合起来——价值的增殖。对于生产要素的购买者资本家来说,他购买的是这些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但这个使用价值不是用来为资本家个人生活所需而消耗从而退出流通过程的,而是作为保存并创造价值的可能性力量成为价值增值的工具的。这里,资本家与劳动、产品以及他人的关系,都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劳动、产品以及他人的关系截然不同。
由此,生产的目的不是人类的自我实现,不是为着共同体的使用价值的需要,而仅仅作为与其具体形式毫不相干的创造价值的纯粹抽象活动而存在。正如美国学者麦卡锡所指出的,“生产之所以持续不断,这不是为了共同体成员的普遍善,不是为了实现使用价值,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7](306)生产过程是否发生,不是取决于资本家的个人喜好或是共同体的需要,而是取决于“价值一般”能否实现。若是不能,那么,生产将会停止。我们看到,马克思将“价值一般”视为一种“社会劳动形式”。价值概念的重点落到了对限制、扭曲人类自我实现的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揭示和批判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存在论批判和指控。
另一方面,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增殖运动机制的“主动轮”而已。作为消费者,资本家有能力购买比工人更多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和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11](44)然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1](683)竞争作为资本的概念中内在包含的东西,强制资本家只有保证资本的增殖才能维持住其地位,竞争使得资本家不得不尽可能多地将积累下的价值重新投入资本得以增殖的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否则,他将在竞争中被淘汰,剥夺作为资本的代理人的资格。因而,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器。”[1](687)
综上所述,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的价值概念超越了“价值唯实论”和“价值唯名论”相争的地平,使价值概念成为“对刻画了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社会和劳动关系的表达”[7](295),构成了价值概念的“术语革命”。在马克思看来,价值的生产过程表现为“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2]。可以说,《资本论》价值概念的“术语革命”代表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的综合,并直指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提出的价值关怀,即消灭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将其还给人本身。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2] 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11: 1.
[3] 广松涉. 资本论的哲学[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4] 马克思.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册[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
[5] 柄谷行人. 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163−164.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7] 麦卡锡. 马克思与古人: 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9]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87.
The meaning r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value in Das capital: the ontology meaning of economic category
SUN Hui
(School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In Das capital and its manuscript, Marx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value of goods as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for hi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His concept of Value has different connotations from the bourgeois economists. In the latter view, Value concept is a pure economic category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apit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First of all, Marx criticizes Ricardo’s “realism” and Bailey’s “nominalism”, and explores the nature and connotation of Value, achieving “meaning r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value. Secondly, believing that the concept of value is a “historic” category, Marx reveals and criticizes the metaphysical nature of the bourgeois political economics by revealing the special way that labor obtains from the society in modern commercial society. Third, Marx regards the concept of value as the embodiment of capit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disclosing and criticizing the alienation of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Value production under the rule of capital. These constitute the deep existential meaning of the concept of value in Das capital.
Das capital; the concept of value; the meaning revolution; the ontology meaning of economic category
A811
A
1672-3104(2015)03−0022−06
[编辑: 颜关明]
2014−08−27;
2015−04−1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资本论》与当代社会发展道路研究”(14JJD720003);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卡西尔的文化形而上学思想研究”(2014BS010)
孙慧(1986−),女,吉林敦化人,哲学博士,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