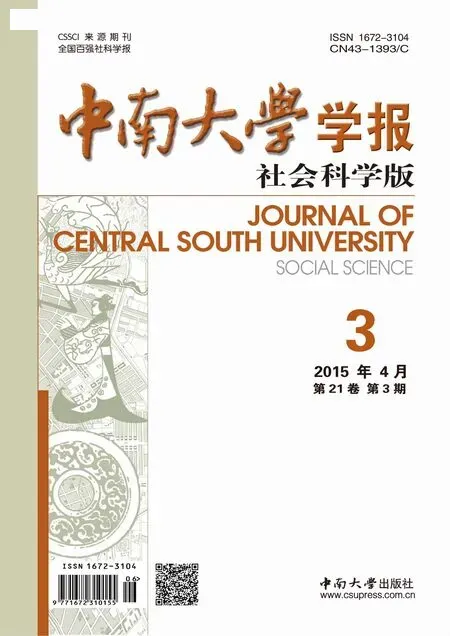“冲突”还是“融合”:马克思的国家起源论探析
姜正君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湖南长沙,410006)
“冲突”还是“融合”:马克思的国家起源论探析
姜正君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湖南长沙,410006)
马克思从哲学、历史和政治三个维度对国家的起源进行全面考察,既探讨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内部因素对国家起源的决定作用,也分析了自然环境、社会意识等外部因素对国家起源的重要影响。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既是社会分工、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公共权力分化的产物,是社会内部和外部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与其说马克思的国家起源观是典型的“冲突论”,还不如说它是“冲突论”和“融合论”的统一。
马克思;国家起源;冲突;融合
国家的起源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千百年来,它一直是政治哲学家关注的话题。从亚里斯多德、阿奎那、马基雅维利,至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弗格森,再到孔德、摩尔根、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对此都有过经典性的系统论述。霍尔(John Hall)和艾肯伯雷(John Ikenbury)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国家起源论分为两派:“合作论”“冲突论”①。乔纳森· 哈斯(Jonahan Haas)则将其概括为三派:“融合论”“冲突论”和“折衷论”②。尽管哈斯和霍尔等人的观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为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是典型的“冲突论”。将马克思的国家起源论贴上“冲突论”的标签,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意愿,能否体现马克思的理论创新?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国家问题是唯物史观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唯物史观必须回答:国家作为人类社会这一最为重要的政治组织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正因如此,马克思非常重视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一生倾注大量精力,从哲学、历史和政治三个维度对国家的起源进行了系统考察。
一、市民社会:国家起源的哲学考察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曾经先后盛行过三种国家观:古希腊城邦国家观、中世纪神权国家观和近代契约国家观,它们分别运用人的需要、神的意志和自然法来解释国家的起源。与此不同,马克思则将国家根植于社会经济关系之中,从市民社会出发考察国家的起源,揭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起源论的序幕。
马克思最早探讨“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1](88)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重要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既直接得益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也受到了德国政治哲学传统的影响。比如,费希特就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他说:“我们已经证明,国家本身是靠社会才存在的。国家本身应向社会表示自己应有的感谢;我们即使没有国家作中介,也会对社会心满意足的。”[2]不过,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特殊利益冲突的舞台,而国家是“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它相对于社会更具有本原的意义,只有国家的普遍性方能救济市民社会的特殊性缺陷。虽然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上,黑格尔用抽象概念的逻辑关系取代了客观真实的历史联系,提出了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结论,“可是,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也是市民社会唯物主义的完成”[3](442),黑格尔又暗中指出了唯物主义的方向,“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4](42)
马克思最初信奉的是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但《莱茵报》的斗争经历使他对原有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斋以后,马克思以《莱茵报》时期的实践经验和《克罗茨纳赫笔记》时期的历史学知识为基础,对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观进行批判,将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再次颠倒过来,恢复了费希特的基本论断,从而实现了对黑格尔国家观的超越。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它们才是原动力”。[3](250−251)简言之,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既是对国家神秘主义历史观的祛魅——将国家拉下神坛,也是考察国家起源问题的方法论变革——从思辨的天国转向现实的世界。这意味着考察人类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但市民社会的谜底又不在社会之中,而应在经济关系之中去寻找。正如马克思后来回忆指出的,“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32)
马克思主张从市民社会出发考察国家的起源,实际上是坚持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世界特别是经济关系之中去寻求答案。因为市民社会主要指一切生产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总和。如果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还缺乏政治经济学解剖,对传统国家起源论的批判主要是一种哲学思辨式的,那么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则真正将国家起源的思考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并从经济基础来考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明确地提出考察国家起源问题的方法和立场——祛除“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马克思指出:
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1](71)
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马克思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历史前提,也赋予了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基础的内涵。他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87−88)“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131)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内涵的界定,意味着考察国家的起源和形成应从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特别是经济利益关系中去寻找答案。
马克思将国家的起源和形成置于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奠定了社会本体论的哲学原则,为解释国家的起源指明了科学方向。国家看起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它实际上是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才出现的产儿和赘瘤。正如恩格斯后来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5](170)20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对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提出了几种影响较大的早期国家起源理论。其主要有两类:一是从动力来考察国家起源,如威特福格尔(Witffogel)的“灌溉说”、卡内罗(Carneiro)的“战争说”、哈纳(Harner)和杜蒙德(Dumond)的“人口压力说”、拉恩杰和赖特的“贸易说”、阿诺德(Arnold)的“再分配说”、科(Coe)的“宗教说”和亚当斯(Adams)的“综合变量互动说”。二是从演进过程来考察国家起源,如柴尔德(Childe)和斯图尔特(Steward)的社会政治演变模式、塞维斯(Service)的“酋邦”模式和弗里德(Fried)的“分层社会”模式[6]。纵观欧美学术界对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考察,尽管其着眼点不同,但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沿着马克思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前进,遵循和贯彻了马克思所提出的考察国家起源的基本原则,即从社会存在本身去探讨国家的起源。
二、“分工”与“所有制”:国家起源的历史考察
如果说马克思早期主要是运用哲学思辨的原则,从市民社会出发考察国家的起源,那么他后来则是继续沿着这一正确方向运用历史实证的方法,从社会生活出发深入探讨国家的起源。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表现为两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80)由此,马克思对国家起源问题的考察从两个向度展开:一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侧重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考察;二是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侧重从生产关系的形态来考察[7]。前者表现为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后者表现为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
(一)“分工”:国家起源的生产力考察
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会出现分工。分工是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和人口的增多发展起来的。“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1](82)分工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三次大分工,即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从狩猎、采摘者中的分离;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商人阶层的出现。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1](68)国家的产生与人类社会第一次大分工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1](104)。伴随社会大分工的发展,每个劳动部门都出现更加细致的分工,由此产生各种具体的职业。随着社会职业的分化,个体家庭也逐渐发展起来了。“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1](83),个体家庭使得财产保留在家庭之中,私有制便产生了。
马克思晚年在《人类学笔记》中再次研究分工表明:伴随着两次社会分工的出现,社会分化逐渐加剧,从而产生了私有制。在考察雅典国家的形成时,马克思认为,提修斯改革把人民不问氏族如何而按照职业将其划为三个阶级: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这在社会大分工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分化。在分析原始公社解体的原因时,马克思指出,“份地的不平等已经很大,这种不平等必然逐渐地造成财富、要求等等方面的各种不平等,简言之,即造成各种社会的不平等,因而产生争执,——这就必然使事实上享有了特权的人极力确保自己作为所有者的地位。”[8](41)这就是说财产多寡导致了社会分化和对抗,“同一氏族中的财产差别使氏族成员的利益的共同性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对抗性。”[9](522)马克思认为,在雅典国家形成过程中,梭伦改革实质上是以立法形态确认了基于财产关系的阶级区分,他“重新提出了提修斯把社会分成几个阶级的计划,但这一次不是按职业划分,而是按财产的多寡划分;他按财产的数量把人民分为四个阶级”[8](313)。由此可见,以分工为基础的私有财产成为氏族公社瓦解并向政治社会过渡的根本内推力。
作为生产力进步标志的劳动分工,孕育了一切社会分化和利益矛盾的根源,“因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1](83)也就是说,分工催生了职业分化、个体家庭、私有制、阶级以及利益冲突。马克思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84)通过分工研究,马克思揭示了国家起源的私有制根源和国家的阶级实质。他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84)马克思还强调,“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1](85)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国家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生产和社会分工发展所导致的利益矛盾冲突。后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将这一观点表述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5](174)
(二)“所有制”:国家起源的生产关系考察
和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所有制。“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1](68)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考察了三种所有制形式。
第一种是部落所有制。“它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牲畜,或者最多靠耕作为生……由此,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部落首领,他们管辖的部落成员,最后是奴隶。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1](68−69)可见,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是“家庭的扩大”,这表明他在分析早期社会政治结构的演化时非常重视家庭血缘关系。马克思认为奴隶制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发展起来的,这表明他在探讨国家的起源时考察了内外多重因素,并未将私有制和阶级斗争视为唯一动因。
第二种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1](69)这一阶段的分工已经比较发达,除公社所有制以外,动产私有制以及后来的不动产私有制已经发展起来。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整个社会结构出现了变化:“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城市内部存在着工业和海外贸易之间的对立”,“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1](69)可见,马克思认为公社所有制是通过“契约或征服”而产生的,私有制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对立和分裂。这表明马克思在考察政治结构的形成和变化时,既重视私有制所导致的阶级对立等内部因素的作用,也注意到了战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第三种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Gemeinwesen)为基础的。”[1](70)马克思认为,它的形成和国家所有制一样,也是基于阶级的对立。“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与古典古代的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这种封建结构同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一样,是一种联合,其目的在于对付被统治的生产者阶级;只是联合的形式和对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有所不同”。[1](70)
不难发现,马克思所说的部落所有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个独立形态,实际上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即国家的起源时期。后来,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用“部落共同体”和“原始共同体”代替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表述史前时代的“部落所有制”。在马克思看来,“部落共同体”是人类历史的原始状态,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其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从社会关系来看,家庭是“部落共同体”的基础,而共同体又是由血缘、语言和习惯等要素联系起来的。其次,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10](472)。再次,这个社会中的基本生产方式是“游牧”。马克思认为,原始共同体社会进一步发展就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处于原生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是原始部落更为动荡的历史生活、各种遭遇以及变化的产物。”[10](474)公社所有制解体之后,人类社会就进入了国家社会。可见,马克思发现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演进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即公社所有制时代。
马克思晚年深入分析了公社所有制的三种形式:“亚细亚的所有制”“古代的所有制”和“日耳曼的所有制”。亚细亚的所有制的特征是公社“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组成部分”[10](474)。古代的所有制的特征是以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和作为共同体的公社互为存在的前提。日尔曼所有制的特征是公社共同体不以实体形式存在,只存在集会及其“战争、举行宗教典礼、解决诉讼”等其他共同活动之中,公社成员对共同体的依赖小。那么,这三种不同的土地所有制是如何形成的?马克思认为,“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的天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以所有者的资格对待土地,就是说,用劳动来获取土地的果实;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受物理条件决定的土壤开发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引起迁移、引起历史事件等等的变动。”[10](484)可见,马克思在考察公社所有制解体即国家起源时注意到了各种因素:自然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内部人口增长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外部影响等。
公社所有制并非最原生态的社会形式,只是原始社会向私有制阶级社会过渡的形式。马克思指出,“奴隶制、农奴制等等总是派生的形式,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尽管它们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和以共同体下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当然的结果。”[10](496)那么,公社所有制是如何解体并向派生形式转变的呢?马克思晚年在人类学笔记中分析了“公社和以公社为基础的所有制解体的原因”[10](493)。
第一,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移民和战争破坏了氏族社会结构。马克思指出,“在每一个人均应占有若干亩土地的地方,人口的增长就给这样做造成了障碍。要想消除这种障碍,就得实行移民,要实行移民就必须进行征服战争。结果就会有奴隶等等。”[10](494)第二,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经济的发展“破坏共同体的旧有的经济条件”。马克思指出,“在农村居民中发展起来的向城市工商业中心的移民,——这种移民破坏了人民与土地的先前联系,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氏族原则的瓦解以及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解体。”[8](41)第三,劳动者的变化破坏了旧的经济条件。马克思指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仅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这种发展使得那种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因而也成为每一个客观的个人的基础的生产方式发生解体。”[10](494−495)第四,交往的扩大瓦解了氏族社会的基础。马克思指出,“移住、航海和各种与商业有关的人员流动——所有这些,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都无法容纳了。”[8](316)由上可见,马克思在考察氏族解体和国家起源时,既重视“经济发展”“贸易”等生产力因素的作用,也重视“交往的扩大”等生产关系因素和“人口迁移”“战争”等社会关系因素的影响。因此,相比20世纪盛行的“战争说”“贸易说”“灌溉说”“人口压力说”等理论强调某个单一社会变量是国家起源的动因,马克思的国家起源论要深刻和丰富得多。
通过考察马克思的“分工”和“所有制”思想,可以发现他的国家起源思想有两条思维链:一是社会分工→剩余产品→私有制→阶级→阶级斗争→国家;二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前者主要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为立足点,后者主要以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次序为视角。这两条主线说明国家起源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分工、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以及社会其他因素都密切相关,国家的产生是社会生产中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生产中的经济因素,无疑是阶级产生和国家起源最为革命性的动因。马克思指出:“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正如它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一样,一当社会达到迄今尚未达到的阶段,它也会自动消失。……阶级利益等等……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种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9](646−647)
三、公共权力:国家起源的政治考察
马克思早期对国家起源的考察主要是基于他对欧洲社会历史的认识。19世纪50年代后,马克思把理论视野从西方延伸到东方,构建起了独具特色的东方社会理论。这一时期,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亚洲式的社会”概念,并将其与“西方式的社会”相区别。通过对印度等东方国家的考察,马克思发现,东方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国家的政治统治以执行社会职能为基础,政府担当着社会许多公共管理职能——“修建和管理公共水利工程、交通道路的任务”。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指出:“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辽阔,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1](762)马克思通过英国人的无知证明了东方社会公共职能的重要性:“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和战争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听之任之原则——行事的农业便衰败下来。”[1](763)在马克思看来,水利灌溉的社会管理职能可以说明国家的衰败和文明的消失,即“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1](763)。
马克思对亚洲国家“公共公程的职能”的分析,表明他看到了公共权力所具有的社会管理职能在东方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换言之,东方专制国家并非完全建基于阶级利益的冲突,而是与生产活动和社会分散的特征有关。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11]。东方社会为什么没有土地私有制?通过考察地理水文对亚洲国家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形成东方社会的重要条件是人工灌溉的需要和交往水平的低下。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他指出:“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通过农业和制造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中心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1](764)
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无论是在土地所有制还是社会结构方面同西欧社会都具有极大不同,因而其政治国家的产生和运行方式也有极大特殊性。一句话,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的规律性,并不排斥各个民族的各个阶段发展的各自特殊性。因此,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实际蕴含了国家起源的多维性观点。但是,在肯定国家起源的多维性时,马克思又强调了一元性。他指出:“他们的国家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宗教的发源地,从他们的札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从他们的婆罗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希腊人的原型。”[1](772)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东方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并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这也意味着魏特夫用东方社会的水利灌溉来解释东方专制主义的产生,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国家起源论。
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公共权力的分化无疑起了重要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组织中公共事务不断增加,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公共权力机构逐渐开始分化。在谈到氏族组织的对外军事职能的分化时,马克思指出,“随着部落联盟的产生,……必须有一位指挥联合部队行动的总司令。设立这一职位,……这是军事权力与民政权力分离的开始,随着这种分离的完成,就根本改变了管理机关的外貌。……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机关的职能就分配在这两种权力之间了。这个新职位是最高行政长官的萌芽;由最高军事首长演变为国王等等。”[8](247)在谈到氏族组织的对内管理职能的转变时,马克思指出:“公社-氏族团体和农村团体被用之于行政和司法的目的。……中央行政机关将警察职权和司法职权,即治安的责任,委托给他们。这就意味着这些氏族和公社已经由与执行这些职能无关的独立的机关变为国家的最下级的警察和保安机关了。”[8](42)在考察氏族组织的宗教事务管理职能时,马克思认为,神权促进王权,宗教崇拜巩固人的崇拜,宗教因素在国家起源中发挥了纽带作用:“在去世者的灵魂与神之间、神与在世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因为有很多祭司和老首领都被认为是圣者,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也会为自己要求神权。”[8](536)可见,马克思在考察氏族组织的社会管理职能时,注意到宗教等精神动力因素在国家起源中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认为萨满巫术在中国国家起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批评马克思无视巫术、原始宗教等因素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12]。显然,张光直不仅片面夸大了“巫”的作用,而且对马克思国家起源论的指责也是有失偏颇的。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管理职能对于国家的存在具有前提性意义,国家是公共权力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过程中分化而产生的。后来,恩格斯多次反复强调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恩格斯指出:“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13]在批判杜林的暴力论时,恩格斯指出,“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3](522−523)可见,恩格斯也认为,国家是公共权力组织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中逐渐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与社会相脱离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5](170)因此,“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5](116)正在此意义上,列宁也认为“国家正是这种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14]。
四、小结
综上所述,马克思从哲学、历史和政治三个维度对国家起源进行全面考察,既探讨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内部因素对国家起源的决定作用,也分析了自然环境、社会意识等外部因素对国家起源的重要影响。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既是社会分工、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公共权力分化的产物,是社会内部和外部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显然,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论思想异常丰富,是不能用简单的“冲突论”加以概括的。把马克思的国家起源论贴上“冲突论”的标签,是一种大而化之、简单粗暴的做法,这不仅不能全面体现马克思在国家起源问题上的理论创新,甚至于一定意义上背离和曲解了马克思的国家起源论。我们与其说马克思的国家起源观是典型的“冲突论”,还不如说它是“冲突论”和“融合论”的统一。新时期,澄清马克思国家起源论的真相,对于我们今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正确履行国家的政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 “合作论”认为国家是为了满足共同的需要而创立的一种机构;“冲突论”又分为“内部冲突论”和“外部冲突论”,“内部冲突论”认为国家是社会内部阶级冲突的产物,“外部冲突论”则认为国家是军事征服与战争的结果。参见霍尔、艾肯伯雷:《国家》,施雪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② “融合论”认为国家是作为协调和管理复杂社会各个部分的融合机构而发展起来的;“冲突论”认为国家最初是作为解决社会内部经济分层引起冲突的强制性结构而发展起来的;“折衷论”是将融合论和冲突论调和的国家起源理论。参见[美]哈斯:《史前国家的演进》,罗林平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8-43页。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 费希特. 费希特著作选集·第1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281.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 陈淳. 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问题[J]. 东南文化,2002(3): 6−15
[7] 刘军. 国家起源新论[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38.
[8]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256.
[12] 张光直. 美术、神话与祭祀[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109−110.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12.
[14]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8.
“Conflict” or “fusion”: on Marx’s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JIANG Zhengjun
(Section of Philosophy Teaching, Party School of Hu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Changsha 410006, China)
Marx mad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from three dimensions: philosophy, history and politics, discussing not only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productivity,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other internal factors, but also 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other external factors on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In Marx’s view, the state is the products of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class struggle, of the social public power differentiation, and of the combining forc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refore, rather than a typical “conflict theory,” Marx’s the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is the unity of “conflict theory” and “fusion theory.”
Marx; the origin of state; conflict; fusion
B035
A
1672-3104(2015)03−0028−07
[编辑: 颜关明]
2014−07−10;
2015−04−09
2014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研究”(14CKS002);2013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国家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3YBA207)
姜正君(1979−),男,湖南常德人,哲学博士,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哲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