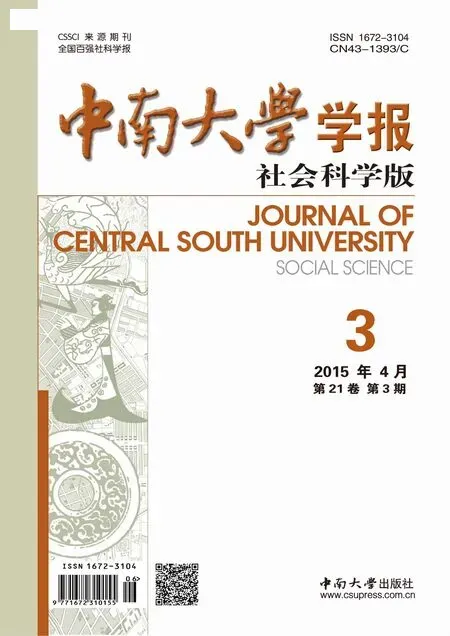“性别操演”中的身体问题
张兵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性别操演”中的身体问题
张兵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把“性别操演”理论中的“操演”误作“表演”,在于预置了一个自为的、自然的身体观。相反,“操演”体现的是建构的身体观,“操演”不是作为行为者的身体的自主择装,而是性别霸权话语在话语“再意指”中的重复性规训,其效应体现为与规范话语相符合的一系列身体风格。与建构的身体观相应,并不存在一个前话语的自然式身体,但巴特勒赋予“性别操演”中所具有的建构的能动性问题使其又不得不重新面对身体的物质性议题,即建构的能动性不在于德里达式“再意指”中的必然“变异”,而在于被否定同时又被保留在身体中的欲望的回返冲动;这一对欲望身体的援引,构成了巴特勒对自然身体观的悬置态度的再否定。由此,有关“性别操演”的诸多争议又以另一种形式延递到巴特勒对身体的解释中,这促使我们应重新思考身体的物质性及与此相关的“活现的身体”观的含义。
性别操演;被建构的身体;被排除的身体;朱迪斯·巴特勒;性别理论
“酷儿”(Queer)或许是朱迪斯·巴特勒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标签,这一称号与巴特勒积极批判异性恋性别规范霸权的性别政治实践相应。但事实上,“酷儿批判”只是巴氏颠覆性别身份、超越性别话语界限的一个例子,作为凝聚这一颠覆逻辑的“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才应被视作巴特勒性别理论的核心词。借用拉康常玩的拓扑学戏法,也可以把“性别操演”比作巴特勒理论迷宫的“莫比乌斯带”——围绕着问题域不断地绕来绕去而没有明确的结点,就像赫拉克利特“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D60》)的谜语式格言——对性别的规训与对性别的颠覆是同一个平面而不是内外有别的两面。这也是性别操演惹人争议并经常遭到误解的原因。这一误解与争议关乎人们对性别操演内涵的理解,巴特勒本人也从多个方面给予澄清和回应。前述无论是误解还是争议,都与某种对身体的理解有关,巴氏本人的性别操演概念亦建基于一种身体观之上,其对该概念的辩护性阐释同样反映在对身体概念理解的运动中。因此,本文试图从身体出发,探讨在这种对身体的多重理解中,巴氏本人的身体图式是否解决了性别操演所遭到的质疑?或者这一质疑所指涉的疑难又以另一种形式延递到巴氏对身体的解释中?
一、对“性别操演”的误解
对“性别操演”的误解与争议自该词提出后从未止息,这一误解或争议甚至也反映在对该词的汉语翻译中①。最常见的误解是将“操演”理解为“表演”,即一个“真人”在舞台上穿上特定的服饰扮演特定的角色。扮演何种角色以及扮演得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扮演者的个人努力。对“性别操演”就理解为,性别身份的获得就像随当天心情喜好选择心仪的性别面具一样,戴上某种面具就“过上”了某种性别生活。于是,性别操演就是一场略带神秘的面具走秀,其所蕴含的自由维度源自面具自身的魔力之中,但这一魔力最终是由戴着面具的人所拥有的表演技巧施予的,就像川剧中的“变脸”高手。
不仅仅川剧中“变脸”可看作一个魔力游戏,今天,我们也可以将一个难度极大的整形手术看作一个魔力游戏。许多整形医院不就在劝诱女人们换一张脸吗?如果有足够的金钱来保证,会有足够多的女性去做这些手术,“就算她们持续蒙受有损健康的手术副作用;即使在某些案例中,手术反而恶化了女性起初所认知到的问题(如隆胸手术并发症),这些女性仍感到更坚强、更快乐,且更能掌握她们的人生,因为她们试图对自我给予一个十分重要的改变,不论这项尝试是否成功。”[1]在这里,对自我的肯定是与对“脸”的欣赏紧紧连在一起的。也许我们更应该注意到,“换脸”并非都如舞台和医院大型手术中表现得那么惊心动魄,几乎每一个女性都在装扮她的脸,乃至不用别人提醒她们总是“戴着她们的脸”②。洗面奶、洗涤液、收敛剂、收缩剂、化妆品去除剂、早霜、晚霜、营养霜、眼霜、保湿液、皮肤均衡液、防晒油、遮光剂、面膜等等,在乐此不疲的分类保健运动中,女性找到了生活的自信与自主。
将性别操演所具有的自由品质归结于女性身体的自主运动,这是一个误解。这一误解可以从两个层次分析:①女性的自我形象建构表面看起来是随心所欲的,实则相反。问题在于,女性自主选择的某些形象,其实是按照男性期望设计出来的“形象帝国”的一部分。考虑到福柯式“全景敞视主义”空间理论,女性在形象选择上所获得的乐趣源自于男性的“无人称的看”,“看”的“欣赏”义代替了“监管”义,女性在这个欣赏空间中将外在监管内化为个体的自主行为。以巴特勒所关注的性别身份而言,女性兴致勃勃的挑选强化了异性恋中女性的性别角色,那些各种各样维护形象的设施与举措,只是一系列持续的施加于身体上的性别化格式,是权力运作的规训技术。②更进一步,不仅化妆的效果是男性话语系统早早提供好了的,而且,那个自主的个体,也是由形象实践生产出来的而非其源头,“性别是操演的这一观点,试图表明我们所以为的性别的内在本质,是通过一系列持续的施加于身体上的性别化风格之行为而生产出来的”[2](xv),这些身体行为并不是由一个性别主体发出,反而是这些身体行为构筑并巩固了这一性别主体。
因此,从身体的角度看,性别操演确与一系列的身体行为有关,通过一系列的身体样式体现某种性别。但操演绝不是身体的自主行为,不是由那种能感觉、知痛痒并有趋利避害式抉择的身体所承担的一系列行为,其原因恰在于“身以体之”的自然化的身体观是与一种自主的、自我统一的主体观相依偎。对于操演来说,性别身份不是源自身体之所是,而是由施加于身体之上的东西所赋予的,是“体之于身”的结果。简单地说,操演根本区别于表演的地方在于,表演中所预置的自主的身体,在操演中恰恰是通过一系列的性别化身体行为建构出来的。
二、“变成”逻辑中祛自然化的身体
从女性主义运动的路线图上看,性别问题的争论经历了一个由生理本质主义到社会建构论的迁变。作为后女性主义的代表,巴特勒坚持操演是社会建构论的而非表演所喻示的生理本质论。在生理本质主义者看来,性别就是对生理状态的忠实表达,弗洛伊德基于身体解剖学基础上的文化阐释看起来“很自然地”描述了男/女二元价值结构,其中女性保持了她“不幸”的头衔。波伏娃“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变成(become)的”开启了女性对“生理即命运”的偏离运动。在巴特勒看来,这句名言潜在地表达了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的不一致,“因为我们所变成的不是我们所已是的,社会性别从生理性别中被驱逐出来;关于性别特征的文化释阐不同于事实或那些特征的单纯存在。”[3](23)但是“become”这个词在波伏娃那里存在着模棱两可之处,即这个“变成”是身体有目的地、自觉地承当还是作为一个接受文化铭刻的场所。这一暖昧或许与萨特在身体观点上的复杂性有关,为了克服笛卡尔灵魂/身体的二元对立,萨特试图将人格统一性的空洞的或超验的特征具身化,即将意识具身化。一方面,身体是世界中之一物,是被超越的东西,另一方面,身体又是超越的出发点,是对诸可感知事物的自为的直接在场,“在一个意义下,身体就是我直接所是的;在另一个意义下我与它之间隔着世界的无限度,它通过从世界向我的人为性的倒流向我表现出来并且这永恒倒流的条件是永恒的超越。”[4](403)对于萨特来说,生存的筹划既在身体之中又在身体之外,“但波伏娃理论中的紧张不在于是‘在身体之中’还是‘在身体之外’,而是在于从自然的身体到受文化同化的身体的位移”[3](25)。通过对威蒂格、福柯著作的阅读,巴特勒采取了彻底的建构论立场,去除了波伏娃躲躲闪闪的生理性别的小尾巴,坚称身体是文化诠释的场所,“身体的物质性早已被置于并被限定于社会情境之中”[3](28)。因此,对身体的思考应聚焦于身体的物质性是如何意指某些特定的文化观念,而不是将身体的物质性置于前语话、前文化的地位。
如上所述,在巴特勒关于波伏娃身体观的分析中,一个基本区分是“已是”(Being)和“变成”(becoming)的区分。这一区分同样是两种主体观的区分,这早已出现在巴特勒对黑格尔Geist(精神)的法国式阅读中。其中,巴特勒强化了对福柯所倡导的身体微观史研究的兴趣,而遗憾于福柯对“复杂历史情境中具体的身体”之分析的疏忽[5](237)。在巴特勒看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为主体是一个过程主体(subject-in-process),是在其游历的整个体系中获得其绝对性、真理性,即只有通过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阶段,绝对精神才能回复到自身而成为一个统一体,获得其绝对性和确定性。这个最终回复到自身、具有自我统一性的“旅行者”在20世纪的法国哲学中变成了一个无法预测下一个时刻情态的“冒险者”。巴特勒重构了这个转化的过程,将其概括为三次迭加运动。第一个时刻来自于科耶夫通过欲望逻辑对黑格尔统一体式主体的拒绝,黑格尔的“扬弃”应被理解为欲望之耗费,是“对他人欲望的欲望”[5](43),而不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收敛综合。第二个冲击波来自于伊波利特、萨特从无目的性和肉体边界对主体的说明,即不把绝对性理解为黑格尔体系的终结,而是理解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开放性,主体化就是一个没有终极目的牵引的无限运动过程,“如果绝对性是无限性,欲望是一个‘绝对的冲动’,那么欲望就不再以‘满足’为努力目标,而是努力将其自身维持为欲望”[5](88)。第三波则彻底将主体打碎并离散,代表观点分别是拉康“分裂的主体”、德里达“错置的主体”乃至福柯的“主体之死”。由以上三个递进阶段的分疏,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系统给巴特勒的教益在于,主体,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统一性,而是一个自我驱逐、持续焦虑的主体,进而言之,主体只是一个精神之运动无限可能性的虚构,一个只能从其所游历过的东西来确认自身身份的浪漫游行者。
借助欲望辩证法,“主体变成论”与身体的祛自然化,构成了巴特勒对黑格尔“主体”观强力阅读的成果,即主体和生理—物理的身体都不是性别“操演”的原因,而恰恰是“操演”的效果,如其所引用的尼采的话,“在所作所为、施行、生成的背后并没有‘存在者’;‘行为者’仅仅是附加到行为之上的一个虚构——行为就是一切”[2](33),主体与自然化的身体以及自然化的性别都是为着某种目的建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操演”,“性别化的身体是操演性的,这表示除了构成它的真实的那些各种行动之外,性别化的身体没有存在论的身份”[2](173),即那表现在外的一招一式之身体风格就是那个人本身,就是那个人的性别身份,这种理解才构成了操演内涵的一部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巴特勒肯定扮妆具有某种程度的颠覆性,即“扮妆含蓄地透露了社会性别自身的模仿性结构——及其偶然性”[2](175),这个模仿结构究其实质只是一个没有原件的仿品,表演即其本真。
上述关于身体和主体的“已在”/“变成”之区分,以及身体的祛自然化所引出的作为场所的身体观,从各个方面澄清了操演不同于表演之处,连带地解释了,巴特勒本人在特定意义上对扮妆的肯定反而会加剧对操演的误解。然而,若如巴氏以上所论,对于“操演”的新问题随之而来:如果性别不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而是一个“变成”,且不由一个先在的主体或能动的身体筹划并推动这一变成过程,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所变成的?或者说是通过何种方式我们变成了它?
三、被话语建构的主体及其身体风格
相对于先天的自然事实,性别身份是后天形成的,但绝不是在感觉经验意义上的身体的自主变化,不是以身体作为能动出发点的超越自身的运动过程,而是从外在性上言及的使之身体化或主体化。无论是德里达还是福柯,都剥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综合功能,把辩证法看作一个无休止地否定、不停息地向他者寻求而又永远得不到欲望满足的过程。在作为决定性的终极目的(telos)被抛弃之后,黑格尔式主体不再处于一个内在关系之中,也不再是一个沿着直线上升的阶段化进展,主体总是在他处,在分裂、移置中不断地认识自身又否定自身,它的一系列自身恰恰是在与“他在性”(alterity)的关系中获得维持。如萨特在讨论身体的另一面时所说,如果把“存在”(exist)用作及物动词,那就意味着“意识使它的身体存在”[4](408),身体是意识作用的效果,对于偏离了意识哲学的拉康、德里达、福柯、德勒兹等人(巴特勒更接近于这条线)来说,萨特此处的“意识”应被理解为外在性(exteriority)或他在性,其意更接近于拉康所阐释的“像语言那样被结构的无意识”。对于拉康来说,“他在性”就是“大他者的话语(disourse de l’ Autre)”;对于德里达来说,“外在性”源于符号内部的不可还原的差异性;对于福柯来说,“外在性”是权力/话语的历史堆积。
可以看出,此处对“外在性”的说明是符号学/语言学式的,借助了索绪尔的发明以及结构主义的行事风格,巴特勒也将主体形成的渊源诉诸于语言符号结构所表征的社会文化系统。“从黑格尔向符号学的转向也就将话语加诸于永远超出了内在关系框架的差异上面;所指的外在性从未能被再占用,并且语言本身成为这个最终不能抵达的外在性的否定证据。”[5](179)借用拉康的说法,所指只是能指的效果而非原因,被话语意指所建构的主体只是一个代理(agency)或者代理之代理。借助符号学,巴特勒分享了福柯、拉康等人对主体的看法,即主体之“变成”是被变成的,主体是被文化符号建构的。通过符号的意指功能来探究事物及其构成,既避免了自然物理客观主义,又避免了心理主义以及唯我论的困境。不过,符号学的引入不在于解决认识论的难题,而在于考察主体是如何被建构的,以及在建构中符号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在建构性中作为“外在性”起作用的主要是语言,把建构中的主动性归结为语言符号,在于符号的意指功能源自于符号系统内部的差异性而不是依赖于所指或符号的指涉物;强调符号的意指实践能力及建构能力,则使符号成为与权力运作一体两面的生产性的“话语”(discourse)。此外,在“操演”所具有的词源学方面,巴特勒还援引了奥斯汀述行性(performative)言语行为理论,以此说明性别主体是由话语建构而来,而不是一个预先存在并等待语言描述的静态事实。
由此,“操演”的建构性即是述行性言语建立或产生其所命名对象的话语实践。需要说明的是,操演的话语建构绝不是“个人意志运用语言的有效表达”[6](139),而是在于话语意指功能对作为“他在性”的整个规范性语话系统的重复性“征引”(cite),“不应把操演理解为一个主体将其所命名之物变成存在的行为,而是话语生产它所规定和限制的现象的可重复的力量”[6](xii)。例如异性恋的规范话语通过医生与护士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询唤为“男孩或女孩”,然后通过变形金刚或芭比娃娃、宽檐墨镜或带碎花的裙子、作为生日礼物的玩具跑车或鲜花等文化符号分类系统不断重复并稳固这一性别身份。由于主体只是一个接受文化建构、等待语言填充的空白场所,被建构的主体只能以一种具体化的样式体现于身体的表层,“通过身体的风格化产生了社会性别的效果,由此,性别效果必须被理解为一个日常方式,其中各种不同的身体姿态、动作和风格建构了一个永恒的性别化自我这一幻识。”[2](179)正如《拉康文集》卷首所引布封的“风格即人”的格言,表明了人只是一个被他者形构的身体性的存在③,但这一身体样式是由语言文化按照一定的格式复现出来的。
在身体被建构的风格化呈现上,巴特勒又以其特有的强辨精神分析了福柯的“身体文化铭刻模式”中“铭刻”(inscription)的含义,借以强化其身体建构的彻底性。按巴氏的分析,“铭刻”指明了风格化身体的由来,即话语/权力通过事件将其自身刻写于身体表面之上,由此,风格化身体的表面就是一个“文本”。福柯“谱系学”对此文本的侦伺即在于追溯“身世”,在其命运载沉载浮中窥探社会运行的权力机制。但福柯的铭刻模式中却可能存在着一个身体悖谬,“尽管福柯似乎主张身体并不存在于它的文化铭刻之外,但看起来‘铭刻’这一特定的机制暗示了一个外在于身体自身的权力”,因此,无论如何理解“铭刻”,这一机制极易引出“‘建构的’或‘铭刻的’身体有一个不同于铭刻的存在论的身份,这恰恰是一个福柯想要反驳的断言”。[7]因此,被建构的身体并不意味着需要预设一个作为载体的纯质料的身体,类似一个在时间序列上承载随后的文化铭刻的“白板”,相应地,建构也不是宙斯对潘多拉式的“铭刻”,将美轮美奂的诸风格加诸于一团泥土之上(《神谱》570-584)。从巴特勒的理论立场上看,宙斯式的“铭刻”仍然是一个“掩藏”式扮妆;对于巴特勒的“操演”来说,作为质料的泥土式身体只是索绪尔意义上的混沌流,离开了话语既无法被谈论,也无法被知及。事实上,那些闪闪发光的、吸引人的身体风格、样式就是就是他/她自身,是按照性别话语规范生产出来的。
四、被排除的身体及其“复仇”
巴特勒澄清了性别操演的一系列误解,即,性别操演不是自然化身体的文化呈现,也不是话语对前话语身体的铸型,而是作为一种重复化规训实践的话语生产。这些重复化规训累积为一种身体的风格或样式,从而被建构的身体即成为一种性别身份。既然操演不是一个自主身体的择装,只是在性别规范话语(如异性恋的男权统治霸权话语)下的强制性重复—复现,“性别操演”如何承载女性性别政治斗争中自我改变的希望?性别的身体建构论立场对于暴露性别规范话语的霸权谱系及其作用机制极其有力,但对于如何摆脱性别霸权话语却罔有顾及。在建构论的身体观中,身体因其埋藏着社会文化权力的运作密码而关涉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同时,身体又是为文化符号包裹缠绕、被排除了物质性的身体,直接当下的、活的身体消失了,身体只是一个“沉默的身体”,一个缺席的在场。建构的身体观中所包含的这种难以两全可以简单地表述为:身体参与了话语的生产,但却只被视为话语生产的效果。将社会建构的身体视作对于自然主义的身体的替代方案,最终“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决定论——话语或社会决定论”[8]。波伏娃的“女人变成论”本欲为女性提供一个规划自我的机会,但在话语建构论中仍陷入一个被决定的困境。为女性存在的自由着想,巴特勒赋予性别操演的性别正义在何处?或者说,性别操演的能动性何在?
按以上对操演涵义的澄清,性别操演的能动性不能寄托于身体或自主个体身上,而应从话语系统内部的分裂中寻求。从话语运作本身来看,建构的能动性又可以表述为操演中改变已有话语意指的可能性,即话语的重新意指如何可能的问题。在巴特勒看来,规训话语内部即包含着突破决定论、违抗权力规训的力量,与福柯一味强调性别身份的社会生产不同,“巴特勒批判了性别述行的管控性作用,同时,她也将操演视作提供一个抵制这一作用的绝好机会”[9]。操演固然是在强制性规范下的重复—复现,但这一重复并不必然是一成不变的,或者说后续的重复未必只是前者的忠实再现,“征引”有可能失败。在德里达看来,这一“失败”恰恰是由于可重复性使用的语言符号超出其原初语境使用而导致的意指的增衍与发展,话语的重复性再现不再是对一个初始性权威的无穷回返,相反,“先在的权威恰恰是源自于征引当下发生的例示”,是时间序列中的“再征引”(re-cite)建构了那个初始权威,而每一个“再”都有它独特的建构力量。建构中的能动性要从那个重复再现中发生变异的可能性里去寻找,因此,操演作为规范霸权的生产性再现,一方面生产了它所命名的,另一方面,“话语的生产性能力是衍生性的,是一种文化复现或再联结,一个再意指的实践”[6](70)。在这个意义上,操演中的言辞是“易激动的”(ex-citable),按巴特勒的构词法,“易激动的”指言语总是能够超出(ex-)它所征引的(citable),“resigni-fication”(巴特勒在Exitable Speech一书中特意如此拼写“再意指”一词)中间的间隔符(break)同样标志了所意指的与原初语境和社会习俗的“破裂(break)”,如此,“操演的力量并不承继于先前的用法,而是由它与任何先前的用法的破裂而来”。[10]
但是,仅仅将操演的能动性,即话语再意指的可能性嫁接在德里达的再征引(re-cite)理论上是远远不够的。德里达“征引”的重复性是符号自身基于符号系统中不可还原的差异性中的变异和增衍,仅仅是对复现中变异可能性的形式说明,未能和具体情境中的女性及其不利的身体形象勾连起来。其次,没有任何作为权威的初始意指这一意指状况,固然在去中心化的意义上构成了对霸权话语形态的解构,提供了颠覆之后所迸现的诸多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偶然性的意义上对规范话语具有冲击力,但缺乏性别操演所特有的朝向特定方向的积极建构,或者说,使那些曾被性别规范话语所压制的女性存在在话语中建构出来。操演性建构需要一个在解构之后朝向特定方向的驱动力。由此,巴特勒不得不重新思考身体的物质性,并在身体物质性中将德里达话语形式的重复性与精神分析被压抑的欲望的重复性结合起来。
身体的物质性完全被话语符号吞噬了吗?身体纯粹是话语的吗?根据巴特勒的词源追溯,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中,物质(materia和hyle)一词并不是一个等待来自于外部意指的空白表面或白板,而是一个内在于时间变化序列、人间化的词。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质料总是统一于形式之下,强行区别“蜡”和“模板铸出来的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模板铸形”之义又体现在schema一词中,“Schema的含义为形式、形状、外形、外观、衣着、姿态、三段论的格以及语法形式”,在这个词所包含的结构中,“如果脱离其schema物质绝不能显现,那就意味着它只以特定的语法形式显现,同时还意味着其可辨识原则、个性化姿态或通常着装都无法从它们对物质的建构中分解出来”。[6](8)因此要避免存在一个作为物自身并等待知性范畴铸形的康德式身体观表述,“把身体的schema理解为因历史情境而异的权力/话语之联结,就会得出类似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犯人身体的‘物质化’”[6](8),这个加了引号的“物质化”只表明身体是权力/话语运作的身体式的具体体现,身体仍然是话语生产出来的身体。在福柯那里,话语的生产性及多样性源于权力的无所不在的匿名性,其复杂性在于摆脱了“压制者/被压制者”的简单框架,人们无法确定权力运作的边界和方向,于是,自我关怀、拯救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身体的物质性不是被话语完全建构的,身体也不必然在纯粹语语之内,巴特勒对此有两个方向上的说明:①话语能指的物质性表明物质性并不必然内在于话语。这一个方向上的说明对于巴氏的后续议论没有实质的帮助,但是却在类比意义上指示了第二个方向。②虽然身体的物质性总是以一定的样式(Schema或Style)出现,但并不意味着身体完全是被决定的,总有一些“剩余”被排除在外,但这个被排除的“外在”绝不能理解成康德自在之物意义上的外在。这个“外在”或“剩余”要通过精神分析的欲望逻辑得以说明。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自我身份的形成源自于对身体力比多之欲望的否定,但同时这个被否定的欲望又被保留在了身体之中,就像黑格尔辩证法中主人对奴隶的身体的否定,却保留为奴隶依赖身体劳动获得其主体身份的可能。但巴特勒建构身体中“被排除的”与其被理解为黑格尔思维辩证运动的“扬弃”,而毋宁说是在科耶夫和伊波利特意义上,被巴特勒放置到身体中并永远朝向“他在性”的欲望,且在拉康“真实域”意义上将被符号域的编码所排除的身体理解为一种不间断的回返冲动。需要说明的是,在拉康那里,“真实域”是指原始禁忌进入符号域的不可能,即原初创伤作为永久性缺失试图表达但永远不能依赖于能指得到表达这一状况。巴特勒不完全遵守这一规则,一如其所称引的拉康的话,“被符号域所否定的将重返于真实域”[6](139),这句话应反述为“被排除于真实域的必将重返于符号域”,即被排除的身体及其欲望必将重新回归到话语秩序中快意情仇,从而改变已有话语的意指。其中的重复性是指,被嫌恶的身体、被否定的欲望总是试图以各种形式在意识中表现出来,借助于萨特的“意识使身体存在”原则,这些在主体中所重复的“彻底排除于主体的形构之外的东西”、“威胁到主体自身的边界和一致性的东西”[6](190),又会建构出新的身体形态。因此,身体的物质性可以看作话语意指的边界及此边界的运动,在这一身体运动中人类的可理知性界域不断扩大,从而将被排除的、受歧视的收纳进来。
归根到底,“性别操演”作为女性政治斗争的策略语,其积极性源自于女性被嫌恶的、被排除的身体运动,其中被否定的欲望成为“操演”的根本驱动力,构成了身体的“复仇”。总之,性别规训重复性中的变异在于被否定同时又被身体保留的欲望,建构中的能动性又被归之于肉体的能动性,这与巴特勒澄清性别操演的误解所做的说明不一致。同样以本文开头的比喻喻之,巴特勒借助身体对性别操演的说明并没有构成一个莫比乌斯带,中间发生了“断裂”,即在对将“操演”误解为“表演”的澄清中排除了自然的身体,性别操演源于语话的规训,这一规训体现为重复行为中展现的身体风格,然而打破此固定风格的重复性变异又源于“被排除的身体”的回返。虽然“被排除的身体”不完全同于自然的身体,但“被排除的身体”对身体欲望、对被伤害的感觉的强调使它仍然逸出了建构的身体观,可将之纳入到自然的、生理的身体观门类之中。因此,对巴氏“性别操演”的误解绝非空穴来风,它提示了操演所具有的能动性难题,巴氏对此难题在身体上的一系列拓展性说明,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难题,但却陷入了一个新的矛盾当中,即建构的身体(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与活现的身体(embodiment)之间的不一致。在此,梅洛·庞蒂的“我是我的身体”可能不是福柯、巴特勒建构身体观的对立面,而是一个有益的资源,或许,跳出西方文化的框架去思考身体的物质性及与此相关的“活的身体”是一个更有益的尝试。
注释:
① 目前,对于巴特勒performativity一词的中文翻译有三种:a) 表演。参见:汪民安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414-417;b) 操演。参见:宋素凤所译的巴特勒的《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的译后记(上海三联书店,2009,第198页);c) 述行或施为。参见李钧鹏所译的巴特勒的《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的文中译者注(上海三联书店,2011,第2页)。本文采用第二种译法,但原因不限于某些学者所说的,该词“依照一定的样式和姿势演练”的中文含义“恰好符合巴特勒认为性别是在强制性地重复性别规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一观点”(参见:都岚岚的“西方文论关键词:性别操演理论”,《外国文学》,2011(5):120)。福柯的管控性自体技术只体现了“性别操演”建构性中受限的一面,未能涵盖其积极生产性的一面,其生产能动性恰恰是源自强制性重复中的增补与延异。选择这一译法的另一个原因在于,performativity虽然可追溯至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但“即使是被借来的,那移植来的也只是这个词而不是这个概念”(参见:James Loxley, Performativity. p. 140),因此选用“操演”来避免上述另外两种译法以体现此词的巴氏派是比较恰当的。
② 可以把“脸”看作一个生动的转喻,既是对整个身体的指称,也是对自主个体的代称,“打人莫打脸,损人休揭短”的俚语正表明了“脸”作为整个自我人格的独特表征。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以巴特勒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来说,“脸”这一身体部位不是其身体形态学的核心,而是“菲勒斯”(phallus)。
③ 在对弗洛伊德“自我首先是一个身体的自我”与拉康的身体镜像形态学(Morphology)的比较说明中,巴特勒澄清了她所意味的“身体自我”含义,即身体自我不是一个感知觉的生物体,而是一个被文化及符号赋予形象及意义的具体性存在。
[1] Jennifer Mather Saul. Feminism: Issues & Arguments [M]. New York: Oxfam University Press, 2003: 163.
[2]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M].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9.
[3] Judith Butler. Variations on Sex and Gender: Beauvoir, Wittig, Foucault [C]// Sara Salih (ed.). The Judith Bulter Reader. Malden·Oxford·Carlt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4] 让·保罗·萨特. 存在与虚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5] Judith Butler. Subjects of desire: 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6]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Sex”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7] Judith Butler. Foucault and the paradox of bodily inscriptions [J].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89, 86(11): 601−607.
[8] Lisa Blackman. The Body: the Key Concepts [M].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2008: 28.
[9] James Loxley. Performativity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123.
[10] Judith Butler. Ex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7: 148.
The problem of bodies in gender performativity
ZHANG Bing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Performativity is easily mistaken for performance which presupposes a notion of natural and autonomous body. Conversely, performativity is related to a notion of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and can be defined as a series of reiteration of bodily acts through gender norm discourse. However, Butler has to review the materiality of body in face of the problem of agency included in performativity. Butler suggests that the agency is not dependent on what Derrida calls “the defferance in iteration” but derives from the prohibited desire preserved in the body. Unfortunately, the re-affirmation of desiring body contradicts the statement Butler has made in distinguishing performativity from performance. So to speak, the controversies over “gender performativity” are transfered in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body, which urges us to re-think the flesh of body in a new context or in a non-west one.
gender performativity; the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the excluded body; Judith Butler; gender theory
B712.6
A
1672-3104(2015)03−0015−07
[编辑: 颜关明]
2014−06−26;
2015−04−10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现象学中的‘身体’运动及其效应研究”(14BZX070);2013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中西哲学比较中的身体维度研究”(13YJC720045)
张兵(1978−),男,河南驻马店人,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哲学比较,身体现象学与当代女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