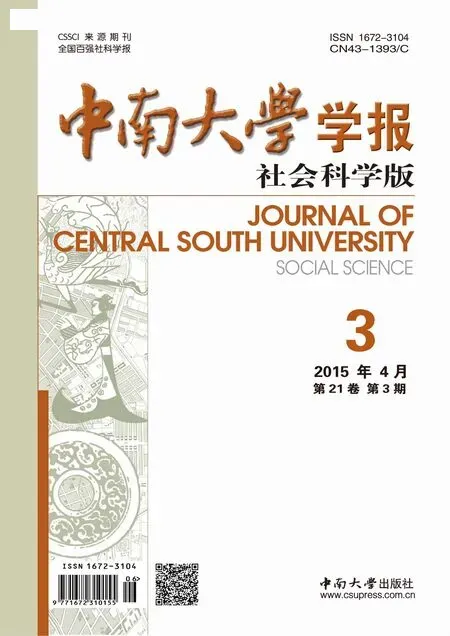论非国内规则在国际商事合同中的适用
刘益灯,陈璐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论非国内规则在国际商事合同中的适用
刘益灯,陈璐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国际商事合同适用非国内规则是国际社会合同准据法发展的重要走势。非国内规则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因其较强的实践操作性而逐渐被各国法院和仲裁机关所适用。在国际商事合同纠纷的解决中,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等非国内规则;当事人没有选择时,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适用非国内规则。但由于非国内规则本身的局限性、法院地法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强行性规范和公共秩序的限制,非国内规则在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适用中不具有普及性,因此,我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从完善非国内规则和加强立法及司法两方面入手,推动非国内规则在国际商事合同中的适用。
非国内规则;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
意思自治作为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的基本方法之一,能有效避免和解决跨国商事合同争议。2011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于总则部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出了宣示性规定,并首次将其扩大到侵权等非合同领域,但并没有明确规定跨国商事合同当事人能否选择适用非国内规则(尤其是将其作为合同准据法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律适用法》的司法解释也未涉及该问题。与美国、欧盟对此问题的密切关注不同,我国法学界有关非国内规则适用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及其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适用。在我国现有国内立法及法律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涉外商事审判实践中的具体案例,探讨非国内规则适用于国际商事合同的可能性,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非国内规则的法律界定及其适用的必要性
(一) 非国内规则的法律界定
长期以来,理论界对非国内规则的概念及内容范围一直缺乏明确的定论。尼格(Nygh)、西蒙尼德斯(Symeonides)等人将非国内规则概括为现代商人法(lex mercatoria)[1],但商人法本身便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兰多(Lando)在谈及非国内规则时也用了现代商人法(the new law merchant)等字眼,并将其渊源分为以下七类:国际公法上的条约(public international law),国际商事领域的统一示范法(uniform laws),一般法律原则(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重要的国际组织的决议、行为准则等(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未)成文的国际商事惯例(customs and usages),国际标准合同(standard form contracts),已公开的仲裁裁决(reporting of arbitral awards)。[2]即便如此详尽的概括也未能穷尽非国内规则,因为它不仅遗漏了影响甚广的伊斯兰法等宗教法,七种分类之间也非泾渭分明,各种渊源相互重叠。[3]我国《法律适用法》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可明示选择适用于其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但立法者并未明确“法律”一词的含义。国际私法的立法目的在于恰当地确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所应适用的一国法律体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一条,涉外民商事合同所应适用的法律为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实体法,并不包括冲突法与程序法。那么,“实体法”一词是否意味着排除了非国内规则的适用呢?有学者指出,此处用“实体法”并不在于强调其内容,而是与冲突法、程序法相区别,着重避免反致。[4]而有关立法理由书、草案、审议记录等资料的缺乏使得我们难以对《法律适用法》及其后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一)》)中所用“法律”一词进行法律解释,无法探究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主观意图。对于法律(law)究竟是指法律规则(rule of law)还是仅限于主权国家所制定的法律(state law),立法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不得而知。因此,不能认为现行立法已明确排除非国内规则的适用。
现有的非国内规则过于繁杂,难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征,因而法学界还没有对非国内规则下一个明确的定义。非国内规则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其为国际商业运行和国际商事交易提供的独特服务,其法律界定应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国际商事领域的非国内规则是:以权威性国际组织(如国际商会、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等)主导制定的、不具有传统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不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没有法律拘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各种反映商业性习惯做法或标准的规范性规则的总称。非国内规则主要包括:未经国内法转化而直接适用的国际条约、成文化的国际惯例及未经编纂的国际惯例。由于篇幅所限,对于如美国证券交易所、美国国家证券交易商协会以及英国银行协会、英国消费信贷贸易协会等国内行业协会所制定的规则则暂不讨论。
(二) 适用非国内规则的必要性
早在19世纪中后期,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便确立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5]根据传统的合同准据法选择理论,当事人依意思自治原则所选择的合同准据法仅限于一国的国内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纵向发展及欧洲统一市场的逐步建立,合同准据法不再囿于各国国内法,非国内规则逐渐被国际商事合同当事人所选择适用。主要原因有:第一,国际商事交易双方当事人出于成本控制等目的,并不会花费相当多的时间、金钱及精力去研究对方当事人所在国家的法律,更不用说第三国的相关法律。因而无论具体合同的谈判过程,还是制订格式合同时,国际商事合同的当事人并不愿意选择其中一方的国内法作为合同准据法,而更倾向于选择普遍适用的、内容为各方所熟悉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来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第二,各国法律制度差异较大,极易出现合同双方当事人各自所在国法律关于合同争议问题规定不同甚至都没有规定的情况,况且立足于规制国内需求的法律往往无法适应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如果适用国内法解决合同争议,既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无法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及效率价值。
另外,以《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欧洲合同法原则》等为代表的非国内规则逐渐被各国国内法院、仲裁机关的涉外司法审判实践所适用,作为国际商事合同争议的裁判依据。究其原因,不仅源自国内法院对传统冲突规则不适当性的反思、对特定场合下国际统一实体条约缺失的补救,还在于对国际商事合同当事人正当期望的尊重。[6]
二、国际商事合同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非国内规则
(一) 国际条约
根据《解释(一)》第三条,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涉及适用国际条约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等法律规定予以适用。当事人若明示选择非国内规则以调整其跨国商事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将存在以下两种情况:①当事人所选择适用的是一个实体私法条约,学者普遍认为此时国际民商事条约可直接适用。需注意的是,前述《民法通则》的规定仅强调当我国批准的国际条约与我国的民事法律存在不同规定时,应优先适用国际条约,而这并非是条约直接适用的效力来源。②当事人所选择的国际条约不仅具有实体法,还包括冲突法、程序法等内容时,法院是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从而根据条约中冲突规则的指引确定准据法,还是将条约中的实体法内容作为准据法适用于合同,抑或是认定当事人该选择无效,从而适用我国的冲突规则?但我国已明确“涉外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不包括该国的法律适用法”,因而排除了第一种可能。但法院究竟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而适用国际条约抑或适用国内法,实践中并不明确,需要具体分析。
如果当事人所选择的非国内规则并非我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但已被其他国家批准,能否视为当事人选择了该国的国内法作为其合同准据法从而适用非国内规则?有观点认为,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为例,非成员国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选择适用公约成员国(该国已将公约转化成其国内法)的法律使公约得以适用于其跨国商事合同。[3]但也有观点认为,我国可以通过对生效的国际条约进行声明保留,排除国际条约中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条款的适用。但对于未经我国批准的国际条约则无法排除此种影响,因而有可能存在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7]我们认为,法院此时应该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将其作为当事人约定适用“外国法律”的情形对待。根据《法律适用法》第十条及《解释(一)》第十七、十八条,由当事人提供外国法律的内容,法院进行审查认定。对前述可能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可通过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共秩序保留条款的适用加以避免。
(二) 国际惯例
海事海商审判实践中,有些案件的当事人在提单中载明适用《1924年统一提单某些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即《海牙规则》)、《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即《汉堡规则》)等我国并未加入的国际条约。[7]由于前述公约尚未对我国生效,故对我国没有拘束力,不能将其作为国际条约予以适用。但其频繁适用于国际海商事领域,能否视为国际惯例,从而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三款作为合同准据法予以适用呢?还是根据《解释(一)》第九条,“当事人在合同中援引尚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的国际条约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该国际条约的内容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仅作为合同并入条款呢?
当事人选择非国内规则作为合同准据法的法律后果便是排除了法院地法中任意性和一般强制性法规的适用。由于对非国内规则缺乏足够的认识以及对其性质的质疑,我国法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更倾向于将其作为合同的条款内容以规制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这样,既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使其选择的规则得以适用;又保证了国内法作为准据法的适用,使合同受我国法律的管辖。当事人选择国际商事惯例作为准据法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 当事人选择成文化国际商事惯例作为准据法
如前述,我国对涉外合同法律适用进行立法时皆采用“法律”一词,因而关于当事人能否选择国际惯例作为合同准据法并没有明确、正式的规定及解释。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缔结过程中及之后,甚至在争议解决过程中当事人都可以明示选择其合同的准据法,而国际商事惯例因其简明清楚、便捷高效等优势在跨国贸易领域得到较多适用。与国内法相比,国际商事惯例灵活新颖、与合同内容联系更为密切,从而更适合商业实际、更利于解决特定问题。因此,允许当事人选择国际惯例作为准据法,能有效避免国际商事纠纷抑或促进国际商事纠纷的快速有效解决。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根据国际惯例及一般法律原则作出的仲裁裁决日渐增多。以《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为例,我国仲裁庭受理的相关案件也经历了从仅将其作为判决说理的辅助工具到作为合同准据法的突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编写的《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一)》在解答审理涉及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时,明确指出,“对于涉外合同纠纷案件,人民法院一般按照如下办法确定应适用的法律:(1)适用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外国法或者有关地区法律;……”[8]这无疑表明最高人民法院是认可当事人选择国际惯例作为合同准据法的。实践中也有不少案件是依据当事人选择的国际商事惯例作出判决的。如瑞士纽科货物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珲春市支行拒付信用证项下货款纠纷上诉案中①,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本案所涉信用证项下纠纷适用UCP500,该约定合法有效,故本案应以该惯例为依据调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又如,中国安徽省服装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与法国薛德卡哥斯公司、中国安徽外运直属储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索赔纠纷案中②,法院认为,提单背面条款规定本案的争议应适用法国1966年6月18日法律及相关法律解释或者适用《海牙——维斯比规则》,故法院选择《海牙——维斯比规则》为本案的准据法。
2. 当事人选择尚未编纂的国际商事惯例作为准据法
与成文化的国际惯例相比,未经编纂的国际习惯做法无论在性质、渊源及范围等方面都较为模糊,难以确定。如果当事人在选择合同准据法时仅表示适用“商人法”“一般法律原则”而未明确国际惯例的具体内容时,这样的意思自治内容能否得到法院的认可呢?
首先,作为准据法的商人法较多出现于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根据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建立的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相关诉讼及仲裁案件数据库UNILEX,当事人在合同中表示同意受“商人法”“一般法律原则”(或类似措辞)管辖时,法院或仲裁庭可以适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如俄罗斯联邦工商协会国际仲裁院第11/2002号裁决、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法院1998年12月作出的598-1165-B号判决等。[9]由此可以发现,当事人选择非特定的国际惯例作为准据法时,法院或仲裁庭仍需根据一定的冲突规则来确定其具体内容以调整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诸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非国内规则得以适用,实际上得益于其已形成一套系统的、能清晰反映各国合同法一般原则及国际商事交易特殊要求的规范性规则,其内容清楚明确,从而有利于法院或仲裁庭的适用。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国际商事仲裁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的产生与发展皆是为了满足国际商业社会对便捷、高效的追求,平等主体间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决定了其与商人法、国际商事惯例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而法院作为主权国家的审判机关,承担了更多的政治和社会功能,更关注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因而,法院对于当事人合同准据法选择的审查更为严格。
最后,我国合同当事人在国际商业交易实践中极少选择适用非国内规则(尤其是商人法等模糊概念),而在准据法的选择问题上,我国涉外民事审判实践中已出现了“回家去的趋势”。我国学者在对近900起涉外民商事案件进行统计后,发现适用我国内地实体法律的高达781件,约占总数的87%。[10]适用非国内规则需要法官具备一定的国际私法素养以及较高的外语水平,而未经编纂的国际惯例的查明难度更是加大了法官的工作量。同时,面对审判文书网上公开、错案率与法官业绩考评挂钩的社会压力,适用其最为熟悉的法院地法成为法官“趋利避害”的必然选择。
三、法院主动适用非国内规则解决国际商事合同纠纷
在我国涉外民商事司法实践中,非国内规则不仅可通过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为合同准据法得以适用,还存在未经当事人选择时被法院依职权主动采用的情况。
(一) 法院适用非国内规则作为合同准据法
根据《规定》第五条,“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如前所述,此时法院倾向于寻找连结点使法院地法适用于合同。但司法审判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是,法院地法对涉外合同争议的具体问题没有规定或规定不全面,法院此时反而会选择适用非国内规则。以马来西亚KUB电力公司(KUB Power Sdn. Bhd.)诉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履行独立性保函承诺案为例③,关于该案所涉中国投资银行沈阳分行所开立的No.APS2297012预付款保函是独立性保函还是从属性保函的问题。法院认为,独立性保函是指一种独立于基础合同,仅以保函自身条款为付款责任确定依据的保函,而从属性保函是指将保函项下义务的履行取决于相应的基础商业合同。由于我国缺乏有关涉外独立性银行保函的具体法律规定,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也没有相关规定,所以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适用有关的国际惯例《见索即付独立保证统一规则》(Uniform Rules for Demand Guarantees)(即国际商会1992年正式公布的第458号出版物)对案件进行裁决。
而连云港口福食品有限公司诉韩国中小企业银行(汉城总行)(Industrial Bank of Korea Seoul, Head Office Seoul)等信用证一案④更是我国法院适用非国内规则的典型。该案属于信用证交易纠纷案件,各方当事人虽未约定本案纠纷所适用的准据法,但在起诉及答辩过程中均以UCP500为法律依据。UCP500规定了信用证关系中各有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国际通行的信用证业务统一惯例,弥补了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的空白,而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认可其适用。另外,由于UCP500并未涉及信用证欺诈及法律救济问题,因而关于该问题是适用韩国法律抑或适用中国法律,各方当事人不能达成一致协议。二审法院更认为,本案争议信用证项下有关单据和提单签发地在中国,即中国是韩方主张的口福公司实施欺诈行为的侵权行为地,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本案关于信用证欺诈及法律救济问题应适用中国法。
(二) 法院适用非国内规则补充或解释法律
在国际商事交易实践中,合同当事人已选择国内法作为合同准据法,但该准据法关于所涉合同问题没有相关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因而法院在适用国内法的同时,也适用非国内规则来进行法律补充或法律解释。例如,在乳山宇信针织有限公司诉韩国中小企业银行信用证赔偿纠纷一案⑤中,尽管双方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但由于该案的索赔发生在信用证关系的受益人与开证行之间,因此法院认为受益人与开证行间的权利义务应当适用国际惯例《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1993年修订本)即国际商会第500号出版物(UCP500)。
可见,我国法院依职权适用国际惯例的前提是,我国法律及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于合同争议事项没有明确规定,也就是说,在法律适用方面,现有国内法及国际条约的规定优于国际商事惯例。但需要区分的是,国际商事惯例此时承担的是补充法律漏洞的功能;而当国际惯例作为合同的默示条款补充和解释合同内容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国际惯例则优先适用。
四、非国内规则适用于国际商事合同的限制
(一) 非国内规则自身的局限性
以现代商人法为代表的非国内规则能否作为跨国商事合同的准据法,从而适用于商事审判实践,深受自身发展程度的影响。[11]适用非国内规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其性质的界定。法律多元主义视野下的法不仅指主权国家的法律,还包括存在于各种规模和性质的社会系统内的规范。以戈德曼(Berthold Goldman)、托伊布纳(Gunther Teubner)为代表的学者将现代商人法视为一个日臻完善、完全独立于国内法的自治法律体系,认为其效力并非来自于国内法,而是来源于国际商事实践的广泛认可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援引非国内规则的合同并非不受法律调整而仅是不受国内法调整。但深受法律国家主义影响的学者并不认同“非国内规则是法律”的观点,认为其既无民主的立法过程导致质量参差不齐,又缺乏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反对将非国内规则作为准据法。
关于非国内规则的渊源,法学界也尚未形成共识。即便是现代商人法的代表人物戈德曼(Berthold Goldman)也意识到,商人法的抽象性及理论性使学者们很难总结或归纳出非国内规则的渊源,从而主张从现代商人法的起源、习惯法性质以及自我发展的本质等角度入手考察现代商人法的范围。在国际社会实践中,编纂水平高超(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的成文化非国内规则毕竟是凤毛麟角,大量未经编纂的国际惯例因其内容的随意性及模糊性遭人诟病。如果当事人仅在合同中表示双方的权利义务受“商人法”约束,则很可能被法院视为无效选择。若当事人约定其合同项下争议适用某一特定领域的国际惯例但并未明确其内容(如“合同受国际贸易法的一般法律原则约束”等),此时法院是否认可继而查明、识别该惯例并加以适用呢?在上述情况中,跨国商事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极不确定状态,很难准确预测其行为的法律评价。更重要的是,法官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查明非国内规则的具体内容并加以适用,这对于超负荷办案的法官来说亦是智力与体力的挑战。与仲裁方式的便捷灵活相比,诉讼程序繁杂冗长,若再拖延,实际上更不利于达成商业社会所追求的高效与可预见性。
(二) 法院地法发展水平的制约
国际私法背景下非国内规则的地位与法院地法的理论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其适用仍取决于一国立法机关对准据法的态度:如该国仅将准据法视为“经冲突规范指引,适用于某一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具体实体法规范”,无疑排除了非国内规则的适用。以《美国统一商法典》为例,1998年版中,各州皆采纳的第1~105条强调了当事方可以选择适用于其交易的法律为某州或某国的法律(the law of either this state or of such other state or nation shall govern their rights and duties)。⑥而在2001年版中,第1~302条允许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权威组织制订的规则或适用于商事交易的原则,以替换《美国统一商法典》中的任意性条款(that their relationship will be governed by recognized bodies of rules or principles applicable to commercial transactions)。⑦由此可见,美国对非国内规则的开放态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商事交易实践尤其是银行托收等业务中非国内规则的广泛适用逐渐变化的。
在跨国商事合同的法律适用过程中,无论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赋予、非国内规则内容的查明还是裁决的做出与执行,都不能脱离法律所允许的范围。结合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立法家父主义,只有立法允许对涉外商事合同的法律适用规范进行扩充解释时,当事人关于非国内规则的选择才能得到认可,这就突破了传统准据法的范畴。为了更好地解决跨国商事纠纷,产生了以现代商人法为代表的非国内规则作为合同准据法的现象,并伴随着《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特殊的法律重述)、《欧洲合同法原则》(国际社会示范法)等作为国际商事合同准据法适用于涉外商事审判实践。如何把握合同准据法这一变化并加以利用,亟需立法机关做出回应。
(三) 强制性规范与公共秩序的限制
当事人选择非国内规则的正当性主要源于意思自治。但意思自治并非当事人的天然权利,而是由国家所赋予,从而国家对意思自治的限制也影响了非国内规则的适用范围。
1. 强制性规范对非国内规则适用的限制
《法律适用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即关于实体法的具体问题,该“强制性”不能为当事人所排除或变更,因而强制性规范的直接适用优先于当事人所选择的准据法,成为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一个重要限制。而运用比例原则厘定国际私法背景下的国家强制与私法自治的合理边界要求“直接适用”应以强制性规范适用范围内的事项为限[12],即强制性规范仅替换多边冲突规范指引的准据法对同一事项的相应规定,而非彻底排除准据法的适用。
2. 公共秩序对非国内规则适用的限制
《法律适用法》第五条规定,“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尽管其将公共秩序条款的排除仅限于外国法律,但关于现代商人法等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非国内规则,当事人协议选择时若仅视为合同条款,人民法院可选择是否确认其适用,无须借助公共秩序这一“安全阀”。当事人协议选择作为合同准据法时,我国未批准的国际条约或可作为某一成员国的国内法进而适用前述第五条规定;而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和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国际惯例的适用不得违背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传统法律国家主义的思想与目前非国内规则良莠不齐的事实相结合,将导致对非国内规则采取比外国法更为严厉的限制措施。因缺乏了解产生的不信任以及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潜在担心不仅使得对当事人证明非国内规则内容的要求更高,法院在适用时的审查标准亦会更加严格。
五、非国内规则适用之反思
(一) 非国内规则的适用不具有普及性
由于国内法在跨国商事活动的法律规制、争议解决等方面的不足逐渐凸显,国际商事主体亟需摆脱国内法的不合理限制。更重要的是,国际商人社会及全球性商事价值体系的逐渐形成,促使国际商事主体的目光转向了非国内规则。不能否认,准据法的非国内法化无论对传统合同准据法的选择范围抑或选择方式都是一种突破,但当前广泛适用非国内规则的条件并不成熟。首先,国际社会并未形成一个科学统一的非国内规则体系。非国内规则的性质、渊源、范围等问题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界定,当事人抑或法院在适用非国内规则时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以现代商人法为代表,其能否为国际商事争议的解决提供数量充足、协调一致的规则体系,其能否为国际商事纠纷的裁判结果提供正当性及执行力依据等,对这些问题的质疑都需要进一步解答。其次,非国内规则尤其是未经编纂的国际商事惯例,其内容的随意性和模糊性都使当事人的选择难以确定,加大了法院查明和适用的难度,不能达成国际商事流转所追求的高效便捷的目的。我们认为,应尊重国际商事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允许其选择非国内规则作为准据法,但应在国内立法中明确规定:非国内规则仅限于那些公认为成熟、完备、科学的规则(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欧洲合同法原则》等)。而法院在适用未成文化的国际惯例时,需要借助一定的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以确定该习惯性做法的存在及具体内容,因其缺乏普遍适用性,暂不适宜作为跨国商事合同的准据法。另外,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非国内规则时,由当事人举证证明该规则的内容,但法院具有最终裁量权。
(二) 我国立法机关及司法机关应当推动非国内规则的适用
尽管目前我国立法对非国内规则的适用问题尚无明确规定,但上述分析表明,我国法院在涉外商事审判实践中并不排斥非国内规则(尤其是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其一,法院允许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选择适用于涉外商事合同的准据法(包括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其二,当国内法律及我国参加或者缔结的条约对合同争议问题都没有规定时,法院主动依职权适用非国内规则以填补法律漏洞。然而,适用非国内规则的涉外案件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案件仍是根据法院地法做出判决。
在我国法律实践中,立法仍是推动非国内规则适用的最重要途径。只有通过立法明确国际民商事条约、国际惯例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及其适用方式,通过对涉外法律适用规范进行扩充解释将其纳入法律规则的范畴,从而减少非国内规则适用的限制性条件等,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更好地促进国际商事社会的发展。而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我国的最高审判机关,在促进非国内规则的法律适用中扮演重要角色,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非国内规则的引用以统一有关国内法的不同解释,并在审判监督过程中鼓励下级法院认可当事人对非国内规则的选择适用,无疑鼓励了下级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适用非国内规则,从而更好地解决跨国商事合同纠纷。
注释:
① (1998)经终字第336号.
② (2001)武海法商字第19号.
③ (2004)沈中民四外初字第12号.
④ (2003)苏民三终字第52号.
⑤ (2006)鲁民四终字第25号.
⑥ U.C.C. §1-105(1) (1998).
⑦ U.C.C. §1-302, comment. 2 (2001 Revision).
[1] Peter Nygh. Autonomy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7.
[2] Ole Lando. The lex mercatoria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J].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1985, 34(4): 747−768.
[3] Zheng Sophia Tang. Non-state law in party autonomy-a european perspectiv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ivate Law, 2012, 5(1): 22−39.
[4] Zheng Sophia Tang. Non-Sate Law in Chinese Choice of Law Rules [EB/OL].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079244, 2011-03-02.
[5] Ole Lando. The conflict of laws of contracts: general principles [J]. Recueil des Cours, 1984, VI(189): 243−244.
[6] 吴德昌. 国外法院适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司法实践与法理探析——兼论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及其立场演进[J]. 江西社会科学, 2010(6): 164−169.
[7] 高晓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的解释(一)》解读[J]. 法律适用, 2013(3): 38−45.
[8] 万鄂湘. 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9] 左海聪. 试析《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性质和功能[J]. 现代法学, 2005(5): 175−181.
[10] 郭玉军, 徐锦堂. 从统计分析方法看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的发展[J]. 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 2008(11): 127.
[11] 贺万忠. 准据法的非国内法化: 理想抑或现实——兼评我国《民法典(草案)》第9编第4、50条之相应规定[J]. 东方法学, 2008(2): 108−120.
[12] 肖永平, 龙威狄. 论中国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10): 107−122.
Application of non-state rul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LIU Yideng, CHEN Lu
(School of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s the theory of the governing law of contracts is constantly evolving, non-state rules have been applied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Non-state rules are not legally binding, but have gradually been adopted by courts and arbitration agencies in many countries owing to their strong practical nature. Non-state rules could be allowed as the applicable law to an international commmerical contract upon the principle of party autonomy or be applied by the judiciary actively. But owing to the limits of the non-state rules themselves, restric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local laws and confinement of the public order, non-state rules can not enjoy popularity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Therefore, 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agencies should embark from two aspects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non-state rul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one is perfecting non-state rules and the other is reinforcing legislation and judiciary laws.
non-state rule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applica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international practice
D996.6
A
1672-3104(2015)03−0093−07
[编辑: 苏慧]
2014−12−11;
2015−03−1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药品消费者保护中的国际私法问题研究”(14BFX132);中南大学教师研究基金项目(7609010048)
刘益灯(1970−),男,湖南洞口人,法学博士,荷兰莱顿大学法学院博士后,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私法,WTO法,民商法,消费者保护法和电子商务法;陈璐(1989−),女,湖南郴州人,中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