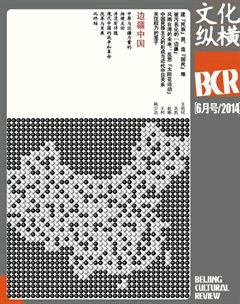编者按
边疆中国
边疆在传统中国是围绕儒家礼乐体系,通过华夏中原与“夷、戎、蛮、狄”这样的文明等级秩序安排的;近代中国革命则以西方民族主义话语动员与整合帝国疆界,以利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通过阶级划分吸纳民族区分,以经济平等弱化民族的文化抗争;而1978年之后开启的市场化改革,则使“利益”成为民族矛盾升温的催化剂,进而推动民族/宗教认同的激进化。从文明民族阶级利益民族/宗教认同的轮回与强化,大致能够概括中国边疆问题的历史发展逻辑。汉族中原与边疆力量的持续互动,并没有伴随现代中国的战争和革命、改革与发展而终结。1990年代之后奉行的发展主义、援助建设、维持稳定这些民族政策所逐渐陷入的困境,就必须放置在这样一个历史脉络中获得理解。
本期作者代表了民族/边疆问题解决的几种经典思路,大致可以概括为再分配主义、文化身份认同与公民权政治。在付桂杰看来,由经济屏障导致的民族隔阂倒逼出了社会混乱的输出,对国家和汉族的怨气,主要来自少数民族经济边缘化的现状。计划经济时代由国家机器强行将少数民族带入现代化产业进程,而市场化改革却排斥少数民族劳动力,微观经济的自然遴选却被少数民族表述为宏观的国家歧视。在革命瓦解了传统边疆的习惯法治理体系之后,只有通过国家力量主导的再分配方案,才能弥合由利益分化与争夺导致的社会原子化进程。而在关凯看来,当代边疆问题的根源,在于一群以“主流社会”自居的功利主义者,以居高临下的“教化”优越感,以发展至上的文化霸权将边疆民众对象化与污名化,并将边疆塑造为恐怖主义的渊薮、发展的落伍者和族群冲突肇事者聚集的空间。作者显然认为,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比民族经济的利益矛盾更为本质。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关凯与王明珂都重新评估了“边疆”作为文化“异度空间”的力量。只有在中原与边疆的相互观看中,才能避免主流民族叙事的傲慢与偏见,进而形成“平等合作、区分与竞争之族群关系”。郑少雄对多吉堪布的人类学观察,同样展示了作为“他者”边疆的文化能动性和独立性,它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的互动,以此争取外部的经济、政治及道义资源,从而也为塑造与恢复边疆社区的文化生态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有意思的是,作为著名的边疆史学家,王明珂最终却希望能“化边疆于无形”。在他看来,“民族”既非边疆之人的唯一选择,也并非最好的选择。近代中国早熟的民族主义运动,其实错过了“再造国民”的历史契机。建民族易,造国民难,如欲形成中国的“新多元一体格局”,迟来的“公民权政治”恐怕难以迈过。
四位作者雄辩地证明,中国边疆绝不只是汉族中原的外廓,从属于猎奇、景观、蛮荒与粗野,也不只是城市乡村空间之外的政治飞地。边疆中国,不仅涉及如何重新理解中国,也是在当代全球化与中国大转型背景下,如何重新再造中国的核心历史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