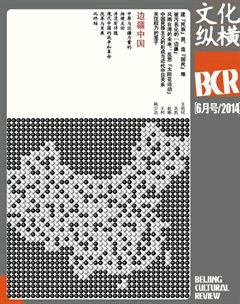香港管治的出路何在?
程东金
自回归以来,香港一直面临着如何实施有效管治的问题。从许多方面看,管治状况在回归之后有恶化的趋势。突出表现在,特区政府处于弱势,处处受制于各种反对力量,行政权力被立法会和法院“篡夺”,政策推行不通畅而且“朝令夕改”。其结果就是,政府难以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状况这两大领域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招致港人对特区管治的不满,进而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处于劣势,反对派占据上风,成功地将这一“管治危机”论述为“受认性”(合法性)问题,迫使中央加快香港的政制民主化步伐,削弱爱国爱港/建制阵营的力量,并让自己可以获得上台执政的机会。而一部分反对派在境外反华势力的策应下,其实质目标在于促成香港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而这又是中央根本不能接受的。
理解回归以来的香港管治问题,行政立法关系是一个关键线索。为了有利于平稳实现回归与过渡,中央曾许诺回归后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无疑是一个带有极大保守和妥协性的安排,十足反映了当年中央为推进改革开放战略而极其倚重和需要香港的现实。然而,就回归后的政制体制而言,还是发生了若干根本性变化。最主要的改变就是立法机关脱离了行政机关,变成了独立于行政机关的监察者、制衡者与竞争者。其结果是,特区的立法会与政府的关系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原先中央希望以相互配合为主,但实际上却以相互制衡,甚至相互对立为主。其具体表现,则是行政与立法机关双方对于权力灰色地带的争夺,权力相互制约经常陷于失衡状态。可以说,管治困难的症结,即在于行政立法之间不断的争斗,立法过程不单缓慢,而且充满变数,施政过程存在不少的不确定性。《基本法》虽然立意在于推行“行政主导”的政制体制,但在现实层面,已无法做到。
殖民地时期,立法机关从属于行政机关,施政效率自然有保证。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所有立法议员都是由香港总督委任,其基本任务是拥护和配合殖民政府施政。正因为立法局是殖民政府温顺的管治伙伴,殖民政府从向被殖民者展示其开明姿态,以及向国际社会标榜香港为所谓的“治理橱窗”的动机出发,把一些原本没有打算被立法局运用的权力交给它,特别是关乎财政资源和人事安排方面的权力。当立法机关在回归后不再从属于行政机关,而立法议员特别是反对派,又希望不断扩大立法权力的时候,那些殖民地时期细碎和繁琐的安排便成为立法会掣肘行政机关的利器,或成为立法议员与特区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此外,为了大力提高立法机关为香港最重要的政治机构,英国人在香港撤退前夕,努力营造一个政府向立法局“负责”的印象,企图为将来的特区起创制和垂范的作用,实际上要让《基本法》规定的行政主导体制无法实现。
香港著名学者、前特首首席顾问刘兆佳在其新著《回归十五年来香港特区管治及新政权建设》中,系统地诊断了新政权建设所遇到的障碍和管治困难。他认为,一个独立于行政机关的立法会在几个方面必然与政府产生难以弥补的结构性矛盾。其一,立法会具有本身的机构性或制度性的利益与观点,自然希望得到更多的宪制权力。其二,立法会议员认为它比特首更具民意授权,也更具政治代表性和“认受性”。其三,不同的选举安排导致立法会和特首具有不同的社会支持基础,在施政方针和政策路线上无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
由于《基本法》禁止特首有政党背景,事实上不允许在香港发展政党政治,特区政府和立法机关之间也就不存在政党这一通常的联系机制。政府在立法会虽然与一些友好党派建立了某种合作关系,但始终没有稳定、可靠与持久的大多数议员的支持,难以推进强势有效的施政。政府的法案、财政预算案及政策方针能否得到立法会的支持,经常存在未知数。在涉及中央权力、中央与特区关系和政制体制等问题上,建制派议员对特区政府的支持是有保证的,因为他们不希望在这些事情上得罪中央。不过,若是涉及社会、劳工和民生事务的话,来自商界的议员不一定支持官方的立场。即使支持,往往政府也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去游说,并经常要通过政治交易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回归之后,特区政府官员花费在游说立法会审批通过数量众多但甚为琐碎的财政和人事事务方面的时间和资源极为庞大,并因此大大减少了能用于思考、制定和推行政策的时间和空间,或者与社会各方面接触的机会,间接降低施政效能。
刘兆佳分析,中央反对政党政治,不愿意组织一个能够同时掌控行政和立法机关的地方性执政党,也不容许行政长官有政党联系,有着非常现实的考虑。尤为要紧的一点就是,一个有政党联系的特首,必须履行他对所属政党的责任,从而不能够对中央完全效忠,使得中央不可以通过他来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中央必须提防,一个整合了的建制势力在选举的压力下,逐步演化为面向本地市民的群众性政党,而这一市民人口的相当部分,对中共执政仍然抱有疑虑。
也即是说,假如允许行政长官有政党身份的话,那么他是否忠诚于中央则成为一个疑问。鉴于在整个特区的政治体制中,特首是唯一的中央与特区的接触点和连接点,中央绝对依仗特首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在香港准确落实,不容有任何差池。容许香港出现管治联盟或执政党,也意味着中央愿意对政党政治开方便之门,即是说同意让政党管治香港,以及接着可能出现的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甚至容许反对派领导特区政府的场面发生。这些都是至关紧要的问题。
中共的基本原则非常明确,它是包括香港在内的全国的执政党。但中共在香港却不但不直接管治,而且不公开活动,也不参加香港的各项选举。刘兆佳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央还没有明确搞清楚作为国家的执政党与参与管治香港的建制力量的关系。如果这些力量不受中共节制,则中共确保执政党的地位就成一疑问。在诸多根本问题没有厘清之前,中央对政党政治只能是禁止,对于管治联盟的组成也只能是处于两难之局。而在中央未有明确表态之前,特首能够整合建制势力的空间亦有限。
由于“执政党”抑或更为紧密的管治联盟这两种方案都无眼下施行的可能,我们在短期内尚看不到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而无论如何,就算在有执政党可以同时控制行政和立法两个机关的情况下,行政立法矛盾也不宜化解。美国和台湾的情况便可见一斑。
如何落实《基本法》规定的行政主导、立法和行政既制衡又配合这一政治体制,刘兆佳认为,解决之道还是应建立特区政府和建制派的管治联盟。广义上说,管治联盟包括所有在利益或信念上与政权相近,且鼎力支持它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特别是指政权可以依靠的政治精英,而那些政治精英则散布在权力架构(尤为关键的是立法会)与社会各领域之中。与此同时,管治联盟的成员又能够通过各种纽带与群众联系起来,在有需要时发动他们支持政府或者反制政府的对手。管治联盟可以不同的组织形式表现出来。较高级的形式是有严密组织和森严纪律的政党,较低级的形式则是松散的、以个别领袖为核心的恩主与附庸网络。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党是从事管治工作最为常见的组织形式。
但香港无疑不属于这一情况。香港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