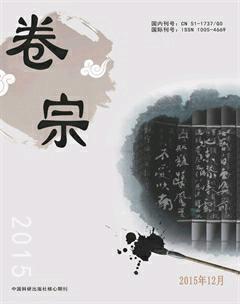《古代城邦》中的信仰问题
胡彦彦
“敬礼死者的宗教是人类最古老的宗教。在崇拜因陀罗或宙斯之前,人都曾崇拜亡灵。人既怕它又祷告它,宗教情感大约即是这样发生起来的。大约古人是因看见人死才发超自然神灵的感想,并希望走出人类所见的此岸。人死是第一秘密,它另人由此想及其他秘密。人类思想正是如此由可见世界而进至不可见世界,由短暂事物的而进至永恒的事物,由人的领域而进至神灵的领域。”
人死的秘密是什么?在、不在,在者怎么能够不在?既然它在过。不在的秘密是什么?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另外的世界?在那个世界,活着的是那些曾经活生生的在我们身边的人。
这世界是否只有一个世界?面对未知,不可证明,我们是信还是不信?
有两种选择,狂妄地不信,或敬畏的信?这里是否应该有一种道德的区分在?无神论者= 没有道德的人。有信仰的人=有道德的人。信的态度似乎也可以分为两种,虔信,匍匐地信,被抨击为迷信。虔信,虔诚地信,被崇高化为圣徒。
信来源于什么呢?未知?恐惧?还是有一种别的什么东西,使我们的信具有了某种道德性,使我们人,比动物崇高了起来。按照儒家的观点,我们看到死去的人会把尸体埋起来,因此我们成为了人,我们会去祭拜祖先我们成为了人,如果我们做不到这样,我们会觉得恥,这使我们成为了人。我们不把死亡当成一个纯粹的物质的灭亡,我们相信有某种东西依旧与我们同在,相信那些亲人们不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观音山》中失去了儿子的张艾嘉说,在才是永恒。这也是我们祖先们的情感,如果一个东西可以纯粹的不在,那么它曾经的在也是一种虚妄,我们会永远在一起,这才是祖先们朴素的信仰。死去的人不但在,而且是如我们一般的在,需要吃,需要住,要回到家乡,会感到痛苦,还会去报复生者。活着的人们害怕自己死了没人葬,回不了家,害怕没有人祭奠自己,会变成孤魂野鬼。看起来,人对幸福的追求延伸到了死后。
“敬礼死者的宗教是人类最古老的宗教。”“人既怕它又祷告它”,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要死去的亲人保佑我在现世的顺利。我也曾怀疑过,扫墓的必要。有人说,对于死者,恐怕是没什么意义的,但对于生者,意义是很大的。即使只是出于寄托哀思的必要。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是无法面对彻底的空?即使是做四大皆空的和尚,我们也要搞一些仪式,如剃度,戒律,这些是实实在在的区别性的东西。要让人坦然地接受实实在在的,毫无神秘性的空,恐怕是很难的。
而对于来生,人们不可避免地抱有两种道德态度,道德的,非道德的。
第一种就是我们熟悉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辈子坏事做尽,下辈子就只能投胎做猪狗,做牛做马。这里边,用尼采的话说就是邪恶的复仇心理。根源在于对此世的憎恨,对受苦的憎恨,因此抱希望与来生,认为一定有一个此生受苦受难,来生吃香喝辣的彼岸世界。
而古代城邦中的祖先们,却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是单纯的,“健康的”。古代城邦中单纯的祖先们,认真地守护着死去的祖先,它们的全部生活都浸泡在古代祖先的血脉牵绊中。它们的单纯既体现在对死去祖先的虔信。又体现在道德化的缺失。
“人不必有德,恶人亦能与善人一样成为神。在来生,恶人所保存的,只是他在现世就有的恶的习心。”
如古人般理解古人,其中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理解古人的精神世界,理解古人的信仰,光理解还不是一切,重要的是尊重,尊重古人的信仰,不用现代进化论的观点把古人视为落后的、愚昧的、不开化的。
这种态度纵向的是历史学,横向的是人类学、民族学,尊重多民族的信仰及生活方式。
但有意思的一点是,伴随着现代科技的过度发展,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了渴望返祖的环保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尊重古人,尊重少数民族,而反而是不要媚古、媚少了。
文化中历来是有各种好古、复古的风潮的。尤其是在雾霾严重,社会道德沦丧的现实状况下,人们怀念从前的青山绿水,怀念从前的路不拾遗。人们总是好古的,孔子亦复如是。我们似乎总觉得在前历史时期,人们是有一个最开始的纯洁时代的。孔子的尧舜禹,卢梭的前文明时代,基督教的伊甸园。
好古如何不媚古,如何不叶公好龙一样的好古,这对今天的环保主义者,和试图复兴中华文化的汉服推广者们恐怕都是一个问题。
《古代城邦》不仅是给我们复原了一个高古的古代社会,让我们知道祖先们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它也描写了人们思想的转变,古老的信仰是如何失落的,单纯的信仰血缘的祖先们又是如何成为了基督教大同世界的公民们。家火的失落,使人们不再安土重迁,受血缘、家乡的束缚,也使城邦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社会变化的原因在于信仰的失落,人们的精神世界一旦从单纯的信仰中挣脱出来,便很难再回去了。这就好比小时候父母在你眼里是迷信的权威,等你长大,看到了更多的世界,自己有了思考,你不会再信妈妈跟你说的话,吃饭掉了几粒米就会减几年寿命之类的,爸爸也不再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壮的人。这是一个独立的过程。以前的信是迷信,是愚昧。但你同样失去了很多,失去了这种信仰带给你的单纯的虔诚,也失去了这种信仰带给你的安全感。
人从对上帝的信仰中挣脱也是一个同样的过程。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但同样,我们发现自己无依无靠地活在这个似乎虚无的世界上。但要回去,恐怕是不能。失落了的单纯是找不回来的。
这也许太武断了,进化论的历史观自然认为过去的回不去,那么循环的历史观呢?螺旋式前进的历史观呢?具有又是怎么个循环法呢?我们不但缺乏看向未来的眼睛,也缺乏面向过去的眼睛。人性在历史地长河中会产生怎样的变化连我们也无法掌控。
《古代城邦》看重的就是这种信仰。尤其是对于死亡的信仰。正是由人们相信死亡不是完全的无,人们才有了精神世界。否则就成了是机械物质主义。但自从科学昌明之后,科技机械物质主义成了真理。人不过是一团化学物质,死了就是物质腐朽了,灵魂是不存在的,看不见的、听不见的、无法在实验室里进行观察的,都不是实体。
这是人类对神秘的反叛。神秘的东西是未知的、不可捉摸的,是令人害怕的,是不确定的。我们有了科技,就有了力量,把神秘的东西打破,真的打破与否,不知道,但观念上,是实实在在的打破了。既然不知道,我可以相信它有,就可以相信它没有。
而无神论带来的,同样包含道德的问题。奇怪的是,无神论像古人一样不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他们因此干脆什么也不信了。这也是奥卡姆的剃刀在起作用吧,既然没有报应,干脆就不要了吧。这样干事不是更方便些么,也更自由啊。
于是我们眼中的古人是奴隶一般的活在家火的信仰中的,时时处处在受束缚。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人们像那样不自由的生活了。但家火这种信仰,真的就不存在了吗?
如果不会不存在,那是说我们是有永恒的人性的,原初的人类所有的情感,我们也会有。
如果会不存在,那是人类没有永恒的人性,我们可以像机器人一样不要血缘,不要家庭,遑论家火这种原始的信仰了。
这也是人类科技发展到今天要面临的问题,机器人、克隆人所带来的伦理问题所带来的挑战是极大的。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历史又会如何记录我们信仰的变化呢?精神的信仰是否会永远地失落,以至于无法再找回?后来的人们是否会无法像我们一样理解我们呢?
参考文献
[1]《古代城邦》[法]库朗热 著 谭立铸 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1月
[2]引自 《古代城邦》(第13页-14页)[法]库朗热 著 谭立铸 译 上海: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