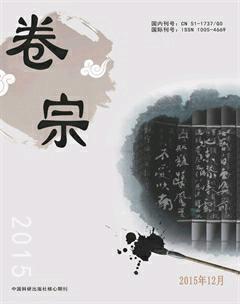文化哲学视角下的中西“法治”观念比较
潘玉龙
摘 要:现代社会中,依法治国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模式,不论中国还是西方社会,都在努力促进法制化进程。然而,受各自历史文化影响,中西方在社会治理思想、法治观念以及法治心理等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而言,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涵盖文化、历史、民族心理等诸多方面。
关键词:社会;儒家;法治
所谓社会,是不同的个体因为血缘、地域、资源、环境、战争等因素,自发或被迫组成的人类共同体。社会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是不同个体的组合,因此,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必然要面临社会治理的问题,以保证资源得到合理分配、社会成员和谐相处、个体权益得以维护。从人类社会诞生至今,社会治理者一直在探索合理的治理模式,然而,不管文化传统多么不同、政体和社会形态的差异有多么巨大,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无法离开一种治理工具,即是法律。
1 中国古代的法治观念
(1)法家思想:“王在法下”
中国早期的法治观念,一般认为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上古社会的尧舜禹时代,以及之后的夏商周三朝,尽管已经有法治现象出现,但是这一管理模式形成为一种社会治理思想,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尤以诸子百家中的法家为典型代表。
早期法家思想的倡导者,是战国早期秦国的商鞅(又称公孙鞅),之后,也是更著名的代表,就是荀子的两位学生韩非和李斯。法家认为,人民是不可信任的,唯有以严苛的刑法加以约束,统治才能稳固,社会才能秩序井然。所谓德治,仅仅是一种美好设想,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法家提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所确立的“王在法下”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王室衰微,诸侯互相攻伐,社会极端混乱。在此种背景下,向来提倡法家思想治国的秦国,在强大国力的支撑下,得以更有效地集中力量,并最终统一了众多诸侯国。然而,严刑峻法只能适用一时,在统一大业完成之后不久,人民终于不堪忍受,推翻了刑罚苛刻的大秦王朝。某种意义上讲,政治上的改朝换代,其实就是社会治理思想不断完善的外在体现。
(2)儒家思想:“王法合一”
众所周知,在百家争鸣中最终占据主导的,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与法家不同,儒家所主张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典型的以德治民。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儒家并不排斥法的运用,而是反对以法治为社会治理的根本模式。明确了这一点,儒家所提倡的“刑不上大夫”,就不难理解了。法律始终存在,但是大夫级别的官员违犯了法律,便可逃脱应有的惩罚,遑论诸侯、王公等高级贵族了。这样,法律的适用度既然仅被限定在人民身上,其存在,便更多的是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社会治理的手段了。儒家最崇尚“内圣外王”的统治,将社会和谐的实现,寄托于统治者个人德行的完善,并由统治者来带动所有社会成员,建立太平世界。所谓“法”,仅仅是作为“德”的补充而存在。因此,在法的执行过程中,人的因素,特别是统治者意志的影响,随处可见。与法家“王在法下”的主张不同,儒家所推崇的法治,是典型的“王法合一”。这种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长远的。两千年封建历史中,受行政权影响,中国的司法权始终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
儒家法治思想的特点有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亲亲相隐”的原则。
《论语·子路》篇中记载: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段对话仅寥寥数言,然而却正是儒家和法家两种伦理、法理思想的直接交锋,也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若仅从严格的现代法制角度而言,父亲犯了盗窃罪,儿子有义务出面举报,否则即是犯了包庇之罪。然而孔子所注重的,并非盗窃行为给社会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是“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这样一种行为给家庭伦理、社会风气带来的极大破坏。与现代法治所主张的、严格完备的外部规定不同,儒家更主张由内而外的、伦理宗法的约束。
对此,孟子也有相同的主张。《孟子·尽心上》 记载: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这个故事,体现了孟子的两种主张。首先,作为统治者,不应该干预司法,即便是自己父亲犯了罪,也不应强行维护。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伦理之情要凌驾于法律的权威、统治者的社会治理责任之上。当然,这样的事例,只是一种理想的假设,在舜的时代,集权现象还不明显,司法独立性还有部分的存在可能。及至统一的集权王朝建立之后,王权完全凌驾于法权之上,类似于舜这样的选择困境,便不复存在了。
统治者放弃统治地位、放弃社会治理责任,带着触犯法律的父亲一起逃跑,这在西方人看来,或许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然而在儒家看来,却是最合理的处理方式。这里,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法治、德治这样现代化的概念,却在实质上明确了德治的优先地位。
2 西方文化中的法治观
(1)西方法治传统的早期发展
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基督教的宗教人文精神、古罗马的法治思想,这是西方文化的三个最重要支柱。然而,人类最早关于法律的明确记载,并非出自罗马,而是出现在古巴比伦。在汉谟拉比大帝在位期间,颁布了明确的法典,并刻在了一块石板之上,即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纯粹的法典,距今已有3770多年。尽管以现代眼光来看,其法条是相当粗糙的(例如“同态复仇”),但是它的出现,对西方乃至全人类的法治进程,都有重要的意义。西方文化中关于法治思想的记载,可追溯至以色列人所记载《出埃及记》,这卷距今三千四百多年的典籍中,记载了以色列人的一系列诫命,比如最著名的“摩西十诫”,这些诫命与现在的法律条文并無太大区别。所以,从《出埃及记》及之后的多卷经文中,也可发现丰富的“法治”思想,尽管此书本身并非专门的法律典籍。
罗马帝国兴起之后,对法律的注重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其法律和法学思想达到了古代世界的最高峰。公元前六世纪,罗马开始形成完整的国家,在民族宗教不断完善的同时,法律体系作为现实秩序的保障也逐步形成。公元前451年,罗马颁布第一部成文法,刻在十二块铜牌上,并树立在罗马广场公之于众,史称“十二铜表法”。将法律条文在公众面前展示,使每个公民都具有司法监督权,这是法治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随着罗马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展,罗马法律体系也不断得到完善,罗马的“公民法”也逐渐成为罗马统治范围内的“国际法”。公元六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搜集整理了自罗马共和时代到他本人时代为止的所有法律,编制了《国法大全》,可谓集罗马法之大成。此时的罗马虽然已将基督教奉为国教,其国家法律的制定却似乎并未过多的受到宗教因素的影响,这在教权日益兴盛的年代显得尤为难得。
(2)历史、文化因素对法治观的影响
历史上,欧洲大陆曾兴起过很多显赫一时的王朝,比如希腊化时期的马其顿帝国,之后还有罗马帝国、日耳曼王朝、斯拉夫王朝、法兰克王国等等。尽管它们都出现在相同或相邻的区域,但它们的文化很少有完全相通之处。以马其顿和罗马两大帝国为例。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施行对外扩张,建立起地域空前的大帝国,曾使希腊文化得以大范围传播。然而,罗马帝国兴起之后,在欧洲大陆,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法律思想迅速取代了本来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希腊文化。在中国,情况显然是不同的。中国古代史上,的確也出现过多次的王朝更迭,并且也有异族入侵并取得政权的时期(如北魏、辽、金、元、清)。然而,不管哪个王朝,都未能丝毫撼动固有的儒家文化之绝对地位。以清朝为例。女真人建立的清王朝,疆域辽阔,且属于典型的异族统治原住民的情况,这与罗马人取代希腊人的状况相类似。然而,强大的女真骑兵虽然完成了政治军事征服,在文化上,却成了被征服者,在潜移默化之中,逐渐被儒家文化所融合。
这样的历史事实,对中西方法治思想的发展,也有显著的影响。在西方的王朝更迭中,能保持相对稳定的,只有宗教和法律。很多西方学者把中国的儒家思想称为“儒教”,即使这种说法成立,它本身也具有极强的世俗性。因为很多时候,儒家伦理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精神层面,而渗透到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力量之大,甚至超越了法律。然而,大多数时期内,西方的信仰体系是作为与世俗力量相平行的一种精神文化力量而存在的,更多的注重在精神上给人指明方向。虽然教会的力量在中世纪极度强大,以至于时常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但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却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因此,西方社会要想保持世俗社会的稳定性,必须依靠相对连贯且具有世俗影响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这样,西方社会对法律与法治的重视,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此可以说,近代西方的法治进程,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与中国不同,西方真正的封建历史要短的多。在悠久的中华历史当中,辉煌的成就会被砥砺得更加辉煌,腐朽的部分也会被沉淀的更加腐朽。而对于西方文化而言,一方面,他们没有太多辉煌的历史可资炫耀;另一方面,他们也免于为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所缠累,从而以一种更加积极务实的态度追求进步,最终在文化竞争中占得一丝先机。中西文化在近现代的不同际遇,反应在社会治理上面,便是中西法治观念的明显不同步。
然而,这并不是说在社会治理方面,西方完全优于中国。不可否认,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是大势所趋,也是中西各国共同的努力方向。但是,法律作为刚性手段,只是社会治理的工具之一,其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一定文化软力量的支持和补充。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至于如何协调法治和人治之间的关系,则要联系具体的历史文化传统及法治化发展现状,做出合理的取舍和选择。
参考文献
[1] 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 陈士果:论亲亲相隐与刑法政治 [J]. 古今论坛,2007,(1):81-83,89.
[3] 吴剑平:“亲亲相隐”法制化浅探 [N]. 刑事研究,2004,10.
[4] 吴丹梅:法治的文化解析 [D]. 黑龙江:黑龙江大学,2003.
[5] 杨文霞:古代儒家德治论 [D].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6.
[6] 刘颖:西方法治的链条 [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4(2):108-113.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