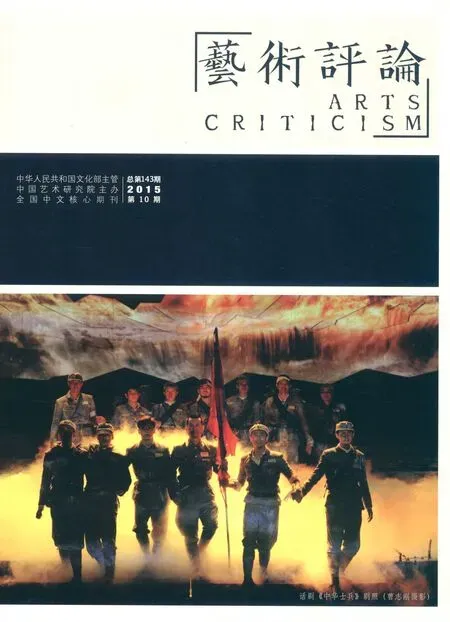论抗战戏剧的民族化道路
田本相
论抗战戏剧的民族化道路
田本相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抗战戏剧的伟大成就,其主要业绩和历史经验,是在民族大奋起和民族大觉醒的时代,适应着民族的需要,走了一条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这一点对当代戏剧的发展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启示。
学界有一种反对民族化提法的主张;但是,对于话剧来说,没有民族化,也就不可能有中国话剧的生存和发展。百年来中国话剧就是中国人以自己的智慧,将它创造性地转化为民族话剧的历史过程。在民族的独创中,把这个“舶来品”改造成为为中国老百姓欢迎的一大剧种。
抗战戏剧的民族化,使它无论在剧作的题材、剧作的思想内涵、话剧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直到演出的体制和演出的组织等方面,无不打上民族性的烙印,无不展现出民族的气派。正是这样的民族化道路,将中国的现代话剧推向一个高峰,涌现出一批戏剧艺术家,一批优秀的剧团,一批杰出的剧作。
一、以戏剧的形式英勇地发出民族的怒吼
中国话剧的民族化精神,在抗战时期首先体现在中国话剧工作者英勇抗敌的精神上。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标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全国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国话剧工作者走在最前面,以话剧为武器,发出民族的怒吼。
上海的戏剧界打响了抗战戏剧的第一枪。“七七事变”之后第八天,1937年7月15日,上海剧作者协会召开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国剧作者协会。会议决定创作《保卫卢沟桥》,并由辛汉文、陈白尘、瞿白音、阿英、于伶等七人组成筹备演出委员会,推定洪深、唐槐秋、袁牧之、凌鹤、金山、宋之的等十九人组成导演团;协会还决定委托于伶、马彦祥负责组织战时移动演剧队;剧本创作组成了以崔嵬、张季纯、马彦祥、王震之、阿英、于伶、宋之的、姚时晓、舒非(袁文殊)等十七人参加的写作集体,由夏衍、郑伯奇、张庚、孙师毅四人整理,不到半个月即拿出《保卫卢沟桥》的定稿。8月7日,《保卫卢沟桥》即在上海南市蓬莱大戏院演出。剧中发出了“保卫祖国,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的吼声。近百名主要演员以满腔热情投入演出和剧务工作,演出气势磅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怒吼,声震山河,轰动了大上海,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他们日夜演出,有时还要另外加演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一直演出到“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
《保卫卢沟桥》的演出,在中国话剧史上是一次标志性的事件。
继之,以“七七事变”为题材的剧本蜂拥而来,如田汉的《卢沟桥》,张季纯的《血洒卢沟桥》,陈白尘的《卢沟桥之战》等。1937年8月9日,南京新闻界联合大华、国民、新都、首都四大剧院,演出田汉的四幕话剧《卢沟桥》(洪深、马彦祥导演),国民党当局虽百般阻挠,仍然胜利演出,激起南京广大群众的抗日浪潮。
很快,抗敌话剧的大浪,在全国各地汹涌而来,如北京、天津、广州、桂林、武汉、昆明、贵阳、西安等地话剧工作者,也发动、 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各样的演剧队和抗日演出团体,掀起全国戏剧界抗敌浪潮。
二、演剧队:演剧体制的民族创举
“演剧队”是中国话剧民族化演剧体制的伟大创举。
在八年的抗战中,为了适应抗战形势而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演剧队,剧宣队、救亡演剧队等,不但是一种适合战时要求的演剧体制,而且是抗战戏剧的有生力量。他们长途跋涉,深入部队、农村、工厂、学校,在宣传抗日、动员抗日,宣传民主进步,启迪民族觉醒上,起到伟大的历史作用。他们历尽艰辛,不惜牺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抗战时期的演剧队在世界话剧史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1937年8月,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决定,成立1 2支救亡演剧队。在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国话剧的大部分精英:第一队队长为马彦祥、宋之的,队员有郑伯奇、崔嵬、丁里、王震之、贺绿汀、塞克、周伯勋、欧阳山尊、王苹、叶子、王余杞、刘白羽等人。第二队队长为洪深、金山,队员有冼星海、黄治、张季纯、田方、田烈、贺路、邹雷、金子兼、白露、王莹、欧阳红缨、熊塞声、颜一烟等人(四十年代剧社成员主要由一、二队成员组成)。第三、第四队总队长为应云卫,成员原属上海业余实验剧团。第三队队长为郑君里、豫韬,队员有魏曼青、刘群、王为一、沙蒙,顾而已、吕班、俞佩珊、舒非、赵丹、伊明、叶露茜、朱今明,金乃华、苏丹、海涛、田蔚等。第四队队长为陈鲤庭、瞿白音,队员有赵明、魏鹤龄、陶金、吕复、汪洋、舒强、张客、严恭、吴晓邦、赵慧深、李琳(孙维世)、吴衡、吴考等人。第五队队长为左明,队员有艾叶、艾琳、仉平、宗由等人,该队原为上海先锋演剧队。第六队队长为李实。第七队队长为丁洋。第八队队长为刘斐章,队员有石联星、王逸、许秉铎、许之乔、朱琳等人。第九队因故未能建成。第十队队长为辛汉文、王惕予。第十一队队长为侯枫。第十二队队长为凌鹤、尤竞。第十三队队长为陈铿然。救亡演剧队的骨干力量大多是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进步的戏剧、音乐、美术工作者,以及一些热爱文艺的爱国学生。

《保卫芦沟桥》之一幕

《屈原》之一幕
救亡演剧队足迹遍布于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湖北等地,深入群众之中,主要演出一些短小灵活的街头剧、活报剧、独幕剧等,受到民众普遍的赞赏。
演剧队不但是编演抗日戏剧的演出团体,也是抗日的宣传队、工作队。他们一边演出,一边进行宣传动员,一边为抗战募款。还采取各种艺术形式,如歌咏、美术、讲演、办壁报等进行宣传工作。演剧队也是工作队,参加看护伤员、组织民工运输军需品、挖战壕、调查户口、家庭访问等工作。
第三厅成立后,设立了艺术处,并于1938年8月宣布成立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等组织。上海救亡演剧队也列入抗敌演剧队,并将上海救亡演剧队的业务民主、生活民主、经济民主等管理方式和民主作风延续下去,有条件的演剧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这十个抗敌演剧队分赴各地,为前线战士演出,为医院伤兵演出,在城镇、工矿、学校进行宣传演出和辅导工作。从流动演出的地域之广,历时之久,演出剧目影响之大等方面看,第三厅领导的抗敌演剧队始终是抗日剧运的骨干队伍。
另外,还有各省市抗敌后援会移动演剧队、军队的士兵剧团和地方上的群众演出团体以及教育部组织的巡回演出队、军委会政治部直属的教导剧团。国民政府教育部也曾组织两支巡回戏剧教育队。
演剧队是在抗战戏剧运动中产生、发展的一支战斗的话剧队伍,这是世界戏剧史所罕见的戏剧现象。它是演剧队,也是宣传队,也是工作队。它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不但为中国话剧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而且在中国的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斗争中完成了中国话剧的历史使命。它培育了整整一代革命的优秀的话剧工作者,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话剧艺术家,并且坚持和缔造了中国话剧的战斗传统。

《国家至上》第一幕

《飞将军》之一幕(国立戏剧学校)
三、演剧方式的创新:创造了独特的民族话剧新形式
夏衍在抗战初期曾经指出,抗战将会给话剧带来新的生机和新的创造。他说:“二十年来束缚着中国新戏剧运动之开展的枷铐,终于在抗战爆发的那一瞬间粉碎了,我将这一次神圣的抗日战争譬喻做摧毁一切旧秩序旧体制,和发源于这秩序体制的观念上的束缚阻碍的雷雨……敌人的炮火与炸弹不仅轰毁了温室的花棚,那些娇嫩的野草接触到了中国的土壤和空气,同时也还炸破了僵硬荒废的地壳,而使那些抛弃在中国之原野上的植物有了生根和滋长的机会。”
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无论是报纸还是广播都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因此受众很少。而话剧此刻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大众传媒的作用。面对大众的戏剧,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满足他们的需要,贴近他们的生活。夏衍则提出要“创造各种形式,产生各种内容的便于上演的剧本。像不要舞台布景,灯光等,一些火把就可以在广场或者农场上上演,甚至于不要剧本,像活报,时事报告,手势哑剧等等。”[1]
演剧队适应演出的需要,充分利用当地的环境,创造出了多种新颖的演出方式,如街头剧、广场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谐剧等。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时期出版、发行的一千两百余部剧作中,街头剧就有近百部。《放下你的鞭子》(崔嵬等)、《三江好》(吕复等)、《八百壮士》(王震之、崔嵬)、《流寇队长》(王震之)等都几乎演遍了各战区与大后方的广大城镇以及农村。其中,流传最广最受人们欢迎的是由崔嵬改编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
活报剧,意即“活的报纸”,它以速写手法和喜剧的手法迅速反映时事。“茶馆剧”则是根据西南地区百姓有到茶馆喝茶的习惯,演员扮作茶客,分别入座,造成故事,引起其他茶客的注意,很自然的进入角色。“游行剧”是采取化装游行进行宣传的戏剧形式:1938年10月中国首届戏剧节期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重庆大街上,在成千上万的观众的簇拥下,演出了《汉奸和十字舞》《争取最后的胜利》《大家一条心》等剧目,轰动整个山城。
这些广场剧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突破剧场演出的局限,推倒了“第四堵墙”,使戏剧更贴近观众;二是打破舞台的局限,使演员忘了是演戏,观众忘了是在看戏,演员、观众的思想感情融为一体,演员与观众之间,观众与观众之间,形成多向的心灵互动和情感的交流。三是广场戏剧演出效果,具有狂欢节的特色,它把戏剧的宣传功能与宣泄功能统一起来。
四、根据地的戏剧民族化、大众化成就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根据地的戏剧民族化走向自觉发展的阶段,以新秧歌剧、新歌剧运动和旧剧改革为重心,构成根据地戏剧民族化、大众化的靓丽景观。
秧歌原本是在我国北方广大农村流行的一种群众性艺术形式。延安的戏剧工作者利用和改造了这一民族艺术形式,从题材选择、人物刻画、情节安排、语言运用,到音乐设计、表演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番去粗取精的加工,创作出了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色彩的秧歌剧。在1943年春节的延安秧歌集会上,涌现出《向劳动英雄学习》《拥军花鼓》《拥军爱民》《红军万岁》等明显具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性质的新的秧歌剧。尤其是“鲁艺”创作的《兄妹开荒》,唱出根据地生活的新气象,唱出了“边区的人民吃得好来,穿也穿得暖,丰衣足食,赶走了日本鬼呀,建设新中国”。轰动了延安,演遍了根据地,并兴起了新秧歌剧运动。这一期间涌现出像《夫妻识字》《一朵红花》《牛永贵挂彩》《赵富贵自新》《刘二起家》等新秧歌剧。由于秧歌本来就广泛流传于民间,这些新编剧目在内容上又通俗易懂、贴近现实,形式上载歌载舞、热闹欢快,显示出“所有中国过去的戏剧所没有过的一种愉快、活泼、健康、新生的气氛”。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对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周扬当时曾撰文指出:“创作者、剧中人和观众三者从来没有像在秧歌中结合得这么密切。这就是秧歌的广大群众性的特点,它的力量就在这里。”[2]
正是这些群众性的秧歌剧运动,给了戏剧工作者极大的启示,引导他们在改造旧秧歌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民族新歌剧。“鲁艺”在继大型秧歌剧《惯匪周子山》的成功探索之后,于1945年1月创作演出了新歌剧《白毛女》,成为解放区戏剧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优秀作品,也成为五十年来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艺术经典。它的成功经验,也促成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无敌民兵》《王秀鸾》《刘胡兰》《赤叶河》等一批新歌剧的诞生。
在延安的文艺运动中,还掀起了一股旧剧改革的浪潮。早在1939年,张庚就在当时的《理论与实践》上发表了《话剧民族化和旧剧现代化》的文章。1942年,解放区开始了改革旧剧的实践。1942年9月,一二师战斗平剧社到延安演出了新编平剧《嵩山星火》之后,与“鲁艺”平剧团及胶东平剧团等合并成立了延安平剧院,而后陆续演出过新编的和传统的剧目《岳飞》《梁红玉》等。1944年元旦,中央党校首次演出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这是对旧剧进行的一次大胆的革新尝试。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看了《逼上梁山》之后写了著名的《致杨绍萱、齐燕铭》的信,提出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以此为开端,继《逼上梁山》之后,延安平剧院又编演了《三打祝家庄》(任桂林、魏晨旭、李纶执笔)。此外,其他各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也改变了以往轻视传统戏曲的观念,投入到各种地方戏曲的改编中去,创作了一批新编的秦腔、山西梆子、山东梆子、淮剧、扬剧等新编剧目。晋西北根据地成立了晋西民间戏剧研究会,山东成立了国剧研究会,并提出了“改造旧形式,团结旧艺人”的口号。
话剧的民族化、大众化,表现在话剧在面向工农兵的生活中,写出一批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如《李国瑞》《同志,你走错了路》等。根据地戏剧的民族化大众化,引领了新中国戏剧的发展,
五、历史剧——民族精神的载体
中华民族素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勇气概。面对日寇的侵略,剧作家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寻找民族英雄和民族传统,以“发挥其更大的力量,作民族的怒吼”。在全民族的抗战中,剧作家把目光转向历史,转向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转向英勇抗敌的历史事件,从历史中汲取力量,从历史中汲取民族精神,涌现出历史剧创作的浪潮。例如,以郭沫若的《屈原》《堂棣之花》《虎符》《高渐离》为代表的战国史剧;以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和陈白尘的《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史剧;还有以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于伶的《大明英烈传》、郭沫若的《南冠草》、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等为代表的南明史剧。这些剧目,以古喻今,借古讽今,宣传团结对敌,暴露黑暗统治,讴歌爱国主义,鞭挞投降变节,演出效果十分强烈。
在众多的历史剧中,以郭沫若的5幕话剧《屈原》最为著名。屈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诗人,其诗作《离骚》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郭沫若首次将其形象塑造于舞台之上。他以神来之笔,在从清晨到午夜这段非常有限的舞台时空里,概括了这位诗人一生的悲剧。于此,郭沫若塑造了一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横遭陷害,处境艰难,“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者的形象。他浪漫的诗情,高洁的心灵,伟岸的人格,光照千古。史剧谱写了一曲屈原的颂歌。 根据《离骚》的诗意,郭沫若在《屈原》中,虚构并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美丽的女性形象,即少女婵娟。作为侍者,她一直守护在屈原身旁,至真至纯,蔑视权贵,是道义美的化身,最后饮下南后加害屈原的毒酒,含笑身亡。《屈原》于1942年首演于重庆,轰动山城。
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取材于太平天国运动,选取导致其由盛而衰的关键性事件——杨韦内讧,作为中心内容。由此,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走向衰颓、困顿。面对惨烈的事态结局,洪宣娇痛悔不已。她惊呼:“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阳翰笙的历史剧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在其另一部史剧《草莽英雄》中,他塑造了一个只讲义气,盲目自信,对凶险的敌人放松警惕的农民革命者罗选清的形象,最后,此人为清兵所杀。阳翰笙的历史剧波澜壮阔,冲突激烈,人物形象鲜明生动。他透过历史悲剧警示世人,弘扬正义。
显然,历史剧的兴盛,是抗战戏剧民族化的体现,也是民族化的辉煌成就。
六、现代民族话剧的高峰
抗战戏剧的民族化,绝非是狭隘的民粹主义,也不是家有敝帚的闭关主义。民族化,一是“化”中国艺术的传统于话剧之中,二是“化”外国戏剧的精华于中国话剧之中。
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经由五四时期的滥觞,30年代的奔涌,到了40年代,已然成为浩荡之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和高水平的剧作,开启了话剧民族化的进程。曹禺、夏衍等人的剧作,因其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而受到观众的欢迎。而在抗战时期,中国的话剧工作者,凭着话剧民族化的自觉,把中国的现实主义推向一个高峰,并最终构筑了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
曹禺在30年代初一鸣惊人之后,在抗战中又大显身手,写了《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独幕剧《正在想》、多幕剧《蜕变》《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成功地改编为话剧。
《北京人》是曹禺创作的高峰。它虽然不是直接描写抗战,却透过一个曾经显赫而渐趋衰败的官宦家庭,对中国的社会作了更深入的文化思考。曹禺的创作艺术也更加成熟了,人物的性格和复杂的心理,都在十分自然的生活状态下演进着,而深刻的主题和文化内涵就潜藏在其中。在《北京人》中,契诃夫戏剧的神韵融合在曹禺的个性的创造之中。
30年代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已经是优秀的诗化现实主义剧作,而1942-1945年间,他创作的《水乡吟》《离离草》《法西斯细菌》《芳草天崖》等多部话剧,更是将平凡的现实生活戏剧化,描写普通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人生的艰难中,所显示出的细腻的心理波动,含蓄的情感状态以及灵感的复杂性。
在抗战中,一位年青的剧作家崭露头角,并显示了浓郁的诗情和雄健的笔力,他就是吴祖光。从1937年到1947年,他创作了《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少年游》《捉鬼传》等一批话剧剧本。《风雪夜归人》表面上写的是爱情悲剧,实际上张扬的是人文思想。剧中的感情戏,写得深婉动人,充满着浓郁的诗意。
宋之的的《雾重庆》创作于1940年,上演后获得了很大的声名。它描写的是,战时重庆的社会现实渐渐消磨了一群年轻人的热情与斗志,使他们卷入碌碌无为的生活之中,在为衣食奔忙中挣扎,沉沦。这些原本应当年青有为的大学生,却蹈入了理想被毁灭,情感受挫折的可悲处境。剧作以此揭露了社会现实的腐朽和黑暗,同时,也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与妥协性。显然,这样现实主义的杰作,对现实的观察和揭示是更加深化了。
此间,李健吾、于伶等都有佳作问世。
抗战以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由于其政治黑暗,官僚腐败,激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掀起一股讽刺喜剧创作的浪潮。
陈白尘是喜剧创作的先锋,1940年,他出版了喜剧集《后方小喜剧》。1942年创作了《结婚进行曲》,写一对年轻人既要追求人身权利,又要反抗庸俗的社会积习,由此陷入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尴尬境地。政治讽刺喜剧《升官图》,更代表着中国现代讽刺喜剧的最高成就。它借鉴了《钦差大臣》的喜剧构思和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丑角造型,该剧的中心内容是梦境,但故事本身却相当完整。它对吏制腐败、恶人横行、庸俗无耻的社会现实做了淋漓尽致的暴露和嘲讽。
老舍在抗战时期写了大量的话剧,他的四幕话剧《残雾》写于1939年,取材于重庆的社会现实,剧中的冼局长道貌岸然,一面高喊抗战,一面贪财、好色、弄权。他不仅利用职权玩弄女性,还与汉奸勾结,为其窃取情报,后来事败被俘,身陷囹圄,不得已供出了女汉奸,而此时这位神通广大的女子,却公然到一位政府要员家中赴宴去了。老舍的喜剧,意在拂去笼罩在抗战形势下的“残雾”,把讽刺的锋芒直刺腐朽的统治。剧中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俏皮。1939年11月,该剧由怒吼剧团在重庆首演。
正是在艰苦的抗战中,剧作家将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精神推向一个高峰。
当前,中国话剧又遇到了一个节点,尤其是最近两三年,成批的形形色色的外国剧目以空前的规模被引进,掀起一阵一阵的浪潮。在这种时候,我们在放眼世界的同时,更要回顾我们民族戏剧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要回顾和总结我们抗战戏剧的历史,提升民族化的自觉,激发民族独创的意志,坚定地走话剧民族化的道路。抗战戏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走了一条民族化的道路,因而使抗战戏剧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历史证明,中国话剧只有适应民族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和大众的需要,走民族化的道路,实现具有民族独创性的创造,中国话剧才能发展和繁荣。
注释:
[1]夏衍.戏剧抗战三年间——祝三届戏剧节并答苏联友人[J].戏剧春秋,1940年创刊号.
[2]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N].解放日报,1944-3-21.
田本相: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郭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