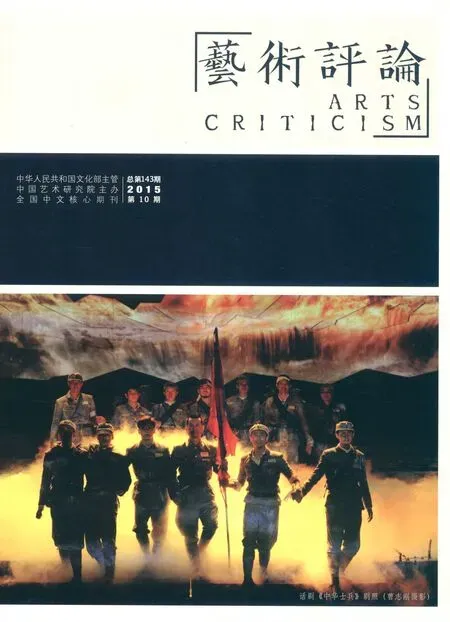抗战音乐的历史“记录”与“记忆”
蒲 方
抗战音乐的历史“记录”与“记忆”
蒲 方
历史是人们对过往的“记录”,知晓历史则构成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当年的“记录”也许是五花八门,倘若都能留存至今,那么人们将得到对那段历史丰富的“记忆”。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全国上下开展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一时间《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等历史音乐作品不绝于耳,甚至苏俄时期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都频繁上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不仅向社会推出了《正义之声——100首优秀抗战歌曲集》[1],还向广大民众推出了“我最喜爱的十首抗战歌曲”的网络评选活动,最终构成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首的10大抗战歌曲[2]。网络评选所构成的名单很复杂,但总的倾向非常清晰,10首作品主要是多年传统教育及音乐教育的结果,大多数为百姓平时能接触到或在学校学唱过的。“熟识”在这其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在当年起到巨大作用的优秀歌曲,如《抗敌歌》(黄自曲)、《长城谣》(刘雪庵曲)、《歌八百壮士》(夏之秋曲)却由于公众知晓程度低而名落其后。其实即使是从事专业音乐工作的人也未必能回忆多少,因此,抗战音乐的重新推出对帮助人们寻回那个战火纷飞年代的历史记忆,从而深刻地思考今天及未来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搜索历史记录,感受当年战火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兴音乐(音乐教育)在多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首先是歌曲创作摆脱了“学堂乐歌”依曲填词的方式,在声乐创作领域中有艺术歌曲、学校歌曲、合唱曲、表演性歌曲等多种体裁的创作出现。其次从中、小学音乐课的普通音乐教育,发展到师范院校音乐系科的设置,最后上升到专业音乐学院(国立音专)的建立,使新音乐基本纳入到系统化发展的轨道上,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0至40年代是新音乐蓬勃发展、不断繁荣的时期,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较长的群众性爱国音乐运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可称为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事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阶层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国立音专作曲教授黄自马上创作了合唱作品《抗日歌》,并很快得到演唱。《抗日歌》是当时最早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合唱曲。由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禁言“抗日”,该作品在发表时被迫改名为《抗敌歌》。这首合唱曲不仅做为国立音专合唱课教材演唱,深受学生们的喜爱,还被当做最早的抗日歌曲刊载于当年及现在的各种抗战歌集上。其实,“ 九一八”事变后国立音专的校长萧友梅先生也立即创作了《从军歌》,著名作曲家黎锦晖在10月10日、15日和18日的《申报》先后发表了《义勇军进行曲》《追悼被难同胞》《向前进攻》3首歌曲[3],但后世影响力均不及黄自的这首《抗敌歌》。
1933年,中国共产党左翼文化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它是由著名剧作家田汉发起的,主要成员有聂耳、张曙、任光等。他们通过学习苏联音乐创作的经验,探讨并开始创作第一批带有进步意义的作品,如聂耳的第一首工人歌曲《开矿歌》等。1934年又进一步成立了“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他们将自己的创作与进步的电影、戏剧结合在一起,在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同时,突出了抗日救亡内容的创作。聂耳是他们当中最为出色的,他为影片《大路》《桃李劫》《新女性》《风云儿女》和话剧《扬子江暴风雨》《回春之曲》创作的歌曲,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风云儿女》中的《义勇军进行曲》,抒发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坚强决心和顽强斗志,是救亡歌曲创作中最响亮的“吼声”,这些作品通过银幕、舞台、唱片、广播等传播途径,迅速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1935年,随着日寇对内地的层层逼近,群众的抗日歌咏热情不断高涨。特别是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群众性歌咏热潮。就全国来说,当时的抗日救亡歌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起来。北京、天津、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数十个城市的青年学生,都组织了不同规模的歌咏团体,并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1935年《良友画报》刊登图片:“北平大中学生联合组织了歌咏团,前月在太和殿开始第一次合唱,全团共男女六百人,其伟大为中国以前所未有。演奏会之日,听众人如山海,为北平最近之盛事。”[4](见图1)

图1 《中国最大歌咏团》,太和殿前歌咏团合唱时之壮观,《良友画报》,1935,第106期。
在上海相继成立两个救亡演出团体:“民众歌咏会”和“业余歌咏团”。“民众歌咏会”是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刘良模发起的,得到了左翼音乐工作者的支持,参加者大多是上海的教员、店员、职员及大中学生,人数从最开始的九十余人,发展到后来的三百多人。到1936年,会员增至上千人,而且在广州、香港等地建立了分会。它通过比赛会、广播、音乐大会等演唱活动,扩大救亡歌曲在民众中的影响。刘良模在《青年歌集》序言里曾写道:“民众歌咏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军号,号声在那里,民族解放的斗士也在那里。”“我们不是为唱歌而唱歌,我们要为民族解放而唱歌。我们要用唱歌的方法来唤醒民众,组织民众。”[5]“业余歌咏团”是由“左翼剧联音乐小组”发起和领导的,由吕骥、沙梅等主持,吸收上海左翼影剧、音乐界人士以及中、小学师生和进步青年。除经常举行歌咏活动外,还分头到工人、学生、市民中教唱救亡歌曲,对上海的群众歌咏运动起指导作用。除以上两个团体外,在上海还有大小几十个歌咏团体。1936年1月成立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进一步把救亡歌曲传播到平津附近的各县城乡。上海、广州、武汉、开封、济南等地也相继举行了同样的活动。香港和国外华侨也被卷入到这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之中,香港“民众歌咏会”成立不到三个月,就发展成一个拥有三十多个小型歌咏队的抗日救亡歌咏团体。
抗日救亡歌咏热潮促进了救亡音乐创作队伍的成长和救亡歌曲创作的丰富。到“一二·九”运动前后,大批新的救亡歌曲产生了,其中有《五月的鲜花》(阎述诗曲)、《救国军歌》(冼星海曲)、《新编“九一八”小调》、《中华民族不会亡》(吕骥曲)、《救亡进行曲》(孙慎曲)、《打回老家去》(任光曲)、《保卫国土》(张曙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孟波曲)、《松花江上》(张寒晖曲)、《大众的歌手》(何安东曲)等。当时的报刊也均以相当的篇幅报道救亡歌咏活动,刊登救亡歌曲,并对救亡音乐创作进行理论探讨。到《八一宣言》发表之后,救亡歌曲的社会影响与日俱增,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从1936年底至1937年上半年,吕骥、刘良模及“青年会战区服务团”等,奔赴绥远抗战前线,举办“军民联合歌咏大会”和“军官歌咏训练班”。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激发起更多作曲家的创作热情,创作出大量的、形式多样的抗战歌曲,如《大刀进行曲》(麦新曲)、《武装保卫山西》(吕骥曲)、《游击队歌》(贺绿汀曲)、《歌八百壮士》(夏之秋曲)、《丈夫去当兵》(张曙曲)、《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冼星海曲)、《长城谣》(刘雪庵曲)等。到1938年前后,各种抗战文化组织和歌咏团体云集武汉地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于同年1月7日,成立了包括全国音乐界各方面代表的“中华全国歌咏协会”。4月1日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第三厅”),这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机构。冼星海、张曙在第三厅负责抗战音乐工作。在他们的领导下,通过举办“抗战扩大宣传周”“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歌咏火炬游行”“抗战献金音乐大会”“九·一八纪念音乐会”等,发动起拥有数十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群众歌咏活动。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一文中写道:“抗战以来,文艺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也可以说:‘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6]这段话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抗战歌曲深入人心,广泛流传的动人情景。当时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组成了数以百计的“战地服务团”“救亡演剧队”和“抗战歌咏团”,走向战区和内地,深入到前线、工矿和乡村,传播和组织救亡歌咏。“新安旅行团”和“孩子剧团”是这些抗战宣传团体中以少年儿童为主的团体;他们长期坚持战斗,克服许多困难,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在开展抗战歌咏活动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见图2)

图2 上海市“八一三”歌咏队。《抵抗画报》,1937年,第2期,第6页。原注:上海市“八一三”歌咏队,已于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举行成立大会,到团员数十人。该团不日将赴各地宣扬救亡歌曲,警醒国人一致抗日。
40年代,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重庆和延安成为两大抗战文化的中心,音乐家们坚持着各自的抗战音乐创作,重庆努力打造战时陪都的一切文化设施和氛围,新的音乐学院、交响乐队、歌剧学校、电影摄制厂纷纷建立起来,国共两党均在此留下了新样式的抗战音乐作品,如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垦春泥》、张定和的抒情歌曲、陈田鹤钢琴曲《血债》、马思聪《第一交响乐》、陈田鹤的清唱剧《河梁话别》、应尚能的歌剧《荆轲》以及黄源洛的大歌剧《秋子》等。据相关资料统计:“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音协”)、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中国音乐学会、浮图关中央训练团音干班、中央大学艺术系、军政部陆军军乐学校、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中央政治学校歌咏团、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中大、重大联合组建的嘉陵歌咏团、二十四兵工厂莲光歌咏团、唯歌歌咏团、龙吟歌咏团、南开中学励志学术研究会歌咏团、重庆民众歌咏会、青年歌咏社、重庆育才学校音乐组等等,上下一致,会合成一股巨大的洪流,使抗战的歌声在陪都城乡各地高唱入云,民族音乐弦歌不辍。到1942年3-4月和1943年3-4月,被定为陪都的两个“音乐月”,和陪都戏剧的“雾季演出”相衔,使重庆抗战的音乐宣传表演活动达到了高潮。”[7]这说明通过文化宣传达到鼓舞斗志,加强民族自强心的救亡启蒙思想随着战争的发展在不断深入。
延安的音乐家们沿着聂耳、冼星海所开创的创作道路,继续深入学习民间音乐,不断探索新音乐各种形式的发展,在秧歌运动及歌剧《白毛女》等作品的创作中,努力实现着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传导的精神。此外,海外华侨也开展了救亡歌咏活动。在法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缅甸等地,均建有各种救亡歌咏团体。其中以任光在新加坡举办的“民众歌咏训练班”和他辅导的“铜锣合唱团”影响较大。1940年后,刘良模在美国华侨中组织了“华侨青年歌唱队”,并与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合作,录制了以《起来》为题的一组中国抗战歌曲和民歌唱片,其中包括罗伯逊用中、英文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
二、加深历史记忆,体会时代风格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战争已远离我们70年了。当时战争的伤痛、人民的哭喊、战火的纷飞都随时间的远去而渐渐消失了,我们在和平的年代里愉快地生活着,对于那场14年的人间劫难似乎无法勾起今天人们更深的感知。我们常常能看到今天的某些“艺术创作”在对历史无知中显得那么苍白,大量抗战题材创作很难深刻地表现这场中国近代历史上历时最长、范围最广的民族战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多年受某些思想影响,回避或忽视某些历史真实情况,造成民众对这段历史理解的偏差是最明显的问题。随着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步步推进,无论是史学界,还是音乐史学界,都产生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足以推翻以往很多不实的历史记录,足以引起我们对那个年代的重视。然而,当今科技的进步使得艺术制作环节及信息传播手段不断加速,人们越来越对技术产生强烈的兴趣,而忽略了对人文历史的深刻理解,粗制滥造、肤浅浮华的艺术作品(类似“抗日神剧“的出现)再一次摧毁了人们对新历史研究成果的关注。
在今年出版的《正义之声——100首优秀抗战歌曲集》和《抗战歌选——1931-1945》[8]都刻意挑选过去较少提及的作品,如吴伯超的《中国人》、任光《抗敌歌》、黄友棣《杜鹃花》、马思聪《控诉》、汪秋逸《淡淡江南月》、何安东《大众的歌手》等。事实上,很多抗战歌曲不断地向人们诉说着战争带来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艰难生活,由此而创作的思乡歌曲、流亡歌曲是抗战歌声中非常具有感染力的,这些音调帮助人们拾回那些战争年月的痛苦。
此外,描写抗战军民英勇战斗的歌曲也有不少。整个抗战过程中,面对日本军队强大的空军力量,以及对中国惨无人道的狂轰滥炸,中国空军以弱抵强、英勇机智的战斗事迹为战争中的中国军民带来巨大的精神鼓舞,空军将士英勇对敌的英雄事迹竞相传颂。因此抗战中曾出现过几十首空军歌曲,如冼星海的《中国空军歌》、何士德《中国空军战歌》、贺绿汀的《飞将颂》、夏之秋的《远征轰炸歌》等。特别是刘雪庵的《中国空军歌》[9]当年得到广泛传唱。(见图3)除了空军歌曲,还有《巷战曲》(陈田鹤)、《挖战壕》(何士德词曲)、《八路军的铁骑兵》(贺绿汀曲)、《出征歌》(李抱忱曲)、《军训歌》(满谦子曲)、《保卫卢沟桥》《保卫大武汉》(郑律成曲)、《保卫大上海》(刘雪庵曲)等,这些音乐都是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的战斗生活,热情地歌颂了抗日军民英勇杀敌的顽强斗志。

图3 《中国空军歌》[10]刘雪庵曲《战歌周刊》1937年,第1期, 第7页。
此外,重庆40年代初轰动一时的大歌剧《秋子》(图4)[11]于去年12月由南京艺术学院复排演出,今年5月山东师范大学又复排了江凌、刘雪庵合作的小歌剧《流亡曲》(1938)。抗战时期是中国歌剧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积累了大量作品,而这些作品不仅产生在歌剧《白毛女》之前,而且在艺术手法上努力探索民族风格,期望创造出中国风格歌剧作品。
面对抗战时期数以万计的音乐作品(歌集、器乐及戏剧作品等),今天的纪念仍深入不到或无心正视,那么带来的就不仅一两部肤浅的抗日神剧,更深层地影响到民众对民族历史的理解,特别是模糊、扭曲对那段历史(音乐史)的公正认识,这是对当年为民族解放救亡图存的先烈和遭受14年战争磨难的中国百姓的最大不公。因此,只有认真攫取和找回更多的历史记忆,才能真正引导和焕发民众以更宽阔的心态来面对未来,创造未来。

图4 战时轰动大后方的歌剧秋子。《艺文画报》,1947年,第1卷第11期,第20页。
三、纵览音乐发展,贴近人民精神
通过对抗战音乐历史的回顾,我们看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歌咏运动在鼓舞和动员人民大众投入抗日救亡爱国斗争时所发挥出的巨大号召力,正如冼星海在《鲁艺与中国新兴音乐》一文中说的:“这种雄亮的救亡歌声为中国几千年来所没有,而群众能受它的激荡更加坚决地抵抗和团结,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件音乐史迹。”由于新音乐在抗战中所发挥出的巨大的社会作用,使它在这一历史时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是三四十年代音乐发展的重要标志。
抗战音乐(歌曲)之所以这样深入人心,很重要的一点不仅在于它产生在中华民族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唱出了当时所有中国人“抗日救国”的共同心声;还在于无论是黄自、陈洪、吴伯超、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还是聂耳、任光、张曙、吕骥、马思聪等,努力走出自我艺术的“象牙塔”,用“新音乐”的语言来唤醒中国大众,奋起抵抗日寇的决心。他们都是借鉴了西方音乐中进行曲的体裁和音乐风格,利用了群众歌咏这种“新音乐”形式,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必须使抗战音乐接近大众的思想情感,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民间音乐语言,才能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这种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民族性、大众性的音乐风格的确立,使“新音乐”从当时学校音乐领域走向更广阔的创作天地,为“新音乐”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也造就出如冼星海这样一批优秀的人民音乐家,以及如《黄河大合唱》这样辉煌的不朽篇章、通俗易懂的群众歌曲精品。抗战时期是近代中国音乐史上群众歌曲发展的顶峰时期,它不仅显示了群众歌曲的巨大威力,同时也展示了群众歌曲独特的艺术风采。著名指挥家严良堃曾在《我与〈黄河〉60年——答黄叶绿同志问》一文中说道:“《黄河(大合唱)》的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这巨大的能量根本无法用现在庸俗的“价值”来衡量。这说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知名度和劳动的价值并不等于他向社会索要的“价格”,而在于它奉献给人民、并留存在人民心中的真正的精神财富。”[12]我们站在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事实上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坚强意志下,在国际反法西斯保卫和平的共同努力下获得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以及大量抗战音乐作品正是站在这样广阔的群众基础之上,才获得了人民的肯定和支持。正是“人民性”充斥在所有抗战作品中,作曲家个人意志、个人风格在国破家亡的紧迫现实生活面前自觉地与民族命运、百姓愿望统一在一起,结成强大的情感战线。无论是器乐作品还是声乐作品,抒发时代的心声——“抗日救国,民族解放”,成为当时广大中国人民投身抗战的有力“武器”。因此,正视历史,关注民众,是找回当年艺术创作澎湃之态的秘钥!
注释:
[1]《正义之声——100首优秀抗战歌曲集》(音响)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出品,2015年7月。
[2]十大抗战歌曲名单:《义勇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松花江上》《毕业歌》《南泥湾》《歌唱二小放牛郎》等。
[3]参见孙继南.黎锦晖评传[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20;101-102.
[4]《中国最大歌咏团》:太和殿前歌咏团(由李抱忱、范天祥组织)合唱时之壮观[J].良友画报(影印本),1935(106).
[5]刘良模.回忆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上海青运史资料1982年第三辑.共青团上海市委青运史研究组编(内部材料),1982:7.
[6]丰子恺.谈抗战歌曲[J].战地.1938(4):98.
[7]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编著《重庆抗战文化史》“二、音乐:民族解放的最强音”,团结出版社,2005:352.
[8]《抗战歌选——1931-1945》(乐谱集及音响),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品,2015年9月。
[9]《战歌周刊》1937(1):7.
[10]该曲首次发表是在1937年,但在40年代又根据国民政府航空新闻处处长简朴的词做了调整,流传甚广。
[11]歌剧《秋子》(陈定编剧,臧云远作词 黄源洛作曲)创作并上演于1942年,此图为战后复演报道。《战时轰动大后方的歌剧〈秋子〉》。《艺文画报》,1947-1(11):20.
[12]黄叶绿编.黄河大合唱纵横谈[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63.
蒲 方: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陈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