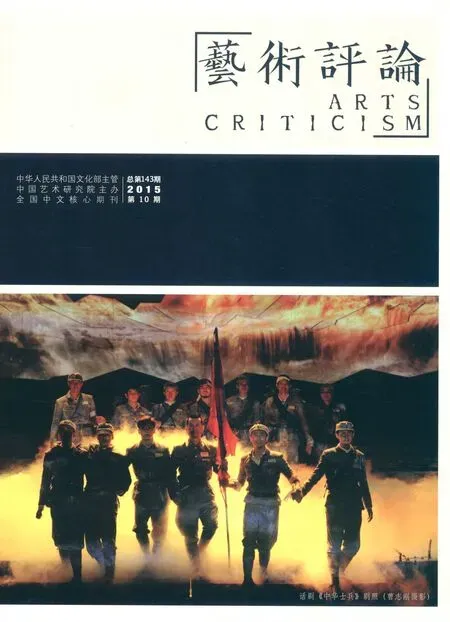《三体》:我们时代的隐喻和精神史诗
徐 勇
《三体》:我们时代的隐喻和精神史诗
徐 勇

刘慈欣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刘慈欣的《三体》(即《地球往事》三部曲:《三体》《黑暗森林》和《死神永生》,俗称《三体》,下同)获得世界科幻文学大奖雨果奖,《三体》也逐渐进入学术研究的殿堂(所谓登堂入室),而不仅仅被视为亚文学或类型文学的代表。这当然是中国科幻文学的极大成功,但若仅仅把它视为科幻文学的崇高经典,或是通过纳入纯文学的范畴以抬高其地位,则又是歧途误区。因为显然,《三体》的出现及其提出的问题,早已超出了科学范畴本身,也非科幻文学或者说纯文学所能涵盖。对于《三体》,其内容的丰富和驳杂,以及视野的宏阔,是任何一种单一的文类所不能比肩的。但也是这驳杂,常常使得我们顾此失彼、左右徘徊。这就有必要采取抽丝剥茧的方法。就《三体》而言,它的核心问题在于,它提出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终极问题,但又借助于科幻这一文体形式表现出来,其中的悖论和矛盾为我们进入此一文本提供了便捷且行之有效的角度。
一
《三体》的出现,无疑与中国作为大国崛起有着某种时间上同步性的特征,这从其中拯救世界和人类文明的英雄主人公汪淼、罗辑和程心等皆为中国人即可以看出。这一时代性征反映了作者对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充分信心及其因之而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必然重整的期望,但另一方面我们从小说中又感到一种作者所特有的对人类的深深的绝望以及因之而来的深刻反思。有意味的是,这一反思,早已超出人类中心主义的高度,也非民族国家的本位主义立场,这一反思,因其借助于科幻文学这一文类和形式,毋宁说带有宇宙的视角,因而也更具有终极性和根本性。
就历史的角度看,自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先贤们(诸如梁启超、鲁迅等)一直都在崇尚科学的旗帜下呼唤科学幻想小说的到来;“五四”前后,乃至80年代初,皆曾出现过科幻文学写作的浪潮。但我们很快会发现,中国科幻文学的写作与科学的发展之间始终存在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换言之,它虽借助于科学的想象而发展壮大,但也存在着对科学的反思乃至批判。这一情况表明中国的科幻文学还未充分发展就已表现出反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的面向,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所不得不面对的:我们在“向科学进军”的时候,科学在西方也已显示出不可化解的矛盾。这是我们理解《三体》的重要前提。
事实上,在《三体》之外,刘慈欣一直都在展开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思考。《时间移民》通过设计一个面向未来不断展开的时间旅行的结构,以表明机器文明具有“非人”或“反人类”的特征;但刘慈欣并没有停留于此,而这,也是他区别于中国其他科幻作家的地方。与王晋康、韩松、何夕等都表现出对科学技术的“异化”作用的反思和批判不同的是,刘慈欣以此为起点,通过把诸如人道主义、爱与美及其人性之恶等等人类哲学命题置于宇宙的高度和层面展开,从而在根本上表现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和对人类诸命题的反思。
《三体》的反思性首先表现在其特有的结构和文体中。这从其书名《地球往事》即可以看出,这是把地球的故事放在宇宙的层面加以表现,地球的故事因而具有了宇宙社会学的含义,而小说时空结构关系上的“将来过去时”,也赋予《三体》整体上的反思总结之意。所谓“将来过去时”,这是刘慈欣独创的一种时态,其得来显然有赖于科幻文学的文体本身及其想象的力量。这里所谓的“往事”并不是今天之前的“往事”,而是从将来的角度回溯中的“往事”,这一“往事”发生在今天(当下)之后地球毁灭(即将来)之前。时间在这里是以“今天—过去—将来”的逻辑演变的。换言之,这样一种叙述,是在今天和将来之间的两端游移,这是一种立足于当下且以将来为起点,从将来的角度对当下展开的反思。当下意识、将来视角和反思立场的结合使得这一系列小说具有了某种超出一般科幻文学和纯文学的高度。
但《三体》并非仅仅意在反思科学,它把对科学的反思糅合进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之中,其后来进入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某种程度上也正源自于此。如果说叙述的起点并非无关紧要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人类的一系列灾难皆源自于人类自身:人性的恶是人类毁灭自身的根源。通过阅读《地球往事》第一部《三体》,我们知道,人类文明的一系列灾难皆肇始于叶文洁向外太空发送的地球文明信号,由此引发了三体文明同人类文明的宇宙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太阳系的毁灭。表面看来,这是叶文洁的一次极其偶然的行为而引发的人类危机,她是人类的罪魁祸首;但通过梳理她的人生经历便会看到,是人性之恶与历史(“文革”)之痛使她产生对人类文明的怀疑和绝望,只不过,她所期盼的解决之道不是己疾自医,而是寄希望于更高级的文明的介入:“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她在发向飞向太阳的信息中如是说。
但更高级的文明就真地能够拯救地球文明吗?显然这是刘慈欣在这部系列小说中始终思考的核心问题所在。确乎,人类自身的疯狂、邪恶与非理性已使得人类文明对地球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两次世界大战、“文革”、发展主义的杀鸡取卵,等等,尽皆如此。对于这些罪愆,显然,仅仅寄希望于主或上帝的惩罚与救赎是不能够的,那么,寄希望于更高级的文明呢?刘慈欣在另两部短篇《诗云》和《乡村教师》中已表现了对这一命题的思考。前者告诉我们,科学再发达,技术再先进,在面对人类的艺术创作如诗歌写作时,仍旧是无效且无能的。这无疑是想告诉我们科技并非万能。而后者则通过中国贫困山区一名乡村教师意外地拯救了人类这一行为,向我们暗示,其虽极其偶然,但这当中爱与责任的力量的伟大却不容忽视。这样来看《三体》就会发现,爱与责任虽在面临生存危机时显得柔弱无力,但并非毫无价值,同样,三体文明的科学技术纵使强大到所向披靡,在面对太阳系的维度灾难时仍旧束手无策,更不用说它在面对人类复杂的内心世界时是那样的恐惧无奈。
二
《诗云》中的命题恰好可以对照《三体》加以解读。不惟艺术创作,人类内心世界的深邃也同样是先进技术所不能窥探的。智子是三体世界发射(或派遣)到人类文明的密探,它无所不能,在它面前任何东西都是透明的,单向度的和简单的,但恰恰是这样一个高级的文明形态,在面对人类内心世界的隐秘和丰富复杂时却是无力无能的。究其原因,是因为人类的内心世界,往往是理性和逻辑思维所不能把握的,小说主人公取名“罗辑”似也包含这一层含义。他所能震慑三体文明的,除了他掌握了宇宙中极具逻辑推理的“森林法则”之外,还在于他那非逻辑的内心及其行为。理性和感性在他身上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并存着。这样来看就会发现,如果说三体文明代表或象征的是一个理性的、平面的和科学的文明的话,那么三体文明同人类文明的冲突,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理性和感性之间的二律背反这一人类永恒命题的投射。科学的发展与人类的感性之间并不总是成正比的,人类控制得了科学,却控制不了自己的内心。三体世界对人类世界的恐惧,正是这一恐惧的表征。“人”的情感的丰富,造成了“人”的形象的难解,其一方面创造了人类艺术的灿烂,一方面也暗藏着人性的无底“黑暗”,而这,恰恰是三体文明对人类所既羡慕又恐惧的,也是人类对自身矛盾态度的根源。小说借三体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复杂态度表达了刘慈欣对这一人类悖论式命题的思考和困惑:理性和科学虽能掌握外在世界,却不能把握人类的内心世界,两者间的矛盾,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人类在发展的道路上能走多远。
但刘慈欣又不仅仅止于此。刘慈欣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仅仅从人类的角度,而是把理性和感性的悖论置于“宇宙社会学”的层面考量。这时,有关爱和美的人类命题,也重新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小说通过对程心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试图告诉我们,爱与美的局限,及其效应。程心当然是爱与美的化身,但当她掌握着决定人类生存命运的按钮的时候,她其实是最为脆弱的。这也就意味着,爱与美的有效性正体现在它们同生存问题的脱节中,一旦彼此缠绕一起,它们的苍白无力便显示出来。科学虽不能控制或窥探人心,但科学可以毁灭人。这正是理性与感性的辩证法。但刘慈欣又试图告诉我们,生存法则虽关乎科学技术,但又不仅仅如此。因为很明显,三体文明的科学技术再先进发达,难保整个宇宙就没有比它更高的文明。以此类推,最终又绕回到哲学上来,即“人类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宇宙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地球往事·三体》,第92页)之类的终极问题。换言之,也就是所谓的“来”和“去”的哲学命题。只不过,刘慈欣在这里所思考的不仅仅是人类的“来”和“去”的问题,它还是宇宙的“来”和“去”的问题,是两者的结合。其中一个事实很明显,即,文明世界即使能制造出光速飞船,逃脱得了维度灾难(太阳系的坍塌),也终逃不脱宇宙在无限膨胀中的毁灭。这也就意味着,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发展到最后,并不是科学技术的问题,而是哲学命题,也即所谓的终极意义上的“来”和“去”的辩证与平衡问题:宇宙的质量守恒。这就又回到了爱与美的人类命题上来。
小说发展到结尾,虽然整个银河系都毁灭了,但关于爱与美以及责任之类的人类命题仍旧存在,小说以程心和关一帆这两个仅存的人类成员的在宇宙中漂流表明了这一倾向。小说中《时间之外的往事》之《责任的阶梯》就是例证。这是程心以“漂流瓶”的形式留给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文明的信息,也是她的对文明世界的思考和对宇宙生存命题——责任的最高阶梯——的彻悟:每个文明发展到 “最后与宇宙的命运融为一体”,这就要求一种最高阶梯的“责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和责任呢?科学理性的高速(或匀速)发展,到最后会导致宇宙在膨胀中毁灭,但如果能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同宇宙的命运融为一体,这样的责任感却可以在终极意义上让宇宙永生。这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人类的爱与美的表现,也是作为理性化身的智子所始终不能理解的(“你还是在为责任活着”,这是她对程心所说的话)。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场宇宙层面的“倾城之恋”,银河系的毁灭正是为了成就其人类的感性及其道德的伟大。
三
这样来看,小说其实是从终极意义上,重新思考了科学、爱与美、人性之善、恶等一系列人类命题。就美的命题而言,其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三体文明向地球舰队发起攻击的水滴,以及智子的形象上。这都是美的极致的体现,但这两个事物却是理性与科学的最极致的结晶;这样的美的形象,虽具有无比完美的线条和黄金比例,但却是毫无感情极端冷漠的。美如果没有感性而仅成为理性之光的表现,这样的美虽具有审美的价值,对于人类却只能是灾难。同样,人性的爱、善及其恶,也是如此。当所有这些命题,在遭遇人类的毁灭与生存这样的宏大命题时,如果仅仅纠缠于纯粹抽象的伦理学与道德感的层面,而不考虑它的具体的历史的语境规定性,这样的人性与善往往也会成为毁灭人类的引线。
当然,刘慈欣并不是反对爱与美,他只是让我们看到,这中间的先后秩序和辩证关系。在他看来,人性的善、美及其恶,它们之间的界限,乃至价值,很多时候都是杂糅一起很难区分的。爱与美,以及人性的善,只有在生存的问题解决之后才有其意义,同样,人性的恶,当它是为了人类的生存问题时,也并不一定是恶。小说中的托马斯·维德和章北海就是例证。同时,刘慈欣也试图告诉我们,虽然人类毁于自身的人性之恶,但也浴火重生于它的爱与善以及责任。这就是所谓宇宙终极命题的人类学内涵,也即所谓的“来”和“去”的辩证法。科学如果不能围绕或以这些问题作为它的思考的起点和终点,这样的科学便不会有任何意义和价值。
这样就可以回到文章的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即《三体》提出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终极问题却又借助于科幻这一形式表现出来这一悖论上来。就《三体》而言,科幻文学的“形式的意识形态”表现在,它通过设置一个宇宙主义的视角,而能抛开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从而使我们能很好地重新审视以人类的主体性建构为基础的一系列命题及其诸如真善美与假丑恶、主与奴、自我与他者等等之类的二元对立范畴。对于这些范畴,仅仅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是很难有深刻的发现的,因为毕竟,解构主义在颠覆这些二元对立时很有效,但在重申这些命题的价值时却是苍白无力的。而如果立足于主体性的立场又只能陷于不可解脱的二元对立的悖论,就像抓住自己的辫子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离开地球一样。科幻文学及其宇宙主义视角的好处正在于,它让我们找到了摆脱地球引力的方式方法,但又不是彻底“逃出母宇宙”(王晋康科幻小说名)。从这个角度看,《三体》就是一个“问题域”,它通过把这一系列命题置于人类面临毁灭的境遇中重新考量,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系列命题的致命的局限,但又不是完全的否定。它从宇宙的角度和哲学的高度重新赋予这些命题以重生的价值,太阳系和银河系虽可能毁灭,但人类的普遍命题却可以永生。这就是刘慈欣和他的《三体》所能给予我们的最大的信心,同时也是一种警示。
徐 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松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