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与反派——读《炽热的改革之心:麦维尔·杜威传》
周 亚
麦维尔·杜威(Melvil Dewey,1851~1931)对图书馆人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甚至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图书馆员。他编制《杜威十进分类法》 (DDC),参与建立美国图书馆协会,创办《图书馆杂志》与美国第一所图书馆学院哥伦比亚图书馆经营学院,这些显赫功绩使杜威的名字响彻图书馆界。对以上这些成就,很多人都可以毫不迟疑地道出。然而,除此之外,人们又对他了解多少呢?迈克尔·哈里斯(Michael H.Harris,下称“哈里斯”)在《麦维尔·杜威:与图书馆事业同在》(Melvil Dewey,his enduring presence in librarianship)一书序文中说:“今天,麦维尔·杜威是现代图书馆员名人堂里最为人所知的一位,尽管他并没有被人们充分地了解。”[1]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性格是温和还是严厉?他是如何确立其图书馆理想的?他在图书馆之外又做了些什么……对于这些问题,韦恩·韦根特(Wayne A.Wiegand,下称“韦根特”)都在《炽热的改革之心:麦维尔·杜威传》 (Irrepressible reformer: a biography of Melvil Dewey,下称“《杜威传》”)一书中一一作答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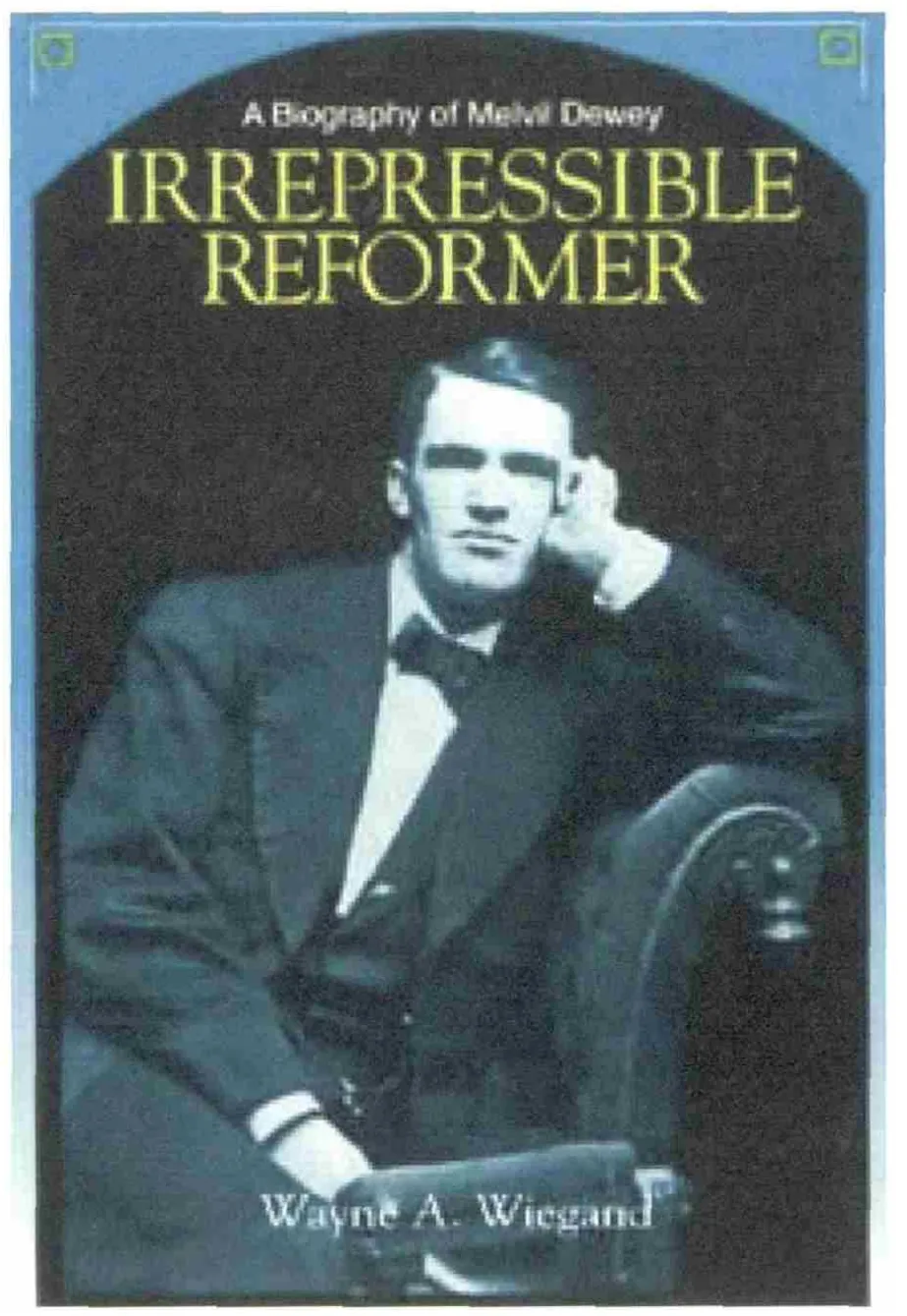
在介绍《杜威传》前,先提一下本书作者。现为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图书情报学与美国研究退休教授的韦根特,由于对图书馆史的杰出成就,是美国图书馆史研究执牛耳者(“dean of American library historians”[2])。作 为一位受过严格史学训练的图书馆史家(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并兼修图书情报硕士学位),韦根特出版了《一个新兴行业的斡旋:美国图书馆协会,1876-1917》 (Politics of an Emerging Profession: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1876-1917)、 《作为宣传的机制:一战期间的美国公共图书馆》 (An Active Instrument for Propaganda: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During World War I)、《杜威传》、《主街公共图书馆:农村腹地公共领域与阅读空间,1876-1956》 (Main Street Public Library: Community Places and Reading Spaces in the Rural Heartland,1876-956)等论著,主编或合编《图书馆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Library History)、 《多元美国的出版文化》 (Print Culture in a Diverse America)等图书[3]。目前他正进行《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民众的美国公共图书馆史》 (‘A Part of Our Lives’: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的写作[4],试图从社会史和大众生活史的角度来研究公共图书馆的历史,践行他所阐扬的“用户生命中的图书馆”的研究取向(library in the life of the user,由Douglas L.Zweizig提出)[5]。
1 扎实的史料与平实的语言
史料是传记写作的第一手材料。自1983年韦根特决定着手撰写传记以来(直到1996年该书才正式出版),他参阅了大量与杜威密切相关的各种资料,包括杜威的论文手稿、日记,与普尔(William F.Poole)、温莎(Justin Winsor)、普特南(Herbert Putnam)等人的往来书信,新闻报道,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报告,《图书馆杂志》刊登的文章,哥伦比亚学院理事会会议记录等各种史料。这些资料分藏于阿默斯特学院(杜威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哈佛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等地。史料之多是一方面,而杜威独特的简化速写字体也增加了作者研究的难度[6]。韦根特以其绵密细致的史学训练,从繁杂的档案中为读者爬梳整理杜威的行事与思想的轨迹。本书大量的脚注在向读者昭示着历史研究的不易与错综复杂,而平实的语言与娓娓道来的叙事风格则更显示出作者作为史家的严谨。然而严谨与平实并不意味着杜绝活泼与文采。比如,当杜威被哥伦比亚学院聘为图书馆长后,韦根特以颇具趣味的笔法写道:“哥伦比亚当政者想要一位馆长来负责学院图书馆;是的,他们得到了,但是他们的所得却远远超出其初衷。在1883年,他们雇用了一位以发展全美图书馆事业为己任的馆长,而且,这位馆长已做好了要清除一切阻挡‘更宏大’事业的障碍的准备。”[7]忠实的叙述与信手拈来的点评相结合使得《杜威传》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2 以改革思想贯穿不同阶段
在叙事方面,本书采取以时间为经、人物活动为维的框架结构。《杜威传》按照时间先后将杜威的活动轨迹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起一项“世界伟业”,1851-1888年。在该阶段,杜威度过了少年时代和大学岁月,编制十进分类法,创办美国图书馆协会和《图书馆杂志》,先后开办读者与作家经营公司、图书馆公司,后任职哥伦比亚学院图书馆馆长并建立第一个图书馆学院。
第二阶段:奥尔巴尼岁月,1889-1906年。杜威被迫离开哥伦比亚学院后,在奥尔巴尼担任纽约州立大学(时为教育行政部门)董事会秘书,并兼任纽约州立图书馆馆长。在该阶段,杜威以旺盛的精力推行图书馆作为教育机构的理念和实践,推动教育立法,在纽约州立图书馆开展立法咨询等业务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继续开展图书馆学教育培养专业人才,以及建立宁静湖俱乐部(Lake Placid Club)和发起成立美国图书馆研究院。在这个时期,杜威曾担任ALA主席,并成功组织协会参与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不过,月盈则亏,杜威也逐渐在美国图书馆协会和图书馆公司中失去影响,甚至退出自己一手创办的图书馆公司(1910年)——这对于杜威来说,是“他所做出过的最大的牺牲”,但是,“直到他和图书馆公司完全脱离关系,这位坚忍不拔的改革家也依然忠于最初的梦想”[8]。
第三个阶段:宁静湖岁月,1906-1931年。在该阶段杜威与图书馆渐行渐远,将主要精力放在宁静湖俱乐部的发展上。随着俱乐部大获成功,成立宁静湖俱乐部教育基金会和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俱乐部分部。不幸的是,分部并未获得成功。最后杜威病逝于佛罗里达州(1931年),留给后世丰富的精神遗产,以及在业界流传的一些争议和诟病。
在这三个阶段中,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杜威的教育改革理想。在少年时代,杜威立下了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改革的宏愿。韦根特写道:“11月15日(1869年,时年18岁),杜威写下另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决定:‘我已经充分做好了一生从事教育的准备。我想为大众开办高层次教育。’……三天之后,他又写道:‘我已经等不及了,我的命运急切地催促我着手这项一生的志业。’那一年,杜威才18岁,而他已经在谈论他的天命了。”[9]而后来占据杜威改革热情的图书馆事业、度量衡公制改革、简化英语拼写改革和速记法都是对他早年志向的实践。从这些不同的事业中都可以寻见杜威追求实用、简洁、高效的改革理念——他甚至一度将名字简写为“Dui”——如同他为ALA所拟的座右铭一样:“以最少的成本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好的读物。”[10]
3 全面总结杜威多方面成就
中国古有三不朽之说:立言、立功、立德。在立言方面,虽然杜威有不少的著述,但韦根特并未就杜威的学术论著作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即使是十进分类法这一广为世界图书馆界采用的知识分类体系,作者也着墨不多。首先,这不是一部学术思想史。更重要的,或许是因为杜威作为实践家和改革者的角色而做出的卓越贡献——这让韦根特更乐于将重点放在杜威的事功方面。杜威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而是起而行之做一个行动者(“A man of action”[11])。不过,“因为前人的研究主要是从杜威在图书馆活动方面的维度出发,出版了很多关于他在世期间(1851-1931)在这方面对美国社会的贡献,而关于他的更多更广泛的记录却被历史学家忽略了。本书旨在尝试修正前人视角,试图从杜威所在的更宽广的时代背景下去寻找定位他的角色和影响”[12]。因此,韦根特不仅着眼于杜威在图书馆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而且详细论述了他在图书馆以外——包括公制改革、英语拼写改革、教育立法、商业等多方面——做出的杰出成就。这些工作虽然不同,但却从内在反映了杜威对于提高效率的狂热追求和勇于改革的创新精神。他多方面的贡献决定了其不仅仅是一个图书馆学家——这也是为我们所最为熟知的一面,也是教育改革家和政府官员,同时还是一个商人,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虽然由于决策失误等原因而导致了平静湖俱乐部佛罗里达分部的失败)。这也是本书不同于以前杜威研究的一个显著之处,是一个新的尝试。
杜威一生的活动极其丰富,是名副其实的多面手②,这是为杜威立传的一个重要难点。事实上,“仅仅是编制杜威的活动编年已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以往的研究多是针对他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成就(例如分类法,或者是他作为教育者的身份)来具体论述,而很少尝试纵览无余地为其树碑立传”[13]。韦根特当然应该深知其中的不易,这也是检验史家功底之处。如何既全面介绍,同时又避免账簿式的罗列,而做到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在不同的时期突出主要活动,同时又交织杜威其他方面的行事轨迹,这些都显示了韦根特作为史家对史料的剪裁取舍和对史实的排列、熔炼之功。
4 对杜威复杂性格的客观描述
立德这方面,涉及到杜威,则是一件复杂的事,确切地说,就是杜威性格的复杂性。如何避免传主性格的简单化与单一性,尤其是通过人物具体的言论、行为来体现其复杂的性格及其背后的心理,把握其外在行事与内心的互动关系,这对于为杜威立传来说并不容易。哈里斯称:“杜威具有争议性的复杂性格成为此类研究的另一个障碍。他对于其追随者的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已经证实的来自其对手的不间断的憎恨、对于他反犹太人的指控、他奇怪而又富有争议的与女性的交往方式及对她们的影响,以及他冷酷而又常常存在问题的商业计划,所有这些都使他成为图书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14]评论家孙郁说:“作者对历史的态度不都是单线条式的,有自己的批判理念又多会心之处。我读传记,感兴趣的是人物性格维度的把握,在复杂性里体味生活会展示另一个历史。”[15]杜威虽然在图书馆事业、教育改革、商业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开创性成就,但他也是一个凡夫俗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其性格中,也有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缺点,甚至因此在社会上多次引起公愤:“‘在杜威周围,又响起了地震的轰隆声,’艾达·爱丽丝·琼斯在给她妹妹的信中写道;她已经追随杜威十六年了,‘我经常感觉像是住在火山附近似的。’”[16]杜威先后从哥伦比亚、纽约州立大学等的离职,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失势,宁静湖俱乐部的风波,等等,都与他性格中的消极面有关。韦根特也并未回避这一点,而是通过重重档案与史实考辨,为我们展现了杜威的另一面。 《杜威传》中体现杜威复杂性格的事件有很多,在此举几个例子以作说明。
首先是杜威作为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秘书的任职经历常为后世学者忽略,尽管他在任期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也使得纽约州立大学成为“当时联邦境内有能力对州内致力于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学校进行监督甚至批评的绝无仅有的高效能机构”[17]。韦根特对此做出分析:“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既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反派,而反派是不太适合让当代人来模仿的。因为别人很难和他一块工作……”[18]
其次是ALA选举事件。在1897年温莎逝世之后,亟待选出一位新的ALA主席。杜威担心“在协会内部日渐增长的地方主义色彩”[19],因此“不明智地”选择介入新主席的选任。在这个过程中,他以欺骗的方式骗取记录员海伦·海恩斯将票投给普特南。在被发现之后,他仍然为自己的行为狡辩,还因选举的事得罪了前ALA主席布雷特和副主席海耶斯[20]。这件事同他在读者与作家经营公司因做账问题被起诉(1880年)[21]的出发点如出一辙——在他看来,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维护集体利益——这种认知显示出他的自大与自以为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甚至使杜威自比摩西:“‘我经常深深地感激这些图书馆事务,’1916年杜威在写给詹姆斯·威尔的信中说,‘上帝让我做(图书馆界的)摩西,领导以色列的子民到达应许之地。’”③[22]
另外一个事件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宁静湖俱乐部排犹太人风波,它则是由于杜威的种族主义在作祟。当一位纽约的犹太人艾伯特·H·哈里斯申请去俱乐部度假时,却被杜威以俱乐部明文规定不接纳犹太人的理由拒绝(其实这是杜威的托词)[23]。当另一个同样被拒的犹太人Leipziger向纽约知名的犹太律师路易斯·马歇尔抱怨时,马歇尔对于杜威这样一位政府官员(杜威当时仍是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秘书)明目张胆地歧视犹太人极为愤慨,于是引发了后来的请愿活动和社会大讨论,这给杜威带来了巨大的公众压力。但是,杜威却拒绝承认错误。“纽约市的报社已经针对争论讨论了好几周,这件事也增加了美国犹太人社区富人的分歧。在事件背后悄悄进行着的私人通信中,充满对杜威的憎恶,憎恶他过去和现在的不当行为、他以前的政治立场、他的自大态度和严重的人格缺陷、他的顽固以及他拒绝承认任何错误。”[24]杜威类似性格的展现在书中不胜枚举。
韦根特希望能够尽可能地揭示杜威的多重性格,“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过去十五年在杜威手稿材料里的钻研来尽可能地揭示一个较为公允的杜威形象,将他那多彩的生活与时代以及其坚韧的性格展示出来。通过从晦暗不明处对杜威进行挖掘,并将他更宽泛的影响——不论是好的或坏——展示给当代人,我希望我已经对杜威做出了他所应得的历史评价”[25]。真实、客观是传记的生命。不虚美、不隐恶,力求真实客观地向读者传递传主的成就、思想、性格、品质是对传记的基本要求,在某些时候甚至成了极高的要求(尤其是当传主与传记作者有着较为亲近的关系时,如师生、亲属等,这一点更是很难做到)。在这一点上, 《杜威传》 做到了。正如韦根特告诫读者的那样:“本书所刻画的麦维尔·杜威既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反派。”[26]是的,借用时下话语,如果你爱杜威,那么,就请翻开这本书——他的斗志、坚韧、高效、创新精神会让你对其由衷钦佩;如果你恨杜威,那么,也请翻开《杜威传》——他的傲慢、专断、自大、种族主义也不会让你失望。
5 结语及其他
正因为韦根特凭借大量史料和强有力的分析客观展现了杜威一生的活动脉络、多方面成就与复杂的人格,使《杜威传》 赢得了1997年年度G.K.Hall奖,可谓实至名归。爱德华·霍利(Edward G.Holley,曾任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图书情报学院院长)评价《杜威传》是“绝对的……极好的研究,具有可读性”,而菲利斯·达因(Phyllis Dain,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教授)也称此书是“非常好的研究成果,巧妙地刻画了杜威的性格和人格”[27]。诚如斯言。此外,从本书中,我们也可以联系到图书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1)既要知人论世,又不能因人废言。知人论世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一个历史人物,从而便于我们查究其思想演变的痕迹。但知人论世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因人废言。中国古代因人废言的传统埋没了许多人才,常常因一个人的德行而全盘否定他的成就,这也成为许多著作失传的原因之一。然而,客观地说,一个人的专业成就与其道德、品行、脾性、地位、政治立场等常常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因此,立足学术本位,以专业成就为主要标准,才是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态度。不因人废言,将“功”与“德”分开,让被埋没的人成为人物,让被神化的人物走下神坛:图书馆史研究也理应如此。
(2)图书馆史研究的跨学科性。图书馆是个客观事物,它本身并不具有学科性质,图书馆事业及人物的复杂性决定了可以采用多重视角进行研究。目前我国图书馆学正在大力倡导跨学科研究,而图书馆史正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一点同西方借鉴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书史的路径是一致的[28-29](事实上,二者也是紧密相连的)。许多图书馆人的成就都是多方面的,杜威、博尔赫斯、王重民、向达等等,都是如此。韦根特在本书中论述了杜威在图书馆、公制改革、英语拼写、教育立法等多方面的成就,上文提到的他的《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民众的美国公共图书馆史》也是如此,这一点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在启发我们转变图书馆史研究思路的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其他专业的研究人员关注图书馆史,促进该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3)一部传记或年谱均可作为图书馆史方向学生的学位论文。这一点看似与本文所论内容关系不大,然而对于图书馆史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最近若干年,国内图书馆史研究渐有起色,然而,历史研究工作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以人物研究为例,涉及的工作包括人物论著的搜罗与汇集、人物活动年谱的编制、传记写作、学术思想的系统研究与评析,等等。对于成就卓著的历史人物来说,这些工作很难在读研或读博一个阶段内兼顾完成,即使仓促完成,恐怕也多有失漏与偏颇。药下得太猛会适得其反,这一点也给研究生选择研究方向增添了几分畏难情绪,从而影响这一领域后继人才的培养。年谱和传记是图书馆史研究的基础文献,对于研究人物具有奠基性意义。因此,笔者在此建议应允许乃至鼓励研究生选择以编纂人物年谱或者书写传记(甚至编纂学者的全集)作为学位论文,允许“慢工出细活”式的研究。这可以为其后续研究和他人的相关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其学术价值并不亚于一篇诸如“某某学术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试想,如果韦根特要以《杜威传》申请其博士学位的话,他的学位授予委员会能不同意吗?总之,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图书馆史研究不必毕其功于一役。
注释
①关于其他几种杜威传记的介绍,可参见郑永田《美国公共图书馆史文献评述》 第34 页(《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 年第4 期)。
②杜威甚至写过一篇题为《图书馆管理中的商业技巧》的文章,将经商与图书馆结合起来(参见:Sarah K.Vann. Melvil Dewey,his enduring presence in librarianship[M]. Littleton, Colorado: Libraries Unlimited,1978:248)。
③应许之地是上帝许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区,见《圣经》中的《旧约·创世纪》。
[1][11][13][14]Sarah K. Vann. Melvil Dewey,his enduring presence in librarianship [M].Littleton, Colorado:Libraries Unlimited,1978: 9,234,10,10.
[2] Wayne Wiegand to Discuss Woman’s Library [EB/OL]. [2014-01-18]. http://cattcenter.las.iastate.edu/events-page/gender-culture-and-politics-at-thechicagoworlds-fair-wayne-wiegand/.
[3] Dr. Wayne Wiegand [EB/OL]. [2014-01-18]. http://hott.fsu.edu/faculty/wayneWiegand.html.
[4] Christine Pawley,Louise S. Robbins. Libraries and the Reading Public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M].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13:264.
[5] 转引自:Christine Pawley,Louise S.Robbins. Libraries and the Reading Public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M].Madison,Wisconsin:The University ofWisconsin Press,2013:24.
[6] [7] [8][9] [10] [12] [16 ] [17] [18] [19] [20] [21] [22 ] [23][24] [25] [26] [27] Wayne A. Wiegand. Irrepressible reformer:a biography of Melvil Dewey [M].Chicago and London: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96:XIV,82,242,12-13,61,XIII,277,189,189, 224, 224-228, 66-67, 377, 260, 278,XIV,XIV,封底.
[15] 故纸堆的旧事,何以成传记[EB/OL]. [2014-01-17]. http://epaper.ccdy.cn/html/2014-01/16/content_116334.htm.
[28] 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J].史林,2007(5):151-180,189.
[29] 姚伯岳.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书史研究:由何朝晖译《书史导论》说开去[J]. 山东图书馆学刊,2013(4):109-11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