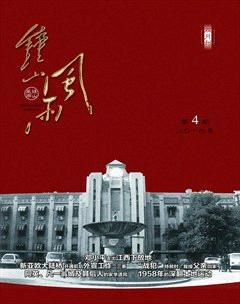尼姑闲谭
陈宝良
作为旧时“三姑六婆”之一的尼姑,无论是在古小说中,还是在戏曲舞台上,不乏她们的身影与形象。我对尼姑的了解,实可追溯到在家乡的儿童时代。犹忆儿时生活在故乡越地的一个小镇,濒河而居,河岸对面就有一座尼姑庵,乡里人通常称之为“庵堂”。尽管横扫“四旧”之余,泥塑菩萨像或被拆毁,或被杂乱堆置一室,尼姑大多还俗,庵堂也已改作他用,面目全非,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听说庵堂这一称谓,且对庵堂中的尼姑有了好奇之心。
在越剧的传统剧目中,有一出《庵堂认母》,故事出自《玉蜻蜓》中的一折。这出戏的故事梗概,大抵是讲富家子弟申贵升与妻子张氏不睦,离家出走,在法华庵与尼姑王志贞相恋,后病死庵中。志贞产下遗腹子,辗转为徐家所收养,取名徐元宰。16年后,元宰得中解元,获悉自己身世,于是到庵中认母团聚。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家乡戏越剧重又繁荣,舞台上开始重演此剧,并为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至于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56年出品的电影版《庵堂认母》,也得以重新冲破禁锢而与观众见面。生逢其时,我有幸得以观看了这部电影,也在家乡舞台上看过草台班子演的同名之剧。正是从这部戏中,我知道了作为出家人的尼姑,其实与凡人一般,也会有儿女情长。故事的结局当然不出中国戏剧的老套路,以母子相认团聚的喜剧告终,但在佛门清规与母子亲情两者之间,终究不免有着让人如何抉择的困惑。
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大学学习,尤喜同乡先贤鲁迅的作品。读过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读者应该记得,当阿Q抚摸尼姑的光头时,曾用轻佻的口气说了一句名言,即“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可见,自明清以来,由于小说对尼姑形象的恶意刻画,导致在民间百姓尤其是一些乡村无赖的心目中,和尚摸尼姑的光头应该是一件见多不怪的常事。至迟在清代,在民间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禁忌,即视早起见到尼姑为晦气的习俗。譬如清代有一则史料记载,说的是苏州有一位乡绅,在初一的早晨起来,途中遇到尼姑,深感愤怒,自认为是“弗失头”。这是苏州的土语,意思是说晦气,于是直唾尼姑之面。
尼姑并非像“道姑”、“女冠”一般,是本土的产物,而是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应运而生。根据宋朝人赵令畤《侯鲭录》的考订,大抵在汉明帝时,济阳有一位叫阿潘的妇女已经开始出家,这可视为尼姑的起源。尼姑的称谓不一。在佛教经典中,一般称尼姑为“优婆夷”。在正统的法律条文或典章制度文书中,则称之为“尼僧”或“尼姑”。至于在民间,则一般称尼姑为“师姑”、“师太”,有时甚至干脆叫“和尚”。
尼姑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人,只是因为皈依了佛门,才被称为“出家人”。尼姑的来源,既有已婚的妇女,亦有未婚的少女。至于出家的原因,细分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是抱有宗教虔诚而出家。有些妇女与佛教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些妇女通常在传统的史料记载中被神化。笔者手头正好存有几则史料,不妨摘录在下面。如明朝宣德年间,丰润女子周氏,幼年时就不茹荤,崇奉释教,发誓足不出户。至七十余岁时,自焚坐化;明朝成化年间,四川古城周氏之女,生而不荤,喜欢诵经,发誓不嫁,最后自焚坐化,被民间视为“智慧菩萨”;崇祯年间,山西临汾泊村窑洪晋的女儿,出生时她的母亲张氏就梦见了菩萨,在一阵鼓乐声中被迎接到家,后来也礼佛趺坐,坐化之后被民间称为“黄明立菩萨”。
另一类则是被迫无奈而出家,缺乏纯真的宗教虔诚情感。在这些出家尼姑中,高者当然是惑于福慧之说,下者则不过是饥寒所迫。当然,其间的原因亦不一:有的是幼小无知,被父母强迫而出家;有的是丧夫之后,成为寡妇,对生活前景失去信心,只得出家;有的是因为没有儿子,无法为丈夫家族延续香火,迫于族内压力而出家;有的是虽然有夫有子,却因有不得已的原因,只能忿然出家。
出家原因不同,势必造成尼姑出家以后的修行迥然有别。出于宗教自觉的尼姑,自然能保持佛门的清净本色。譬如明代有一位姓孟的小姐,在去苏州惠日庵访尼姑时,曾在亭上写下一诗,诗云:“矮矮墙围小小亭,竹林深处昼冥冥。红尘不到无余事,一炷香消两卷经。”此诗甚雅,基本道出了尼姑日常的清修生活。还有清代佚名所撰小说《山水情》,记录下了苏州寒山庵尼姑了凡的早课,“明晨起身薰沐浴,摆设齐整道场,做其朝功课来。擂鼓作乐,开经起忏,热闹之极”。到了晚上,尼姑又“做了夜功课,一同吃了散堂斋儿,各自去睡了”。可见,尼姑属于一群脱离尘俗、皈依佛门的出家人,她们已经不再留恋红尘,并与世俗隔绝,在庵院中与青灯、佛卷、木鱼为伴,过一种清修的生活。
不过,在尼姑群体中,确实不乏被迫出家之人。尤其是那些年幼出家的尼姑,到了后来,就会后悔自己轻率出家,开始羡慕红尘的繁华生活。为此,传统时代的法律,无不对妇女出家的年龄作了限定。如明朝对女子出家的年龄限制,洪武时期定为必须40岁以上,至建文年间更是升至59岁以上。这是规定中年以上妇女方可出家为尼。清代的《礼部则例》规定,只有40岁以上的妇女,方可出家为尼。这种在年龄上的规定,究其用意而言,无非就是为了使尼姑能安于清修,并保持佛门庵院的宗教纯洁性。
被迫出家是一种违背人性之举,最后难免会出现超脱佛门清规的行为。这是因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旦舍弃酒肉之甘,而就蔬水之苦,或者抛弃室家之好,而同鳏寡之衰,这确实是最为不近人情的事,难免会使尼姑做出一些怨旷无聊、窃行非法的事情来。那么,妇女出家成为尼姑,其心情究竟如何?她们果真可以抛却世俗的烦恼,安心沉浸于青灯念佛的生活?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而人的感情却又最为复杂。很多文学作品,对尼姑的矛盾心态多有揭示。如明代著名文人徐渭作有一首《陈女度尼》诗,专门描写了一个陈姓少女在即将度身为尼时的心情。诗云:“青春正及笄,削发度为尼,别母留妆粉,参师歇画眉。幻真临镜现,生灭带花知,未必今来悟,前身受记谁?”一个青春年少的少女,不再敷粉画眉,而是削发为尼,难道真的是今生已经大彻大悟?真如徐渭所言,其实未必。在少女做出这种无奈选择的行为背后,只能将之归为“前身受记”,亦即前身的一种佛缘。陈铎也有一首题为《尼姑》的散曲,其中云:“卸除簪珥拜莲台,断却荤腥吃素斋,远离尘垢持清戒。空即空色是色,两般儿祛遣不开。相思病难医治,失心风无药解,则不如留起头来。”可见,尼姑尽管已经身持清戒,远离尘垢,但在情感问题上终究还是要得“相思病”、“失心风”。明无名氏辑《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中有一首《寺里尼姑》歌曲,其中云:“寺里尼姑,缺少儿孩没丈夫。每日吃斋素,又没个神仙度。嗏,扯碎大衣服,变规模,留起头发,走上烟花路,嫁个丈夫不受孤。”尼姑受不了空门的寂寞,其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留起头发,重新嫁人,回到世俗的生活中去,亦即所谓的“还俗”。明人李开先所著《新编林冲宝剑记》一剧,就尼姑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有深刻的揭示。剧中所塑造的尼姑,确实正如她自己所说:“脸是尼姑脸,心还女子心。空门谁得识,就里有知音。”作为一个出家人,原本已是六根清净,但这些尼姑却对民间流传甚广的山歌,诸如《锁南枝》、《山坡羊》、《清江引》之类相当熟悉,而且经常挂在口头哼哼。随后,剧作为了对这些尼姑作更深入的描摹,就故意写了一首《清江引》,让尼姑清唱,其中云:“口儿里念佛,心儿里想:张和尚、李和尚、王和尚。着他堕业根,与我消灾障。西方路儿上都是谎!”尼姑不但与张和尚、李和尚、王和尚之流偷情,而且惯于说些风月话,诸如借佛之言云:“法轮常转图生育,佛会僧尼是一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尼姑与世俗的交往相当密切,时常拜认一些干爹、干娘、干兄、干弟,甚至结识一些“好风月的游僧”。清初嘉兴人朱仲莪所写的《嘲尼诗》云:“不惜风流世所传,一生随处觅姻缘。超升已出平康巷,解厄还登波若禅。节按木鱼移此日,歌翻虎凤想当年。一心未绝红楼梦,春夜犹思醉管弦。”诗中刻画的尼姑,同样难以割舍红楼情缘。还有清代小说《山水情》刻画了寒山庵中尼姑云仙为情欲所困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她自己还能意识到作为出家人,应该六根清净,断绝情欲,亦即她自己所自言:“可惜我年二十,虽然出家,身尚未破,何可以一时欲念之萌,而丧终身之行,论起来只是不可”;另一方面,转念一想,道:“呸!我的出家原为父母将身错许蠢子,怨命立志,投入空门,真个什么‘身具佛骨,心种佛心,必要修彻上西天的。”所以,最后还是情欲战胜了佛心,面对俊俏郎君,她就不能白白无故放过去,去学“陈妙常的故事”,在破色戒上去走“一遭再处”。endprint
诗歌、戏曲、小说等作品文学化的夸张,固然有对尼姑整体形象加以妖魔化之嫌,然揆诸宋代以来佛教社会史的实际,尼姑心存恋世情结,享受世俗化的生活,甚至与僧人、俗家子弟私通,无疑也是当时佛教社会的基本面相。尤其是入清以后,“娼尼”的广泛出现,以及登徒子游冶尼庵之风的勃盛,显然已是“风俗淫靡”的具体反映。至于“花禅”的流行,更是佛教日趋世俗化的典型征候。
所谓娼尼,清代文献又作“秃娼”,众多史料已经证实应当始于南宋时期的“尼站”。不过仔细考察一下南宋临平明因寺所设的尼站,里面的尼姑大多不守清规戒律,仅仅是为了应付在佛教界具有相当势力的“僧官”,满足他们的不时之需,显然尚属被动的无奈之举。反观清代以江浙娼尼、泰山姑子为代表的花禅异军突起,则是名为尼姑,实则形同娼妓,是一种迎合嫖客心理的主动行为,致使原本属于修行佛地的尼姑庵院,反而成为了楚馆秦楼。随之而来者,不惟是佛教社会史出现了内在的转向,更可为青楼文化史发生转变下一注脚。
这无疑与当时士大夫的游冶趣味的转向是桴鼓相应的。那么,士大夫为何开始厌倦花街柳巷,转而留恋庵堂中的尼姑?这倒可以从清代一首咏小尼姑的诗中找到部分的答案。诗云:“绰约小天仙,生来十七年。孤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晓院花留立,春窗月伴眠。回眸虽欲语,阿母在旁边。”细玩诗旨,起首二句是说尼姑年貌之美,三四句是描摹尼姑的慧美,五六句是描写尼姑生活的岑寂,末二句则说尼姑的情态。声声摇曳,窍窍玲珑。有如此小尼,不得不有如此之诗。柔情醉骨,绮语销魂,不能不勾连起文人雅士对小尼姑的好奇与怜香惜玉之情。
突破佛教的清规戒律,转而追求与世俗女子一般的个人情感,仅仅是自宋以后尼姑转向世俗化的一个侧面。此外,清代江南盛传一则谚语,叫“师姑趁夜载来去没得闲”。这句谚语,一则道破了尼姑的“前事”或者“隐事”。换句话说,很多尼姑多是半路出家。古代才女,不乏身落青楼之人,到了晚年,有所醒悟,开始吃斋念佛,焚修闻道。如宋人苏东坡与妓女琴操聚在一起论诗,对答如流。到了最后,在披诵“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一句之时,琴操翻然有悟,披剃出家。二则道出了当时尼姑的实情,即这些尼姑并未限于庵中清修,而是为了赚取报酬,积极参与民间百姓家的夜忏之会。
由此可见,尼姑不仅有难破色欲之戒的世俗行为,过着衣食讲究的时尚生活,而且不乏世俗化的言论,公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清代震泽镇新庵尼姑五宝堪称典型一例。她公开宣称:“饮食男女,大欲所存,僧俗当无二致。”所不同者,僧家格于佛戒,不能畅所欲为。她进而认为,讲学家“龂龂以气节责人”,不过是少见多怪而已。若是开通之人,就不应当如此固执。这般惊人之论,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
不过话又说回来,世上的人有好有歹,难道尼庵都是不好的吗?其实,在当时社会,与其他出家人一样,尼姑中尽有一些修行学道之人,不可一概而论。尽管如此,尼庵中不守戒行之辈确乎不少,这才导致很多正统的文人学士将尼姑归入“三姑六婆”之中,成为文学作品所刻意描摹的范型人格。如明朝人周清源在小说《西湖二集》中,直言“大抵妇女好入尼庵,定有奸淫之事”;清朝著名的师爷汪辉祖,在其所著《双节堂庸训》中,同样有“三姑六婆,先民所戒;尼姑一种,尤易惑人”的陈腐之论。这或许是因为那些文人士大夫为了挽回世风,而不得不将尼姑世俗化的危害加以夸大,但确实部分道出了当时实情。■
(责任编辑:武学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