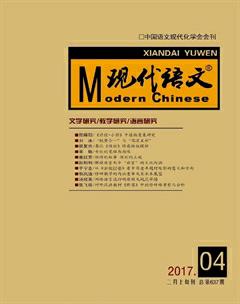封建伦理中女性的压抑与反抗
摘 要:主要集中于对子弟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探讨,通过对子弟书文本的阅读可以发现与当时上层社会所描绘的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对两个不同女性群体(尼姑以及民间所称道的侠女)的分析,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当时人们对这三种女性群体所持有的不同的社会心理以及其中体现的封建伦理束缚。
关键词:八旗子弟书 侠女 妓女 尼姑 压抑与反抗
近年来对《子弟书》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了《子弟书》作者、形成发展与衰落、《子弟书》改编、《子弟书》的文学价值等上,对《子弟书》中的女性故事还较少涉及。本文将主要集中于《子弟书》中的女性故事,这些涉及到女性的故事类型非常丰富,有传统的“负心汉”模式、“两女侍夫”模式,也有“西厢记”“君妃恋”等在前代经典作品影响下形成的模式。本文将主要着眼于尼姑以及侠女这三个不同的女性群体,对其进行简要分析。
一、尼姑(或者道姑)
《子弟书》中关于尼姑的故事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描写尼姑庵中的尼姑与男人甚至是和尚发生的情感纠葛,如《陈云栖》《玉簪记》《思凡》等,第二种主要体现尼姑生活的世俗化,着重表现尼姑与世俗生活的融合,如《灵官庙》《续灵官庙》,两种模式分别以感情及日常生活为切入点,但其本质上都是强调尼姑情欲的复苏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就这一点而言二者其实是密不可分、相互交融的。
在第一种故事类型中,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尼姑还俗的举动,还俗是她们心恋尘世的行动表现。《陈云栖》中有“云栖改装易服”之举,《僧尼会》中有“实对你说我本私逃将山下,小尼说两人原是一規模”之言,更不用提《思凡》《思凡》整篇都是描写尼姑思凡渴望还俗的心理。《灵官庙》主要描写的是世俗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借拜寿为名在灵官庙发生的荒唐故事。广真姑子摆酒庆贺生辰,赶来庆贺的人却五花八门,“专请朝中显贵臣,还有那久搅久闹的堂客夫人。也有亲藩与国同休称为屏捍,也有官宦世代书香掌丝纶。也有经商家财万贯,也有应役广交衙门。还有男僧与优童妓女”[1]这短短的一段话已经将当时尼姑与世俗之间的紧密联系描写的淋漓尽致。
正常情况下尼姑还俗的过程都会带有一定的矛盾性——心恋俗世与身循戒律的矛盾。《陈云栖》中的女主人公虽然对真毓生心生好感,但面对真毓生“不才潘生真真凑巧”的暗示陈云栖却因自己的尼姑身份而予以拒绝,及至流浪还俗后还惦念着自己的“潘郎”,并以“只说幼时曾许字潘郎”为名拒绝其他人的婚嫁请求,甚至在大胆的《僧尼会》中,尼姑也会以“授受不亲夫子语,难道你没见圣人书”做挡箭牌,小沙弥也是希望通过“还俗”“娶一个娇娇滴滴如花的女,陪伴我朝朝日日有情的夫”,这其中体现了一个永恒的矛盾,社会伦理的存在压制了人的自然情欲,然而也正是外在规则的存在为人自然情欲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因而妥协成为这种情况下最经济划算的选择。
与前代相比,明清之际出现了大量尼姑与俗人私通的情况,当时民间就流传着“短发蓬鬆绿未匀,袈裟脱却着红裙。于今嫁与张郎去,羸得僧敲月下门”的事迹,甚至在弘治七年(1494)明孝宗曾下令,“僧道尼姑女冠有犯奸宣淫者,就于本寺门首枷号一个月,满日发落”,这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大致可以归为非自愿的出家动机。
就动机而言,明清越来越多的女性是出于对现实的逃避或无奈,其成员往往是走投无路的贫苦百姓,这与前代众多的尼姑是来自贵族的形成对比,她们出家的动机往往是收到宗教的感召。例如《续比丘尼传》中记载唐长安济度寺尼法显,“俗姓萧氏,兰陵人,梁武帝之六叶孙,唐故司空宋国公瑀之第三女也”[2];宋东都崇真资圣院尼清裕,为“太宗第七女申国大长公主”;元京师妙善寺尼舍蓝蓝,出入皇室,“凡历四朝,事三后”。与此对比,明清之际女性的出家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之举。明末清初人陆衡分析:“每见人家妇女,或丧夫,或无子,即有夫有子,而别有不得已,辄忿然出家,薙去其发”,一个“忿然出家”道出了真谛。女子丧夫,朝廷的礼教要求其守节,这就是所谓的“节妇”。许嫁而未婚,未婚夫一死,也被迫守节,这就是所谓的“贞女”。尽管这种守节的行为可以为家庭乃至自己带来一时的虚名,但时日一久,青春难度,白日无聊,最好的结局就是遁入空门。正如《僧尼会》中小沙弥“我又不是黉门客,谁晓得酸文假醋者也之乎”及“佛门弟子并非儒”之语则直接点明遁入空门相对的逃避世俗的伦理束缚,本就不是真心,又如何谈的上遵守那些清规戒律呢?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曾有过这么一段话:“一部《二十四史》,中间节妇烈女最多的莫如《明史》了”“《二十四史》中的妇女,连《列女传》及其他传中附及,《元史》以上没有及六十人的。《宋史》最多,只五十五人。”[3]《元史》是宋濂他们编的,明朝人提倡贞节,所以搜罗的节烈比较多。到清朝人修《明史》时,所发现的节烈传记,竟“不下万余人”,因此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封建伦理束缚在这个时候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诸多被迫遁入空门的女尼反映出当时女性生存环境的恶劣。因为古代女性不高的社会地位使得她们对男性有着极大的依赖,因而女性一旦被丈夫抛弃或者遭遇战争天灾就很难在社会上独立生存,这时寺庙就凸显出它的独特作用,寺庙已经成为女性避难的绝佳场所,而寺庙一旦具有了这种俗世的作用就会不可避免地与俗世生活发生接触,因而身处寺庙中的尼姑才会做出种种不合寺规的举动。
二、侠女、女性复仇
古代社会因为男性主导着话语权,所以“英雄救美”的故事数不胜数,但后期随着社会的腐败和文学发展的需要,书生开始寻求其他解决问题的途径或者新的文学题材,这时候“侠女”或者“女性复仇”的故事就应运而生了。
这类故事情节基本千篇一律,或者是为民除害或者是家族复仇或者是为国家大义。主要的代表有《侠女传》《盗令牌》《盘合》《拷玉》《红梅阁》《刺虎》《渔家乐》《藏舟》《新凤仪亭》《炎天雪》等。其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女性复仇的方式以及复仇后的结果。
(一)复仇方式
1.委身复仇
委身复仇简单来说就是以美色或者身体为筹码,诱惑男性使其放松警惕进而达到目的。比如《刺虎》《新凤仪亭》以及《刺梁》《刺汤》等。
《刺虎》的故事来源于《铁冠图》,讲述的是明清战乱之时闯王李自成破京入宫,前朝宫人假意成婚刺杀奸贼的故事,费宫人正是通过自己的美色诱惑使得一只虎醉酒放松警惕,刺虎行动才得以成功。《刺虎》中多次出现了类似“见他金凤冠垂珠掩映春风面,恰似娇滴滴带雨的梨花对月新”“杏眼含情桃腮带笑,欠香躯花枝招展递到流寇的跟前”“费贞娥莺声燕语殷勤让,一只虎眉低眼闭醉在席前”“赔笑的家人伸玉指,与他松白玉带慢解绛袍红”[4]的描写,《刺梁》描写的是渔家女邬飞霞为报父仇混入梁府,乘隙用神针刺死梁骥的故事。邬飞霞的复仇也是以美色诱惑迷惑奸臣为主要手段,文本中也充斥着大量的对于女性外貌以及男子沉溺美色的描写,“但看她两鬓风流羞花闭月,一身俏丽倾国倾城”“这奸贼一双醉眼神都定,独瞅飞霞不转睛”等。这类描写都突出了女性生理特征在复仇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2.以智谋复仇
这类故事的主要代表作品是《盘合》《拷玉》《藏舟》《盗令牌》《盗令》等。以智复仇在这里主要与委身复仇相区别,主要突出的是女性身上的谋略与胆量。
《盘合》及《拷玉》脱胎于民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文中寇珠巧用激将法让陈琳将皇子带出宫中,“寇承御柳眉直竖说你也是男子?不及一女辈尚且不敢把心亏。可惜我害怕耽惊往夹空儿里等,等着个不忠不义负恩的贼!罢了么天呀太子合该随奸妃的愿,破着我寸步儿不移小命儿陪”短短的几句话说得太监陈琳满身熱情,将太子带出宫去,充分体现了寇珠对人性的洞察以及智慧。《拷玉》中寇珠面对的是身体上钻心的疼痛,来自刘妃的严刑拷打并没有让寇珠屈服,即便是“血道儿滴嗒泪道儿淋”[5]寇珠都没有松口,在与陈琳对质时寇珠更是为了成全他人“触阶而死”,《拷玉》一回更是将女性身上的不屈与硬气展现得淋漓尽致。
3.以技复仇
在以《红梅阁》《侠女传》《慧娘鬼辩》为代表的“以技复仇”模式中女性伸张正义的主要方式是自身的武艺或者带有“聊斋”意味的非自然力的技能,前者也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最为广泛认可的如隐娘般满身武艺、锄奸惩恶的侠女,后者则更多的是类似于聊斋中正直善良的鬼怪。这两种模式紧密结合,往往为人所称颂的侠女身上有着“神鬼”的色彩,这也往往是民间崇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的结果。
《红梅阁》与《慧娘鬼辩》取材于周朝俊的《红梅记》《红梅阁》与《慧娘鬼辩》讲述的是慧娘被残害后化为鬼魂解救书生的故事,文中“鬼火儿磷磷魂灵儿闪闪,满堂前阴风儿滚滚凉气儿飕飕”“冷森森阴气儿逼人透骨头”[6]等环境描写突出了慧娘在化为鬼魂之后拥有的令人战栗的能力,而《侠女传》中侠女“冷森森手挥飞剑斩去了狐头”以及“去若惊鸿”[7]的表现也使得侠女的身上有了某些超自然的能力。
4.天行正道
天行正道即通过向上天喊冤得以洗清冤屈,以《炎天雪》为代表,它就是我们熟知的“窦娥冤”故事。“只哭得悲魂两个风飘荡,只哭得女犯一监肠断折”[8]是窦娥对自己受到不公正冤屈的控诉,“推赴法场阴云忽起,三伏大雪粉饰山河”是上天在面对此类冤屈的反应。
(二)结局
复仇或者侠女模式中女性的结局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好坏两种结局,造成这两种结局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依靠,而这种强有力的依靠又来自于男性。
诸多故事中只有《藏舟》《渔家乐》可以称作是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女主人公邬飞霞最后与刘蒜喜结连理母仪天下,但邬飞霞拥有刘蒜喜这样一个强大的依靠,他是世俗权力的最高代表,邬飞霞自然无须担心自己复仇可能遭致别人报复,尽管这类故事中女性仍有对男性的依附性,但这类故事中女性已经不再是传统眼光中的“大家闺秀”,而是具有了反叛的意味,《炎天雪》中的窦娥敢于怒骂为人所敬畏的“老天爷”;《红梅阁》和《慧娘鬼辩》中的慧娘更是敢直言对才子的爱慕“你看他:身躯相貌多秀丽,衣冠动作,别样的端庄。何必用头戴乌纱方能贵重,虽然说,身无管带俏非常”;《盘合》《拷玉》中的寇珠巾帼不让须眉,“但凭着耿耿的丹心映日月,只落得腾腾的杀气化愁云”“生辉史册春秋笔,惭愧须眉陷佞臣”更是将“生辉史册”这一评价极高的词语用到了女子的身上;《刺梁》中的邬飞霞更是“仇怀家国”使得“奸佞伏诛君父仇报”,赢得了“奸佞伏诛君父仇报”的大好局面,“侠女”模式或者“复仇”模式中的女性身上增添了许多的阳刚之气。
这种兼有男性阳刚之气的女性形象的出现与《子弟书》的作者有很大的关系。满族本是“宁质毋华,宁朴毋巧,宁强劲果毅,毋汩没诡随”[9]的民族,清代的满族子弟出身于这样的少数民族,天生身体强壮,骑马射箭无所不能,因而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女性既呈现出传统女性丰富细腻的微观情感,又具有率直爽朗的潇洒气魄;另一方面,这与八旗子弟所处的特殊的时代有关。满族立国后,统治者们积极倡导子弟们对汉族文化进行学习,骑射武艺与文化学习是他们的必修课程。如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数岁即习骑射,稍长工文翰”。[10]从雍正到康熙两朝,共取中满洲、蒙古、汉军翻译进士72名,翻译举人393名[11],从清初开始,“满洲子弟在国家鼓励、家庭熏陶及自身对汉文化向往的多种因素下,积极学习新的文化,完成了从游猎武士到封建文明传承者的角色过渡,真正融入了以汉族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主流文化之中”[12]。但后期伴随着清廷对子弟的“优惠政策”使得大量的子弟享受俸禄不事生产,逐渐养成了“遛鸟斗鸡”的恶习以及子弟自身的堕落,使得嘉庆发出“不知节俭”“华服引酒,赌博听戏”“所为之事,竟同市井无赖”[13]的感慨。(子弟书中以“叹”字为题的文章有数十篇之多)八旗子弟的没落自然使得其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为此担忧,伴随着国力的衰弱、政治的腐朽、社会矛盾的逐渐尖锐自然使他们将这种企盼重返淳朴旧俗的愿望寄托在了女性身上,他们笔下的女性自然就具有了“救世报国”意味,也就出现了“侠女”的形象。
三、结语
《子弟书》的作者均为旧日京城中那些文化素养较高的旗人子弟,子弟书作为一种可以演唱的独特的叙事诗歌,尽管其曲调已经失传,但它的曲文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子弟书》可以说是众多的文学体裁中比较特别的一类,因为很少有文学作品能够像子弟书一样是清一色的男性作家,因为性别意味颇具研究价值,这也是我们研究《子弟书》中女性形象的重要原因。
就如我们在上文论述到的子弟身份的特殊性一般,正是汉族文化对满族文化的剧烈冲击造成了满族人对女性的要求已经由具有粗犷豪放之气的女子形象转变为与汉族视角中歌颂的妇女形象别无二致现象的出现,《子弟书》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示出了当时满汉文化的融合。
尽管是男子执笔,《子弟书》中也有很多的女性人物,从尼姑到侠女到妓女,从平民百姓到深宫妃子无所不有。通过对作品的阅读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哪个阶层中的女子,她们的命运都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将这些女性故事中的社会背景进行简单的归纳总结我们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无论是身处哪个阶层的女性,“三从四德”等对妇女的要求使得她们根本不可能离开自己所依傍的夫家,伦理道德都带给她们巨大的束缚,社会又没有提供给她们足够的生存空间,连自身连独立都没有办法做到,又如何谈得上男女平等?
(指导教师:尹变英)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西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资助项目——八旗子弟书的故事模式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6014293。)
注釋:
[1]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辑校:《清蒙古车王府藏八旗子弟书——灵官庙》,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69页。
[2]民国释震华:《续比丘尼传》(六卷)。
[3]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4]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辑校:《清蒙古车王府藏八旗子弟书——刺虎》,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725页。
[5]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辑校:《清蒙古车王府藏八旗子弟书——拷玉》,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53页。
[6]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辑校:《清蒙古车王府藏八旗子弟书——红梅阁》,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543页。
[7]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辑校:《清蒙古车王府藏八旗子弟书——侠女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81页。
[8]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辑校:《清蒙古车王府藏八旗子弟书——炎天雪》,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59页。
[9]盛昱:《八旗文经》(卷38),辽宁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10]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484),第13361页。
[11]福隆安等奉敕续纂:《钦定八旗通志》(卷107),第1-20页。
[12]崔蕴华:《书斋与书坊之间——清代子弟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13]华文书局出版《清仁宗实录》(卷227)。
(卫玥 山西太原 山西大学文学院 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