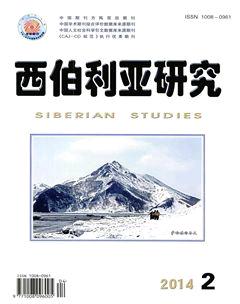德国学者对西伯利亚萨满教的研究
王旭
中图分类号:B989.18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8—0961(2014)02—0093—03
19世纪,由于历史原因,德国宗教史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对萨满教这种奇特的宗教形式产生了浓厚兴趣。多年里,这些德国学者为弄清萨满教的来源,对萨满教流行地区特别是西伯利亚地区进行过广泛调查,收集到许多珍贵资料,发表了大量关于萨满教的著作和文章。
1696年,彼得大帝下令组织庞大的俄国大使团周游欧洲,拉开了俄国数百年向西方学习的序幕。彼得一世改革的一项重要动因就是文明向心力,无论从民族还是语系角度,俄罗斯都属于欧洲,然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俄罗斯已被西欧、中欧远远抛在后面,它们先进的文化吸引着年轻彼得的目光。正因如此,这项改革在科学文化方面的措施便是聘请大量西欧学者、教授和科技人员,其中就包括许多德国学者和科学家。
1732年12月,女皇安娜批准了西伯利亚考察方案。经过一年多筹备,于1734年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北方大考察”。北方大考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历史、民族、语言等进行全面系统考察。考察队成员包括从德国聘请的科学家和学者。从北方大考察起,德国学者开始了对西伯利亚土著民族宗教——萨满教的研究。
德国学者最早把有关西伯利亚萨满教知识传播到西方,接受者也包括俄国的阅读大众。这种现象非常正常,因为第一位受过教育来到西伯利亚研究和记录西伯利亚萨满教的人,是18世纪的德国学者和德语研究者。他们受俄国政府委托,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穿越西伯利亚荒野,绘制完成了大片冻土带和主要地区的地图,寻找煤炭资源,记录文化古迹,并普查西伯利亚人口。
18世纪,德国学者帮助俄国创建了自己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并在19世纪继续“滋养”着这些领域。俄国和德国学者和知识分子关系十分紧密,以至于有时很难将他们分开。此外,在19世纪甚至是20世纪前半叶,俄国学者记录的大量关于西伯利亚萨满教的信息,都是通过德国文摘和译文提供给西方读者的。米尔卡·伊利亚德从全球范围视角研究萨满教的传统印象派就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料。尽管其著作研究的是西伯利亚萨满教,却很少涉及俄国民族考古学。因此,可以推断他并不懂俄语,研究过程中十分依赖俄语资料的译文。
一、对萨满教起源的研究
北方大考察开始后,乔治·帕拉斯和许多工作在西伯利亚的德国传统学术领域的探险家,辛勤地将土著人口进行了分类、记录。他们发现了一种“奇异的迷信”——萨满教。作为第一批科学收集者,他们不可避免地怀疑这种本土精神具有“迷惑性”。这种评价完全符合普遍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怀疑方法。很多探险家把萨满教降神误认为是欺骗的诡计也不足为奇。
著名的德裔俄国历史学家格哈德·米勒来到西伯利亚不仅是为了寻找矿藏,还为了寻找文化古迹,更是为了了解当地民族的历史。米勒来到阿尔泰山北部,这里居住着绍尔部落,他把其称作鞑靼人和特留特人,他有机会观看了一次萨满降神会。整个表演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只能说这些神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萨满发出让人不愉快的嚎叫,同时毫无意识地跳动并击打着一面内有铁铃的平鼓,使场面更加喧闹。”米勒强调这些萨满是神秘的骗子,应该受到谴责:“降神会持续的时间不长,它是一种无意义的闹剧,萨满用欺骗的方式谋生。萨满教仪式像是从家长到孩子的交易。”另一位学者约翰·戈麦林像米勒一样有机会身体力行去探究萨满教,深入遥远的地方进行调查。他认为这些普通的表演者即萨满欺骗了他们的信众,他们应受到惩罚,被流放到银或铜矿区。在其他德国研究者特别是18世纪前半叶的丹尼尔·梅塞施米特和乔治·斯特勒的文章中,用同样的研究方法揭穿了土著民族精神从业者的实质。
18世纪下半叶,尽管十分怀疑萨满教这种行为,启蒙学者们仍开始试着去探究这种“欺骗”行为的起源,并很快得出结论——萨满教是宗教。米勒和乔治总结出萨满教最早可能源于普通宗教。在《西伯利亚史》一书中,米勒推测萨满教曾在印度出现并逐渐传播到整个亚洲。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研究者承认萨满懂得如何掌握萨满鼓,认为土著民族精神从业者和传教士具有相同的职业特点。同时,帕拉斯认为萨满教是试着探究萨满文化起源的一种方式。这些学者并不赞成亵渎土著民族信仰的神圣性甚至对萨满们产生了同情与好感。同样地,乔治强调,萨满建立并维护了当地土著民族的传统。最早的浪漫主义学者之一的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否认启蒙科学,认为启蒙科学过于绝对,以至于否认土著居民正当的信仰。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他把所有去过西伯利亚旅行的人关于萨满教的见闻都集合在一起,并附上北美的人种学资料,承认萨满教是宗教。然而,赫尔德反对把土著民族精神从业者叫做“欺骗者”,并且认为萨满教是组织早期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因为萨满是混乱中秩序的建立者。
二、对萨满教内在文化的研究德国学者不仅对西伯利亚萨满教的起源进行了研究,同时也在探寻萨满教内部存在的文化,这包括萨满教神话故事、诗歌、音乐等文化因素。
在德国学者研究西伯利亚文化的过程中,宗教学者和作家无法忽视萨满教,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对于欧洲人来说,它是最具异域风情和吸引力的本土文化,同时萨满教也是最具有明显特征的古代本土传统宗教。第二,由于对俄国东正教的悲观态度,宗教学者自然而然地转向本土宗教。
基督教神学中很好重读土著精神教义的例子是瓦斯里-沃比斯基(Vasilii Verbiskii)的著作,他写出一部有价值的阿尔泰部落民族志(1870,1893)。以一次土著萨满教降神会为例,沃比斯基描述了年度的祭祀神圣乌尔根的仪式。在整个降神会过程中,萨满的行为和赞歌没有涉及本源,而只是关于行为准则,那是十分平常的练习。
沃比斯基把阿尔泰山部落萨满教多神划分为两类相反的神,乌尔根和埃利克,他们被描述成“善”与“恶”的代表。乌尔根,“至高无上的神”,可能是“最为善良的”,不像他的弟弟、“恶魔”埃利克,总是沉迷于给人们带来各种灾难。沃比斯基书中关于阿尔泰信仰特征的章节以这样的叙述开始:“根据阿尔泰人一般的信仰,世界有两个本源的规则:乌尔根,善的本源;埃利克,恶的本源。他们俩都管理许多精神,前一个是‘干净的精神,后一个是不干净的。”
安卓特·阿农金(1869—1931年),另一个宗教学教圈内的成员,对萨满教音乐有一定的研究。他强调“萨满教音乐代表了阿尔泰音乐的最高水平,意志薄弱的人们不能抵挡通过萨满传递的感受和力量”。对这些学者来说,“萨满教神秘表演”和“祈祷”的力量像希伯来人的诗歌:“同样清廉真诚呈现在一个简单的、但却十分敏感的灵魂上,同样的暗喻和同样自然壮丽的画卷”。
三、对阿尔泰地区萨满教的研究
萨满教主要存在于操满一通古斯和突厥语族的民族中,而这两类语族又同属于阿尔泰语系。因此,阿尔泰地区萨满教信众多,信仰方式复杂多样,许多德国学者都来到阿尔泰地区对当地萨满教进行研究。
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邦吉于1826年旅行至阿尔泰山寻找植物和矿产,同时对阿尔泰地区萨满教进行探究。一方面,邦吉称土著萨满是具有技艺的“欺骗者”;另一方面,他传达给读者一些没有缘由的理论,他只是本能地描述土著仪式包括萨满教的降神会。事实上,他十分清楚,尽管他以前的目标是收集关于这个地区的植物和地质信息,实际上他经常跋涉很长的路去调查土著人生活和信仰。他并不受阿尔泰人欢迎,但他仍试着参加降神会去“见证欢庆的场面”,听“萨满鼓迷人的声音”。邦吉不但描述降神会,而且在旅行过程中当他的话语成功在当地土著部落中传播时,他成为一名“土著”医生。尽管缺乏对植物和古迹的研究,没有遵循“游戏规则”,但作为一名“土著”医生,在治疗的“仪式”上他收到了毛皮礼物。一次,邦吉与一位土著萨满交流经验时,这位土著萨满用公羊的肩胛骨给邦吉呈现了一场预言仪式。
第一次全面考察西伯利亚萨满教,并且对西伯利亚萨满教研究产生很大影响的西方观念学者是威乐汉姆·拉德洛夫(Willhelm Radloff)(1837—1918年)。他是一位德国东方学家,移民至俄国并改名为卫斯理·卫斯理维奇·拉德洛夫(Vasilli Vasilievich Radlov),之后他成为俄国人类学院院长之一。在一些领域,拉德洛夫在俄国人类学上扮演的角色可以同另一位德国人法兰兹·鲍亚士对美国人种学的贡献相媲美。这位刚从柏林大学毕业的学生,急切地在18世纪60年代,探索研究南部西伯利亚不符合规律的语言学以及形成的人种地理。他出版了《人种学信件》(18世纪60年代),然后他又重新研究出版了《西伯利亚》(1884),这些著作成为研究西伯利亚萨满教的俄国和西方学生的人类学经典。
自从第一次踏上阿尔泰的土地,拉德洛夫就执著地寻找并观看本土萨满活动的场景,找机会观察萨满教降神会并从中得到准确的证据。在某些方面,他的日记撰写过程是很曲折的,“萨满,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成为我们研究的有力来源,通常是害怕揭露他们的秘密。他们身边都要围绕着神秘的空气,这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是非常重要的。”他曾见到两个曾经是萨满的人,他们转变了信仰成了基督教徒。他希望这些精神实践者可以口述在仪式上他吟诵的赞美诗的最后一部分。很遗憾,一位萨满回答说,“我们以前的神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如果他能像我们一样学习,他就可以想象出他所做的事情,在万物之上,背叛了他。我们甚至很害怕俄国的神灵会发现我们是如何谈论以前信仰的神。那时候谁会来拯救我们?”拉德洛夫唯一记录下来的和人种学者分享的是一个来自倍查特(Bachat)村的特鲁特(Teleut)萨满做的简短的感恩祷告,做一个仪式为家中有人去世清理房屋。在接下来的仪式中,拉德洛夫最后有机会感受类似于哥特式传统的萨满教降神会,这种仪式他曾在德国和波罗的海的德国旅行者来到西伯利亚所写的书中读到过。清理仪式包含萨满教著名的“狂喜”因素,这在20世纪成为学术上的暗喻。拉德洛夫可以听到“野兽的叫声”并伴随着剧烈的跳动,接下来是疯狂的舞蹈,一位精疲力竭的萨满倒在地上:“看了一会这种野性的场景、被火燃烧的神秘兴奋,萨满给我一种强烈的感觉:他已经完全忘了他现在是谁了。阿尔泰人也被这种野性的场景震撼。他们把口中的笛子拿出来保持长达15分钟的死一般的寂静。”
不同于牧师和许多世俗研究者,拉德洛夫把萨满教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放在同一位置上,并且总结出,“萨满不比其他宗教的传教士逊色”。在欧洲观众的眼中,萨满开始合法化,道库恰耶夫写道,“可怜的萨满不像以前认识的那样糟糕。他们为其民族输送伦理道德”。
德国学者、学术界对西伯利亚萨满教进行了极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对俄罗斯本土学者研究西伯利亚萨满教起到了引导作用,对萨满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责任编辑: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