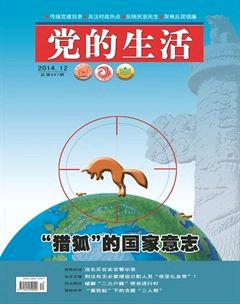刑法有无必要增设公职人员“收受礼金罪”?
王雪+杨天军+曹元新

编辑点评: 收礼入刑是否势在必行,围绕科学立法据理争鸣
话题背景:据《京华时报》报道,9月27日,在北京举办的2014年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高峰论坛上,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陈兴良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拟设置“收受礼金罪”。这一罪名是指如果公职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都可以认定为此罪。这条消息被媒体发布后,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不过,在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官网公布的相关草案中,“收受礼金罪”的条款并未列入。对此,草案说明解释:“考虑到这些问题各方面认识还不一致,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未列入本草案。”尽管如此,围绕这个话题的争议仍在继续。有人认为,“收受礼金罪”能有效遏制公职人员以礼尚往来名义掩盖受贿行为,是密织法网的客观要求;也有人觉得,增设“收受礼金罪”既无必要,又不具备可操作性,很容易沦为“口号立法”。本刊邀请持不同观点的两位嘉宾——法学学者杨天军和资深检察官曹元新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正方:剑指托词,能有效遏制礼金腐败
反方:多此一举,可修改法条解决难题
主持人:我注意到,前些日子发布的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意见指出,利用节庆及婚丧嫁娶之机收受礼金问题,在多个被巡视地区和单位仍然存在。自中央八项规定发布至今年9月30日,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六万多个,其中“大操大办婚丧喜庆”“收送节礼”的违纪问题发生率排名第四,5000余干部因此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对比这组数据,关于增设“收受礼金罪”的话题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对此,杨老师怎么看?
杨天军:我认为应该增设“收受礼金罪”。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定罪除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外,还必须满足“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在多年来的司法实践中,一些贪官虽然收受了巨额财物,却以“礼尚往来”、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作为抗辩理由,从而逃避刑责。这种制度性缺陷加剧了“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现象的出现。我看过一份资料——2011年,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和南京大学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对正在服刑的150名贪官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服刑贪官认为,过年过节收受的购物卡、代金券以及高档烟酒等日用品,都是“礼尚往来”幌子下的受贿行为。倘若能增设“收受礼金罪”,将有助于改变这一现实。11月15日,《新京报》与优数咨询公司联合推出的“京报调查”,曾就此问题访问了1003人,其中有59.3%成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增设“收受礼金罪”。
曹元新:我不赞成杨老师的观点。事实上,公职人员收受下属或服务对象的礼金后,大多会为对方谋取利益,收受礼金之举极易转化为受贿行为。对于这一点,即便没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人都能想清楚。再者说,公职人员收受礼金又不构成受贿犯罪的,纪检监察部门完全可以依党纪政纪对其做出撤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处理。其实,这些处分的威慑力,如果执行到位并不亚于刑罚。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增设这项罪名,只需将收受礼金行为纳入受贿罪惩处范围即可。
杨天军:如果将公职人员收受礼金行为都以受贿罪来定罪量刑,势必打击面过大且处理程度过重,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也脱离当今人际关系交往的国情现实。我们要看到,“收受礼金”之所以成了“问题”,就在于一些公职人员可以通过某种借口将受贿行为“合情化”,以规避犯罪。一旦案发,只要公职人员尚未为他人谋取利益,则无法定罪。比如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受贿案,检方原来指控,辽宁天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焦某为与马向东密切关系,通过他人送给马向东50万元。而法院审理后认为,马向东虽然收取了焦某的钱财,但没有为焦某谋取利益,所以不能定为受贿罪。类似情况可以说不胜枚举,因而凸显了增设“收受礼金罪”的现实针对性与必要性。
曹元新:应该看到,“收受礼金”极易转化为“受贿”,其实两者并无本质区别。我很认同刑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阮齐林教授的一个观点。他说,在司法实践中,公职人员收取大额礼金,虽然送礼者没有明确请托事项,但只要送礼者和收礼者存在职务上的管理关系,就可以认定为受贿罪。不仅仅是收受礼金,包括接受古玩、字画、性贿赂等不当利益,只要侵犯了职务的廉洁性,司法上就应当认定为“受贿”。如果单独设“收受礼金罪”,将破坏受贿罪的逻辑体系——刑法明明已经有受贿罪条款,为什么还要叠床架屋新设一个“收受礼金罪”?我倒是觉得,将公职人员收受礼金行为纳入受贿罪惩处的范围,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主持人:对于收受礼金行为,其实二位都认为应当从法律上予以约束,分歧在于罪名如何归类。有学者认为,基于目前的国情现实,恐怕不宜将收受礼金行为一律入罪,需要有一个入罪底线。我注意到,在关于增设“收受礼金罪”的议论中,也有一些网友提出“收礼与受贿难以区分,这个罪的刑罚标准怎么定、收受多少礼金算犯罪”等疑问。对于这些操作层面的问题,杨老师怎么看?
正方:定罪量刑需逐步完善
反方:标准不清致操作困难
杨天军:针对这项新罪名的动议,社会舆论有一些操作层面的担心也很正常,毕竟立法是一个充分论证和逐步完善的过程。我觉得,要想让“收受礼金罪”具有可执行性,首先必须在法律上给“收受礼金罪”定性。在我看来,如果公职人员为送礼者谋取了利益,自然就应该按受贿罪论处;但如果只是收受礼金,并未为他人谋取利益,按照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来看,还够不上受贿,这种情况就可以用“收受礼金罪”进行规制。另外,“收受礼金罪”的立案标准和起刑点可以与受贿罪一致,不能太高,且可以按年累计,以免变相纵容公职人员持续性地收受小额、中额礼金。
曹元新:您的想法未免过于理想化了。公职人员也需要人际交往,彻底杜绝公职人员的礼尚往来是不现实的。如果因为红白喜事或探望病人,熟人、朋友之间相互赠送几百元、几千元的,并不涉及利益交换,如何进行法律上的认定?就算增设了“收受礼金罪”,首先在确定起刑点上就面临着“两难”困局——如果不划定起刑点,司法执行就会有相当大的难度;如果划定了起刑点,就等于公职人员只要收受的礼金数额不超过起刑点,行为就是合法的。换句话说,如果起刑点定低了,将会与正常的人情风俗相冲突;如果起刑点定得太高,适用群体就会很小,起不到应有的惩治作用。
杨天军:在这个方面,一些国家的相关法律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比如,新加坡规定,公务员接受礼品金额不得超过50新元(约250元人民币),超过部分必须上缴或个人出资买下;德国规定,官员收受礼品价值不得超过50欧元(约500元人民币),否则要受到警告、严重警告、开除公职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的处分。
曹元新:立法必须立足国情、着眼现实,并非简单借鉴域外经验就能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学者总结,增设“收受礼金罪”将面临“三难”:“礼金定量之难”“行为定性之难”“公平执行之难”,这些都将直接影响其可操作性。依我看,之所以有很多人支持增设“收受礼金罪”,说到底还是因为制度性尴尬——明明是受贿,又不能以受贿罪追责。扩大受贿罪的范围是解决这个问题最现实的路径。
主持人:曹检察官强调增设“收受礼金罪”面临着“三难”困境,而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某些受贿行为不能以受贿定罪的司法尴尬。正是因为这些困境与尴尬,才会在很多地方出现以礼尚往来为幌子的“事实行贿”与“事实受贿”,才会导致党风政风以及社会风气的不断恶化。那么,如果在两难境地中增设“收受礼金罪”,利大还是弊大呢,这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杨老师显然是认为利大于弊的吧?
正方:增设罪名能让反腐更有力
反方:顾此失彼带来反腐新漏洞
杨天军:对,我认为利大于弊。因为增设“收受礼金罪”,能够加大对公职人员收受礼金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公职人员借收受礼金之名贪腐的违法成本。如果公职人员在接待“送礼人”时顾及触犯“收受礼金罪”的风险,就可能拒绝“收受礼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既然行贿与受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那么“馈赠礼金”与“收受礼金”也是同样道理,如果超过一定限度,送礼者也要顾及是否触犯法律的问题。
曹元新:我认为,在动议设置“收受礼金罪”时,不能不考虑到设置此罪可能带来的负效应。按照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的说法,“收受礼金罪”的量刑比“受贿罪”轻,这在客观上将引导一些受贿的公职人员想方设法往“收受礼金罪”上靠,最终导致重罪轻判。近年来,饱受争议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前车之鉴。在著名的“表哥”、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一案中,他因受贿25万元被判10年,因504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6年,两项罪名案值和量刑的巨大反差,再度让很多业内人士质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的必要性。可以断言,增设“收受礼金罪”会给司法机关查处和审理案件带来麻烦,也将给犯罪嫌疑人提供钻法律空子的机会。
杨天军:认为“收受礼金罪”的设立将为贿赂犯罪提供“避风港”的观点,显然忽略了刑事证明责任的存在。检察机关在控诉受贿罪的过程中,由于举证方面的原因,往往不能证明行为人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时有收受财物的故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退而求其次”,按照“收受礼金罪”提出处罚意见,这样就可以发挥本罪的堵截作用,防止腐败公职人员逍遥法外。这有利于司法实践中对案件性质的判断,可以把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之笼织得更细密、更科学。
曹元新:不改变治腐理念,专注于走增设法条、细化罪名的技术路线,是扬汤止沸的权宜之计。某些行为一旦被具体化、详细化,就意味着“法无禁止即可为”。罪名只能有限增长,而贿赂方式却在不断增加。以增设罪名的方式反腐,在战略上只是消极的防守战。所以说,以简单明了的受贿罪法条应对变化无穷的腐败行为,方可“以无招胜有招”。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在中央强力反腐的大背景下,要不要增设“收受礼金罪”,是一个严肃的法治命题。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下,首先需要从立法的角度分析问题,堵塞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漏洞,消除司法实践中的灰色地带,从而对职务犯罪严格规制、严厉打击。应当说,法治反腐的程度最终决定着反腐的成效。法治反腐首先要求“良法之治”,即需要一套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符合现实国情的反腐败法律制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进行这样的争论与探讨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