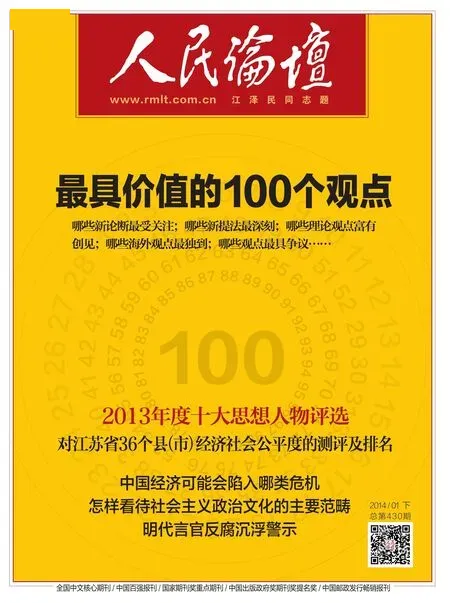透过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看中国维稳困局
张 敏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凸显,近年来民众为维护自身权益经常发生群体性事件,如2008年瓮安事件、2009年石首事件、2010年马鞍山事件、2011年乌坎村事件等。探讨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及解决路径,就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理性或非理性: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解释机制研究
群体性事件可以看作一种激烈的社会利益表达形式。这种形式主要的特点在于其参与者数量较大,并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破坏。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学者们提出了从不同角度提出多种解释机制,下面简单介绍几种影响广泛的解释框架。
框架一:传统的社会解体理论范式。美国早期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理论是在勒庞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起步的。勒庞的理论核心是心智归一法则。勒庞认为,人作为个体是理性的,但是在群体中其思想和思维方式将会逐渐变得和群体保持一致,变得非理性,迷信权威和领袖,欺负弱小。①在他看来,群体性事件值得肯定的很少,因为它们都是非理性产物。
在勒庞的社会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理论有布鲁默德循环反应理论、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斯宾尔塞德加值理论等,这些以勒庞的社会心理学为中心的理论被统称为社会解体理论范式。布鲁默认为,群体性事件源于社会变迁引起的不安,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分为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三个阶段。在三个阶段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相互感染并持续加强,直至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认为,个体人怀有价值期望,社会具有价值能力,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如果个体人的价值期望无法从社会价值能力中得到实现时,就会有被剥夺的感觉,这种感觉越强烈,个体人反抗的意念就越强烈,对社会的破坏就越大,这就是格尔所谓的“挫折-反抗机制”。斯梅尔塞的价值理论认为,集体行为的产生,取决于社会结构诱因、人们的负面情绪、大众信念的形成、引发集体行为的事件或因素、动员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弱化等六个方面因素,社会中这六个方面因素越多,群体性事件发展概率就越大。
框架二: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范式。20世纪60年代,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在在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与传统社会心理学视角不同,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都将群体性事件看作是带有政治性的行为,而不是病理性行为。传统社会心理学用“非理性”特征来解读群体事件参与者,而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则对此完全持相反观点,指出其恰恰是理性的参与者,认为其参与群体事件时摈弃了感性色彩语言,而使用了利益、兴趣等带有强烈理性色彩的话语。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范式都强调强调组织力量和政治机会在群体性事件发起和发展中的作用。政治过程理论是西方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强调群体性事件是政治性而非病理性的行为,政治过程理论同时重视组织、社会网络、机会和策略这样的微观和中观条件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但是,政治过程理论过度强调了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微观机制而忽视了宏观因素;在微观机制中,政治过程理论又过多地强调了理性选择、策略、组织和网络以及政治机会在群体性事件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从而忽视了情感、文化文本、空间环境等其他因素对群体性事件的起源和动态的影响。
框架三: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赵鼎新在分析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国家社会关系理论。②他把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条件概括为变迁、结构和话语三个因素,并认为这些因素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一成不变的关系。认为在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中我们所有的仅仅是一些分析问题的切入点,而不是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这三大视角的核心和有机连接点就是国家社会关系。现代社会群体性事件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和组织起来的社会之间相互碰撞的产物。一个国家一旦发生了群体性抗争事件之后,它的发展走向也取决于该国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
在政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赵鼎新指出,决定一个群体性事件的兴起和发展轨迹的是一个社会中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群体性事件背后的国家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宏观结构条件对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方式,以及这些宏观结构条件和微观机制在该群体性事件中所呈现的特定的作用方式。
必然或应然: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分析
首先是因为当今中国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在中国改革进程中,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对中国传统稳定的社会结构形成巨大冲击。在城市国企改革中,国企工人“国家主人翁”的感觉变成不复存在的回忆;农村城市化改革,造成大量失地而就业无门的农民,地位下降的民众不满情绪积压;城乡交流、地区间交流的加快促进了区域间的人口流动,刺激了社会的离异,社会的离散化大大加快,社会呈现“碎片化”;市场化拉大了贫富不均,社会财富的“马太效应”造成了贫富阶层之间的社会紧张;不完善的社会制度给不法商人的违规运营和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提供了机会,而这又在大量消耗合法性资源,造成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这些都是当前社会中存在并逐渐凸显出来的社会不和谐因素,它们加剧了社会不公平,造成了社会紧张。民众受教育水平和组织能力的提高使其表达自身意愿的要求和积极性增强,向政府施压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潜在、积压和新催生的矛盾开始交织、喷发,成为中国目前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是因为当前群众利益表达机制阻塞。体制内维权渠道的阻塞和高成本是促使民众转而诉诸群体性事件来维权的主要原因。而造成体制内维权渠道不畅的根源可以归结于中国政治生态背景、中国政府的民权观和“政府玻璃墙”的存在。第一,就中国政治生态背景而言,中国政府官员的命运是由上级政府掌握,底层选民的话语对官员的仕途影响微弱。这就造成中国官场的唯上主义风气,各级政府努力向上层展示其功绩,而对底层民众的个体利益置若罔闻。第二,就国家与社会关系而言,国家强大而公民社会弱小,维权者掌握的资源的稀少,社会组织发育欠缺,维权者难以寻求有效帮助。中国现有的单一体制内维权渠道加大了民众的维权难度和维权成本。
第三是因为现存政绩考核机制扭曲。稳定在中国政府官员中起着一票否决的作用,政府官员为自身政绩,竭力维持面子,形成政府官员怕曝光”弱点,导致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病态上访。有利益诉求的群众在体制内方式行不通的情况下,采取群体性事件这种影响社会秩序的方式寻求维权,便成为底层民众的一种不得不考虑的备选方案。
最后,谣言的传播也导致了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在群体性事件中,谣言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2009年石首事件为例,原本是一名青年厨师的命案,法医未查清死亡原因提出解剖尸体,遭到家属拒绝后双方僵持。可是之后经过无数版本谣言的发酵后,演变成敏感的权势阶层欺压弱势群体,而警察帮权帮富不帮理的事件,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其中,迅速升级为群体性事件。
刚性稳定维稳结构与维稳困局
现今社会矛盾凸显,群体性事件频发,维稳一直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个重要执政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孙立平提出“断裂社会”来描述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③面对这些风险,执政者为了维系自身的执政地位,采取偏离国家利益的措施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刚性稳定结构的特征:以排他性、闭守性的政治权利为基础,以对社会的绝对控制作为目标,将一切抗议视为无序和混乱,采取一切手段打击和压制。
刚性维稳模式产生巨大的维稳成本,不仅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产生高昂的政治成本,包括社会资本的消耗、干群关系的疏离、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削弱等。仅从经济成本上看,唐皇凤指出天价维稳会增加地方财政的压力甚至财政危机,并且经济欠发达地区维稳支出通常高于发达地区维稳支出,这导致很多地方政府负债经营。④在刚性稳定结构下,社会稳定作为考核党政官员的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对地方官员起着一票否决的作用,有些地方不惜牺牲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利益来维稳,造成民众利益正常的表达渠道阻塞,导致现阶段弱势群体不满情绪的不断积聚。
在刚性稳定结构下,我国各级政府每年在维稳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资源,但是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却逐年上升,由此导致了“维稳怪圈”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民众表达利益的渠道被阻塞,矛盾积累,却又在刚性稳定结构下被压制,一旦矛盾积累到无法承受的程度,就会大规模爆发,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而且在刚性稳定结构下,由于群众诉求的大多数问题并不是基层这个层面的政府部门所能解决的,基层政府只能采取截访、拘留等手段打压闹事群众,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更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第三,由于资源有限,地方政府对一些问题采取敷衍的态度;而如果百姓闹事,政府为了维护稳定局面,对产生较大影响的问题却优先解决,解决的力度基本上也与问题的影响程度呈正相关,这就形成问题“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现象。敢于闹事者问题往往会得到妥善解决,而安分守己者问题则得不到解决。这实质上是在鼓励百姓闹事,诱导社会的不和谐。
新型维稳路径
新型维稳体制必须具备两个功能:第一,提前预防、及时引导社会负面情绪最大可能减少不稳定因素的社会能力。第二,能够包容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缓冲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冲击力。为此,笔者在现阶段具备的条件下提出以下几项尝试性建议:
首先,正确认识群体性事件,理性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马克思强调的是社会冲突的破坏作用,是一种功能失调的社会病态。将社会冲突视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和表现,忽视了社会冲突的积极功能。社会冲突反映了一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具有促进社会系统的整合性和适应性的作用。部分群体性事件也可以称为“社会泄愤事件”,有不满情绪的群体在社会冲突中将怨愤发泄,如果社会系统能据此做出回应,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詹姆斯·斯科特提出“社会伦理”来解释东南亚的农民抗争运动,解释我国目前的农民工的维权抗争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面对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压力,他们首先诉诸生存取向而非利益取向,在生存保障未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们宁愿选择忍受。我们在分析通过非正常途径进行维权的事件时,我们应该明确:维权主体是理性人。在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能够顺利地保障自身权益的情况下,理性人是不会冒险选择非正常途径维权的。在中国目前体制下参与群体性事件也面临被拘捕的危险。所以说,群体性事件这种激烈的社会冲突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现行的体制触及了维权主体的生存底线。
其次,在正确认识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保障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使民众能够通过体制内的方式来实现利益诉求。主要措施包括培育社会组织,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育成长,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保证公民维权的组织力量;进一步增强政府工作人员“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切实保障新闻自由,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作用,在群体性事件中,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已初见成效。
再次,在群体性事件中,地方政府理念要由对抗转向治理,树立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对于地方政府执政实践至关重要,因为其表明了某种政治秩序被社会肯定的作用。地方政府的对抗态度往往是一个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导火索,瓮安事件、石首事件、乌坎事件爆发和升级的因素中,地方政府的对抗态度是重要因素。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地方政府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对抗与镇压。调动警察和防暴部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应对措施。而地方政府对抗性的态度往往容易激怒聚集起来的民众,使群众情绪失控,也为具有不良动机的人提供了煽动群众的机会。在此情况下,发生暴力冲突、流血事件便是不可避免的。对照之下,美国纽约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蔓延到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波士顿、丹佛等全美多个城市,但是却只在示威群众阻断交通、冲击博物馆时遭到警察的驱逐,大部分情况下处于和平状态,骑警和防暴部队始终处于准备阶段,更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这为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最后,建立一种维护群众利益导向的官员政绩评价机制。政府权力来源于大众对权利的让渡,作为执政行为具体实施者,政府官员的政绩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在西方,政绩不好的执政党会失去执政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政绩不良持续下去会导致制度合法性危机。因此,我国相当长时期内,政绩导向将是难以替代的。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一种基于顶层设计且将群众满意要素纳入其中的官员考核机制将是必要的。根本措施在于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分配体制。社会不公、贫富分化严重是社会矛盾的根源,改革分配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增加民众满意度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通过“二次分配”,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成果更公平更多的惠及全体民众。
【注释】
①Bert Useem. Breakdown 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4(1998), p215~238。
②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7~29页。
③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④唐皇凤:“‘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9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