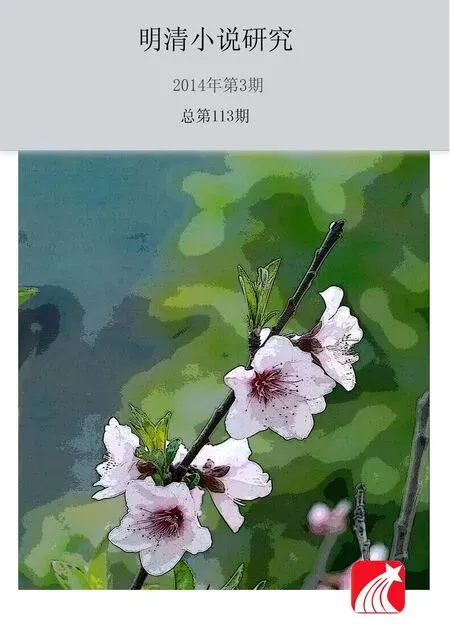《杜骗新书》福建地方属性考述
··
《杜骗新书》福建地方属性考述
·吴朝阳·
明末通俗作品《杜骗新书》,近年来得到学术界较多的关注,涉及词语解释、版本源流、作品性质及其历史背景、社会影响等等。不过,其作为通俗作品的地方属性特别是与福建地区的密切关系,却从未有学者提及,而此一问题无疑是《杜骗新书》研究的关键之一。本文通过对《杜骗新书》中的闽方言特点、人物的地方属性、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等几个方面的探讨,力图对此一问题有所揭示。
《杜骗新书》 福建方言 地方属性
一、《杜骗新书》与福建方言
先看语词方面。
(一)“水城”。见《杜骗新书》中第九类“谋财骗”之《盗商伙财反丧财》。曾昭聪谓“二人相隔一墙而住,故刘兴所挖水城,实即是为偷盗而挖开的墙洞”,认为其中的“城”是“城墙”之意,而“水”指钱财①。赵红梅与程志兵则认为“水城”是“排水沟、阴沟”,词中的“水”与钱财之义没有关系②。事实上,曾氏所言固不正确,赵、程的改释亦为失误。“水城”之“城”原字应作“墭”,所指是一种置于室内的大型容器。而明清二代有所谓“皇史宬”,其“宬”字的音、义以及构字方式,也与此“墭”字一脉相承。
“墭”作为一种自古以来南方人常用的大型室内容器,在1960年代的福建农村还可以见到。《康熙字典》“墭”字条引《集韵》,解释为“盛物器,与‘盛’通”③。福建农家以前常用这种容器储存谷物,但也有用以储存水或其它物品者。其中,用以储存谷物的称为“谷墭”,由于这种“墭”一般以木为之,所以闽南语的俗字中改以“木”为偏旁④。
《杜骗新书》有两则故事出现“墭”,除《谋财骗·盗商伙财反丧财》中的“水城”外,还有《买学骗·银寄店主被窃逃》中的“土库城”。两处都写作“城”:
(1)(刘兴)在福建省城陈四店卖,房舍与(张)沛内外……一日,有客伙请沛午席,兴将水城挖开……陈四亦老练牙人,四顾兴房,兴所挖水城,已将物蔽矣……沛开房门,看衣箱挖一刀痕,遂曰:“遭瘟。”待开看,银悉偷去,四顾又无踪迹。陈四入兴房细看,见水城挖开……(《谋财骗·盗商伙财反丧财》)
(2)(棍)用银七十两买屋,内系土库城,外铺舍开一客店……店主出曰:“列位与此客议封银事,客人难防,这门壁浅薄,若夜间统人来劫,可要提防。依我说可藏入我城门内,你外间好心关防,可保安稳。”三秀才曰:“是也。”共将六皮箱银,都寄入店主家内去。(《买学骗·银寄店主被窃逃》)
第(2)则中,店主“棍”所买是一所房屋,当然不可能分处城内外,因此,“土库城”三字必然是一个词,而且所指之物位于屋内。“棍”为达到窃银目的,劝“客人”将三千两银“藏入我城门内”;客人也依其言,将银两“寄入店主家内去”。可见,店主屋内这个“土库城”是一个室内的、有“城门”的、具有储存物品功能的容器,这与《康熙字典》中“墭”字的解释正相符合,与闽南方言也合若符契。
明白了“城”为古语及闽南语所说的“墭”,而它在具有商业用途的房屋中的功能与现代保险柜约略相似,《谋财骗·盗商伙财反丧财》故事中的相关情节就容易理解了。张沛藏银的衣箱本来存放在具有保险柜功能的“水城”之内,刘兴所住“房舍与(张)沛内外”,而“水城”依墙而建,因此刘兴挖通自己房间的墙壁,可以从“水城”背后将其挖开。可见,此故事中的“水城”正是“墭”。
(二)“亢傲”。《引赌骗·好赌反落人术中》一则中,谓徐华胜“为人矜夸骄亢”、“素性亢傲”;《谋财骗·傲气致讼伤财命》中,魏邦材“为人骄傲非常”,文中则谓“况材亢傲”,又有“始知侄为人亢傲”之句。可见“亢傲”是一个固定词,其词义同于“狂傲”。在泉州闽南语中有一个意思相同的常用词,此词在漳州厦门一带词义近于“狂而愚”,周长楫《闽南方言大词典》写作“圹怣”⑤。按当前闽南语读音,“亢傲”与“圹怣”音调全同,读音中也仅是后一字的韵母有阴阳之别。根据词义和读音,可知这个词本应依此处所引写作“亢傲”。
(四)“姆婶”。《杜骗新书》中“姆”、“婶”出现数十次,“姆”、“婶”并称、对称时指“妯娌”,其中“姆”即是《康熙字典》所谓“弟妻谓夫之嫂”⑦,“婶”则是“兄妻谓夫之弟妇”。而“姆”若用在非亲属身上,则用作年长妇人的称呼。为讨论方便,姑引数例如下:
(1)两妯娌并坐,适有卖油者过。婶石氏曰:“家下要油用,奈无银可买。”姆左氏曰:“先秤油来,约后还银未迟。”……有人叫卖肉,姆婶二人叫入,各秤二斤,吩咐再来接银。(《妇人骗·哄婶成奸骗油客》。按:本篇此后十数次称左氏为“姆”而称石氏为“婶”,例繁不具引。)
(2)有三妇轻身同行,遇马夫牵回马三匹,三妇各租乘一匹。末婶曰:“伯姆善乘马者先行,我二人不善乘者随后。”……妇指马夫曰:“快去扶我小姆。”……次姆曰:“我跌坏了,前去须买补损膏药贴。只好随路歇,赶不得稍头。你前去,叫我大姆少待。”(《妇人骗·三妇骗脱三匹马》)
(3)“你声音似我邻居王二姆一般,千万叫我娘与哥来认我……”王二姆听其叙来历皆真,收留入家……(《伪交骗·刺眼刖脚陷残疾》)
闽南方言中伯母称为“(阿)姆”,婶母称为“(阿)婶”,因此口语中“妯娌”常从子辈称呼而作“姆婶”或“婶姆”。在闽南口语中“姆”、“婶”均可以单用,分别是“弟妻谓夫之嫂”和“兄妻谓夫之弟妇”之称,与《妇人骗·哄婶成奸骗油客》中的用法相同。而上引《妇人骗·三妇骗脱三匹马》篇中“大姆”、“小姆”、“末婶”等均是闽南语常用,并且是除《杜骗新书》外而未见于其他明人通俗小说的称谓。此外,《伪交骗·刺眼刖脚陷残疾》中的“王二姆”意思等于普通话中的“王家二伯母”,这种以“姓+丈夫排行+姆”方式构成的称谓,也是闽南方言中的惯用称谓。
我们注意到,明人小说如《警世通言·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存在与闽南语中的“姆”、“婶”等价的“姆姆”、“婶婶”二词⑧,而《杜骗新书》中也多次出现“伯姆”一词。但“姆姆”、“婶婶”是叠字词,与闽南方言所用的单字词有实质上的差异。而《杜骗新书》中出现“伯姆”一词,是撰写者同时也使用当时通用白话的缘故。因此,书中“姆婶”和“姆”的准确含义与用法,确应如上以闽南语做出解释。
(五)“寄”。《杜骗新书》全书出现“寄”字三十余次,绝大部分与普通话中的“寄”字意思、用法均相同,但有四个地方颇为可疑,仔细考察后可以断定它是闽南语词。四处原文分见两条:
(1)左氏扯住曰:“我报你知,你须谢我。”卖油者曰:“明日寄两斤油与你。”过数日,果寄油来。姆又变说,持与婶曰:“……卖油者心虚,许我两斤油,今果寄来。此是你换来的,须当补你。”(《妇人骗·哄婶成奸骗油客》)
(2)店主出曰:“列位与此客议封银事,客人难防,这门壁浅薄,若夜间统人来劫,可要提防。依我说可藏入我城门内,你外间好心关防,可保安稳。”三秀才曰:“是也。”共将六皮箱银,都寄入店主家内去。(《买学骗·银寄店主被窃逃》)
在《妇人骗·哄婶成奸骗油客》故事中,卖油客被左氏勒索时,回答说“明日寄两斤油与你”。这里的“寄”字值得仔细研究。依常理,卖油客在此妯娌家附近卖油,答应的两斤油应该自己送上门而不必托付别人,故正常回答中“寄”字处应是“拿”、“取”之意。尤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两斤油涉及男女奸情,所以卖油者为避人耳目应该亲自送才是。因此,本篇故事的“寄”字若理解为“寄托”他人之“寄”,则情节不合常理,若理解为“拿(来)”、“取(来)”之意,故事才会显得符合情理。再看《买学骗·银寄店主被窃逃》故事,其中写道:“共将六皮箱银,都寄入店主家内去。”如果将其中的“寄”字理解为“寄托”他人之“寄”,则“都寄入店主家内去”句语法欠通,全句是一个的病句。而若“寄”字训为“搬取”,则“寄入”即是“搬入”,全句便文从字顺,妥帖而无语病。
总之,从以上两个例子看,其中四个“寄”字应是方言用字,应该有“拿”、“取”之意。而我们发现,这个方言字是闽南方言常用的单字。据《闽南方言大词典》“揭”、“寄”两条⑨,以及“揭(二)”条⑩,在闽南语中“揭”字的意思是“举起”、“拿”、“抬起”,是最常用的日用动词之一,而“寄”与“揭”在闽南话中的读音仅仅是声调略有不同。因此,从音、义分析,以上所引的几个“寄”字,正是闽南语“揭”字的讹写或俗写。
(六)“大巡”。《谋财骗·傲气致讼伤财命》叙魏邦材“又奔大巡、军门、各司、道告,及南京刑部告,然久状不离原词,皆因原断”。《露财骗·诈称公子盗商银》则有“本府不能判断。栋又在史大巡处告”。两则故事中出现的“大巡”一词,是福建、广东民间明、清以来对巡抚都御史、巡按监察御史、按察史司按察史等的惯用称谓,至今福建乡村和台湾还有很多供奉“五大巡”、“七大巡”、“九大巡”等等的庙宇。“大巡”是一个闽、粤俗文化词汇,正式文献中很少出现,但明朝符锡《新浚韶郡东河堤记》文中仍称巡按御史陈大用为“大巡陈公大用”,可以作为本条新释的旁证。
(七)“和”。《杜骗新书》的《谋财骗·傲气致讼伤财命》中多次出现与其常用义不同的“和”字:
(1)(魏邦材)屡出言不逊,曰:“你这一起下等下流,那一个来与我和。”动以千金为言。又曰:“一船之货,我一人可买。”如此言者数次,众毕不堪,大恨之。
(2)时有徽州汪逢七……不忿材以财势压人……材怒其敌己,曰:“船中有长于下流者,有本大于下流者,竟无一言,你敢挺出与我作对,以丝一百担,价值数千金,统与你和。”逢七骂曰:“这下流,好不知趣,屡屡无状,真不知死小辈也。我有数千金与你和,叫你无命归故土。”二人争口不休,众皆暗喜汪魏角胜,心中大快。有爱汪者相劝,各自入舱。
(3)次日,李汉卿背云:“幸得汪兄为对。”材听之,乃骂汉卿而及逢七,语甚不逊。
曾昭聪认为此“和”字“当为‘斗’义”,而此义源自其“掺和”、“混杂”之义,此一释义显为错误。在以上引文中,“暗喜汪魏角胜”意思与“幸得汪兄(与魏邦材)为对”相同,“与你和”即是“与你作对”,而“与我和”也与“与我作对”同义。因此,这些“和”字无疑就是“作对”的意思。事实上,闽南语中有一个意为“作对”的单音词,依读音可以写作“和”或“回”字。值得指出的是,“和”字的这个义项其实早已出现,古代诗人写作“和诗”,相互“唱和”,其“和”正是“对手回应”的意思。事实上,可以说“和”字有“作对”的意思并非是闽南语的特别用法,但因为闽南语是俗话而非文言,因此这里引闽南语作注释无疑更为恰当,更有说服力。
(八)“嫁”。《杜骗新书》中“嫁”字共出现近三十次,除了两处之外,其用法都与“嫁娶”的“嫁”字相同。然而《妇人骗·佃妇卖奸脱主田》中的两处“嫁”字,语法却有些特别。这两处相关文字如下:
(1)(佃户)知其完了,在房外高声喝曰:“你和甚人讲话。”打入门去,二人忙不能躲。佃户喝曰:“嗳也!你这贼奸我妻!”便在床上揪下打,妻忙起穿衣,来拿夫手曰:“你嫁我,我不在你家。”佃户曰:“这花娘也要打死。”三人滚作一团,也不能打得。
(2)主人……曰:“我不管你有套否,今晚更与我睡一夜,便当送你。”佃母连声应曰:“凭媳妇。”妇曰:“拼定陪你。男人若有言,嫁我便是。”
当佃户捉田主人与其妻之奸,揪打田主人时,其妻“忙起穿衣,来拿夫手”,说“你嫁我,我不在你家”。后来此妇为多索田地再陪田主人过夜,又说“拼定陪你。男人若有言,嫁我便是”。考察对比可以发现,除了这里两处“嫁我”中的“嫁”字,《杜骗新书》中其它二十多处“嫁”字以及诸明朝通俗小说中“嫁”字的各种用法都与现代汉语“嫁”字的对应用法相同。从句法细节看,如果语句之谓语是“嫁娶”之“嫁”而直接宾语是“你”、“我”等代词,则其后需有“于某人”或“于某地”等补足成分。也就是说,这里所引两处“嫁我”中“嫁”字,其用法独特,不同于“嫁娶”之“嫁”的正常用法。
再考察文句中的逻辑,佃户揪打田主人,其妇阻止,并说“你嫁我”,而佃户接话说“这花娘也要打死”。依此上下文的逻辑,“你嫁我”的句意应是“你别打他,有本事你打我”。而后文的“嫁我便是”若理解为“(让他来)对付我便是”,文义也更为妥帖。因此,这两处“嫁我”,应是“对付我”、“欺负我”的意思。循音求字,我们也发现闽南语中极常用的单音词“共”正与此处的“嫁”字对应。闽南语中的“共”字用作动词时的意思等于“欺负”、“对付”,此外它还可以用作介词和连词。据《闽南语大词典》,闽南语中的“共”字作为介词时漳州、厦门的读音与闽南话中“嫁”的读音一致,作连词时漳厦读音也与“嫁”字相同。
如上所论,上引两处“嫁我”中“嫁”字的用法与该字的通常用法不同,而且“嫁我”理解为“对付我”、“欺负我”句意才妥帖,因此,这两处“嫁”字确应解释为闽南语中的“共”字。闽南语中的“共”字目前只有在作介词、连词时才与“嫁”字读音相同,但依本条看,它在明朝后期作动词时读音也应如此。
(九)“揭”。在陆澹安所编《小说词语汇释》一书中,明代《警世通言》等通俗小说中出现的“揭债”被释为“借债”,而《清平山堂话本·董永遇仙传》中的“揭折”一词则释为“抵偿”。古文中“揭”可训“举”,故“揭债”即为“举债”,“揭”字因此转而有“借”义,似是顺理成章之事。据此,《杜骗新书》中多处出现的“揭借”一词,词义应即与“借(债)”相同。然而,《脱剥骗·乘闹明窃店中布》说:“吴胜理徽州府休宁县人,在苏州府开铺,收买各样色布,揭行生意最大,四方买者极多,每日有几拾两银交易。”文中出现的“揭行”一词,却暗示“揭”字的词义并非那么简单,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为深入考察此字,以下分别摘引《清平山堂话本》和《杜骗新书》的几段文字:
(1)(董永)……无钱殡送,心思一计:不免将身卖与人佣工,得钱揭折。(《清平山堂话本·董永遇仙传》)
(2)张霸曰:“你将还人的及各店买去的,都登上帐,只说他揭借去,俱未还银。我将帐去告取,你硬作证,怕他各店不再还我?”(《牙行骗·贫牙脱蜡还旧债》)
(3)梅爷曰:“那有揭借客蜡,都不还银者。”即出牌拘审。(《牙行骗·贫牙脱蜡还旧债》)
(4)丘牙曰:“蜡非卖他,是小人先欠诸店旧帐,张霸蜡到,他等诈言揭借,数日后即还银。及得蜡到手,即坐以抵前帐,非小人敢兜客银也。”(《牙行骗·贫牙脱蜡还旧债》)
据上引《牙行骗·贫牙脱蜡还旧债》的三段文字,所有“揭借客蜡”者都是卖蜡的商铺,他们“揭借客蜡”之后,不是应该“还蜡”而是“还银”。因此,这里的“揭借”并非是简单的“借”,而是先提货后付货款的交易模式。再看上引《清平山堂话本·董永遇仙传》之“得钱揭折”,董永“与人佣工”,每日工钱微少,付清欠债需要董永“佣工三年准债”,因此这种“以工抵债”的“揭折”方式事实上是“分多次逐步偿还债务”。两则故事相互印证,可知“揭”字并非只有简单的“借”义,其词义中包含着特定的还款方式。
“揭”字在古代的福建、广东方言中早已具有以上所论的丰富词义,现代的“按揭”一词,其“分期还款”的涵义便出自粤语“揭”字的字义。此可见,“揭”字词义中所含的特定还款方式就是“分多次逐步还款”,而《脱剥骗·乘闹明窃店中布》故事中“揭行”的意思也因之昭然明白:此商行以将货物“揭借”给零售商家的方式运营。
除以上诸条外,《杜骗新书》中还有不少词语也可能是闽南语用词,例如上引“内系土库城”句中的“系”字,可能就是闽南语中意为“放置”的“下”字;而赵红梅等《〈杜骗新书〉词语补释》所释之“做苦春”一词又作“弄苦葱”,则依音、义推求,“苦春”或“苦葱”本来可能是闽南语中意为“屁股”的“尻川”二字。总而言之,《杜骗新书》中这类疑似闽南语的词汇颇多,由于论证所需的证据不足,我们只能略而不论。
再看句子方面。
《杜骗新书》的主体虽是以明、清以来的通俗白话写成,但书中却夹杂着大量具有典型闽南语特征的句子,此仅就《奸情骗·和尚剪绢调佃妇》及《妇人骗·哄婶成奸骗油客》两篇中部分典型的句例考述如下:
(一)“你好歹。”《奸情骗·和尚剪绢调佃妇》故事中,佃妇收受僧人的全匹好绢而不受剪下的二尺,所以僧人说她“取多辞少,你好歹”。此句中的“歹”非闽南语读者也容易理解其意,但不说“你好坏”而说“你好歹”,则是典型的闽南语。
(二)“弄你受气。”《奸情骗·和尚剪绢调佃妇》的情节发展过程中,僧人故意编造谎言迫使佃妇交出已收受之绢,然后“复买蓝绢半疋,并前绢送与之”。在被佃妇怒骂之后,僧人解释自己的行为,说:“正为你常骂我,故意取(绢)回,弄你受气。”其中的“弄”字在闽南语中是“玩弄、引逗(并产生某种效果)”之意,其用法及语句的句法也是典型的闽南语。
(三)“男人未在家,过两日来接银。”《妇人骗·哄婶成奸骗油客》故事中,两妯娌中的“婶”石氏听信“姆”左氏而向卖油者赊油,这两句就是石氏对卖油者说的话。句中说“接银”而不说“取银”,其“接”字的用法是典型的闽南语。此外“男人未在家”中“未在”的用法也颇具闽南语特征。
(四)左氏扯住曰:“我报你知,你须谢我。”卖油者曰:“明日寄两斤油与你。”《妇人骗·哄婶成奸骗油客》此段对话中,“我报你知”意为“我报信与你”,与《闽南方言大词典》“报”字条第一个例句完全相同,其“报”字的用法是典型的闽南语用法,而全句则是一个典型的闽南话语句。故事后文左氏说“婶婶说油银未还,你适间慌忙说还了,必有缘故,我在此等报叔叔”。其中的“报”字同样是典型的闽南语用法。此外,卖油者口中的“寄”字是闽南语词“揭”的俗写或讹写,这在本文第一小节已有论证。
(五)“此是你换来的,须当补你。”如上条所引,“姆”左氏从卖油客处索取两斤油。这是左氏将索得的这两斤油送与“婶”石氏的时候说的话。显然,“须当补你”句中“补”字为“补偿”之义,但用来构成“补你”却是具典型闽南语特征的句法。
(六)“你不该把师父摊出来。”《妇人骗·哄婶成奸骗油客》此句中的“摊”字,意思等于“攀引”,此字《闽南方言大词典》写作“澶”,写成“摊”字是同音字混用。据《集韵》,“澶”的原意是“漫也”,其“攀引”之义是闽南语中常用的近引伸义。
(七)婶曰:“你偷肉不该惊死我。”姆曰:“我惊那人,不惊他去,怎得他肉。”在《妇人骗·哄婶成奸骗油客》的这段文字中出现三次“惊”字,其用法都是很典型的闽、粤方言用法。
(八)余者烟干后食。《妇人骗·哄婶成奸骗油客》此句中的“烟”等于普通话中的“熏”字。普通白话中“烟”为名词而“熏”为动词。“烟”、“熏”词性不分、二字混用是典型的闽南方言。
二、《杜骗新书》人物、故事的福建地方属性
《杜骗新书》中有一些人物、故事可以考出其原型,并与福建关系密切。
明代福建地方总志,自《八闽通志》以后,有万历九年纂《闽大记》五十卷、万历四十四年纂《闽书》一百五十四卷;清康熙时,纂有《福建通志》六十四卷。自雍正七年起纂辑新志,至乾隆二年编成七十八卷,“视旧志增多十四卷,如沿海岛屿诸图旧志所不载者,皆为详绘补入,足资考镜,于体例亦颇有当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雍正乾隆修《福建通志》,纂集明中期以后地方史料甚富,颇有总揽之效。《杜骗新书》中有多则发生于万历中后期的建阳及附近府县的故事,其中涉及的多个官绅人物可以在《福建通志》中找到他们的踪迹,我们逐一列举这些人物如下:
(一)《脱剥骗·借他人屋以脱布》故事中,邵武布客因布匹被骗“状投署印同知钟爷”。据《福建通志》卷三十记载:“钟万春,清远人,举人。万历间任邵武府同知,精敏有吏才,盐弊奸薮,悉心清革”。对比可知,故事既发生在“万历间”,邵武府的“署印同知钟爷”必然就是这个钟万春。
(二)《诈哄骗·诈学道书报好梦》说:“庚子年,福建乡科上府所中诸士,多系沈宗师取在首列者……省城一棍,与本府一善书秀才谋,各诈为沈道一书,用小印图书,护封完密,分递于新春元家。”故事表明,作者曾见过这个骗子“写与举人熊绍祖之书”。这些伪造的“沈宗师”书信均预言诸位新举人来年将中进士,但举人们第二年都“铩翮而归”。这则故事里出现的“沈宗师”、“熊绍祖”以及诸落第举人,都可以在《福建通志》中找到。
在《诈哄骗·诈学道书报好梦》中,“沈宗师”也被称为“沈道”。据明朝官制,按察使司设按察副使二员、佥事四员,诸郡分巡道各一员或副使或佥事,因此这个“沈宗师”在庚子年(万历二十八年,1600)应为按察副使或佥事,而故事形诸文字时应是“建宁道”。据《福建通志》卷二十九记载:“沈儆炌字叔永,归安人,进士,有文武才。万历间督学副使,三年考校,咸颂得人。不徇权贵,保全士类。寻迁建宁道,纪纲肃然,属吏惮之。”据此可知,这位沈儆炌正是先当“督学副使”而后“寻迁建宁道”,他无疑就是故事中的“沈宗师”。
故事中所说的“上府”指建宁府之建宁、建安和建阳。据《福建通志》卷三十八记载,建阳熊绍祖为万历廿八年庚子“周起元榜”举人。同年建宁府“上府”共有郑际明、龚士遴、袁文绍、熊绍祖四人中举,他们在次年科举考试中全部落榜。这些记载,与《诈学道书报好梦》故事内容完全符合。
(三)《牙行骗·贫牙脱蜡还旧债》中有一位福建建宁府“署印梅爷”,故事谓其“刚正之官”。“署印”即建宁府同知,《福建通志》卷二十五所列载万历年间的建宁府有一位名叫“梅守极”的同知,据雍正重修《江南通志》卷一百二十九,梅守极为宣城人,是万历四年(1576)举人。梅守极的姓、职务和时代都与《牙行骗·贫牙脱蜡还旧债》故事相符,因此他应该就是故事中的“署印梅爷”。
(四)《露财骗·炫耀衣妆启盗心》中游天生:“次日,搭后船往建宁府,即抱牌告于王太爷。”由于故事说疑犯“人赃俱拿到府”,并由“王爷审问”,因此这个“王太爷”是建宁知府。查《福建通志》所载,万历及其后任建宁知府而又姓“王”者仅“王继善”一人。王继善是华亭人,万历甲辰(1604)进士,他应当就是故事中的“王太爷”。
(五)《婚娶骗·媒赚春元娶命妇》讲的是“福建春元洪子巽”在京城纳妾被骗的故事。故事中,骗子向人介绍说洪春元“世家宦族,姻眷满朝,即在京,亦多人看顾”。由于这话是当着洪春元的面所说,考虑到骗子会担心骗术露馅,我们认为洪家实际境况虽未必真是“世家宦族,姻眷满朝”,但洪氏必定不是寒门。“洪子巽”在孟昭连整理的、书首有熊振骥序的一种早期版本中作“洪子选”,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特别值得注意的线索。
据《福建通志》卷三十八及卷三十六记载,福建泉州府南安县有一位“洪承选”,是万历二十五年举人第一名,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洪承选中举时名列第一,恰好是一位“福建春元”。洪承选在中举十六年后方中进士,他很有理由也很可能在京城久住,因此也很可能如本篇所述在京城纳妾。南安洪氏“承”字辈之上为“启”字辈,再上为“有”字辈,统计《福建通志》中的记载,可知南安洪氏此三辈份在嘉靖之后共有举人、贡士数十人,进士二十余人,洪承畴就是其中最为知名的一位。南安洪氏在明朝后期科举的盛况,与本故事所言“世家宦族,姻眷满朝”情形正相符合。由上可知,《婚娶骗·媒赚春元娶命妇》中的这位“福建春元”就是南安洪氏的洪承选。而《婚娶骗·媒赚春元娶命妇》不同版本中将“洪承选”分别印成“洪子选”及“洪子巽”则并非偶然,这应该是书商在雕版完成之后由于某种原因(例如南安洪氏的压力或交涉)有意改字的结果——先将雕版中的“承”字铲改成“子”字,后来又将“选(選)”字铲改而成“巽”字。
三、《杜骗新书》故事发生的时间与地点
《杜骗新书》总共有88则故事。这些故事中,《诗词骗·伪装道士骗盐使》是明朝嘉靖年间名士唐寅的故事,《衙役骗·吏呵罪囚以分责》是北宋名臣包拯的故事。而《婚娶骗·因蛙露出谋娶情》故事中,陈彩与游氏对话都有成段韵文出现,与《杜骗新书》全书绝不相类,潘建国所引《菽园杂记》的记载证明这个故事曾被改编成《虾蟆传》。据中华书局版《菽园杂记》“校点说明”,其作者陆容卒于公元1494年。也就是说,《菽园杂记》于《杜骗新书》百余年前即已成书,因此《婚娶骗·因蛙露出谋娶情》应即是由《虾蟆传》改写,并袭用其中某些文句而成。除了这三则之外,其余85则基本都可以断定故事发生的时间在万历年间,并且大多发生在万历中期之后。
仔细统计可知,《杜骗新书》88则故事中故事发生地点确定者有65则,其中发生在福建者为38则,这些地点全部位于建宁府及周边地区,此外还有三则故事的主人公为福建人。而余下的24则故事中,发生在南京或“京城”者有13则。在故事发生地点不明的23则故事中,约有13则故事据内容、细节判断应发生在福建的建宁府。
再据故事分类考察可以发现,《杜骗新书》前半部中,除了四则《伪交骗》故事全为外省故事外,其余基本都是福建省建宁府及周边发生的故事。而后半部情形则相反,除了五则《买学骗》故事疑似为福建故事之外,其余《诗词骗》、《衙役骗》、《婚娶骗》、《奸情骗》、《妇人骗》、《拐带骗》、《僧道骗》、《炼丹骗》、《法术骗》、《引嫖骗》共43则故事大多发生在福建之外或者地点不详。
我们知道,《杜骗新书》的编著者署为“浙江夔衷张应俞”,然而熊振骥在此书的序言中却称作者为“莒潭张子”。据《八闽通志》“刘应李”条所载,元初刘应李曾于福建建阳县的“莒潭”创建“化龙书院”。再据《福建通志》卷四“西山”条注文,明代建阳县城北崇泰里有一座“西山”,山麓有“莒潭”,其上有“化龙书院”。由于熊振骥是建阳人,由于明朝并无名为“莒潭”的县级或县级以上地名,因此熊振骥序言所说即为建阳崇泰里的“莒潭”。显然,熊振骥认为张应俞是建阳“莒潭”人。根据古人对个人籍贯的处理方式,可知张应俞之籍贯虽为浙江,但本人已经长期居住在福建建阳,因此熊振骥才会称张应俞为“莒潭张子”。
据《诈哄骗·诈学道书报好梦》故事可知,《杜骗新书》编著者本人读过故事中骗子冒充沈宗师“写与举人熊绍祖之书”。本文第一小节曾指出,建阳县人熊绍祖为万历二十八年(1600)“周起元榜”举人。再根据张应俞长期定居建阳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断定《诈哄骗·诈学道书报好梦》所讲述的是真实发生之事,张应俞也确实看到过那封伪信。从熊振骥为《杜骗新书》作序看来,熊振骥与熊绍祖应为同族。并且张应俞与建阳熊氏颇有交情。据上引《八闽通志(下)》的“刘应李”条、“熊禾”条,以及《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六《刘希泌先生应李》,宋末的刘应李与建阳熊氏之熊禾交好。很可能,建阳熊氏自宋末以来的聚居地距刘应李创建“化龙书院”的“莒潭”不远。居住地的相近,可能是张应俞与建阳熊氏建立交情的一个因素。
《杜骗新书》于万历丁巳年(1617)在福建建阳初版。在其初版序言中,建阳人熊振骥称作者为编著此书“乃搜剔见闻,渔猎远近”。根据以上对故事地点的统计分析,《杜骗新书》中的故事多半是明朝万历年间发生在福建建宁府或其周边的故事,这证明《杜骗新书》确是“搜剔见闻”之作。而本文第一小节的讨论已经说明:如果一个可能在《福建通志》中出现的官员或士绅出现在《杜骗新书》的故事中,他往往也可以在《福建通志》中找到,这说明《杜骗新书》中发生于福建的故事的可信性是相当高的。因此,尽管《杜骗新书》中有不少故事源自远方外地的传闻,但全书至少半数篇章是根据本地传闻编写的纪实性故事,所以《杜骗新书》应该被认定为纪实文学作品。由此可见,黄霖认为《杜骗新书》“既有小说性,又有新闻性”,确是有洞察力的看法。而刘文香认为《杜骗新书》多为前代故事的“扩充和改写”或“复述与增益”,其结论则未免以偏概全。
四、余 论
本文前两个小节证明《杜骗新书》中含有许多与闽南语相同的字词和语句,这已经在告诉我们:《杜骗新书》是一部操闽南语的作者编著的作品。然而,第三小节也证明:《杜骗新书》是基于在其出版地福建建阳流传的故事而创作的作品,而且其编著者张应俞是一位长期定居于建阳的文人。这显然又在暗示:《杜骗新书》文字中所夹杂的更应该是建阳方言(另一种闽方言)而不是闽南语。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有三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种是:闽南语是《杜骗新书》的编著者张应俞本人的母语。由于浙江南部的苍南、平阳、洞头、玉环、温岭等地是闽南语地区,而张应俞的籍贯正是浙江,因此张应俞虽然是定居于闽北建阳的浙江人,但他的母语却大有可能是闽南语。
第二种是:明代的建阳方言与闽南方言差别比现在要小很多,《杜骗新书》中很多被证明与闽南语相同的字词与语句其实是当时的建阳方言。这种解释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闽省方言随时间推移而日渐分化却是不争的事实。据《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前面所讨论的“落锥(钻)”一词,在现代福州话中可写作“擂钻”,在建瓯话中作“落钻”,而温州话则作“铼钻”,这个例子说明闽方言诸子方言的某些词汇至今仍然差别不大,更从一个侧面说明:《杜骗新书》中我们考定为闽南语词汇者可能真的是闽南语词,也可能是明代闽方言中多个子方言的共同词汇。因此,这种解释相当合理。
第三种是:《杜骗新书》的编著者采用了部分以闽南语叙述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出自一部比《杜骗新书》更早的闽南语作品,也可能是《杜骗新书》编著者对操闽南语的讲述者口述故事的记录。由于《杜骗新书》中与闽南语相同的字词和语句相对集中地出现于《谋财骗·傲气致讼伤财命》、《妇人骗·三妇骗脱三匹马》、《妇人骗·哄婶成奸骗油客》等数篇之中,这种解释无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无论哪一种解释,《杜骗新书》的福建地方属性都可以说是确凿无疑的。这一事实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杜骗新书》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内涵,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注:
③⑦ [清]《康熙字典》,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39、258页。
⑧ [明]冯梦龙《警世通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7页。
责任编辑:徐永斌
南京大学数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