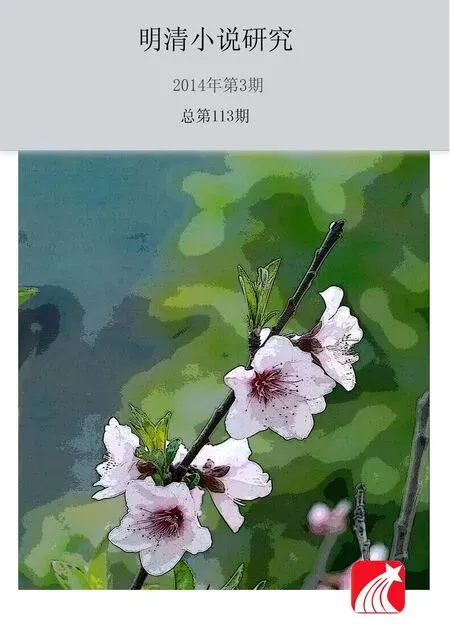《歧路灯》的俗陋语与小说家言
··
《歧路灯》的俗陋语与小说家言
·刘永华·
《歧路灯》作者李绿园开创性地使用了“撒朘”、“鸭娃子”和“尖尖”三个至俗至陋之词,此三词至今仍仅见于其书而未见于他书,是其不愿使用又不得不用的词语,与理学家主张的庄重语体形成了紧张关系。为了语言“小说化”的需要,作者苦心孤诣锤炼字句,力图回避日常通用语的遮遮掩掩的做法,反映了文学家与理学家的身份冲突,也表明文学语言的边界存在于作者思想和表达所能许可的最远处。
撒朘 鸭娃子 尖尖 文学语言边界
清中期河南重要作家李绿园主张“惟其于伦常上立得足,方能于文藻间开得口”的创作原则,以宏扬“道性情、裨名教”的理学理想为己任①。本文注意到,李绿园理学精神许可下所能“开口”的最大自由度即语言边界在哪里,是一个尚未经学界认真讨论的话题。本文拟以三个最为边缘化的词语为据对此问题做出尝试性探索。
一、《歧路灯》独有的俗陋语
《歧路灯》语体以庄重严肃的理学风格为主,以自然活泼的俗语体为辅。其语言中最为边缘的表达,是作者李绿园精心简选甚或独创的,至今仍为仅见于该书而未见于他书、义核相同的三个俗陋语。
1.撒朘
“撒朘”,依上下文当为便溲之义,但该词罕见于他书,为李绿园自造。现代汉语方言中,仅有广州话的“屙朘”一词专指小男孩撒尿②,与之相类,其他少见报道。
学台立起身来告便,伺候官引路到西边一座书房。院子月台边一株老松树,其余都是翠竹,六位大员各有门役引着陆续寻了撒朘地方。到了书房,门役捧盥盆,各跪在座前,洗了手,坐书房吃茶。③(《歧路灯》第九十五回)
“告便”本义为“告诉某人以趁其便行某事”,为谦词。《苏东坡全集》第二十卷:“正辅提刑书,告便差人达之,内有子由书也。”④其中“告便”有目的宾语“差人达之”。当目的宾语在字面上消失后,“告便”即为“告退”义,但不是中性的“告退”,仍隐含有某种目的的含义。《小五义》第三回:“天交三鼓,五爷告便,回自己屋内稍歇。”⑤“告便”的目的可以完全隐含,由当事双方会意,这就是“告便”成为“上厕所”隐婉语的语义接口。《小五义》第九十九回:“芸生看见由墙头上倏地过来了一条黑影,假装着没看见,特意说:‘老兄弟,你多留点神,我先告告便。’艾虎说:‘大哥请便。’芸生就奔太湖山石那里,假装告便。”⑥《歧路灯》中还有一个“告便”与此相同。
少刻,篑初告便,观察命小厮引去。……篑初回来,小厮奉水授巾,洗手坐下。⑦(《歧路灯》第九十五回)
《歧路灯》两例之“告便”,均有别人“引去”及返回“洗手”之事,都是对如厕情节的描述。
“撒朘”之“撒”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表达。《元曲选》下卷:“先该除他这铁帽子,撒脬尿在里面。”⑧《金瓶梅》第八十六回:“婆子正在门前扫驴子撒的粪。”⑨《禅真后史》第十回:“撒屁也是香的。”⑩
在某些现代汉语南方方言中,“朘”泛指男子生殖器。主要分布在以下区域:赣语——福建泰宁;客话——福建连城庙前、明溪、广东五华;闽语——福建沙县、三明、福清、永安、崇安、广东汕头。
“椎”、“槌”、“棰”、“锤”、“垂”等字与“朘”音义相通,或为不同记音字。《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五:“椎也,经从追作槌,俗字也。”“棒槌”在北京官话中指愚笨。“那么大不识数,真棒槌。”其中“槌”与“朘”音近义通,并引申为詈语。男阴或曰棰,分布于中原官话——甘肃甘谷。“锤子”指称男性生殖器、同时用作詈语的,分布于西南官话——四川成都;客话——四川西昌。“抓你们是犯了啥子事?锤子事。”“垂货”,指笨蛋。分布于江淮官话——安徽安庆。
“踆”与“朘”相类。《淮南子》卷七:“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论衡》卷二十二:“日中有三足乌。”赵国华认为,三足即为一阴茎二睾丸的变形。《山海经》卷一:“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踆于东海,多沙石。”此“踆”义与“锥”义相通。《荀子》卷四:“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锥”与“椎”、“槌”等亦通。“朘”后也指雄性动物生殖器。《小畜集》卷十四:“乃以数牝马诱之,乘作之势,以巾幂其目,间而进其母。”《通雅》卷四十六:“虫之曰螸,言垂腴狀之也。凡类曰丑鼈窍,亦曰丑海狗之腎,曰腽肭脐,今南方有鹿鞭,鹿外肾也。”以方以智之意,“朘”似得音义于“垂”。
医书中“朘”字用的较多,有较强的医学术语色彩。《张子和医学全书》卷三十六:“发则小肠大痛,至握其,跳跃旋转,号呼不已,小溲数日不能下,下则成沙石。”《本草纲目》卷五十一上:“者,天地初分之气、牝牡相感之精也。时珍按:,音子催切,赤子阴也。今作鹿精之名,亦未为稳。”《全元文》卷二一三:“痣黡文理,涕咳远近,爪甲修短,牝便溲,莫不有法,而相气色为尤难,其说出于《素问》。”《素问》的材料,是把“便溲”作为“牝”的功能看的。后世极少量以“朘”表示“便溲”的用法,很可能是一种语义沾染现象。
2.鸭娃子
“鸭娃子”,詈语,河南方言词,罕见于书面。
魔王道:“我看您共不得事,原俱是些软蛋内孵出来的。难说一个嫩鸭娃子,都结果不了,还干什么大事。晦气,晦气。出门不利市,把这一个忘八崽子宰割了罢。”(《歧路灯》第七十三回)
“软蛋”由“软壳鸡蛋”缩略而来,喻没骨气,懦弱。《今古奇观》第七卷:“做小娘的,不是个软壳鸡蛋。”老舍《歪毛儿》:“我没遇上一个可恶而硬正的人;都是些虚伪的软蛋。”“蛋”字形本为“蜑”,《说文解字》卷一三下:“蜑,南方夷也。从虫延声。”后形变为“蛋”。《字汇补》:“蛋,俗呼鸟卵为蛋。”引申为睾丸及詈语的用法。《醒世姻缘传》第七十四回:“二位薛相公躲在屋里瞅蛋哩么?”“蛋”与“卵”为历时替换关系。《国语》鲁语上第四:“鸟翼卵”,韦昭注:“未孚曰卵。”也指睾丸。《黄帝内经》卷五:“脉弗荣则筋急,筋急则引舌与卵。”泛指男性生殖器。《蕲春语》:“卵,郎果切。吾乡呼男子阴器正作此音,而呼睾丸为卵,仍力管切。”也作詈语。《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五十二回:“他就在廊底下骂,说道:‘好日的货,你下西洋一个卵功’。”
“鸭娃子”之“娃子”当为幼雏之义。“鸭黄儿”与之类似,“黄”为小鸭毛色。《喻世明言》第三卷:“不出去门前叫骂这短命多嘴的鸭黄儿!”陈卫恒认为“鸭黄”对应于“龟儿子”、“鳖孙”之类的方言说法。《歧路灯》此例中的“崽子”本也指幼子。《水经注》卷十一:“至若娈婉丱童及弱年崽子,或单舟采菱,或叠舸折芰。”后引申为詈词。《红楼梦》第五十八回:“这一点子小崽子,也挑幺挑六,咸嘴淡舌,咬群的骡子似的!”
现代汉语方言中,以“鸭”为词或语素称男性生殖器的,广泛存在于官话方言区。“鸭儿”,指小孩儿的阴茎,西南官话——四川成都。“鸭子”,男性生殖器。冀鲁官话——山东寿光;胶辽官话——山东青岛、牟平、荣成;中原官话——河南商丘、通许。“鸭蒂”,阴茎。西南官话——湖北武汉。
《歧路灯》中的“鸭娃子”,是以“鸭”指称男根的较早记录。现代河南方言中“鸭子”指男根,“鸭子毛”指阴毛。这与“朘”的构词有平行之处。“朘子”,男子生殖器。西南官话——四川成都;客话——福建永定下洋,也作朘仔;闽语——福建沙县。“朘毛”,阴毛。客话——福建连城、庙前、明溪。可见,“朘子”和“鸭子”在地理分布上是对立的。“朘”应是中古以后“南迁”的中原古代词语之一。
《鸡肋编》卷中:“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水浒传》第二十五回:“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此两例为江浙方言,其中的“鸭”均与妇人不洁有关,而与指称男根的“鸭”没有关系。
3.尖尖
“尖尖”,男婴生殖器的昵称。罕见于他书及方言著录。
你好好的,叫我养个腰里有尖尖的孩子,我也在人前,好争一口气。(《歧路灯》第六十七回)
尖尖,本为男婴生殖器外形。与“把儿”、“棒儿”等相类。口语性极强,很少出现于书面语中。现代河南方言中,“带把儿的”、“带棒的”用以指男孩,而“尖尖”已从口语中消失。
二、《歧路灯》俗陋语的文学作用
《歧路灯》独有的三个俗陋语与作品人物身份、语境相契合,构筑了小说世界的不同类型和层次,饱含作者倾向。可见,三词的运用是作者的精心挑选、主动选择,并具有积极修辞效果。
1.与人物身份和语境相契合
李绿园苦心孤诣为官员们“创造”了“撒朘”一词,适用于“六位大员”等官宦人士,力图为尊者讳、为官者讳。有趣的是,《歧路灯》自序中竟有“老子云,童子无知而朘举”一语,虽然所引与原文有出入,但足以表明李绿园知道“朘”为男根的本义。在“撒朘”一词出现的语境中,还有书面化很强的委婉语“告便”与之照应,环境则为优雅的“书房月台边”、“老松树”和“翠竹”下;程式也很威严,“伺候官引路”、“各有门役引着”,“门役捧盥盆,各跪在座前,洗了手,坐书房吃茶”,可谓极尽铺排之能事。而相比之下,《歧路灯》第五十八回写赌徒谭绍闻以较为中性的“出外解手撒尿”,《歧路灯》第七十回写夜遇厉鬼的夏逢若则完全为贬义的“裤裆撒尿”,《歧路灯》第四十六回过堂的王紫泥则“裤裆中早犯了遗尿之症”。很显然,李绿园仿“撒尿”而造出“撒朘”一词,并配以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使用。
《歧路灯》引入生活化极强的方言口语词“鸭娃子”,适用于“久惯杀人的魔王”,通过魔王满口脏话“软蛋”、“鸭娃子”、“忘八崽子”、“小羔子”等展示其粗鲁鄙俗的个性。除魔王之类的强盗,《歧路灯》中经常讲脏话的还有两类人。一类是“悬罾等鱼”的张绳祖和“见景生刁”的茅拔茹等骗子。《歧路灯》第二十七回张绳祖说谭绍闻赌博“干我屌事”,《歧路灯》第四十三回张绳祖骂小厮“忘八羔子”。另一类是盛希侨之类的“宦门中不肖之子、天生匪人”。《歧路灯》第二十七回盛希侨骂张绳祖“狗杀才”、“不是货”,《歧路灯》第三十七回盛希侨骂夏鼎“狗肏的”。《歧路灯》中,詈语是“匪人”之间的语言。“端方正人”娄潜斋、程嵩淑、孔耘轩等与之无染。
“尖尖”、“娇儿”、“乖乖”、“亲亲”、“根穰儿”、“麒麟子”等都是《歧路灯》对男孩的昵称。《歧路灯》第二回谭孝移欲为儿子请师,诗赞“欲为娇儿成立计,费尽慎师择友心”。《歧路灯》第二十八回王氏对孙子兴官儿“笑的眼儿都没缝儿,忍不住拉到怀里叫乖乖,叫亲亲”。《歧路灯》第六十七回张类村管幼子叫“根穰儿”。《歧路灯》第七十七回苏霖臣赞张类村子为“麒麟子”。“带把的”、“带锤的”一般是相互熟悉的人对男孩的昵称,语体并不庄重,“尖尖”用法与之相似,该词由妒妇杜氏在争吵中对丈夫说出,比较符合语境特征。“娇儿”语体相对正式,符合谭孝移“端方正直,忠厚和平”的性格特征。“乖乖”、“亲亲”表现了王氏的祖孙亲昵之情。“根穰儿”反映了张类村几经周折得子后的感受。“麒麟子”则表达了对他人幼子的赞颂和祝福。
2.构筑小说世界的不同类型和层次,饱含作者倾向
“撒朘”、“鸭娃子”、“尖尖”三词被李绿园精心挑选、主动选择,分别运用于三种人,表达不同的好恶和褒贬,《歧路灯》的小说世界因而被分成不同类型和层次,不妨称之为诸神的世界、恶魔的世界和庶众的世界。
诸神的代表为谭道台和各任知县,他们不仅权大势重,是资源的支配者和矛盾的仲裁者,更重要的,他们还是理学上的模范,有不证自明的天然合法性,无论他们做了什么事,李绿园都不吝笔墨给予盛赞。《歧路灯》第九十回谭道台“隐衷欲见弟侄”,彻夜想出一个“观风”的妙计,令“生童各携笔墨、砚池、镇纸、手巾,团围守侯”,“两个县学,飞跑在门左点名,两个府学,侍立在大堂柱边书案前散卷”。谭道台本人则“神气蔼蔼,丰标棱棱”,坐在“红幔斜撩,银烛高烧”的暖阁口。对于此种劳师动众陪太子读书的行径,李绿园竟赞叹“谭道台昨夜筹画,果然明鉴万里”。谭绍衣嗣后提携已过而立之年的“老苗”谭绍闻,戏剧般击溃倭寇,选了县令,成了正果。之前谭绍闻吃喝嫖赌,堕入下流,甚至连上命案,屡获“父母斯民”的县尊荆公、程公、董公、边公诸人左袒,侥幸得脱。《歧路灯》第三十一回却赞荆公为“荆八坐老爷”,“一天足坐七八回大堂”,取勤勉政务之意。《歧路灯》第四十七回赞程公“严中寓慈,法外有恩的心肠”。《歧路灯》第六十回边公“满腔中名教,为民存耻”。除《歧路灯》第五十一回“裤带拴银柜”的董公因贪被参,其余无论如何“法外有恩”、“为民存耻”都得到作者颂扬。
恶魔中人物众多,有杀人越货的“魔王”卢重环、同伙邓林和谢豹,有“盘赌诱嫖”的张绳祖、王紫泥和虎镇邦,有“嫖赌场的小帮闲”细皮鲢、小貂鼠、白鸽嘴,有奸滑“匪人”夏鼎、无赖戏主茅拔茹,有夜间招嫖的店主、路上拐人行李的骗子等等。李绿园对此类人疾言快语、直斥其恶。《歧路灯》第三十四回张绳祖自比与王紫泥的关系为“疥疮药怎能少了你这一味臭硫磺”。《歧路灯》第五十四回夏鼎与张绳祖、细皮鲢、小貂鼠等人厮混在一起为“这两样人心里都似蛱蝶之恋花,蜣螂之集秽,不招而自来,欲麾而不去的”。据考证,夏鼎名字来源于《左传》。夏鼎,字逢若。《左传》宣公三年:“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夏鼎”为“有德”之方也,助民避开不祥。这恰是对“夏鼎”这个《歧路灯》中最典型“匪人”的反讽。可见,李绿园语带褒贬,字字不虚落。
《歧路灯》中有个广泛存在的庶众阶层,这个阶层处于社会的底层,少有政治地位,几乎看不到翻身的希望,一心一意的经营生活,既无大善,又无大恶,不时掀起几朵生活涟漪,却也无关宏旨。“生意中精人”王隆吉接手家铺生意,忙于操持。《歧路灯》第十五回盛希侨邀其赴席,王隆吉“也难再辞”。《歧路灯》第四十九回谭绍闻约其看戏,王隆吉“只得陪往看戏”。《歧路灯》第二十八回街坊邻舍、铺户房客为谭绍闻送礼晋贺,王隆吉“代为周旋”。“也难再”、“只得”和“代为”数语,已将王隆吉忙于生意、勤于经营的面貌刻画出来。王隆吉最终得到“椿萱并庆”的美好结局,寄寓了作者的平民理想。“生意上发一份家业”、“素以看戏为命”的巫翠姐,就是稍次的人物。《歧路灯》第五十回巫翠姐开了赌风,把谭家内政,“竟成了鱼烂曰馁”。《歧路灯》第八十五回揶揄道“这巫家正是看翠姐姿性聪明,更添上戏台上纲鉴史学,是出众的贤媛”。《歧路灯》第六十回刘家“老豆腐”卖豆腐为业,“单门独户发了家,专管小心敬人”,遇到无赖欺侮,“门低身微,不敢争执”,小心翼翼地生活,却被儿子赌博输去不少家业,笔端饱含同情。
为挣“束修”的低层知识分子也属于这一阶层。《歧路灯》第八回以《西厢》和《金瓶梅》教学生的侯冠玉“初在各铺子前柜边说闲话儿;渐渐的庙院看戏,指谈某旦角年轻,某旦角风流;后来酒铺内也有酒债,赌博场中也有赌欠;不与东家说媒,便为西家卜地。轩上竟空设一座,以待先生”。《歧路灯》第十三回:“侯冠玉年节赌博疲困,也在碧草轩中醉翁椅上,整睡了两三天,歇息精神。”《歧路灯》第三十八回惠养民“早把个谭绍闻讲的像一个寸虾入了大海,紧紧泅了七八年,还不曾傍着海边儿”。《歧路灯》第四十一回:“这是惠养民终日口谈理学,公然冒了圣人之称”,“弄得身败名裂,人伦上撤了座位。”作者持明显的批评态度。
“优等秀才”娄潜斋、孔耘轩、程嵩淑、苏霖臣、张类村其实也在此阶层,张类村家中就有妻妾争执之窘事,与普通人家长里短并无二致。娄潜斋出仕也不过说明,此类人不过是众庶中的上层、诸神世界的预备队而已。进入下降渠道的则更多,诸如夏鼎、张祖绳、盛希侨、早期的谭绍闻等等。总体上魔与非魔的世界是割裂的、不相交通的。《歧路灯》第一回“那些比匪的”对娄潜斋等人“都敢望而不敢即”。《歧路灯》第七十二回强盗谢豹说“他们是本城绅衿,又方便,又有体面。我们虽是亲戚,却搭识不上”。
李绿园怀着喜悦和欣赏的笔吻描写男婴的体貌,表现了对庶众生活的热爱。《歧路灯》第二回端福儿“面似满月,眉目如画,夫妇甚是珍爱”。《歧路灯》第二十七回冰梅“生了一个丰伟胖大的小厮”。《歧路灯》第七十七回张类村幼子“丰面明眸”。《歧路灯》第三十五回兴官儿“把绿袄襟掀开,露出银盘一个脸,绑着双角,胳膊、腿胯如藕瓜子一般,且胖得一节一节的。绍闻忍不住便去摸弄”。男孩给众人带来了快乐。《歧路灯》第二十七回冰梅私生了兴官儿,王氏“喜的是男孩儿难得”。《歧路灯》第二十八回慧娘“半年后自娘家回来,带的偷缝的小帽儿、小鞋儿,与兴官儿穿戴。抱兴官儿在奶奶跟前作半截小揖儿玩耍”。《歧路灯》第六十七回张类村得子张正名,“伯侄两院,无人不喜”。《歧路灯》第八十九回:“这名相公将笔濡在砚池内一染,横涂竖抹,登时嘴角鼻坳,成了个墨人儿”,“这名相公又被小厮将头上插了一朵小草花儿。总角带花,鼻凹抹墨,正心看见,一发亲的没法了,抱起来亲了个嘴,轻轻把名相公嘴唇咬住。”李绿园虽选任过漕运、县令等职,但底层出身,仍使其作品中透着浓郁的庶众意识。
三、作家的身份紧张与语言边界
李绿园在写作之前已然树立了文学和理学方面的行文模式和创作目标。《歧路灯》前言中,李绿园谓《桃花扇》、《芝龛记》和《悯烈记》为“填词家当有是也!藉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读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厨妇爨婢,皆感动于不容已”。《西厢记》和《燕子笺》等则为“桑濮”淫词,不可“暂注目”,因而,“仿此意为撰《歧路灯》一册”,以达到“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和“于纲常彝伦间,煞有发明”两个方面的创获。
可见,李绿园试图达到的写作目标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理学标准的政教目标和易于接受的语言目标。李绿园曾著《四谈集》,以剧本的形式辅助教学,开创剧教先声,在豫西民间私塾之中广为传抄。这也是其重视以文艺形式传道授业的明证。
但吊诡的是,文学创作中的描写和虚构在李绿园看来往往是“小说家言”、“小说家窠臼”,有自觉抵制的倾向。《歧路灯》第二十二回:“若是将这些牙酸肉麻的情况,写的穷形极状,未免蹈小说家窠臼。”《歧路灯》第一百八回:“二更天气,垂流苏压银蒜六字尽之,不敢蹈小说家窠臼也。”《歧路灯》第一百一回:“谭绍闻道:方才过的‘黄粱梦’,果有其事么?娄朴道:‘小说家言,原有此一说’。”如果说前两例“小说家言”均为“桑濮”淫词须加以回避的话,那么最后一例则为小说创作中正常的积极修辞的需求,不应为回避的对象。其中存在着理学家庄重语体与小说家生动语体之间的巨大紧张关系。一方面,出于传播的需要,小说家应尽力使用生动活泼、为受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而另一方面,出于理学说教的要求,李绿园不得不收敛语言张力,以避免流入“桑濮”一路。
然而“撒朘”、“鸭娃子”、“尖尖”等俗陋词语,体现了的恰恰是“小说家言”的语言特征,与理学家主张的庄严语言风格相去甚远。这三个词语的出现,我们既可看到李绿园理学家与文学家身份的内在矛盾与调和,也可以看到李绿园所能许可的文学语言的边界所在。出于表达的需要,李绿园不得不选择了“撒朘”、“鸭娃子”、“尖尖”三词,此三词恰恰又是至今不见于他书,为其苦心孤诣精选甚至是独创而出,这种试图回避日常通用语的遮遮掩掩的做法,正是理学精神使然,此三词也正是《歧路灯》文学语言的边界所在,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和创作启示。
相比之下,与《歧路灯》同时期的《红楼梦》语言边界要广远得多。《红楼梦》不仅不回避“几巴”、“膫子”和“屄”等俗陋语,更重要的是,《红楼梦》中的词语一般来自于全民新鲜的口语——因而更有生命力;而完全不是“空前绝后”的、与人工语言相类的风格——无论那些人工语言多么的机智讨巧。这或许也是两书在文学艺术上和传播上的差距根源之一。
注:
② 牛尚鹏《试谈“出恭”的由来》,《大同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我国后卫队员破紧逼防守乏术,是中国男篮在国际大赛上始终没能解决好的一个老问题。第29届奥运会中国男篮的失误,从位置上分析, 后卫的失误居首,失误主要发生在三分线区域。中、前锋的失误次数大致相当,分别主要发生在限制区以内和限制区至三分线区域。失误方式排序依次为持球(43)、传球(28)、运球(18)、进攻犯规(7)、时间违例(5)。
④ [宋]苏轼《苏东坡全集》,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614页。
⑤⑥ [清]石玉昆《小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95页。
⑧ 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第三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0页。
⑨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276页。
⑩ [明]方汝浩《禅真后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责任编辑:王思豪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楼梦〉〈歧路灯〉〈儒林外史〉词汇比较研究》”(项目编号:08BYY043)阶段性成果。
河南大学文学院语言所
——评杜贵晨《李绿园与〈歧路灯〉》(增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