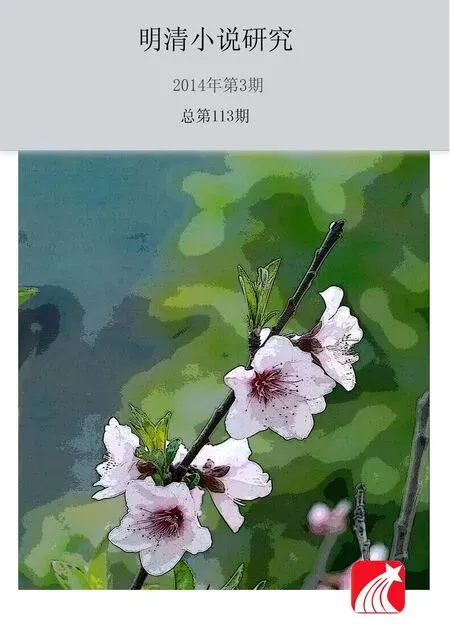明清文言小说的文体焦虑与尊体实验——以《剪灯馀话》《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为例
· ·
明清文言小说的文体焦虑与尊体实验——以《剪灯馀话》《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为例
·陈赟·
在小说体卑的普遍观念下,明清文人写作小说时常常伴随着一种“文体焦虑”。他们一般只是在较雅的文言小说里才肯以真名示人,并试图在写作中对小说文体进行“雅化”改造,以便提高小说文体的地位。本文以《剪灯馀话》、《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三部文言小说为例,探讨小说体卑观念下文人们不同的小说写作心态,及他们为摆脱文体焦虑而进行的“小说诗文化”、“小说学术化”和“小说的情感叙事追求”三种尊体的努力,考察文体变革与文化土壤之间的内在关联。
文言小说 文体焦虑 尊体实验
明清时期是中国小说创作的鼎盛期,白话小说成绩尤为突出,充分展现了小说文体的巨大潜力。与此同时,发达的文章辨体意识与理学正统思想的合流,进一步强化了小说体卑观念。小说实践与理论之间出现巨大的地位落差,使得士大夫文人对小说既倾心向往,又心存顾忌,小说创作的文体焦虑因此而生。于是,小说中身份较高、形式较雅的文言小说,成了文人们公开介入小说写作的主要选择。文言小说体制杂乱的历史,也为文人们推尊小说的努力留下了操作空间。本文以《剪灯馀话》《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三部文言小说为案例,考察在小说体卑观念下文人们的不同小说写作心态,及其为摆脱文体焦虑而做出的几种文体处理方式。
一、《剪灯馀话》:体卑焦虑下的“诗文小说”实验
“诗文小说”的创作是明代文人在小说体卑压力下进行的一种小说雅化尝试。“诗文小说”的说法最早由孙楷第提出,用以概括明代由瞿佑、李昌祺开创的“多羼入诗词”的文言小说①。从语言形式上看,唐传奇中《游仙窟》等“辞赋派”小说已开“诗文小说”之先例②,但唐辞赋派小说羼入诗文的程度较轻,总体上不影响小说叙事,“用意固仍以故事为主”,而且唐代辞赋派小说的出现原因与“诗文小说”有显著区别。据今人研究,唐代辞赋派小说的出现一方面是文体内部自然演变的结果,是“从秦汉以来的叙事辞赋演化而来的”③,另一方面可能与唐代举人的“温卷”行为有关,因为辞赋派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云麓漫钞》卷八),可以为作者带来名声和机遇。而“诗文小说”盛行于小说体卑观念深入人心的明代,创作小说并无直接的功利目的,往往是出于对小说本能的喜爱,含有推尊小说的意图。王恒展认为“明代是中国小说的雅化时期”,其基本思路是把源于“街谈巷议”的小说,改造为“以儒家文化为主流,以诗书礼乐为内核,以标准的书面语言即文言为外壳,以传统诗文为主要形式”的“典型士大夫文化”④。显然,这样的“雅化”改革源于小说体卑观念,目的是提升小说在儒家社会中的地位。
明代“诗文小说”,以瞿佑《剪灯新话》名气最大,但从小说文体的诗文化改造程度来说,李昌祺《剪灯馀话》(以下简称《馀话》)最为典型,更适合作为研究的范例。李昌祺(1376~1452),永乐二年进士,官至广西布政使。《馀话》的“自序”里⑤,李昌祺称他十分喜欢《剪灯新话》,“锐欲效颦”,于是“捃摭文”,编为《馀话》。然而,身居从二品高官的李昌祺,不能无视小说体卑的现实,担心《馀话》“取讥大雅”,于是在序文中不惜笔墨对自己的小说创作进行辩解。他首先承认《馀话》“成于羁旅,出于记忆,无书籍质证”,一度“不敢示人”,乃至想“亟欲焚去以绝迹”,但考虑到这些小说可以“豁怀抱,渲郁闷”,“较诸饱食、博弈,或者其庶乎”,于是“遂不复焚”。
需要注意的是,李昌祺在肯定此书价值的时候,引用了孔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这句话为依据。表面上看,这是承认自己小说价值不高的低调姿态,但这段话的用典指向更可能是汉宣帝论辞赋一事。其本事见《汉书·王褒传》: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
可见,西汉辞赋文体面临“淫靡不急”的价值危机,与李昌祺时小说文体遭受的境遇相似。汉宣帝在维护汉赋时虽引用孔子关于博弈的言论,但其意却是高度赞扬辞赋文体,认为辞赋不仅有“绮縠”之美,而且还有“仁义风谕”之善和“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超出博弈这种小道“远矣”!李昌祺此处把自己的小说与辞赋比,明贬暗褒,故序言中才会提及《高唐》《洛神》两篇辞赋,称赞二赋的“修辞缛丽,千载之下,脍炙人口”,委婉地肯定了《馀话》的“浓丽丰蔚,文采烂然”。
显而易见,《馀话》在创作上是有意识地把辞赋文体作为效法的榜样,要求语言具有“虞说耳目”之美,兼及“仁义风谕”,以提高小说文体品味,减轻小说体卑带来的创作焦虑。在此种小说观念下,李昌祺读《剪灯新话》后“惜其词美而风教少关”⑥就不奇怪了。在《馀话》的创作中,李昌祺继承了瞿佑的“词美”的风格,加强了小说“风教”内容,试图从诗文之美与伦理之善两方面改变小说体卑的现状。小说中展开伦理训诫,是明清小说十分流行的做法,不算什么特色,而且小说文体“涉于语怪,近于诲淫”(瞿佑《剪灯新话序》)的内容倾向,大大减弱了“风教”的效果。因此,《馀话》在小说文体上的特点,或者说李昌祺企图在小说中实现的小说尊体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为“诗文小说”的写作实验,“对瞿佑、李昌祺来说,除了显露诗才的动机之外,同时也含有当社会舆论鄙薄小说之时,借助正统文学之力,以较温和合法的形式提高小说地位的意味”⑦。
李昌祺对小说的诗文化改造首先表现为叙述语言的雅化。《馀话》无视小说的叙事本位,把语言之美当成小说的主要目的,于是在叙述语言中大量使用骈文俪句,深典僻字,将读者设定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精英阶层,借此与“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小说划分界限,提高小说的文化地位。如《月夜弹琴记》叙述节妇赵氏祠的荒凉景象,全用骈体:“但见鼠穿败壁,苔绣空街。谷变陵迁,怅贞魂之已远;时殊事异,慨老屋之之仅存。”句式虽雅,然语义重复,破坏了叙事的流畅性、含蓄性。又如《听经猿记》,叙述禅师睡觉“朴握暖足,伊尼卫床”,简短的八个字,就用了两个较为生僻的典故,“朴握”指兔子,典出苏轼诗《游径山》;“伊尼”指鹿,典出黄庭坚诗《德孺五丈和之字诗韵难而愈工辄复和成可发一笑》。此类炫弄学识的小说叙述,简直就是给小说制造阅读障碍,读者如非博学大家,只能不知所云了。
不仅如此,李昌祺还把骈体和典故大量运用于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常常不顾及人物的身份和说话的语境。如《贾云华还魂记》中老妇向魏鹏介绍娉娉:“语颜色则若桃花之映春水,论态度则若流云之迎晓日;十指削纤纤之玉,双鬓绾嫋嫋之丝;填词度曲,李易安难继后尘;织锦绣图,苏若兰岂容独步!”文辞虽华丽整饬,但出于老妇之口,总是有些别扭造作。再来看该文写侍女福福奉劝娉娉的话:
小姐禀赋温柔,幽闲贞静,其性不可及,一也。天资美艳,绝世无双,其貌不可及,二也。歌词流丽,翰墨清新,其才调不可及,三也。谙晓音律,善措言辞,其聪明不可及,四也。至于考究经史,评论古今,然如贯珠,洒洒然若霏雪。……矧又为蓟公之孙,平章之女。母有邢国之贤,弟又令尹之贵。四德俱备,一族同推,行配高门,岂无佳婿?……诚所谓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妾时耻之,无面目将去也。
这段长篇宏论,思路清晰、语言典雅、立场正统,与一个贴身侍女的身份严重不符,更像一个大家族长的道德说教。曹雪芹批评才子佳人小说“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红楼梦》第一回),移诸《馀话》,颇为恰当。
《馀话》诗文化改造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小说中穿插了数量庞大的诗词文赋,小说几乎变身为一个收藏诗文的容器,叙事则成了串联诗文的绳索。全书21篇作品,篇篇都有诗文的羼入,羼入诗文的篇幅比例全部超过小说全文的10%⑧,其中3篇超过了50%,极端者如作者颇为自负的《至正妓人行并序》,诗文所占比例超过80%。《馀话》中所羼入的诗文种类非常之多,文类有启(《听经猿猿记》),有论(《何思明游酆都录》),有书信、答书(《鸾鸾传》),有祭文(《贾云华还魂记》),有檄文(《胡媚娘传》),有铭文(《何思明游酆都录》),有制诰(《泰山御史传》),弹劾文(《泰山御史传》),有撒帐文(《洞天花烛记》);诗类有近体诗,有古体诗,有乐府,有词曲,有楚辞体,有回文诗,有步韵诗,有联句,有集句,有仿《长安古意》的模仿诗《峨眉古意》(《江庙泥神记》)、仿《胡笳十八拍》的《悲笳四拍》(《鸾鸾传》)、仿《琵琶行》的《至正妇人行》等等。诚如刘敬子《序四》里所称的,“有文、有诗、有歌、有词”,符合诗文的审美要求,可以“漱艺苑之芳润,畅词林之风月,锦心绣口,绘句饰章”,甚至被誉为“辞藻之盛,未有过于此者”(《至正妓人行·跋四》)。
诚然,《馀话》中的诗文本身有一定审美价值,钱谦益《列朝诗集》选李昌祺诗有《馀话》中的《至正妇人行》及《月下弹琴记》里的集句诗,并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引安磬的评价,肯定《馀话》中部分诗文“对偶天然,可取也”⑨。但是,从小说的角度来看,这些诗文大多数都属于骈拇枝指,与情节、人物、情感等皆无关联,给人一种“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红楼梦》第一回)的印象,破坏了叙事的明晰性、流畅性,造成叙事的拖沓、冗长,大大减弱了小说的故事性、趣味性和伦理意义。如《田洙遇薛涛联句》《江庙泥神记》这类人鬼恋故事情节单薄,毫无动人心魄的感染力,只有才华的卖弄;《记月夜弹琴记》过多的集句减弱了节烈的主题;《洞天花烛记》也许当作一本婚礼应用文的汇编更为合适。在整部《馀话》中,反而是插入诗文较少的《芙蓉屏记》,写出曲折起伏的感人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当李昌祺《馀话》把小说写作引向诗文化道路的时候,小说自身的叙事特征被抹掉了,小说最终丧失了独立身份,沦为诗文的附庸。齐裕焜认为瞿佑、李昌祺的小说诗文化创作“在语体方面,与唐传奇相比,似有所倒退”⑩。陈大康也说:“自瞿佑、李昌祺之后,作品中多羼入诗词便成了明代初中期文言小说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然而,尽管那些诗文尽受时人称赞,小说的地位在实质上并未提高,反而是将其自身弄得文体复杂,体例不纯。”李昌祺的声誉甚至因《馀话》而受影响,“景泰间,韩都宪雍巡抚江西,以庐陵乡贤祀学宫,昌期独以作《馀话》不得入,著述可不慎欤!”
二、《阅微草堂笔记》:体卑焦虑下的“著书者之笔”“著书之体”实验
同样是在小说体卑压力下进行的小说创作,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阅微》)选择了另一种小说雅化的路径:把小说从“才子之笔”引向“著书者之笔”,进行小说文体的学术化改造,以帮助小说度过体卑的困境。
纪昀(1724-1805)乾隆十九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这样的身份和经历,无疑给他的文论思想带来官方正统的色彩,限制了他小说观念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纪昀对小说体卑的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他主持修纂的《四库全书》收录小说仅限于少数文言小说,完全没有收录白话小说。他主笔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文体也时有贬低,如论及《大唐新语》时认为该书“繁芜猥琐……有乖史家之体例,今退置小说家类”,意谓小说卑于史传,且与“繁芜猥琐”为伍。在他的小说《阅微》卷十八第38条后有一段议论,“青衣童子之宣赦,浑家门客之吟诗,皆小说妄言,不足据也”。此处“小说妄言”一词显然是随手拈来,但这四字的习惯组合,证明了在当时文化背景中“小说”与“妄言”已成近义词,都面临“不足据也”的价值危机。因此,喜欢小说的纪昀,才会情不自禁地在《阅微》里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小说价值申辩:
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滦阳消夏录序》)
念古来潜德,往往籍稗官小说,以发幽光。因撮厥大几,附诸琐录,虽书原志怪,未免为例不纯;于表章风教之旨,则未始不一耳。(卷十四第61条)
此当是寓言,未必真有。然庄生、列子,半属寓言,义足劝惩,固不必刻舟求剑耳。(卷十八第7条)
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辞,鲁史皆然,况稗官小说。……惟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劝惩之旨,不颠倒是非如《碧云騢》,不怀挟恩怨如《周秦行记》,不描摹才子佳人如《会真记》,不绘画横陈如《秘辛》,冀不见摈于君子云尔。(卷二十四第18条)
寓言滑稽,以文为戏也……偶一为之,以资惩劝,一无所不可;如累牍连篇,动成卷帙,则非著书之体矣。(卷二十二第17条)
观其大旨,纪昀似乎颇纠结于小说内容的不真实,但又对小说的教化功能寄以厚望,不同意对小说全面否定。在《四库全书》的小说归类及其《总目》里的小说家评论中,纪昀对小说文体的看法和态度有更为具体的表现。
《四库全书》把小说列入“子部”,这可视为对《汉书·艺文志》传统的继承,但其中也暗藏玄机,因为纪昀所面对的小说创作现实,与刘歆、班固时期的小说已有很大的差别。古典文言小说发展至宋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以叙事为宗”的倾向,附庸于“史部”;一种是以“述道见志”为主的倾向,依托于“子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里将小说分为六类,三类属史,三类属子,充分体现了小说在子、史之间摇摆不定的归属困境。纪昀把小说列入“真伪相杂,纯疵互见”的子部,一定程度上回避小说文体真实性不足的“缺陷”,减轻小说体卑带来的创作焦虑感。《阅微》“题诗二首”中提醒读者“稗官原不入儒家”,其意也应在此。
《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叙述中,纪昀对小说文体有一段概括: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於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
纪昀首先指出早期小说的三个派别:杂事、异闻、琐语,这是他把小说划归子部的理论依据。接着,他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小说的三大功用:“寓劝戒”“广见闻”和“资考证”,藉此解决了小说在儒家文体价值体系中的合法性问题。这三大功用成为纪昀小说观的核心,也是《阅微》这部小说文体实验的指导原则。
“寓劝戒”是指小说可以承担起道德教育功能,这是纪昀对小说价值最为看重的一方面。他始终把伦理训诫放在著书的第一位,“儒者著书,当存风化,虽齐谐、志怪,亦不当收悖理之言”(《阅微》卷六第31条),声称他的小说,“大旨期不乖于风教”(《姑妄听之序》)。《阅微》里涉及伦理的故事非常之多,古代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各种伦常关系,在小说中都得到了多方面的展示,整部小说写鬼事而不废人事,处处散发“神道设教”的影子。《阅微》每叙述完一个故事,作者都会给出一段评价,通常是他直接介入评价,有时则是借用亲友同僚之言乃至小说中狐鬼之言来完成,目的在于阐发故事大义微旨,实现风教目的。
叙事里夹杂教训劝善的情况在明清小说中并不少见,但大多陈腐平庸,成了装样子的套话摆设,而《阅微》里的议论却是小说的精华所在,每每抉奥阐幽,词明理正,展示一种智慧之美。《阅微》的议论常常涉及许多伦理难题,表现了学术探究的旨趣。如卷一第44条论地形吉凶与立身正邪之矛盾,卷二第13条关于身体、情感与诚信的矛盾,卷七第21条人律与兽律等例,其思考的深度与广度,远在时人之上。
“广见闻”,“录之亦足资博物也”(《阅微》卷十九第4条)是纪氏对小说的第二个要求。小说的魅力之一是记载各种神鬼奇事以餍足人们的好奇心,许多小说记载下奇异怪事就结束了,但《阅微》作为学者之文、“子部”之书,为了实现“资博物”的功能,不满足于“知其然”,还努力“知其所以然”。《阅微》常常对所记异事“揆以天理”“以理推求”,展开质疑、思考和解释。如卷一第21条纪氏以为“此事荒诞,殆尊汉学之寓言”,然后分析汉学、宋学意气之争,指出其“非无因而作也”。又如卷五第14条讨论鬼是否有轮回,卷十三第5条质疑“不识天下一灶神欤?一城一乡一灶神欤?抑一家一灶神欤?”卷二十一第6条借狐精论生男生女之“原理”,卷二十一第21条论梦之产生原因等例,无不表现出好学深思的“著书者之笔”特色。
“资考证”显示了纪昀对小说价值的矛盾态度。尽管他深知小说“妄言”传统而将之归于子部,但学者的惯性使得他非常珍视文献的考证价值,禁不住要为小说寻找到考证层面的意义,故将“资考证”列小说三功能之末位,意为小说记载的部分内容可以用于学术考证,而不是要求小说直接承担考证的功能。“资考证”的学术意识,以及作者的博学多才,使得《阅微》叙事中呈现出一种学术化、考证化的倾向。《阅微》在议论中喜欢旁征博引,考镜源流,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然而,小说内容多涉神怪无稽之说,故《阅微》中多数考证仅是徒具形式,并无实质内容。如卷十三第30条,对族叔见怪兽一事,引《博异传》《史记》《列异传》《枯树赋》《祭纛文》等三教九流之文论证此怪兽为女夜叉,虽材料宏富,结论荒唐可笑。此外,《阅微》讲述故事时,作者常会对笔下许多相关人物、地理、词语补上“自注”,体现了学者的严谨,然而有些“自注”似无必要,如卷二十三第23条:“余十岁时,闻槐镇一僧”,随后自注:“槐镇即《金史》之槐家镇,今作淮镇,误也。”这样的注释对小说的理解并无帮助,只是一种学术习惯的流露。
《阅微》的创作体现了纪昀小说观念,是纪昀对当时流行的“才子之笔”小说进行反击的文体实验产品。盛时彦在《姑妄听之·跋》里透露,他的老师纪昀对《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的现象颇有微词,认为这类小说在叙事上过于详尽,在伦理上、学术上站不住脚,“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必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妮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见而闻之?又所未解也”。纪昀把《聊斋志异》为代表的小说文体称为“才子之笔”,而他心中的小说正统却是“著书者之笔”。盛时彦评论说,《阅微》“辨析名理,妙极精微;引据古义,具有根柢,则学问见焉”,“灼然与才子之笔分路而扬镳”,这一附在《阅微》书中的评论是经过纪昀同意的,显然《阅微》是纪昀有意识树立一种学术化小说的文体榜样。
纪昀把小说划入子部,在回避史部的真实性问题的同时,也失去了史部以叙事为中心的文体认同,造成了《阅微》“过偏于论议”、叙事粗疏的文体缺陷。而纪昀在《阅微》中进行的小说议论化、学术化尝试同样没有改变小说体卑的命运。盛时彦称赞《阅微》“虽托诸小说,而义存劝诫”。此一“虽”字,已含有为老师写小说的行为进行辩解之义。稍后的张维屏(1780-1859)说得更为明白:“或又言文达不著书,何以喜撰小说?余曰……稗官小说,搜神志怪,谈狐说鬼之书,则无人不乐观之。故文达即于此寓劝戒之方,含箴规之意。托之于小说而其书易行,岀之于谐谈而其言易入。……观者慎无以小说忽之。”他们认为《阅微》志不在小说,而在“劝诫”。他们在维护纪昀人格的同时,忘记了纪昀对小说价值的肯定,忽略了《阅微》改造小说的苦心。《阅微》在后世之声誉甚高,并非其小说文体改革的成功,而是纪昀的高才卓识难以企及,“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故服膺、嗜好《阅微》者皆为学者文人。对于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典型小说接受群体而言,以“才子之笔”写就的《聊斋志异》才是他们为之心往神驰的小说典范。
三、《聊斋志异》:克服焦虑的“孤愤之书”、“异史”之文
《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创作时间早于《阅微》,但从文学叙事的角度来看,《聊斋》更像是后来居上、后出转精的成功之作。其成功的诸多原因中,值得关注的是蒲松龄创作《聊斋》时的文体心态与文体理念。
蒲松龄(1640-1715)博学多才,科场失意,直到71岁,才按例补为贡生。坎壈的一生使他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始终保持一种疏离感,卑微的身份让他对底层大众文化生态有了深切的体验和认识。他常常以草根的视角来看待通俗文化,积极参与通俗文化的创作,公开编写了大量“田夫野竖矢口寄兴”的俚曲。可想而知,写作《聊斋》这样的文言小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顾忌的了。《聊斋自志》中记录了他对《聊斋》这部文言小说的看法: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展如之人,得勿向我胡卢耶?然五爷衢头,或涉滥听;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从首两句“披萝带荔”和“牛鬼蛇神”的用典看,“不择好音”当指《聊斋》语涉鬼神。小说文体常因此类“不雅驯”内容为人所诟病,故此处“不择好音”可视为蒲氏对当时盛行的小说体卑观念的表面承认,但在背地里他却以屈原、李贺两大天才诗人自比,把《聊斋》当作“天籁”,可见他在心底深处对《聊斋》这部小说有着足够的自信。当然,在那样一个时代,他的小说免不了会遭受“展如之人”(保守道德家)的指责和批评,但他并不放在眼里,以狂放、“不讳”应之。他相信自己是“病瘠瞿昙”(穷病和尚)转世,与儒家本不相干,故能将儒家等级观念搁置一旁,公然把《聊斋》这样的“幽冥之录”,当成是自己一生最为重要的“孤愤之书”,在书里尽情地“遄飞逸兴”“永托旷怀”。对蒲松龄来说,《聊斋》就是他的《史记》,不仅可以“偿前辱”,还要“藏诸名山,传之其人”。
蒲松龄对文言小说的态度也隐含于《聊斋》中刻意标举的“异”字之中。《聊斋》的书名“志异”并非随手而写,其间有微言大义。高珩《聊斋志异·序》说:“志而曰异,明其不同于常也。”这个“常”,当指文字写作理应符合礼法伦常,以“六经之文,诸圣之义”为范本,它们是儒家话语体系中得到确认的经典文体。体卑的小说显然是被排斥在“常”之外的,一般的小说作者对此都讳而不言,《聊斋》却公开宣称自己是违背“常”的,是正统文体的异类。与此相应,在《聊斋》各篇的结尾,蒲松龄刻意地创造了“异史氏”这一特殊的称谓来充当故事的评论者,进一步凸显了他的小说独立意识。从文体上看,“异史氏曰”这一说法至少双重意义:一方面,“异史氏曰”体例与《左传》“君子曰”、《史记》“太史公曰”类似,都是放在故事的结尾表达对事件的评价和感叹,阐发叙事的意义。《聊斋》显然有意识继承经、史中伟大的叙事传统,坚持小说以叙事为中心,然后用“异史氏曰”来弥补叙事文体意义不足的缺陷。与李昌祺和纪昀分别从文字修辞和学术议论上寻找小说文体的意义的方案相比,蒲松龄显然更高一筹。另一方面,“异史氏曰”的“异”字提醒我们,这个《聊斋》的权威评论者不属于史家,暗示《聊斋》不属于史学著作,《聊斋》只是在技术上继承了经、史的叙事,但内容上、立场上与经、史著述不同,“别是一家”。“异史氏曰”显示了蒲松龄《聊斋》有意与正统的经、史宏大叙事保持距离,确以保小说叙事的自由空间,最终实现了文学叙事的突破。
《聊斋》以叙事为中心的小说写法,今天看来理所当然,当时却是一个颇为大胆的实验。纪昀嘲讽《聊斋》“燕妮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正是不满意《聊斋》叙事过多;写过文言小说《子不语》的袁枚也对《聊斋》叙事太“繁衍”颇有异议;甚至十分欣赏《聊斋》的冯镇峦,也认为《聊斋》是“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读聊斋杂说》),其潜台词是:叙事技术为史部传记的专业本行,狐鬼志怪的内容才是小说文体的本质所在,《聊斋》的叙事虽精彩,手法上却越出小说文体的界限,侵入了史学的领地。也许是意识到这个表达所隐含的小说偏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才改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来概括《聊斋》,以纠正冯镇峦的说法。鲁迅用“传奇法”替代“传记体”,意谓叙事并非专属于史部,唐传奇等古小说早已有之;以“志怪”替代“小说之事”,意为“志怪”只是“小说”题材中的一个类别,“志怪”不能完全涵盖“小说”的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聊斋》中关注叙事的重大意义,它突破了当时正统小说(文言小说)的陈规惯例,为时人所不解,却与现代小说观念遥相契合,展示了超越时代的眼光和魄力。
从叙事的角度来看,《聊斋》的场景描写、人物刻画及情节安排都是十分出色的,冯镇峦赞叹“《聊斋》之妙,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写景则如在目前,叙事则节次分明,铺排安放,变化不测”。《聊斋》虽时有用典,但总体上采用简洁优雅的文言来进行叙事和描写,有时能化用口语俚语,生动自然,富有表现力,如《王成》说王家之穷,“王呼妻出见,负败絮,菜色黯焉”,寥寥数语,给人印象深刻。又如《翩翩》里花城娘子戏言“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与白话小说的没有多大区别了。在情节安排上,作者在选择题材和下笔时始终注意情节的曲折有味,力求写法变化多端,紧紧地吸引住读者。如《葛巾》“不惟笔笔转,直句句转,且字字转”,故事紧扣人心。甚至在很短的一段文字里也可以做到悬念迭起,如《西湖主》书生陈明允误入花园,等待主人处罚的过程一波三折,戏剧性极强。相比之下,《阅微》“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不屑屑于描头画角”,叙事略具梗概而已;《馀话》则志在诗文,叙事只是串联词章的线索,情节十分单薄。《聊斋》叙事中也有插入诗文的现象,但其比例远远低于《馀话》,且部分诗文还兼有重要的叙事功能,如《续黄粱》中的弹劾疏奏文字,兼叙曾孝廉得势后的种种罪过,是故事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聊斋》在内容选择、文笔刻画和价值取向中都表现出对主流、正统的伦理秩序一定程度的疏远和抗拒。尽管《聊斋》的立场未能完全脱离那个时代的忠贞孝悌观念,但其故事情节的主要叙述驱动力已不再是礼教的维护和追求,而是来自于情感与欲望,形成了所谓“多言鬼狐,款款多情;间及孝悌,俱见血性”(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会评本卷首)的尊情宣欲倾向。以作品的特色而言,如果说《馀话》是以文炫人,《阅微》是以理服人,那么《聊斋》最成功的地方,也许就是以情感人、以欲诱人。《聊斋》正面描写了很多“狂人”“痴人”“癖人”,有情痴(《阿宝》)、棋痴(《棋鬼》)、花痴(《葛巾》)、书痴(《书痴》)、诗痴(《白秋练》)、石痴(《石清虚》)等等,记载了很多为了情和欲“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的例子,在礼教伦常之外发现了人生的价值。因此,《聊斋》的故事最为感人,《促织》令人愤慨,《赵城虎》让人感叹,《缢鬼》使人悲伤,《翠云仙》大快人心,《婴宁》忍俊不禁,七情六欲在这里宣泄,压倒了正面的陈腐说教。《聊斋》的“异史氏曰”也有异于经、史正统的理性姿态,言辞激情洋溢,形象鲜明,读者恍若见“异史氏”或手舞足蹈(《镜听》),或怕案而起(《伍秋月》),或童趣盎然(《红玉》),或沉痛哀戚(《缢鬼》),或热潮冷讽(《金和尚》)。这些评论虽不如《阅微》冷静深刻,却具有前者所不具备的文学色彩,与文中的叙事相映成趣。
摆脱文体焦虑的蒲松龄获得了文体创作的自由,在《聊斋》中充分发挥了他的叙事才华,最终写出了享誉后世的文言小说杰作。但这种轻松的写作心态也给《聊斋》的文体实验带来一些不足,使得《聊斋》写作不够严谨,出现“体例太杂”的问题。书中除了那些优秀的长篇叙事文章外,也有短不成章记异小文;“异史氏曰”有时议论过长,有蛇足之嫌;羼入诗文也偶有无关紧要的卖弄文字,然瑕不掩瑜。
总之,在蒲松龄的笔下,文言小说成了“孤愤之书”、“异史”之文,获得了独立的文体意义与价值。《聊斋》的叙事因此不再屈身于经、史的藩篱之下,也无须用诗文或学术来装扮自己,在主流话语之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生存空间,“司风教者,重务良多,无暇彰表,则阐幽明微,赖兹刍荛”。在自信的心态下,蒲松龄跳出宋明以来的文言小说规范,直接承接唐传奇的叙事,大胆借鉴“低俗”白话小说的叙事手法,重启了文言小说的叙事之路,最终形成了以情感欲望为内核的虚拟叙事文体,造就了现代意义的文言小说经典。
综上所述,盛行于明清时期的小说体卑观念给文人们的小说创作带来一种焦虑心理,促使他们在实名创作的文言小说中进行有意识的文体改革,力图提高小说文体地位。考察这些文言小说的创作心理及其在文体上的成败得失,为我们的理解和把握明清文言小说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视角。
注:
①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
②③ 程毅中《古体小说论要》,华龄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45页。
④ 王恒展《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页。
⑤⑥ [明]瞿佑等著《剪灯新话》(外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122、120页。
⑧ 此处数据参考了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的相关统计,见该书第114页。但氏著在统计时认为《何思明游酆都记》一文诗文比例低于10%,似乎忽略了此文所引“何思明”《警论》的大量文字,这些文字和后面的铭文加起来约占全文篇幅的20%,故此把《何思明游酆都记》也算在10%以上之内。
⑨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191-192页。
⑩ 齐裕焜《明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责任编辑:王思豪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108LZD102)阶段性成果。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