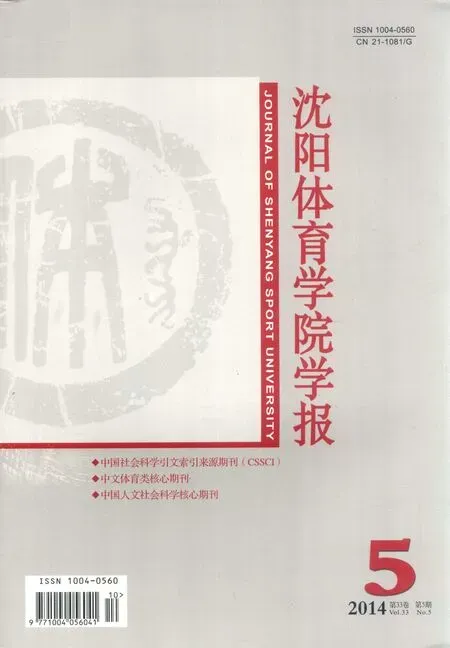大众文化视域下的中国武术发展研究
侯胜川,刘同为
(1.闽江学院体育部,福建福州350108;2.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上海200438)
◄民族传统体育学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中国武术发展研究
侯胜川1,刘同为2
(1.闽江学院体育部,福建福州350108;2.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上海200438)
以大众文化的视角切入,对20世纪中国武术的变迁做了剖析。研究认为:清末民初,武术以悲情面孔出现,作为救亡图存的药方以唤起大众身体和精神的觉醒,使武术具备了“大众”的基础;建国初期,武术作为政治需要成为大众增强体质的体育活动;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众文化的崛起带来了武术的全方位发展,同时也产生了大众文化审美泛化和机械复制的弊端;因此,必须审慎地对待武术在大众文化中的影响,引导大众文化“快感美学”的审美幻觉,创新武术发展的当代新路径。
武术;大众审美;大众文化
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在《民众的反抗》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大众文化”的概念,主要指地区、社团、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和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的英文为Mass Culture,意为乌合之众的文化,带有显而易见的贬义色彩,是西方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在西方社会20世纪30—50年代的文化批判思潮中,Mass Culture指为商品利益所驱动的文化产品。今天所有的影像崇拜物品如电影、广播、电视、音像制品、广告、流行出版物等在当时都属于Mass Culture,难以登上大雅之堂。直至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大众文化的命运才真正发生逆转。在该派灵魂人物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汤普森等的相继努力下,大众文化被重新认识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链条[1]。
中国的文化结构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的二元格局划分——大众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化,在内容和基础上与西方大众文化最为接近的当属相对于贵族文化的民俗文化。经过清朝末年以来一个多世纪的改造,相当一部分民俗文化具备了西方大众文化的特征。从作为民俗文化代表的中国武术的近代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大众文化在中国的起始、发展、壮大历程。分析中国武术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轨迹,剖析其内部建构和生成机理,对今后中国武术的发展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中国武术20世纪的大众文化转型
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并以大众媒介和现代技术手段为文化传播形式和生产形式,按照市场规律去运作,能为大多数群体所感知接受;其受众主要为现代都市大众。它与以往的大众革命文化和民间的通俗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大众文化的出现改变了当代社会审美风尚的基本格局。
中国的大众文化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清末民初的精武体育会、“中华新武术”和“中央国术馆”等革命事件借助民俗文化中的代表——武术,以唤起大众的革命热情和精神觉醒;民俗文化是依附于人们生活习惯信仰而产生的文化,带有浓厚的宗法血缘色彩,是一种小团体结构;革命需要唤起大众的参与,就必须打破以往的小团体结构,这便是革命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矛盾之处。即使如此,当时各种组织的“大众”也属于时代精英,远非今日的普罗大众。所以武术的大众文化转型显得势在必行。而大众文化条件的真正形成则肇始于建国后武术的“增强人民体质”政治需求;大众文化的崛起则是归功于改革开放春风和市场经济沃土的培育;大众文化的崛起使得延传千年的中国武术具备了商品化、媒介化、标准化、审美化、娱乐化的特征。
1.1 武术的“大众”由来
大众是相对于精英群体的,指普通的大多数社会成员。海德格尔认为大众就是常人,“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特定的人,而是一切人都是这个常人,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2]由于大众指代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大众正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力量。一般而言,中国武术在古代从属于和贵族文化相对立的民俗文化。理论上讲,中国民俗文化是前工业化社会的产物,亦即中国农耕文明中的文化形态。农耕文明封闭、各自为政的宗法结构和血缘关系决定了其特定生活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中国武术的传统里,“执师如父”、“传内不传外”等宗法传承规矩限定了武术的社会传播范围;一定程度上这种传承制度也是维系宗法成员凝聚力的必要纽带;由于武术血缘传承和类血缘传承的限制,武术具有明显的地域化特征。武术中常见的“东枪西棍”“南拳北腿”“少林武术”“陈式太极拳”等即为此类。这使武术只能依附于当地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信仰,难有更大发展空间。
然而,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风雨飘摇,唯有“大众”觉醒才能救中国。在民间有较高普及的武术成为拯救大众觉醒的药方之一。20世纪初,被赋予救亡图存、强国强种的国粹武术与西式体操结合,开始了其大众化转型的第一步。从创立于1909年的“精武体育会”,到1911年旧式军阀马良创立的“中华新武术”,再到1928年张之江创办的“中央国术馆”,武术的发展由繁至简、由暗到明,由创编统一教材到创办专门的武术培训机构、学校,武术的传承方式和生存空间走上了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逐渐摆脱了数千年血缘谱系传承的缓慢之路。武术的受众从乡间“门里人”开始面向都市大众,武术第一次向“大众”张开怀抱,也由此开启了其“大众”化之路。
1.2 新中国成立后武术的大众化发展
1.2.1 政治挂帅的武术大众化发展 建国后,我国人民终于从百年的社会动荡中稳定了下来,祖国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1949年政务院批准筹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时任国家副主席朱德同志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筹备会议上提出:“要广泛地采用民间原有的许多体育形式。”1952年,毛泽东同志挥笔写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号召人民参加包括“打太极拳”在内的各种体育运动。同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把武术列为推广项目,并设置了民族形式体育研究会,根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负责对武术等民族形式体育的挖掘、整理、继承和推广工作。”[3]362从建国初期一系列关于武术的关键词中看到了武术面向大众的号角已然吹响。接下来数年直至文革开始,中国武术的发展呈现了建国后的第一个高潮。这期间成立了各级武术协会,制订了我国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成立了各级武术队,武术内容进入中小学体育课,创编了简化太极拳和长拳、刀术、剑术、棍术等套路,编写了体育院系通用武术教材。显然,武术原有的地域性、宗法性被高度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所取代,武术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和健身道具开始走进广大市场需求的大众中间来。
1.2.2 经济主导的大众文化崛起 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席卷神州大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社会摆脱了百年革命斗争的心态,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后革命时代,确立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文化作为反映社会生活和关系的重要层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中国大众文化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并跻身于原有的主导文化、精英文化、民俗文化阵营。大众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审美日常性、传播媒介性、娱乐生活性等特征,恰好迎合了大众对时代的审美需求;于是,大众文化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央,改变着一系列的文化艺术事件。这一时期,中国武术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则是1982年电影《少林寺》的热播,“一毛钱一张的电影票的时代创下了上亿元的票房”,这样的电影票房纪录再无人能打破。参加表演的演员以李连杰为首均为专业武术运动员且无演出经验,单从电影剧本、演员等电影本身因素而言,很难解释这一电影界奇迹。但是,从大众文化的视角发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孕育已久的中国大众文化在现行体制的默许和市场逻辑的笼罩下异军突起”[4]取代了传统精英文化所长久支配的社会文化范式和审美品位,打破了传统戏剧和政治样板戏的美学范畴,以动静迅即的快感美学审美迅速俘虏了全国大众。此外,较之传播千年之久的口传文化和印刷文化,电影是一种以影像来传递信息的现代传播媒介,电影视觉彰显了动感图像接受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这使武术的视觉因素在大众中更具优势地位,也是《少林寺》成功的原因之一。
借助电影《少林寺》的轰动效应,少林寺则从禅宗祖庭演化为武术界的泰山北斗。少林武僧团全球巡回表演,注册少林实业公司,办少林药局,全球海选“功夫之星”等一系列少林事件,在被媒体称为少林寺CEO的方丈释永信这里,“少林寺的‘生存之道’,便演绎为‘生存模式’,‘品牌’、‘市场’、‘策划’之类的现代营销学名词……”[5]周伟良把少林武术的过度包装称为演艺化,把其分为3类:1)影视作品,如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少林寺》《少林小子》及《新少林寺》等;2)以武术为元素,借助布景、道具、声光等表现一定剧情内容的舞台剧,如《风中少林》《功夫九卷》及《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等;3)少林僧徒,包括少林寺武僧团培训基地等向外展示的拳械及功夫表演[6]。作为佛门圣地的少林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亦未能免俗地融入大众文化的潮流中,显示了大众文化的难以抗拒性。少林武术仅是大众文化崛起中“少林寺事件”的缩影,也是中国武术由民俗文化转向大众文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电影《少林寺》不仅显示出中国大众文化第一次对原有主导文化、精英文化的猛烈冲击,也使代表中国武术的竞技武术走进亿万大众的视野,成为一代人心中的集体记忆。此后的十多年间,中国武术风靡神州大地,少林寺更成为大众心中的武学圣地,众多国外团体来此寻根问祖;各地拳师携《少林寺》的春风而成立的武术馆校,一个个赚的盆满钵满,农家作坊也因此而一跃成为现代教育的民办专业武术学校。不同于民国期间的“中华新武术”和中央国术馆的悲情武术,改革开放中的武术彻底扭转了数千年来人们因因相袭的群体形而上沉重。至此,中国武术完成了一个世纪的文化转型:从闭塞的乡间走向都市,从“下里巴人”的“乡下把式”成为寻常大众的娱乐休闲活动。
2 大众文化主导下的中国武术审美变迁
由于大众文化具有审美日常化、形式娱乐化的特征,作为大众文化的武术必然要凸显其娱乐和审美的功能。大众文化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因此在大众文化中,中国武术对师徒伦理森严等级秩序的注重和对内心深度的追求逐渐瓦解,传统的自我超越审美体验无缘于大众文化中的武术形式,传统文化注重的神性美学体验让位于大众文化中的视觉美学刺激;如丹尼尔·贝尔所言:“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图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7]亦可以认为,大众文化新技术带来的视觉冲击和崭新的想象空间以及大众文化所蕴含的身体解放为中国武术拓展了新的存在空间,正如竞技武术的蓬勃发展也给中国武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历次的《武术竞赛规则》演变中可以寻觅这一审美历程变迁。
2.1 《武术竞赛规则》视域中的审美变迁
《武术竞赛规则》这一硬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出现,使大众对武术的审美有了自己的评价标准。由此,武术表演审美从艺术欣赏转化为竞赛评判,使人们从经典艺术的“美的陶冶”转向对身体感觉和生理欲念的“快感美学”关注。《武术竞赛规则》的出台也拉开了竞技武术主导中国武坛半个世纪之久的序幕。竞技武术是在传统武术基础上,由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发展形成的,以套路和散打为两大活动内容运动形式,以教练员和运动员为活动主体,依照竞赛规则,以争取优异成绩为根本目的的中国现代竞技体育项目[8]。1956年4月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暂行规定(草案)》中,第一次把武术列为表演项目。表演性是大众日常审美的最基本原则。武术成为表演项目,一开始就奠定了其作为“大众”审美的存在基础。
建国以来,《武术套路规则》经历了8次修订。1956年在北京举行12省市武术表演赛,试行了5条40字的评分标准。1958年,中国武术协会起草了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规定了竞赛套路的组别、内容、动作规格标准,以及允许创造自选套路。对自选套路的放开,标志着武术传承的“规定性”开始向日常审美的“个体性”倾斜,武术套路不再拘泥于祖传的神圣,而妥协于大众审美改造,这是武术开始走向大众审美化的第一步,表明了武术竞赛套路开始了突出个性的张扬和对大众审美的尊重,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由此,拉开了武术套路布局、编排、动作创新、难度、服装、配乐等方面的时代气息。
1960年国家体委又审定了第二本《规则》。与第一本《规则》相比,增加了规定套路比赛的条文,把动作质量作为衡量运动员技术水平的主要标准。同年9月在郑州举行全国武术比赛,项目除原有的长拳、太极拳、长器械和短器械外,增设了南拳比赛。另外,表演项目也予以计分。这次比赛的特点之一是套路中高难度动作(如腾空、翻转等)普遍增加,并且速度快、腾空高、落地稳。“快”“高”“稳”恰好是日常审美停留的瞬间。从第一本《武术竞赛规则》的制订、颁布到这次比赛,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武术套路的难度提高之快,运动员年龄结构变化之大,充分体现了《规则》对武术发展的巨大影响和导向作用[9]5-6。1963年修订后的《规则》规定了套路时间必须在1 min 45 s至2 min 30 s内完成,这也是《规则》向大众审美意识妥协的佐证之一。传统武术注重“内视”的体验,运动员在演练套路时,全神贯注地进入拳术的世界,实践自身对拳术内核的体悟,一趟拳短则数分钟,长则数十分钟;在时间的流动过程中,人们才能感知、体验、思考,但是大众文化追崇即时性的审美体验,不愿“费力”进行精神思考,要求在短时间内得到感官刺激,给精神以“快餐”食粮,以达到内心短暂的喜悦;时间的延续会使人们产生审美意识的疲劳,因此,《规则》对时间的界定同样是基于大众审美的现实考虑。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体委明确提出了“难度大、质量高、形象美”的武术技术发展方向。在1963年的《规则》补充规定中,对技术的评价注重于动作准确、劲力完美、节奏鲜明、形象逼真等方面。在整个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初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武术的发展陷于停顿。需要注意的是,在1973年的第3本《规则》中增加了难度动作加分的条款,鼓励运动员使用跳跃、翻腾、平衡等难度动作,“提出了武术套路运动应向高、难、美、新的方向发展。”[9]81987年,第6届全运会中,武术比赛的成绩计入到各省市代表团的团体总分和金牌数中,这一重要决定提高了竞技武术比赛的地位,极大地调动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竞技武术的快速发展。
在1991年实施颁布了第6本新修订的《规则》,其“内容更加完善、周详、使武术竞赛向规范化、科学化迈进了一步。”[10]本次修订的亮点在于“对完成规定难度创新动作的运动员给予0.2加分作为鼓励”。难度动作有了分值,对于竞技武术套路来说,这是个历史事件,表明最吸引大众眼球的、具有惊险刺激的难度动作开始在赛场上具备了话语权。最近的一次武术规则修订是在2003年,“力争使武术竞赛规则更加科学化,更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的要求,为争取竞技武术进入奥运会创造条件。”[11]本次规则的修订一改原有的评分办法,实行切块打分的原则,难度分值提高到2分,并且设置了难度等级,创造性地允许在比赛中配音乐。音乐的出现,一改以往武术竞赛的视觉审美主导原则,视觉和声音交织在一起,组织了全新的美学想象,全面具备了大众美学的基本特征:影像和声音。视觉和音乐的融合,使观众对武术套路的欣赏有了全新的审美体验,更容易投入到直接的审美交流过程中。
从《规则》的演变历程中,分明看到了竞技武术对中国武术经典审美的重构,逐步趋同于大众视觉感性的飞扬,竞技武术向表演性审美的靠拢,乃是大众日常审美生活化的必然,因为任何表演、比赛只有吸引大众才能赢得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2.2 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武术审美麻痹化
毫无疑问,武术的大众化审美发展也提高了大众的审美趣味,促使武术习练者不断追求突破“大众审美”的内在冲动。武术难度动作不断得到突破,武术套路的编排愈加考究,刘同为[12]将形式美学的定律——黄金分割率引入武术套路编排中,认为将套路中的高潮点安排在黄金分割点上,可促进审美主体情绪变化,彰显节奏的最佳张力效果。程大力坦言:“坦率的讲,不得不承认,要论漂亮,没有哪个民间武术流派门派比得上竞技套路;要论漂亮,没有哪个民间武术家比得上李连杰、赵长军、王萍、彭英,他们的武术舞蹈——竞技套路表演登峰造极,我估计是没有人能超过他们了。”[13]但是,武术发展的“大众审美”是否充分体现了美学所倡导的那些精神自由、人格独立、超越意识、完善任性的观念?周宪在论及“日常生活审美化”提出了假设:“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只是在表层上缓解和转移了日常生活本身的压抑和限制,并未从根本上把它改造成符合美学精神的活动?”[14]137亦可假设,武术的“大众审美”发展是否只是从大众文化崛起的历史场域中得到暂时的解脱,并未在根本上为武术的发展指明方向?
曾经全国武术馆校有12 000多家,而随着人们对武术热潮的消退,这一数字已大大缩水;以登封市为例,2004年的统计表明该市有武术馆校45家,而此前的鼎盛时期,武术馆校达100多家;周口市的武术馆校数量已经由数年前的200多家锐减到2004年的48家。武术馆校的没落反映出众多的社会问题,无可争议的一个原因就是“大众审美”的武术在人们心目中已近“麻痹化”。与“大众审美”相对的是武术的“大众实用”,即武术的审美发展并不能解决习练者的现实问题(社会生存、社会地位等);上个世纪末,各地主办的印刷着精美的武术运动员封面的武术杂志被大众哄抢而空,如今大多停刊歇业,剩下几家仍在苦苦支撑,且发行量锐减。退却的武术热潮和曾经的武术赛事门庭若市到今天的门可罗雀都在诉说一个事实:武术在大众文化主导的日常审美化中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威尔什认为当美的事物到处泛滥时,当人们沉浸在舒适美观的生活环境之中时,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麻痹化’和冷漠”[14]137;大众审美造成的麻痹化实际上就是审美在千篇一律的美学机械复制中“疲劳化”,中国武术原有那种令人震撼和其他武技难以企及的独特美学品质在广泛的大众审美过程中被逐渐消解,人们无法从一次又一次的难度动作中得到丝毫的惊险刺激和快感审美。武术动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逐渐变得僵硬起来,武术套路的编排和创作表现出日益明显的技术机械复制化和显而易见的商业化倾向。当武术套路的装饰化和人工化日益充斥着人们的眼球时,武术原有的质朴、自然、自由特性就距离人们越来越远。于是,近几年另一种思潮逐渐回响起来——回归自然的传统武术。
3 大众文化语境中武术泛化与机械复制
3.1 武术的泛化发展
美国《时代周刊》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9%的中国男人都有匡扶正义的武侠梦,96%的女人都有飞檐走壁的幻想,100%的中国人都认为武术是中国传统文明、文化的代表,是中国文化的神韵[15]。由此可见,在大众心中,武术所代表的不是“太极十年不出门的”艰辛修炼,而是大众心中幻化出水墨山水般的武术意象;试问,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各种所谓武林秘籍公开发行的现代,有几人练成了少林72绝技,又有几人根据铁砂掌的秘方练着或者练成了血肉之躯与铁石争强的硬功呢?无疑,武术在当代被幻化成一系列与武术相关且又远离武术本质的泛武术形式,人们所熟知的影视武术、艺术武术、网络武术、文学武术皆属此类。虽然此类武术并非真实操练的武术,但是却是对大众影响最为广泛和最为深刻的武术形式。
在当代,“大众文化改变了传统文化资源的分配方式,创建了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等级的文化消费空间和消费方式,大众可以更自由、更方便、更快捷地获取自己喜爱的文化资源;与过去文化为精英阶层垄断的情形不同,大众作为主人自由地参与到大众文化的消费和受用中,在消费和受用的过程中,大众凭借自身的文化影响力不断加强自身的现实合法性。”[16]大众对武术的自由想象演化为对武术的无限制攫取,武术泛化为一个符号,不仅是少数人健身、实用的工具,更是大众任意想象的素材。大众借此成就了某种自我想象,如宋明炜所言:“所谓‘功夫神话’是以功夫为核心意象的一套使我们倾向于将幻觉当作真实的话语系统,它出现在许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文化和思想议论之中,启发着我们发挥无尽的想象力,去扩张功夫在强身健体、磨炼意志、塑造新民、驱除外敌、救国救民、扬我国威等功能方面的重大意义。”[17]
3.2 武术的机械复制发展
由于大众文化的日常审美生活化特点,大众作为审美主体趋于同质化,所以,以吸引大众眼球为主要目标的武术发展必然在风格、结构、动作等方面表现出机械复制的特点。
以竞技武术套路为例,早期的武术套路充分利用了传统武术动作的原型,如长拳是在“吸取了查、花、华、炮、少林拳诸拳种之长的基础上形成的。”[18]早期的陕西武术队创编的武术套路有着鲜明的西北劈挂、通背等地域风格。“这时(1978年)竞技水平提高很快,特别是长拳类项目,不但腾空动作高,还创造了腾空旋风脚接劈叉、腾空摆莲接做盘、侧空翻接劈叉、旋子转体等高难动作。”[3]405随后,竞赛规则的放开,“难度大、形象美”成为套路发展的主导思想,“难度、形象”等视觉审美术语在传统武术套路中符合标准的动作并不多,“华而不实”所适用的审美标准在中国武术身上并未例外,于是运动员所表演的武术套路中旋风脚、旋子转体、空翻等难、美动作“不约而同”地扎堆出现。武术套路的发展成为本雅明所描述的“机械复制艺术”,“难度大、形象美”变成竞技武术套路的美的黄金分割点。武术套路逐渐演化为一种工业模式,所以,运动员的套路呈现“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之趋势;武术套路的“难度大、形象美”在大规模的工业复制面前开始变得平淡、平庸甚至于庸俗。
无独有偶,本应远离机械复制的传统武术,也未能免俗地成为大众复制的素材。传统武术的复制以流派、拳种为特点。以太极拳为例,“仅太极拳就至少衍生出上百余个新流派,‘九天玄女传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尼姑’现象再度随处可见”[19]。“海灯神话”中,一个懂武术的普通老人被复制为成为身负少林寺方丈、一指禅、梅花桩、童子功等武功绝学的多重形象;有些复制更为简洁,直接套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功名称,“贴牌”为降龙十八掌、九阴真经、六脉神剑;武侠小说中各大门派陆续粉墨登场,在各大掌门隆重而严肃的表演中,大众得到了暂时的精神愉悦和感官享受。
本雅明指出,由于机械复制在现代艺术生产中的广泛应用,艺术品原有的某些特性和属性便会消失,最重要的就是“光韵”。所谓光韵即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反应[20]13。任何艺术品都是创作者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中的特殊创造,即具有古典艺术的原真性,这是任何完美的机械复制品所不能达到的独一无二特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体现了历史又囿于历史。“韵味的衰竭来自两种情形,它们都与当代生活中大众意义的增大有关,即现代大众具有着要使物在空间上和人性上更易接近的强烈愿望,就像他们具有着接受每件实物的复制品以克服其独一无二的强烈倾向一样”[20]57。武术门派、套路原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日益强大的大众文化面前模糊了自己的界限,“‘光韵’的消失便是大众文化特点的显现”[21],传统文化所不齿的审美在大众文化成为首当其冲的选择;然而,过度的强调感官的享受,忽视对理性的反思,极易造成武术“光韵”的迷失。
4 结束语
从强国强种的悲情武术开始,中国武术的大众化经历了救亡图存、增强体质、大众审美等阶段。罗森贝格认为大众文化的不足之处是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大众文化的审美实质是一种以欢乐为核心的理念,如竞技武术套路的开始就笼罩上了“诗化”的特点,既要“突出项目特点,加强攻防技能,严格动作规格”,又要“难度大、形象美”,实际上陷入“鱼和熊掌”的两难逻辑,所谓武术的技击含义和文化内涵往往成为空谈。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大众文化的文本选择不得不降低自身的的审美层次以满足更大群体的需要,从而使武术达到最大程度的审美泛化。
过于排斥或者拒绝大众文化的文本形式会陷入某种程度的狭隘偏执,那种以华夏为中心坐地称雄视“番邦”“蛮夷”为非我族类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必然陷入中国武术发展的“反启蒙民族主义”;同样,大众文化的市场机制是一把双刃剑,过于追求普通大众的经验和感受,就会背离中国武术特有的文化内涵,淡化人们对其理想主义和人文精神的追求。所以,必须审慎地对待武术在大众文化中的影响,要秉承一种开放宽容的胸怀,在深入研究大众文化的生成机制和文化生产范式的基础上,引导其超越感官刺激和身体欲望所创造的审美幻觉,达到精神和肉体的完美统一,或许这才是中国武术发展的应有之义。
[1]董琦琦.大众文化及相关问题论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1(2):299.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上海:三联书店,1987:156.
[3]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362,405.
[4]傅守祥.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意象和批判[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1.
[5]胡展奋,杨继桢.云游方丈营销少林[EB/OL].[2007-06-20]http://travel.sohu.com/20070620/n250680805.shtml].
[6]周伟良.少林武术,繁华后的沉思[J].中华武术,2012(2):8.
[7]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156.
[8]周伟良.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25.
[9]刘同为.武术套路竞赛裁判操作指南[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5-6,8.
[10]邱丕相.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75-176.
[11]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武术套路规则(草案)[S]. 2003.
[12]刘同为,王昊宁.黄金分割率在武术套路编排中的应用[J].中国体育科技,2009,45(4):92.
[13]程大力.舞蹈之魂艺术武术——竞技套路来自何方去向何方[D].申江国际武术专家论坛,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07:131.
[14]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37,137.
[15]佚名.失落的中国功夫[EB/OL].世界一家功夫网,2010-05-14.
[16]张伟.消费语境下大众文化的生成与发展[J].学术界,2010(7):124.
[17]宋明炜.功夫神话西渐之累[EB/OL0].[2007-03-14]http://2008.163.com.
[18]编委会.中国武术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86.
[19]马廉祯.论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转型与竞技武术的得失[J].体育学刊,2012,19(3):119.
[20]本雅明.机械复制艺术[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13,57.
[21]陈玉霞.机械复制艺术与文化工业—本雅明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之比较研究[J].理论探讨,2010(3):60.
责任编辑:乔艳春
Development of ChineseW ushu in the Context of M ass Culture
HOU Shengchuan1,LIU Tongwei2
(1.P.E.Department,M injiang University,Fuzhou 350108,Fujian,China;2.Wushu School,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200438,China)
Based on themass culture perspective,analysi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Chinese Wushu.studies suggest that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Wushu aroused public awareness as a sad faces.Wushu has a“popular”foundation.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as a political need,Wushu enhanced physical fitness activities of the public and w ith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rise of popular culture has brought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Wushu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mass culture aesthetic generalization and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drawbacks.Therefore,we must carefully deal w ith the influence of Wushu in themass culture,guide themass culture“pleasant sensation aesthetics”and create the new path of contemporar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ushu.
Wushu;mass aesthetic;mass culture
G852
:A
:1004-0560(2014)05-0139-06
2014-08-10;
2014-09-25
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武术‘文化空间’的秩序调整、重组与跨越研究”(12BTY051);闽江学院2013年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MJUC2013072);2014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A类(JAS14256)。
侯胜川(1980—),男,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武术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