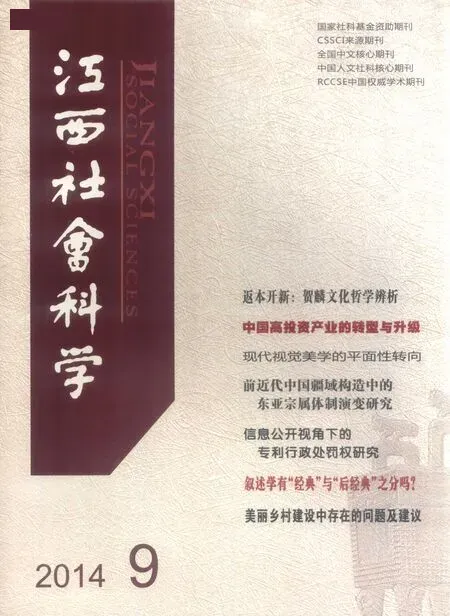《拟邺中集诗》对曹植诗文的接受与解构
■王 津 李剑锋
《拟邺中集诗》深蕴着谢灵运对曹植人生遭遇、文学创作特点及其人生与创作关系的深刻理解,在曹植接受史具有突破性意义,对后来者之模拟、阐释曹作影响深远。该组拟诗为《文选》杂拟类悉数录入,《诗品》亦誉之为“五言之警策者”,梁人对此拟诗评价之高可见一斑。但后代对此拟诗则颇有异议。如宋代刘克庄言:“谢康乐有《拟邺中诗》八首,江文通有《拟杂体》三十首,名曰‘拟古’,往往夺真。”[1](P8356)而明代张溥则言:“谢客儿《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评者谓其气象不类,下逊文通。”[2](P218)这两种不同观点实基于“类与不类”的衡量标准,与梁人的批评着眼点有所不同。刘勰曰:“文辞气力,通变则久。”[3]萧子显言:“若无新变,不能代雄。”[4]梁人对文学“变”之追求反映到他们对拟诗的评价上,不只重其“像”,更重其“变”。《文选》、《诗品》对《拟邺中集诗》的重视表明他们显然视之为富有独特个性的创造性作品,而非简单的模拟之作。正因其有像之一面,所以后人有“夺真”之论;而其又有变之一面,所以亦有“不类”之谈。后人相反的观点恰恰说明灵运此组拟诗之成就,正在于“似”与“不似”之间。“似”是模仿,“不似”则是创造,该组拟诗是虚与实的融合,是精心结构与不断解构的并置,探究拟诗这一特点正是解读此组拟诗之于曹植其人其文接受之关键所在。
一、拟诗的真实与虚构
《拟邺中集诗》是拟邺中曹丕与七子某次宴会创作的诗歌。但就现存文献言,并无曹丕与七子同时聚集写作之记载,《初学记》所引北园及东阁讲堂赋诗者仅曹丕、王粲、阮瑀、应璩四人。曹丕《又与吴质书》中回忆“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5]者,徐、陈、应、刘诸人而已。另外,曹植有《侍太子坐》,应玚有《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曹植、阮瑀、应玚、王粲、刘桢有《公宴诗》,陈琳有《宴会诗》,现存史料中,曹丕、徐干无公宴类诗。[6]而即此公宴诗言,是否写于同一次宴会,此宴会是否为曹丕所主持,同一宴会上是否皆有诗作,均难以确定。因此,《拟邺中集诗》很可能把建安中多人多次参与之不同聚会剪接到一个由曹丕主持的同一宴会上。故此“拟”本身即有虚构之意味,同时亦有建安集会创作情景的影子,如哀声、美酒、欢谈、清论、朝游暮饮等。因此,它是虚构的,又是真实的。
总序以曹丕口吻不无怀念地写建安末年欢娱之极的往事。但建安十七年阮瑀卒;二十二年春,王粲卒;二十二年冬,陈、刘、应、徐,一时俱逝。而拟诗中魏太子、王、陈、徐、刘、应之诗反映的则是诸人初聚邺下之情形。建安四年,阮瑀入魏;五年,刘桢、应玚归魏;建安九年,陈琳归曹操;十二年,徐幹入魏;十三年,王粲入魏。建安九年,邺定,曹操家属迁居邺城。[7]据此,拟诗的时间范围应该是建安十三年王粲入魏,六子俱在,至十七年阮瑀卒这段时间。因此拟诗总序中言“建安末”,与史事不合。何焯以为是讹误,“末”应为“中”。但曹丕于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立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卒,如果改成“中”,拟曹植诗中所称“副君”则又不能与史实相合。另外,建安末曹丕苦于太子之争,“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8],其间心情与拟诗中所写之欢娱实不相合,更不用说“朝游夕宴”了。孙明君先生从邺下文士与曹氏集团的实际关系角度指出:“拟诗与史实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在拟诗中诸子放弃了各自的理想,安于享乐的生活。同时,诗人也忽略了曹氏父子与邺下文士之间的矛盾和摩擦。”[9]
这些错乖的史实让人以为是灵运疏忽所致,但除上文言拟诗中有建安集会赋诗情景的影子外,灵运拟王、陈、徐、刘、应、阮诗则多有史实依据。就小序看,小序写作思路有两种:一是由作家个性而及其创作,如徐幹、刘桢、曹植。一是由作家经历而及其创作特色,如王粲、应玚、陈琳、阮瑀。就作家身世经历、个性特征、创作特色言,多有史书或作家的相关作品作依据。而从拟作思路看,拟王、陈、徐、刘、应等诗的思路大致相同,即由经历遭遇而及宴会之欢娱与感恩之情。现存建安诗作,惟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与拟诗结构最为一致,其他诗人的公宴诗,或侍宴诗,则多欢饮之辞,并不涉及身世经历,灵运拟其他诗人之诗思或取自应诗。
综上而言,灵运对建安历史与作家作品相当熟悉,拟作基本上依据史实而写。那么,如何理解拟诗中史实的错乖与相合呢?唯一的解释是,这可能正是灵运的精心结构。
二、拟曹植诗对整组拟诗之解构
拟曹植诗作为集体赋诗的总结者,置于组诗最后,其小序与拟六子诗小序在语句结构以及用语来源上大有不同。拟六子诗小序前后句间基本上是因果关系,而拟曹植诗小序前后句则是转折关系;其他拟诗小序多依据史书或曹丕的相关评论,但拟曹植诗小序则别无依傍,即便史书所谓“十一年中汲汲无欢”,但其实为失志之苦闷,而非“忧生”之悲情,此小序完全属于灵运自己领悟曹植人生与创作的深切评论。
另外,小序中“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美遨游”与“忧生之嗟”的对立转折中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张力。拟六子诗基本上由辛酸的身世而及宴会的欢娱,整体基调是欢乐的,但到了拟曹植诗,则陡然沉入痛苦。有论者以为,限于宴会主题,拟诗中没有涉及曹植黄初之后的生活,即认为拟曹植诗所反映的是曹植早期游乐无忧的生活,这实是误解。
从整组拟诗看,除拟曹丕诗结尾“何言相遇易,此欢信可珍”外,拟七子诗,凡小序从经历入手的,其拟诗均以赞美、欢乐结尾。如拟王粲诗言“既作长夜饮,岂顾乘日养”;拟陈琳诗言“且尽一日娱,莫知古来惑”等。而凡小序从个性入手的,其拟诗均以表露心志结尾。如拟徐幹诗言“中饮顾昔心,怅焉若有失”;拟刘桢诗言“唯羡肃肃翰,缤纷戾高冥”;拟曹植诗言“中山不知醉,饮德方觉饱。愿以黄发期,养生念将老”。由宴会之乐而陡转为忧生之念。如此看来,从经历入手的小序突出的是过去的悲伤;而从个性入手的,则突出的是当下的心情。组诗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整体都是欢乐的,在拟徐幹、刘桢诗里即已流露出与宴会之极欢气氛不相协调的情绪,不过这种情绪恰恰又紧扣小序,突出了所拟诗人的个性特征,因此,读者很容易忽略它。而至曹植,其小序结构、用语来源与其前小序不同,而其独特的开篇与结尾方式,让人不禁要问,既然如此欢娱无忧,为什么突然以“饮德”、“养生念将老”结尾?所以此结尾即是“忧生”之表现,那么“不及世事,但美遨游”,是不能“及世事”,是只能以“遨游”来发泄心中的悲忧,也只能以“遨游”来全生保身。拟曹植诗与小序实际上隐藏着极深的不可解决的矛盾冲突与忧伤。可以说,在整组拟诗中,唯拟曹植诗与小序内容最为对应,拟诗思路结构紧扣小序,由“美遨游”而转至“忧生”之思。
拟曹植诗置于组诗最后,其独特的小序与拟诗中的情绪暗示整组诗的情感落脚点正在此首,灵运以拟曹植诗解构了他整篇所虚拟的主宾之欢。因此可以理解,为何拟六子诗小序特别强调其经历的痛苦与作品的感伤情感特征了。也即是说,整组诗的情绪抒发点在“七子”,而“七子”的重点则在曹植。拟诗在模拟、虚拟之中,又采用代言方式,而当“七子”自说自话时,他们就逐渐逸出了曹丕所定下的欢乐无忧的调子。谢灵运将曹丕脑中关于邺下之游的完美记忆“扩大为一个时代一个精英群体的集体性的完美记忆”[9]。其实,从拟曹植诗反观整组诗,可发现拟诗并没有忽略建安邺下的志士失意与主宾矛盾,只是它隐含在拟诗的虚拟形式之下。诚如吴淇所言:“此诗于陈、于阮,皆略其出身,而目以书记,似乎重之,而实微之也。”[10](P385)而整组诗中史实的相乖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即灵运心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盛宴。作为曹丕最温馨的回忆,怎么可能记错时间?此皆灵运精心之营构。他依据相关史料、作家作品等真实性资料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沉湎其中,而又无比清醒。他向往无猜无忌的主宾关系,但他清醒地知道,即使让人艳羡的邺下之游也依然隐含着漂泊无奈和忧生的叹息。
三、拟诗对曹植文学之接受
(一)化用曹植作品语句
如拟王粲诗“伊洛既燎烟,函崤没无像”,李善注前句时引用曹植《送应氏诗》“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焚烧”。拟陈琳诗“爱客不告疲”,浓缩了曹植“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公宴》)句。拟徐幹诗“华屋非蓬居,时髦岂余匹”,化用了曹植“生存华屋下”(《箜篌引》)句,以及曹植“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赠徐幹》)句。拟阮瑀诗“金羁相驰逐,联翩何穷已”则直接化自曹植的“白马饰金羁,联翩西北驰”(《白马篇》)句。另外,拟曹丕诗:“天地中横溃,家王拯生民。区宇既涤荡,群英必来臻。”李善注曰:“陈思《行女哀辞》:‘家王征蜀汉’”(现存曹植《行女哀辞》中未见此句),似暗指拟曹丕句与曹植诗句的关系。在现存曹丕诗文集中,不见曹丕对曹操拯民于祸乱之赞美,即连最可能称誉曹操的《登台赋》、《短歌行》中亦无此等内容。相反,在现存曹植不同文体的创作中,此类内容则多处可见。如:“皇佐扬天威,四海无交兵。权家虽爱胜,全国为令名。”(《赠丁仪王粲》)其他如《责躬诗》、《登台赋》、《娱宾赋》、《宝刀赋》、《与杨德祖书》、《魏德论》、《王仲宣诔》、《武王诔》等作品对曹操均有泼墨之赞。因此,此拟曹丕诗中对曹操歌功颂德之句似化自曹植作品。
(二)模仿曹植作品开篇
1.比兴发端。“兴”,源自上古时期的乐舞,《论语·泰伯》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说。自“兴”与诗教紧密关联,便成了诗歌作用于人的基本方式。[11]拟曹丕诗开篇言:“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照灼烂霄汉,遥裔起长津。”明代胡应麟把它与曹植“高台多悲风”“明月照高楼”句相提并论,作为千古发端之妙者。黄节引陈胤倩曰:“前半不类建安。澄觞以下,极意模仿。”[12]“前半不类建安”,是因此四句句式结构非常别致,两两相对,而又一、四句相应,二、三句紧相承接,此句式见于西晋诗作,而不见于建安作品。又吴淇言:“此诗后人有讥其与文帝不相似者。”[10](P383)主要指拟诗中文帝对诸子的倾心之言与文帝性情实不相符。但此诗与文帝不相似者,更重要的是气象不类。此种气象尤其表现在开篇四句诗。文帝诗便娟清丽,即使有所谓壮气,亦缺少波澜壮阔之气象。此诗开篇以比兴手法,形象地铺写出曹操光亮天下的功德、胸怀与感召之力。这种开篇,把时代特征与个人命运、情志等糅合一起,极富气势。此具足骨气之起调,正源自曹植。
2.辟空开篇。拟阮瑀诗言:“河州多沙尘,风悲黄云起。金羁相驰逐,联翩何穷已!庆云惠优渥,微薄攀多士。念昔渤海时,南皮戏清沚。今复河曲游,鸣笳泛兰汜。”其写作思路仿自曹植《白马篇》。按照建安诗作写法,一般开篇先点出事件,即“今复河曲游”事应在开端,但拟诗则辟空而来,上来即是一幅特写般的雄阔画面,风悲云起,沙扬尘飞,佩戴金羁的群马相互驰逐飞奔,一股英雄之气激荡其中,让人不禁疑问,此何人哉?然后由昔而及今,点出曹丕与诸人的河曲之游,至此方知开篇风起云涌、英雄驰逐的镜头正是曹丕与诸子的豪放之游,此与《白马篇》开篇即给人以白马金羁健捷奔驰的视觉冲击,然后引出人物身份介绍的思路结构非常一致。此亦可谓倒叙结构,它以特写似的笔法直接呈现画面或情感,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曹植《野田黄雀行》、《美女篇》、《名都篇》等都是如此。
(三)拟曹植诗的深婉风格
“朝游登凤阁,日暮集华沼。倾柯引弱枝,攀条摘蕙草。……平衢修且直,白杨信袅袅。”拟句融骚入诗,看似闲淡的游玩背后则颇具象征意味,主人公高洁自恃,又不免清寂孤独,此写法与曹植“南国有佳人”(《杂诗六首》其一)一诗对楚辞的化用颇为相像。下由独游之乐转为宴集之娱,而以“饮德”“养生”作结,这一愿思似与前文脱节,致使不少人以为此感叹与曹植个性不符,但它确实显示出灵运对曹植及其诗作技巧的深刻理解。首先,“愿以黄发期”化自曹作“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赠白马王彪》)句,而“养生念将老”之养生念头在曹植中后期诸多作品中亦有充分体现。其次,这种结尾的突然转折正是曹植作品的突出特点。如黄节言:“余观子建诗,其结语独高,往往出人意表。大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奇胜。盖其诗多用进一步写法,层出不穷,愈转愈高,至结意遂登峰造极矣。”[13](P4)再者,最后的突转使得前面的遨游之愉成为一种发泄苦闷的无奈之举,作品中具有隐、显两种情绪,从而使作品呈现委婉幽深的风格特征,深得曹植后期作品之神韵。
四、拟诗所隐知音之感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言:“康乐隐情,尽在诸序之中。……诸子中,唯仲宣才高而望重,故康乐首取以自况。”[10](P383)“康乐隐情,尽在诸序之中”,是有道理的,但认为康乐以王粲自比,则不免牵强。
以整组拟诗看,拟曹植诗为组诗之落脚点,它隐含着灵运对曹植的重视与深刻理解。拟诗小序言“公子但美遨游”,但现存曹植诗赋中,此类内容并不为多,史书中亦无相关记载。拟诗所写曹植遨游之内容,在曹植诗赋中亦无相应篇目。但《谢灵运传》中则多次直言灵运之游,如“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遨游”,“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出郭游行”,“灵运以疾东归,而游娱宴集,以夜继昼”,“灵运既东还……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等。[14](P1753)且在灵运作品中,多有化用楚辞意象语句,其表述与拟曹植诗中写法极为相像。如《东山望海》言“采蕙遵大薄,搴若履长洲”;《初去郡》言“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从斤竹涧越岭溪》言“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等等。这些表明,拟诗所写曹植之遨游,更多乃灵运自身经历之折射。
灵运之游不仅因其性爱丘山,更因失意之痛,非山水何以解忧。白居易指出:“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岂惟玩景物,亦欲摅心素。往往即事中,未能忘兴谕。”[15](卷七)此可谓对“公子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的自我感叹之诠释。赵昌平言:“拟魏太子序所论实启《文心雕龙》先声,可见其于建安精神领会之深。尤其是论曹植一条,可视作谢客遨游以抒幽愤的夫子自道。”[16]亦为中肯之见。
因此,灵运以自比者是曹植而非王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灵运与曹植有更相近的特征。如两人幼即敏悟,博览群书;两人都任性高傲,有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但更重要者是两人都自恃其才而终不得意。灵运曾言:“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继之?”[17](卷六十八)在高推子建的同时,又何尝没有自得之意?且依其言,王粲只在“古今同用一斗”之范围,以其心高气傲,焉能以王粲自比?又《谢灵运传》载:“灵运尝自始宁至会稽造方明,过视惠连,大相知赏。时(何)长瑀教惠连读书,亦在郡内,灵运又以为绝伦,谓方明曰:‘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何长瑀当今仲宣,而饴以下客之食。’”[14](1775)灵运以长瑀为“当今仲宣”,批评方明不能礼贤,又岂会以王粲自比?“奇才博敏,安有继之?”这不仅是对子建之高赞,亦是灵运之自恃。灵运曾讥刺太守孟凯:“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14](P1775 -1776)可见他对自己天赋才华之自信。史载其“自谓才能宜参政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14](P1753),其激愤之情即根源于对自我才能之自负。在这些方面,灵运与曹植颇为相像。
而对自我才能的自信、自负与时代种种因素相作用,最终酿成二人一生的悲剧。以曹植言,因血缘而来的强烈的责任感与强烈的功名愿望同其对自身才能的自信相结合,使他无时无刻不关注朝政,希望为国尽力,其生命之支柱在此,其刻骨之痛苦亦源于此。但太子之争的阴影使他一直被压制在为国治政的外缘,抑郁而终。而谢灵运,身处士族被压制削弱的时代,先祖的荣耀一去不返,自己在政治上屡遭重大挫折,一生在仕与隐的矛盾中挣扎,直至以谋反的罪名被杀头身亡。“植常自怨愤,抱利器而无所施”(《曹植传》),灵运“自谓才能宜参政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愤”字可谓是贯穿二人生命的一贯情感。也许正因为这些相似,才有灵运对曹植作品“忧生之嗟”情感内涵的挖掘,而子建也在身后几百年才得到同情与理解。
五、拟诗的接受史意义
在拟诗中,曹丕是组织者,其他七人,正是后世所谓的“邺中七子”,如皎然《诗式》言“邺中七子,陈王最高”[18](P110)。但在灵运之前,曹丕《论文》中所提建安“七子”并无曹植。可以说,此组拟诗首次明确纳曹植于“七子”之列。组诗以拟曹植诗作结,不仅合于曹植王者之身份,而且突出其凌驾诸子之上的文学地位,此于后世对邺下作者文学成就高低之评价有着直接影响,若钟嵘之谓曹植为“建安之杰”,与灵运之诗未尝没有联系。
以上从“七子”之概念及其成就高低着眼,说明灵运拟诗之接受史意义,下从曹植为人与为文两个维度,论述灵运拟曹植诗之影响。魏晋南北朝,除曹魏时期,曹植党如杨修、丁廙等盛称其品性外,其他人对之则多批评之辞。《三国志》中《陈思王植》、《王粲》、《崔琰》、《毛》、《贾诩》、《邢颙》等传记里的相关记载,均表明建安时曹植之任性自我、饮酒不节、恃才傲物、欠缺自律。两晋时期虽乏对曹植为人之评论,但直到郦道元《水经注》尚言“曹植尝行御街,犯门禁,以此见薄”[19](P264),《颜氏家训》亦言“曹植悖慢犯法”[20](P237),可见曹植任性轻薄已成后世公认之事实。另一方面,东晋葛洪在《抱朴子·论仙》中把曹植改造成一亲道人士,宋初《世说新语》中曹植亦只是一遭受迫害的才王形象,与隋唐以后对曹植及其诗文的道德、精神内涵的探讨相比,曹魏两晋时期对曹植及其诗文的理解还相当狭隘。
而对曹植为人内涵的理解影响着对曹植作品内容与情感之理解,亦影响着曹植文学史地位之确立。曹魏晋初,对曹植作品,多赞其文采富艳。如吴质言“是何文采之巨丽”[21](P309);陈寿言“陈思文才富艳”;鱼豢言“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8](P431)等;两晋始稍涉对曹植作品情志之评价。如李充曰:“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22](P560)何谓“远大”?“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宜以远大为本,陆机议晋断,亦名其美矣。”可见“远大”,意指着眼大局,考虑长远,立心纯正,为君为国而不局于个人私利。何谓“成文”?“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美矣。”[22](P560)可见“成文”,即文章要符合文体要求。李充从文体角度指出曹植“表”中之精神,但相对客观,似不掺杂对曹作个体情感之评论。苏彦《女贞颂序》言:“昔东阿王作《杨柳颂》,辞义慷慨,旨在其中。余今为女贞颂,虽事异于往作,盖亦以厉冶容之风也。”[22](P1493)“冶容”指艳丽的打扮,所谓“厉冶容”,或是对当时浮华奢侈之风进行讽刺批判。曹植《杨柳颂》原文今不存。《柳颂序》言:“遂因辞势,以讥当世之士。”可见苏彦主要着眼于曹植文中借物喻人之讽刺手法,而其关于曹文“辞义慷慨”之论,则较早注意到曹植文的“慷慨”特质,似为南北朝阐释曹植诗文情感特质之发端。
总体言之,终曹魏、两晋,曹植及其作品中的个体精神与情感内涵基本上被忽略了,直到谢灵运拟曹植诗,方以拟诗形式挖掘出曹植的忧生情绪,暗示出曹植之“美遨游”只是一种保身全命的无奈选择,表面的潇洒风流之后是失志之痛和不可把握自我命运的深沉苦闷。在曹植接受史上,谢灵运第一次以文学为媒介,深入走进了曹植的灵魂世界,从而改变了先前文史论中曹植的形象。他对曹植人生与作品超越前代之理解,实基于相似命运之联系及其对曹植高才之认同与向往。灵运《拟邺中集诗》,尤其是拟曹植诗,对谢庄《月赋》、江淹拟陈思王诗有着直接影响;而钟嵘“情兼雅怨”之论,更是对灵运拟曹植诗及小序内涵的进一步揭示与概括。正是谢灵运对曹植精神世界的首次揭示,揭开了曹植接受史上重塑曹植形象的序幕,也开启了解读曹作的新方向,之后,谢庄、江淹、钟嵘、萧绎、王通等从不同角度挖掘了曹植及其作品的深沉内蕴,为后代对曹植及其作品进行道德阐释奠定了基础。曹植的伟大人格经由一代代读者逐步发现、挖掘出来,他最终与陶渊明、杜甫等成为塑造民族心灵的人物,追溯其源,谢灵运拟曹诗可谓影响深远。
[1](宋)刘克庄.后村诗话[A].宋诗话全编(第八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江醴陵集题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3]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5]魏宏灿.曹丕集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6]俞绍初,辑较.建安七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7]张可礼.三曹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3.
[8](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
[9]孙明君.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中的邺下之游[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1).
[10](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M].扬州:广陵书社,2009.
[11]李乐.《论语》诗“兴”之境的现象学解读[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12]黄节.谢康乐诗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3]萧涤非.读诗三札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14](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16]赵昌平.谢灵运与山水诗起源[J].中国社会科学,1990,(4).
[17](宋)无名氏.释常谈[A].说郛[M].(明)陶宗仪,纂.北京:中国书店,1986.
[18](唐)皎然.诗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20]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1](清)严可钧.全三国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2](清)严可钧.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