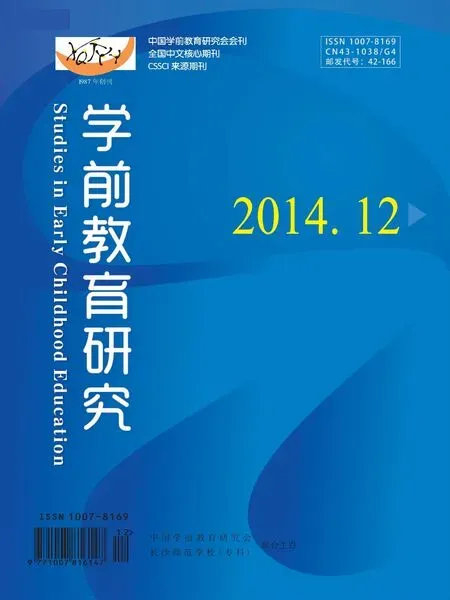中瑞两国婴幼儿家庭政策比较*
郑 杨
(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哈尔滨 150025)
一般而言,家庭政策主要指政府通过承担一定的家庭功能以达到稳定家庭和社会的目的而制定的社会政策。瑞典由于发展工业化不久,便出现了人口危机,为了确保劳动力,其政府没有将婴幼儿的抚育责任全部归于家庭,而是通过社会保险的方式,让社会共同承担抚育成本。尽管在建国初期,中国政府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育儿责任,但在改革开放后,不断强调家庭的责任,以此减轻国家负担,由此带来突出的隔代养育问题。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政府需要未雨绸缪,向瑞典这样的先行国家学习如何在国家责任与家庭责任之间取得平衡,以保证社会和家庭稳定发展。
一、瑞典的家庭政策
(一)亲职假与父母津贴
由于瑞典的经济腾飞和人口老龄化同步进行,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瑞典政府一直将女性作为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并沿着以下两条思路对家庭政策进行了调整:一是将女性的一部分家庭责任转移给政府,政府利用税收建立收费低廉、服务优质的托儿所,从而保障并积极鼓励已婚女性继续工作;一是让男性分担一部分女性承担的家庭责任。[1]
瑞典于1974年开始将母亲单独享受的产假,修改为父母双方可以轮流使用的带薪亲职假。按照父母保险计划规定,产妇分娩前可以享有180—270天的生育津贴,孕妇在产前一个月即可开始休假,并领取产假补贴。在父母轮流休假期间,可以得到的父母津贴由请假而损失的工资进行折算,为该从业者总收入的90%。此外,这一政策还保障让休假的父母重回原工作岗位或类似的岗位。
从2005年开始,亲职假延长至480天,并规定亲职假可以在孩子出生或被领养当日起至孩子满8岁期间的任何时候申请得到这480天中的390天。[2]同时为了提高男性使用亲职假的比率,让父母双方平均分担抚育婴幼儿,1995年规定有30天的亲职假是父母双方不得转让的,2002年又新增加了“父亲和母亲必须各申请60天,不得转让,其余自行协商解决”的规定。其中390天的亲职假的津贴额度为该从业者总收入的80%,余下的90天为每人每天60克郎。亲职假的出台与完善,让“瑞典家庭形成了夫妻双方充分利用产假,轮流使用产假的育儿战略”。[3]在1974年亲职假以及补助金制度实施之初,“男性申请人数仅占总人数的4%,之后随着家庭政策的完善,1985年、1995年、2003年的男性申请人数分别上升到23%、28%和43%”。[4]另外,享受亲职假津贴不受工资额度和工作年限的限制,特别是无收入的父母也可以享受父母津贴,即390天内的津贴为每人每天180克朗,其余的90天为固定的60克朗/天。父母保险制度作为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其财政来源为雇主、自雇者支付的亲职保险费以及国家基金。
(二)多样且价廉质优的托幼机构
瑞典大致有四种托幼服务:日间照顾中心(day care center)、幼儿园(kindergarten)、开放的学前教育(open pre-shool)、家庭托儿所(family day care),其中被广泛利用的是日间照顾中心。据2008年的数据统计,有50%的1岁儿童、90%的2岁以上儿童都在接受日间照顾中心的服务。而家庭需要缴纳的费用很少,托幼机构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具体而言,地方政府会为每个儿童提供一笔1—6岁的儿童基金,通常是“第一个孩子每月补助1260克朗,第二个孩子每月840克朗,第三个孩子每月420克朗,这些补助直接交给托儿所,而非家庭。瑞典政府规定托育服务机构最高收费标准为每个儿童每月不能超过1260克朗”。[5]托儿费用包括两部分:“一个是人人需要交的伙食费,另一个是管理费,但是低收入或多子女家庭可以少交或免交”。[6]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瑞典家庭支出的托儿费大约仅占其工资收入的10%,因此不会成为家庭的经济负担。瑞典政府提供的廉价而质优的日托服务,让瑞典女性能够把工作和抚育孩子完美地结合起来。
二、中国的家庭政策
(一)不断增加的产假与家庭政策的非普惠性
为保证女性平等就业,自1949年建国之初我国便确立了生育保险,但主要覆盖对象是城镇女职工,而不是全体女性。例如,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关于生育保险的规定,其保障对象为“女工人与女职员”。她们享受的产假为56天(包括产前产后),产假期间工资照发。国务院于1988年颁布《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将产假由56天增加至90天(其中产前15天)。2011年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草案)》,将女职工享受的产假由90天延长至98天。此外,自1979年我国颁布计划生育政策后,凡是晚婚晚育者,女方除了享有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再额外增加60天,并给予男方护理假7天。与瑞典不同,在我国产假只能连续使用,护理假也只能在女方产假期间使用,且不适用于无业人员。不过,在补助额度上中国优于瑞典,上述假期都视为出勤,工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另外,中国生育保险的财政来源与瑞典不同。新中国初期,我国生育保险实行的是国家统筹模式,由企业缴费和支付,中华全国总工会管理,个人不负担任何费用。市场经济时期,我国各地开始尝试社会统筹、由夫妇双方所在单位共同分担的改革,但具体试行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减轻国家压力的目的,反而增生了对女性的“生育歧视”,这是1990年代以后女性在就业时面临的重要社会阻碍之一。[7]
(二)低廉方便的托幼机构逐渐消失
在“家国同构”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托幼事业被提到全党事业的高度来看待,因此从1950年代开始兴办了各式各样的托儿所幼儿园,对我国城镇女性就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时的托幼机构不仅收费低廉,在地点、时间安排等方面都比较注意适应家长的需要,例如孩子入托年龄与女职工的产假时间相衔接,孩子出生56天后便可入托;托幼机构一般就近设立,既保障了母亲哺乳时间,又方便了家长接送。然而,自1992年国企改革后,许多企业就停止或减少对托幼机构的投入。集体开办的幼儿园,也由于街道和社队集体经济的瓦解,大多数转而依靠收费来维持。政府办幼儿园则主要只针对政府机关公务员子女和教育部门教职工子女,难以满足社会需要。更为甚者,目前我国政府没有为3岁以下儿童提供任何公共服务。[8]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目前3岁以下婴幼儿都是由家庭来承担全部照顾之责,也就必然会“迫使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女性(不得不)选择从正式就业转入非正式就业”,[9]即很多女性不得不做全职妈妈,以此来平衡既没有亲属网络的帮助,又没有足够的能力购买看护劳动的现实。上海市一项针对0—3岁婴幼儿扶养方式的调查显示,与祖辈一起生活的婴幼儿占73%,如果再加上祖辈参与抚育婴幼儿的话,其比率高达84.6%。对无锡市民育儿状况的调查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10]
三、对中国家庭政策未来发展的建议
从上述介绍可知,与瑞典育儿是父母的共同之责,也是家庭和国家共同之责相比,当下我国家庭能够获得的公共育儿资源是相当“贫瘠”的,由此催生了庞大的婴幼儿服务市场,但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市场资源又过于昂贵而无力购买,因此目前对于中国普通家庭来说,最有效、最便捷、最经济实惠的育儿援助便是以祖辈为核心力量的亲属网。
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取之不竭的育儿资源。我国目前正处于孙辈数量激减时期,让祖辈有了可以提供抚育帮助的可能性,但显然这一“人口红利”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当“人口红利”消失时,也就是能够提供抚育帮助的人群小于寻求抚育帮助的人群时,这一资源必然会逐渐减少,所以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地思考,“人口红利”消失后我国将如何提供公共的育儿资源,并为此做出相应的政策设计。这是我国今后一个没法回避的问题,及早学习瑞典的先进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5]李慧英.瑞典:公共政策与女性就业[EB/OL].http://www.women.org.cn/allnews/1003/458.html,2005-6-9.
[2][4]堂文慧,杨佳羚.瑞典育婴休假制度之研究:共同照顾的价值[J].台湾政大劳动学报,2006,(19):88.
[3]船桥惠子.育儿战略和家庭政策中的社会性别[J].家族社会学研究,2005,(2).
[6]何玲.瑞典儿童福利模式及发展趋势研议[J].中国青年研究,2009,(2).
[7]陈琳.生育保险、女性就业与儿童照料——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分析[J].经济学家,2011,(7).
[8]胡湛,彭希哲.家庭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J].人口研究,2012,(2).
[9]方英.市场转型与中国城市性别秩序分化[J].江西社会科学,2008,(1).
[10]落合惠美子.現代中国都市家族の社会的ネットワーク―無錫市の事例から[A].见首藤明和,落合恵美子,小林一穂編著.分岐する現代中国家族:個人と家族の再編成[C].日本:明石書房,2008:6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