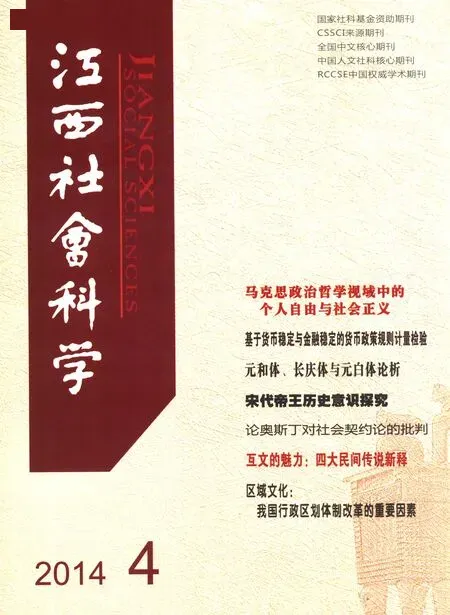论1930年《骆驼草》周刊的文学观念
■焦敬华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处于进入历史的转型期。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奉系入关,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幻使北京丧失了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1926年至1928年间,军阀对文化界进行大肆围剿,有广泛影响力的《京报副刊》、《晨报副刊》等被查封,《语丝》、《现代评论》等被迫迁往上海,知识精英大规模南下当时的商业中心上海,北京丧失其中国文化中心的地位。《骆驼草》周刊正是在北京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荒漠化巨变中得以问世,并成为1930年北京唯一一份综合性纯文艺期刊。《骆驼草》是留守北京的周作人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的一份富于自由主义气息的刊物。他们摒弃《语丝》时期的进击精神,退守书斋过着隐逸式生活,其草木虫鱼式的趣味闲谈蕴含着“自我性灵的自由抒写”的文学观念。
一、自我性灵的自由抒写
大革命失败后,理想失落的虚幻感和欲有所为却不能的郁愤,使周作人体内的“隐士鬼”在与其体内的“叛徒鬼”的较量中占上风。于是他从时代激流中退出,隐居“苦雨斋”,“胡乱”作文,玄思冥想,在文学上寻求安慰,于动荡的1928年提出“闭户读书论”,1929年则以整理旧作为主。但随着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与1930年“左联”的成立,文学彻底向左转,且急速发展为时代的主导文化。与此同时,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创作也带有极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在与左、右翼文化的对抗中,留守北京的周作人等苦雨斋文人于1930年5月12日创办了《骆驼草》周刊。
1924年,正在负责编辑《语丝》的周作人与好友张定璜、徐祖正拟另辟文学阵地《骆驼》,追求迥异于《语丝》风格的纯文艺创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只在1926年6月出版了一期。周作人曾在《语丝》上著文《代表骆驼》声明:“骆驼社里一共只有三个人,即张定璜、徐祖正、周作人是也。此外帮助我们的朋友也有好些,不过那不算是驼员之一,即如江绍原君虽然通晓‘骆驼文’,却也不是其中一员。《骆驼》出发时还在奉直再战之先,等走到时却已在奉直联军入京之后了,未免有沧桑之感罢。现在他回来了,只是这个是我所愿意报告给诸位听的。”[1]《骆驼》虽仅存一期,但追根溯源仍可看作是《骆驼草》的前身。
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1930年上海发行《开明》、《北新》、《新月》等25种文学期刊,但同时期的北京只有《未名》、《戏剧与文艺》、《骆驼草》在出版发行。而《未名》在《骆驼草》创刊前的4月30日停刊,《戏剧与文艺》只是一份纯粹的提倡戏剧的刊物,只有以苦雨斋为中心的一批自由主义文人创办的《骆驼草》周刊称得上是综合性文艺期刊。”[2]《骆驼草》的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最初由废名、冯至主持,9月12日冯至去德国留学后由废名独自主持,但就文学创作和文化影响力而言,周作人是《骆驼草》实质意义上的精神领袖。该刊主要的撰稿人有周作人、废名、俞平伯、徐祖正、冯至、徐玉诺等。刊名“骆驼草”由废名拟定:“骆驼在沙漠上行走,任重道远,有些人的工作也像骆驼那样辛苦。我们力量薄弱,不能当‘骆驼’,只能充作沙漠地区生长的骆驼草,给过路的骆驼提供一点饲料。”[3](P31)
1930年《骆驼草》时期,已届中年的周作人对自我与社会都有了一种的新的认识与妙悟。他在《知堂说》一文中写道:“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4](P24)此文充分彰显了他的思想转向,强调他不懂的东西再也不说了,不该说的也不再说了。周作人称自己是“爱智者”,他自信参透了人世沧桑与日夜轮回的物像世界,站在自我的思想至高点来俯视纷扰的世俗红尘,在愚昧且盲从的芸芸众生面前表现他理性的高傲。归隐书斋,闭户读书,奉“苟全性命于乱世”为安身立命之本,坚持创作草木虫鱼内容式的小品美文写作,以及张扬文学趣味思想,这成为周作人的生存理念与文学主张。
周作人在《骆驼草》时期的作品主要有“专斋随笔”系列(《反书石刻》、《草木虫鱼小引》、《古希腊拟曲》、《冰雪小品选·序》、《杨柳风》、《文字的魔力》、《骂人论》和《重刊〈霓裳续谱〉序》)以及散文《水里的东西》、《西班牙的古城》、《村里的戏班子》等。周作人在《草木虫鱼小引》中指出:“我个人却的确是相信文学无用论的。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即是禅宗与密宗,假如容我借用佛教的两个名称。文学无用,而这左右两位是有用有能力的。文学的要素是诚与达,然而诚有障害,达不容易。禅的文学做不出,咒的文学不想做……许多事不想说,或是不好说,现在便姑且择定了草木虫鱼。第一,这是我所喜欢,第二,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5](P3)周作人在《村里的戏班子》中,写在年里年外的纷乱忙碌与大家真诚的起哄中,戏班子热热闹闹地卖力表演,年味陡增。有赤着背、挽着绍纠头的阿九拿了象鼻刀在台上摆出好多架势,把眼睛轮来轮去;有一穿白袱的撅着一枝两头枪与阿九对打;还有至今让人回味的儿童俗歌:台上辈云班,台下都走教。可是慢慢地,戏班子不再有了,年味越来越淡了,戏趣也越来越散了。《水里的东西》不写我们常看得见的菱角、鱼虾,而是一种子虚乌有的河水鬼与日本的河童,他认为中国的人类学与民俗学还不发达,也不知将来会如何,他想做个先锋,来引导大家对于这些方面的兴趣。可见他的趣味闲谈中蕴含了自我个性和人生隐逸倾向,不仅文学创作,他的读书、批评,甚至学术研究都是以智性趣味为中心。周作人热衷于创作趣味之文,寄望文中“有叛徒活着”成为一种虚幻之像,在精炼逸致之外显露着空虚与颓废。周作人对北京茶食的赞语“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恰可以来阐释他的趣味之文的实质。
从《骆驼草》周刊第一期中《身后名》到第二十五期的《怕》,俞平伯共有九篇文章刊登于《骆驼草》周刊上。《身后名》中,俞平伯开篇就指出“恐怕再没有比身后之名渺茫的了,而我以为毕竟也有点儿实在的”。“姓屈的做了老牌的落水鬼,两千年以上,而我们的陆侃如先生还在讲屈原。曹雪芹喝小米粥喝不饱,二百年后却被胡适之先生给翻腾出来了。……阮籍见了人老翻白眼,刘伶更加妙,简直光屁股,倒反责备人家为什么走进他的裤裆里去。这种怪相,我们似乎看不见;我们只看见两个放诞真率的魏晋间人。”因而,他认为“忆中的人物山河已不是整个儿的原件,只是经过非意识的渗滤,合于我们胃口的一部分”。[6]在《标语》、《又是没落》、《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坟》等文中,俞平伯汲取晚明小品文的古朴凝练,推崇素朴的趣味,再加上富有哲理的分析,情思交融,夹叙夹议,没有刻意的雕饰,自有一种朴实自然之感。俞平伯虽无周作人广博之学问与深湛之思想,但他曾研习哲学、沉迷释典,虽以不善表现之故有深入深出之讥,而说话时自然含有一种深度,一种明末王思任、张岱等名士的风范。他的《冰雪小品跋》与周作人的《冰雪小品选·序》一起在当时的文坛上力争推崇小品文的正宗地位,也借此诠释了他们的趣味小品文观:“小品文的不幸,无异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不幸,这似乎有点发夸大狂,且大有争夺正统的嫌疑,然而没有故意回避的必要。因为事实总是如此的:把表现自我的作家压下去,使它们成为旁岔伏流,同时却把谨遵功令之文抬起来。”[7]同时,周作人还说:“言志派是无庸置疑的正统,小品文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8]小品文是“言志的散文”、“文艺的少子”、“个人的文学之尖端”。借助《骆驼草》周刊,他们共同建构了“知识与趣味双重编制”的小品文理论观,并最终完成小品文美学境界的定型。
废名的两部著名抒情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均在《骆驼草》周刊上连载,就其艺术风格而言,可谓是他的创作高峰、小说绝笔了。废名从1925年开始写作《桥》,延续十余载方才完成,是他最为精雕细刻之作,由此人们说废名“十年造桥”。《桥》以未受西方文明、现代文明浸染的宗法制乡村为背景,在理想的世界中过滤掉凡尘俚俗,描绘可爱、天真善良的乡村儿女们,用散文诗的形式展现他们纯粹、真性情的生活形态,构筑了一个诗意缤纷的小说世界。他平静而有意地淡化琴子的孤儿身份、长工三哑幼时的乞讨生活,刻意营造一种自然和谐、宁静超脱、绝无世俗冲突的达观化人生境界。《莫须有先生传》的写作开始于1930年《骆驼草》创刊之时,该刊的开办也是废名写作此部长篇小说的最直接的缘由。《莫须有先生传》没有《桥》的空灵色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神秘面纱,有着废名借他的化身莫须有先生来抒发对生命玄妙不可知的奇思异想;小说也不似《桥》那样有着固有的情节逻辑性,而是执著于写作中的自由、真实的内心情感,废名试图在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细小夹缝中追寻精神个体的自由发展。这部小说也预示着废名在《骆驼草》终刊后转入宗教一途。喜欢注重事实与生活,不求精致的结构,只求写得有趣味的废名是“知识与趣味的双重统制”更具体的阐述者,只不过废名在周作人等的草木虫鱼之外又多了些世情风俗。
《骆驼草》同人的自由主义文艺观是由徐祖正著文加以理论建构阐释的。《一个作家的文学理论》、《理性化与文学运动》(上、中、下)、《文学上的主张与理论》、《文学运动与政治的相关性》、《对话与独语》、《文艺论战》等理论文章集中阐述了《骆驼草》同人以个体的情感抒发为本位的理论体系。“文学还是以情感为主成分而成就的。各国新兴文学的开始大都直接于浪漫运动的。浪漫运动乃是唯理论主义之反动运动。”[9]“文艺界思想界里只有个人。为要摆脱政治社会的束缚,维护个人主观的尊严,因此才有文艺思想的园地。……团体国家须要建筑在有健强的判断,有明敏的思索,有丰厚的情感的个体上的。只有文艺可以养成这种个体。”[10](P1)徐祖正发表在《骆驼》上的《兰生弟日记》和《骆驼草》上的《某天的日记》等散文风格如一,极真率的记录,血肉精灵之作。《某天的日记》中,关于山西军退出北平,奉天军进驻北平一事,作者在电车上看到一商铺掌柜“安佚而冷静”的态度,于是自问自己对这种时局的态度或认识,作者惭愧不能直截说出自己的一个态度。“我个人关于教育界对于奉天军之重来北平未必因此有所恐惧,也说不到有什么冀希。”行文淡然从容,知识厚重,趣味亦在废名、刘半农之间,大有深意。石评梅曾著文称:“很慕敬作者那枝幽远清淡的笔致,处处都如一股幽谷中流出的清泉一样,那样含蓄,那样幽怨,那样凄凉,那样素淡。”[11]
冯至发表在《骆驼草》上的诗《酒醒》:
我酒醒自问,/生命啊/在什么地方?/过去的时光已经非我所有,/将来的岁月也要去我不停,/那些水一般流动的/留不住我的生命。//我也会相信/它散布于宇宙的万象,/它潜伏在我深深的灵府,/它随着白云飘浮,/它充实了我的梦境——//但是呀,/那都昨夜的酒/从我全身/蒸发出无边的幻想……/如今——/它们离开了/我的身体,/它们散入了/远远的虚空。
此诗笔落自然,语言灵动。徐玉诺于1929年除夕夜写作的《死的斑点》:
许多时光已经过去了吗?/在那里留着她的痕迹?/古老的墙壁上不曾有日光的白痕,/清水池沼里也没有月影的印记;/有些地方不分黑夜和白昼,/有些地方没有春秋的分际。//许多时光已经过去了吗?/在那里留着她的痕迹!/礼拜堂的钟楼上却曾上过几回发条;/人类史的新页却已翻过,/甲子的大轮也已转过几齿;/这可以证明时光吗?/不,这都是人类无聊的把戏。//许多时光已经过去了吗?/平看古今,/似乎是一样天地:/青山不改故态;/花开花落,/燕来燕去。……//许多时光已经过去了吗!呀,/在人身上留着鲜明的痕迹。/青丝偷白了/额头变枯皱了/小小暗黑的死的斑点/渐渐沾满了颈部和手背。
结构整饬、情感流淌中富有人生哲思。还有冯至的《夜半的园林》、《君的来访》、《父亲的生日》、《老屋》、《蒙古的歌》以及徐玉诺的《谁的哭声》、《云破天青的月夜和蔴花王的政论》、《海上的火灾》等诗与散文,两位诗人的性灵之作再次彰显着《骆驼草》周刊独特的抒写性灵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念。
由《骆驼》可知,《语丝》时期的《骆驼草》同人已开始追求平和冲淡的写作风格,但有鲁迅等人的牵制,未能得以充分发挥。但到了他们自著自编的《骆驼草》时就讲闲话、玩古董,尽情发挥了。尽管《骆驼草》时期也有一些相当尖锐、具有批判性的随笔散文,如周作人的《骂人论》、《八股文》等。但总体上,《骆驼草》同人此时期的随笔已不及《语丝》时期的凌厉与鲜明,也没有了当初的思想斗争锋芒和批判力度。从《骆驼草·发刊词》“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12](P1),可以看出已无《语丝》时期“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与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的战斗激情。在文坛意识形态化与商业化发展过程中,他们专注于表达个性的自由主义纯文艺创作,写作闲话古董、草木虫鱼式的性灵趣味之文。
《骆驼草》同人在知识与趣味的道路上构筑了闲适冲淡的文学境界,在与现实的抗衡中自主选择了隐逸式的生活,每个成员的创作都不尽一致地传达了这种趣味和隐逸,他们在“自我性灵的自由抒写”的总体文学观念下又显现着各自独特的文学个性,彼此相得益彰。此时期的周作人一直充当着“精神领袖”的角色,废名曾诚挚地表露“我自己的园地,是由周先生的走来”[13](P12)。《骆驼草》出刊不久就受到了部分左翼作家的严厉批评。1930年末一些文人陆续返京,《骆驼草》周刊丧失了它存在的文化环境,再加上它本身与时代的距离和主要创作成员的兴趣转向(周作人转向“文抄体”创作,废名转入宗教一途,俞平伯则专钻研古典文学,尤其是《红楼梦》研究)等诸多原因,《骆驼草》于1930年11月3日停刊,历时虽短,其创作实绩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此时期,《骆驼草》同人虽然从事于自己设计的“胜业”,但并没有完全丧失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关怀。“五四”启蒙侧重于思想文化启蒙,处于一种两面受敌的尴尬处境中,对上要抗衡庙堂的压迫,对下则要批判、教育不觉悟的民众。因而,随着革命性民族信仰的形成和民族危机的加剧,知识分子对普通民众的启蒙开始转向革命文学,旨在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过程中教育、引导民众。但自由主义者却认识到凡事都由个人来解决,提倡个人解放才是最紧要的,别人的干涉于事无补。于是,自由主义者注重内部自我觉醒的启蒙意识背离了主流革命话语,从而开辟了另一片广阔的启蒙天地。
周作人读书广杂,通晓古今且学贯中西,在纵向继承与横向移植的整合下,建构起了一个融合中西文化、以“知道你自己”为中心的知识体系,包括“个人者”、“人类及生物者”、“自然现象者”、“科学基本者”、“艺术者”等五组知识。周作人认为普及这些“常识”比空讲虚幻的主义或是理论更能触及“人”的本质,起到启蒙大众的作用。《骆驼草》时期正是他文艺常识启蒙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希腊拟曲”(《乐户》、《妒妇》、《上庙》、《塾师》)和漫谈“希腊拟曲”的《古希腊拟曲》、《希腊的古歌》均写作于此时期。在《希腊的古歌》一文中,周作人对鲍文蔚译法国比埃尔路易著作《美的性生活》中的希腊诗提出质疑,参阅荷马《伊里亚特》以及东亚病夫父子的译本《肉与死》之后,他对安得洛玛刻与赫克多耳的故事提出翻译见解,认为可以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把书名《美的性生活》改为《阿弗洛狄德》。周作人真切地认识到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源头,要汲取西方文化营养须从源头下来研习,因而他对古希腊文化的研究终其一生。他偏重于理性的、求知的古希腊文化传统,把希腊精神归结为求知、求真与求美。周作人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影响了一大批现代文学作家与翻译家,如石民翻译俄国莱蒙托夫的《孤帆》,还有F的《塞尔维亚民歌一首》、石民的《回魂》(by Charles Baudelaire)、如稷的《中国艺术之衰退的原因》、杨晦的《亨利·雷克罗夫的随笔序》等,形成了一个小的翻译圈。《骆驼草》同人的文化常识及抒发性灵的创作和对外国文化的翻译为寂寞又萧条的北平城带来了异域新鲜文化,也影响了一批与他们有着相同或相似文艺观的学生,成为当时学生团体最主要的精神食粮。他们在学院文化浓郁的北平城回避文学的政治化与商业化,在整合中西方文化过程中,希求影响国民大众的思想,对他们进行常识启蒙。
二、特殊时期自我性灵自由抒写的原因
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与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产生于17—18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发展,遍及欧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达到鼎盛,成为一个源远流长且内容庞杂的理论学说,但到20世纪初则日益衰落。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生不逢时,恰恰是在欧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式微之时。以封建伦理为内结构和宗法等级制度为外结构的中国,本无“个性”与“自由”之说,维新改良运动、民国宪法的制定与国会的活跃等自由主义政治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军阀混战时期,军阀们忙于争权夺利致使思想文化界的自由主义思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借助部分欧美留学生的大力宣传,此时期的大学、期刊和出版业也异常活跃,“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自由主义成为“五四”文化先驱们的利器之一,也成为部分知识分子的中心价值观。这场运动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极为深远,形成了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的主潮。
随着出版业的发达、职业作家的涌现和自由主义政治文化运动的兴起,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在“五四”思想启蒙和革命启蒙的大潮流中分化定型。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作家反对艺术工具论、艺术意识形态化,专注于人性的探索,坚守非功利的文学本体观和人本主义思想,坚持自主、随意的写作态度,强调艺术世界中的人生意蕴,孜孜以求审美艺术的创造,追求一种诗性人生。他们是最具有自觉意识的作家,如周作人突出强调艺术中的人生情趣,梁实秋偏重于艺术中宽泛的人性含义,朱光潜主要从审美情感来理解艺术的自足自律性等。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从一开始就与学院文化紧密相连,因为自由精神是学院文化的突出特点之一。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大学教员,深受学院文化自由精神的濡染。自由主义作家与政治和商业保持一种超然的人生姿态,主要原因就在于学院与时代的距离,也因此他们能够在学院象牙塔般的文化环境中以平和的心态与文化的理性,撷取传统文化精华,延续其精髓。“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14](P75)自由主义作家在学院中以传播知识、教育学生为己任,从而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不用再攀扶社会团体来维持生计,拥有了人格的独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依附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坚持用个性主义立场和观点批判社会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由于新的价值观念和标准都未建立,当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旦拒绝了对政治力量的依附,他们就失去了对社会发言的影响力,唯一可做的,就是退回书斋去过默默无闻的寂寞日子。而周作人应该说是这群人中唯一在价值转换中获得成功者,他在拒绝了政治力量以后,奇迹般地在自己的专业——散文创作上建立起新的独创的价值标准:美文。”[15](P374)
作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最早的理论家之一,周作人为达到启蒙民众的功利性目的,在“五四”初期就提出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20世纪20年代初,周作人从西方引入“美文”概念,一种能自由抒发性灵和准确传达自我感念、随心所欲又弥漫着灵气的自由式文体,有着英国随笔与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散文的双重外衣,这实质上就是后来周作人、俞平伯等一起提倡的小品文的前身。这种自由精神既在“五四”激进思潮中萌生,又受到了“五四”激进精神的束缚,并未自由舒展。“五四”落潮后,周作人正式开辟以个性为中心、以言志为主旨的“自己的园地”,走向生活艺术化,即生命的趣味之途,此时期周作人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风格。这种保守性退隐心态虽与时代相距甚远,却使其作品呈现出一种静穆的美,拒绝了激进和浮躁,坚守着文学的独立性和个性化。正是在此意义上,周作人影响了从《语丝》派到《论语》派直至京派的大批具有自由主义文学倾向的作家。而1930年《骆驼草》时期,正是周作人自由主义思想的集中表述期。他的文学观发生了重大转向,由“五四”时期对于文艺与人生还抱着一种什么主义,期望文艺有觉世的效力,发展到只为满足自己的趣味,实现自我性灵与心灵的自由抒写,这一转变深深影响了《骆驼草》同人,也使《骆驼草》周刊在发行上走精英主义的小众化路线,在当时的文坛独树一帜。
1930年的《骆驼草》周刊以个人性灵的自由抒写为艺术创作之基调,坚守纯文艺的、无功利性的、精英主义式的艺术立场,不与政治意识形态化和商业化的文坛发生直接关系,构筑起一个与世隔离的文化堡垒,耕种着“自己的园地”,坚守着“自我性灵的自由抒写”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在文化中心南迁上海、文坛向左转以及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骆驼草》同人远离动荡的现实世界而归隐书斋,从中西文化传统中寻求到新的人生价值取向,对国民大众进行常识启蒙,希求他们的自由主义文学观能得以充分发展。《骆驼草》周刊的文学观念为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化、商业化的中国现代文坛提供了另一发展路径。
[1]周作人.代表骆驼[J].语丝,1926,(89).
[2]唐沉,韩之友,封世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3]冯至.《骆驼草》影印本序[A].俞子林.书的记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4]周作人.知堂说[A].周作人散文全集(6)[C].钟叔河,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周作人.草木虫鱼小引[J].骆驼草,1930,(23).
[6]俞平伯.身后名[J].骆驼草,1930,(1).
[7]俞平伯.冰雪小品跋[J].骆驼草,1930,(20).
[8]周作人.冰雪小品选序[J].骆驼草,1930,(21).
[9]徐祖正.文艺论战[J].骆驼草,1930,(10).
[10]徐祖正.对话与独语[J].骆驼草,1930,(2).
[11]石评梅.再读《兰生弟的日记》[J].语丝,1926,(104).
[12]周作人.发刊词[J].骆驼草,1930,(1).
[13]废名.《竹林的故事》序[A].废名集(第一卷)[C].王风,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4]张晓唯.蔡元培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15]陈思和.关于周作人的传记[A].程光炜.周作人评说八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