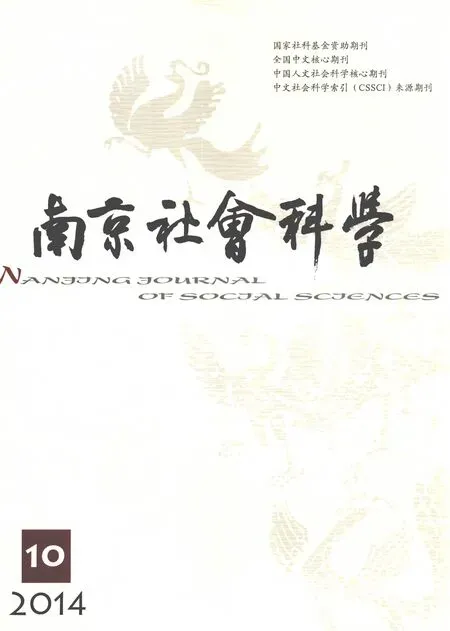刑事司法的民意道德性分析
张 毅 刘旺洪
刑事司法的民意道德性分析
张 毅 刘旺洪
民意有时是大众社会道德观的体现,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与其相关的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刑法本身包括道德的内容,刑法的善恶需要由道德标准加以判断。但刑法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是必定存在的,民意实际上成为刑法与道德冲突协调的载体和外在表现形式。在正当的民意实现的过程中,刑事司法将法律与道德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完美的融合。但是,民意不能等同于公共道德,民意是可煽动和引导的情感,民意缺乏标准,从而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刑事司法应当坚守罪刑法定的底线,因为法律本身的价值得到确认,比迎合民意要求更加具有社会的正义。
民意;道德;刑事司法;社会正义
一、民意:刑法和道德协调与冲突的载体
刑法本身包括道德的内容,刑法的善恶需要由道德标准加以判断;同时刑法以符合道德的规范来促进和维护道德,使得善恶的形象不仅通过社会道德来实现,而且还能在法律上提升人们更加理性的思维和行事。然而,对于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刑法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是必定存在的。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但是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规则的遵守,而这些道德规则乃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①法律不管从形式还是实体上,都来源于国家的权力,在国家层面上的法律,首先要体现的应当是普遍的公平正义以及在国家权力保障之下的统治利益,形式化和规范化是法律的应有之义,即便考虑法律的道德来源,在立法成型之后,为了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效力权威,只要不对基本的统治和秩序产生影响,也就不会再对新生的社会道德做出迎合;而道德的评价主体是社会大众。社会大众评价道德的标准是由民族的风俗习惯等复杂因素积累而成,而且总是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变化,所以社会大众并不会把法律所要追求的目标放在首位(当然也不是完全不考虑),更不会通过法律来验证道德的正当性。作为来自不同主体的,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的判断,罪刑与道德的对立将是客观存在的。
在刑法的发展脉络中,法律与道德的区分和融合是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刑法和道德的冲突通过罪刑的规范不断的外化和显见,而且伴随着文化和民族传统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刑法与道德的冲突本质也就在于此,法律需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需要反映掌权者所代表阶级的利益和思维方式,而道德的相对稳定使得在法律制度不断变迁造成的不同社会形态下能够保持相当的传承。虽然法律也要求稳定,但是法律的稳定性总是没有道德来得牢固,例如我们常说的“杀人偿命”,在刘邦“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的约法三章里初见端倪,两千年从封建到社会主义的嬗变也未能阻断这种道德的延续,而我们的法律,已经历经了从封建到近代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再到沿袭前苏联直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沧海桑田。法律和道德的纠葛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和否定之否定的哲学观念。例如“杀人偿命”的报复意识和现代刑法宽缓人道的价值理念之间的冲突,或者“重刑轻罪”的古老刑罚观念和罪刑均衡的现代刑法思潮之间的矛盾。他们的对立是客观存在的,而我们关注的是他们如何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运行,又是如何在对方的领域里产生作用。
在刑法的发展史上,罪刑法定的确立是近代刑法诞生的标志。而罪刑法定的确立过程,本身就是法律与道德相分离的过程。有学者指出,“费尔巴哈确立罪刑法定原则,首先是基于他对道德与法的严格区分。在他之前,贝卡里亚也对此有深刻的论述,认为法律应当只惩罚人的行为,而不能追究人的主观思想动机。人的善恶是一个道德问题,属于道德责任的范畴,不应当由法律来解决,不能承担法律责任。费尔巴哈在此基础上的努力在于,以罪刑法定原则使犯罪认定标准化,从而防止了将道德过错与犯罪混为一谈”。②罪刑法定严格区分了法律与道德,并且在道德的向度上不加以限制,而是一切以法律为依据,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解决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内部,仍旧不能摆脱道德的影响,“罪刑法定要求刑事立法不应该是任何个人的肆意妄为,而应是民意(包含了人的善恶观念)的体现,国家的刑罚权也应当受到民意的限制,当民意的善恶观念改变时,才能在正当程序行使下修正法律”。③对于法律来说,强制的适用是法律权威得以树立的标识,但是法律并不仅仅需要权威。权威可以带来极权和专制,更可以引发社会道德的坍塌,因此法律的强制必须获得信仰,才能在多数人的心里建立起能够被服从的态度,所以“能够确立公民忠诚信念的刑法是正当的刑法;一部足以动摇公民对刑法忠诚而只会导致恐惧心理和厌恶情绪的刑法是不正当、不合理的”④。在多元化道德观支配下并且分层明显的社会里,关于同样事件的声音显然是不同的,这些“声音”就是所谓的“民意”,民意可以是代表传统道德判断的国民感情外化,也可以是对于社会某些现象发出的偏激的态度,更可以通过那些分散民意的集中对法律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威胁”而成为“多数人的暴力”。
二、民意的表达:刑事司法中民意影响的多元性
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民意对于立法和司法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对于司法,从古至今,民意的参与使得司法裁判必须考虑“裁判的民意可接受性”。有学者用法律思维的缺失来解释民意对司法的影响:“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职业法官,审判的思维方式是平民化和大众式的思维,其实质在于用大众思维来制作判决,力求判决体现民众的意愿。”⑤这恐怕只是形式上的原因,民意参与立法和司法的内在实质在于中华法系对待法律的传统习惯——在中国古代,法律是从属于政治和国家治理之下的,“德体法用”的法律观,使得法律的存在效用在于维持社会的基本道德,如果道德能够自然的树立,那么就是最高的境界:“无法”;当法律存在的时候,所考虑的重心是“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家思想,法律既然必须迎合伦常道德,而民意把持着对于伦常道德的舆论,因此造就了中国独特的法律判断——对于民意的尊重和膜拜,民意的指向决定了法律的作用方式:民意是“第一性”的,法律对于伦理道德的尊崇就是通过民意实现的。
在当代中国,法律的规范已经在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颇有成效,却在对待“民意”的态度上表现出与古代惊人的相似,这似乎更和法律思维职业化与否没有太大的关系,毕竟在法治化数十年的国家,法律职业化已经初步形成的前提下,却仍旧需要依靠民意来裁判,个中原因是异常复杂的。在刑事判决书中曾经大量存在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和“民怨极大”,以及“得民心、顺民意”的国家治理原则,都在显示着民意的重要,在中国式的裁判合理性和公正性判断中,我们甚至把民意放在法律之上,以民意的符合与否来判定裁判的优劣。为了民意,我们可以把许霆改判为五年,也可以把刘涌判处死刑;为了民意,孙伟铭和胡斌可以构成交通肇事和危害公共安全两个不同的罪名;民意还可以让药家鑫被处以死刑立即执行,也可以让喧嚣一时的吴英案件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改判死缓。在民意判断和裁量司法判决的基础上,法律可以在民意的范围内作出更有利于或者更倾向于民意的解释。“真正的指导力量是人民,尽管政府的形式是代议制的,但是人民的意见、偏好、利益,甚至激情对社会的经常影响,都不会遇到顽强的障碍”。⑥民众对于法律的思考,通常的认知或者朴素的判别都可能对法律是一种强大的考验,在法律的强势与民众“上善若水”的民意面前,我们应当如何带着理性而有“选择性”地倾听呢?
从根本上说,民意是道德的一种,如果我们把道德归结于习惯和风俗的集合,那么民意就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与其相关的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⑦而且民意的异质化也是不出道德窠臼的,道德的价值判断取决于判断主体的主观意志以及判断时的客观条件。法律对于民意的遵循似乎可以从民主的角度去解释,规范意义上的民意,应当是“作为非统治群体的广大公众的利益诉求”,这种诉求是“政治系统正常运作和做出合理输出行为的基本前提,也是民主政府政策输出的基本原料”⑧,简言之,就是民主政府应当代表民意,政策的做出也需要考察民意。这并非虚诳,休谟就说过,“政府只建立在民意之上,这个原则既适用于最自由和最得民心的政府,也应用于最专制和最黩武的政府”,⑨而民意在转换到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也“有助于国民将刑法由他律的外在的东西内化为自律的内在的东西,增加国民的法规范情感和刑法认同感”⑩,同时,民意的反映与否,应该也是评价法律是否良善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说,民愤是否得到平息,是社会公正实现程度的一个尺度,也是刑罚目的实现程度的一个标志。显然,民意也有正面的作用,在正当的民意实现的过程中,法律不但行使了权威和强制,更是生动的在“全民参与”的司法活动中让刑事法律获得了公众认同的同时,让民众对法律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三、民意的非理性:刑事司法中民意的非道德性
民意可以代表一部分正当的道德,但是又不能和道德混淆,民意的负面作用也就在于此,如果民意能够等同于公共道德,那么托克维尔所说的“法律只要不以民意为基础,就总要出现不稳定的状态”就没有值得苛责的瑕疵。和公共的道德不同,民意是可煽动和引导的情感,而道德至少是具备一定外部特征而在某个文化圈子里共通适用的思维——德夫林说过,“根据大多数人的观点得出社会的道德判断是不够的,要求每个公民同意又太过分了。我们希望在理智健全和有正义感的人们中找到社会的道德,从而确定社会的道德判断”;而民意不具备“理性和正义感”特征,民意可以被煽动引导,也可以源自于非理性和非正义。因此,民意非理性的情形要比理性多得多——希特勒政府“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是民意的象征,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也是日耳曼人民意的集中体现,而这显然不是社会的公共道德。既然民意是感性的多变的情感,和法律的规范客观要求一定是冲突的。虽然我们说,法律的必须考虑道德意志的因素,但是一旦经过正当的立法程序确定之后,就不应当再受到民意的摆布。
四、罪刑法定的坚守:刑事司法如何回应民意
既然民意是客观上不可控的情感因素,又是可以被引导和改变的舆论潮流,那么在法律的判断里考虑民意就必须谨慎和小心。如果对于大多数人出于非理智因素产生的民意,随意的法律支持将会成为“多数人的暴力”,正如贺卫方说:“尽管在普遍的层面上可以肯定民意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然而就一个具体案件而言,民意也许是相当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如果法官完全顺从民意,便可能出现对一个社会中少数派的不宽容”在中国传统的对于审判公正性的判断中,正是因为民意观的存在,才产生了“寄明智审判之希望寄托于清官”的思维,在公众看来,既然法不能做出恒定的评价,那么“能够或者善于听任民意”的司法官,才是司法官成为“清官”的标准。所以,民意的滥用是危险的,但是民意对法律的影响仍将在客观上存在。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或者合适地适用“理智”的民意。
“民众的集体意识与正义情感不仅具有非理性、情绪性,而且往往变动不居、起伏不定,往往一个孤立的突发的犯罪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公众对刑法的态度”,这种情感意义上的民意往往被称之为“民愤”,但“民愤”是一种没有制度化的“民粹”正义,并不能代表完整的民意。同时,情感型民意是没有刑法意义的,民众对于案件的事实的情感反映都不具备法律上关注的意义。例如在杭州胡斌案,民众有感于富二代对社会公平的蔑视,发出了对于肇事者严惩的民意。这些因素的考虑,大多是民众对于现实社会中某些不平衡现象的情感发泄和非理智反映,这种民意的形成与案件本身的处理没有关系,而仅是对于案件背景的评述。在中国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富二代穷二代的鸿沟,让社会本能的嫉恨蔓延并且扩大,根植于社会现象的民意可能也能够体现出某些直观的正义。但是这些因素其实没有任何法律意义,更谈不上定罪量刑的价值。然而,正是这种民意的躁动,让法律在做出裁决之前必须异常小心,以免冲破民意的闸门。而知识性民意,是指民众关心的事实具有刑法意义,甚至就是构成要件事实本身、具有直接的定罪量刑价值,进而基于社会知识表达的群体性意见。知识型民意是民众法律意识积累所表达出的理性思考,例如在邓玉娇杀人案中,民众对于邓玉娇行为的性质做出的判断,并不因为她是在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基于反抗而致人死伤而有所偏袒,民意有意开脱她是对于“反抗”这种天然的自卫权的认识,而这一民意体现在法律上,就是对于防卫的肯定。邓玉娇最后的判决结果,也是法律和民意的双重体现,既符合了法律的规定,又契合了民意的指向。
所以,法律对于民意的取舍,应当根据民意的性质做出具体的区分。当民意与法律的规范相同的时候,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认可,这个时候法律裁量不仅仅是司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于民意的顺应和加强。然而,当民意与法律出现冲突和矛盾时,我们将面临如何选择的困境。在古代,我们的司法传统没有独立的法律思维,法官既是司法者,同时也是执政者,当执政的目标是“顺应民意”的时候,司法的性质也就随之改变。然而,如今法官的评价标准仍然是能否“让人民满意”,而不是是否尊重了法律。评价标准的习惯让我们的司法者在裁判过程中难免受到民意左右,即使民意是被操作和控制的非理性思维。在法治化的社会里,法律应当是一切冲突的判断标准,对于民意和法律的冲突,也应当以法律的规范为最终的参照。这样,即使是民众不理解甚至发对个案的判决,也会在长期同样的判决中领会到法律的价值。“在美国的辛普森案中,民意倾向于辛普森杀人了,但是司法判决辛普森无罪,民众最终尊重了法律,这说明在司法长期坚持正义的社会背景下,即使人们暂时不理解判决,民意也会尊重司法”。同时,法律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某一个案件能否得到公正,而在于整个社会的法律观念以及法律意识的树立,法律活动的价值应当引导民众的理性思维。所以,即使在个案当中,法律不能尽量满足于民意要求,但是法律的规范裁判仍旧会确认法律的独立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本身的价值得到确认,比迎合民意要求更加具有社会正义。因为“法官的法袍不是权威的象征,而是良心的象征”,而“法官的良心就是指不受其他影响,忠诚地履行包括法律、遵守法律在内的一切职务活动”。
注:
①【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68页。
②陈兴良:《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③任喜荣:《伦理刑法及其终结》,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苏佩斯主张的科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主要由科学理论的层级系统和科学理论的表征与不变性等两部分组成。科学理论的层级系统回答了理论模型是如何连接作用于现象与理论之间的问题;科学理论的表征与不变性说明了科学理论本身是对于世界本性的探讨。
④周光权:《刑法诸问题的新表述》,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⑤孙笑侠、熊静波:《判决与民意——兼比较考察中美法官如何对待民意》,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
⑥【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4页。
⑦张隆栋:《大众传媒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9页。
⑧【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⑨【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3页。
⑩梁根林:《刑事政策:立场与规范》,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
〔责任编辑:李杏〕
AnalysisofPublicMoralityofCriminalJustice
ZhangYi&LiuWanghong
Public opinion is sometimes the embodiment of the popular social morality, and is similar opinions, emotion and behavior tendency, held by the most members of a society, toward relevant phenomenon. Criminal law has the element of morality. Whether the criminal law is good or evil needs to be judged by moral standard. But the conflict between criminal law and morality is bound to exist. Public opinions have actually become the carrier and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coordinat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criminal law and the moral.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right of public opinions, criminal justice and moral will achieve the perfect integration in legal practice. However, public opinion is not equal to public morality, and public opinions are the provocative and guided emotion. Public opinions lack of standards, and pose a serious threat and challenge to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The criminal justice should stick to the bottom line of legality. Because realizing the value of law is more important to social justice than catering to public opinions.
public opinion; morality; criminal justice; social justice
张毅,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南京 210097;刘旺洪,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南京 210097
D90-052/D926
A
1001-8263(2014)10-009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