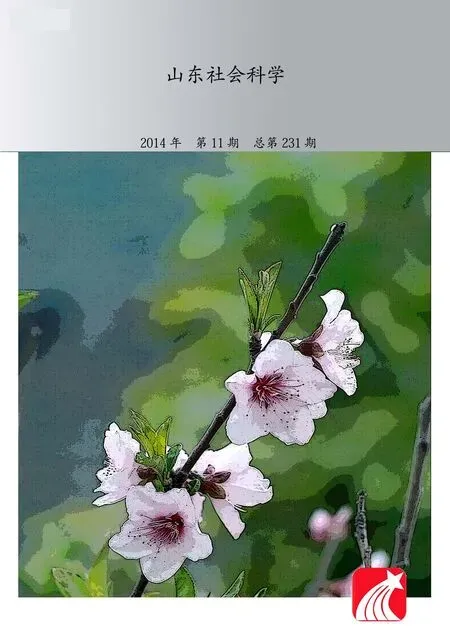论托克维尔民主心灵习性理论的现代政治价值
——对我国公民理性政治参与的若干启示
胡艳蕾
(济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其经典之作《论美国的民主》,指出与法国的民主革命相比,美国的民主之所以运转良好的根源在于美国国民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心灵习性(moeurs),即指美国公民所具有的积极的爱国情感、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自觉遵守社会规则且能实现良好自治管理等理性政治参与的心理习惯。近年来,一方面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不断提高;而另一方面,公民非理性参与事件屡有发生,如反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事件中的打砸抢烧行为等。显然,公民非理性政治参与事件的频发直接原因在于我国国民普遍缺乏公民理性政治参与的教育与认知,且存在着群体政治参与中的强烈去个性化等政治参与,而其深层原因则在于我国公民尚未构建理性政治参与的心理机制。而托克维尔的民主心灵习性理论恰恰是对美国人形成有序的政治参与心理机制的精辟概括。因此,本文基于政治心理学的理论视角对托克维尔的民主心灵习性理论内涵进行重新解读,即将该理论的理论内涵、理论构成要素及其形成机制进行系统解构,最后总结归纳出该理论对于我国公民理性政治参与心理机制构建的若干启示。
一、民主心灵习性的传统理论内涵
托克维尔著作中的心灵习性(Moeurs)一词在国内译著中通常翻译为民风民情或习俗等,而英文译本通常基于宗教文化语言与托克维尔本人的理论思想倾向而将之译为道德习俗或心灵的习性。如罗伯特·N·贝拉等人(Robert N Bella et al)在《心灵的习性》一书中提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社会哲学家托克维尔对美国国民性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有史以来最透彻的分析。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基于对美国人的敏锐观察和同他们进行的广泛交谈,描述了他时而称之为‘心灵的习性’的习俗观念,并说明这些‘心灵的习性’是怎样作用于美国国民性的形成的。他认为,是我们的家庭生活、宗教传统和对地方政治的参与造就了美国人,使我们能够保持同更大范围的政治共同体的联系,并进而维护自由制度的生存。”[注]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我们认为应将moeurs一语译为心灵习性而非习俗,将moeurs et costumes意译为民主心灵习性而非“风尚与习俗”或“政教习俗”[注]王焱:《托克维尔和他的“新政治科学”》序,载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篇)序,曹冬雪译,2012年版,第9页。更能符合托克维尔著作的本意。
关于民主心灵习性的理论内涵,托克维尔在书中并未进行直接而全面的概念界定,但他在书中一直强调美国式民主社会中公民具有一种心灵(heart)[注]注:英文版本译为heart。的习惯,而且他所谓的道德习俗不仅涉及有关宗教、政治参与和经济生活的各种思想、观念,而且也包括各种习惯行为。[注]参见泽维尔·苏比里:《自然,历史,上帝》,马里兰州美国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如他在该书上卷绪论的第一段便指出美国人具有一种 “特殊的风俗习惯”,且该习惯是由于美国社会身份平等这一事实影响所致。[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篇),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之后,他在对美国政治社会的论述中不断提及美国人这种源自心灵的民主习性。如在对美国基于民主的法律制度的形成的论述中,亦将之与民主心灵习性联系在一起[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篇),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托克维尔在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更是将研究关注点集中于美国人民主心灵习性形成的原因、过程及其政治影响。总之,美国人的民主心灵习性成为贯穿托克维尔上下两部著作的核心观点与理论线索。如托克维尔在对美国人的公共精神的描述中不断强调了美国人所具有的这种民主习性,他认为本能的爱国心在美国几乎不存在,美国的普通民众习惯将国家繁荣看做自己努力的成果,且这种爱国心是由于他们主动参与各种社会公共事务而形成的心理习惯。[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篇),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在论及美国出版自由时,他再次指出出版自由不仅能够使国家改变法律,且能使社会改变风气,而美国的出版自由则给美国人思想提示的方向,并使美国人的精神和思想养成民主的习性。[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03页。在探讨美国司法制度对人民大众的影响力时,托克维尔再次提到习性问题。[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0页。此外,托克维尔还对美国人的这种民主心灵习性的特点、产生及本质进行了集中系统论述。[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33-634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托克维尔所谓的民主心灵习性(道德习俗)是指那种塑造概念、意见和思想等心理习惯的东西,是社会中人的道德与智慧习性的总和,它不仅涉及有关宗教、政治参与和经济生活的各种思想、观念,而且也包括各种习惯行为;它是美国人得以维持其自由体制的关键;[注]朱世达:《美国的文化模式:对中国文化的启示》,《美国研究》1994年第3期。其产生的根源在于美国社会的自由与平等。因此,民主心灵习性本质上即公民个体的一种民主政治心理习惯,具体包括民主心理意识与民主习惯行为两部分内容。民主心灵习性是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实现良好运转的根本保证,托克维尔的这一观点对现代国家民主建设依然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现实意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前苏联解体掀起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举着民主价值大旗而进行政治制度变革的浪潮,然而大部分变革的结果是社会的持续动荡与经济衰退。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系列的变革过度关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存的制度形式而完全忽略了自己国家的国情实际,尤其是本国国民的政治心理、政治文化、制度环境等因素。因此,我们认为公民意识培育机制的构建应为我国民主制度建设完善的根基,而托克维尔的民主心灵习性理论不仅以事实论证了公民意识建设的必要性,且他对其理论内涵的阐释对于当前我国公民意识培养机制的构建依然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二、民主心灵习性理论的现代政治价值
近现代以来,一些国内外学者对民主心灵习性的理论内涵进行过一些解读与阐释。如1985年美国学者贝拉等人在《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一书中,首先肯定了托克维尔的民主心灵习性理论观点,但对于该心灵习性产生的根源与托克维尔持不同观点,认为美国人的个人主义而非平等促使美国人具有民主的心灵习性。[注]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国内学者任剑涛指出所谓公民民主的心灵习性,具体内容包括:公民惯于服从法律规则、熟练地进行社会自治以及公民理性容忍与妥协的精神。[注]任剑涛:《群体诉求伸张的制度安排》,《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0期。纵观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民主心灵习性的理论观点,分歧之处在于美国人民主心灵习性的形成根源问题上[注]注: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民主心灵习性产生的根源在于美国社会的平等;而贝拉等人则认为其产生的根源在于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但对于民主心灵习性理论内涵的认知基本一致,即都认为是一种涵盖公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民主心理习惯,基本内容包括民主的情感、理念、意志、认知及目的,具体表现为公民具有遵守法律规则、进行社会自治、理性容忍与妥协的心理习惯。显然,公民民主心灵习性属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基本研究内容为公民个体的民主心理及其与政治社会现象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因此,我们将基于政治心理学的理论视角对公民民主心灵习性的理论构成要素进行系统解析。
政治心理学认为,公民政治行为受公民个体的人格、态度、认知因素的根本制约和影响,而公民政治行为的强度和稳定性与实施政治行为的情感支持、个体认同以及社会认同有关。因此,公民民主行为的基本影响因素为公民的人格特征、民主行为态度、民主行为认知,促使其内化为公民民主心灵习性的间接影响因素为民主行为的情感支持、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因此,基于公民政治心理的基本结构理论,我们认为公民民主心灵习性由下述七项要素构成。
(一)民主人格
现代心理学中,人格概念通常被划分为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外在表现层,即个人在社会化之后的种种言行,即人格物化成的“外壳”(面具);二是内在特征层,指个体做出规律性言行背后的心理原因,即面具背后的真实自我[注]尹继武、刘训练:《政治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因此,我们认为所谓的民主人格,即是公民个体经历政治社会化后由于具有民主心理习惯而表现出的民主言行特征,也可称为具有民主倾向的政治人格,它是在遗传和社会、政治环境的双重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民主心理特征,包括民主行为模式、民主情感体验方式、民主思维方法、稳定的民主态度、信念和价值观等等,上述民主心理特征构成了公民外在民主行为的内在动力系统。基于政治人格理论,公民民主人格亦是具有渗透于人内心的主体倾向性,既表现为后天形成的有意识的政治取向,亦表现为个体遗传获得的生物个性,具体包括民主意见、民主信仰和价值观和民主气质。
(二)民主态度
民主态度属于政治态度的一种具体形式,即是指公民在政治生活中受由民主信仰与价值观等因素的支配而对民主现象与民主行为具有积极肯定的内在感受、情感和意向。政治态度通常具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的政治态度至少包括感情、认知和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而狭义的政治态度仅是指公民在政治生活中对政治现象与政治行为的内在感受、情感和意向。[注]H. J. Ehrlich,“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ejudice”,New York:Wiley,1973,pp.3-25.因此,我们此处所述及的民主态度仅仅是政治态度的狭义概念。作为政治态度,公民的民主态度亦是经过后天的主动或被动学习而形成的。且民主态度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持续性及抗变性;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需通过语言暗示、说服等方法影响条件反射系统以促使民主态度发生改变。
(三)民主认知
狭义的政治认知是指人们在与其它政治角色和社会政治生活现象的接触与交往过程中,通过对它们外部特征的知觉,判断其他政治角色的动机、兴趣、个性和心理状态,或判断政治生活现象的是非善恶美丑等状态,从而形成人们对于各种社会政治生活现象的认识、印象、评价和理解。广义的政治认知是一个包括政治认识、政治情感、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即知、情、意、行)四个方面的认识体系。四种要素相辅相成,逐级递增,共同促成了政治认知实现过程中教化—内化—外化三个阶段的统一。[注]尹继武、刘训练:《政治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为便于系统研究,文中我们所指的民主认知为狭义上的政治认知,即指公民在参与民主政治生活过程中,通过对民主行为外部特征的知觉,形成对民主政治角色动机、兴趣、个性等心理状态的判断,以及对民主行为与非民主行为的是非判断,从而形成其对民主行为的认知、印象、评价和理解。
(四)民主记忆
所谓民主记忆是指公民在民主认知过程中所形成对民主的理论内涵与外在形式等概念的民主记忆,公民的民主记忆是决定其是否实施民主行为且为其评价他人民主行为的基本判断标准,该判断标准由于其民主记忆库中那些具体民主行为概念本身具有正负面情感评价而导致民主记忆本身具有正负面情感之分。如公民个体在民主认知过程中,遭遇了地方听证会制度作伪现象而对民主参与评价制度形成负面情感,由此其今后会对地方再次举办的听证会存在抵触情绪,且对听证会这类民主行为的结果存在怀疑或否定态度。
(五)民主知觉
所谓民主知觉,即民主政治知觉,它是指人们在参与政治生活过程中对自己的感觉提供的民主信息进行加工、选择、组合以后而形成的对民主行为的完整印象,就其本质而言,民主知觉是政治知觉的正确发展趋势,即政治知觉形式的一个侧面。在民主知觉的建构过程中,应注意避免由于民主教育方式方法、公共传播媒体、民主制度环境等因素造成公民的民主知觉不全面、僵化刻板的民主印象以及民主认知偏差。
(六)民主情感
民主情感,即是指公民个体在民主政治环境下,对于民主行为的价值及实施形成较为稳定的正面情感并由此不断强化其个体对民主的认同。情感本质上为态度的中心成分,当个体的认知与情感不一致时,情感决定行为。在政治生活中,情感通常被视为非理性因素,但有时它影响甚至超过了理性因素。如热情和恐惧作为情感智力理论中的主要情绪,对于政治民主生活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如热情可以强化民主认同,而恐惧则会弱化民主认同。[注]尹继武、刘训练:《政治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83-108页。
(七)民主认同
所谓民主认同,是指公民个体在参与民主政治生活过程中,其产生于天资的才能与民主社会角色机会相互整合而形成的一种民主身份感。公民一旦形成民主认同,其民主行为亦成为具有自觉性、自发性的习惯行为。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团体成员极力获得或维持一种积极的社会认同感;团体成员将这种社会认同建立在内群体和外群体成员的有益比较基础之上;且当团体成员对现有的社会认同不满时,他们试图离开他们的团体或者加入一个社会身份更显著的团体。[注]Martha Cottam, Beth Dietz-Uhler, Elena Mastors and Thomas Presto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p.46,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2004.社会认同对社会信念体系或社会变革体系的树立具有一定的影响,并进而对党派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注]尹继武、刘训练:《政治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因此,民主认同对于公民形成稳定的民主身份感、正确的民主信念、民主价值、民主态度等具有积极影响。
三、构建公民理性政治参与心理机制的路径分析
综上所述,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之所以能够积极有效地进行政治参与,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形成了一种公民理性政治参与的心理习惯,并将之称为民主心灵习性。基于前述对于公民民主心灵习性理论构成要素的分析,以及勒温的场论与系统科学理论,我们认为公民理性政治参与心理机制的构建应由两个层面的内容构成:一是公民理性政治参与心理意识的建构,即是指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心智程序表,具体内容由理性政治参与人格、理性政治参与态度、理性政治参与认知、理性政治参与情感、理性政治参与认同、理性政治参与知觉、理性政治参与记忆七个要素构成;二是公民理性政治参与行为情境的构建,即通过不断健全完善公民理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外部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等情境因素,促使公民群体具有理性政治参与情感、理性政治参与认同及社会认同,继而使形成公民理性政治参与行为反应的多次重复成为一种心理习惯行为。
(一)公民理性政治参与心理意识层
第一,应逐步培育公民形成一种理性政治参与人格。公民理性政治参与人格的培育主要包括公民理性政治参与意见与态度、理性政治参与信仰和价值观、理性政治参与气质等要素的培育。根据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著名人物雷斯曼的大众人格理论,普通公民人格有三种“动机模式”,即“传统导向” (traditional directed)、“他人导向”(other directed)与“内我导向” (Inner directed)。他指出传统导向的人,行为以传统、习俗为标准;他人导向的人,行为以其“同龄集团”(peer groups)的规范为标准;而内我导向的人,则像罗马门神努斯一样是双面人:一面回顾过去,一面展望将来;一面服膺传统,一面憧憬现代。由于这种“双重价值系统”,所以常会遭遇“价值的困境”,在价值观和情感上发生严重冲突,既要创新以求促进社会进步,又要传承以保存传统,所以内外导向的人经常生活在心理冲突中。[注]David Riseman, Nathan Glazer, Reuel Denney,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p.20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因此,公民的理性政治参与人格培育中,要注意防止公民遭遇双重价值冲突而产生理性政治参与价值观与专制情感的心理冲突,从而严重阻碍公民理性政治参与人格的形成。
第二,应不断促使公民树立正确的理性政治参与态度。公民理性政治参与态度的培育过程中首先要兼顾其结构性理性政治参与态度与功能性理性政治参与态度。其中,结构性理性政治参与态度包括公民的平等意识、参与意识、自由意识、多元意识与制衡意识;第二类功能性理性政治参与态度包括公民的表达权意识、改革意识、诉求权利意识和干预权意识。此外,结构性理性政治参与态度与功能性理性政治参与态度二者间呈正相关关系,即结构性民主态度的民主取向愈强,功能性民主态度的民主取向就愈强。政治心理学中的合理行动理论指出,人对环境的客观评价,才是态度形成的主要原因,短暂的信息刺激比长期的感情制约更能影响人的态度。[注]胡佛:《政治文化的意涵与观察》,载乔健主编:《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胡佛:《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活》,三民书局(台北)1998年版。因此,公民理性政治参与态度的培育过程中,一方面应通过多元化的社会媒介对公民进行理性政治参与信息的宣传教育,促使公民的结构性理性政治参与态度与功能性理性政治参与态度形成积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不断健全理性政治参与制度体系,使理性政治参与制度实施程序化与常态化,从而通过不断的理性政治参与信息刺激以促使公民形成健全完善的理性政治参与态度。
第三,应逐步提高公民的理性政治参与认知水平。根据前文对理性政治参与认知内涵的解析,理性政治参与认知是指公民通过对理性政治参与行为外部特征的知觉、判断而最终形成对理性政治参与行为的个体认知、印象、评价和理解。公民理性政治参与认知的提高依赖于公民个体所处外部物质、制度及文化环境,即公民的理性政治参与认知受到其个体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的高低、社会理性政治参与制度体系是否健全以及理性政治参与文化氛围。卡尼曼等人在其关于政治认知的前景理论中指出:大多数人在面临收益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偏好的;人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注]D. Kahneman and A.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s, Vol.47,No.2,1979.且由此得出三个假设:第一,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 即损失的效用要比等量收益的效用的权重更大,损失的痛苦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第二,参照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即我们往往不是根据事物本身的价值量多少来支付它的价格,而是根据一个直观的参照系来决定它是否物超所值。第三,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即人们对于不同来源的钱产生不同的心理评价,即“心理账户”。[注]D. Kahneman, J.Knetsch and R. Thaler, “Experimental Tests of the Endowment Effect and the Cost Theore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1990.因此,公民理性政治参与认知的培育是应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政府应在制度上对公民的就业、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提供基本保证以使得公民以一种开放、积极的心态主动或被动学习理性政治参与行为的理论与现实特征。其次,通过多样化的社会媒介对理性政治参与行为的理论内涵不断进行宣传教育,以不断推动公民理性政治参与认知水平;最后,还应通过政治与社会媒介的多方位理性政治参与理论宣传,不断加强公民理性政治参与文化氛围以对公民理性政治参与认知水平的提高发挥潜移默化式的影响。
第四,应逐步确保公民具有正面情感的理性政治参与记忆。理性政治参与记忆是公民在政治认知过程中将大脑所获得的理性政治参与行为理论与外在形式等理性政治参与信息加工处理以形成的那些处于大脑深层的稳定、积极的理性政治参与认知结果。由于个体对理性政治参与行为进行政治认知程中,受到到个体主观因素与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可能会由于某些失败的理性政治参与行为案例而对该民主行为产生负面情感评价而产生具有负面情感的理性政治参与记忆。因此,公民理性政治参与记忆的沉淀不仅依赖于个体教育水平、理论认知能力等个体因素的影响,而且依赖于社会理性政治参与制度的健全化、程序化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公民理性政治参与记忆的沉淀应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应通过教育机构、社会媒体等多种路径不断提高公民个体教育水平、理解认知能力等个体因素;二要不断健全完善国家理性政治参与制度及其实施机制,从而确保公民形成具有正面情感的理性政治参与记忆。
第五,应不断促使公民具有正确的理性政治参与知觉。理性政治参与知觉是理性政治参与认知的直接成果,是公民个体对理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完整印象。由于理性政治参与知觉具有整体性、选择性、恒常性、理解性等特点,在理性政治参与知觉的培育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下述几点:首先,必须保持理性政治参与信息的时代性、公开性及信息本身的易懂性,以确保公民积极主动地接纳理性政治参与信息以形成完善的理性政治参与知觉。知觉的整体性会造成人们在面对陌生的理性政治参与制度、行为等理性政治参与现象时会根据自己原有的理性政治参与知识经验进行归纳统一为原本的理性政治参与知识经验,[注]S. Hong and R. Wyer, “Determinants of Product Evaluation: Effects of Time Interval between Knowledge of A Product’s Country of Origin and Information about Its Specific Attribut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17, No.3,1990.这样极易导致公民个体在理性政治参与知觉形成过程中存在保守、排斥等现象。其次,由于知觉的恒常性会造成公民的政治知觉中产生刻板印象、偏见等负效应,而刻板印象或偏见会造成某种虚假的民主认知错觉,进而引发情绪上“相对剥夺”的怨恨,最终导致“法不责众”的群体行为。因此,在公民理性政治参与知觉的培育过程中,应注意根据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心理的变化,利用多种社会媒介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教育,以促使人们摒除偏见,逐步形成正确的理性政治参与知觉[注]尹继武、刘训练:《政治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68-69页。。总之,公民理性政治参与知觉的培育过程中,应结合政治知觉的基本特征构建完善具体的培育机制,以避免形成错误的理性政治参与知觉。
第六,应不断促使公民的理性政治参与情感正强化。公民民主情感作为理性政治参与态度的中心成分,是公民理性政治参与心理的培育过程中关键要素之一。由于情感通常以价值基础,此处的价值即是指事物对自己的有用性[注]尹继武、刘训练:《政治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所以理性政治参与行为的价值是公民产生理性政治参与情感的根本影响因素。公民理性政治参与情感的产生源自于公民主体以自身的精神需要和人生价值体现为主要对象的一种自我感受、内心体验、情境评价、移情共鸣和反映选择。因此,在对公民的理性政治参与情感培育过程中,如何使公民感受到理性政治参与行为的价值应为研究的重点,如公民参与制度的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考量到公民个体参与的经济社会成本与收益,尽可能保证公民以最小的经济社会成本参与公共参与行为,且能获得较大的经济社会收益,从而不断促使公民对于公共参与这项民主行为形成正面情感。《论语·雍也》中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此处的“乐”即是强调正面情感的积极作用。一方面,正面情感能引起人们的兴奋、激动、愉快的情绪体验以发挥动力功能;同时,它还具有巩固或改变个体行为的强化功能,由此个体民主行为产生肯定的理性政治参与情感体验会在条件反射系统下重新得到巩固,最终促使理性政治参与情感正强化。[注]尹继武、刘训练:《政治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第七,应逐步促使公民形成稳定的理性政治参与认同。理性政治参与认同是个体将自己身份界定为理性政治参与社会成员的基本方式,即公民理性政治参与身份感的确定。公民理性政治参与认同的确立不仅依赖于个体的自我综合,亦依赖于对他所存在的群体中各种角色的整合。[注]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社2004年版,第12-13页。埃里克森指出,认同是一个动力结构,它随着各个生命周期中自我的不断合成而逐渐建立起来,其建立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下述现象:一是认同混乱或称为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指公民从青少年到成年过渡的关键时期内,面对各方面的变化和选择,个人没有做好心理准备,遭遇重大事件后感觉手足无措,陷入一种内心与外界的不稳定与不平衡之中。即对前面各阶段建立的自我连续性和一致性表示怀疑。二是消极认同(negative identity),是指当社会的要求与其原有的认同模式之间相差太大,以至于根本无法融和二者,这时的青少年就会重新寻找出路来维护自我,常常表现出反社会行为。这些消极认同原本是个体不得不压抑的一个个本我,也是导致仇恨、妒忌、暴力战争的原因。因此,公民理性政治参与认同的培育应具有持续性与周期性,即应在公民青少年时期就通过学校等教育机构与各种社会媒体、青少年公益组织等对他们进行理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宣传教育并辅以模拟参与活动,促使他们在早期便形成正确、健全的理性政治参与身份感,以避免他们成年步入社会后无法将个体身份与社会民主身份形成一致性认可而出现各种反社会行为或社会脱离行为。
(二)公民理性政治参与的行为情境层
第一,应不断健全公民的理性政治参与行为制度环境。此处的理性政治参与行为制度环境仅指正式制度,具体包括法律制度与社会规章制度。首先,法律制度的健全化是民主行为实施的基本保障,亦是公民理性政治参与行为价值体验的基本保障,是公民理性政治参与行为心理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其次,健全完善各项社会规章制度,尤其是理性政治参与行为的激励制度对于公民理性政治参与行为具有很好的正强化效应。以理性政治参与行为激励机制为例,可通过电视等多元化大众媒体,以公益广告宣传理性政治参与;或对于某些坚持理性政治参与的部分公民进行访谈,以实现对社会大众理性政治参与行为的激励效果。
第二,逐步培育公民理性政治参与行为的文化环境。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结构—功能主义的创立者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依据政治态度对公民文化类型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心理学研究。他在《公民文化》一书中指出:“政治文化一词表示的是特殊的政治取向,即对政治系统和系统各个部分的态度,以及对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注]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制》,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3页。由此,理性政治参与文化即为公民对政治参与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等持有的政治态度,以及他们对政治参与制度体系中自我角色的态度。因此,公民理性政治参与文化环境构建中的直接影响因素即为公民理性政治参与态度,其次为理性政治参与制度的健全完善程度。此外,阿尔蒙德还将政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村民的政治文化、臣民的政治文化和参与的政治文化。其中,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公民与政府体系密切相关,政治体系在各个方面都影响人民的利益;同时,人民也倾向于接近政治体系,通过广泛而积极的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系统,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扩大自己的利益。显然,理性政治参与文化即为参与型政治文化模式,而其实现的根本保证为成熟健全的政治参与制度、公开透明的公共舆论氛围及积极主动的理性政治参与行为意识。
第三,不断健全公民理性政治参与行为的社会环境。公民理性政治参与行为的社会环境即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时所处的一些非正式的公共参与习俗、公共监督习俗等具有民主特性的社会习惯或习俗,这些习惯或习俗不仅是公民的理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动力来源之一,且对公民的政治行为发挥着政治监督的作用。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提到的,“美国居民享有的自由制度,以及他们可以充分行使的政治权利,使每个人时时刻刻和从各个方面都在感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里的。这种制度和权利,也使他们的头脑里经常想到,为同胞效力不但是人的义务,而且对自己也有好处。同时,他们没有任何私人的理由憎恨同胞,因为他们既非他人的主人,又非他人的奴隶,他们的心容易同情他人。他们为公益最初是出于必要,后来转为出于本意。靠心计完成的行为后来变成习性,而为 同胞的幸福进行的努力劳动,则最后成为他们对同胞服务的习惯和爱好。”[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33-634页。他认为是美国的自由与平等制度促成了美国民主文化,继而使公民形成了民主心灵习性。虽然目前对该观点的第一部分存在争议,但民主文化是促成公民民主心灵习性的基本环境保障这一观点早已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可。因此,应通过建立健全公民理性政治参与的多元路径、不断提高公共参与的公开透明性以及扩大公共媒体的理性政治参与宣传教育等方式逐步培育理性政治参与文化环境,最终促使理性政治参与行为习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