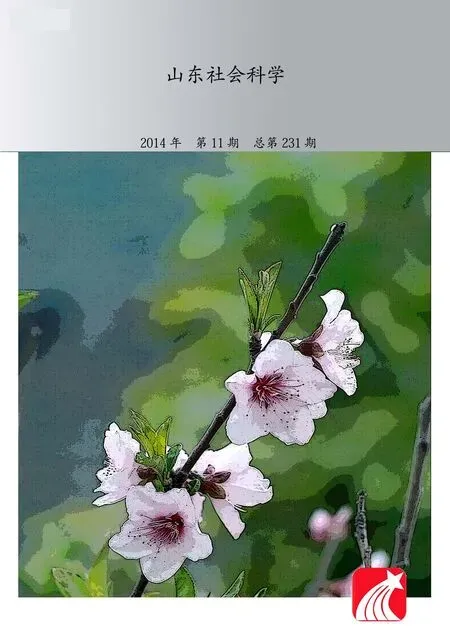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农村私法文化的建构问题
席书旗
(山东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中国现阶段法治建设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城市而不是农村,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以及法治资源在城市和农村分布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毋庸置疑,推进农村法治改革仍然是我国目前法治建设的艰巨任务。离开了农村法治改革的有效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就永远只能是不彻底的。经过数十年的农村法治建设,农村缺乏的不再是先进的法律制度,而是一种由私法文化所倡导的法律实践精神。“没有私法文化支撑的法治必然是跛了脚的法治”,*易继明:《跛了脚的“法治”——与夏勇先生商榷》,《法律科学》2006年第2期。这句话恰恰是当前中国农村法治改革现状的写照。然而,私法文化对法律实践的支撑绝非理论构建所能完成,因为“理论构建方面的成功,并不标志着现实操作上的一定可行,而对于背负着沉重历史传统的中华民族而言,尤其是如此”*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总第5期。。因此,农村私法文化无论是制度形态抑或是观念形态的建构,都必须结合我国农村的特殊情况在实践中不断进行修正。
一、建构农村私法文化是加强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第一,农村私法文化是一种亟需构建的异质权利文化。所谓农村私法文化,是指建立在农村市民社会和农村市场经济之上的,以私法特有的权利神圣、身份平等、私法自治理念为内涵,以构建新型农村秩序与维护农民权益为宗旨,运作于农村社会生活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心理态势和行为模式。然而中国传统的农村法律文化却是一种公法文化。它以知足忍让、和谐无讼、权力至上、义务本位为基本特征,与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私法文化截然不同。所以,私法文化对于中国农村来说既是一种异质文化,又是一种权利文化。
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是一种立法先导型的改革模式,法律观念更新滞后严重影响了整个法治改革的进程,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如此。依据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观点,文化是人类用来解释其经验和指导其行动的意义结构。一个较为现代的法律制度若缺少与之相协调的观念性法律文化的配合,就不可能正常运转。例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正式颁布施行至今已有26年,但由于缺乏法治精神和权利意识,村民实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依法治村的美好愿望在大部分地方未能得到有效落实,往往被讥之为“乱哄哄的民主”。“贿选”“家族控选”等有悖于民主与自治精神的违法行为普遍存在,其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形式上是村民自治,其实是传统文化中“裙带风气” “荫庇心态”“宗派倾向”“人治观念”等陋习的再现。长期以来“我们只偏重于法律制度的建构,而忽略了法治的运行机制及其得以生成、运行和发展变化的社会根基”*马长山:《法治的社会根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从法律观念与制度本身的演进而论,公法的精神莫不发端于私法,私法乃市民“社会生活之根本大法”。私法文化所倡导的权利神圣和契约自由精神,构成了宪政和法治的文化源泉。可以说,脱离了私法文化就难以预期现代法治改革的成功。当前,我国农村法治建设推进艰难缓慢,农村法治“表层化”问题尤其突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既有的公法文化缺乏私法文化的根基,故而构建先进的农村私法文化已成为进一步深化我国法治改革的当务之急。
第二,建构农村私法文化有利于整体推进我国农村法治建设。在世界各国所倡导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中,虽然理念与定位各不相同,但大都重视并依托法治。各国政府都极为重视和致力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法律素养,如俄罗斯曾提出在农村发展中法治和人是关键,印度提出要用法律保障农民就业,美国作为法治发达的国家重视用法律确保农村发展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韩国则在由政府主导的“新村运动”中非常重视提高农村的法治水平。然而是用国家的行政权力、宗族权力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组织和调控社会,还是用私法、法治通过法律运作的方式来组织控制社会,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选择。实际上,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是一个由政府主导而民众被动参与的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这种模式虽在法律制度的创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各种法律法规陆续制定颁布,甚至在短期内构建起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但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民众普遍缺乏主动参与的积极性,所以法治建设的推进并没有伴随着农民民主与私权观念逐步强化。
我国当前农村法治建设整体步调极其缓慢,究其缘由,在于我国的农村法律文化是一种义务本位的公法文化,农民习惯于服从权力,缺乏为权利斗争的精神。私法文化则是一种权利文化,崇尚为权利斗争的法律实践精神。然而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几乎找不到私法文化的印痕。儒学、儒家文化是中国这个族群文化自我认同的根基和伦理共识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情理法”。这种“情理法”实际上是一种“义务本位的法”,它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表现为以义务为逻辑推演的起点,以培养一味服从权力的“良民、顺民”为目标宗旨,法与情理搅混在一起,且排在情、理之后,法律在权力之下,完全背离“权利至上”的现代法治精神。实际上,“情理法”所涉及的不仅是一个中国法哲学的问题,还是整个文化的问题,它在观念上严重阻碍着我国农村法治建设的整体推进。然而,任何法律制度要得到有效实施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信念、信仰和伦理共识等文化观念作为铺垫和支撑。就法治而言,其核心内容是规范和限制国家、政府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并对公共权力制定具体、明确的规则、程序,防止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它需要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文化。但在我国农村既有的社区文化甚或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都难以找到这种权利文化,其必然的后果就是法律所确认的农民的各种权益在“权力至上”“人治观念”“法律无用人管用”的文化背景下得不到切实维护,最终难以实现。
显然,由于文化模式的排异和原有农村传统习俗、观念的羁绊,私法文化的建构问题在我国农村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我国法治建设难以整体推进的重要缘由恐怕也在于此。现代法治是在私权与公权的持续博弈中逐步建立的,在这场博弈中,私权不仅涉及财产权、人身权,同时它也意味着需要构建一种以平等、自由、权利本位、意思自治为特征的私法文化。唯有在农村构建私法文化,确立私法精神,才能夯实法治的社会根基,才能突破当前我国法治建设难以整体推进的尴尬局面。
二、建构农村私法文化必须走与民俗观念、草根精神融合之路
“礼失求诸野”,意思是如果礼制在社会上层沦丧后,那就只有到民间去访求。自古以来,草根阶层就被认为是沦丧后的社会秩序得以重建的根基。究其缘由,主要是礼制精神已深深植入草根阶层的头脑和血脉之中。与之相类似,我们现在建设法治中国,就必须把作为近现代法治主义基石的私法精神切实融入草根精神之中,使现代先进的私法观念与传统的民俗观念相互融合,且成为农村文化的内核,农村的法治建设才能取得扎扎实实的进步。
第一,农村私法文化的构建是一个缓慢的移风易俗的过程。“村落文化”是一种存在较大差异性、蕴含各地历史传统、反映当地居民感情皈依的观念性文化,它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排异性特征。私法文化要融入“村落文化”并上升为民俗观念、草根精神,首先面临的是文化认同问题。文化认同是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指文化群体或文化成员承认群内新文化或群外异文化因素的价值效用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的认可态度与方式。只有经过认同后的新文化或异文化因素才有可能被接受和传播”[注]冯天瑜:《中华文化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在此意义上,我国农村私法文化的建构实则意味着传统法文化的彻底转型——由义务本位的文化转向权利本位的文化。而一种文化、一种规则一旦能在聚落中得以确立、认同,它必然已是全面地融入了现实的民俗生活。
生活于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都是以自己的文化为基准的。一种文化体系中正常的现象,在另一种文化中却难以理解、接受。一方面,在我国农村,涵纳乡土规范的“村落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多有抵牾,不能为法律的运行、发展和完善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而现行法律也往往忽略了“村落文化”的特质,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农村社会的特殊性,以致法律的推行常使农村社会业已形成的和谐与默契被打破;另一方面,任何国家的整体性政策与法律又都必须经由“村落文化”的洗涤与过滤方可顺利实施,法律运行必须“以某种方法求助于民众熟悉的习惯、制度或象征”,[注][美]费里德曼:《法律制度——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李琼英、林欣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而在我国农村,村规民约中也有许多规定如禁偷、禁赌、禁吵架斗殴、禁乱放牲畜、禁滥伐林木等,传统上也一直是家族规约的内容,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是一致的。上述两方面说明私法文化不可突兀地强行植入“村落文化”,而应尽可能地遵循文化认同的一般规律,借助于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但详细了解中国这个族群文化后会发现这又是一个莫大的缺憾:我国民间所苟存的契约本性之平等、自由因素以及尊重、敬畏契约的态度和理念,也仅是一种在重压下的坚持,并未能形成契约精神,更远不足据以建构中国的私法文化。然而从文化的本质上看,世界上绝没有完全封闭的文化,文化本身应该是一个开放体系。“中国在引入种种并不为其历史文化所知的现代性的变革过程中,就必须作出相当幅度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这种现代化的发展。”[注]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但这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要在这一过程中建构我国农村私法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让私法文化潜移默化地融入传统、习俗、道德、宗族活动之中,与民俗观念、草根精神相互融合。然而,这毕竟涉及到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与磨合,同样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然是一个缓慢的移风易俗的过程。
第二,农村私法文化的构建是一个通过法律方式逐渐培养农民权利意识和法律情感的过程。在古代中国,尽管官吏在解决纠纷、处理政务时依据伦理, 照顾“人情”,即所谓情、理、法“迭相为用”,但始终未能撼动民间“法即是刑”的观念。一切社会关系都被打上“刑”的烙印,农民对法律始终秉持冷漠、厌恶、排斥的心理。正如伯尔曼所言,如果“剥夺了法律的情感生命力,则法律将不可能幸存于世”[注][美]哈德罗·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9页。。因此,必须改变农民对法的错误认识,重新培养农民的法律情感。
由于受传统民俗观念的影响,我国农民对法律的认知整体上仍停留在法律是“国家意志”,甚至是“政府意志”的层面上,无法和个人私权联系在一起,更谈不上权利意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通过何种方式培养农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情感呢?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一系列思想教育运动中,民间固有的许多知识、信仰、观念、仪式和行为方式都被视为愚昧、落后、陈旧、过时的东西遭到批判和禁止,族谱、村庙、家祠等被认为是旧时代的遗迹而遭到毁弃。[注]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8页。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新思想新观念,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科学、民主等,但这些观念并不是通过法律运行的方式引入农村文化生活,而是以政治力量或政治运动的方式导入的。国家权力的触角曾一度深入到基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结果是政治权威确立的同时,法律权威丧失,私权观念也被一并扫除。我国当前农村私法文化建设中必须吸取这一教训,要坚持以法律方式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培养法律情感。正如椰林所言:只有斗争才是法的实践。权利斗争通常是由权利被侵害、被抑制而引发,“某一国民拥护并主张自国法的激情强度取决于为获得法所付出的劳苦和努力的量”[注][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但在我国“立法先导”的法治改革模式下,几乎找不到农民为了获得有利于自身的立法而进行抗争的先例。实际上,这种“先导立法”是一种权力层的“主动立法”,它本身不可能培养出农民积极的法律情感。就理论上而言,私法文化天然具有平等、自由、民主精神和极其温和的色彩,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法即刑”的观念,重新唤起农民对法律的好感。然而绝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只有让农民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反复法律实践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法律的关怀和保护,才能够真正产生对法律的亲近、喜好、尊重和信仰之情。在此意义上,农村私法文化的构建过程就是一个逐渐培养农民权利意识和法律情感的过程。
第三,私法观念融入农村文化的方式:挖掘、移植、整合、创新、通俗化。弗洛姆曾指出,文化是人的第二本能。由于受儒家文化和人治观念的影响,农民对现代法治观念的接纳需要一个文化渗透的过程。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他们还主要是依靠习惯、道德、宗教等规范,而不是法。那么如何把私法精神融入草根意识、把私法文化引入“村落文化”呢?笔者认为主要通过挖掘、移植、整合、创新、通俗化引入等方式来渐趋实现。尽管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法律文化整体上无法创生私法文化与现代法治,但并非是说传统法律文化中没有任何可以挖掘的元素。契约精神是私法文化的核心。对契约的敬畏、尊重和信守,强调“和同”的自由和“两共对面平章”的平等,是中国古代契约生活中出现的朴素契约意识。挖掘出这些因无人问津而久藏于传统民族文化的元素,有意识地通过文学艺术手法、电影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形式引入农村社区文化生活,扩大其影响力,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契约意识毕竟不同于契约精神,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已经证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催生契约精神,还必须进行移植、整合、创新,把外来的文化因素同化到传统文化中去。实际上,“任何文化都是一件东挪西借而凑成的文化百衲衣”[注]刘云德:《文化论纲——一个社会学的视野》,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然而这的确是一个漫长渗透的过程,任何急于求成的作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绝大多数情况下,现代私法观念是合乎情理的。然而私法语言的深奥、非生活化的术语以及学者们追求理论体系的优雅与完美的癖好,往往使普通农民难以理解其中的“法理”。因此,必须把私法精神、私法观念加以通俗化,打上草根创新、群众智慧的烙印,这是私法文化理念向民俗观念、草根精神融会的必经程序。私法就是“将普通老百姓的一种所谓的‘大众情感’加以专门化的过程。在这种‘专门化’过程中,私法理论完成了它的抽象(如法律行为及其模式),而理论与社会的结合又形成一种历史的积淀,最后便自然导致精神与制度磨合成一种私法文化”[注]易继明:《私法精神与制度选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页。。
三、农村私法文化建构要与新农村建设实践同步进行
据学界通说,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善的市民社会体系,学者们往往借鉴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实践历史来构建我国的私法文化体系。不同的时空或域点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理论上成功构建的私法文化在我国农村却没有现实生息的环境。事实上私法文化绝非理论构建所能完成,法律是实践性和斗争性的,私法文化本身就应该是法律实践的产物。就此而言,我国农村私法文化的构建必须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同步进行。
第一,私法规则须与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的“土办法”、习俗惯例等乡规民约的改善同步进行。一方面,农村社会民风淳朴、崇尚礼让,不考虑农村社会的特殊情况,私法就难以运作。美国法学家埃尔曼指出:“那些深深地根植于诸如家庭、手工业作坊和村户的传统和价值制度通常更顽强地抵制着现代法律”,而“当法律规定和根深蒂固的态度和信念之间展开鸿沟时,法律就不能改变人们的行为”[注][美]亨利·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77-278页。。就中国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国家力量尚无法将自己希冀的法律秩序和私法规则切实有效地向农村贯彻落实。私法规则往往与一些农村中的“潜规则”“土办法”相悖,而在解决农村社区纠纷中难以实际发挥调控作用。这些“土办法”“潜规则”的背后多隐藏着农村社会特殊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而“当一条规则或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注][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9页。。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私权意识的觉醒和传统农村社区模式的解体,这些农村传统社会原有的“潜规则”、“土办法”已无法解决诸如土地承包经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拆迁补偿、农村集体财产处置等现代社会纠纷,必须改善或重新建构一套规则。中国农村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决定了即使将来农村不再是“熟人社会”甚或“半熟人社会”了,它也不可能完全蜕变成“陌生人社会”,而是一个由阶层分化所形成的“多元化秩序空间”,它依然受多种规则调控,每一种规则都不可或缺。鉴于这种情况以及文化变迁在多数情况下会倾向于产生一些保留了以前的价值或态度的亚文化,私法规则必须与“潜规则”、“土办法”等多种规范优化配置、协调统一、同步建设、同步完善,才能构建出和谐的农村社会秩序。
第二,农村私法文化须在新农村建设实践中发生的村民私权与公权力的反复博弈中同步建构。权力与法律并非互斥、不可调和,恰恰相反,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就是把权力运行纳入自己的轨道,而不是排斥或摧毁权力。然而权力一旦脱离了法律的制约成为个人谋取私利、为所欲为的工具,则蜕为法律最糟糕的践踏者。故两者的制衡至关重要。在缺乏对抗性的社会结构下,“公”的因素会自然地增长,最终会将“私”的因素吞噬。私法文化是一种权利文化,私权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对公权的制约。私法文化必须以权利斗争的形式在法律实践中创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滥用公权的现象时有发生,村民权益屡遭侵害,特别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对农村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采取类似于“圈地运动”的非法“掠夺”“强征”以及拆迁过程中野蛮地使用“夜袭”“断水断电”等非法强制措施,严重侵害了村民的私权,危及民生,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这些恶性事件固化了农民心中早已形成的这样一种认识:法律是由权力来制定的,权力在法律之上,法律只是为了方便权力的行使,而不是束缚和制约权力的行使。这种状况使私法文化完全失去了生存空间。因此,只有通过村民权益与公权力的反复博弈,促使国家在从上至下策动改革的同时,加速变更政府职能,主动地、逐渐地撤出不应干涉的社会领域,农村私法文化才能得以建立。
四、建构农村私法文化须与村民自治制度同步完善
第一,私法自治与村民自治具有极其相似的理论框架。私法自治是私法的基本原理,也是私法文化的核心内容。从私法自治的理论架设看,它被市民以社会与政治国家界分为理论前提。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发展早已打破了传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二元对立的僵化、停滞的局面。一方面市民社会强调自身的独立性,要求防止国家公权力非法侵入;另一方面,市民杜会本身的不自足性又只有凭靠政治秩序化方能解决。因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应是一个“良性互动制衡的结构关系”。私法文化正是在此意义上,以不受政治国家肆意介入的市民社会为语境,主张尽可能地让老百姓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过平等地协商处理相互间的人身与财产关系。而从村民自治制度的理论架构来看,农村社区同样也是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对独立的秩序与价值空间。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自治强调在特定的政治框架下个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强调村民委员会及村民个人的独立民事主体地位;强调村落共同体内部的事务的自主决定、自主管理与自主解决,而不受来自于外部的不当干预。显然,私法自治与村民自治具有极其相似的理论框架:两者均以自治领域的划定、自治权的行使、以及政治国家对自治领域的介入方式的限制为核心内容,强调自治权不受国家权力肆意干涉,强调各自所属的“自治性结构领域”。“中国现代化两难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注]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就此而论,私法自治与村民自治亦担负着共同的使命:在中国改革开放向政治领域纵深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村民自治与私法自治”发展和培育多元自治组织,为实现我国民主政治创设社会条件。
第二,建构农村私法文化须与村民自治制度同步完善。一方面,我国农村虽没有私法自治的历史,但却已有多年的村民自治经验。众所周知,西方私法文化的发达与古代希腊的“城邦自治”实践不无渊源,作为私法文化源头的罗马法本身就是由一系列来自实践的惯例、习俗、规则、原则所构成。我国历史上虽没有“城邦自治”实践,但“村民自治”制度从1987年施行至今已有二十多年,村民自治理念在广大农村已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建构我国农村私法文化,贯彻私法自治精神奠定了实践基础。另外,村民自治实践还拓展了社会“自治性结构领域”,为私法文化的建构提供了更广阔的范域和素材,农村私法文化建构必须以村民自治实践为切入点。另一方面,从1980年广西宜州第一个村民委员会诞生,到1988年6月《村委会组织法》颁布试行并先后经过1998年11月、2010年10月两次修订实施以来,村民自治制度虽经不断完善,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宗族文化观念的困扰,自治制度被基层政权“过度侵蚀”,“权限配置机制不科学”导致“以党代民”、“以政代民” 等问题。还有相当一部分村民错误地认为,村民自治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文化是制度之母。制度的有效运作离不开基本社会价值理念的支撑。”[注]王会玲:《农村政治文化视域下的村民自治》,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页。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完善必须借助现代私法文化。将私法文化中的“私法自治”精神贯彻于村官民选、村财民理、村事民管等村民自治实践中,通过解决“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及分配、村集体债权债务、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大病医疗救助、农业四项补贴、农村公益事业”等一系列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热点问题,来不断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范围,从而促使村民自治进一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