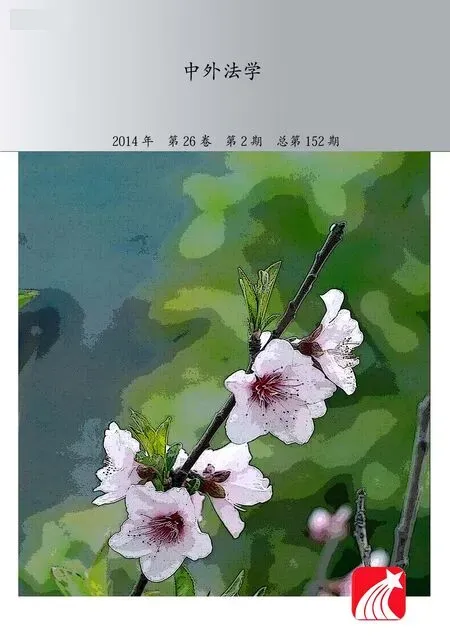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效力
常鹏翱
引 言
移转财产权的有偿交易中,为了特定目的,会有优先购买权(下称先买权)的存在。这类权利除了常见的法定先买权,如承租人对承租屋的先买权(《合同法》第23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24条,下称该解释为《租赁合同解释》)等,*此外,主要还包括按份共有人对份额的先买权(《民法通则》第78条第3款、《物权法》第101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股权的先买权(《公司法》第72条第3款、第73条)、合营企业的合营者对股权的先买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第2款)、合伙人对合伙份额的先买权(《合伙企业法》第23条)、地方政府对于低价转让土地的先买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26条第1款)等。优先购买权强调通过有偿购买来受让财产权,以此内涵为准,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的优先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第5项)、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四荒”的优先承包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7条)、职务技术成果的完成人对于该成果的优先受让权(《合同法》第326条第1款)、委托人对于专利申请权的优先受让权(《合同法》第339条第2款)、共有人对于共有的专利申请权的优先受让权(《合同法》第340条第1款)尽管未以“优先购买权”来表述,但也属于先买权。还包括当事人通过法律行为设定的先买权,即意定先买权。
涉及先买权的纠纷相当常见,*以“优先购买权”为关键词检索“北大法宝”的民事案例,届至2013年5月1日,相关案例有1521个。但由于法理模糊和规范缺失,行使先买权能产生怎样的法律效力,理论和实务莫衷一是。以房屋承租人的先买权为例,有关其法律效力的争论主要集中在:①该权利行使能否或如何在租赁双方间成立买卖合同?②能否或如何影响出租人和第三人的买卖合同?③能否或如何对抗已登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第三人?*对这些争论问题的新近研究,参见冉克平:“论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法学评论》2010年第4期;张朝阳:“论承租人先买权纠纷中第三人的保护”,《法律适用》2011年第2期。这三个问题依次展开,环环相扣,构成先买权法律效力制度的讨论框架。从不同的认识角度出发,考虑不同的制约因素,问题会有截然不同的解答,比如,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法院认为先买权属于附强制缔约义务的请求权,在出租人违反强制缔约义务将租赁物出卖给第三人的情形,承租人可以诉请公权力介入,强迫出租人依照同等条件与其签订买卖合同;*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南市民一终字第1680号民事判决书。该见解与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对《租赁合同解释》的释义完全一样,参见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页286-287。本文引用的我国大陆法院的判决均出自“北大法宝”。有法院则认为,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规定承租人在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即可以确认承租人与出租人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根据法学理论以及合同法律制度的精神,无法直接确认承租人在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即可以认定承租人与出租人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78号民事判决书。可以说,要准确回答上述问题,需尽量全面把握与先买权相关的制度,立足于规范体系的关联性进行分析,这将是本文的主要任务。
为了完成上述论述任务,本文将在我国先买权的规范、理论和实践基础上进行探讨,对我国经验的梳理因此是本文的基点。这意味着,本文不涉及先买权存续正当性的讨论,而是着眼于既有的现实展开分析。但由于规范疏缺,本文除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还将主要借鉴德国、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知识资源来补正对先买权规范的理解。这种比较分析非常注重制度功能的制约,只有功能相当的域外制度才是可借鉴的对象,而且还把它们放在我国相应制度的整体架构中进行通盘考虑,以遴选出调适成本最小的理解路径和改进方案。出于论证简约的考虑,本文不拟把我国规范以及域外经验的整体盘点当做文章的独立部分,而是在必要处点到为止,更多的笔墨将花在功能性分析和论证之上。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大陆对先买权的既有研究成果中,有不少相当注重德国经验,但在借鉴时忽略了我国规范与异域做法的整体差异,因而产生了知识错位和逻辑断裂。指出和弥补这样的缺憾,也是本文的任务和意义。
与既有的多数作品不同,本文不局限在承租人先买权或按份共有人先买权等具体的先买权,而是在整体上统一把握先买权的法律效力,把它作为先买权一般规范的内容进行处理。这种论述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各类具体的先买权不仅共享同一名称,在制度内涵上也有实质的相通性,这为先买权一般规范提供了坚实基础,在此方面,德国和瑞士的经验即为镜鉴,它们的民法均为先买权设置了一般规范(《德国民法典》第463-473条、第1094-1104条;《瑞士民法典》第681-681b条、《瑞士债法》第216-216e条),各自的理论阐述也以先买权的一般规范为重,以特殊规范为辅。而且,我国的多数作品也常逾越讨论对象的范围,从其他类型先买权规范中汲取资源,这表明尽管我国缺乏先买权的一般规范,但一体化地论述先买权的基础规范已有研究实践的支持,缺乏的只是研究先买权一般规范的自觉意识或明确形式而已。
还需指出的是,除了普通民商交易中的先买权,我国还有行政先买权,即为了实现管制目的,行政机构依法行使公共权力而排他的、有偿的取得特定标的的权利,如出于保护珍贵文物的需要,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根据文物行政部门的指定,对拟拍卖的文物有先买权(《文物保护法》第58条)。行政先买权与民商交易中的先买权有根本差异,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此外,为了凸显问题,本文只关注自由协商的、非竞价交易中的先买权。至于法院强制执行以及委托拍卖中的先买权,因为它们相当特殊,可适用的规范和理论缺乏普适性,而且它们的规范相对完整和成熟,*这方面的规范主要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14条、第16条、《租赁合同解释》第23条、《公司法》第73条、《合伙企业法》第42条第2款。带有根本性的争议问题较少,故亦不涉及。
一、 买卖合同的成立
先买权为权利人争取到购买的机会,至于如何落实该机会,即先买权的行使能否以及如何产生买卖合同,涉及先买权的定性,不同的界定会有不同的路径和后果。由于我国先买权规范仅以法定先买权为对象,而未涉及意定先买权,那么,法定权利与意定权利的定性是否相同,就是首要问题。下文分析指出它们均为形成权,一经行使就在权利人和转让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
(一)法定权利的定性
对于我国规范未予明确的先买权权利属性,理论和实务的争议颇大。在不同的交易情景,先买权的功能有所差异,如房屋承租人的先买权能维持和巩固财物使用状态,减少因主体变更所引致的使用调整成本,而按份共有人的先买权在上述功能之外,还有简化财产权属关系的作用。*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256-258。但这些功能差异是在先买权这种法律手段既定存在的前提下得到的分析结论,不影响先买权自身的定性。要完成法定先买权的定性,还应以法律规范为支点进行探讨。
先买权规范的通常表述是“权利人在同等条件下有先买权”。以房屋承租人的先买权为例,其基础规范《合同法》第230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在这种规范结构的约束下,只要无额外的特别调整,各类法定先买权应有同一属性,正是约束条件的同一性为它们提供了归纳共性的基础平台。为了论述方便,下文仍以房屋承租人的先买权为例,分析和结论对其他先买权同样适用。
立法部门对《合同法》第230条的解释指出,房屋承租人的先买权兼具形成权和请求权的双重特性。具体说来,它是附条件的形成权,以同等条件作为前提,但又是承租人对出租人出卖房屋的请求权,不能直接对抗第三人,在行使前不影响出卖人与其他人协商。*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页340。这种见解值得商榷,因为尽管从请求权和形成权存于特定主体之间的共同点来看,它们均为相对权,*von Tuhr, Der Allgemeine Teil des Deutschen Buergerlichen Rechts, Bd. I, 1957, §11, S. 218 f.; Koehler, BGB Allgemeiner Teil, 33. Aufl., 2009,§17, S. 233 f.但两者的差异大于这种共性:比如,请求权总是相对于义务人而言的,形成权则不会导致当事人产生义务;*(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143-144。又如,请求权的实现需借助义务人的协力,而形成权凭借权利人的意思表示即可涉足他人的权利范围,如债权人为保全债权可撤销债务人的行为。这些差异如此根本,以至于请求权和形成权在理论上分属不同的权利层次,前者属于原生权利,与他人的固有权利范围无关,他人的权利只能基于该他人的意思而得丧变更,后者则属于衍生权利,无需他人意思即可涉足他人的权利范围。*von Tuhr, a.a.O., S. 133 ff. 另参见申海恩:《私法中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16-24。既然如此,就不宜认定先买权融这两种权利属性于一体。
与立法部门的见解不同,理论和司法通常兵分两路,一派认为先买权是形成权,另一路将它定位成请求权,主要是附强制缔约义务的请求权。*对相关观点的简要梳理和总结,参见邓志伟、陈小珍:“承租人先买权纠纷司法裁判差异的实证分析”,《人民司法·应用》2007年第4期;张朝阳,见前注〔3〕。把先买权当成形成权,权利行使的结果固然是在租赁双方成立房屋买卖合同,但正如上文所见,即便把先买权定性为附强制缔约义务的请求权,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仍不妨碍租赁双方成立房屋买卖关系。就此而言,先买权的定性争议似纯属头脑风暴,对承租人作为房屋买受人法律地位的影响不大。其实不然,形成权与请求权的差异对租赁双方的买卖合同影响颇大。
首先,在先买权是形成权的定性上,买卖合同因承租人以同等条件购买房屋的意思表示到达出租人而成立,无需考虑出租人有无承诺的意思。当然,若承租人在诉讼中无法证明该时点,则以出租人收到法院诉讼通知的时点,作为买卖合同的成立时点。若将先买权视为附强制缔约义务的请求权,则对于先买权人的购买请求,义务人有成立合同的义务,这表明针对承租人的诉请,法院可强迫出租人承诺,从而使承租人取得买受人的地位。*奚晓明,见前注〔4〕,页286-287。不过,由于强制缔约不能替代承诺,因强制缔约成立的合同仍要遵循要约与承诺的一般规律,*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62;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页433。买卖合同在承诺生效时成立。故而,即便承租人购买房屋的意思表示到达出租人,但后者拒绝承诺的,买卖合同仍无法成立,只有通过法院生效判决的救济,才能强制成立合同。
其次,在先买权是形成权的语境中,先买权的行使直接导致买卖合同成立。《合同法》第230条足以为该法律效果提供请求权基础,法院的介入只是确认该效果,所涉诉讼应归于确认之诉。如果承租人直接诉求出租人承担该买卖合同的违约责任,在承租人先买权依法行使的情况下,法院的处理通常是确认买卖合同成立,判令出租人实际履行或损害赔偿,由此合并了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诉讼便宜相当明显。
基于先买权是附强制缔约义务的请求权的定性,仅凭《合同法》第230条不能给这种效果提供完全的根据,还需强制缔约等其他规范的配合。从德国的经验来看,强制缔约应依据《德国民法典》第249条第1款,即负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当事人应回复损害前的原状,这种责任运用到拒绝缔约的出租人身上,就是应与承租人订立合同。*Medicus/Lorenz, Schuldrecht, Bd. I, 18. Aufl., 2008, §11, S. 44.而我国缺乏这样的规范,适用强制缔约并无法可依,还需法官造法。此外,既然强制缔约要遵循要约和承诺的规律,当然还需结合相应的规范。就此看来,这种强制缔约诉讼应为给付之诉。而且,由于租赁双方的买卖合同经由该给付之诉才能成立,只要出租人未把房屋所有权移转给第三人,承租人通常无法在该诉讼中主张出租人承担违约责任。在出租人不履行合同时,承租人只能另行起诉,该诉讼仍为给付之诉。显然,两次给付之诉的操作成本已高出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合并。
综上可知,将先买权定位为形成权或请求权,不仅影响到租赁双方买卖合同成立的方式和时点,还影响到请求权基础、诉讼类型和诉讼成本。对比而言,形成权的法律定性有利于承租人尽早进入买卖关系,在司法操作上也相对简便,更为可取。据此,承租人依法行使先买权的意思表示到达出租人,双方直接成立买卖合同。
除了上述的实践优势,把先买权定性为形成权,在规范和理论上的优势也很明显,即它既不同于自由缔约机制,也不同于强制缔约机制,具有独立的地位。若把先买权当成附强制缔约义务的请求权,它就应归于强制缔约机制,在规范适用上还需求助于要约与承诺,在理论上则被强制缔约所覆盖,无独立存续的意义,但这显然不是既有规范和理论的布局。其实,强制缔约的功能旨在维护公共利益,且以当事人双方没有同等的缔约能力为前提,先买权并无这样的功能和前提,*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版,页280-285。不能与强制缔约相提并论。
此外,将法定先买权定性成形成权,也有其他法例可供参考。从先买权规范布局上看,我国台湾地区与大陆一样,均调整各类具体的法定先买权,主要包括基地所有人和承租人的先买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426条之2)、耕地承租人的先买权(我国台湾地区“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第15条)、土地共有人的先买权(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第34条之1第4项)等,它们的规范表达均为“权利人在同等条件下有先买权”,权利定性为形成权。*对例举的这三类先买权的分析,分别参见黄立主编:《民法债编各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321;史尚宽:《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244;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32号民事判决,《台湾法学杂志》2011年第183期,页 211。瑞士也有具体的法定先买权规范,主要涉及共有人及建筑权人的先买权(《瑞士民法典》第682条)、与农业经营和农地有关的亲属先买权等(《瑞士民法典》第682 a条、《瑞士建筑基地法》第42-56条),它们同为形成权。在这些个别调整之外,瑞士还有法定先买权的一般规范,即《瑞士民法典》第681-681 b条,它们属于土地所有权的限制规范,用以调整法定先买权的存续、行使等共性问题。*Schmid/Huerlimann-Kaup, Sachenrecht, 4. Aufl., 2012,§18, S. 228 ff.从节约立法成本,减少制度分歧的角度来看,瑞士这种一般与特殊结合的规范布局值得我国借鉴。
(二)意定权利的定性
意定先买权通常由当事人双方约定产生,但不排除财产权人通过特定的单方表示或遗嘱来设定。*Rey, Die Neuregelung der Vorkaufsrechte in ihren Grundzuegen, ZSR I (1994), 39, 39.无论设定基础如何,意定先买权是财产权人自我限制处分权的结果,且以同等交易条件作为内置的约束条件,其结果就是在同等条件下,先买权人可凭单方意思表示与转让人成立买卖合同,这种构造与法定先买权并无本质差异,应同为形成权。这表明,先买权的法定或意定,仅表明权利的产生机制不同,并不影响它们的同质性。
从比较法经验来看,我国台湾地区与大陆一样,也没有调整意定先买权的规范,但学理和实务将意定先买权定性为形成权,与法定先买权完全一样。*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506-507;黄茂荣主编:《民法裁判百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63。瑞士则有意定先买权的一般规范,即债法第216-216e条,它们属于土地买卖规范,*不过,这些规范可准用于动产交易。Rey, a.a.O., S. 39; Lanz, Von der wirtschaflichen Betrachtungsweise im Privatrecht, ZBJV 137 (2001), 1, 3.完全围绕形成权的定位来展开,尽管与法定先买权规范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均属于土地所有权的限制规范。*Tuor/Schnyder/Schmid/Rumo-Jungo, Das Schweizerische Zivilgesetzbuch, 13. Aufl., 2009, S. 962 ff.与瑞士一样,德国也有意定先买权的一般规范,但不同之处非常明显。德国的意定先买权规范分别位于债法和物权法,前者在民法典第463-473条,属于特种买卖规范,后者在民法典第1094-1104条。学理对债法中的意定先买权的属性有争论,通说认为是能产生法律关系的积极形成权,行使先买权的意思表示可成立买卖合同。*(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页128。物权法中的先买权以保障权利人取得不动产所有权为目的,属于不同于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取得权,只能存于不动产之上,而债法中的意定先买权无此限制。*Baur/Stuerner, Sachenrecht, 18. Aufl., 2009, §3, S. 29,§21, 280.
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先买权不像建设用地使用权或抵押权一样,被法律明定为物权。故而,受制于《物权法》第5条的物权法定,先买权在我国不是物权,当事人无法通过意定的方式来创设作为物权的先买权。这意味着,上述的德国模式不能映照我国现实,在理解我国的意定先买权时,不宜参照德国物权法的先买权规范,而应从瑞士相应规范以及德国债法的意定先买权规范寻找知识支持。
(三)合同成立的基础
法定先买权与意定先买权均是形成权,一经依法行使,无论转让人是否愿把财产权转给先买权人,径直在转让人与先买权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这说明先买权有限制转让人缔约自由的效用。需要强调的是,引发先买权行使的诱因通常是转让人的通知,它无疑是一种表示行为,目的是把转让人与第三人的买卖合同内容告知先买权人,结果导致先买权存续期间的起算,如根据《租赁合同解释》第24条第3项,承租人在出租人通知后的15日内未明确表示购买的,就不能再行使先买权。显然,通知是表示行为,但先买权逾期不能行使的法律效果取决于法律规定。这种构造符合准法律行为的结构,*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710-712。属于当中的观念通知,*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302-303。因此不成立意思表示。既然如此,通知就不是要约,因为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合同法》第14条),先买权人基于通知来行使权利的意思表示也就不是承诺。这再次表明,要约和承诺的规范因此在优先购买的场合无适用余地。
不过,若通知中除了转让人与第三人的合同信息,还有转让人愿以同等条件与先买权人成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该意思内容就符合要约的要求,先买权人对该要约的同意则为承诺,即便先买权因存续期间届满而不能行使,只要承诺在要约确定的期限或在合理期限内到达相对人,仍不妨买卖合同的成立(《合同法》第23条)。当然,这种情形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已与先买权无关。
二、 双重买卖的规制
依法行使先买权的后果,首先是在转让人与先买权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问题是,应否依据转让人与第三人的买卖合同(下称先前合同)来界定转让人与先买权人的合同内容?这种双重买卖与通常双重买卖的规制有无区别,如基于先买权的合同是否影响先前合同的效力,先买权人与第三人的法律地位是否平等?解析这些问题的结果表明,先买权的行使不影响先前合同,先买权人与第三人处在相同的买受人地位,处理双重买卖的通常机制在此仍可适用。
(一)合同内容的确定
先买权的行使以同等条件为制约要素,也就是先买权人对转让人负担的义务应与第三人负担的义务完全相同,结果就是先买权人需以先前合同的主要内容为标准,确立其与转让人的买卖合同内容。*陈自强:《民法讲义I 契约之成立与生效》,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页91-92;韩世远:《合同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页458-459。换言之,经由先买权而成立的合同,除了主体不同,在内容上与先前合同并无差别,转让人则有义务向先买权人转让财产权,先买权人则应与第三人一样,按照约定金额、期限和方式支付价款。
不过,先买权人与转让人的买卖合同毕竟成立在后,在先买权行使时,若先前合同约定的价款支付期限届满,强求先买权人遵守该期限,反而对其不利,此时应认定先买权人支付价款的期限尚未届至,并无违约问题。*(德)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吴越、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页243。与此道理相当,为了避免使转让人陷入不利,若先买权在行使时,转让人的债务履行期届至,先买权人也无违约请求权。
此外,先前合同的成立,除了市场规律的主导,特定交易目的或第三人具体情况可能也起重要作用。为了照料这些特殊因素,就应对先买权人的合同权利或义务进行适当调整,比如:第三人对转让人负担从给付义务,而该义务对先前合同有决定作用的,若该义务不能用金钱估价,先买权人又不能实际履行的,如第三人有照料转让人起居生活的义务,先买权人就不能行使先买权;若该义务可用金钱估价,权利人须支付相应金额来替代;若该义务不妨碍买卖合同订立的,就不予以考虑(《德国民法典》第466条)。又如,转让人信赖第三人的信用,给与第三人分期付款或延期付款的优待,若允许先买权人照猫画虎,就不利于转让人,先买权人应一次付款或按期付款,或对延期支付的金额提供充分担保(《德国民法典》第468条)。
(二)先前合同的效力
先买权的行使客观上导致双重买卖。在通常的双重买卖,只要符合合同的生效要件,买卖合同均有效,合同成立时间、方式等因素不影响合同效力。但在房屋承租人先买权的介入下,我国立法部门曾经认为先前合同不能生效,*胡康生,见前注〔8〕,页340。从而不同于双重买卖的通常处理方式。这种认识不足为取,不仅合同不能生效浪费了缔约成本,给无辜的第三人带来不测风险,还因为这会使同等条件失去依托,先买权的行使也就失去条件,租赁双方的买卖合同因此岌岌可危,谈何优先实际履行。不过,根据《租赁合同解释》第21条第2句,上述认识已失去市场,只要先前合同符合生效要件,就不会因租赁双方的买卖合同而无效。这样一来,先后的买卖合同相安并存,该结论对其他先买权同样适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先前合同绝对不受先买权行使的影响,为了避免转让人陷入双重买卖困境而承担违约责任,先前合同可约定以先买权的行使为解除条件,先买权的行使因此有了副产品,即先前合同的失效。由于这种约定专为转让人的利益而设,不影响转让人有偿转让财产权的真实意思,故同等条件仍然可得认定,不影响先买权的行使(《德国民法典》第465条)。该做法既维持了先买权的法律效力,又妥当照料了转让人的利益,可谓两全其美。
问题在于,若先前合同没有约定这样的解除条件,而第三人又明知有先买权的存在,能否据此推定双方默示以先买权的行使为先前合同的解除条件?德国学理和实践的态度不一,*参见朱晓哲:“论房屋承租人先买权的对抗力与损害赔偿”,载《民商法传统与现代化论文集》(下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2012年版,页700。如有持肯定态度,*Berger, in: Jauernig, 14. Aufl., 2011,§464, Rdn. 7.有持相反见解,认为是转让人而非第三人因双重买卖而陷入义务冲突困境之中,故转让人应据诚信原则事先予以防范,不宜根据第三人的明知来推定先前合同有解除条件的默示约定。*Mader, in:Staudinger, 2004,§464, Rdn. 43 ff.对此,若选用肯定态度,就意味着只要第三人明知先买权,则先买权的行使会导致先前合同失效,转让人因此摆脱了双重买卖,依约向先买权人实际履行即可,这样就无需再考虑先买权能否对抗第三人。这种做法简化了问题,好处显而易见,但问题也不少:首先,正如下文所见,如何证明第三人是否明知先买权,并非易事;其次,它不涉及不知先买权的第三人,先买权能否对抗这种第三人,还需再设规范予以规制;最后,也是更重要的,如何从第三人的明知演绎为双方默示约定解除条件,不仅要经得起意思一致达成合同的规范和法理检验,还要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或且如何救济第三人,而从我国目前的理论储备和司法实践来看,要圆满解释这种做法并妥当进行法律适用,难度不小。鉴于上述的问题,本文选用相反见解,认为第三人明知先买权不影响先前合同的效力。
(三)双重买卖的处理
在通常的双重买卖,受制于债的相对性,买卖合同的地位平等,出卖人有权决定履行的方向,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一方只能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以商品房双重买卖为例,无法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2项,下称该解释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将上述规范运用到涉及先买权的双重买卖,只要财产权尚未移转,转让人就有权选择向第三人或先买权人实际履行,实际受领的债权人由此取得财产权。这是意思自治和有权处分的结果,正当性十足,不能取得财产权的一方只能请求转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梅迪库斯,见前注〔23〕,页131-132;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怀中民再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也就是说,先买权不能排斥先前合同,转让人拥有实际履行的发球权,可依其意愿选择向权利人或向第三人实际履行。这表明,无论在合同成立还是履行,先买权并未使权利人的法律地位优于第三人。据此,只要先买权无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只要转让人向第三人实际履行,由第三人取得财产权,转让人就违背了与先买权人之间的合同,应承担损害赔偿等违约责任。
这一结论完全符合我国的现实,即法律不要求公示先买权,实践中也没有公示机制,而缺乏公示的先买权仍在相对权的行列,无法突破相对性,它只能确保权利人成为买受人,而不能否定第三人同为买受人,无法强求转让人只能向权利人实际履行。否则,既违背合同的平等性,也违背作为形成权的先买权的相对性。即便无视合同平等性的法理而限定转让人只能向权利人实际履行,但一旦不能以先买权来禁止转让人的处分行为,根据《租赁合同解释》第24条第4项,财产权在正常交易中移转给不知情的第三人,先买权仍要落空。
尽管转让人主导了实际履行,但在财产权为房屋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不动产物权的场合,先买权人仍有机会确保合同得以实际履行,从而取得财产权。比如,我国的查封登记和预告登记有禁止转让人处分不动产物权的效力,登记机构不得办理相应登记(《房屋登记办法》第22条第6项、第68条第1款;《土地登记办法》第62条第4款、第69条),先买权人通过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来办理查封登记,或就取得不动产物权的请求权申请预告登记,可使转让人无法向第三人实际履行,确保先买权人取得不动产物权。当然,无论财产保全还是预告登记,均需先买权人积极主动争取,与先买权自身的法律效果无关,第三人也能通过相同途径来实现合同目的。
在转让人不实际履行,而先买权人和第三人均诉求转让人实际履行合同时,只要任一方均未申请财产保全或预告登记,法院如何判决就是难题。根据目前的司法经验,在受让人未受领交付,也未支付价款时,先成立合同的受让人可优先取得财产权(《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第1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9-10条)。但这一做法不能适用于优先购买的情形,因为受制于同等条件,基于先买权的合同注定落后于先前合同,采用上述做法,只能使权利人吃亏。这样一来,若转让人不愿针对任一方为实际履行,尽管先买权人和第三人均有请求转让人继续履行的权利,但为了表现先买权人和第三人的平等地位,也为了打破权利争执僵局,对于转让人来说,恐怕也只能通过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来替代实际履行的责任,结局当然是先买权人和第三人均无法取得财产权。
三、 对抗效力的辨析
身陷双重买卖的转让人一旦向第三人实际履行,财产权由第三人取得,先买权能否对抗该第三人,即先买权的行使能否否定第三人对财产权的终局取得,转而由先买权人取得?我国的先买权规范基本上对此语焉不详,在解释和补充时不能不借助域外经验,但域外经验之间的差异也不小,在分析时必须慎重对待。
(一)能否对抗的标准
我国的先买权规范以法定先买权为调整对象,这是先买权规范的最突出特点,那么,能否以权利源自法定这个特点,赋予法定先买权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瑞士的经验提供了肯定答案,即法定先买权以确保先买权人取得土地所有权为终极目的,无需登记就能对抗任何人,即便第三人不知该权利的存在而从转让人处取得土地所有权,也不能求助于善意保护。*Schmid/Huerlimann-Kaup, a.a.O., S. 217.法定先买权之所以能对抗第三人,看上去似乎是其法定性的作用,但究其实质,还是因为先买权人与先买权指向的标的之间有特别的结合关系,如先买权人是长期承租人、建筑物所在土地的所有人,或与转让人有特别的人身关系,如先买权人是转让人的亲属、共有人,*Ghandchi, Das gesetzliche Vorkaufsrecht in Baurechtsverhaeltnis, 1999, S. 94; Simonius/Sutter, Schweizerisches Immobiliarsachenrecht, Bd. I, 1995, S. 350 ff.为了保护这些特别关系,法律严格限制土地所有权人的处分权,确保先买权人终局取得土地所有权,正是这一制度目的决定了先买权的对抗力。
这一点在德国也能得到验证,德国的法定先买权对第三人有无约束力,需综合规范文义和制度目的而定,如住房承租人的法定先买权没有对抗力,而公益垦荒企业对农地的法定先买权以及乡镇对建筑物的先买权就有对抗力。*Baur/Stuerner, a.a.O., S. 282.我国台湾地区同样如此,基地承租人与土地共有人均有法定先买权,但前者可对抗第三人,后者则无此效力,差异仍在于法条表述和制度目的。*参见林诚二:《民法债编各论》(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346-348。这意味着,在判断法定先买权有无对抗力时,除了考察规范表述,还必须紧紧围绕制度目的进行价值判断。
与法定先买权有无对抗力的判断不同,正如下文所见,在德国和瑞士,若不借助不动产登记,意定先买权就无对抗力。以此为准,由于我国缺乏先买权的公示机制,无论法定先买权还是意定先买权均无公示外观,在扣除无需公示即有对抗力的法定先买权后,其他的先买权均无对抗力。而为了使先买权获得对抗力,我国学理多倾向于依靠登记机制,这种制度改革方向值得肯定,但因为德国和瑞士的具体操作方案并不相同,如何取舍还需斟酌。总之,先买权有无对抗力的判断标准有二,一是从规范文义和目的出发考察法定先买权,另一是从公示与否出发考察意定先买权,这个标准同样适用于不符合前一标准的其他法定先买权。
(二)法定对抗的情形
考察法定先买权有无对抗力的初步,是看规范如何表达。在我国先买权规范中,对此明文涉及的是房屋承租人的先买权,根据《租赁合同解释》第24条第4项,它不能对抗善意购买出租屋并办理所有权登记的第三人,若能对该规范进行反面解释,结论应是先买权能对抗恶意第三人,故而,第三人善意与否是先买权有无对抗力的根源。不过,该条规范并未界定善意或恶意的判断标准或例示情形,需要细加辨析。
承租人先买权涉及房屋所有权移转这一物权法领域的事项,而《租赁合同解释》第24条第4项显然借鉴了《物权法》第106条的善意取得制度,*奚晓明,见前注〔4〕,页332-333。在善意判断方面,应借道物权法的判断标准,即以第三人是否信赖登记簿为标准。*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页290-291。据此,登记簿的权利记载是决定第三人能否取得房屋所有权及负担他物权的关键,而先买权并非物权,无法在登记簿中显示。这样一来,所有的第三人均为善意,承租人先买权也就没有对抗力。这意味着,《租赁合同解释》第24条第4项根本就无反面解释的余地。
若不采用上述标准,就需要证明第三人不知先买权的存续,或反证其明知或因过失而不知先买权的存续。要做到这一点,应先证明第三人是否知悉房屋租赁。在我国,房屋租赁以租赁合同为依托,既不以承租人占有房屋为标志,也无需登记,*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4条,我国城市房屋租赁合同应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但不登记备案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租赁合同解释》第4条第1款)。此外,尽管各地主管部门近些年在大力推动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但实践效果并不突出,参见“太原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缘何落实这样难?”, http://house.baidu.com/;“济出租房登记制名存实亡 登记者不到百分之一”,http://newhouse.hz.soufun.com/2012-08-30/8466220.htm;“房东们,租房合同备案了吗?”,http://fj.qq.com/a/20120802/000163_1.htm;“房屋出租备案遇冷,市民称回报率低交税‘吃不消’”,http://www.anhuinews.com/zhuyeguanli/system/2011/05/30/004089636.shtml;“贵阳租赁管理办法:租房需备案,市民称不现实”,http://news.gy.soufun.com/2012-02-22/7094847.htm。上述网络资料的最后访问日期均为2013年5月1日。第三人要想准确探查房屋租赁与否的信息,需支出相当的成本。即便这一步顺利完成,还需探知承租人有无先买权,因为有房屋租赁的事实并不表明承租人一定有先买权,承租人还会通过放弃先买权等形式失去权利,*我国有不少学者和实务人士把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作为承租人先买权的公示方式,以是否登记备案作为先买权有无对抗力的标准,对此除了前引的论述承租人先买权的主题论文,还可参见史浩明、张鹏:“优先购买权制度的法律技术分析”,《法学》2008年第9期;奚晓明,见前注〔4〕,页327。这种看法值得斟酌,因为租赁合同登记备案仅表明租赁关系的存在,但承租人是否必然有先买权,还要看有无权利人单方放弃或双方约定排除的抗辩,故不宜把租赁合同登记备案作为承租人先买权存续的单一标志。第三人因此又要再次支出探知成本。这个探查过程对于第三人而言,绝对是不可承受之重,只要未完成该过程,就表明第三人是有过失的不知,是可被先买权对抗的恶意第三人。这一结论无疑过度增加了第三人的成本和风险,会阻碍合同有效、价格合理的正常房屋买卖,与以登记簿为基础的不动产交易现实不符。鉴于反面解释并非纯属逻辑操作,而是具有规范目的的评价活动,*王泽鉴:《民法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204。而强调第三人的善意将过分限制正常交易,提高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和证明成本,为了削弱这种负面效应,就不宜对《租赁合同解释》第24条第4项进行反面解释,*与此相同的结论,可参见韩世远,见前注〔27〕,页461。承租人先买权因此也无对抗力。综合上述,《租赁合同解释》第24条第4项并未促成房屋承租人先买权的对抗力。
在条文表达之外,还应注重制度目的。在此方面,地方政府对土地的先买权应属典型,尽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26条第1款的条文未明确其效力,但它防止土地低价交易、维护土地转让秩序、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目的非常明显。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第4点,土地转让价低于标定价20%的,市、县政府即可行使先买权。而且,它还有增加土地储备来源(《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10条第3项)、实施公共建设规划等政府管制功能。*杨遴杰、周文兴:“中国政府土地优先购买权功能分析”,《中国土地科学》2011年第2期。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地方政府的先买权就必须有对抗力,即便交易双方的土地转让登记完成,也没有法律效力,只能由地方政府根据同等条件受让土地使用权。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优先权也应有对抗力。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所以有优先权,是为了充分发挥农地对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其能排他地取得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页92。具体到实践中,在未经书面公示的情形下,即便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取得了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不妨碍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取得人开始使用承包地两个月内主张优先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2款)。
(三)登记对抗的方案
除了上述法定对抗的情形,其他先买权无当然的对抗力。要弥补这个亏空,以德国和瑞士的经验为鉴,就需借助不动产登记,这意味着,无法借力不动产登记的先买权没有对抗力。不动产登记分为物权登记和预告登记,德国主要依靠前者,瑞士则靠后者,在这两种方案之间,我国应如何取舍,就不得不细加斟酌。
1.物权登记的方案
在德国,法定或意定先买权的区分意义不大,登记与否的分类才有根本意义。正如前文所见,德国以意定先买权为主导,分别由债法和物权法加以规范。债法调整不登记的先买权,它是相对性的形成权,与我国的先买权相同。与债法中的先买权不同,物权法调整的先买权是物权,在登记后具有对抗第三人的绝对性。据此,若忽视德国法的上述差别,直接参照德国物权法的先买权规范来解释和补充我国现有规范,所得结论就值得怀疑。以德国经验为鉴,首先需把可登记的先买权定位成物权,这将为我国限制物权增添新类型,即取得权。就我国目前的物权法规范、学理和实践来看,这种观念变革可能颇费气力,再付诸实践更需要巨大勇气,*我国法院以物权法定原则为根据,把先买权排除出物权的看法,参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衡中法民一终字第213号民事判决书。难度不小。
这一步若能实现,接下来要考虑先买权登记的法律效力。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98条第2款,先买权与预告登记的效力完全一致,由此套用旨在规范预告登记的《德国民法典》第883条、第888条,能得出以下结论:在先买权登记后,转让人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给第三人的行为妨碍了先买权的实现,该行为对先买权人无效,但对其他人有效,这就是所谓的相对无效。既然如此,对于先买权人而言,转让人仍是所有权人,先买权人有权请求转让人移转所有权,但由于第三人已登记为所有权人,仅凭转让人不足以让先买权人取得所有权,为此,先买权人有权请求第三人同意先买权人和转让人之间的所有权移转登记。
若注重德国物权法将先买权与预告登记效力一体化的做法,那么,先买权登记与预告登记的效力在我国也应相同。在我国,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登记机构不得办理处分该不动产物权的登记,预告登记因此有禁止登记的效力,顺应该法律效力,若因登记操作原因导致未经权利人同意的处分得以登记,该登记绝对无效(《物权法》第20条第1款)。*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362;程啸:《不动产登记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页547。据此,第三人在预告登记中根本不受保护,预告登记权利人只要请求转让人协力登记,就能完成预期的物权变动。套用这一思路,未经先买权人同意,登记机构不得办理处分先买权指向的不动产物权的登记,否则,该登记错误,先买权人只需转让人的协助即可取得物权。
两相对比,德国相对无效的制度安排更有意义,它不仅与禁止登记的效力安排一样,能有效实现物权变动的预期目的,而且它同时顺应了意思自治的价值,即登记向第三人警示了风险,第三人的行为是在信息完全的条件下自治决定,法律没有禁止的正当理由。而且,登记机构还无需审查登记事项是否与预告登记或先买权登记的目的相悖,便于提高登记效率。*常鹏翱:《物权程序的建构与效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36。此外,与相对无效相比,绝对无效的后果是先回复转让人的物权人地位,权利人再受让物权,法律适用稍显周折,制度成本和运作成本并不经济。再者,根据德国的实践,因为登记的公示作用,很少有人冒险与转让人再为处分交易,实际效果与禁止登记一样。*Baur/Stuerner, a.a.O., S. 261.可以说,相对无效制度巧妙地在意思自治和保全权利之间达成了平衡,更为可取。
若改用相对无效,我国的先买权登记就不应有禁止登记的效力,从而会涉及先买权人、转让人和第三人相互间的关系。根据德国经验,在先买权人和第三人之间,若第三人已通过登记受让了所有权,但尚未向转让人支付价款,则应无条件同意先买权人与转让人的所有权移转登记;若第三人已向转让人支付价款,在该价款未还给第三人时,第三人可拒绝同意登记和返还不动产(《德国民法典》第1100条)。在先买权人和转让人之间,先买权人有权按照约定请求转让人移转所有权,自己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但对于已向第三人偿还的价款,权利人不再向转让人支付(《德国民法典》第1101条)。在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第三人因先买权的行使而失去所有权的,若其未支付价款,就不再支付;若已支付价款,不得请求转让人返还,而应由先买权人偿还(《德国民法典》第1102条)。
2.预告登记的方案
与物权登记方案不同,预告登记的方案将先买权纳入预告登记之中,进而产生对抗力,这是瑞士的做法。在瑞士,法定先买权和意定先买权的区分价值最为根本,前者无需登记,后者可被预告登记(《瑞士债法》第216 a条)。未预告登记的意定先买权只能约束当事人双方,反之则能对抗取得该不动产的任意第三人(《瑞士民法典》第959条)。
与德国不同,瑞士未将先买权纳入物权,无论预告登记与否,先买权的形成权属性不变。不过,通过预告登记,先买权成为附在不动产上的负担,对此后取得该不动产所有权的任意之人均有约束力。换言之,无论谁取得不动产所有权,均要承受先买权,成为先买权的相对人,权利人可针对相对人来主张先买权,这就是预告登记的继受保护效力。*Zobl, Grundbuchrecht, 2. Aufl., 2004, S. 127.据此,预告登记给了先买权人最有力的保护,在不动产所有权未移转时,转让人是相对人,在不动产所有权移转时,受让所有权的第三人、再受让所有权的第四人等,也是先买权的相对人。只要权利人合法行使先买权,权利人与相对人就有买卖合同关系。以瑞士经验为鉴,我国就无需改变物权制度,不用在物权中增设先买权,需要调整的只是预告登记制度,这样既减少了制度改革的成本与阻力,还能稳定先买权的相对权属性,似更好用。
在调整我国的预告登记制度时,首先要扩张对象范围。我国预告登记的对象与德国一样,限于旨在将来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请求权,*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页61。而瑞士预告登记的对象是相对性的对人权,包括先买权等形成权和租赁权等债权(《瑞士民法典》第959条)。根据《物权法》第20条第1款,我国预告登记的请求权源自“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对此可扩张解释,把与不动产物权变动有关的权利内容均包含进来,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的先买权就属于该相关内容,能被预告登记。当然,这种预告登记需要当事人共同申请才能完成。此外,还应将法定先买权容括到预告登记的对象范围,并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由权利人单方申请登记。在此基础上,再改良预告登记的效力,思路与前述一致,应废止禁止登记的制度安排。
不过,因为预告登记的先买权的形成权定位不变,能约束房屋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不动产物权的受让人,受让人自动成为先买权的相对人。在先买权行使后,相对人有义务将不动产物权移转给先买权人,先买权人则有义务向相对人支付价款,引起祸端的转让人反而由此出局,无需再考虑转让人与先买权人、转让人与相对人的关系。显然,与物权登记方案相比,预告登记方案在保持先买权属性不变的前提下,扩张了相对人的范围,这既简化了法律关系,也便于实践操作,更为可取。
采用预告登记的结果,不仅使财产权的受让人成为先买权的相对人,还增加了登记机构的义务,即在预告登记后,为了最大程度地确保先买权能及时行使,登记机构有义务将所有权移转的信息通知先买权人(《瑞士民法典》第969条第1款),登记机构违背该义务导致先买权人受损的,负有赔偿责任。*Schmid/Huerlimann-Kaup, a.a.O., S. 230.
四、 结 语
我国的先买权属于形成权,在转让人与第三人成立买卖合同后,先买权的行使将导致转让人与先买权人径直成立买卖合同,其主要内容比照先前转让人与第三人的买卖合同而定,由此产生双重买卖。由于制度目的的特殊性,地方政府、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先买权能对抗第三人,包括房屋承租人的先买权、按份共有人的先买权在内的其他法定先买权以及意定先买权只能约束转让人,适用通常的双重买卖规则即可。
就此而言,我国的先买权规范看似差别不大,但实则有两派分化。一是能对抗第三人的先买权,它不仅能限制转让人的缔约自由和处分自由,在先买权人与转让人之间径直成立买卖合同,使转让人处于双重买卖之中,显示出“购买”的效力,还能确保先买权人最终取得财产权,从而表现了“优先”于第三人的效力。另一是不能对抗第三人的先买权,它只有“购买”效力而无“优先”效力。
以上结论主要针对我国的实然规范,而完善先买权的措施是引入登记机制。通过对比德国和瑞士的经验,不难看出瑞士的预告登记方案不仅更简捷,而且,需要进行制度改革的环节较少、难度较低,更为可行。据此,不能对抗第三人的先买权在预告登记后,在“购买”效力之外,还因相对人负有向先买权人移转不动产物权的义务而有“优先”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