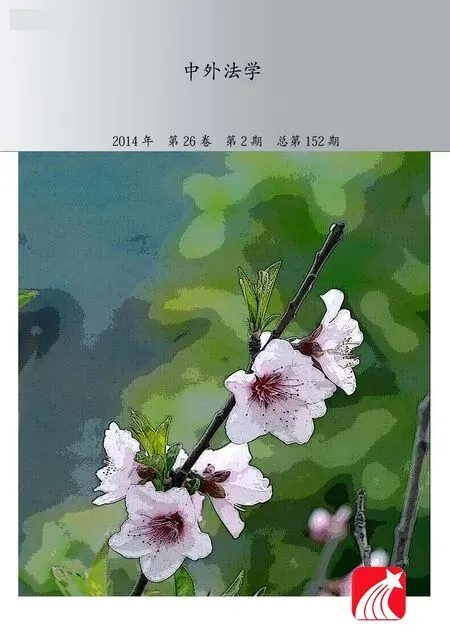也论刑法教义学的立场与冯军教授商榷
张明楷
冯军教授在《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发表了“刑法教义学的立场与方法”一文(以下简称冯文)。冯文对刑法教义学的传统、转向与趋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与分析,选择了法规范维护说的立场,并对刑法教义学的方法提出了一些见解,读后颇受启发。笔者对冯文所提出的刑法教义学的方法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但对于其选择的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则持反对意见。因此,本文仅就刑法教义学的立场提出以下商榷意见,以求教于冯军教授。
一、 刑法教义学的性质
正如冯文所言,我国刑法学界对“Strafrechtsdogmatik”这个德语词存在不同译法,但在笔者看来,译法是次要的(本文暂且使用刑法教义学的表述)。现在,刑法教义学概念的使用越来越频繁,问题是,应当如何把握刑法教义学这一概念?换言之,是否需要在刑法学或者刑法解释学之外再建立一门刑法教义学?
“法律教义学”一词源于希腊语中的“Dogma”,“Dogma这个概念首先在哲学中使用,然后在(基督教的)神学中使用。其中,Dogma是‘基本确信’、‘信仰规则’的意思,它不是通过理性的证明,而是通过权威的宣言和源自信仰的接受(Akzeptanz)来排除怀疑”。*(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页136-137。换言之,“从历史上看,法律的权威不是建立在人们对它的理性研究的态度之上的,而是借助于政治上的强者。因此,传统法学对法律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种对之深信不疑的基础上,而鲜有批判精神。一如对圣经的解释态度,法律解释学亦被归属为一种独断型解释学”。*焦宝乾:“法教义学的观念及其演变”,《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它的前提是:文献中的意义是早已固定和清楚明了的,无需我们重新加以探究。”*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16。不难看出,刑法教义学原本就是刑法解释学或者说就是狭义的刑法学。另一方面,刑法解释学之所以将刑法作为基本确信、信仰规则,还因为解释原本就是以承认被解释对象的存在为基础的,如果对之进行否认,就难以称为解释。
事实上,德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学者所撰写的刑法学教科书,就是刑法教义学的载体,当然也是刑法解释学的载体。我们不能说这本教科书属于刑法教义学,那本刑法教科书属于刑法学或者刑法解释学。正因为如此,日本刑法学界一般将“Strafrechtsdogmatik”翻译为刑法解释学。例如,大塚仁教授指出:“刑法学(Strafrechtswessenschaft; science de droit pénal),狭义上指刑法解释学(Strafrechtsdogmatik),即实定刑法的解释学。”*(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有斐阁2008年版,页7。再如,罗克辛教授的刑法教科书已经被翻译成日文,其中的“Strafrechtsdogmatik”也是被翻译为刑法解释学。*(德)克劳斯·罗克辛:《刑法总论》(第1卷),山中敬一监译,信山社2009年版,页780。也许受日本刑法理论的影响,笔者不认为刑法教义学与刑法解释学存在什么区别。
或许有人认为,“刑法教义学不得批判法条,而刑法解释学可以批判法条”。但是,这个说法难以成立。这是因为,刑法解释学既然是对实定刑法的解释,原则上就是阐明实定刑法的真实含义,而不可能以批判法条为本体。如果说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批判刑法条文,那么,只要在刑法教义学的基础上增加批判现行刑法条文的内容,就由刑法教义学变成了刑法解释学,但这是不可思议的。
冯文指出:“只要刑法是有效的,就应当服从刑法的权威,这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当然要求。任何以刑法条文的内容不符合自然法、不符合正义或者脱离社会实际为由而否定刑法效力的做法,在现代的民主法治国家里,都不会具有正当性。”并且他以罗克辛教授的法益保护说的立场不能说明德国刑法中的亲属相奸罪的处罚根据(只能主张废除此罪)而法规范维护说则能说明其处罚根据这一比较作为理由之一,论证在刑法教义学的立场上,法规范维护说优于法益保护说。问题在于,刑法教义学也好,刑法解释学也罢,是否必须绝对、全面肯定刑法条文的妥当性?尽管笔者一直反对批判刑法,但在此问题上,也不主张像冯文那样走向另一极端。
首先,即使在德国,刑法教义学一词,恐怕也不意味着无条件地将刑法的所有法条当作基本确信与信仰规则。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德国的被害人教义学(Viktimodogmatik)概念。被害人教义学通过讨论被害人的利益是否需要以及是否值得刑法保护,进而确定被害人的行为与犯罪成立的关系。*参见申柳华:《德国刑法被害人信条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93以下。但是,这种被害人教义学并不是直接将被害人或者刑法条文当作基本确信与信仰规则,实际上也是一种被害人学或者被害人解释学。
其次,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撇开技术细节,当今立法者不可能设立不合理、不妥当的刑法规范,但这一点并非绝对。制定刑法的是人而不是神,任何一部刑法典都可能存在缺陷。即使在制定的当时似乎没有缺陷,但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稍微经过一段时间也会显现出缺陷。法治应当是良法之治,而不应当是恶法之治。因此,即使在法治社会,也不得不承认人民的“小额反抗权”。正如考夫曼教授所言:
原则上(作为通常情形的案例)人民不服从是违法的,即使以非武力的方式行之。这表示在法治国家必须只有服从吗?当然不是。在法治国家也有反抗不法的合法行动。我称之为小额反抗权,在此可能会把“反抗”一词的意义认为过于强烈,然而并非如此。此类说“不”的行动会被归属为不法,真是笑话。下面提出一些例子。如果大多数的人民能够即时展现出必要的人民勇气,纳粹不法政权是否能够如此的稳固;没注意到此一问题的人,仍可去思考。*(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页227。
如果一概无条件地全面肯定刑法条文,就会绝对否定人民的“小额反抗权”,这并不符合以限制权力为核心的现代法治精神。
再次,正如冯文所言,“刑法教义学的解释结论,应当有利于维护法秩序的统一”。以刑法与宪法的关系为例:一方面,对刑法的解释结论不得违反宪法;另一方面,当对刑法条文的解释结论无论如何都会违反宪法时,就必须对该条文进行批判。正因为如此,国外不少学者总是会判断某些刑法条文是否违宪,一些法治国家还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说,以刑法条文的内容不符合宪法为由而否定刑法效力的做法,在现代的民主法治国家里具有正当性,在这种场合,就不可能服从该违宪条款的权威。
最后,正如冯文所引罗克辛教授所言:“今天,在德国刑法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见解,是不再以存在事实(例如,因果关系或者目的性行为),而是以刑法的任务和目的为导向,来建构刑法教义学体系。”不管是罗克辛教授还是雅各布斯教授,“都把刑法的目的理性作为建构刑法教义学体系的基础,试图使刑法教义学的内容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力求在刑法教义学的严密体系中实现刑法的社会机能”。可是,当刑法条文的表述不能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不能实现刑法的社会机能时,刑法教义学也不会袖手旁观。*如果说一部刑法典的规定,必然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其自身完全能够实现刑法的社会机能,罗克辛教授与雅各布斯教授提倡的以刑法的任务和目的为导向构建刑法教义学体系的观点,就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了。换言之,即使“任何以刑法条文的内容不符合自然法、不符合正义或者脱离社会实际为由而否定刑法效力的做法,在现代的民主法治国家里,都不会具有正当性”,但按照冯文的逻辑,以刑法条文的内容不符合刑事政策、不能实现刑法的任务和目的为由而否定刑法效力的做法,则具有正当性。事实上,罗克辛教授的刑法教科书并非没有批判刑法条文的内容,*Vgl., Claus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d. II, 2003, S. 66f.雅各布斯教授也认为刑法规范中存在过时的规范。*参见(德)克劳斯·罗克信:“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樊文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164-165。所以,指出法益保护说不能说明某个犯罪的可罚性根据,进而认为法益保护说在刑法教义学上存在缺陷的观点,难以被人接受。
冯文一方面认为在现代社会必须服从刑法的权威,不得以任何理由否认刑法规范的效力;另一方面又认为,现代刑法科学不再把刑法秩序看成是一种封闭的体系,刑法理论“以刑法的任务和目的为导向,来建构刑法教义学体系”。笔者完全赞成后一种观念,问题是,当对现行刑法的解释不可能实现刑法的任务和目的时,应当如何处理?这涉及解释法条与批判法条的关系,至少需要分清三种情形:
其一,通过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就完全可以实现刑法的任务与目的,而不需要对刑法条文或者其中的用语进行任何补正或者批判。就此而言,不存在任何问题。
其二,解释本身就包含了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是指必须修改法条,而是通过补正解释等方法,得出合理结论。例如,冯文所指出的,日本学者在相当长时间内将《日本刑法典》第109条第1项中的“或者”解释为“并且”即“而且”。*参见(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各论》,创文社1985年版,页194;(日)平野龙一:《刑法概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版,页247;(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有斐阁1992年版,页365。这种解释本身就包含了对该法条用语不当的批判。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在1995年将该条的“或者”修改为“并且”。
在刑法条文的表述存在缺陷的情况下,通过解释弥补其缺陷,是刑法教义学的重要内容或任务之一。事实上,将批判寓于解释之中,是刑法教义学的常态。*笔者自以为,笔者的许多精力都是在做这种事情(将批判置于解释之中),笔者的目的就是“将一部乱糟糟的刑法典解释得好好的”。但是,当刑法典规定的“数字”存在缺陷时,任何解释者都无能为力。解释者的智慧,表现在既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不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又使解释结论实现正义理念,适合司法需求。可以认为,刑法完善的路径是: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后,解释者根据正义理念与文字表述,并联系社会现实解释法律;在许多情况下,为了实现社会正义,解释者不得不对法律用语做出与其字面含义不同的解释(对刑法的解释当然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经过一段时间后,立法机关会采纳解释者的意见,修改法律的文字表述,使用更能实现正义理念的文字表述;然后,解释者再根据正义理念与文字表述,联系社会现实解释法律;再重复上面的过程。这种过程循环往复,从而使成文法更加完善,使司法不断地追求和实现正义。
其三,在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对现行刑法的法条进行合目的的解释时,只能批判该法条。这种情形虽然很罕见,但不能完全否定其存在。例如,现行《日本刑法典》第200条曾规定:“杀害自己或者配偶的直系尊亲属的,处死刑或者无期惩役。”团藤重光教授在其教科书中便指出,杀害尊亲属罪的这一规定违反《日本宪法》第14条;即使认为是合宪的,从立法论上来说,杀害尊亲属罪的规定也是欠妥当的。*参见(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各论》,创文社1964年版,页318。或许人们会说,团藤重光教授在此提出的观点,已经不是解释论,而是立法论,既然是立法论,就不是刑法解释学的内容。但是,团藤教授的结论是通过解释而得出的,刑法解释学是刑法学的本体,在一本刑法教科书中或一本有关刑法教义学的著作中,完全可能在立法论上对某个或者某些问题发表看法,如果认为团藤教授的上述观点不应当放在其教科书中,恐怕不合适。同样,在我国,完全可能认为,对组织卖淫罪规定死刑是不合理的,是违反《刑法》第5条所规定的刑法基本原则的。
“文革”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刑法学基本上是刑事立法学,主要内容是批判现行刑法,建议修改《刑法》,提出修改内容,而且这些批判基本上不是建立在解释的基础上。这不仅因为当时的解释能力低下,或许还因为“文革”期间盛行的“批判精神”依然在刑法学中起作用。正因为如此,笔者一直主张解释刑法而不是批判刑法。但是,笔者不希望刑法学走向另一极端。
以前一些法官在概念法学的约束下也能凭借熟练的技巧达到其所欲的结果这一事实已经表明,人们不能对严格受概念约束的法律适用方法的法治国价值有过高估计。早在人们在德国经历纳粹主义的法学和司法之前,考夫曼(Erich Kaufmann)即对自足和自明的教义法学提出了怀疑。他说:“纯粹技术性的法学不过是一个妓女,可以为任何人服务,也可以被任何人利用。人们早就说过,每个受到良好训练的法学家基本上都能证明任何其想要的结果,反而是那些并非法学家的正派人士不愿意利用这一技能。”*(德)莱因荷德·齐佩利乌斯:《法哲学》,金振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页294。
在此意义上说,冯文强调刑法教义学必须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必须有利于刑法的任务与目的实现,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以刑法条文的内容不符合正义或者脱离社会实际为由而对之进行批判,乃至因为刑法条文违反宪法而否定其效力的做法,*笔者也注意到,冯文的表述很巧妙。他并不是说不能批判刑法条文,而是说不得否定刑法条文的效力。这给人的感觉是在主张“恶法亦法”。笔者虽然也不一概赞成“恶法非法”,但是,也不一概赞成“恶法亦法”。在现代的民主法治国家里,也都是具有正当性的。换言之,在无论如何解释都不可能得出符合正义的结论的情况下,对某个或者某些刑法条文进行批判,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刑法》对受贿罪与贪污罪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按数额规定相同的法定刑就是不当的:在贪污或者受贿5万元至10万之间时,每增加1万元会增加1年徒刑,而在贪污或者受贿10万元以上时,每增加10万元也不一定增加1年徒刑。这样的规定,同样是不正义的。
行文至此,有必要再次重申以下观点:第一,不管是使用“刑法教义学”的概念还是使用“刑法解释学”的概念,解释学永远是刑法学的本体;对个别刑法条文的批判,并不被排斥在刑法教义学之外,尽管其只是例外,但不承认这种例外并不合适。第二,不要以为刑法教义学有别于刑法解释学,不要试图在刑法解释学之外再建立一门刑法教义学。更不要以为,将刑法解释学更名为刑法教义学之后,我们的刑法学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二、 法规范维护说的缺陷
法规范维护说不仅在刑法教义学中得出了不少新的结论,而且自成体系。在法益保护说占主导地位的刑法教义学中,法规范维护说与法益保护说的抗衡,的确有利于刑法教义学的发展。尽管如此,笔者依然认为法规范维护说存在不少缺陷。
(一)法规范维护说的话语转换没有实际意义
在笔者看来,法规范维护说虽然自成体系,但大体上是话语的转移,而且这种话语的转移没有明显的实际意义。以下,笔者将以四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例一:按照法规范维护说的观点,在乙已经被甲杀害的场合,对甲的处罚不可能保护乙的生命,只能保护被甲破坏的规范。*参见周光权:“行为无价值论的法益观”,《中外法学》2011年第5期。诚然,在乙已经被甲杀害的场合,对甲的处罚当然不是为了保护乙的生命。但是,对甲的处罚是为了保护其他人的生命,在乙死亡之前,刑法规范也保护乙的生命。另一方面,规范不可能被破坏,也不需要所谓的修复。规范一经制度化,在其存续期间,只存在是否有人违反规范的问题。只要规范没有被废止,规范就是有效的,对犯罪人的惩罚不可能是为了保护规范本身。所谓维护法规范效力,也不过是“违法必究”的另一种表述而已。但是,之所以“违法必究”,也是因为违法的行为侵害了法益,所以,维护法规范效力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真正的目的仍然是保护法益。如果说甲的行为已经破坏了规范,那么,规范曾经被破坏的事实也是无法弥补的。在这一点上,法规范维护说与法益保护说并没有实质差别,只是一种话语的转换。
例二:如后所述,虽然雅各布斯教授认为违法的本质是对法规范的否定,但为了区分未遂与既遂,仍然不能不将“利益损害”作为一种既遂标准。所以,“当不法仅作为规范违反存在时,行为无价值的确已是作为整体不法而适用的客观化。另一方面,如果在既遂犯的场合通常仅存在一项可归责的‘利益损害’作为‘一项对规范违反而言的显著事件’,则不法事实上仍以一项法益损害为基础。由此可见,雅各布斯的论题即刑法保护是规范效力而非法益,毋宁是一种术语的争论。”*Vgl., Claus Roxin, Das strafrechtliche Unrecht im Spannungsfeld von Rechtsgüterschutz und individueller Freiheit, ZStW 116 (2004), 929, 941.
例三:法规范维护说实际上只有借助法益保护说,才能说明一个刑法规范的合理性。例如,冯文指出:“惩罚受贿犯罪的理由在于:国家工作人员按照法律公正地履行职责,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基础,禁止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法律规范必须是有效的,否则,就不能保障这一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基础不被动摇。”这实际上是说,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如果不严格适用受贿罪的刑法规定,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基础就会动摇。显然,如果不借助于法益侵害,冯文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刑法要制定受贿罪的规范。再如,冯文指出,法益侵害说不能说明德国刑法中的亲属相奸罪,“相反,法规范维护说的主张者认为,只要社会还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家庭,就不允许损害家庭的构造,不允许混淆家庭成员的角色与性伴侣的角色,处罚这种角色混淆行为的法规范就具有合理性”。可是,如果冯文不借助家庭的构造这一法益,也不可能直接说明处罚亲属相奸罪的合理性。*或许有人认为,如果说“家庭的构造”也是法益,那么,法益概念的外延就过于宽泛,不能对刑事立法起限制作用。可是,就此而言,即使法益概念再宽泛,也比完全肯定刑法规范的效力因而不可能对刑事立法起限定作用的法规范维护说要好一些。
例四:法规范维护说只有借助法益保护说,才能为犯罪化(增设对新型犯罪的处罚规定)提供合理根据。当下,各国基本上都在实行犯罪化,不断增设新的犯罪。然而,法规范维护说基本上不可能为增设新的犯罪提供根据,因为这些行为并没有否定法规范。所以,只有借助法益保护说,通过证明某种行为严重侵害了国民的生活利益,才能使其犯罪化具有合理根据。
(二)法规范维护说难以对构成要件的解释起指导作用
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原则上具有违法性。正因为如此,刑法目的或者违法的本质,对构成要件的解释起着指导作用。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认为刑法目的是为了维护法规范的效力,那么,对刑法条文尤其是分则的法条,就难以进行合目的的解释,只能进行字面含义的解释,或者只能采取法实证主义的解释。可是,用“不得杀人”、“不得盗窃”这样的行为规范指导对杀人罪、盗窃罪构成要件的解释,是无济于事的。例如,当人们认为《刑法》第264条对盗窃罪的规定,就是为了维护盗窃公私财物就会受到刑罚处罚的规范效力时,就不可能对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做出合理解释;同样,当人们认为《刑法》第243条对诬告陷害罪的规定,是为了保护“不得诬告陷害他人”的规范效力时,人们就不可能知道经过被害人同意的诬告行为是否成立诬告陷害罪,也不可能知道向外国司法机关诬告本国公民的行为是否成立诬告陷害罪。
在冯文看来,故意摔碎他人一个贵重花瓶的行为,还不能因为其侵害了他人的法益而被解释为故意毁坏财物罪。
更紧要的是在这一现象中体现的法规范意义:行为人并不尊重他人的财产权,以致于像对待自己的东西一样任意地处置了他人的财物。一个其中并未显示出对法规范进行否定的法益侵害行为,并不需要刑法加以惩罚,充其量能够成为侵权行为法的调整对象,由行为人给予民事赔偿就够了。如果一个行为不仅损害了法益,*冯军教授虽然自称为纯粹的法规范维护论者,但在此,他也不得不承认,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需要损害了法益。而且显示出否定法规范的含义,那么,就会由于其被特定行为人反复实施的可能性(主要在故意犯罪中)或者由于其被不特定行为人普遍实施的可能性(主要在过失犯罪中),而需要社会用刑法来加以反应。只有在一种社会状态中,才能确保“即使我的财物被人毁坏了,我仍然拥有对它的财产权利”这种法规范意义。
问题是,这样的观点对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的解释会起作什么作用?换言之,根据冯文的观点,在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中,除了毁坏财物的行为与结果以及主观故意(倘若认为故意是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话)之外,还需要什么构成要件要素呢?回答或许是,需要行为人具有“并不尊重他人的财产权”的态度,或者其行为显示出否定法规范的态度。可是,司法机关不可能在毁坏财物的行为与结果以及主观故意之外,再寻找这种态度的素材;立法机关也不可能在毁坏财物的行为与结果以及主观故意之外,再规定这种态度的素材。结局只能由司法人员在毁坏财物的行为与结果以及主观故意之外,另行判断,但这样的判断只会导致结论的恣意性。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今变幻莫测的时代,法规范维护说难以根据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重新确定法条的目的。因为只要刑法没有修改,法规范效力就是固定不变的(如果认为法规范效力会发生变化,就必须借助于法益保护说)。但是,即使刑法没有修改,保护法益也可能发生变化,因而构成要件会发生变化。所以,法规范维护说会导致构成要件成为封闭的行为类型,难以应对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
(三)法规范维护说不利于对违法性的认识与判断
具体而言,法规范维护说在这一方面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法规范维护说难以说明违法性的本质
冯文指出:“‘法益’本身不过是人的法规范本质即自由的实现条件。法益侵害只是法规范否认的现象形态,它是法规范否认的认识工具,法规范否认才是法益侵害的本质……很明显,在刑法中,重要的并不是法益受到侵害,而是谁应当在法规范上对法益侵害负责。”在没有法益侵害或者危险就不能认定法规范否认的意义上,法益侵害的确只是法规范否认的现象形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规范维护说具有妥当性。
其一,不能因为法益侵害是法规范否认的现象形态,就据此认为,法规范否认才是犯罪或者违法的本质。这是因为,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当刑法将法益侵害作为实质理由而禁止某种行为时,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表现为法益侵害时,才可能定罪处罚。所以,法益侵害不只是一种现象形态,同时也是违法的本质。考虑一个行为为什么被刑法规范所禁止时,人们不应当做出“因为刑法规范禁止”的循环回答,相反完全可以做出“因为该行为侵害法益”的正确回答。所以,法规范否认只是认定犯罪的法律根据,而不是认定犯罪的实质根据。换言之,法规范否认只是说明了形式的违法性,而没有说明实质的违法性。
其二,法益是否受到侵害与谁应当在法规范上对法益侵害负责,并不是相矛盾的问题。法益侵害说并不认为,侵害法益的行为都是犯罪,因为刑法只能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范围内保护法益。法益侵害说也并不认为,只要行为与法益侵害事实之间具有条件关系,就要进行客观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的产生,反而是以法益保护为导向的。罗克辛教授指出:
从法益保护原则出发经过一定的必然发展衍生出了客观归责理论……因为如果刑法希望保护法益免受人为的侵害,恰恰只有藉此理论方能实现:刑法禁止威胁法益存在的不允许危险的制造,并且将以法益侵害的形式违反禁止规定的实现该种危险的情形评价为刑事不法。因此,构成要件行为始终都是以实现人为制造的不允许危险的形式存在的法益侵害行为。*Claus Roxin (Fn. 17), S. 929.
罗克辛教授还说:
刑法是为“辅助性法益保护”服务的。当人们思考如何才能通过刑法来实现对法益的保护时,借助无法反驳的逻辑就可以给出这个答案:为了受保护的法益来禁止不可容忍的风险,并且,把那个通过逾越法定的可允许风险而造成被禁止结果的人,当作一个既遂行为的行为人加以判决。在这里所说的,就已经是由我发展起来的客观归责理论的基础思想了:当一个人为刑法保护的法益创设了一个不允许的风险,并且,当这个风险在一种被禁止的结果中实现时,只要他不具有正当化根据,那么,他就是刑法性不法的行为人。*(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犯罪原理的发展与现代趋势”,王世洲译,《法学家》2007年第1期。
冯文所举的高级摩托车案,在法益保护说的立场来看,也是不可能归责的。
2.法规范维护说不能说明违法程度
对刑法规范本身的违反并无严重不严重之分,抢劫与盗窃对规范的违反程度并无不同,不能说抢劫违反了规范的全部(100%)或者100%地违反了规范,盗窃只违反了规范的60%或者只是60%地违反了规范。同样,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对规范的违反程度也是一样的,不能说故意犯罪100%地违反了规范,而过失犯罪只是违反了规范的60%。事实上,人们通常所称的违法程度不同,并不是指对规范的违反程度不同,而是指实质的违法程度不同,即侵害的法益不同,或者对相同法益的侵害程度不同。正因为故意杀害一人与过失致一人死亡所侵害的法益相同,侵害的程度相同,所以,二者的违法性相同。正因为杀人与盗窃侵害的法益不同,所以,故意杀人罪与盗窃罪的违法程度不同。
最为明显的是,法规范违反说难以说明未遂与既遂的违法程度。雅各布斯教授指出:“未遂的处罚根据是有规范违反的表现力的形成。”*Günther Jakob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 Aufl., 1993, S. 713.这种将犯罪行为的违法程度仅归入对规范的否定之中的观点,必然使违法程度在行为无价值中消耗殆尽,导致不能区分未遂与既遂的违法程度。诚然,按照雅各布斯教授的观点,规范的否定总是需要一种客观化的外在事实作为沟通过程。但是,未遂与既遂一样,都存在客观化的外在事实。从客观化过程来说,依然不能区分未遂与既遂的违法程度。反过来说,如果一方面以法规范的否定取代法益的侵害,另一方面将法益受损害当作既遂不法的前提条件,则明显自相矛盾。*Claus Roxin (Fn. 17), S. 940ff.所以,雅各布斯教授也指出:“一项对规范违反而言的显著事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与未遂相比,“既遂行为由于利益损害应具有更大的显著性”。*Vgl., Günther Jakobs (Fn. 22), S. 166.显然,如果离开法益侵害,仅凭法规范违反或者法规范否定,就无法解释未遂与既遂的违法程度。
3.法规范维护说难以说明违法阻却事由
在三阶层体系中,违法性论实际上是违法阻却事由论。假若认为违法性的实质是违反法规范,那么,在违法论中,应当讨论的是客观上违反了法规范,又由于某种原因使之成为未违反法规范的行为。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例如,正当防卫杀人的行为之所以合法,并不是因为这种行为虽然违反了禁止杀人的规范,但同时遵循了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行为规范,因为违反一个规范的行为人,不可能因为遵守了另一规范而否认其违反了一个规范。换言之,我们不可能说,如果一个行为违反了一个规范,同时遵守了一个规范时,该行为就是符合规范的。或许有人认为,正当防卫杀人时,违反了“不得杀人”的原则性规范,又符合“在正当防卫等场合除外”的例外性规范。可是,其一,为什么“不得杀人”的原则性规范受到“在正当防卫等场合除外”的例外性规范的限定呢?这显然不是将“正当防卫时可以杀人”的容许命题与“不得杀人”的禁止规范一体化所能回答的,只能是在法益存在冲突的情况下进行法益权衡的结果。同样,为什么“不得杀人”这样的原则性规范不受到“在被害人承诺的场合除外”、“在自救行为的场合除外”的例外性规范的限定呢?这恐怕也是法规范维护说难以回答的问题。其二,任何规范都会有例外,将保护充满了例外的规范作为刑法的目的,将违反充满了例外的规范作为违法性的实质,也存在疑问。因为人们难以确定,何时以原则性规范为标准做出判断,何时以例外性规范为标准得出结论。其三,法规范维护说或许认为,违法阻却事由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容许命题与禁止命题一体化。那么,可以进行正当防卫而不进行正当防卫的,可以进行紧急避险而不进行紧急避险的,是否违反了刑法规范呢?
4.法规范维护说所主张的正当防卫限度存在缺陷
冯文认为,行为是否成立正当防卫,不应当权衡法益。“应该认为,只要妇女甲用一块砖头向小偷头上砸去是阻止小偷偷窃甲放在门口的衣物的唯一手段,甲的行为就是正当防卫,因为必须实现正当防卫制度的规范目的:正确的东西不能向不正确的东西让步。”即使这是德国的通说,*例如,罗克辛教授指出:“如果向逃走中的盗窃犯开枪射击是防卫财产的唯一方法,开枪射击就是‘必要’的。”(Claus Roxin (Fn. 17), S. 679.)恐怕也难以借鉴到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来。
首先,德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强调防卫行为为避免不法侵害所必需(或防卫的必要性)。“防卫的必要性并不受防卫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与被防卫的损害之间的比例关系的拘束。”*Claus Roxin (Fn. 17), S. 679.因此,只要是避免不法侵害所必需的防卫行为,就处于必要限度之内。也正因为如此,德国刑法理论主张正当防卫的根据是个人保护与法确证原理。但是,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不仅强调防卫行为的必要性,而且强调防卫限度。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造成伤亡的防卫行为,不属于防卫过当。这一款规定虽然并不意味着凡是对非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造成伤亡的均属防卫过当,但至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防卫过当(尤其是在造成不法侵害者死亡时)。所以,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是重视防卫限度,强调法益衡量的,法规范维护说的观点难以解释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
其次,法规范维护说给人的感觉是,只要行为目的是正当的,实现目的的手段具有唯一性时,不管这个手段会造成什么结果,采用这种手段的行为都是正当的。换言之,手段是否正当只是取决于该手段是否具有唯一性,而不考虑该手段是否可能或者已经造成其他严重后果。于是,对于冯文所举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盗窃一件衣服),也可能以致人死亡的方法进行防卫,以维护行政法规范的效力。这是否符合冯文后来所说的“实践理性的衡量”标准,不无疑问。
此外,法规范维护说也难以承认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即使法规范维护说认为自己对违法性的把握是实质性的,但是,在刑法规定的违法阻却事由之外,如何说明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的合法性,也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在三阶层体系中,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的构成要件,固然违反了原则性规范,但是却不能认为其符合刑法中的例外性规范。
(四)法规范维护说导致违法与责任合而为一
冯文指出:
未达到法定年龄、不具有责任能力的人的加害行为,不属于不法侵害,因为他们根本无能力认识法规范的意义,也无能力在意义沟通的层面上否定法规范的效力,有哪位正常的人会认真对待未达到法定年龄、不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对他人行为的法律评价呢?因此,即使未达到法定年龄、不具有责任能力的人的行为损害了他人,由于他们总是值得同情者,刑法也应该保护他们。
在通说看来,法规范维护说并不承认没有责任的违法,也可以说没有区分违法与责任。
可是,“发现不法与罪责是作为构筑刑法体系与众不同的材料,依照Hans Welzel的看法,这是最近这二到三代学者在释义学上最为重要的进展;Wilfried Küper认为这个发现是刑法释义学的重大成就而无法再走回头路;此外,依西班牙法的观点来说,Santiago Mir Puig表示这个发现也建立起 los dos pilars basicos,也就是犯罪概念的二大支柱。”*(德)许迺曼:“区分不法与罪责的功能”,彭文茂译,载许玉秀、陈志辉合编:《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迺曼教授刑事法论文选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页416。违法与责任的区分,具有哲学与社会心理学的根据,与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自由保障机能相协调,有利于区分违法阻却事由与责任阻却事由,能够妥善解决共犯的成立以及从属性程度等问题,还有助于实施和完善保安处分制度。*参见张明楷:《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49以下。
如果将违法与责任合而为一,就会带来诸多问题。例如,如果将责任能力也作为违法要素考虑,那么,在甲以为乙具有责任能力而唆使其盗窃,但乙事实上没有责任能力而实施了盗窃行为时,对甲便难以处理。一方面,甲仅有教唆的故意,但教唆犯的成立以被教唆者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为前提(限制从属性说),按照法规范维护说的观点,乙没有责任能力而不能将其盗窃行为评价为违法行为,于是甲的行为不成立盗窃罪的教唆犯;另一方面,虽然从客观上看甲的行为属于间接正犯,可是甲没有间接正犯的故意,因而也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盗窃罪的间接正犯。于是,对甲只能宣告无罪。但是,这样的结论难以被人赞成。倘若要使甲承担教唆犯的刑事责任,恐怕就需要采取共犯独立性说或者最小从属性说。可是,采取独立性说,是过度的权威主义或过度关心社会防卫的结果,其理论根基与具体结论存在诸多疑问;*参见张明楷:“论教唆犯的性质”,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82以下。最小从属性说导致参与他人并不违法的行为也可能成立共犯,难以被人接受。
在笔者看来,我国传统的犯罪论体系的最主要缺陷就在于没有区分违法与责任,在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一缺陷时,冯文却主张不存在没有责任的违法,这种维护传统的犯罪论体系缺陷的做法,或许不可取。
(五)法规范维护说所采用的功能责任论存在明显缺陷
如上所述,认为法规范维护说没有区分违法与责任,是以通说观点为根据得出的结论。事实上,法规范维护说仍然有自己的责任观念。换言之,由于法规范维护说将通说的责任要素纳入违法要素,所以主张功能责任论。
功能责任论的核心主张是:要根据行为人对法规范的忠诚和社会解决冲突的可能性来决定行为人的责任,如果行为人即使忠诚于法规范也不得不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或者如果社会不依赖于行为人的责任而能够自己解消冲突,那么,就无需把责任归属于行为人……责任与预防具有共同的本质,它们只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行为人曾经是否忠诚于法规范是责任问题,行为人将来是否忠诚于法规范还是责任问题,同时,行为人是否忠诚于法规范也决定了行为人将来是否犯罪,还会影响一般公众今后对法规范的态度,因此,也是预防问题。*冯军:“刑法中的责任原则——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
功能责任论很有新意,也能解决部分难题,但是仍然存在缺陷。
首先,功能责任论将人当作维护社会利益的工具,违背了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的原则。根据功能责任论的观点,一个不法行为是否存在责任,不是取决于行为人本人的情况,而是取决于是否有必要对市民的“守法精神的修炼”,取决于是否有必要使市民“稳定对被犯罪行为扰乱的秩序的信赖”。*Vgl., Günther Jakobs, Schuld und Präwention, 1976, S. 8.于是,刑罚不是犯罪人“应得”的东西,而是积极的一般预防所需要的东西,犯罪人便成为一般预防的工具。这是因为,“应得”的概念是惩罚和正义之间的联接点。只有当一个刑罚是应得或不应得时,我们才能说它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如果我们不再考虑犯罪人应得什么,而仅仅考虑如何可以实施一般预防,我们就会将犯罪人从整个正义领域中排除出去了,我们所面对的就不再是一个人、一个权利主体,而是一个纯粹的对象。*参见(美)詹姆斯·P. 斯特巴:《实践中的道德》,李曦、蔡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518。这种将犯罪人当作工具的观念,不应当被我们采纳。
其次,功能责任论难以为责任的程度提供标准。对犯罪人科处什么样的刑罚会影响一般公众对法规范的态度,判处什么样的刑罚才能使一般公众的守法精神得到修炼、才能稳定一般公众对法秩序的信赖,在功能责任论者的内心里可能有自己的标准,但这种标准恐怕不能被法官掌握。此外,哪些不法行为不依赖于行为人的责任就能够自行解消冲突,也只能完全由法官没有约束地进行自由裁量。
最后,功能责任论不仅导致责任刑模糊不清,而且导致责任不能限制刑罚。因为根据功能责任论的观点,只要是积极的一般预防所必要的,就是在责任范围之内的。换言之,只要是积极的一般预防所必要的,即使超出了报应的限度,也是适当的刑罚。在重刑主义盛行于司法实践的我国,不可低估这种功能责任论的消极影响。正因为如此,考夫曼指出:“雅各布斯的理论的危险性是极为显著的。如果责任概念成为纯形式化的东西,其内容仅由一般预防的理念来赋予,那么,在量刑时,就可以随意超出从行为人角度来看被认为是正当的刑罚限度。因此,笔者对放弃实体的责任刑法理论的做法,想提出强烈的警告。因为在牺牲责任思想的同时,所牺牲的正是刑法的自由主义性质。”*(德)阿图尔·考夫曼:《转换期の刑法哲学》,上田健二监译,成文堂1993年版,页157-158。
综上所述,法规范维护说存在诸多缺陷,我国的刑法教义学不宜选择这种立场。
三、 法益保护说的坚持
法益保护说不仅是大陆法系国家的通说,也是英美法国家的通说。“在英语国家,刑法规范合法性的基础主要是19世纪以来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的‘损害原则’(Harm Principle)。……‘权力被合法地行使于市民社会任何成员的唯一目的,只能是阻止他对别人造成损害,即便是这种权力的运用违反该成员的意志。’”*(英)安德鲁·冯·赫尔希:“法益概念与‘损害原则’”,樊文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190。笔者一直在为法益保护说辩护,在其他论著中对法益保护说进行了许多论证。*参见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明楷:“行为无价值论的疑问——兼与周光权教授商榷”,《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张明楷:《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在此,仅就冯文对法益保护说的批判作一些回应。
(一)总体回应
冯文指出:“社会是由法规范所构造的交往系统,法规范是人们在社会中行动时的标准定位模式。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法规范,反之亦然。法规范是社会真实形态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因此,法规范总是与社会的真实性相契合。”在冯文看来,法规范维护说能够为人们提供行为准则,也有利于一般预防;法益保护说则不能为一般人提供行为准则。
诚然,刑法规范是公之于众的,任何人都可以知道其内容,如果一般人都知道刑法规范的内容,当然有利于实现一般预防。然而,这基本上只是一种假设。社会的真实现状是,一般人不可能阅读和熟记刑法规范,大多数一辈子从未犯罪的人,也可能不知道刑法规范的内容。也正因为如此,违法性的认识不是责任要素,或者说,只要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就不能阻却责任。事实上,一般人对自己行为性质的预测,并不是依赖于对刑法的禁止性规范的认识,而是依赖于对刑法禁止的核心内容(实质)即法益侵害的认识。亦即,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要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会侵害他人的利益,就足以产生反对动机。而一个人能否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侵害他人的利益,是相当简单、容易的。所以,法益保护说能够为公民提供全面的行为准则,因而更有利于一般预防。
冯文一方面说,罗克辛教授的法益保护说不能说明德国刑法处罚亲属相奸罪的合理性,因而只能主张废除此罪;另一方面又说,雅各布斯教授的法规范维护说,能够合理说明学生物的大学生在餐厅打工时,明知盘子里装的是有毒蘑菇而端给客人吃,导致客人死亡的行为(以下简称蘑菇案)是无罪的,而法益保护说则会认为该大学生的行为构成犯罪。
在此,首先要说明的是方法论问题。如果说在当下,能够论证一个行为无罪就是合理的,那么,法规范违反说能够论证亲属相奸行为有罪,因而并不合理;如果说,能够论证一个行为有罪才是合理的,那么,法规范违反说不能论证蘑菇案构成犯罪,因而也不合理。显然,不能离开所论证的案件本身来讨论问题。我们既不能认为处罚范围越宽越好,也不能认为处罚范围越窄越好,只能认为刑法应当处罚值得处罚的行为。所以,接下来需要判断的是,与亲属相奸相比,蘑菇案究竟是否值得处罚。笔者十分赞成冯文的以下表述:
既存的学说和判例关于刑法规范的理解,作为历史性先行理解,往往属于一种成熟的共同生活智慧,具有刑法文化的价值。刑法教义学者在解释刑法规范时,必须首先研究既存的学说和判例关于刑法规范的看法,不能为了追求思想自由,而把既存的学说和判例作为历史遗留的陈腐物来轻视;……要用实践理性来检验关于刑法规范的先行理解,并在权威性见解的基础上发展出更加符合社会真实状况的解释刑法规范的新方案。
但是,如果考虑到我国既存的学说与判例,考虑到哪一种结论更加符合我国社会的真实状况,恐怕认定蘑菇案不成立犯罪的理由是不充足的。
其次,将蘑菇案解释为无罪,似乎成为法规范维护说的当然结论,但是,也并非没有疑问。“因为相应的构成要件表明,刑法将对人的生命保护作为主要任务。这种保护虽然通过紧急状态法和归责规则受到限制并以适用社会的方式具体化,但是,究竟应当存在何种利益能将这种轻易可以避免的、完全不理智的故意杀人认定为无罪,却非显而易见。”*Claus Roxin (Fn. 17), S. 943.冯文指出:“有哪个客人会期待一个服务员不把有毒的蘑菇端给自己呢?客人都会期待饭馆不提供有毒食物,但是,不会期待一个服务员把自己从菜单上点的厨师做好的菜不端给自己;相反,客人期待的是服务员把自己点的厨师做好的菜赶快端给自己。”但对此并非没有反问的余地。当客人得知服务员知道是有毒蘑菇时,怎么会不期待他将蘑菇倒掉或者告诉客人真相呢?既然大学生是在饭馆打工,为什么还将饭馆意外做成的有毒蘑菇端给客人呢?显然,法规范维护说是为了得出无罪结论而对服务员的角色进行主观设定的。
再次,即使站在功能责任论的立场来考虑,亲属相奸明显属于一般预防必要性特别小的行为,即便不处罚亲属相奸行为,也不会导致人们不信赖法秩序。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处罚亲属相奸行为。这或许也是我国没有规定亲属相奸罪的原因吧!
最后,与亲属相奸罪相比,法益保护说将蘑菇案认定为犯罪,并无不当之处。服务员的行为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这种危险已经现实化,将客人死亡结果归责于其行为并没有超出杀人罪构成要件的作用范围,而且服务员具有故意。况且,在有毒有害食品泛滥的当下,对这种行为更有预防的必要性。
冯文指出:“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并不能给刑法教义学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法益保护说完全可能导致刑罚处罚范围的扩大,这是因为,把行为人危险的主观想法当作犯罪来惩罚,总是更能够保护法益的。”冯文旨在说明,如果采取法益保护说,就必须采取主观主义,但主观主义并不妥当,因此,法益保护说也不妥当。
但是,这一批判并不成立。
首先,法益保护说本身就要求行为侵害或者威胁了法益才能作为犯罪处理。如果只是有侵害法益的想法,而没有侵害法益的事实,法益保护说当然不可能主张予以刑罚处罚。
其次,不可否认的是,“‘法益保护’概念,如果不被严格解释,就有被滥用的危险”。*(日)甲斐克则:《责任原理と过失犯论》,成文堂2005年版,页85。换言之,刑法只能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发挥法益保护的机能。法益保护说从来没有主张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保护法益。例如,妇女(包括幼女)的性的自主权是值得特别保护的法益,但如果行为客观上侵害了这一法益、主观上缺乏故意,就不可能以其行为侵害了法益为由,将这种行为认定为强奸罪。即使从更为抽象的角度来说,法益保护说与罪刑法定原则也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刑法将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行为类型化为构成要件,并且将为了保护更为优越的法益之行为规定为违法阻却事由,所以,在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处罚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行为,与法益保护说完全一致。
最后,冯文用来批判法益保护说的逻辑,同样适用于法规范维护说。因为把行为人否定规范的主观想法当作犯罪来惩罚,总是更能维护规范的。可是,法规范维护说也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是认为“只有行为,并且只有一种侵犯了他人外在自由的行为,才是违反法规范的。没有引起他人外在自由的任何不利变更的行为,就完全没有违反法规范,因为法规范仅仅保障人的外在自由不被改变。”然而,冯文为法规范维护说的这一辩护,也完全可以适用于法益保护说:只有行为,并且只有一种侵犯了他人外在自由的行为,才是侵害法益的。没有引起他人外在自由的任何不利变更的行为,就完全没有侵害法益,因为刑法仅仅保障人的外在自由不被改变。
冯文指出:
法益保护说也可能导致对一些重要的刑法规定产生怀疑。例如,在打击受贿犯罪的司法活动中,很难说实现了法益保护。为打击受贿犯罪而花费的代价与取得的法律成果往往不成比例,国家机关付出了打老虎的成本,却往往仅仅抓获了几只苍蝇。而且,越是严厉地打击受贿,就越是抬高了行贿人的成本,使得受贿人用更加高超的隐蔽方式为行贿人谋取更大的利益,从而制造出更大的法益侵害。因此,惩罚受贿犯罪并不必然带来更大的社会利益。
对法益保护说的这一批判,实在难以成立。
打击受贿当然是为了保护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或者职务行为的公正性。经验表明,如果不打击受贿犯罪,受贿犯罪会更加普遍与严重。法益保护说所说的法益衡量,并不是指在打击犯罪所花费的成本与犯罪本身所损害的利益之间的衡量,而是在判断违法阻却事由时,需要对相关法益进行衡量。例如,为了使一个盗窃了1万元财物的行为人受到刑事追究,国家可能花费了2万元甚至更多的财产,这与法益保护说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也不能进行孤立地比较,还需要将惩罚一个盗窃犯所带来的预防了更多的法益侵害的事实纳入进来判断。倘若这样判断,就会发现,惩罚受贿罪、盗窃罪,依然保护了更为优越的利益。事实上,即使采取法规范维护说,行贿人与受贿人也同样会以更隐蔽的方式实施贿赂犯罪。但我们也不能据此认为法规范维护说存在缺陷。借用冯文的话说,惩罚贿赂犯罪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尽管如此也要惩罚受贿犯罪的理由在于:国家工作人员按照法律公正地履行职责,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基础,如果不处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行为,就不能保障国家工作人员公正地履行职责,就会动摇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基础。这就是法益保护说的主张。这再一次说明,法规范维护说只不过是一种话语的转换。
(二)具体事例
冯文在“立场”部分对法益保护说进行了一般性批判之后,进一步列举四例说明了法益保护说的问题性。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都不是真正的问题。
1.关于“法益保护说不能妥当解释正当防卫的对象”
冯文认为,法益保护说不能妥当解释正当防卫的对象。因为根据法益保护说以及违法与责任相区别的观点,对于未达到责任年龄、没有责任能力的人的不法侵害行为,也是可以进行正当防卫的。但是,没有责任的人“总是值得同情者,刑法也应该保护他们”,故不能对之实施正当防卫,只能进行紧急避险。但笔者认为,这一批判难以成立。
第一,事实上,将责任年龄、责任能力纳入不法要素,恰恰是我国不区分违法与责任的传统刑法理论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例如,我国坚持四要件体系的学者指出:
如果承认儿童或精神病人的侵害行为属于“违法”或“犯罪”,在理论上便可推导对之可以实行正当防卫——正当防卫的条件可以完全符合,于是会出现不利于保护这类无责任能力人权益的负面后果。对此,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如果明知侵害人系无责任能力人,则只能实行紧急避险——能躲则躲,只有万不得己才可加害侵害人;如果不知,则当然可以实行防卫。*冯亚东、邓君韬:“德国犯罪论体系对中国之启示”,《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根据这种观点,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在被害人能躲避时不是“不法侵害”,在防卫人知道时不是“不法侵害”;但在被害人不能躲避时是“不法侵害”,在防卫人不知时也是“不法侵害”。倘若如此,“不法侵害”便没有判断标准了。*倘若上述学者观点不是从精神病人的杀人行为是否属于不法侵害的角度而言,而是单纯从能否防卫的角度(对正当防卫的伦理限制)而言,就意味着上述观点肯定了精神病人的杀人行为是不法侵害。但肯定精神病人的行为属于“不法侵害”,是与四要件体系相冲突的。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属于不法侵害,由被害人能否躲避来决定,由被害人或第三者是否认识到行为人无责任能力来决定的做法,难以令人赞同。此外,在被害人知道却又不能躲避时,如何判断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是否是不法侵害呢?
第二,对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不是对不法侵害的法律制裁,只是对不法侵害的制止。没有理由认为,如果14周岁的人杀人就应当制止,而13周岁的人故意杀人就不能制止。刑法不处罚没有达到责任年龄和没有责任能力的人,本来就是对他们的保护。
第三,主张对没有达到责任年龄或者没有责任能力的人的不法侵害可以进行正当防卫,同时主张在容易回避不法侵害的场合不宜进行正当防卫,或者主张防卫时尽量控制防卫限度,并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因为正当防卫之所以阻却违法,不仅因为其是防卫行为,还因为其具有正当性。一个防卫行为是否正当,总是要根据不法侵害的具体情形特别是不法侵害人的具体情形进行判断。
第四,冯文虽然不主张对没有达到责任年龄或者没有责任能力的人进行正当防卫,但主张可以对他们进行紧急避险。可是,当人们对他们进行紧急避险时,同样会给他们的利益造成损害。这似乎并没有满足冯文所称的“刑法也应该保护他们”的观念。诚然,紧急避险只能在不得已时实施,并且其必要限度不同于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可是,如果按照法益保护说的上述观点,对没有达到责任年龄和没有责任能力的人造成的损害,不会与冯文主张的紧急避险存在明显区别。
第五,按照冯文的观点,对没有达到责任年龄和没有责任能力的人的行为不能进行法律评价,但是可以进行紧急避险。可是,在针对人的行为进行紧急避险时,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行为,而不可能针对合法行为。显然,一方面认为没有达到责任年龄和没有责任能力的人的侵害行为不违法,另一方面又认为可以对之实施紧急避险,是自相矛盾的。或许有人认为,没有达到责任年龄和没有责任能力的人的侵害行为不受法律评价,因而并不违法。可是,这种事实上承认法外空间的观点,并不能自圆其说。既然法律不关心某种行为,就意味着法律放任这种行为,进而意味着这种行为被法律所允许,当然不能对之进行紧急避险。也许有人主张,虽然可以承认没有达到责任年龄和没有责任能力的人的侵害行为也是不法侵害,但是,对他们采取紧急避险更合适。可是,如上所述,对正当防卫的适当限制就能解决这一问题,或者说能够达到与紧急避险相同的效果,而且不存在任何理论上的障碍。
2.关于“法益保护说不能妥当解释偶然防卫问题”
冯文指出:在乙偶然防卫杀人场合,
由于不存在法规范所要防止的人的死亡,所以,乙的行为既不可能成立既遂的故意杀人罪,也不可能成立未遂的故意杀人罪。但是,在乙的行为中总是表现了否定法规范的态度,并且出现了一种客观上的否定法规范的抽象危险,而这种否定法规范的态度和抽象危险在乙开枪杀害丙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不会因为丙的死亡而发生任何改变,明白地说,在乙以杀人故意持枪走向丙时,乙的行为已经因为让人产生不安全感而不能自由地前往乙走向的地方,已经侵害了他人的外在行为自由,因此,乙的行为应当成立预备的故意杀人罪。
其实,冯文关于偶然防卫的讨论,已经偷换了讨论的对象。人们在讨论偶然防卫时,并不是讨论前面的预备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只是针对实行行为而言,如同人们讨论不能犯时只是针对其有无实行行为,而不是针对前面的预备行为一样。例如,甲以杀人故意购买毒药后,却误将健身药品当作毒药提供给了被害人。在讨论甲的行为是否属于不能犯因而不可罚时,并不是讨论其前面购买毒药的行为,而是仅讨论将健身药品提供给被害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因而是否成立故意杀人未遂。至于前面的预备行为是否成立预备犯,则并非不能犯所讨论的问题。事实上,偶然防卫也是不能犯的问题。*参见Claus Roxin (Fn. 9), S. 644.讨论偶然防卫是否成立犯罪,只是针对防卫行为本身而言,并不包括前面的预备行为。所以,笔者也曾指出:“在因为行为人的认识错误,导致后来的行为没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因而不成立未遂犯的情况下,如果此前的预备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抽象危险,并达到了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则可以将预备行为认定为犯罪,但不能认定为犯罪未遂。”*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页333注〔41〕。显然,在这一点上,冯文的观点与法益保护说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按照法规范维护说的观点,能否得出偶然防卫仅成立预备犯的结论,倒还存在疑问。因为法规范维护说强调国民对法规范的忠诚,在没有认识到对方正在进行不法侵害,而以杀人故意向对方开枪射击时,恐怕不能得出行为人忠诚于法规范的结论。正因为如此,雅各布斯教授也认为,成立正当防卫要求有防卫意思。*Vgl.,Günther Jakobs (Fn. 22), S. 359.既然如此,偶然防卫就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所以,冯文所主张的偶然防卫之前的预备行为成立预备犯的观点,是否与法规范维护说相一致,不无疑问。
3.关于“法益保护说不能妥当解释特定犯罪的重罚规定”
冯文指出:“提倡法益保护说的学者认为,非法拘禁罪的‘法益是人的身体活动的自由’,但是,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将他人非法拘禁一周,与一个普通人用同样的方式将他人非法拘禁一周,对他人身体活动自由的侵害,原本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重处罚呢?法益保护说似乎难以说明。”不能不认为,冯文又偷换了评价对象。
保护法益对构成要件起指导作用,当人们说某个罪的保护法益是什么时,事实上是仅就基本犯的构成要件而言的。换言之,加重犯完全可能同时侵害了另一法益。例如,当人们说强奸罪的保护法益是性行为的自主权时,并没有包括被害人身体健康与生命,但是,强奸罪中的结果加重犯如强奸致人重伤、死亡的规定,当然同时保护了被害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所以,强奸致人重伤、死亡的加重法定刑,依然可以用法益保护说来说明,亦即,这一行为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性行为自主权,而且侵害了被害人的身体或者生命,所以,违法程度更严重,因而需要加重刑罚。基于同样的道理,当人们说非法拘禁罪的保护法益是人的身体活动的自由时,也是仅仅就基本犯而言,而不包括其中的加重犯。例如,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而加重法定刑时,不仅因为其行为剥夺了被害人的身体活动自由,而且因为其行为侵害了被害人的生命。由于行为侵害了另一重要法益,所以加重法定刑。同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非法拘禁行为时,之所以从重处罚,不仅因为其行为侵害了被害人的身体活动自由这一法益,还因为其利用职权的行为侵害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合法性、公正性。
冯文指出:“法规范维护说的解释是,对于普通人,法规范仅仅期待他不要非法拘禁他人,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规范不仅期待他不要非法拘禁他人,而且还期待他向被非法拘禁的人提供保护(将他解放出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了法规范的一个更大期待,因此,要从重处罚。”这一说法不无疑问:并不是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要对被拘禁人提供保护义务。例如,一位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于与其职务无关的非法拘禁案件,并不存在将被害人解放出来的义务。如果说有,只是道义上的义务;如果公民有期待,也只是道义上的期待。另一方面,即使冯文的说法是成立的,也离不开法益保护说。易言之,所谓期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将他解放出来”,也就是期待其保护被害人的身体活动自由这一法益。
4.关于“法益保护说也不能妥当解释非目的性犯罪的轻罚规定”
所谓法益保护说不能妥当解释非目的性犯罪的轻罚规定,无非是说法益保护说不能妥当解释目的性犯罪的重罚规定。换言之,为什么骗取贷款罪的法定刑轻于贷款诈骗罪的法定刑?
这一问题,在法益保护说内部虽然说理不同,但并非不能解答。非法占有目的是贷款诈骗罪的主观要素,却不是骗取贷款罪的主观要素。问题仅仅在于非法占有目的是什么性质的要素。如果说非法占有目的是违法要素,就表明贷款诈骗罪的违法性重于骗取贷款罪;如若说非法占有目的是责任要素,则表明贷款诈骗罪的非难可能性重于骗取贷款罪;倘若说非法占有目的中的排除意思是违法要素、利用意思是责任要素,那么,贷款诈骗罪的违法性与有责性均重于骗取贷款罪。
冯文用法规范维护说所作的回答是:“因为一个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欺骗行为与一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行为相比,在行为人想归还银行财产的意思中就表现了行为人对保护银行财产的规范的更小不尊重。”这无非是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非难可能性要素的另一种表述。
总之,冯文对法益保护说的各种批判都难以成立。在当下中国,不管是从立法角度来说,还是从司法角度而言,坚持法益保护说既有利于保护法益,也有利于保障人权。刑法教义学应当坚持法益保护说的立场。
——评黄明儒教授《刑法修改理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