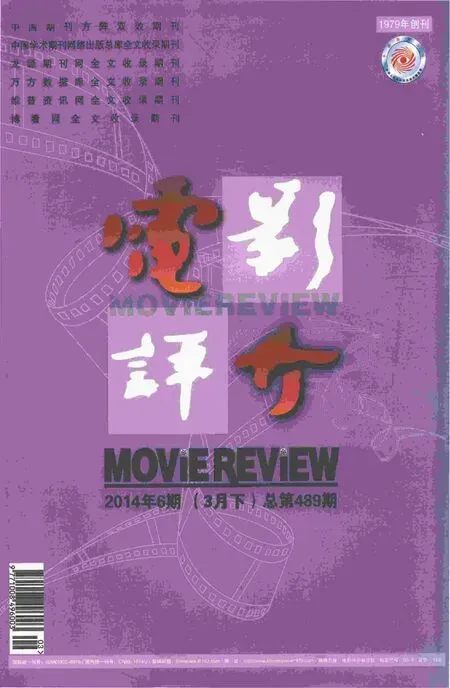文学语言与电影间意味深长的联系
□文/干瑞青,山东政法学院新闻传播系讲师
百年电影史中,电影历经从无声到有声,再到彩色,对文学语言的使用一直不离不弃。因为“一种艺术绝不可能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产生出来,而突如其来地在我们眼前出现,它必须吸收人类知识中的各种养料,并且很快的把它们消化。”[1]因此,电影人积极吸收文学精华,不断完善自己的表现符号系统。但是文学语言特有的意蕴性、凝练性等特点对电影的表达形成一种风险。这也引起我们的疑虑,正如对话的出现有可能导致银幕成为一种高雅的戏剧一样,文学语言的广泛应用是否也在导致某种更加危险的倾向呢?在风险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文学语言电影化处理,优化了电影表现符号。因此,文学语言与电影表现符号之间形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联系,风险还会继续存在,但文学语言对电影的渗透也在加剧。
一、应用文学语言符号引发的电影表现风险
文学语言的特性引发的风险在于其对意义的或明确、或揭示,这都有可能与画面形象的表达产生冲突或意义的相互抵消。
首先,文学语言一般涵义明确、具体,可以独立完成意义的传达,这有可能导致影片画面地位的降低。影片《赛德克﹒巴莱》结尾有字幕“事件之后,小岛源治煽动道泽部落,以为铁木瓦力斯报复为由,趁夜击杀在收容所里手无寸铁的老弱遗族……”这明确了人物命运的悲惨性,具有完善情节的作用,但也使道泽部落对莫那鲁道部落老弱病残的屠杀成为一种翻版图画,因为在电影中有部落之间仇杀的片段,易于产生民族仇恨等同于部落之间的仇杀的倾向。
其次,文学语言具有高度的凝练性和内涵性,以引发观众的联想、想象为宗旨。但是与电影画面的结合,便产生观众心目中“千万个哈姆雷特”与影片的“那一个哈姆雷特”的冲突。在许多影片中,导演试图运用文学语言的刺激性力量来吸引观众,如在《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开篇字幕即引用原著中文字:“从那天起,振宝就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这确实引起我们对张爱玲优美语言文字的回味,但也可能导致观众对影片中振宝角色形象的失望的风险。
再次,文学语言具有展现情感意蕴的功能,连冯小刚都直言:“电影是文学酿出的果实,每场戏都是一个果实。没有文学底蕴的电影只能是快餐式电影。”[2]抒情性的文学语言确实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增强电影的艺术感染力。电影《城南旧事》片头旁白以林海音伤感的口吻奠定了“淡淡的哀愁,浓浓的相思”的影片基调:“不思量自难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是多么想念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呀!……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迂哀而神圣吗……”这些都是经过文学润色和锤炼的语言,它们强化了影片“离别”、“忧思”的意蕴,使得感伤的情绪统摄了整部影片。但是有多少观众能记住伴随旁白的画面呢?由于观众的接受能力有限,视觉形象与语言文字形象必然产生一种抵触。
因此,文学语言的特性导致观众“像布里顿的骡子似得,不知道该吃那种料,结果反而挨了一场饿。”[3]这是一种风险,化解的办法也许只有对文学语言的电影化处理。
二、文学语言对电影表现符号的优化
文学语言对电影表现符号的优化,即文学语言的电影化处理。爱因斯坦在论述文学与电影的关系时,曾断言:“必须从‘间接的’祖宗,从具有数千年悠久传统的文学、戏剧和造型艺术那里寻找养料,来构成电影表现形式。百年电影发展史中,电影人积极吸收文学精华,对文学语言进行电影化的处理,使文学语言的应用出自‘画面表现的洪流,而非画面的流向’”[4]来完善电影的表现符号系统。
首先,电影台词、说明词等字幕形式镶嵌在画面形象中。在无声电影时期,通过插入字幕来代替演员的台词叙述,非但是技术的原因,字幕可以一种强制的姿态打破观众的收视节奏,完善形象刻画,强化观众记忆。经典的例子是《一个国家的诞生》,字幕“林肯先生的保镖站在他包厢的门口”、“为了看到演出,保镖离开了他的位置”配合画面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焦躁的保安形象;字幕“约翰·威克斯布斯”(杀手出现)强化了杀手冷峻的特写和紧握的手枪,是画面告诉我们总统太危险了……
而电影《投名状》的片头字幕“十九世纪中叶,清廷腐败,民不聊生,太平军义举反清。中国陷入长达十四年的内战,造成死亡人口近七千万。这个数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死亡人口的总和。”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嵌入画面形象,但是这些说明词是《投名状》故事产生的残酷历史背景的注脚,先通过文字引起观众对清末战乱情况想象的心理图景,然后配合后面清军与太平军战斗的影像画面予以完善。
其次,画面对文学语言的触发。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莫斯科餐厅片段中,马小军疯狂、发泄的画面,触发了旁白语言“千万别相信这是真的,我从来没有这样勇敢过,这样壮烈过……”画面停顿,使我们去关注旁白内容,这更强化了文学语言的从属地位。马小军挥舞的动作使我们的思想随之停顿下来,引导我们思考和品味:文革中那群孩子生活在一个怎样真假难辨的世界。同样,在电影《一九四二》结尾,在镜头升起的过程中,老东家与小姑娘的身影在茫茫雪原模糊消淡,从此这祖孙两个开始相依为命。看到这样的画面观众不禁产生疑问:其他人物的命运如何?这时导演用用字幕做了交代:“十六年后,留宝在洛阳找到了花枝。铃铛下落不明。”“20年后,有人在宝鸡见到星星。星星给家里捎了钱,不愿再回延津,不愿见到认识的人……”
再次,以画外音为外在形式的文学语言还具有某种结构性,配合画面形象去引导观众的注意方向。在电影《投名状》的开头,画外音内容“他说,那天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他已经死了。他还说,在这个年代,死,很容易,活着的更难……他后来跟我说,其实他不相信投名状。我问,那你相信什么?他说,他相信二哥,还有我。”我们发现“他说”、“他还说”、“他后来跟我说”组成一个比较严密的语言结构,与庞青云失魂落魄、踉跄而无目的游走的形象相配合,引导观众加深对庞青云的认识,成为揭示枭雄庞青云复杂人物性格的一个注脚。类似的还有影片《特洛伊》结尾,奥德赛王火化阿基里斯的尸体,伴随画外音“如果世人传颂我的故事,让他们说我曾与英雄同在。人的生命犹如冬麦般脆弱,但这些名字将永垂不朽。让他们说我活在赫克托时代,一名伟大的统帅;让他们说,我曾活在阿基里斯的时代……”。三个“让他们说”组成了一个声音结构,配合画面形象增添了影片摄人心魄的魅力,展现了导演由衷赞赏传奇英雄的高贵品质,也使观众对英雄的命运扼腕唏嘘不已。
最后,文学语言使得画面形象获得未有过的深度。文学语言能够诱使观众更加注意特定画面形象,去思考画面的意义。在电影《一代宗师》宫二与叶问离别的段落中,叶问(梁朝伟饰)的文学化的对白有:“人生如棋落子无悔,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恩怨,有的,只是一段缘分。你爹讲过,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灯就有人……”画面在叶问与宫二之间来回切换,画面与文学化的语言形成一种形式上的平行,但我们更关注宫二(章子怡饰)的面部特写,她是那样忧伤、凄苦,晶莹的泪花顺着脸颊流淌。这也引导我们体验宫二为父报仇,奉道,不能嫁人的孤苦的一生。
文学语言还有对画面人物形象有强化的效果。在影片《我的1919》中,观众留下印象的画面是:在阴暗的街巷中,一辆马车走来,马车中的顾维钧微低着头,面色凝重。文学色彩浓厚的旁白只是强化顾维钧内心压力的一个外在标示。“……我把即将召开的和会视为中国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对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这段旁白的感染力量强化的是在面临弱国无外交的情形下,一个中国外交官奋争而又无奈的形象。
文学语言对画面的优化处理的形式还有很多,其重点在于突出画面在电影中的主导地位,因为只有文学语言辅助画面,从属于画面才符合电影的本体特征。
三、文学语言与电影表现符号未来关系
如前所述,文学语言符号高度凝练,内涵丰富,具有一种含蓄之美。同时,文学语言具有展现情感意蕴深厚,能够传达导演或编剧的态度与情感。未来,电影内容的庞杂,电影表现形式的丰富,只有文学语言才能把电影人从累赘的、为情节纠葛的清晰而设置的画面中解放出来。
首先,在文学改编的电影中,为了忠实于原著,体现原著的思想,达到原著的表达效果,影片的视觉表现符号将进一步接受文学语言的指导。导演或编剧会对影片中景别、角度、焦距等等更加精益求精,以更忠实于原著,给观众创造一种原汁原味的感觉。如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改编自刘以鬯的《对倒》,“对倒”指的是一正一负的双联邮票。刘以鬯将“对倒”的意念转化为一正一负的手法,小说形成一种并行发展的双线格局。为了与小说对应,影片在结构上取意对倒,让周慕云和苏丽珍在扮演自身的同时,还扮演对方的伴侣,而且在镜头调度中也有“对倒”意涵的体现,如镜头段落:幽暗的路灯中,细雨飘落,周慕云站在昏暗的楼道中,低头吸烟,火红的烟头闪亮……另一边,苏丽珍低头揉搓着手帕,看一下老板,等待,雨中张望……。
其次,文学语言会以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去诠释时代环境,对缺失的画面形象具有补充作用,就像弗拉哈迪说的,“我当年要能给《北方的那努克》配上声音就好了……北方尖厉的风声和狗的吠叫声,将使人对那个地区产生完整的感觉。”[5]在电影《一九四二》中,片头画外音“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这段旁白源于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的第一章,基本忠实于原著,揭示在一九四二的世界环境中,河南发生的吃的问题无非是小事一桩。片尾字幕“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失去大陆,退踞台湾”表示那些他认为本就无用、是社会负担的受灾百姓,最终改变了他的命运,改变了历史的方向。
再次,文学语言参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提高电影的国际传播影响力。历史题材电影的拍摄,再现历史真实,文学作品成为重要的资料库。谷剑尘在《一九二六年之国产电影》中所说的,“拍古装戏如宋朝戏在服饰、表演动作方面需要下功夫去考据。至于对话,只要模仿宋人小说的笔法就行了。”[6]因此,在许多古装剧中,我们看到了大量取材于古典文学文本的台词。根据古典名著《聊斋志异》改编的电影《画皮》中,庞勇边巡街边歌唱“穿金甲兮,遇强愈强;抛头颅兮,为爹为娘;洒热血兮…”其中的“兮”字是古诗辞赋中典型助词,虽然这几句唱游诗出处不详,但它契合了中国古典四言古诗的用法。在《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中武昭登基段落中,宣召的画外音是“应天顺时,受兹明命。天后武氏,睿哲温恭,宽仁慈惠。今克成大统,即皇帝位,布告天下,咸使闻之。”这完全取材于我国古代圣旨的用语,符合圣旨行文洗练,基本四字成句的惯例,其无可增删的程度喻示皇权神圣和权威。这些文学语言带有强烈的中国古典文学特征,对传播我国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在文学改编电影作品中,原著中的对白、修辞会在电影中不时闪现。如吴宇森导演的《赤壁》中,不但情节取材原著,如“群英会蒋干中计”、“草船借箭”等。台词中也不断有“贤臣择主而事”、“主公”、“郡主”、“细作”、“鼠辈”等等,这些都得益于古典文学名著或者直接引用文学小说中的词语。因此,电影中文学语言特别是古典词汇运用的良好有助于提升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我们更期待文学语言进一步优化电影表现符号,换言之,电影的语言文字符号缺少了文学性,无异于切断了一条与观众沟通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要警惕,文学语言引发的电影表现符号的风险也许会继续存在,这与导演有直接的关系,也与艺术发展和社会潮流有关。
[1](法)萨杜尔(Sadolnl,G.).世界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125.
[2]叶辰亮.作家对话:文学与电影 谁是更真实的虚构[N].文汇报,2012-08-17.
[3][4][5](德)齐格佛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M].邵牧君,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93,113,143.
[6]徐文明.题材流变与身体景观:1927—1937年的中国清代题材影片创作[J].当代电影,2012(8):8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