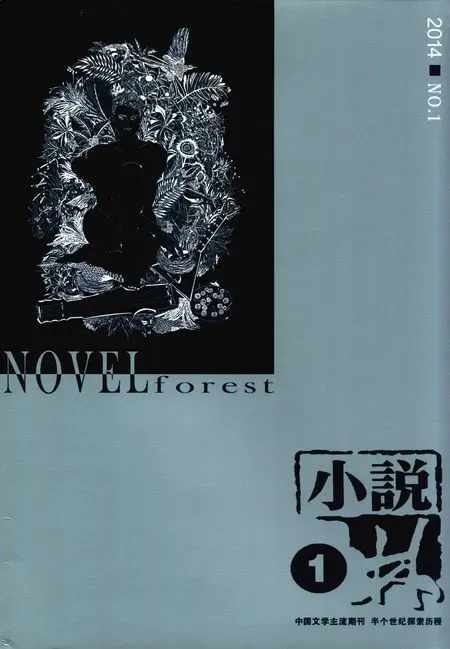剧本写在小说中
——评陈鹏的中篇小说《六一节》
◎海力洪
剧本写在小说中
——评陈鹏的中篇小说《六一节》
◎海力洪
陈鹏小说《六一节》中的“我”,是个不入流的影视人。似乎是为揭示小说中“我”拙劣的文化身份,《六一节》中插入一个名为《万国大厦》的影视短剧剧本,“我”在小说中一“走神”,就会按场景顺序“构思”它。从文本看,《万国大厦》可谓标准且规范的剧本,但若以专业标准视之,《万国大厦》的编剧水准则不及格,可归为缺少才华的平庸之作。于是小说中“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成色如何,便有了个切实的依凭。
但问题随之出现——结构风险。《六一节》看似中篇小说的规模,实为剧本《万国大厦》和短篇小说《六一节》的组接。考虑到两者之间一念相牵(“走神”即“构思”)的结构关系如此脆弱,似乎甚至无法在“组接”前冠以“有效”“有机”之类的词。此外,读者反应——我们谁会去读剧本呢?那枯燥无味的拍摄手册!这样一来便可能导致《万国大厦》被忽略、无视(跳过不读),或遭到抱怨(损坏了小说的情节节奏)。的确,我们都很清楚剧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是看过无数电影,却从没想要读一行剧本的资深影迷;或,我们看看小说就够了,请不要拿乏味的剧本来搅了雅兴吧……
有鉴于此,对《万国大厦》在《六一节》中顽强的存在,我给小说读者的阅读建议如下:先略过剧本,把小说阅尽,再回过头来,将以楷体字列印的《万国大厦》耐着性子读完。那么,便可能会发现《万国大厦》的故事其实颇为有趣。虽说此间剧本文本与小说文本两相脱节的风险极大,但这风险的大小,显然又与小说家进行写作实验的热情成正比。所以,不论成功与否,对于愈发罕见“胆大妄为”的先锋写作而言,此举可被证为某种久违的正向姿态。
还是让我们先前往一探《万国大厦》,看看与小说《六一节》“骨肉分离”后的纯粹剧本有何奥妙吧。《万国大厦》的李,虽说是“我”“走神”时虚构出的男主人公,但在剧本中却是不折不扣独立的角色。在剧中,李数次手捧花盆,坐上出租车前往环西路8号空房平台中,向一不出场的神秘人物“宝宝”献花。此举剧情无交代,可称莫名其妙;而李途中必经一烂尾楼达十三年的万国大厦,正所谓道听途说——前后三名载李的出租车司机向李讲述了不同的“烂尾”缘由。其后,李反客为主,客串出租车司机(此设置表明“构思”中的“我”学得些编剧皮毛:身份置换戏剧性足!)两小时当中,两位打的人再添“烂尾”新说。至此,反反复复,共得“烂尾”小故事计五则。李好奇心起,最后,深入一探万国大厦,遇不测事,惊惧急奔,摔倒在深坑里,渐渐死去。剧情以莫名其妙始,以倍加莫名其妙终。李的行为动作不交代动机、场景重复且情节缺乏逻辑,以此手法营造出的那种“神秘”感,颇显粗糙和廉价。
然而,又一有意味的问题随之产生:小说家为结构和小说实验计,执著“组接”剧本,那么,《六一节》之内,是否有套接一个不那么廉价,更完善精致些的剧本的必要或可能?换言之,《万国大厦》在《六一节》内显出如此这般不堪的剧作样貌,是“刻意”还是“无力”为之呢?
若以小说为本,又着眼于情节的真实,对于《万国大厦》的剧本质量,就不必苛求了。我们在小说里读到,剧本源起于开篇“我”对身边女人心生厌倦之时,接续于此后乱哄哄一片集会抗议的人群中。此间“我”售卖口罩双重牟利、与便衣警察周旋乃至跟失足女搞车震时,仍“构思”不缀。常言道一心不能二用,大事件当前,微电影能写出39场戏,已属不易。和影视圈中拍时代剧要“做旧”一样,作家写小说为实现意图把内中的剧本“做坏”, 似同为匠心所在。
这样看来,《万国大厦》在《六一节》中的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一个好的剧本,而在于其呈现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当“我”意欲将现实世界推到身后时,便自己构造出了这么一个虚拟世界。《万国大厦》是超现实的,被小说化了的,很像一个噩梦的场景。其实与一般影视剧不同,《万国大厦》主角并非人,而是物,是万国大厦本身。李之流,无非是受其魔力控制的提线木偶。那么,万国大厦的本质究竟为何呢?
万国大厦既是一个低劣的社会谣言,也是一则令人生畏的都市传说。它与当下流传在中国各地此起彼伏的“醉后盗割肾”“被扎艾滋针”“公交上的幽灵”等一样,体现出一种变形了的时代焦虑。《万国大厦》更放大了恐怖的心理因素——空间恐惧与血腥暴力。于不同人的叙说中,万国大厦在超现实之外,仿佛又渐渐获得了某种充满污秽的现实感,这样的一种现实性与“我”的生存感受相吻合,也与当下中国都市的氛围合拍。
于是,《万国大厦》成为《六一节》叙事的心理背景,成为小说所写的“人人为己”的现实世界的注脚。在那一小撮为公义而行的人群中,“我”是如此好歹不分、立场不明,又是如此利欲与色欲熏心……皆因我生存在一个催生无数“万国大厦”的时代,而“我”的人生,像此地千千万万的人一样,早已经“烂尾”。
海力洪,出版小说《药片的精神》、《左和右》、《夜泳》等多部。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执教于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