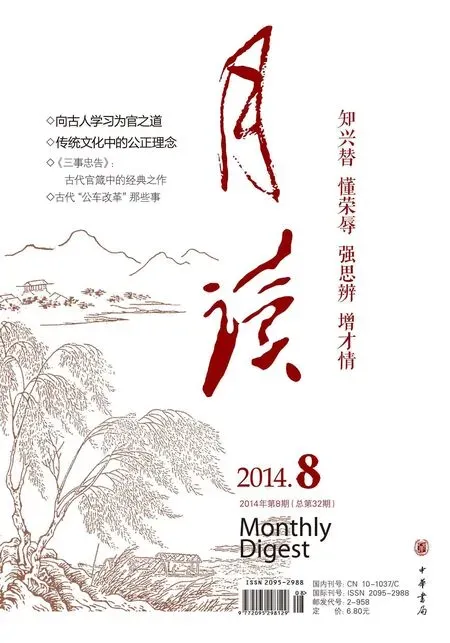相较后的抉择:陈嘉庚眼中的重庆和延安
◎ 吴晓波
相较后的抉择:陈嘉庚眼中的重庆和延安
◎ 吴晓波
重庆:官贪将骄,民不聊生
1940年3月26日,由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的南侨回国慰问团一行50人,乘飞机抵达重庆珊瑚坝机场。抗战期间,华侨的无私捐献是除了美援之外最重要的外援。当时,国民政府为支撑财政不断发行救国公债,国内民众虽出全力却自救不暇,1940年的公债认购仅得800万元,可谓杯水车薪。在这样的情形下,华侨成为被寄予厚望的一个群体,从1937年至1942年间,南洋华侨认购公债达11亿元,可谓居功阙伟。而在南洋诸国日夜奔波、总其事者,就是67岁的陈嘉庚。此次,慰问团冒着被日机击落的危险归国,当然是大大激励国民士气。当日,200多个团体的上千人到机场热烈欢迎。
慰问团抵重庆后,自蒋介石以降所有的党国政要纷纷宴请。谁料,正是这份热情让陈嘉庚的担忧一日盛过一日,他在这里看到的景象竟是歌舞升平,官贪将骄,民不聊生。
慰问团一行下榻的是当时重庆最豪华的饭店嘉陵宾馆,有人告诉陈嘉庚,这是孔祥熙的私人财产,他十分惊讶不敢相信。在孔祥熙前来拜访时,他当场问及真假,孔祥熙坦然承认,陈嘉庚在当晚日记中写道:“余至此深讶我国政治,与外国相差甚远。英国政府公务员,不但不得私设营业,亦不得买卖公司股份,虽地皮业产,银行及政府债券亦然,防弊甚严,违者立即开革科罚……”陈氏的这段感慨很发人深思,自李鸿章、盛宣怀办洋务以来,官商身份纠缠,国事私事不分,一直是众所周知的积弊,这也是中国改革常常变形和倒退的重要根源之一。
陈嘉庚在重庆60多天,无日不被邀请赴宴,常常一天要赶两场,因而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感叹。有一次,他去参观成都武侯祠,却看到旁边正在为死去的前任四川省主席刘湘建造硕大的坟墓。他很天真地问:“试问刘湘后人款自何来,是否民脂民膏?”陪同者无人敢应。他还听说,四川农民的钱粮税竟已经征收到了民国七十年(1981年),不由大为咂舌。在全国经济学社的年会上,陈嘉庚作演讲,对国内政局表达了忧虑:“光复之后,军阀劣绅,土豪盗匪,欺凌抢劫,甚于满清,华侨几于视家乡为畏途,空身回省庐墓尚不自安,奚敢言及投资祖国哉?”在他演讲之后,经济学家马寅初上台继续控诉:“现国家不幸遭强敌侵略,危险万状。而保管外汇之人,却不顾大局,盗窃外币,贪利无厌……”坐在陈嘉庚旁边的四川平民银行总经理周季梅悄悄对陈嘉庚说:“这种话除了马寅初,已无人敢说。”
鲜明的对照:延安军民的亲密融洽
在大后方观察近两个月后,陈嘉庚的笑容日渐消失,最后竟心事重重。他在后来出版的《南洋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几十年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可忧虑。”正是在失望之下,陈嘉庚把目光投向了西北。5月底,他辗转抵达陕西延安。
他受到了与重庆一样热烈的欢迎,自毛泽东以降的中共高层全数接待了慰问团。当时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部队很感好奇与神秘。陈嘉庚在延安参观了七天,他看得十分细致,特别是关于商业的部分。
延安城外一里路,有一条百米长的小街,当地军民称它为“新市场”,是唯一的商业街。陈嘉庚专门前往观察。这里有百多家商铺,还有一家照相馆,土特产不少而工业品奇缺。陈嘉庚问一个店主:“政府有没有存货公卖?”答:“没有,都是我们自行经营的。”又问:“这里大商店大概有多少资本?”答:“大商店很少,听说有十万和二三十万的,大多是收买土产生意的。”回到招待所后,陈嘉庚遇到从南洋归国投奔延安的女学生,又悄悄问:“这里有没有国家经营的店铺?”女学生答:“没有国营的,所有的店铺都是民营的。”
最让陈嘉庚感慨的是延安军民的亲密融洽,他亲眼看到总司令朱德杂坐在勤务兵的人群中,狼吞虎咽地吃同样的杂粮。他与毛泽东闲聊南洋趣闻时,很多人都跑来围听,顷刻座位告满。有个勤务兵就往毛泽东所坐的长板凳上挤,毛泽东扭头看他一看,自己移开一些,让他坐了下来。这些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恰与重庆的官气森严形成了鲜明对照。
客观地说,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经济政策,因为身处在野,没有任何的包袱和既得利益,因而,所有经济关系均十分简单。也正是这种清明简快的状态,使很多到过延安的人顿时有了深刻的印象和好感。
延安之行后,陈嘉庚对国共两党形成了新的看法。回到南洋,他随即发动商人捐献了一批药品和医用器材运到延安。而他在大陆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带头驱赶了家乡福建省的国民党大员。
〔选自《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