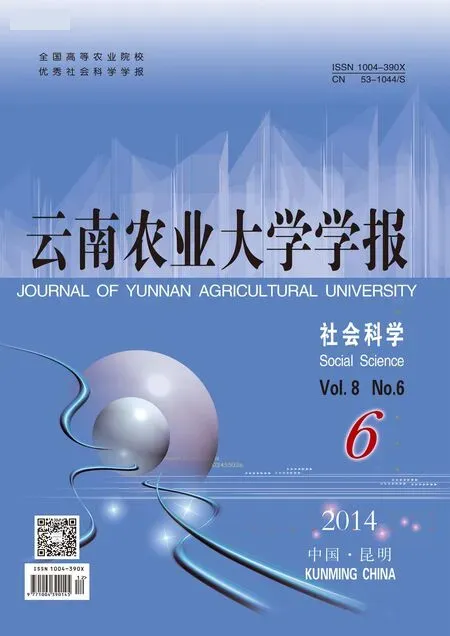取法自然:纳西东巴文美学风格分析
王树勋,娥 满
(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纳西东巴文是丽江一带纳西族东巴教的祭司——东巴使用的一种文字,纳西语称作“sel jel lv jel”,即“斯究鲁究”。所谓“jel”,是痕迹的意思,也就是文字; “sel”为木, “jel”为石[1],可以看出,东巴文即“木石上的痕迹”或“木石上的记录”,引申为“见木画木,见石画石”[2]。尽管东巴文准确的形成年代仍旧难以确定,但目前研究者已初步达成共识,认为它是在公元7世纪纳西族定居丽江以后才开始形成的,并且东巴象形文字的形成与东巴教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纳西族在唐代受到过汉、藏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使得其原氏族内部信奉的原始宗教在西藏苯教、藏传佛教、汉地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下发展成为具有纳西族社会特点的东巴教[3]。继而,东巴教的祭司东巴便运用稍早形成的象形文字开始写经传教,可以说,东巴文正是通过东巴经而得以流传至今。
极具象形形态的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象形文字,作为一种以图像的方法写成的文字,东巴文因其本身独特的造字特征,有着甚为重要的艺术审美价值,笔者在《纳西东巴文的美学内蕴》一文中已对其美学特色做过浅显的探究[4]。文章中笔者更多地是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分析东巴文的线条感和形体动态之美,论述主要停留于东巴书法的外在形式,而对潜藏在文字后面的审美观念,尤其是观念蕴涵的深厚的思维惯习与人文精神几未谈及。事实上,文字的艺术性与审美性必须要与其背后的人文精神与民族文化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被认知,也只有如此,东巴文才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字符号,而是富于生命与灵魂的“有意味的形式”①一般认为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说将形式视为艺术的本体,强调艺术必须找到对应的恰当的表现形式,例如文学之语言,音乐之声音,绘画之色彩等,在没有找到对应的表现形式之前,都可以看作是非艺术的东西,故贝尔被归为形式主义美学家。事实上,形式并不天然就带出“意味”。形式也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内容才可能而直接成为本体。富于“灵魂”的形式才是“有意味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记录了纳西文化深刻变迁的东巴文可以成为贝尔学说的注脚。。
一、“林泉之心”
在纳西族的口传神话中,有纳西先民“看见山就写山,看见人就写人,看见牛就写牛,看见马就画马”[5]的传说,这说明东巴文是纳西先民以其所见所闻而模仿、描绘其形状所形成的文字系统,可以说,东巴文的形成过程与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所说的“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及“庖羲氏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比类万物之情”[6]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着直接观照自然的态度而创造文字,自然山水的审美形象才能渗透在东巴文中,从而东巴文从一开始也就具有了艺术审美的属性。在直接观照自然的同时,纳西先民还有着审美的心胸,也就是郭熙所谓的“林泉之心”,“看山水亦有体。以林泉之心临之则价高,以骄侈之目临之则价低。”[7]这里所说的“价高”、“价低”即是指自然山水的审美价值,没有审美的心胸就无法实现审美的观照,即便是直接面对自然,也无法发现审美的自然,更不可能将自然山水迹化为表现宇宙动力、生命力量与人的情感的东巴文。
“林泉之心”,即审美的心胸,是实现审美观照的主观精神条件。这个审美的心胸,对东巴文的创造是必要的,纳西先民不仅要发现审美的自然,而且要创造审美意象—东巴文,尽管创作者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审美考虑,东巴文也是集宗教、道德、政治、审美于一身的整体,但毕竟已有“审美”存在其中。纳西先民造字,是从实用的目的出发,但这并不妨碍东巴文本身的美学特色,因为创造者的心胸不是利欲的心胸,不是狭隘、死寂的心胸,而是始终纯洁、愉悦的心胸,是充满勃勃生机的心胸,在他们眼中,自然山水皆有生命。有了这种审美的心胸,才能见出审美形象,在此前提下,使自然山水与自身的情感相融合,从而生成富有审美内涵的东巴文。
以东巴象形文字为主体的东巴文化的载体是东巴教。作为一种文化,东巴教起着组织族群、统一民众意识的作用,“没有文化模式,即有意义的符号组织系统的指引,人的行为就不可控制,就将是一堆无效行动和狂暴情感的混杂物,他的经验也是模糊不清的”[8]。集纳西传统文化之大成的东巴教对纳西族的意识形态、文化习俗、民族性格、审美理念等有着重大的影响,它是在纳西族原始部落时期的信仰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东巴教的主要特征是信奉万物有灵、自然崇拜、多神崇拜,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由于同时融入了藏族苯教、喇嘛教和汉族道家思想的内容,所以东巴教是具有多元文化因素的综合性民族宗教,但它仍然保持了其原始宗教的突出特点和基本风貌,强调多神崇拜,没有至上神。东巴教的神灵构成形式和并未形成体系的教义中的文化互渗现象反映了多种宗教因素在东巴教中的掺杂、糅合,这样的宗教文化传统体现了东巴教开放、亲和及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特点[3],也使得在宗教文化影响下的纳西族形成了心胸豁达、性情温和、镇静沉思的民族性格,而这些都可以从负载纳西文化的东巴文中感受得到。
虽然“林泉之心”从属于以汉文化为主要资源的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范畴之中,但通过对东巴教及其与东巴象形文字的关系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文化的互相渗透与原始信仰中的多神崇拜的传统,使得纳西先民同样具有了郭熙所说的审美的心胸,在这基础之上,审美地观照自然,涌现意象,东巴象形文字才得以生成。
艺术的任务在于创造意象 (东巴文),但是这种意象又必定是情感饱和的,情感出自于纳西先民,他们在情感的作用之下对孤立的自然山水进行经验的整合和审美的观照,在创作主体与客体之间既能“超以象外”,又能“得其环中”,[9]这突出表现在跟人的动作 (包括劳作)和动物有关的东巴文上。例如“打”字(图1),用简约的线条描绘出人的形状轮廓,继而通过线条的变化,传达出“打”的动作形态,动态感十足;再比如“蛇”字 (图2),飘逸流畅的线条抓住了蛇在刹那间移动的神情,形体动态之美,跃然纸上。所以在对东巴文做艺术欣赏的同时,我们也能体会到文字背后所蕴含的纳西先民审美的心胸—— “林泉之心”,原因就在于情感最易感通,这也是“诗可以群”的原因所在。


二、“同自然之妙有”
既然艺术的任务在于创造意象,即是说,艺术的本体是意象,艺术的创造就是意象的创造。东巴文化特有的“意象”—东巴文作为一种线的艺术,就具有一个由线启象、由象悟意的本体结构。唐五代的孙过庭认为,审美意象应该具有和造化自然一样的性质,即所谓的“同自然之妙有”,他在《书谱》中把书法艺术的意象比作鸿飞、兽骇等,就是为了说明书法意象应该表现自然万物的本体和生命[10]。东巴文的线条,具有生命的律动感,自然界本无纯粹的线条,它只是人创造出来的形象的抽象,抽离了具体的物象,但却是为了表现“道”而与普遍性的情感形式同构。东巴文正是用精练的笔画而非完全绘画的形式对事物或意的外部形态作近似表达,它“依于笔,本乎道,通于神,达乎气。……是一种以书法线条与天地万物和人的生命同构的书法艺术论”[11],“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笔的缓急……,就像音乐艺术从自然界的群声里抽出乐音来,发展这乐音间相互结合的规律,用强弱、高低、节奏、旋律等有规律的变化来表现自然界社会界的形象和内心的情感。[12]”
从道家的哲学思想观点出发,造化自然的本体和生命就是“道”和“气”,书法意象如果表现了“道”、“气”,就达到了“同自然之妙有”的境地。东巴文的生成与东巴教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东巴教在形成过程中又大量吸收了老、庄的哲学思想,那么作为道家哲学中心范畴的“道”自然也就在东巴象形文字中有着极为深刻的反映,用“同自然之妙有”这样一个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范畴剖析东巴文的人主义价值的合理性也就没有任何疑问了。老子认为是“道”产生万物,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讲的就是这层意思,万物是从阴阳二气交通和合中产生出来,所以自然万物的本体和生命就是“道”、“气”,如果脱离了两者,意象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自然山水并不是孤立的“象”,只有体现了“道”才能成为审美对象,从东巴文中可以看出,纳西先民的审美观照是从对“象”的观照继而进入到对“道”的观照的,也就是说纳西先民审美观照的实质是自然山水的本体和生命,而对物象形式美的把握只是次要的。
关于这一点,东巴文本身呈现的很清楚,作为一种象形文字,东巴文的线条极为简练,比绘画更为集中和概括,使人能联想到更多的具体事物所共有的审美特征,是现实美的形象反映,而不是纯粹抽象的符号。但东巴文毕竟是一种象形文字,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没有抛弃这一原则,从而就使这种符号作用所寄居的字形本身,以形体模拟的多样可能性,取得了相对独立的性质[13]。东巴文对自然万物的模拟、吸取有着极大的灵活性、概括性,正所谓“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即艺术想象活动在创作审美意象时是一个集中、提炼、概括的过程,它比绘画更为精练、更有概括性,已不是一般绘画的形式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因为东巴文既状物又抒情,兼备模拟与表情两种成份,并且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后者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13]。正如张怀瓘所说:“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岂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测?非有独闻之听、独见之明,不可议无声之乐、无形之相[10]。”东巴文的线条之中见出道,表现情思,融生命本体存在之意而非外在物象迹化于线条的律动流转之中。像表示十二年份的字中都有一部分是由动物的头像组成,而“鼠”字 (图3)与“兔”字 (图4)的头像非常相似,区别就在胡须的细微变化,这也表明东巴在书写文字的时候是对事物的提炼和概括,抓住主要特征来区分同类或者相似物,只选取动物的头部来替代整体,这样看起来不仅一目了然,这样看起来不仅一目了然,而且生动传神。


在这里,也可以尝试着运用“再现”、 “表现”这两个西方美学的概念来分析东巴文所传达出的自然万物的本体和生命—— “道”。西方美学所说的“再现”即模拟,而“表现”即表情,如果按照这样的区分,那东巴文既可以说是“再现”的,它“再现”的是自然万物的普遍规律,而不是个别的事物;同时又是“表现”的,是一种表现了纳西族民族性格中“与天地同和”的普遍性的情感形式。所以无论是“再现”或是“表现”,都可以论证东巴文是纳西先民表现自然的本体与生命的形式化反映。摒除了世俗利害的关系,进一步才能把握万物的本体与生命,自然万物的形象进入到了纳西先民审美的胸怀之中,化作已不同于自然形态的物象,此时的主客体已融为一体,意象 (东巴文)的创造自然也就得心应手。“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的就是这个过程,它是在审美观照的基础上,“意”与“象”相契合,从而产生审美意象的过程[14]。
三、任自然的生活境界
在中国美学的发展史上,人们习惯对书法和绘画进行分品,而“逸品”通常被认为是书画艺术的最高品格。“逸”是指一种超脱世俗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这与道家的精神思想不谋而合,反映到艺术中就是所谓的“逸品”。当代学者徐复观就曾说过老、庄的哲学是“逸的哲学”,而上文中笔者也已就东巴教与道教及东巴文与东巴教的关系进行过简单分析,由此可见,粗犷、大胆、朴拙的东巴文所体现出的正是纳西先民一种任自然的生活形态,这与东巴教影响下所形成的民族性格有莫大的联系。
纳西族的原始宗教有着多神崇拜的传统,在吸收了道教等宗教思想形成东巴教后,它依旧保持了原有的传统,多神在纳西精神世界里形成一定的生命感受及审美追求,内化为情感活动,使其达到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而纳西族的民族性格就是这种情感活动的外化:注意调节自我,自我控制,达到灵与肉的统一,因此是道教哲学与多神崇拜传统共同导致了纳西民族性格的形成。东巴文并不是个体情感的自我表现,而是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形式,它从一开始就排斥了各种过分强烈的、反理性的情感展现,也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具有情感洗涤特点的净化论,它追求的是情感符合现实身心和社会群体的协同,真正从内心塑造民族性格这种普遍性的情感形式。[10]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用酒神狄奥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解释古希腊文明发展的独特性,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把人类文化分为酒神型与日神型两种,日神型的文化冷静、节制,而酒神文化则癫狂、漫无节制。粗略地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似有日神精神严肃静穆的一面,道家则更多表现为酒神超脱狂欢的一面。虽然纳西东巴教受道家影响远甚于儒家,但透过东巴文我们很难将纳西文化简单地归于日神或酒神文化之一,其文字粗犷的一面似有酒神文化的影子,但朴拙的一面又显示出日神精神的节制。
“逸品”除了“得之自然”的特点之外,另一个特点便是“简”,东巴文的“笔简形具”同样是纳西先民任自然的写照,是其生活态度与精神境界的一种表现。把对象外形的某些不必要的部分加以删减的“简”事实上是反映了纳西先民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情趣,也反映了他们从重“再现”到重“表现”的变化,这种后者逐渐占据主导和优势的倾向,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写意”的倾向[15]。这种“写意”是写特定的意,即“逸气 (逸品)”,或许纳西先民在创作中也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但创作者的思想情感却通过纯客观的描写自然山水而终于被传达出,从而这种思想情感也就不再拘泥于自然万物和文字本身,而是成为蕴含着整个纳西社会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等在内的情感宽泛、广阔而丰富的外在艺术形式。书写者通过线条的粗细、长短、曲折、笔直等变化来描绘各种事物形态,使得东巴文字的线条夸张、大胆、简约、概括力强、生动有力,例如“鹤”字 (图5),线条轻盈优美,同时又力道遒劲,充分显示出鹤的体态神情特征,可以说,寥寥几笔便使得东巴文出于物象而又超于物象。

东巴文通过对万物的客观描写极为清楚地表达了纳西族的生活、环境、情感、思想,欣赏者面对东巴文似乎是在想象中面对着客观真实的自然万物。这种“见其大意”式的形象想象的真实事实上已经被融入了纳西人深厚的情感,它不是直观性的形体感觉的真实,从而可以给欣赏者更多的想象自由。在直接观照自然的基础上,东巴文要求的是一种宽阔久远的自然山水与生活环境的真实再现,表达的是整个纳西族的生活、人生的环境、理想与情趣,因此,我们可以说东巴文的这种特点正是中国传统美审美内核的外在映照,想想中国山水画的“无我之境”,不恰恰和东巴文的审美意境同出一辙吗?
就其象征功能来说,东巴文直接是纳西先民情感的迹化,或圆润丰满、隽秀流畅,或豪放粗犷、刚劲挺拔,东巴文的线条流转使得创作者的情感迹化而禀有宇宙精神和生命情思,在灵动的线条中表现出大千世界,从有限中抽离出无限,化实在客观的象为空灵,以生动的与“道”、“气”相通的线条勾画文字形体而呈现出纳西族超脱世俗的任自然的生活态度与精神境界,传达出一种超越象的不可言喻的思想意绪和生命风神。宇宙精神和生命情思流动不止,东巴文自然也就成为时间的、节律的、大化流行轨迹的写照,这种创造性的可视语言也就映衬出了纳西民族性格中的精神意志与个性风貌。
四、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巴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东巴象形文字受其深刻影响而具有了丰富灵动的生命精神。东巴文作为纳西文化的主体部分承载着灿烂的美学传统,蕴含着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其文化精神契合于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体悟和生命意识,化有形于无形之中,来呈现宇宙之气,从无意到有意之境,以抵达玄冥之道。纳西先民以“林泉之心”直接观照自然,继而把握万物的本体和生命,把他们超脱世俗任自然的生活形态与精神境界都铸化在文字当中,东巴文正是他们体悟宇宙生命的外化形式,艺术生命与宇宙生命的纽带是主体能动地感悟自然山水的体现。以简练净化的线条概括天地万物的变幻流动,将鲜活的生命精神贮存于字里行间,取法自然的东巴文是以主体之心体悟宇宙生命的结果,是宇宙之道的主观体现[16]。
东巴象形文字作为一种生命形式,是一种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的凝结,它是以生命形式去显现生命,它兼具美学的内蕴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并自然地融入了纳西人的情感和思考,以自身的生命状态去表达性情。“同自然之妙有”的“道”是指一种纳西先民对艺术体现出来的生命意义的关怀,以林泉之心“观物取象”的结果便是“中得心源”,客观世界的生命和生命精神以其无止的运动而给予创作者触动,使其以笔画的运转感应万物的韵律,追求对于道和人格所依赖的生命秩序,而终于抵达惟本惟真的艺术彼岸(实则是人生彼岸),这种本真的境界就是东巴象形文字的人文主义精神价值观。
[1]赵净修.东巴象形文常用字词译注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2]陈正勇.审美人类学视野中的东巴文字 [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7(1):137-141.
[3]耿丽涛.古老的东巴文在设计中重生 [D].天津:天津工业大学,2007:12-14.
[4]王树勋,娥满.纳西东巴文的美学内蕴 [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研究生学术交流年会专刊),2013(增):164-167.
[5]邓章应.西南少数民族原始文字的产生与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3-44.
[6][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7]郭熙.林泉高致[M].北京:中华书局,2010.
[8]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M].New York:Basic Books,1977:46.
[9]朱光潜.谈美 [M].北京:开明出版社,1994:83.
[10]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93-294.
[11]王岳川.书法文化精神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8.
[1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65.
[13]李泽厚.美的历程 [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43-46.
[14]王岳川.书法文化精神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0.
[15]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 [M].北京:三联书店,2008:7-34.
[16]王昳,李娟.中国传统书法的生命美学意蕴 [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6(6):720-722.
——纳西琵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