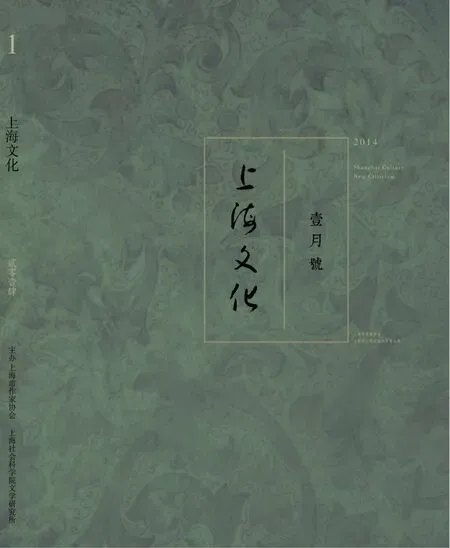先秦的鬼神以《礼记》为中心
谢科峰
先秦的鬼神以《礼记》为中心
谢科峰
一
鬼、神二字由来已久,但其含义古今殊异。商代甲骨文里有“鬼”字,是指戴驱鬼面具的人形,意思与今天的完全不同。而卜辞中的“鬼”只出现在以“鬼方”作为名称的方国上,与后来的鬼神之“鬼”意义有天壤之别。西周的金文中亦有“鬼”字,出现在“鬼壶”的铭文里,但这是指西周早期的一个人名,亦非今天意义上的“鬼”。《易经·睽卦》上九谓“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此处之“鬼”也不是后世所言的鬼神之鬼。而“神”字迄今尚无商代出土材料的发现。虽然《尚书》各篇关于“神”的记载很多,但写作时代较早的篇章里仅有两例,一是《盘庚》篇的“予念我先神后”;一是《多方》篇的“惟典神夭”。这两例的“神”的意思是对于“后”和“天”的形容之词,都并非后来意义上的神灵。在《尚书》里面载有表示神灵之义的“神”字的篇目,如《尧典》的“群神”、《微子》篇的“神祇”等,往往成书时代已在东周之后。可见以“鬼”、“神”二字进行概括,正式引申出鬼神的概念,是春秋以后的事情了。
从字形上分析,鬼、神的造字本义都与祭祀相关。《说文》所引鬼字古文从“示”,“示”字其本义为宗庙里的先祖神主形。学者据此推断,“鬼”字古文之义指是祭祖时戴面具的巫师,人们见其如见先祖,进而以“鬼”作为先祖神灵的代称。“神”字不见于甲骨文,甲骨文里只有形同连绵状的“申”字,从“申”的甲骨文字多与“电”有关。金文里的神,初并不从“示”,而以“申”代之,后来才加上“示”旁。据《说文》“神,天神引出万物者”,说明“神”与带有闪电之义的“申”字相关。因此一般认为,先秦时期,鬼多指祖先神,神多指天神。两者之间有所区别,但这种区别又不是绝对的。先秦人们普遍认为,祖先中杰出人物的魂灵可以成为神,其义正是在先秦文献中常见的“鬼神”。当然,“鬼神”一词也可能泛指包括祖先神和天神在内的所有神灵,但大多数情况下,“鬼神”往往单指祖先神而言,这在《左传》等先秦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左传》昭公二十年有载:齐景公有疾,佞臣说是祝史祭祀不当所致,谓“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可见祖先神灵是包括在鬼神之内的。昭公三十年又载:楚子西劝谏楚昭王,不要避吴锋芒,建议楚国“故亿吾鬼神而宁吾族姓”。子西所谓的鬼神是楚族姓神以保楚国族姓平安的,可见这里的鬼神是楚国的祖先神。
先秦时期,鬼多指祖先神,神多指天神
《礼记》一书,由汉儒收集整理春秋战国时期相关文献编纂而成,虽然最终结集成书于汉代,但其内容来源很早,各篇目多写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内容还直接来源于孔子,是孔门弟子及其后学的许多重要思想的总结。《礼记》中,“鬼”字单独出现十六次(《乐记》一次、《祭法》六次、《祭义》三次、《表记》四次、《问丧》一次、《檀弓》一次),其中七处涉及鬼的定义。从这些定义中可以看出,《礼记》中的“鬼”带有明显的人格特征。以《祭法》篇“人死曰鬼”为例,其义字面上看与今天差别似乎不大,但其实是强调人死后的称谓,这与我们理解的人死后变成鬼的状态有一定差别。其他几处的情况亦大致如此,在《祭法》中“鬼”字又出现了五次,分别为“去墠为鬼”、“去坛为鬼”、“去王考为鬼”和“死曰鬼”,在这些记载中,虽然天子、诸侯、大夫、官师、庶人等不同的等级在祭祀先祖时所遵守的礼制有所不同,但他们都统一称“鬼”。
“神”字出现次数要比“鬼”字多,共有三十九次(《檀弓》二次、《月令》十四次、《文王世子》一次、《礼器》一次、《郊特牲》二次、《乐记》四次、《杂记》一次、《祭法》二次、《祭义》四次、《祭统》一次、《哀公问》一次、《孔子闲居》二次、《中庸》二次、《表记》一次、《缁衣》一次),根据《祭法》篇“山林川丘谷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的记载。可以看出,“神”的自然属性比较突出。事实上,与“鬼”相比,先秦神的定义较为复杂,有神怪,有祖先神,但在《礼记》中,多为带自然属性的神灵。“天神”和“人鬼”是不同的,祭祀的礼仪也不一样,“所以别事天神与人鬼也”。
更多的情况是“鬼神”二字连用,一共有三十九次(《曲礼》四次、《王制》一次、《礼运》十次、《礼器》五次、《郊特牲》一次、《乐记》三次、《祭义》四次、《祭统》三次、《仲尼燕居》三次、《檀弓》一次、《中庸》三次、《表记》一次),《礼记》里并没有直接给出“鬼神”的定义,但根据其中的许多记载来看,应该是取当时约定俗成的祖先神之义。
二
从全书的篇章来看,“鬼神”二字出现在《礼记》中的频率并不高,载有“鬼神”的篇目只有十二,不到全书的四分之一,但这些篇目,多与祭祀有关,如《礼运》、《礼器》、《祭义》、《祭统》等,反映出“鬼神”与祭祀的密切关系。实际上,祭祀中“鬼神”的地位很高,“祭有十伦”,“见事鬼神之道”排在第一,足见其地位。也正因为兹事体大,因此在祭祀鬼神时必须抱着虔诚的态度,态度好,就会“鬼神飨德”,态度不好,就会“鬼神弗飨也”。正因为这重意义,《礼记》以非常慎重的态度来记载“鬼神”,“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孔子就是以此为由诛杀了少正卯。其实先秦时期鬼怪观念已较为盛行,许多文献中都有此类记载,例如《小雅·何人斯》即有“出此三物,以诅尔斯,为鬼为蜮,则不可得”。《左传》里鬼怪的记载亦有不少,可见鬼怪之说在当时已有一定影响。但在《礼记》中绝不见此类记载,“鬼神”的定义也较为统一。这和《论语》中“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记载相一致,反映出了《礼记》对“鬼神”记载的慎重。
因为“鬼神”是祖先神,所以祭祀的人和被祭祀的神之间往往关系紧密。在先秦观念里,“鬼神”是其后人祭祀的。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关系,祭祀者在祭祀的时候,不仅要保持足够的虔诚,也会向“鬼神”通报与自身相关的大小事务。大到新王践祚,“畛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小至娶妻,“齐斋戒以告鬼神”。总之,“鬼神”与别的文明的神不同,他更像是个威严的长辈,在未知的鬼神世界里注视着人间后人的一举一动。
因此,《礼记》里的鬼神地位非常崇高,“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左右”。人世间的一切也要为之看齐,政治上,要“并于鬼神以治政也”,礼制上,要“列于鬼神”,向鬼神取法,行为举止上也要以鬼神为标准,“鬼神以为徒”。鬼神俨然已经成为人世间大小事务的指导者。
而“鬼神”的这些特点,反映出《礼记》中的“鬼神”带有明显的人格特征,这不仅体现在这种鬼神观里的“鬼神”与人间的密切关系,更在于鬼神观的构建,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礼记》中的“鬼神”,“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是万物之精华、造化之极品。这一设计,正如冯天瑜所说,“显然是‘圣人神道设教’的另一说法”,也就是说,“鬼神”的作用在于使百姓畏服。这种带有鲜明人格特征的鬼神观,既体现了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鬼神思想的大致演进情况,亦反映出《礼记》鬼神观思想的极具特色之处。
三
先秦鬼神思想有一个明显变化过程,大体上经历了原始的鬼神崇拜——夏商时期“重天敬鬼”——西周“敬天保民”——春秋战国“重人轻鬼”这几个阶段。虽然夏商时期的资料有限,但根据已有的材料来看,此时的人们宗教信仰十分狂热,崇拜着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王室先祖和山、岳、风、水、雷、雨等诸多自然神则是其辅佐,人只能完全顺从神的意志,因此这一时期处在“重天敬鬼”阶段。而西周以一个蕞尔小国灭商的经历以及随之而来的统治需要,使得西周统治者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改造,形成周人自己昊天上帝的原始崇拜,并产生了“以德配天”的新观念,开始重视人民的作用,人的地位也随之提高,“敬天保民”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观念。到了春秋时期,人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人的价值也得到了更深入的认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随之而来的是神的地位的降低,晋国星占者预言郑国将要发生大火,郑国大夫子产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进入战国以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甚至产生了比神更为重要的观念存在,《庄子·大宗师》中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将“道”视为根本,认为“道”在没有天地以前就已经存在,是“道”生出了鬼神和天地,生出苍天和大地,“道”比鬼神、上帝重要得多。
因此,进入春秋战国之后,鬼神观念依然存在,但受到的挑战亦不少,在这新的时代因素之下,孔子及其弟子,他们内心对鬼神究竟是一个什么态度?是否像前人所说的那样,产生了时代理性精神和传统宗教观念的激烈冲突下的矛盾?
虽然《论语》里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记载,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孔子对鬼神持开放的态度,典型的例子就是《论语·乡党》里记载的“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这件事情亦在《礼记·郊特牲》能得到验证。应该说,孔子对鬼神的开放态度是和他对天的态度有关,他相信有天命的存在,对天命是畏惧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同时又认为自己是担负着天降大任的,有“天生德于予”之叹。他对天始终保持着尊敬,“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天乎”。在当时的思维序列里,天帝是至高无上的,但鬼神又和天帝有密切的联系,孔子既然对天命有着虔诚的信仰,对鬼神持开放态度亦顺理成章。
(4)情志养生法:护理人员可根据产妇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为其提供相应的娱乐活动,如播放新闻、讲幽默、有趣的故事等,以缓解产妇产后抑郁情绪。
但与相信天命的虔诚不同,对于鬼神,孔子的态度并不是那么坚定,多少有些怀疑,“祭如在”,“如”多少“尚有些怀疑的成分”,这种怀疑,不是怀疑鬼神是否存在,而是怀疑鬼神是怎样一个存在。事实上,“孔子是个怪物通”,但不管他知识如何渊博,史官出身的孔子不可能不求真实的妄发言论,对于自己说不清楚的东西,他当然只好选择“不语”。
客观来讲,在二千五百年前的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必然是和当时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发展情况相对应的,我们不可能要求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能超脱那个时代,创造出一个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思想来。事实上,在《礼记》一书里,作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设计了一个自己心目中美好的社会蓝图,这就是礼制,而礼制的建立,在对鬼神的态度上,正是需要孔子这种“敬而远之”的开放态度。
春秋时人,如子产,显然并不认为在人生前,先有某种实质即所谓灵魂者投入人身,而才始有生命。由此联系女娲造人的传说,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先秦时期普遍有这样一种观念,即人先有其形体,然后被赋予一种精气神,也就是灵魂,才成其为真正的人。人死后,形体灭亡而灵魂出窍,就成为鬼魂。所以,鬼是后于人而成的。这与西方传统的灵魂观完全不同,西方人认为,人是由天堂中众多灵魂堕落凡间的过程中与肉体结合而成的,死后灵魂会再度回到天堂,灵魂是独立于肉体而存在的,不仅不依赖于肉体,甚至常与肉体发生冲突。中国古人认,为灵魂更多的是是灌注于身体中的“气”,是与肉身融合一体的,人死之后的鬼魂仍然是生命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因此,西方人的灵魂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而中国人的鬼魂是连接鬼神世界与人间世界的。他们甚至有时候能传达天命,对人间的行为进行裁判,“这种非理性的司法裁判建立在这样的信仰上;被压迫者的呼叫会招来鬼神来复仇……对于鬼神之报复的认同信仰,迫使每一位官吏在面对可能造成自杀危险的群众狂乱的情况时,不得不让步”。
在这种裁判行为中,鬼神是公正的代言人,它代表的是所谓天道正义,当家族祭祀祖先的亡灵以求获得永远的荫庇时,鬼神则成为人的保护者。此时鬼魂的保护原则并不以正义为准绳,而是以是否为其家族成员而定。这样一来,鬼神又成为其宗族利益在人间的代言人,西周至高无上的昊天上帝就被认为是住在嵩山的天室山上,鬼遵循着与人世相仿的生活法则与道德判断,同样有等级、有情感,而且其等级会根据其前世的所作所为来划分。正因为先秦时代世人对鬼神世界的这些理解,决定了以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对礼制思想的设计,孔子正是在重视人事的基础上重视鬼神,提出“敬鬼神而远之”,因为过于痴迷鬼神会使人脱离现实生活而走入玄想与迷信,所以必须对鬼神保持一定的距离。与鬼神保持距离的前提却不是漠视鬼神,而是要尊敬它,因为“敬鬼神”就是敬祖先,就是孝,而且只有保持距离的尊敬才能真正成其为尊敬。正如《礼记》所载,祭祀鬼神在孔子及其弟子们看来是非常庄重严肃的事情,是容不得任何马虎和怠慢的,所以孔子说“祭神如神在”。
也正因为鬼神的存在和必须对鬼神所持的尊敬态度,《礼记》的作者们制订了一系列的祭祀原则和制度,这些原则和制度,后来构成儒家礼仪的主要成分。《礼记·祭统》篇开宗明义:“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在后来的儒家看来,礼是治国的最重要手段,而祭礼又是五礼中最重要的一种。其实这里所说的礼,其本义就是祀神。许慎《说文》里是这样解释礼:“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王国维也指出,“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这都说明了礼和祭祀的关系密切。同样,对于祭祀而言,礼也非常重要,“非礼不庄不诚”。正因为如此,对待礼制和对待祭祀的态度一样,必须要庄重而虔诚,必须要“敬”。
要做到敬,就对道德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礼记》里提出这样一个标准:“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如此之谓备。能备然后能祭。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诚信之谓尽,尽之为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这种对鬼神的尊敬,是在人世间事奉君长的敬的延伸,“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祭祀时态度不敬,就会使祭祀流于形式。所以孔子曾有这样的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因此,敬是孔子视为事奉鬼神的首要原则:“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祭祀需要一个总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事死如事生”。祭祀的目的何在?“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这才是《礼记》中倡导敬奉鬼神的真正目的。对此,《论语》中亦有类似的阐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❶对于《礼记》成书的年代,至今仍有争议,但大体都认定,此书是成书于西汉,而内容为先秦古书,近年来,王锷著有《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一书,对《礼记》各篇的成书年代进行了详细考证,本文中有关《礼记》成书年代的确定依据即主要来自此书。
❷《礼记》一书,各篇目成书时间不一,所涉及的作者问题亦非常复杂,可以肯定的是其成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但与孔子的弟子及其后学传人有莫大关联,此问题的相关论著很多,可参看《礼记成书考》,此处不再赘述。
❸如《曲礼》篇里记载的“齐斋戒以告鬼神”,《表记》篇里记载的“是以无害乎鬼神”,《中庸》篇里记载的“质诸鬼神而无疑”,无一不是指祖先神的意思,而像《礼运》、《祭义》这样专门讲述礼制的篇章,更是通篇将如何祭祀祖先神之事,事实上,《礼记》中出现记载鬼神的地方,除了极少数地方之外,一般都是指祖先神的意思。
❹关于孔子诛杀少正卯之事,后人多有争议,徐复观先生就认为孔子诛杀少正卯为后人杜撰,参见徐复观《一个历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进——论孔子诛少正卯》(载于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但此事的记载,确实反映出孔门对“鬼神”的慎重态度。
❺例如庄公十四年载: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繻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8,第196-197页。
❻相关记载为:乡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❼参见(日)伊藤清司:《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4-58页,据作者考证,孔子其实对“怪力乱神”的了解,远在同时代人之上。
❽《左传》昭公七年,晋国的赵景子向子产询问关于鬼的问题时,子产回答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日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指出魂魄皆为人死后所生成。
❾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中华书局,2004,第222页。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