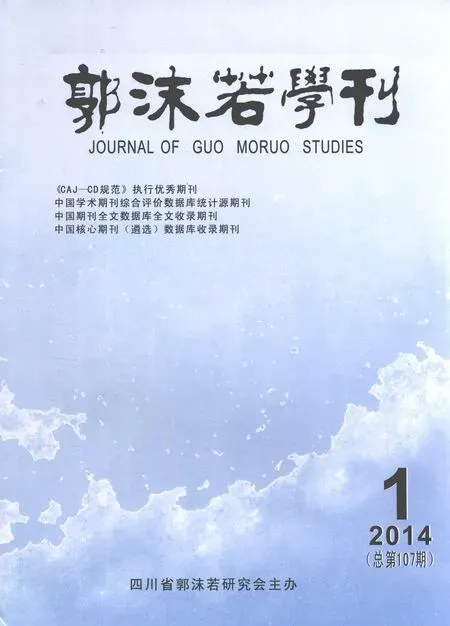《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的修改
孟文博
(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山东威海264209)
《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的修改
孟文博
(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山东威海264209)
《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是郭沫若非常重要的一篇文艺论文,他在论文中以大部分篇幅第一次较为系统的阐述了其“对于创作上的态度”,让该文成为我们考察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极为重要的参考材料。但是郭沫若在日后对这篇论文进行了相当大的修改,使得学界在对此论文进行研究或引用时,经常出现偏差,得出错误结论。通过对勘可知,郭沫若所写这篇论文的直接动因与翻译问题的论战并不相干,而是“感发”于“沈雁冰君《论文学的介绍的目的》一文”,通过分析郭沫若在日后的诸多修改,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文艺“功利性”和“功利主义”创作观的表达非常谨慎,但对文艺作品“艺术性”和“功利性”的辩证却一直明确。
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修改
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的巨匠,他一生所涉猎领域之广泛,成就之斐然,为一般作家学者所难望项背,因此被誉为“球形天才”。同时,郭沫若在历史纵向上又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善变”的作家,他横跨晚清、民国、新中国初期和文革四个历史阶段,其思想观念总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的变化,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不同时期所创作的作品上,同时还体现在他对同一篇作品在不同时期的修改上。学界以往对前者的研究较多,但对于后者却较少涉及,这主要跟郭沫若修改自己作品的习惯有关,他对作品的修改从不加以具体说明,而篇尾却依然延续最初版本所注明的时间,因此就给后来学者的研究带来不小的困难,甚至造成各种失误。像《女神》中的名篇《匪徒颂》,最初发表在1920年1月23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时并无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赞美,而是歌颂的罗素和哥尔栋,替换成马、恩是到了1928初版的《沫若诗集》。同样,《巨炮之教训》一诗最初发表在1920年4月27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时,篇尾列宁的“喊叫”是“为自由而战哟!为人道而战哟!为正义而战哟!……”,直到了1928初版的《沫若诗集》中才又改作:“为阶级消灭而战哟!为民族解放而战哟!为社会改造而战哟!……”由这些改动来看,说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即具有了共产主义思想,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具体作品是这样,扩大的一部文集,也有类似的情况。近期就有学者通过细致考证让我们看到了可谓触目惊心的情形:本应最全面的《郭沫若全集》竟然比1977年出版的《沫若诗词选》少了187首诗,而郭沫若研究的工具书如《郭沫若作品词典》、《简明郭沫若词典》也因此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误!这样的明显的疏漏长期为学者们所忽视,一方面折射出了目前郭沫若研究界的某些混乱,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基础的版本校勘工作是何等必要而刻不容缓。
事实上,早在近30年前黄淳浩先生就以郭沫若的《文艺论集》为例,提出“现代文学研究需要注意版本”的问题,而他的《〈文艺论集〉汇校本》也正基于这一点而出版的。《文艺论集》是郭沫若最早的论文集,同时也是其最重要的论文集之一,它收入了郭沫若1920到1925年间的30多篇论文,涵盖历史、文化和文学等方面,是学界研究郭沫若历史观、文化观和文学观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这部《文艺论集》于1925年出版后,又曾在1929年、1930年和1959年改版三次,每一次郭沫若都亲自参与订正和改动,可见其本人对这部论文集的重视。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这部论文集的修改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使得很多学者始终都没弄清各版本的区别,“往往把五十年代经郭老改动了的观点当成他二十年代的观点,造成了失误”,结果造成许多错误的观点至今还在以讹传讹。
鉴于以上所述,笔者近期对各个版本的《文艺论集》重新进行了校对,发现郭沫若诸多修改所反映的问题相当多,但由于篇幅所限,本篇主要讨论其中的一篇影响较大同时改动也很大的论文进行讨论,即《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这篇论文最初发表于1922年8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此时正是郭沫若步入而立之年的开始,也是他出版《女神》一周年,在文坛暴得大名之际。这时的郭沫若已有资历“回顾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并向文坛标明自我基本的文艺观点,于是他在论文中以大部分篇幅第一次较为系统的阐述了其“对于创作上的态度”,而这也让该文成为我们考察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极为重要的参考材料。这篇论文在1925年被收入《文艺论集》后,历经多次改版,均没有被删除,一直到1959年的《沫若文集》中,郭沫若又亲自在多处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变更了其中很多观点,使其成为《沫若文集》版《文艺论集》中修改比例最大的论文,因此它对于我们考察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到后期的流变和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坛状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因为此,这篇论文历来为学者们所重视,曾在大量的研究文献中被加以引用,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自改革开放至今,此文仅在各种研究论文中就被引用四百多次,如果再加上专著,当然会更多。不过与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和被引用次数所对应的遗憾是,几乎所有的学者在引用它时,都根据的是解放前的《文艺论集》诸版本,或者1959年版《沫若文集》中的《文艺论集》,甚至是《郭沫若全集》中的版本,而事实上,《郭沫若全集》中的《文艺论集》是根据《沫若文集》所编的,内容相同,它们与解放前的《文艺论集》诸版本有着很大差别,再进一步说,收入到解放前《文艺论集》诸版本中的这篇论文,与其最初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时又有不同。有极少数学者曾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便根据1984年出版的《〈文艺论集〉汇校本》(以下称《汇校本》)进行研究,但岂不知这个《汇校本》只标注出了幅度较大的修改,而对于很多“一般文字变动”也都忽略了。
在现代文学研究正在推向纵深的当下,学界“回到历史现场”的呼吁已经呼吁多年,这种研究方略对我们摒弃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眼镜,以纯洁的眼光洞窥那段复杂的历史,并得出更为客观的研究结论,都是极有帮助的。正缘于此,笔者以郭沫若这篇论文的最初版本为依据,着重考察其在历史纵向上的各种流变,于细节变动中分析总结,以期对郭沫若研究有所增益。
一、创作动因考察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把郭沫若写这篇论文的起因看作是与沈雁冰关于翻译问题辩论的后续,而忽略了郭沫若自己所述的直接动因。这是因为学者们多根据各时期的《文艺论集》中的版本进行研究,却没注意到在初版本的最后,郭沫若还用了较长的文字描述为何写这篇文章,在此我不妨把这段文字摘录下来,以供大家更直观地考察。
我这篇文字的动机,是读了沈雁冰君《论文学的介绍的目的》一文而感发的。沈雁冰君答覆我的这篇评论的态度是很严肃的,我很钦佩。不过在落尾处有一段论作家的文字,我还嫌稍微隐约含糊了一点。至于括弧中“猪”的一句骂詈语,因为我读书太少,我还不知道出处。但是骂我国的同胞是“猪”,这是我们听惯了,见惯了的。依资本主义为爪牙,依物质文明为利器的东、西洋人,骂我们无抵抗能力的中国人是“猪”,这是我们听惯了,见惯了的。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现状,混沌到不可名状的地步,并不是“猪”的人太多,实在是「非猪」的人太多了的缘故。一些买些东、西洋人的烂枪旧炮来我们头上蹂躏着的军阀,一些采仿资本主义来我在我们心坎上吸吮着的财东,这些都是“非猪”的东、西洋人的高足弟子,我们中国的糜烂都是他们搅出来的。我在此诚恳的劝告沈雁冰君:这些“非猪”的人尽可以诅咒,不要再来诅咒我们可怜的同胞,我们可怜的失了抵抗能力的一群羊儿——或者可以说是猪儿。这种骂法觉得使我们伤心的很!雁冰君的答辩,本来再想从事设论,不过我在短促的暑假期间,还想做些创作出来;我就暂且认定我们是意见的相远,不再事枝叶的争执了。我们彼此在尊重他人的人格的范围以内,各守各的自由罢。
十一年八月二日,上海
可见,郭沫若所写这篇论文的直接动因与翻译问题并不相干,而是“感发”于“沈雁冰君《论文学的介绍的目的》一文”,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郭沫若在此把这篇文章的名字记错或者写错了,实际的名字为《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兼答郭沫若君》(1922《文学旬刊》第45期)。郭沫若所针对的“括弧中‘猪’的一句骂詈语”,在沈雁冰的文章中实际也有两句,前一处是:“我是十二分的憎恶‘猪一般的互相吞噬,而又怯弱昏迷,把自己千千万万的聪明人赶入桌子底下去’的人类”,后一处是:“难道还少‘猪一般的互相吞噬,而又怯弱昏迷,听人赶到桌子底下去’的人类么?”沈雁冰关于“猪”的比喻,本是痛恨当时的人们“彼此不能相谅”,却能“低了头一声不响忍受军阀恶吏的敲剥”,但郭沫若却没有“从事设论”,而是把沈雁冰的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看作“诅咒我们可怜的同胞”,并呼吁彼此要“尊重他人的人格”,结合郭沫若的记错或是写错,这些纷争其实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文坛论战的某种意气与浮露。
至于这一段文字为何在1925年并没有随其所在的文章一起收入《文艺论集》,而且在以后各个版本的《文艺论集》中也再没有出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或许是为了文章更为简洁,而从大的背景看,应与当时创造社创作风格的转变有关,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创造社进入后期,转向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学研究会合流,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篇“动机”介绍自然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二、意义修改分析
除了这段“动机”说明和一些不涉及意义变动的一般字词调整,此文在收入1925、1929、1930年版本的《文艺论集》时,并没有大的变化。但在被收入1959年版本的《文艺论集》时,郭沫若对其中五段话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现也把其摘录于下:
1、原版本:
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以从事创作,上之想借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的精神太远了。这个作家惯会迎合时势,他在社会上或者容易收获一时的成功,但他的艺术(?)绝不会有永远的生命。
文集本:
艺术本身是具有功利性的,是真正的艺术必然发挥艺术的功能。但假使创作家纯全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以从事创作,所发挥的功利性恐怕反而有限。作家惯会迎合时势,他在社会上或者容易收获一时的成功,但他的艺术的成就恐怕就很难保险。
2、原版本:
这种功利主义的动机说,从前我也曾怀抱过来;有时在诗歌之中借披件社会主义的皮毛,漫作驴鸣犬吠,有时穷得没法的时候,又想专门做些稿子来卖钱,但是我在此处如实地告白:我是完全忏悔了。文艺本是苦闷的象征,无论他是反射的或创造的,都是血与泪的文学。
文集本:
功利主义的动机说,我从前也怀抱过来;有时在诗歌之中也披着件社会主义的皮毛,觉得空洞而无实。那是由于没有从生活出发的原故。自己的生活是一套,写作是一套,结果只是空虚。文艺如由真实生活的源泉流出,无论它是反射的或创造的,都是血与泪的文学。
3、原版本:
个人的苦闷,社会的苦闷,全人类的苦闷,都是血泪的源泉,三者可以说是一根直线的三个分段,由个人的苦闷可以反射出社会的苦闷来,可以反射出全人类的苦闷来,不必定要精赤裸裸地描写社会的文字,然后才能算是满纸的血泪。无论表现个人也好,描写社会也好,替全人类代白也好,主要的眼目,总要在苦闷的重围中,由灵魂深处流写出来的悲哀,然后才能震撼读者的灵魂。不然,只抱个死板的概念去从事创作,这好像用力打破鼓,只是生出一种怪聒人的空响罢了。并且人的感受力是有限的,人的神经纤维及脑细胞是容易疲倦的,刺激过烈的作品容易使人麻痹,颠转不生感受作用。
文集本:
人生的苦闷,社会的苦闷,全人类的苦闷,都是血泪的源泉,三者可以说是一根直线的三个分段,由个人的苦闷可以反射出社会的苦闷来,可以反射出全人类的苦闷来。当然要看你怎样写法,从什么角度来写。无论表现个人也好,描写社会也好,替全人类代白也好,主要的眼目,总要有生活的源泉。由灵魂深处流写出来的悲哀,然后才能震撼读者的灵魂。只抱个概念去创作,不从生活实践出发,好像用力打破鼓,只能生出一种怪聒人的空响。人的感受力是有限的,人的神经纤维和脑细胞是容易疲倦的,刺激过于强烈的作品很容易使人麻痹,不发生作用。
4、原版本:
总之我对于艺术上的功利主义的动机说,是不承认他有成立的可能性的,我这种主张或者有人会说我是甚么艺术派的艺术家的,说我尽他说,我更是不承认艺术中会划分出甚么人生派与艺术派的人。这些空漠的术语,都是些无聊的批评家——不消说我是在说西洋的——虚构出来的东西。我认定艺术与人生,只是一个晶球的两面,只如我们的肉体与精神的关系一样,他们是两两平行,绝不是互为君主臣仆的。而有些客气未除的作家或者批评家,更揭以自行标榜,在口头笔下漫作空炮的战争,我觉得只是一场滑稽悲喜剧罢了。
文集本:
总之,我不反对艺术的功利性,但我对于艺术上的功利主义的动机说,是有所抵触的。或许有人会说我是甚么艺术派,但我更是不承认艺术中可以划分出甚么人生派与艺术派的人。艺术与人生,只是一个晶球的两面。和人生无关系的艺术不是艺术,和艺术无关系的人生是徒然的人生。问题要看你的作品到底是不是艺术,到底是不是有益于人生。有些客气未除的作家或者批评家,爱标榜自己是人生派,而斥骂别人为艺术派,在口头笔下作空喊的战争,我觉得只是一场滑稽悲喜剧罢了。
5、原版本:
有人说:“一切艺术是完全无用的”,这话我也不十分承认。我承认一切艺术,她虽形似无用,然在她的无用之中,有大用存焉。她是唤醒人性的警钟,她是招返迷羊的圣菉,她是澄清河浊的阿胶,她是鼓舞生命的醐醍,她是……,她是……,她的大用,说不尽,说不尽。文集本:
有人说:‘一切艺术是完全无用的。’这话我也不承认。我承认一切艺术,虽然貌似无用,然而有大用存焉。它是唤醒社会的警钟,它是招返迷羊的圣菉,它是澄清河浊的阿胶,它是鼓舞革命的醍醐,它的大用,说不尽,说不尽。
综合以上修改来看,郭沫若从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文艺思想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有一些变化带有清晰的时代烙印,比如在艺术发生论方面,从信奉“苦闷说”到强调“生活源泉说”;在文艺功用方面把“唤醒人性”改为“唤醒社会”,把“鼓舞生命”改为“鼓舞革命”等,这些观念的变动由对比郭沫若在不同时期所写的不同作品即可得出,因此长期以来也为学界所熟知,在此不必赘言。然而如果我们通过对此作品在不同时期修改的角度再来加以考察,这些问题就会暴露得更为清晰,甚至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就郭沫若的这篇论文的修改来看,至少有以下两点需要注意。
1.对文艺“功利性”和“功利主义”创作观的表达非常谨慎。
在第一段的原版本中,郭沫若没有提及文艺“功利性”的问题,而是把“借文艺为宣传的利器”和“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全都归到“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的创作中去了,称这些“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的精神太远了”。但在文集本中,郭沫若首先说明了“艺术本身是具有功利性的,是真正的艺术必然发挥艺术的功能”,然后再强调“但假使创作家纯全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以从事创作,所发挥的功利性恐怕反而有限。”正是从这一句修改开始,郭沫若就把文艺“功利性”和“功利主义”创作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了,在他看来,“功利性”是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属于客观层面,而“以功利主义为前提”的创作,是一种创作态度,属于主观层面。不过接下来郭沫若没有再具体说明什么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而仅是把“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以从事创作”改为:“假使创作家纯全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以从事创作”,加了一个“全”字。这种修改显得有些语焉不详,并且更加啰嗦,但细究起来,其实应与50年代的文学环境相关。在那个年代,文学创作早已被规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螺丝钉”,发挥着“宣传的利器”的作用,所有作家也都经过思想改造成为了“文艺工作者”,不再“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因此这样一来就不存在原来的那种“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的创作,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郭沫若无法说清恐怕也不愿说清什么样的创作才是“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的创作,所以他干脆不再像原来那样具体举例说明,而只在“纯”字后面加上一个“全”字,把所谓“功利主义”的范围尽量缩小,如此也就最大限度的避免了某些可能遇到的诘难。
以上所述是这种谨慎性的第一个层面,另外它还有第二个层面。在第四段的原版本中,郭沫若称“对于艺术上的功利主义的动机说,是不承认他有成立的可能性的”,而到了文集本中他改为:“我不反对艺术的功利性,但我对于艺术上的功利主义的动机说,是有所抵触的”。显然郭沫若对这段话的修改相当微妙。他继续首先强调“艺术的功利性”,但对“功利主义的动机说”却从明确的“不承认他有成立的可能性”修改到语气和缓的“有所抵触”。事实上,两处不同的用语和语气也正体现了郭沫若在两个时期中对“艺术上的功利主义的动机说”的不同态度以及心理状态。20年代的文学环境可以让年轻的郭沫若直白而明确的表达观念,但在50年代整个文化环境已大不同,在大一统的文化政策中,文艺作为“宣传的利器”,实际上在践行着“功利主义的动机说”,这时的郭沫若也已成为文艺界的领导人物,自然不能再如以前那样直白明确的表示反对,然而郭沫若首先还是一个艺术家,他依然只愿意承认艺术在客观上的“功利性”,而不愿完全附和“功利主义”的创作动机,因此他也只能谨慎地使用“有所抵触”这样的表达方式了。
2.对文艺作品“艺术性”和“功利性”的辩证一直明确。
郭沫若在这几段话中没有直接提及“艺术性”一词,但他由多处的修改均表达了对“艺术性”的着重强调,例如在第一段话的文集本中称:“艺术本身是具有功利性的,是真正的艺术必然发挥艺术的功能”,在第四段话的文集本中,郭沫若先论述了“艺术与人生”关系,之后又表示:“问题要看你的作品到底是不是艺术,到底是不是有益于人生”。究其因,这一点正是他一贯以来所坚持的把艺术首先当作艺术来创作的文艺观,如果结合郭沫若对其他作品的修改,我们就会有更清楚地发现,比如在《艺术家与革命家》一文的原版本中,郭沫若就有这样的话:
这种人的态度虽是矫奇,但我们还可以容恕。因为无论若何艺术没有不和人生生关系的事情。更无论艺术家主张艺术是为艺术或是为人生,我们都可不论,但总要它是艺术。刀说是杀鸡的也可,说是杀人的也可,我们总要求它是刀然后才能承认,这是易明的事实。
《沫若文集》修改后为:
其实任何艺术没有不和人生发生关系的事。艺术家无论是主张艺术为艺术或为人生,但总要他的艺术是艺术,刀可以说是杀鸡的,也可以说是杀人的,但总要求它是刀。
郭沫若前后两次用到“刀”的比喻,都在强调艺术家的“艺术是艺术”,而不仅仅是改造人生和社会的工具。
类似的还有《儿童文学的管见》一文,郭沫若在原版本中认为:
要之就创作方面主张时,当持唯美主义;就鉴赏方面言时,当持功利主义:此为最持平而合理的主张。
到了文集本中,郭沫若放弃了这“持平而合理的主张”,改为:
要之,创作无一不表现人生,问题是在它是不是艺术,是不是于人生有益。
在这些论文中郭沫若都明确表示“艺术”首先应该是“艺术”,“艺术”只有在“是艺术”的基础上,才能“发挥艺术的功能”,只要作品的“艺术性”得到了保证,那么她自然会“于人生有益”。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郭沫若始终“不承认艺术中可以划分出甚么人生派与艺术派的人”。不过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强调作品的艺术性一点上,郭沫若的理论与创作显然是分裂的,就在他对《文艺论集》诸多论文进行修改的时期,也创作了如《百花齐放》这样“迎合时势”的作品。事实上这也并不奇怪或者矛盾,它只是当时郭沫若人格分裂的一种表现,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作为艺术家的郭沫若和作为政治家的郭沫若是不可能得以完全重合的。
三、汇校条目补全
如前文所述,上世纪80年代黄淳浩先生出版了《〈文艺论集〉汇校本》,这是迄今唯一一部对郭沫若《文艺论集》的汇校本,长期以来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本,也得到广泛的好评。但是黄先生根据“至于一般文字变动,为避免繁冗,则不一一录出”的原则,在使此《汇校本》简洁明了的同时也因个人标准的参与而忽略了很多客观史料。事实上,这些未被标注出的修改并非全是“一般文字变动”,其中有很多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比如《〈文艺论集〉序》篇尾的一首诗出现在1925、1929、1930和1959年的诸版本中,却未出现在《洪水》杂志的最初版本中,此诗是郭沫若后来所加?还是在《洪水》发表时删除?值得探讨;再如《天才与教育》中有一段话:“但在我们教育破产,司教育的人只知道罢课索薪,受教育的人只知道罢课闹事,卖教育用具的人只知道献贿名人以推广商业的时代”,此段话在文集本中删除了“受教育的人只知道罢课闹事”一句,删除此句是郭沫若在解放后对学生运动的看法转变的结果?或者仅仅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情势?也值得研究。进一步说,那些看起来很“一般”的“文字变动”,也并非完全没有研究价值,比如《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一文,最初版本中对胡适的称呼是“胡适之”,而在文集本则全部改成了“胡适”,这与另一篇文章《反响之反响(一)·答〈努力周报〉》的改动十分相似,这篇文章最初版中的“胡先生”到了文集本中也均改成了“胡适”,结合两个时期的政治形势,郭沫若对胡适的态度已经从平等论敌转变成了阶级敌人,而称谓的变化正是这种态度转变的体现。更进一步说,很多“一般”的“文字变动”在目前“一般”的学者处可能没什么价值,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研究眼光和角度,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真正有眼光的学者会因新方法的运用而在其中发掘出很有价值的成果。因此综合看来,它们不应被简单地忽略。有鉴于此,本篇沿用《汇校本》的体例,还原郭沫若对此篇文章在各个时期的全部修改,把其中关于《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所遗漏的汇校条目收录于下:
(1)〔我觉得有一种极不好的习气充溢着〕《学灯》、订正本、改版本同,文集本作:“有一种不好的习气充溢着”。
(2)〔并且反转激成一种反动〕《学灯》、订正本、改版本同,文集本作:“反而激成一种反动”。
(3)〔生出一种执着来〕《学灯》、订正本、改版本同,文集本作:“生出一种执着”。
(4)〔我想批评家总当抱着博大的爱情以对待论敌〕《学灯》、订正本、改版本同,文集本作:“批评家总当抱着博大的爱情以对待被批评者”。
(5)〔Impulsivist〕《学灯》、订正本、改版本同,文集本删除。
(6)〔每肯向我如是说〕《学灯》、订正本、改版本同,文集本作:“每向我如是说”。
(7)〔一匹死了的河豚〕《学灯》、订正本、改版本同,文集本作:“一只死了的河豚”。
(8)〔经脑精的作用〕、〔储积在脑精中〕《学灯》同,订正本、改版本把两处“脑精”都改为“脑筋”,文集本把前后两处“脑精”分别改为“脑神经”和“脑”。
(9)〔表现了出来〕《学灯》、订正本、改版本同,文集本作:“表现出来”。
(10)〔直接尽我一点〕订正本、改版本、文集本同,《学灯》作:“直接尽效我点”。
(11)〔应得是属于后的一种〕订正本、改版本、文集本同,《学灯》作:“当得是属于后的一种”。
(12)〔并且人的感受力是有限的,人的神经纤维及脑细胞是容易疲倦的,刺激过烈的作品容易使人麻痹,反转不生感受作用〕订正本、改版本同,《学灯》“反转”作“颠转”、文集本作:“人的感受力是有限的,人的神经纤维和脑虤胞是容易疲倦的,刺激过于强烈的作品很容易使人麻痹,不发生作用”。
(13)《学灯》中“艺术”的代称均为“牠”,订正本、改版本改为“她”,文集本中又改为“它”。
(14)时间及地点《学灯》作:“十一年八月二日,上海”,订正本、改版本作:“十一年八月间作”,文集本删除。
长期以来,对同一作品在不同时期的版本考察一直都是现代文学研究学界的薄弱部分,这一方面由于近百年来的历史历经动荡,材料收集非常困难,另一方面也与学界的某种浮躁有关。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版本研究是我们“重返历史现场”,梳理作家思想观念流变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关于这一点,黄淳浩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专门著文呼吁:“在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版本学”,“这是因为我国的近现代社会,曾长期处于动荡不定的、不断变革的状态中,作家的思想必然受社会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对自己的著作加以修改,这是极其自然和无可非议的事情。因此,我们研究现代作家,不仅可以从该作家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去探索他的思想的变化,还应该从他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同一著作中的不同版本去发现他的思想变化。”而具体到郭沫若这样一个重要而又“善变”的作家,我们尤其需要对他的著作做追根溯源式的研究。
(责任编辑:陈俐)
[1]魏建.《沫若诗词选》与郭沫若后期诗歌文献[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11).
[2]黄淳浩.现代文学研究需要注意版本——从郭沫若《文艺论集》的版本说起[J].人文杂志,1986(2).
[3]黄淳浩.《文艺论集》汇校本[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G256.22
A
1003-7225(2014)01-0054-07
2013-11-21
孟文博(1977-),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讲师,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