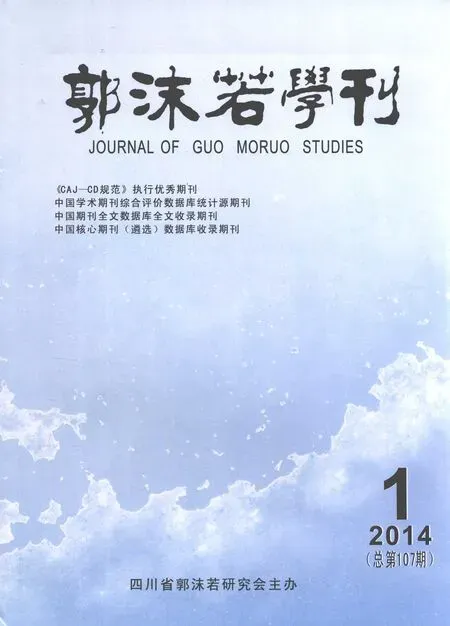郭沫若海洋体验与《女神》中“海的精神”
彭冠龙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郭沫若海洋体验与《女神》中“海的精神”
彭冠龙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郭沫若是第一个在中国诗歌中注入了真正的“海的精神”的人,“海的精神”通过郭沫若的海洋体验进入《女神》中,具体表现为自由灵动的节奏和雄浑高昂的格调,这“海的精神”是《女神》“时代精神”的具体化,更是“时代精神”的核心。
郭沫若;《女神》;海洋体验;海的精神
对于《女神》中所包孕的精神,前人已有很多研究,然而这些研究普遍是围绕着“时代精神”展开的,另外一种精神始终少有人提及,那就是“海的精神”。目前来看,王富仁先生最早关注到了这一点,《“郭沫若在日本”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收录了他的论文《他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境界——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文中指出,“郭沫若是第一个在中国诗歌中注入了真正的海的精神的人,是第一个以海的精神构成了自己诗歌的基本审美特征的人”。的确如此,仅对这种精神在字面上的反映——“海洋”意象——进行一下统计,就会发现,《女神》一共收录57首诗,有41首中出现了“海洋”意象及其相关意象,比例约为71.9%,这一覆盖面是非常广的。
沿着王富仁先生的观点继续思考下去,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海的精神”是如何进入《女神》中,并成为这部诗集基本审美特征的?毫无疑问,“海的精神”是一种抽象形式的观念,无法直接转化为诗歌创作,更无法凭空进入作品中,必然要通过一种诗人接触过的具体物象作为媒介,而且这一物象还要能够凝聚诗人各种复杂的感受,使诗人的主观情绪能在这个具体的物象上自如展开。根据上文的统计数字,可以确定这一媒介就是“海洋”。但是,还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有了“海洋”这一具体物象能与诗人心灵深处某种感情情绪相对应,这一具体物象也未必能够成为媒介,使“海的精神”进入《女神》中。具体的物象——“海洋”——之所以能够成为媒介,不仅仅是因为它契合了诗人的内心感受,还因为郭沫若对“海洋”进行了“体验”,这一“海洋体验”才是“海的精神”得以进入《女神》,并成为这部诗集基本审美特征的关键所在。
所谓“体验”,是一种基本的精神现象,直接联系人自身的生命存在方式,“它不是概念性地被规定的。在体验中所表现出的东西就是生命”,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体验’是我们感受、认识世界,形成自己独立人生感受的方式,也是接受和拒绝外部世界信息的方式,更是我们进行自我关照、自我选择、自我表现的精神的基础”。郭沫若的海洋体验与他的留学经历有关,在留学的几年中,他既近距离的看到了大海,又坐着船在大海上飘过,既感受到了大海的气势,又看到了海边上发生的一切,这些都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在这一感受中,他自我关照、自我表现,《女神》就是这种自我观照和表现的结晶。
一
那么,郭沫若的“海洋体验”究竟是怎样的?对于这个问题,郭沫若自己没有说过,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他的自述去寻找答案。
从郭沫若的自述文章中,可以梳理出他在留学时期历次与海洋的重要接触。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留学,当时“是由火车穿过万里长城从朝鲜渡海而来”,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大海,这个时候,他正因求学无路而“苦闷到了绝顶”,应该是无心观海,所以在任何文章中都找不到他对此时海洋体验的描述。半年后,考取第一高等学校,“心情无比舒畅,也放松了不少”,于是与杨伯钦、吴鹿苹来到房州避暑,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在海边生活,他在这时所作的两首旧体诗第一次反映了他的海洋体验,一首写的是“飞来何处峰,海上布艨艟。地形同渤海,心事系辽东。”由海洋上的军舰联想到祖国的屈辱。另一首写的是“白日照天地,秋声入早潮。披襟临海立,相对富峰高。”由海景引发了自由自在的心情。1915年,郭沫若在一高读书期间,发生了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日本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郭沫若与其他留学生一样,决定回国抗争,但是当他坐着船还在东海上漂荡时,袁世凯已经迫于压力,同意签署“二十一条”,当时郭沫若在海上的心情可以通过他的诗反映出来:“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1918年,郭沫若进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来到了福冈市,住在了博多湾附近,由于居住时间长,这片海湾给郭沫若带来了丰富的海洋体验,由于《女神》中的诗歌基本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郭沫若在这片海湾上的海洋体验直接影响了《女神》中的海洋精神。
基于以上梳理,结合郭沫若的自述文章,可以概括出郭沫若的两种海洋体验。
首先,郭沫若的海洋体验是“自由”的。在郭沫若的自述性文章中,对海洋景色的直接描写并不多,但每次海景描写都透着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今津纪游》中描写的海景是“海湾中水色青碧,微有涟漪。……海湾左右有岩岸环抱,右岸平削如屏,左有峰峦起伏。正北湾口海雾蒙蒙中有帆影,外海不可见。天际一片灰色的暗云,其上又有一片白色卷层云,又其上天青如海”,显然一片自由自在的景象。在《创造十年》中,也有一段海景描写:“天色也晴起来了。海湾中的海水呈着浓蓝的颜色,有好些白鸥在海上翻飞。”同样是自由景象,加之“与久别的旧友重逢,夜来的忧郁已被清冷的海风吹送到太平洋以外去了。我那时候委实感受着了‘新生’的感觉”,更增添了一种心情舒畅之感。郭沫若这次启航回国,是在自由自在的心境下开始的。同样自由的景象在郭沫若致宗白华的一封信中也有描写:“是日微有风,湾中波浪汹涌。海鸥飞扬上下。对此胜观画图,湾形如池。”[9](P103)
由以上列举的片断可知,这种“自由”的海洋体验是郭沫若意识到的,他在给田汉的信中曾说:“我的灵魂久困在自由与责任两者中间,有时歌颂海洋,有时又赞美大地。”说明他在歌颂海洋时,内心是感受着“自由”的。然而,与这种海洋体验相反,他的另一种海洋体验是完全无意识的,即“渴望祖国独立强盛”。
虽然完全无意识,但是这种“渴望祖国独立强盛”的海洋体验却在他的自述文章中明显传达了出来。郭沫若在关于他留学时期的所有自述性文章中,几乎都要介绍他的住处——博多湾附近,只要介绍他的住处,就一定要详细介绍博多湾,并且一定与“弘安之役”联系起来。比如《创造十年》中的介绍:“这博多湾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地点,它是650年前元世祖的大将范文虎征伐日本时,遇着大风全军覆没了的地方。(日本史家称为“弘安之役”,当西历1281年。)当时的遗迹在那沿海一带还是不少,有所谓‘元寇防垒’、‘元寇断首台’、‘元寇纪念馆’。”其他文章中的介绍都与这一段大同小异,从介绍中可以体会出一种“自嘲”和“屈辱”的意味,而继续深究会发现,使得郭沫若对发生在这片海域中的屈辱历史反复提及的原因并不是“自嘲”和“屈辱”。在郭沫若致宗白华的一封信中记录了他与田汉的一次对话,说到了博多湾,除了介绍弘安之役外,还提到了他是如何得知这段史事的:“这段史事是我初到福冈时,就在这海岸上听得来的。一群小学生围着一个教习,手舞足蹈,指天划地的在这沙岸上讲演。我近身听时,我真多谢他:他同时也呼起我无限的敌忾。”这“敌忾”才是使郭沫若对发生在这片海域中的屈辱历史反复提及的原因,因为这一情绪是他最初听到这段历史时的第一反应,其中包含的就是“渴望祖国独立强盛”的感受。由于郭沫若一看到博多湾就想到这段历史,“渴望祖国独立强盛”的感受也就成为了他的第二种“海洋体验”,博多湾中的屈辱历史就成为了这一海洋体验的源头。
另一件事也可以证明这种海洋体验的无意识性和确实存在。在郭沫若的自述文章中有对日本“成金风”的描述,在描述中,他目睹“成金”们奢侈享乐生活的地方就在博多湾,这在《创造十年》中记录的比较详细。他与张资平吃完中饭在海边散步,看到了博多湾中的筑港工事,感受到了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也看到了“成金”们的享乐挥霍,然而在记录中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关于弘安之役的两句对话,郭沫若说的一句是:“令人有点不相信啦,元军的几百艘战舰,在一夜之间通统沉没在这里了。”从这里可以知道,郭沫若眼睛中是“成金”们的各种享乐行为,但脑子里却又是弘安之役,也就是说,看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却想到了祖国的屈辱历史,其中所反映出的就是“渴望祖国独立强盛”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海洋体验,但又是一种确实存在的海洋体验。
二
“自由”与“渴望祖国独立强盛”是郭沫若的两种海洋体验,经过诗人艺术思维的加工,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法,进入作品中,就形成了《女神》所包蕴的海洋精神,这一海洋精神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由灵动的节奏,二是雄浑高昂的格调。郭沫若有一个诗歌观点是用海水做比喻,可以算作概括地诠释了《女神》海洋精神的这两个具体方面:“我想诗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张着的情调。……这种诗底波澜,有他自然的周期,振幅,不容你写诗的人有一毫的造作。”
(一)自由灵动的节奏。
郭沫若“自由”的海洋体验进入《女神》后,形成了作品“自由灵动”的海洋精神,这种海洋精神的具体表现就是自由灵动的节奏。正是因为郭沫若看到了大海的浪飞涛涌,才会由海的波澜想到诗的波澜,认为“诗底波澜,有他自然的周期,振幅,不容你写诗的人有一毫的造作”,才会由这一观点继续推广,不重视诗的外在形式,而是强调情绪自然消长,注重诗歌创作过程中的情绪波动,进而提出“诗的原始细胞只是些单纯的直觉,浑然的的情绪”,“情绪的吕律、情绪的色彩便是诗。诗的文字便是情绪自身的表现”,“新诗便是不假修饰,随情绪之纯真的表现而表现以文字”。
《雪朝》的创作过程可以充分体现出郭沫若怎样把“自由”的海洋体验转化为诗中“自由灵动”的海洋精神。这首诗创作出来之后,作者曾把它寄给成仿吾,成仿吾非常欣赏这首诗,“但他不高兴那第二节,说是‘在两个宏涛大浪之中哪来那样的蚊子般的音调?’”郭沫若作出的解释是这样的:“但那首诗是应着实感写的。那是在落着雪又刮着大风的一个早晨,风声和博多湾的海涛,十里松原的松涛,一阵一阵地卷来,把银白的雪团吹得弥天乱舞。但在一阵与一阵之间却因为对照的关系,有一个差不多和死一样沉寂的间隔。在那间隔期中便连檐溜的滴落都可以听见。那正是一起一伏的律吕,我是感应到那种律吕而做成了那三节的《雪朝》。我觉得要那样才能形成节奏。”成仿吾所提的意见是按人所具有的常识得出来的“常理”,而郭沫若却是按照他所体验到的大海的自由节奏进行创作,把大海自由节奏所产生的声音效果全部融入诗中,摆脱一切人类“常理”的干扰,完全自由灵动地予以展现,这就把“自由”的海洋体验变为了诗中自由灵动的节奏,形成了诗中“自由灵动”的海洋精神。
另外,《浴海》这首诗的感情基调也如大海自然的波涛,由平静而逐渐高涨,最终近于咆哮:“新中华底改造全赖吾曹!”。《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也遵循着大海波涛的自由起伏状态,诗中的句子长短变化很大,最长的一句有19个汉字加一个英文单词,最短的一句只有6个汉字。
除了这类直接描写海洋景色或直接出现了海洋意象的诗作之外,其他没有写海洋景色的诗中同样存在着自由灵动的节奏,体现着“自由灵动”的海洋精神。比如《地球,我的母亲!》,这首诗是作者“突然受到了诗兴的袭击”的成果,作者为了完成这首诗,“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把‘下驮’脱了,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这种近似发狂的行为完全是为了让诗歌具有他自己的天然节奏,也就是“他自然的周期,振幅”,而不去人为的雕饰、遣词,通过真切地亲昵、感触皮肤和受着拥抱,来形成一种自然的情绪,并让这种情绪自然消长,在“诗的推荡、鼓舞”中完成诗作,保证诗的节奏自由灵动,完全是一种“自由灵动”的海洋精神。
其他诗作无不是如此。对于郭沫若的诗歌,单独拿出任何一句来,都无法产生一点诗意,即便那些最好的诗篇,其每一句话的独立性都是很差的,然而,作为整体,诗的精神一下子显现了出来,究其原因,正是由于这种“自由灵动”的海洋精神的贯穿,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由灵动的节奏的组织,使得郭沫若诗歌不仅没有散架,而且极富自然生气。
(二)雄浑高昂的格调。
前文已经提到,郭沫若“自由”的海洋体验是他能够意识到的,而“渴望祖国独立强盛”的海洋体验是无意识的,也就是存在于潜意识中。根据弗洛伊德文艺观中的潜意识创作论可知,文艺创作的本质是潜意识的心理活动,是一种潜抑愿望的达成,潜意识中愿望的实现途径除了梦之外,就是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使其得以升华,潜意识活动的能动性,激发着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因此,郭沫若潜意识中的海洋体验同样能够进入《女神》中,并根据这种体验的内容升华为一种“雄浑高昂”海洋精神,其具体表现就是诗作中雄浑高昂的格调。
这一格调在《凤凰涅槃》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首诗的内容完全是想象出来的,字面上是写一对凤凰先“集香木自焚”,后“从死灰中更生”的经过,诗中雄浑高昂的格调是通过生与死的对比来实现的。“集香木自焚”时,诗的格调不断凝重雄浑,“啊啊!/哀哀的凤凰!/凤起舞,低昂!/凰唱歌,悲壮!”在《凤歌》中,这雄浑的格调开始强烈,“我们飞向西方,/西方同是一座屠场。/我们飞向东方,/东方同是一座囚牢。/我们飞向南方,/南方同是一座坟墓。/我们飞向北方,/北方同是一座地狱。/我们生在这样个世界当中,/只好学着海洋哀哭。”进而在《凰歌》中,凝重雄浑的格调越来越重,“啊啊!/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痴!痴!痴!/只剩些悲哀,烦恼,寂寥,衰败,/环绕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贯串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最后,在死亡时,这种格调达到极致,“啊啊!/火光熊熊了。/香气蓬蓬了。/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身外的一切!/身内的一切!/一切的一切!/请了!请了!”而“从死灰中更生”时,诗的格调一下高昂起来,“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翱翔!翱翔!/欢唱!欢唱!”在《凤凰和鸣》中,每一节内容几乎都是重复的,只是个别字句有所变动,这可以看作是以不断提醒读者凤凰已获新生的方法,把高昂地“欢唱”推向极致。
在生与死的对比中,雄浑高昂的格调被成功容纳在这首诗中,赋予全诗一种雄浑高昂的海洋精神,通过这种格调,使整首诗成功的“象征着中国的再生”,这种象征意蕴是郭沫若自己提出来的,不能不说是与其潜意识中“渴望祖国独立强盛”的海洋体验相联系,是这种潜意识中的海洋体验在作品中的升华。
除《凤凰涅槃》之外,其他诗作中同样都存在着这种雄浑高昂的格调,展现着雄浑高昂的海洋精神。比如《晨安》和《匪徒颂》,“这两首奇拔的诗,便是诗人用热血燃烧起的民族反抗的熊熊烈火”。《晨安》从“常动不息的大海”写起,“涌着的白云”“燃着的海山”,开篇就是雄浑高昂的格调,继而呼唤着年青的祖国,俯瞰着“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冻结着的北方的黄河”“万里长城”“雪的旷野”,进而推广到先驱的俄罗斯、喜马拉雅山、“尼罗河畔的金字塔”,最终完全落脚到对大西洋、太平洋的大声问候,38行诗句中全是雄伟壮阔的宏大意象,其中,仅海洋意象就出现了12次,可以说从外在意象到内在格调完全透着雄浑高昂的海洋精神。《匪徒颂》同样如此,通篇是伟大的形象,而且以打破时空的方法,把古今中外一切真正的匪徒放置在一起进行歌颂,每节结尾的“万岁!万岁!万岁!”都把诗中包孕的情绪推向顶峰,强烈的呼喊配合着伟大的形象,雄浑高昂之气贯穿全篇。
(三)海洋精神的作用
自由灵动的节奏和雄浑高昂的格调是《女神》海洋精神的两个具体表现,这样一种海洋精神对《女神》产生了巨大作用,它使诗出现了起伏感,由此超越了平面的文本呈现,在起伏中显得丰厚。
海洋精神对《女神》的首要作用就是使诗产生了起伏感。类似分行散文的“胡适之体”在《尝试集》中一出现,就广受追捧。这种“作诗如作文”的诗歌体式很难透出一丝诗歌情绪的起伏,显得平板呆滞,但影响很大,“当冰心那一段段散文文字被分行排列时,竟会造成‘小诗流行的时代’”。就在这种诗风盛行时,《女神》显现了异乎寻常的起伏感,自由灵动的节奏使诗歌不拘成法,随自然之音和情绪起伏而不断变化节奏,影响到诗的外在形式和音乐感上,就形成了长短差距极大、毫无规则可言,甚至出乎意料的诗句,时而长,时而短,时而高涨,时而低落,即使短篇幅的诗作,也显得波澜起伏。加上雄浑高昂的格调,就使诗歌的起伏感不仅停留在诗的表面,而且深入到诗的精神,《女神》中的诗作大气磅礴,用诗集中的诗句来表述,那就是“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从里到外的起伏中,透露出了诗作的丰厚感,也就是说,诗在起伏中显现出了包容量,诗的内容并非只有字面上的那些,在诗的内容中,还包含着大量有待读者去体会的东西,这就是海洋精神对《女神》的第二个作用。比如《天狗》,整首诗从外在上看起伏不断,从内在上看动感万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起伏中包孕着一种个性解放精神,这种精神是需要读者透过诗句的字面意思去深入体会才能发现的。又如,《夜》中也有从外到内的起伏感,“你把这全人类来拥抱:/再也不分甚么贫富、贵贱,/再也不分甚么美恶、贤愚,/你是贫富、贵贱、美恶、贤愚一切乱根苦蒂的大熔炉。/你是解放、自由、平等、安息,一切和胎乐蕊的大工师。/黑暗的夜!夜!”这起伏之中传达的是渴望世间一切平等、人类和谐共处的心声,这心声也是包容在诗句之中,没有外漏。
海洋精神给《女神》带来的起伏感和包容量,很容易使人想到是惠特曼《草叶集》对郭沫若诗风的影响,这种影响郭沫若也曾多次提到,并认为在他的作诗经过中,“惠特曼式”是最值得纪念的一段时期。但是郭沫若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有他自己的审美爱好和感情倾向,他不可能囫囵吞枣地全面容纳惠特曼,而是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接受与自身体验相符的内容。“《草叶集》气势之恢宏,恰如太平洋的洪涛,在无限的洋面上,波浪滚滚,涌动奔流”,这一特点正好与郭沫若的海洋体验相符,于是被郭沫若吸收借鉴到《女神》的创作中,并大声歌颂“太平洋一样的恢铁莽(即惠特曼——引者注)呀”。
如果将《女神》的海洋精神放到整个“五四”时代的大背景下予以观照,那么,结合以上论述,可以进而探讨一个问题:《女神》的“海的精神”与“时代精神”是什么关系?
文章开头已经提到,前人对于《女神》中所包孕的精神的研究,普遍围绕着“时代精神”展开,这些研究当然是有道理的。闻一多于1923年在《创造周报》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最早提出:“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然而,“作为一种历史抽象,‘时代精神’更多是一种假定性存在,很难说存在一种凌驾个体差异之上的普遍的、统一的精神取向”。摆脱这一假定性的存在,立足于郭沫若的留学经历等一系列的基本史实,再去探索《女神》所包孕的精神,我们就会看到《女神》中的“海的精神”。
但这并不是说《女神》的“海的精神”与“时代精神”没有关系,实际上,“海的精神”是“时代精神”的具体化,是“时代精神”的核心。
根据前文的论述,再去看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就会发现,自由灵动和雄浑高昂这两种海洋精神,正是闻一多所提出20世纪“动的精神”和“反抗的精神”在诗作中的具体表现。闻一多在他的文章中只是非常感性的指出“动的精神”和“反抗的精神”在《女神》中映射的最为明显,没有理性分析怎样映射和如何明显,虽然经过了后来周扬、周恩来、臧克家等许多人的继续论述和引申发挥,但是始终没能突破感性分析的局限。根据前文对“海的精神”两个具体表现的论述,并结合前文所分析的郭沫若海洋体验,发现自由灵动的海洋精神正是闻一多所说“‘自由’的伸张”的具体表现,雄浑高昂的海洋精神正是闻一多所指出的“何等激越的精神”的具体化。
如果跳出史料梳理和文本分析的局限,放眼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那么就会发现,20世纪的世界,各大洲交流空前密切,由于中国国门被打开,这片古老的国度也像地球上其他地方一样踏上了世界化的进程,“五四”时代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当时联系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路线几乎全部在海上,大海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空间的一个现实、具体、重要的组成部分,郭沫若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师法西洋、救国图存的过程中,外国先进文明从海洋上运进中国,中国留学生从海洋上走入先进国度,他们正是以海洋为基础感受着20世纪的时代精神,“海的精神”必然成为了“二十世纪时代精神”的核心。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女神》这部诗集第一次体现了真正的“海的精神”,这一精神通过郭沫若的海洋体验进入《女神》中,具体表现为自由灵动的节奏和雄浑高昂的格调,对《女神》的艺术风貌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从整个时代的高度审视《女神》“海的精神”,就会发现这一精神是《女神》“时代精神”的具体化,更是“时代精神”的核心。
(责任编辑:廖久明)
[1]王富仁.他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境界——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A].“郭沫若在日本”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1988.
[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译本)[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3]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郭沫若.今津纪游[A].沫若自传(上卷)[M].北京:求真出版社,2010.
[5]郭沫若.我的学生时代[A].沫若自传(上卷)[M].北京:求真出版社,2010.
[6]蔡震.郭沫若的青少年时代[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7]郭沫若.《女神》及佚诗(初版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8]郭沫若.创造十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9]郭沫若.郭沫若致宗白华函·三叶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0]郭沫若.郭沫若致田汉函·三叶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1]郭沫若.谈诗的创作·通讯三则[A].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郭沫若专集[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12]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A].沫若文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3]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A].周扬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14]刘静.以《女神》为例反思新诗“散文化”之路[J].西南大学学报,2008(5).
[15]陈永志.《女神》与《草叶集》比较谈(下)[J].郭沫若学刊,2003(4).
[16]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J].创造周报,1923(4).
[17]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I207.22
A
1003-7225(2014)01-0042-06
2012-09-17
彭冠龙(1988-),男,山东泰安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