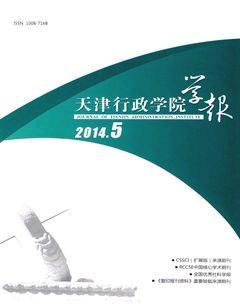转型中国的民众正义观念
麻宝斌 杜平
摘要: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领域改革为先导的全面社会转型。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所包含的不同内容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观念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众正义观念是民众评价社会正义时遵循的价值标准,会影响到公共政策的设计与执行。在内容上,民众正义观念包括正义观念主体、正义主体、正义客体、正义原则及其适用等多个分析维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转型对民众正义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使其呈现出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并存、弱重叠性等基本样态。
关键词:中国转型时期;民众;正义观念;正义主体;正义原则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5-0053-09
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以经济领域为先导,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全面社会转型。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此过程中一些社会不平等问题也得以显现。同时,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也深刻影响了民众的正义观念,使其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因此,回答“当代中国社会里普遍发生的正义诉求是否以及怎样得到满足的问题”[1](p.15),不仅需要关注收入差距等问题,也要将目光投向人们的内心世界。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等客观问题,对民众的“‘主观认知和评价等议题却缺乏有效讨论”[2],并且已有相关研究主要从“共时态”角度分析不同社会群体正义观念的区别,从“历时态”视角对民众正义观念转型的研究有待加强。本文从民众正义观念的定义和相关研究状况入手,提出民众正义观念的分析框架,进而立足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背景,分析社会转型对民众正义观念带来的影响,探讨中国民众正义观念的转型样态。
一、民众正义观念及其研究
(一)民众正义观念的含义
正义一词起源于西方国家,与其相对应的是Justice一词。学界一般认为,Justice一词起源于拉丁语中的Justitia,是由jus一词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3](p.463)。此后,不同时期的学者都对正义的内容进行了探讨。本·杰克逊(Ben Jackson)系统回顾了西方国家的相关研究后发现,现代社会正义概念与古希腊时期相关概念存在质的区别,前者认为正义不仅是个人层面上的一种美德,而更应当是社会层面上的一种责任①。
今天我们所探讨的社会正义主要是分配正义,它是围绕如何对社会的基本善进行合理分配等问题展开的。在此,我们将正义理解为“人类对于理想社会状态的一种描述”,是“对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关系是否正当的一种追问”[4](p.2)。
本文中的“民众”指普通社会公众,与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社会精英相对应。我们将观念(观)界定为人们对于特定事物或事物的看法。这样,民众正义观念就是指普通的社会公众对社会正义的看法,即民众对于社会正义的相关问题进行判断时所持有的价值标准。
在民众对社会正义主观评价的相关研究中,正义感受与正义观念经常在一起使用。尽管二者都属于民众对社会正义状况主观评价的范畴,具有一定联系,但也存在明显区别。首先,从二者之间的联系看。正义观念与正义感受是相互依存的,“正义原则的存在是正义感存在的逻辑前提,而正义感的存在又使正义原则不致成为空洞无物的东西”[5](pp.4445)。其次,二者又有明显区别。第一,“外显”与“内隐”的区别。正义感受是民众对社会正义状况的“外显”的直观感受;正义观念是民众对社会正义的现状进行评价时所遵循的“内隐”的价值标准。第二,抽象与具体的区别。正义观念是一种抽象的价值标准,适用于不同领域;正义感受则是具体的认知,反映了民众对具体社会问题是否正当的直观感受。第三,稳定与动态的区别。正义观念相对稳定,一旦形成不会轻易变化;正义感受更具动态性,易受相关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二)国内外学界对民众正义观念的研究
一是关于民众是否具有正义动机的研究。个人是单纯的理性经济人还是具有正义的行为动机?这是民众正义观念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以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为代表,主要通过最后通牒实验等方法进行。埃尔斯特(Ernst Fehr)等回顾了有关研究,发现大约有60%~80%的受试者选择40%~50%之间的份额,只有大约3%选择20%以下的份额[6]。叶航、陈叶峰等的实验研究也证明了民众公平偏好的存在[7]。陈叶烽等通过实验考察了分配动机公平和分配结果公平对人行为决策的影响,发现响应者对提议者“分配动机公平”有显著不同的反应[8],这又证明了个人公正偏好的存在。但是,类似研究主要在“真空”环境下进行,通过它来证明民众正义动机的存在只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更复杂的问题是在现实的社会情景中民众的正义观念呈现何种样态。
二是关注民众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已有研究发现,民众普遍能够接受一种结构化不平等的存在,认为不同职业之间存在收入差距是合理的[9]。凯利(Jonathan Kelly)等根据国际社会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人们普遍认可结构化不平等的合理性,即同意一些职业应当有高收入、另一些职业相对较低,但在多大差距才合理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10]。马库斯(Markus Hadler)对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约三千五百名民众的研究发现,民众普遍能够接受不平等的存在,但在具体的数量和比例上存在差别[11]。李路路等的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对于社会不平等的接纳程度越来越高[2]。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对中国民众正义观念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有六成以上的民众理性看待并接受社会的不平等[12]。
三是对民众正义主体偏好的研究。社会正义的实现主体是多元的,现实中民众更倾向于哪一类主体?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人支持“为了保证平等,由政府给予社会下层的人们一些额外的帮助”[13](pp.194199)。韩春萍等对中国民众政府再分配偏好的研究发现,经济社会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村居民反而对政府再分配的支持程度最低,这与农村公共服务相对薄弱有关[14]。潘春阳等从个人利益和分配公平两个维度,对中国民众的政府再分配偏好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个人利益因素和公平的动机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15]。郑永流等进行的调查发现,有44.73%的调查对象在面对经济纠纷时选择干部帮助解决和私了的解决方式[16](pp.126)。endprint
四是对民众正义客体偏好的研究。英格尔哈特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对民众正义客体偏好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发现收入水平提高会使得民众不断增加正义清单的内容,虽然经济和安全仍然重要,但民众会更加重视参与等内容②。从国内研究来看,苏力根据《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两部电影反映的问题分析了中国民众的法权观念,认为民众对于正义客体的理解并不是规范层面上的法权观念;应星和陈柏峰等还从“讨个说法”、“气”等社会现象入手,对中国民众的法权观念进行了研究③。
五是对民众正义原则的内容及其适用的研究。民众支持的公平原则是什么?克鲁格尔(James R.Kluegel)研究发现,人们普遍认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得到一定数量的最后收入;同时,也普遍反对按照平等原则对所有的社会资源进行分配,认为由教育水平、能力等差别导致的收入不平等是合理的[17]。诺尔曼(Norman Frohlich)、丁建峰等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了民众的公平原则,得出了类似的结论④。多元的公平原则在不同的情境中如何适用?张静等的研究发现,中国民众的正义原则具有通用性和专用性的特征⑤;李强认为,应首先对城市和农村进行区分,然后在城市对“体制内单位”和“体制外单位”区分,在农村对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进行区分[18];黄光国从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以及情感性关系等方面对中国民众正义原则的适用进行了探讨[19](pp.144)。民众不同的正义原则之间有无序列性?张明澍、杜建政等的研究发现,民众对公平原则的重视优于公正原则⑤;而张光和刘祥琪等的研究发现,民众对于公正原则的重视要优于公平原则⑥;张静等的研究发现,民众的公平原则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序列⑦。
六是对民众正义观念影响因素的研究。综合来看,民众正义观念往往受教育水平、文化以及社会转型等因素的影响。李骏等就受教育程度对民众公平观念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0]。李强认为,应当从“等级公正观”、“革命公正观”、外来的公正观等方面对中国民众正义观念进行研究[18];黄光国从“人情”入手,对中国民众的正义观念进行了分析[19](pp.144)。迈尔乌(Mérove Gijsberts)研究发现,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之前,其民众要比市场经济国家的民众更具有平等观念,但转型以后所有国家的民众所能接受的社会不平等的比例都在增加,并且前社会主义国家民众能接受的收入差距的增速要比市场经济国家的民众快[21]。
七是研究民众正义观念对政策内容设计和执行效果的影响。有研究发现,民众正义观念的不同是国家之间税收政策差异的影响因素[22];民众正义观念能够对社会福利政策的设计产生影响⑨;民众的正义观念还能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影响[23]。
对民众正义观念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相关研究有助于拓宽社会正义实证研究的范围,全面了解特定社会中公平正义的实现状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民众对社会正义问题的主观认知与收入差距等客观层面的问题都应当看作是社会正义现状的组成部分。因此,自二十世纪末期以来,国际社会公正调查项目、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等都开始关注民众对社会正义的主观评价问题。“在对全球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研究时,是否把中国包括进去,经常会改变所得到的基本结论”[24](p.2)。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显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界关注。但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正义的客观状况方面,对中国民众正义观念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因此,加强中国民众正义观念的研究有助于拓宽社会正义实证研究的范围。此外,这一问题的研究还能够提供一个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的窗口。社会的现代化必然会要求人们思想行为的现代化,其中就包括民众正义观念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无论在方式还是在内容上,不仅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存在明显的区别,也与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转型具有显著的不同。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容是全方位的,但转型的方式又是渐进的。这种转型路径对民众正义观念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类似问题只有通过深入的研究才能找到准确的答案。
从现实层面看,研究民众正义观念能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积极的政策建议。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的持续深入,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民主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就是构建起由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组成的公共治理体系。那么,民众是否认可市场机制进行的分配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又是如何认识政府的再分配?在遇到纠纷时倾向于找政府部门解决还是找社会上的权威人士处理?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民众正义观念的研究才能找到答案,进而制定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政策建议。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在现代社会,政府一般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方式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民众正义观念对政府政策内容的设计和政策的执行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是人们是否遵守法律的重要影响因素,为此也要对民众的真实动机进行分析。
二、民众正义观念的分析维度
正义是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人类社会需要按照某种正义的原则来分配稀缺的社会资源,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关系,但它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唯一价值。效率、和谐、自由和诚信等也是重要的社会价值。因此,民众正义观念研究的前提是关注民众对正义价值重要性的认知。只有明确民众对正义(及相关价值)的重视程度,才能进而寻求解决其他相关问题。因为,如果民众普遍认为正义价值根本不重要的话,那么后续研究就失去意义了。
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民众正义观念应从哪些方面着手分析。这实际上就是民众正义观念的分析维度问题。民众正义观念是民众对社会正义进行判断时所遵循的价值标准,因而正义的构成要素就成为民众正义观念的分析维度。一般认为,社会正义的核心问题是由何种主体、在哪些人中间、按照怎样的原则、实现哪些价值的合理分配。由此,我们提出一个六维的民众正义观念分析框架(参见图1)。endprint
正义观念主体着眼于回答“谁的正义观念”的问题。毋庸置疑,正义观念的主体是人。但在现实中,民众不仅是“原子化”的个体,还具有不同的组织归属,民众“既可以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人的群体”[25](p.202)。进一步看,群体又具有不同的划分标准:依据自然属性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性别、年龄等;从地理差异上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等;依据文化因素则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民族、宗教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从政治因素上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国家、地区等[28]。民众正义观念的研究需要按照上述分类对不同个人或群体进行比较分析。
正义主体偏好关注民众倾向于由何种主体或机制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发展出了多样化的组织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求,萨瓦斯将这些形式概括为:家庭、氏族、部落等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各种类型的志愿团体;市场及其在其中运行的各类组织;政府。从分配正义的实现主体看,市场的初次分配、政府的再分配以及社会组织的第三次分配是最重要的分配形式,家庭等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现代化程度不同,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民众对市场初次分
配、政府再分配的支持程度并不高,反而认为亲戚和邻里间的互助等是解决生活困难的重要形式。从矫正正义的主体看,政府部门、司法部门以及一些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群众自治组织等)是最重要的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正义的主体。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设计以及文化
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民众对不同正义主体的偏好是不同的。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社会上的权威人士等也是民众支持的对社会矛盾进行调节的主体,甚至有的民众还会将希望寄托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社会正义专注于将特定或某些社会价值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并且对于那些损害他人合法权利与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惩罚。综合来看,按照客体对人自身的效用层次和作用方式的不同,正义客体可分为三类:尊严、权利和机会等可视为人类发展社会条件的基础价值;收入、资产和资源等可视为人类发展经济条件的外在价值;幸福和能力等可视为所有基础价值和外在价值服务目标的内在价值[27]。这就要求在分析民众正义客体偏好的过程中,深入了解民众内心世界中对不同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偏好。同时,由于这些价值都是权利、尊严和机会等基础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因而还要考察民众对这些价值的认知是否符合现代社会的法权观念。
正义原则偏好的核心是民众倾向于按照何种原则来分配社会价值。正义的原则包括公平和公正两类,其中公平主要是对机会和结果是否合理的评价,可以分为平均、平等、衡平等多种类型;公正则是对过程是否正当的评价。在现实中,对结果是否合理评价时,民众更倾向于接受哪种公平原则?平均、衡平还是其他类型?对过程的正当性进行评价时,民众会支持每个人都能得到不偏不倚的对待、过程的公开与透明还是倾向于依靠个人的社会关系?在纠纷解决依据的选择上,民众希望按照国家的正式法律还是生活中的一些惯习来解决?这些都是民众正义原则偏好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
“人们对于客观状况的反映是基于主观上的比较做出的。”[28](p.1)在现实中,选择特定的比较对象进行比较,是民众对社会正义状况进行评价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综合来看,这种比较可以分为反身比较和横向比较两类:反身比较指民众将自己当前的状况与自己过去的经历进行比较;横向比较则指民众同社会上的其他人进行比较。进一步说,民众在与他人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所选择的对象也有差异:有的可能会选择自己身边的人比较;有的则可能会选择和自身实际情况相似的人比较;还有的甚至可能会选择比自身经济社会条件更好(或更差)的对象比较。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类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同时,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不可持续性的问题也日益突出。面临自然资源优先性以及环境承载能力的制约,为了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效维护后代人的利益,代际正义的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当代人之间的分配正义问题,更需要关注如何在代与代之间合理分配社会资源的问题。这就将代际正义问题也纳入了民众正义观念的研究范畴。
总之,对民众正义观念的研究需要以上述分析维度为依据,综合运用问卷调查、访谈、观察、社会实验等多种方法,进而形成对于民众正义观念的认识。具体来看,民众正义观念的研究应包括两个方面:总体的民众正义观念;不同群体或个人的正义观念之区别。就前者来说,理论研究需要系统探讨:民众正义观念在整体上呈现出什么样的样态;具有怎样的特征;体现出怎样的变化规律和趋势;多元的正义原则在不同的情境中如何适用。就后者来说需要回答:国家、地区、城乡、区域、行业以及所有制类型之间个人或群体的正义观念具有怎样的特征;他们之间呈现出怎样的差异;是否具有“重叠共识”。
三、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民众正义观念
影响民众正义观念的因素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从微观层面看,个人的收入、财产数量的变化以及受教育程度都是重要的影响变量。从宏观层面看,国家的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社会转型等都会对民众正义观念的变化产生影响。
(一)政治转型对民众正义观念的影响
中国政治转型的目标是实现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具体内容包括:民主制度逐渐健全;基层民主制度不断完善;依法治国战略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入,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加快。以民主化、法治化为主要标志的政治转型对民众正义观念有多重影响。从正义主体看,在历史上,受“皇权不下县”制度安排的影响,基层主要由乡绅和宗族来治理,当时的乡村治理是一种“礼治”,主要是依靠一些社会风俗而不是法律进行的,这些都使得民众倾向于由社会上的权威人士来调节社会纠纷。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国家政权建设逐步向基层延伸,普法教育活动也提高了民众的法律意识。这对民众的正义主体偏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今天的农村,“国家的、行政的和法律的力量已成为调节和影响村落社会关系的主导力量”,“行政正义和法律途径也越来越多为农村居民所运用”[28](p.166)。从正义原则看,在传统上,中国民众更为重视结果的公平,缺乏公正的观念和参与的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基层群众自治实践的历练,民众的参与意识也逐渐增强。endprint
(二)社会转型对民众正义观念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转型实质是逐步实现由共同体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过渡。农业社会本质是一种基于血缘和地缘形成的共同体社会。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被费孝通称为“差序格局”,这种结构是影响民众正义观念的重要因素,个人依附于家庭并根据血缘关系来选择交往的原则,在家庭内部和家庭之外的原则截然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化、信息化以及工业化等浪潮的持续冲击下,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础逐渐被消融,民众正义观念也相应逐渐发生转变。在交往原则的选择上,一些原来只适用于同“陌生人”交往的原则,也逐渐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出现。此外,在农业社会,社会成员的流动性是很低的。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实践表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必然会伴随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传统中国以小农经济占主导,社会流动性不强。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以及严格的户籍制度也限制了社会成员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逐步解体以及户籍制度的松动,城乡之间的流动性不断增强。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两亿多的流动人口。城乡流动性的增强使得民众扩大了正义比较对象的范围,也正因为如此,流动人口的不公平感要比农村居民的不公平感强,他们对政府再分配的支持程度也比农村居民高。
(三)经济转型对民众正义观念的影响
中国经济转型的主题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过渡。与市场经济改革相适应,政府的职能定位、经济制度以及分配制度设计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资源配置机制看,政府逐渐从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退出,市场逐步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主体,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从经济成分看,“一大二公三纯”的经济制度逐步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转型。从分配制度看,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转型。这些变化也在冲击着民众的内心世界。首先,在民众正义主体偏好和正义原则偏好上,已经开始认可市场分配原则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其次,经济制度的转型也造成“体制内单位”和“体制外单位”成员之间正义观念的差别。最后,社会整体收入水平的变化对民众正义客体的偏好也产生了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人们不断往正义清单中增加新的内容,开始关注收入之外的价值。近年来所发生的一些由于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众关注内容的变化。
(四)文化转型对民众正义观念的影响
民众正义观念可以看作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的民众正义观念是被一个国家的文化规定的。因此,国家文化的不同在根本上决定了民众正义观念之间的差异。同时,国家的文化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且这种变化也会对民众的正义观念产生影响。传统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儒家文化的一些主张对民众正义观念有深刻影响。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使得民众从内心深处接受社会上的一些不平等,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克己复礼”,以尽可能维持这种差别的存在。此外,“和为贵”的文化传统也对民众正义原则的选择产生了影响,由于怕伤了彼此的和气,在一个组织内部,大家会更倾向于支持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社会主义文化以及个人主义文化等都对传统的民众正义观念产生了冲击。“差序格局中关于私的观念、自我的观念以及等级观念,在经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后以及多种政治运动等历史事件的洗礼后,已经发生变迁,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观念和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动”[29]。在现实中,性别平等的观念等已经逐渐被民众接受,同时“人人为己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和全球化的消费主义开始支配家庭生活和私人关系”[30](p.42)。
四、中国民众正义观念的转型
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民众正义观念的嬗变。总体上看,中国民众正义观念正在经历从“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正义观念向“公民权利本位”的现代正义观念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并存、序列性和弱重叠性等过渡性特征。
(一)中国民众正义观念具有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并存的特征
在中国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民主化、法治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等是最突出的标志。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一个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相互交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元素和现代的元素是并存的。转型初期,传统元素多于现代元素。随着转型的持续深入,传统的元素会逐渐被现代的元素所取代。当现代元素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就意味着社会转型基本完成。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有着自身的独特性,是在几十年时间里走完西方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时间走过的历程。由于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短时期内的急剧社会转型并不能轻易使民众正义观念挣脱传统因素的束缚,古老的文化传统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惯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民众正义观念也为社会转型的大背景所规定,体现出过渡性特征:既蕴含着传统元素,又具备一些现代元素。这种特征具体体现为:在正义主体的偏好上,一些民众还倾向于依靠社会上的权威人士来解决社会矛盾,或者将希望寄托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正义客体的偏好上,民众对于相关价值的认识还停留在“说法”、“面子”等一些传统的认识上,这并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法权观念;在对正义原则的偏好上,民众对于程序公正的认识还不足,这显然是与民众只重视结果而不重视程序的传统相一致的,虽然有的民众已经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但仍有一些民众支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平均分配原则。
(二)中国民众正义观念具有序列性的特征
所谓序列性,借鉴于罗尔斯使用的“词典式的序列”概念,意指民众正义观念的不同内容之间具有一定的序列性。民众正义观念包含多个维度的不同内容,现实中民众对不同内容的偏好存在差异,对其中的一些内容具有明显的偏好。在这个意义上,民众正义观念的不同内容之间呈现出序列性特征。具体体现为:在正义的主体上,民众对于政府的偏好要强于市场;在正义的原则上,民众对于公平的重视要强于公正;在正义的客体上,民众重视收入、财产、医疗卫生、就业、教育等内容,相对轻视参与、环境等内容;在正义比较对象的选择上,民众普遍倾向于同自己附近的人进行比较;在对代际正义问题的认识上,民众对于当代人之间的正义问题的重视要高于代际的正义问题。endprint
(三)中国民众正义观念具有弱重叠性特征
弱重叠性是指不同群体或个人的正义观念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别,相互重叠的内容很少,缺乏共识。按照具体制度设计的不同,正义观念的主体可以划分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国有部门工作人员、私营部门工作人员等若干类型。由于相关制度的影响,不同群体在收入水平、享有的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也对民众的内心世界产生很大影响,进而使不同群体的正义观念呈现弱重叠性特征。具体来看,这种弱重叠性的特征体现为,上述不同群体在正义主体偏好、正义原则偏好以及比较对象的选择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至此,我们只是对转型中国民众正义观念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总体分析框架,后续研究还需要依托这一分析框架,通过实证方法来检验前述理论假设和命题。
注释:
①参见Ben Jackson:“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Social Justice”.Political Studies Review,2005,(3).
②参见[美]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严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③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三联书店2001年版;应星:《“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陈柏峰:《“气”与村庄生活的互动——皖北李圩村调查》,《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④参见Norman Frohlich,Joe A.Oppenheimer and Cheryl L.Eavey:“Choices of Principl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Experimental Group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87,(3);丁建峰:《无知之幕下的社会福利判断——实验经济学的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3期。
⑤参见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杜建政,等:《国民公正观的结构》,《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7期。
⑥参见张光,等:《中国农民的公平观念:基于村委会选举调查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刘祥琪,等:《程序公正先于货币补偿:农民征地满意度的决定》,《管理世界》2012年第2期。
⑦参见张静:《转型中国:社会公正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⑧参见[韩]朴炳炫:《社会福利与文化——用文化解析社会福利的发展》,高春兰,等,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李春成:《价值观念与社会福利政策选择——以美国公共救助政策改革为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⑨参见Tom R.Tyler:“Why People Obey the Law”,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Samuel Bowles:“Policies Designed for SelfInterested Citizens May Undermine‘The Moral Sentiments:Evidence from Economic Experiments”.Science,2008,(320).
参考文献:
[1]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李路路,唐丽娜,秦广强.“患不均、更患不公”——转型期的“公平感”与“冲突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4).
[3]吕世伦,文正邦.法哲学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麻宝斌,等.十大基本政治观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5]张康之,李传军.行政伦理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Ernst Fehr,Klaus M.Schmidt.A Theory of Fairness,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3).
[7]陈叶烽.社会偏好的检验:一个超越经济人的实验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0.
[8]陈叶烽,周业安,宋紫峰.人们关注的是分配动机还是分配结果?——最后通牒实验视角下两种公平观的考察[J].经济研究,2011,(6).
[9]John F.Stolte. The Legitimation of Structural Inequality:Reformulation and Test of the SelfEvaluation Argument[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3).
[10]Jonathan Kelly, M.D.R.Evans .The Legitimation of Inequality:Occupational Earnings in Nine Nation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3,(1).
[11]Markus Hadler.Why Do People Accept Different Income Ratios?A MultiLevel Comparison of Thirty Countries[J].Acta Sociologica,2005,(2).endprint
[12]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中国公众的平等与特权观念调查报告(2012)[J].人民论坛,2012,(11).
[13]沈明明,等.中国公民意识调查数据报告(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4]Chunping Han.RuralUrban Cleavages in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D].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2007.
[15]潘春阳,何立新.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11,(5).
[16]郑永流,等.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7]James R.Kluegel,Eliot R.Smith.Beliefs about Stratification[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1,(7).
[18]李强.社会分层与社会空间领域的公平、公正[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1).
[19]黄光国,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0]李骏,吴晓刚.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2,(3).
[21]Mérove Gijsberts.The Legitimation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StateSocialist and Market Societies[J].Acta Sociologica,2002,(4).
[22]Alberto Alesina,GeorgeMarios Angeletos.Fairness and Redistributiv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4).
[23]李秉勤.社会公正的理论与英国的实践分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24]王丰.分割与分层: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的不平等[M].马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5]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M].北京:三联书店,2007.
[26]麻宝斌.社会公正正义测评的理论前提与基本逻辑[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2,(5).
[27]麻宝斌.社会公正测量的五个维度[J].理论探讨,2012,(1).
[28]Iain Walker,Heather J.Smith.Fifty Year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Research[C]//Iain Walker,Heather J.Smith,eds.Relative Deprivation:Specification,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29]陆益龙.乡土中国的转型与后乡土性特征的形成[J].人文杂志,2010,(5).
[30][挪威]贺美德,鲁纳.“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M].许烨芳,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何敬文]endprint
[12]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中国公众的平等与特权观念调查报告(2012)[J].人民论坛,2012,(11).
[13]沈明明,等.中国公民意识调查数据报告(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4]Chunping Han.RuralUrban Cleavages in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D].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2007.
[15]潘春阳,何立新.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11,(5).
[16]郑永流,等.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7]James R.Kluegel,Eliot R.Smith.Beliefs about Stratification[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1,(7).
[18]李强.社会分层与社会空间领域的公平、公正[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1).
[19]黄光国,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0]李骏,吴晓刚.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2,(3).
[21]Mérove Gijsberts.The Legitimation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StateSocialist and Market Societies[J].Acta Sociologica,2002,(4).
[22]Alberto Alesina,GeorgeMarios Angeletos.Fairness and Redistributiv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4).
[23]李秉勤.社会公正的理论与英国的实践分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24]王丰.分割与分层: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的不平等[M].马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5]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M].北京:三联书店,2007.
[26]麻宝斌.社会公正正义测评的理论前提与基本逻辑[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2,(5).
[27]麻宝斌.社会公正测量的五个维度[J].理论探讨,2012,(1).
[28]Iain Walker,Heather J.Smith.Fifty Year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Research[C]//Iain Walker,Heather J.Smith,eds.Relative Deprivation:Specification,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29]陆益龙.乡土中国的转型与后乡土性特征的形成[J].人文杂志,2010,(5).
[30][挪威]贺美德,鲁纳.“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M].许烨芳,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何敬文]endprint
[12]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中国公众的平等与特权观念调查报告(2012)[J].人民论坛,2012,(11).
[13]沈明明,等.中国公民意识调查数据报告(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4]Chunping Han.RuralUrban Cleavages in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D].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2007.
[15]潘春阳,何立新.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11,(5).
[16]郑永流,等.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7]James R.Kluegel,Eliot R.Smith.Beliefs about Stratification[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1,(7).
[18]李强.社会分层与社会空间领域的公平、公正[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1).
[19]黄光国,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0]李骏,吴晓刚.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2,(3).
[21]Mérove Gijsberts.The Legitimation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StateSocialist and Market Societies[J].Acta Sociologica,2002,(4).
[22]Alberto Alesina,GeorgeMarios Angeletos.Fairness and Redistributiv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4).
[23]李秉勤.社会公正的理论与英国的实践分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24]王丰.分割与分层: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的不平等[M].马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5]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M].北京:三联书店,2007.
[26]麻宝斌.社会公正正义测评的理论前提与基本逻辑[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2,(5).
[27]麻宝斌.社会公正测量的五个维度[J].理论探讨,2012,(1).
[28]Iain Walker,Heather J.Smith.Fifty Year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Research[C]//Iain Walker,Heather J.Smith,eds.Relative Deprivation:Specification,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29]陆益龙.乡土中国的转型与后乡土性特征的形成[J].人文杂志,2010,(5).
[30][挪威]贺美德,鲁纳.“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M].许烨芳,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何敬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