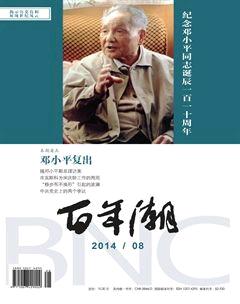“移步而不换形”引起的波澜
张颂甲
梅兰芳主张京剧改革要“移步而不换形”
我和梅兰芳的结识始于60多年前的1949年11月。那时,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刚刚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梅兰芳作为代表从上海来京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会后,他在京作了几场公演。在返沪途中,又应他的好友、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钱杏)之请,在天津作短暂演出,他在津受到热烈欢迎。
就在那一年,22岁的我离开母校北京师范大学进入天津《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做了一名记者。我在学校时就酷爱京剧,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四川国立中学读书时,还曾与同学排演过京剧《捉放曹》的一折。梅兰芳自然是我心仪已久的偶像。当我得知梅兰芳到津的消息后,多么想一睹大师的风采啊!于是,我便向报社采访部主任李光诒(后任北京《大公报》副总编辑)请缨,去作一次采访。当时,有的老同志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能否很好地完成这次访问曾表示善意的质疑,更激励我决心搞好这次采访。
1949年11月2日下午,我前往天津解放北路,在靠近海河的一所公寓里见到了梅大师。他身着深灰色西装,容貌光彩照人。那年他已经56岁,在北京接连演出十场营业戏和一场义务戏,但精神一直很好。当他看到记者时,毫无架子,笑容可掬地和我握手。
“您多少年没在天津登台了”?我问。
“有十四五年了吧”!他感慨地说。
他先从参加人民政协谈起。对于能参加盛会,感到非常兴奋,他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大会,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齐集一堂,共论国家大事,大家可以自由发表主政建国的各种意见,发扬了真正的民主作风……”
交谈不久,他的秘书许姬传先生也参加进来并不时插话。
慢慢的,我们的话题转到京剧改革和京剧艺人改造问题上来。一谈到本行,梅大师颇有主见地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他认为,时代变了,进入新社会,旧艺人需要改造是不成问题的,任何人不改造、不进步就一定落伍。虽然这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在人民政府的大力帮助下,绝大多数艺人从此将走上新的道路,看到这一点,他个人更感到由衷的高兴。
说到这里,一股发自内心的兴奋浮现到他的脸上。
谈起京剧的改革,他沉吟了一会儿。“京剧的改革又岂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他认为,京剧作为古典艺术,应该保留它的传统魅力。如果进行改革,也要保存它固有的规范和程式,只能渐进,不能冒失地大动手术。他说:“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革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技术)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思想)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才不会发生错误。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它有几百年的传统。因此,我们修改起来也就更得慎重,改要改得天衣无缝,让大家看不出一点痕迹来,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达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他特别强调,“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
听了梅大师这番京剧改革的主张,使我眼前为之一亮。
他列举苏联艺术家西蒙诺夫的话来印证:“最近来华访问的苏联文化科学艺术代表团团长西蒙诺夫对我说,中国的京剧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唱、念、做、打、舞合一,这在外国是很少见的。它既是古装戏,在形式上就不要改得太多,尤其在技术上更是万万改不得的。”
梅大师告诉我,他一向在致力着的京剧改革工作,无论在场面、音乐、剧情各方面随时都在修改。比如,在《苏三起解》里不把崇公道说成是十足的好人,而加强渲染他的同情心;在《霸王别姬》中,略减低“楚国歌声”的反效果;在《宇宙锋》剧中,把赵忠的自刎改为被误杀,等等。这是一些初步的小改小革,还不能令人满意。
他承认京剧界的沟通联系做得还不够,今后需要加强团结,互相砥砺,携起手来,使京剧成为团结教育人民,为人民所欢迎的艺术。
接着,他还就编写新京剧、如何练“武把子”硬功和是否继承“踩跷”苦工等发表了意见。
一篇访问记给梅兰芳捅了“娄子”,一时被困津门
和梅大师的谈话一直在亲切、和蔼的气氛中进行。他并不因我是一个青年记者而加以怠慢,相反,谈话都是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使我如沐春风,获益良多。不知不觉间,时钟已敲打了四下,我不便多打扰了,因为再过四个小时,他就要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登场演出了。我起身告辞。那时没有照相机,未能与大师合影,是为遗憾,只请大师亲笔签名留念。大师和许姬传先生送我到门口。
当晚,我写出《“移步?”而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的访问记,刊于次日(11月3日)《进步日报》第三版。文末刊登了梅大师的签名。
大约过了五六天,梅大师在天津演出已经结束,正准备返沪。不料,事起突然,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副局长孟波把我叫到局里,告诉我这篇访问记发表后,在北京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名家如田汉、阿甲、马少波等认为这是在宣扬改良主义观点,与京剧革命精神不相容,他们已写出批评文章,要刊登在报纸上。后来,是周恩来总理(一说陆定一)考虑到梅兰芳是戏剧界一面旗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很有影响,于是出面予以阻止,建议由天津市妥善处理。梅大师因为捅了“娄子”,暂时不能离津。
面临如此变故,最于心不安的是我这个“始作俑者”。过了两天,我怀着歉疚和不安的心情,再次登门看望梅大师。

梅大师从阿英局长处得知不幸消息后,精神紧张,心绪不宁,他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一位从旧社会走来的艺人,刚刚进入新社会,就遭此打击,他如何承受得了!我看他容貌有些憔悴,也瘦了一些。他焦急并带有埋怨地说:“那天我只不过随便和你说说,没想到那么快发表,又那么快惹来许多麻烦……”endprint
我歉意地说:“这事应由我承担责任。您可以写个声明,说那个观点本出于张某人,是记者强加给您的,与您无关。然后,我写个检讨,承担责任。”许姬传先生沉吟半晌说:“不好,那样反而会愈描愈黑,让人感觉到梅先生胆小怕事,推脱责任,不虚心认错。”他接着说,“不如由我出面写篇东西,讲明那天记者来访,梅先生有事,只说了几句就走了,对于‘移步的观点,本是许某人所说,应由我负责。”对此,梅大师和我都觉得这样处理也不妥。三人琢磨半天,终无良策。大师这次计划只演出7场,原定11月10日返沪,现在被此事缠身,等待处理,被困津门,一困就是半月。
梅兰芳被动作检讨,自己收回成命,度过这一关
那些天,不仅梅大师惴惴不安,我作为当事人,也是烦闷不已。我当即向报社社长孟秋江(《大公报》名记者、后任香港《文汇报》社长)、采访部主任李光诒汇报了有关情况。孟社长安慰我说:“记者如实报道是没有责任的。”话虽如此,我总觉得稿子未经梅大师审阅,也未经文化局领导审查,就贸然见报,事情办得不妥。
又过了几天,阿英局长电话告诉我:“梅先生的问题好解决了。”让我一同去梅大师寓所。
阿英对梅大师说,为解决这个问题,准备由天津市剧协出面,召开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请天津市知名人士参加,也请梅、许二位先生参加,颂甲自然也要参加,大家可以就梅先生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当时未用“批评”、“批判”这类词),梅先生也可重新修正一下自己的观点(未用“检查”、“检讨”这样的词)。然后将座谈记录在《进步日报》全文刊登,由《天津日报》转载,这事便可告一段落,梅先生会后可以返沪了。
梅大师闻讯,心里像一块石头落地一样,顿时有如释重负之感。当然,检查是必须做的,对于朋友们的苦心安排,他只能欣然接受。这个办法不仅解了梅大师的燃眉之急,也使我这个涉世未深、缺少经验、被牵连进去的记者得以解脱。梅大师和我都感到喜出望外。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座谈会召开。在市剧协主席何迟致辞后,第二位就是梅大师发言。他站起来作检讨说:“我很高兴在南下前期还有这样一次集会。我也很感谢大家在这回演出中给我以很多帮助。”在涉及发言主题时,他说:“关于剧本的内容与形式问题,我来天津之初,曾发表过‘移步而不换形的意见,和田汉、阿甲、马少波诸先生研究的结果不同,他们觉得我那意见是不对的。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大家都静静地听他发言。只见他沉着稳重,谈吐大方,讲话像在舞台上的唱腔、道白一样,字正腔圆,娓娓动听。讲话完毕,阿英局长带头鼓掌欢迎,与会者都热烈拍起掌来。今天看来,大师的检讨可以说“很不深刻”,只是表了个态而已。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大师的思想还没有经过“左”的思潮洗礼,所以他可能感到他的主张并没有什么错误,也并不知道为何获罪?在很大的压力下,他只能糊里糊涂地认个错,借以收场。他发言后,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华粹深、作家方纪等人相继讲话,对梅大师做了与人为善、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会场气氛相当温和,不像此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批斗会那样激烈,没有让梅大师感到难堪。最后,梅大师站起身来,频频点头向大家致谢意。
直到万家灯火时分,座谈会才结束。次日(11月28日)晚8时多,我到车站送梅大师、许姬传先生和梅大师的弟子言慧珠登上了去沪的火车。三天后,即11月30日,座谈会全文发表在《进步日报》第一版和《天津日报》第四版上。在记录稿的最后,我加注了一段文字:“本报记者前请梅兰芳先生发表对旧剧改革意见,因时间倥偬,访问记录未遑经梅先生审阅,其中内容或有与原意出入处,特向梅先生致歉。”
系铃人自我解铃后,虽无人再追究,但梅兰芳的一生并不轻松
对这次批评,除在天津开了一个会外,中央未让媒体做任何报道,因此,知道此事的人并不多。天津会上只有几位婉转地提了点意见,轻打轻放,几乎是不露声色。梅大师当场“收回成命”,由系铃人自己解铃,无伤大雅。至此,这次风波似乎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后来再无人提起,也没有人再议论这一命题,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
通过这次风波,我和梅大师倒是结下了“患难”友谊。他每次到天津来演出,都打电话约我到剧院后台见面,他边化妆边与我叙谈,很是亲切,并由许姬传先生陪同我在剧场前排加座看戏。
此后,因工作变换,和梅大师的直接联系渐渐减少,但我始终通过各种渠道关心着大师的一切。我偶尔写点儿有关京剧的小文章寄呈梅大师和许姬传先生教正。
回首60年前的这场风波,对梅大师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全国解放之初,他是满腔热情地拥抱革命,积极投身于戏剧改革运动中的。不曾想,刚刚参加到革命行列中来,就被狠狠地“蛰”了一下。这和他的和善、温良、恭俭、谦让性格对照,无疑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形成极大的反差。我能看出,那时他心里是充满了后悔、懊恼、着急和迷茫情绪的,着实愁苦了一阵,让他领教了“左”倾思想的无情和厉害。
这场风波对他后来的涉身处事来说,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从新中国成立后梅大师的整个经历来看,自那次以后,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因他谨言慎行,再未受到政治风雨和风浪的侵袭与冲击。在土改、“肃反”、审干、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他都能安然度过,这或许得益于解放初期的那次“教训”。
纵观梅大师从新中国成立后直到逝世前,他虽然还不至于“噤若寒蝉”,但总是让人感到有些“沉默寡言”。自那次天津风波后,好像再没有听到他关于京剧改革的任何理论观点和独到见解了。因为多年以来,一直没有人再提起,大师也未再次重申自己的主张,他的言路受到堵塞和扼杀,这对京剧的发展和进步来说,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损失。

1961年夏,大师因心脏病住院,周恩来总理特地从北戴河赶回北京探视。1961年8月8日,大师不幸在阜外医院逝世,享年68岁。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8月10日隆重地举行了追悼大会,各界政要和各界代表人士2000多人参加了悼念会,国家主要领导人都送了花圈以示哀悼。参加公祭和遗体告别的还有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等。作为一位艺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殊荣。
至今仍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梅大师提出“移步而不换形”主张后,几十年来再无人提及,好像大家都唯恐避之而不及。且不说梅大师主张本身就是真知灼见求之不得,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来说,再无人加以阐释和论述,也是很不正常的。
“文革”“旗手”把梅兰芳的主张评为反对京剧改革的“第一株大毒草”
谁也没有料到,事隔17年后,这件似乎已被忘怀的事情又被翻腾出来。人们不会忘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所谓京剧改革开始的。那位自封为京剧革命的“旗手”,扬言搞京剧革命几十年来,曾不断地受到阻挠和破坏;她还无中生有、煞有介事地说,早在解放之初,就有人“发难”了。她拼凑出有所谓“三株大毒草”,梅兰芳通过张某人的手笔发出的“移步而不换形”论有幸荣登“榜首”,是为第一株!而另两株是孟超的“有鬼无害”论和吴晗的“海瑞罢官实为彭德怀翻案”论。
此时,梅大师已作古。红卫兵为此曾几次冲入梅家,揪斗家人,有一群红卫兵甚至扛着铁锹到北京西郊万花山要挖梅大师的坟。所幸,周总理曾指示梅兰芳的墓碑要精心设计,因“文化大革命”使设计方案搁浅,梅墓迟迟未立碑,红卫兵找了半天,没有头绪,才悻悻而去。
至于我所在的北京《大公报》早在50年代即被中央明确为“财经党报”(中共中央文件:“《大公报》是党在财经工作方面的公开报纸”)。报社人员全部转变为经济工作人员,与文学艺术界逐渐断绝了联系,我和梅大师更是难得谋面了。因此梅大师的追悼会我也无缘参与。大公报社原属国务院序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周总理无暇顾及,便划归北京市代管,名义上由“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理,实际上是军管,大公报社全体人员都被关入旧市委党校,按军队连、排、班编队,天天搞运动,时时大批判,弄得人人自危。

一天,两位军人在第三分指挥部二连领导陪同下很神秘地把我叫到一间办公室,审问我和梅大师的关系,令我将当年密谋反对江青的事情交代清楚。我除了详细交代采写稿件的经过外,着重说明:1953年,随着《进步日报》由津迁京,恢复为北京《大公报》。按照中央级报纸分工,《大公报》由综合性报纸改为财经党报,全体编辑记者都转为宣传财经的新闻从业人员,我这个文艺记者也被动地转业为财经记者。从此,我不仅与梅大师逐渐失去了联系,和整个文艺界也不再联系了。由于我与戏剧界绝缘,再没有这方面的采写活动了。连面都难得一见,何谈“密谋”?他们再三审问,见我始终交代不出什么新材料来,只好作罢。后来,他们不再找我,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改革开放后的1995年,为怀念梅兰芳大师,我和妻子韩嵘曾到梅大师的故乡江苏省泰州访问。泰州市人民政府在梅大师祖居鲍家坝隔水相望、四面环水的凤凰墩上,兴建了古色古香、风格典雅的“梅兰芳史料陈列馆”,旧宅与梅兰芳纪念亭、梅兰芳汉白玉大理石塑像组成了一个完整和谐的建筑艺术群。陈列馆馆长刘华热情接待了我们,我把当年所写的访问记和座谈会记录稿等影印件相赠,当即被展入陈列厅中。我随后到梅大师塑像前与大师合影,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怀念。
(编辑 王 雪)
(作者是原北京《大公报》夜班总负责人、《经济日报》原副总编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