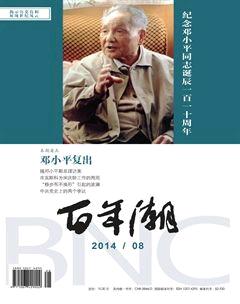周恩来与北京人艺的情缘
章文晋
周恩来总理对话剧的喜爱和关心有深远的渊源。他青年时代在南开中学时,就和同学们一起创建了南开剧社。他对话剧有着一种特殊的爱好,认为话剧是宣传革命道理的有力武器。
对北京人艺,周总理更是十分关注,据我所知北京人艺演出的剧目他都很认真地看过。北京人艺是他终生的朋友,无论院长、剧作家、导演、演员,以至舞台工作者,他都认识。他还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他们曾经扮演过什么角色。说起北京人艺,总理总是露出灿烂的笑容。
北京人艺的老人们都会记得,有一天晚上周总理去首都剧场看完演出之后,听说舒绣文大姐生病了,他走出剧场徒步奔向史家胡同北京人艺的宿舍,和随行的北京人艺的同志们形成了长长的队伍。走进舒绣文的房间,绣文要起身接待,周总理把她按到床上躺下,细问病情,得知是心脏病。他对绣文说,必须卧床休息。回到办公室,他让秘书告诉专家局,让最知名的心脏病专家为绣文会诊医治。
新中国建立不久,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虽然那时国内的经济情况十分困难,但却建起了中国第一处专门演出话剧的剧场“首都剧场”。首都剧场无论设计、建筑材料、音响设备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的。
人艺老院长曹禺是周恩来南开中学的前后校友,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已经相识。在曹禺遇到困惑时,周恩来总是帮助他化解。记得抗战初期,曹禺的新作《蜕变》演出,遭到国民党政府审查机关的禁演。曹禺修改了剧本再演出时,有些左翼作家又写文章批评《蜕变》是为国民党政府官员涂脂抹粉。双重的压力使曹禺极为困惑,这时周恩来即召开座谈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左翼评论界的文章是错误的,《蜕变》描写国民党政府官员积极抗战是好事,完全正确。这正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基础,这是大局,也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成果。《蜕变》是很好的作品。而曹禺的《北京人》演出之初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说《北京人》的思想内容是为封建社会唱挽歌,是与抗日无关的题材。周恩来为此让重庆《新华日报》召集座谈会,并发表长篇评论文章,阐述《北京人》是曹禺的另一佳作,批评了封建主义思想,为青年一代指出了前途。他还请曹禺和老舍先生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小酌,一直畅谈到深夜。
新中国成立以后,曹禺满腔热情地创作了当代题材的话剧《晴朗的天》,新篇历史剧《卧薪尝胆》,但这些新作却得不到“圈内人士”的赞赏,相反认为曹禺在新中国没有写出好作品,被称赞的只有旧时代写的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这些情况周总理也知道了。一次会议后,周总理特别要我留下来,问起有关情况。我直白地告诉他,确有此言论。周总理沉思良久,然后对我说,这种论调不对。曹禺在新中国的新作品都是好作品,无论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都是成功的,这些作品反映了曹禺思想发展的历程;反映了他对新时代、新思想的追求,而且对推动整个社会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反映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晴朗的天》也只有曹禺能写得深刻。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时期写出了《胆剑篇》,这是作家伟大胸怀的反映,是作家的良心。能鼓励全国人民克服困难增强信心,是作家对社会的巨大贡献。难道不值得称赞吗?周总理表情严肃,语调舒缓……一国总理,如此繁忙,却用了一个多小时来评论一位作家的作品,我十分感动。最后他突然问我:你的看法呢?我重重地点着头说,我也曾这样想过,但没有认真思考和研究。从此以后,我曾在多次戏剧创作座谈会上发表意见,为曹禺鸣不平。当然,我没有说过曾经听到周总理的意见。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一个著名作家和他的所有作品。
“文化大革命”中,文艺界受到极大冲击,所有的著名作家、艺术家都被关进“牛棚”,称为“牛鬼蛇神”。曹禺当然也不例外。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周总理、邓颖超大姐完全断绝了联系。有时我只能在大字报上看到一些他们的情况。周总理那几年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四人帮”一直在捣乱。
1970年,我从外交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没过多久,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邓颖超大姐叫我到西花厅家里见面。我感到意外,她怎么知道我回到北京呢?我十分激动,多年不见,有什么话题呢?
星期日吃过早饭后,等到10点半,我出门搭上无轨电车到中南海西北门。办公室已交代门卫,我很快走进西花厅,进入二道门即看到邓大姐,我跑过去紧紧握住她的双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几年过去了,一切如旧。坐下来她即说,恩来同志有点儿事,一会儿就来,他也很想见你。不一会儿周总理进来了,我见他显得有点儿憔悴,但精神很好。他让我坐下来,他却站着,心情像是突然沉下来。他说,老舍先生走了,你已知道,田汉也因病死在狱中。邓大姐插语说,孙维世也在狱中被害。客厅的气氛凝固在悲伤中。过了好一阵,还是周总理打破这难忍的一刻,他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话:你从干校回来看望过文艺界的朋友们吗?我听说巴金老被弄去挖防空洞,冰心老都过了古稀之年还到干校劳动。光未然手臂断过,也去干校劳动……那几年周总理工作极为繁忙,心烦的事情也多,但他却常常想起文艺界的朋友们。知道我回到北京就抽时间见面,他多么想知道这批朋友的情况啊。但他可能没有想到,我们这些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被关进“牛棚”,根本无法通消息,我也只能把从小报上看到的情况向他说一点儿。他突然问我万先生(曹禺)怎么样?身体还好吧?那时我家正好住在首都剧院旁的报房胡同,我听说,也曾见到曹禺在北京人艺看守大门,整天缩在门旁的小房里。我告诉周总理,曹禺在看大门,但我没敢和他说话。周总理显出不高兴的样子说:你不在文艺界工作,对这些朋友就不关心了吗?我无话可说。随即他命令我:你尽快抽时间想办法去看望万先生,就说是代表我去看望他,问候他还有方瑞(曹禺夫人)好。以后你应该多去,关心这些老朋友。我只得唯唯答应。时已过中午,我起身辞别,并抱歉占了他俩的休息时间。邓大姐把我留住说:“恩来平时没有休息时间,也休息不了,你今天来和他聊聊这些老朋友们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休息,坐下吧。”于是我只好留下,并与他俩一起吃完午饭才回家。
从干校回来,我被分配到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和周总理见面的机会多了,每次我都带去一些文艺界老朋友的情况向他汇报。
北京人艺演出的新剧目在全国来说是最多的,也可以说是最精彩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先生的创作热情至高,没有一刻停滞,他的话剧作品都是北京人艺首演。我个人也认为北京人艺最能够体现出老舍创作的风格与韵味。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演出的《龙须沟》《女店员》《骆驼祥子》《西望长安》及随后的《茶馆》等,无不成为时代的经典之作。这期间我还记得有一段插曲:《茶馆》初排正式演出前,北京人艺请市委领导观看并审查。市委宣传部一位领导认为该剧思想内容不健康,是在赞扬封建资产阶级,不能演出。这样的说法使该剧的导演和演员们都难以理解和接受。大概没有过多久,有一天我偶然遇到焦菊隐老师,他是《茶馆》的导演。他对我说《茶馆》不能上演了,市领导批评本子有问题,是否可以请周恩来总理来看看这出戏,他对人艺一直非常关心,而且这是老舍先生的作品。我答应了他,随后很快找到机会向周总理汇报了。没过几天周总理就到首都剧场来看《茶馆》彩排。看完之后,他和焦菊隐及演职员座谈。周总理首先称赞戏排得好,随即说这是一出好戏嘛,没有什么问题。在舞台上反映旧社会,写出封建资产阶级的没落,这很好,让人们了解历史,还可以教育年轻一代,使他们认识新社会的可贵。周总理还拉着于是之的手说,你演得好,塑造了这样一个没落阶级人物的典型形象。
周总理与老舍先生也是在抗战时期就相识、相知,成为好朋友的。当周总理知道老舍先生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时,还特别去灯市口老舍先生家中祝贺。“文化大革命”中得知老舍先生去世,他十分伤心,还不断责备自己没有好好照顾这位老朋友。
北京人艺的经典演出剧目还有许多: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周总理都不止一次地去观赏。他对《关汉卿》尤为赞扬,还邀请陈毅元帅与贺龙元帅去观看,并与演职人员合影留念。他认为这是田汉最成功的作品,对该剧的主要演员,扮演关汉卿的刁光覃,扮演朱廉秀的舒绣文,还有扮演蔡文姬的朱琳,以及扮演《雷雨》中四凤的胡宗温等人更加关注。他谈起这些演员的演技总是津津乐道,意犹未尽。有时候周总理忙完一天的工作,突然想到去看戏,于是带着一位副官,警卫员偶然会打电话叫上我一起去首都剧院。副官买几张票,都是后排的剩余票,我们便悄悄地进入剧院去看后几场的演出,周总理说要听听演员的台词是否能传到每个观众的耳中。也有过这样的情景,周总理进入剧场后,被人艺的同志发现了,要他到前排的首长席去坐,周总理会很不情愿。
周恩来总理不仅对北京人艺情有独钟,他与青艺、总政话剧团、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都极有感情极为关注。周总理一向认为文艺是宣传与发展进步思想最有力的武器,应该而且必须给予重视。
(摘自《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增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