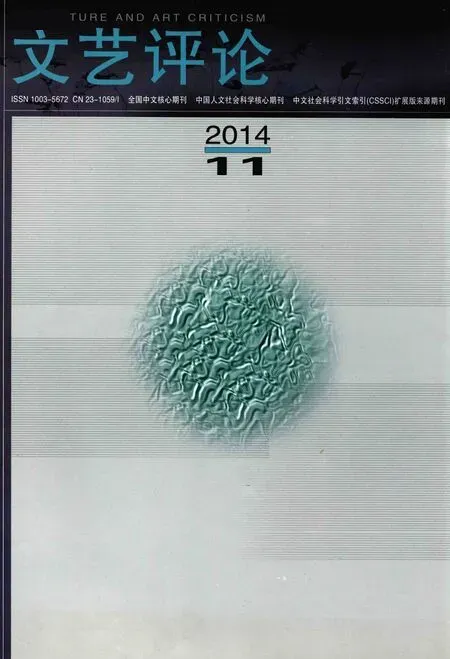数字电影本体论
○熊 立
传统的电影本体论建立在胶片电影的基础上。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电影生产的转型,传统的电影本体论的基石已经被瓦解,因此,重建能够涵纳数字技术时代电影创作的现代电影理论就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本文从数字技术的角度对新语境下电影文本生成的诸多环节予以了分析,认为超真实性、交互性、自由情感是数字电影特有的三大属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数字电影的本质规定性——数字电影本体。数字电影是动态的有机活体,其生命力来自多要素之间的交互共生,而不仅仅是来自某一要素。
一
从字面意义而言,电影本体是指电影的最初本原,这个“本体”是唯一的,不可能有两个或更多的“本体”。而电影本体论是对电影本质的形而上研究,一方面,“对于本体论哲学来说,本质与存在必须同一,这是必要的前提”。因此,电影客观存在就是电影本质、本性,对处于不断变化中电影的不同认识就会形成不同的本体论。另一方面,由于本体论是人对“本体”进行研究时获得的主观性认识,不同的研究背景、研究者和研究方法等因素也决定了本体论呈现多种面貌。因此,自从电影产生以来,关于“电影是什么”的问题,虽然随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在不断走向深入,但目前为止仍然未达成共识。在世界电影理论史上,对电影本体的研究集中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著名电影理论家达德利·安德鲁将经典电影理论划分为两种主要思潮:造型主义和写实主义,与此相对应的是两种对立的电影本体论,分别是蒙太奇本体论和摄影影像本体论。前者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爱森斯坦,后者则以巴赞为代表。蒙太奇理论认为电影的意义不在于单个的镜头,而是取决于连接镜头的方式和手段——“蒙太奇”。爱森斯坦曾强调指出:把无论两个什么镜头对列在一起,就必然产生新的表象、新的概念、新的形象。通过镜头的对列冲突,产生新的意义,以引导观众的理性思考。这是爱森斯坦“杂耍蒙太奇”和“理性蒙太奇”要旨所在。普多夫金也指出“电影艺术的基础是蒙太奇”。虽然,蒙太奇理论在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之后,不断地有学者在摸索和总结其规律,但蒙太奇是胶片时代,通过镜头的剪辑而形成的产物,这一点大多数理论家都认同。如电影美学家贝拉·巴拉兹认为:蒙太奇是电影艺术家按事先构想的一定的顺序,把许多镜头联接起来,结果就使这些画格通过顺序本身而产生某种预期的效果。同样,巴赞在描述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的蒙太奇时也说,蒙太奇产生的意义并不在影像中具体表现出来,而是银幕上一个影像叠加在另一个影像之上后的抽象的结果。在这种风格的剪辑中,意义并不是影像所固有的,与被表现的物的意义是两回事。可见,“蒙太奇”本体论是电影早期技术发展的阶段性产物。
第二种可称为“影像本体论”,与第一种论点相对,它认为存在于虚拟三维空间里的影像是电影的本体。1945年巴赞发表了《摄影影像的本体论》,并于1958年将自己的论文集定名为《电影是什么》,从而形成了他的“影像本体论”。巴赞认为“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象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电影是从一个神话中诞生的,这个神话就是完整电影的神话”。①巴赞“影像本体论”的核心和基本观点是影像与客观现实中的被摄物同一。因为“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参与为基础的,唯独在摄影中,我们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②所以摄影取得的影像具有自然的属性。同时,他认为电影起源的心理原因是再现完整电影的神话,也就是再现声、色、主体感受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这种心理因素决定了银幕形象的真实感,决定了电影技术的完善和电影艺术的发展方向:再现一个真实的世界。正是在此基点上,巴赞提出了不以人的介入为特性的、能够复现现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来反对蒙太奇本体论。可见,巴赞的理论建立在特定时期电影的实践基础之上,银幕的影像脱离不了现实的客观存在物。当摄影术还是电影影像生成的为唯一方式的时候,巴赞的摄影影像的本体论无疑是符合电影特性的界定。
一个多世纪以来,电影的技术领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每一次电影技术的重要发展,都毫无疑问会对电影的哲学——美学发生革命性的震荡。彼得·沃伦认为:“数字技术给电影的创作和接受所带来的变化自然会引起电影理论的重新思考。与此同时,我们也越发对早期电影感兴趣,因为数字技术使人回想起早期电影的技术和形式,两者的比较则会引发人们对电影本体的重新思考。”③沿着彼得·沃伦的思路,还原历史的语境,从20世纪电影发展的史实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爱森斯坦和巴赞都是从电影特有的技术特性出发,前者提出的蒙太奇本体观是默片电影艺术创作的总结,而后者的摄影影像本体论,则是在声音和色彩技术进入电影创作后对电影作为艺术的本体的认识。而后,随着技术的进步,电影复原现实的可能性大大地提高,人们对电影记录特性的要求增强,而爱森斯坦的蒙太奇只是被当作与巴赞长镜头并列的电影的艺术手段存在,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成为电影理论研究的重要范畴与基本出发点之一。但是,不管是爱森斯坦的蒙太奇本体观还是巴赞的摄影影像的本体论,应该说可以被看作对“彼时”人类对电影本质把握的顶峰。随着时代的变迁,电影技术的发展,“彼时”的电影观显然不能适用于“此时”的电影现象。如果我们承认对电影本体的认识,是主体对客体所进行的“对象化”活动。那么,要认识电影的本体,主体必须得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作为客体的电影在这一个世纪以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进一步而言,如果我们将电影视为一个在时间维度上不断延展、变化和生成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在主体的认识活动中一个静止凝固的影像,那么,在新的语境中,作为电影客体的变化必然导致电影本体的位移和跃迁,也必然要求我们修正对电影的看法。
二
电影是一门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现代艺术,从诞生之日起它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变迁:从固定到运动、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单声道到立体声、从窄银屏到宽荧幕。在每一次重大的变革中,技术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电影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人类运用技术对电影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力不断拓展的过程。然而,以往的电影本体论只是将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没有立足在技术的本性之上考虑。如今,因为数字技术的强势介入和全面运用,电影正在经历一次“华丽的转身”,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回顾电影诞生以来的技术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之前的技术进步都是建立在胶片电影的基础之上的,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却正在超越胶片电影。于是,“胶片电影的技术进步与超越胶片电影的技术进步,构成电影技术史甚至整个电影发展史的两个时期”。④而现在的电影,正处于第二个发展时期的开端。
今天的科学技术,正处在更新换代的时期。从机械、光学、声学、化工到电气等领域,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把诸多的成果传递到了电影这里。数字技术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电影制作、发行、传播、接受中。“数码技术的使用已经被融入到电影生产的各个阶段:布景设计、拍摄、剪辑、音效、后期制作、发行和放映,就连表演也未能与数码设计划清界限”。⑤电影在技术领域所遭遇的冲击,以及日益全面和深刻的变革与更新,几乎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加以表达。“越来越多的影片运用电子游戏的叙事手法和表现方式,在卖座的好莱坞电影以及相当数量的美国独立制作影片中,我们都不难发现这样的经典范例”。数字技术给电影带来的冲击,不仅使电影形式不断的丰富和变化,也给沉寂多年的电影研究吹进了一股强劲的春风。美国艺术批评家格林伯格曾言:“每门艺术都不得不通过自己特有的东西来确定非它莫属的效果。显然,这样做就缩小了该艺术的涵盖范围,但同时也更安全地占据了这一领域。”“如此一来,每门艺术将变成‘纯粹的’。并在这种‘纯粹的’中寻找自身具体标准和独立性的保证”。⑥电影实践对新的技术全面吸收已经成为当前的电影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事实,爱森斯坦的蒙太奇本体观和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的理论起点已经不复存在。据此我们认为,要回答电影本体的问题,一方面必须分析电影艺术的本质、本性,另一方面也要正视电影的现实存在,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理解才能回答电影的本体问题。即,应该坚持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立场。
当代西方的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它对电影的艺术和美学带来的冲击。“的确,很多电影研究学者对于技术的极大兴趣就在于它和美学实践的联系上面”。⑦国际电影界,一些初步的、零散的、试探性的理论总结正悄然展开,如《多幕影院之外:电影、新技术和家庭》《重新创造电影:媒体融合时代的电影》《浸泡的艺术:数字一代是如何重塑好莱坞、麦迪逊大道和叙事方式的》《21世纪的好莱坞:转型期的电影》《电影的未来:数字时代的银幕艺术》等等。同时,有关的理论观点也在逐步的探索中趋于成熟,如,从对网络视窗技术的模仿中,学者们提出了“电影阵列美学”⑧、“网络浏览美学”⑨等观点,也有学者借鉴电子游戏的特点,把电影中的互动叙事看作是“空间游牧形式”⑩、“花园路径式”的叙事策略。⑪另外,有关电影镜头剪接的新方式和新形态,也形成了新的术语,如“拼贴蒙太奇、链接蒙太奇、空间类蒙太奇”等,有待于电影的实践发展和理论的验证。种种迹象都在表明,电影的理论研究开始关注电影由于技术更新所呈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新动向。从表面的技术层面,到创作层面,直至理论层面上的美学研究,正在全方位地展开。
马克思哲学认为“实践——理论——实践”永远是一条循环科学的道路。电影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对待电影的本体—本质也应该按照一个历史范畴来处理。艺术本体在历史与时间中生成,艺术伴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不断地创新,不断地生成,不断地积淀,不断地超前。“艺术本体的生成性原则向我们表明,必须以历史的眼光、生成的视域、流变的辩证法来思考艺术本体”。⑫开放技术条件下的本体论,要求保持电影理论自身和不断发展中的电影表现形式和手法的统一,因此,电影本性的发展从理论上讲应该是永无穷尽的,电影史的延续性也要求这种开放性。尽管现阶段数字技术在电影中的发展还是“现在进行时”,无法预言它的未来走向,但是我们却能够通过研究目前数字技术揭示世界的方式,来探究其本体论潜质。因此,立足于电影发展的角度,从当下的电影实践中的具体的、鲜活的作品出发,建立数字电影本体论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理论自我更新的需要。
三
与传统电影相比,数字电影最大的特征就是用“比特”来替代“原子”物质,作为电影构成的新材料和新工具。它给我们看的,不是传统胶片上的化学试剂通过光学透镜与机械运动所记录的现实物质世界中的光影变化,而是运用计算机通过数字组合生成的视觉魔幻。因而,数字技术改变了电影反映世界的方式。数字技术也造成了电影语言的变化,传统电影的画面、蒙太奇、表演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数字制作技术的影响。电影观众将面对一个重新组织起的影像和声音世界,接受新的电影语法。如果不掌握数字技术就无法进行数字电影创作,同时,不了解数字电影的特性观众也不能领会技术的魅力。在这种基础上,数字技术对电影的变革由以往的表现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发展为影像生成方式、传播、存储、发行、放映的变化,从而使电影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这是数字电影本体论建立的前提和基础。从这个层面出发,数字技术使电影具有了超真实性、交互性和自由情感的特质。
1.超真实性。在数字技术的发展日趋成熟的状态下,由计算机参与创造的电影将在视听、触觉、嗅觉等感官上全方位模拟真实成为可能。此外,通过对物理时空的大胆重组、对现实与想象界限的僭越,数字技术将为人类创造由“比特”构成的视觉化数字空间,在这个与原子构成物理空间不同的虚拟世界中,数字技术创造的超真实将为人类带来感知的新体验。在这种电影中,视觉化数字空间创造出的仿真环境将与“真实生活”本身没有区分,观众置身于其中,不在是以往通过传统影像所能接受到的平面的、单纯视听的信息,而体验“浸泡式”立体的、全方位的感受。到时,坐上太空船周游宇宙与在电影院坐在模拟仪器上“感受”周游宇宙将没有什么感觉上的区别。可见,数字技术的超真实性使电影不仅能为我们展示“已有”现实世界的存在,更重要的它还对人类的“尚无”的生存境遇敞开,因此,如何正确利用数字技术、营造数字空间,寻找到一个“诗意地栖居”的精神家园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并亟需解决的重大命题。
2.交互性:传统电影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表现主义或者是先锋电影,它们履行的是从影片到观众的一维、单向输出,观众与电影的互动,主要是思想情感层次方面的反馈和交流。而数字技术使观众和影片之间的互动达到了实践操作的层面,观众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对原作进行“二度创作”。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用“互动式多媒体”(InteractiveMultimedia)一词来描述电子计算机的图形界面。“数字技术电影与传统艺术相比,具有实时互动性、多媒介性、多维性、虚拟沉浸性等特性”。⑬这种特有的双重虚拟互动性机制,使得接受者不必再像传统的电影观众那样一味接受或者遵从来自影片独有的审美判断,他们可以从容地、自由地表达自己对影片的意见,甚至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参与影片的改写,决定故事的走向和结局,从而实现影片与观众不再分离。1996年,互联网上播出了第一部“交互影视剧”——《现场》,观众可以同影片中的人物交朋友,还能展开想象力重构故事情节,从而实现和影片的对话与互动。观众不再是影片情节的被动接受者,而一跃为故事的创作者,这不仅使观众获得了主体的自由,也将使影片内容不断更新,获得富有连绵的生命力。因为对于艺术来说,“不管是野蛮人,还是文明人,都不是由于本身的身体特征,而是由于他所参与的文化,才获得其存在的。艺术的繁荣是文化性质的最后尺度”。⑭显然,观众参与数字电影艺术的创作,能更好的促进电影事业的繁荣,这是电影作为大众艺术,在大众文化兴起的时代,充分发展的良性路径。
3.自由情感。艺术品的魅力在于它“较之自然的审美客体和其他人工创作的非艺术品审美客体更容易引发自由情感”。⑮有史以来,不同种类的艺术品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构建并拓展、延伸着人类的审美经验。传统电影以胶片为依托、建立在单向度传播的基础之上,它帮助建构人类审美经验的途径不外乎两条:即“现实的途径和理想的途径”。⑯写实型电影在审美效应上的表现主要是通过再现现实引起审美主体的情感共鸣即移情来实现的,理想型电影则主要是通过引发审美主体奇特的情感体验来吸引观众的。而借助于计算机高超的技术,再加上创作主体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数字技术可以将理想与现实不受时空限制地任意组接、合成、转换和创造,创造出虚实共生的空间和无限的艺术形象。“全方位”“沉浸”于数字电影现实与虚拟交织的世界,可以满足人们尽情的放松的交流和满足自己的审美趣味的需求,不仅能引发观众传统的情感体验,还能激发观众超越现实的自由情感,实现传统电影难以企及的梦想。因此,数字技术电影大大开拓了人类情感的深度和广度,使艺术主体第一次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审美自由,从而将人类的审美经验导向了一个新的高地。
综上所述,超真实性、交互性、自由情感就是数字电影特有的三大属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数字电影的本质规定性——数字电影本体。数字电影是动态的有机活体,其生命力来自多要素之间的交互共生,而不仅仅是来自某一要素。正是靠着以上的这一本质规定性,数字电影与传统电影划清了界线。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将数字技术因素纳入到电影理论研究之中并非要否定以往传统观点对电影艺术的研究,而只是认为,在数字技术兴起、在大众文化范畴的商业性电影风靡全球的背景下,我们的理论研究应该将这些因素一并纳入到电影本体的研究之中。正如声音和色彩技术在历经冲击、震荡、调试的曲折历程才得以成为电影完美的组成部分,传统电影观念对于新技术的接受、吸纳亦须适应和调整。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数字技术的运用从稚拙到成熟,电影会突破“技术至上”论的桎梏,在技术与艺术两极中求得有效平衡和完美结合。正如诗人福楼拜在一个多世纪前曾预言,艺术愈来愈科学化,而科学愈来愈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将在山顶重逢。相信人类定会摆正技术和艺术的关系,福楼拜的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现实,电影艺术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