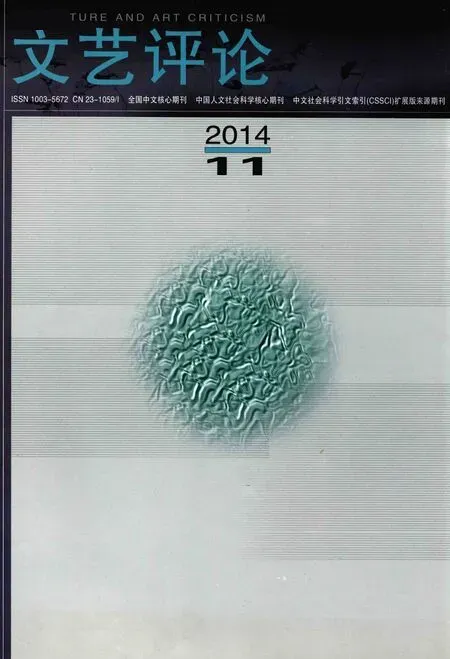新现实主义美术的批判性解读
○曾 玲
社会批判性是现实主义美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和素养,这一点在西方现实主义美术传统中表现得较为明显。而在我国,由于美术创作受主流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多以歌颂美化和客观纪录为主,批判性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现实主义美术创作中是缺失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界,现实主义文学奉行独特的艺术立场,“对现实世界的真诚关注和对人类众多成员生存处境、生活命运的热烈关切与同情,注定了现实主义文学奉守积极入世的、有批判锋芒的、有理想追求和生活寄托的艺术精神”,①这使得他们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性表现得更为强烈和直接。与之相比,现实主义美术的批判性要含蓄很多。近年来,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开放,以及艺术家对社会生活关注的愈发深入,使一度艺术与现实相脱离的状况有所改观。对社会生活中阴暗的以及不和谐现象的揭露也逐渐在美术作品中有所体现。特别是对社会底层人群的关注也成为当代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重要题材。由此,新现实主义重拾自我批判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四分之三的农业国家,多年来,农村、农民、农业共同构成的所谓“三农问题”也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中共中央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且每年都下发指导农村工作的政策性文件,就是要研讨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如何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体现了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农业农村问题的高度重视和逐步解决好农业农村问题的坚定决心。
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在向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是必经的过程。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这是不可避免的。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全面发展。之后几年,基本上是每年增加的农民工人数都维持在一千万左右,到1996、1997年的时候,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已经达到八千万。截至2002年底,据农业部的统计,农民工达到九千四百六十万。②如此庞大的数字直接引发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不可否认农民工对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对城市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积极贡献,但由于各种客观现实原因,农民工在实际生活中还是不能得到社会的公正待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歧视和不理解,这一群体始终无法融入社会的主流,只能游走于都市生活的边缘。所以,农民工问题既是一个公众关注的话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对于农民工来说,平等的工作权、劳动报酬权、健康权、生命保障权在现实生活中都离他们很远。毋庸讳言,农民工群体已成为关乎社会能否和谐发展的重要问题。已经达到过亿规模的农民工群体,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力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就是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决他们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解决了社会矛盾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批敏感的现实主义艺术家认识到处于城市边缘的民工群体的尴尬处境,试图通过表现民工的生存状况唤醒社会对这一群体的重新认知,用绘画的艺术表现为人们提供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视角。正如忻东旺在1995年为自己的作品起名为《诚城》所隐喻的内涵就是“诚心诚意地做一个城里人”,这是多么质朴的期盼。忻东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农民工群体、表现农民工题材,体现出其所具有的艺术敏感。同样是从农村走出的探索者,城市生活所经历的曲折辛酸,让忻东旺对踩着同样足迹的后来者抱有深切的同情与期待。之所以画农民工,正如他所说:“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一社会景观是极具时代表情的,而艺术作品的艺术魅力和价值除了绘画本身的因素之外,更是应该承载反映社会和时代批判的责任。”《诚城》是其早期代表作,创作灵感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民工潮,一时之间,城市的街头车站涌现出大量的肩扛行李、手拿工具的农民,促使了其表现的欲望。画面中的5个人物显然是初次进入城市,兴奋、彷徨、迷茫和期待的复杂情绪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在空间感的处理上,忻东旺弱化了纵深空间对主体形象视觉冲击力的消解,同时将装修工粉墙的手法应用到油画创作,笔触感的突出使画面极具质感,形象的块面堆积塑造出强烈的立体感,也发挥了油画所具有的艺术特质,展现出具有质感的美。
在《诚城》之后,忻东旺又先后创作了《明天,多云转晴》《适度兴奋》《远亲》等,随着对问题认识的逐渐深化以及艺术表现技法的成熟,忻东旺己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化的艺术语言,这在第十届全国美展获得金奖的作品《早点》中得以充分体现。《早点》的创作动因源于忻东旺真切的生活体验:在每天路过的胡同里,破烂的砖墙上歪挂着一块三层木板,上面两个红字——“早点”。嘈杂、破落的环境中,即将开始一天工作、生活的人们,享受着辛劳前的休憩。尽管环境如此的不堪,却丝毫没有削弱他们的享受和满足感:每人手中一碗热腾腾的豆腐脑,如果能有两根油条、一个鸡蛋就已经是一种奢侈。尽管《早点》中的人物并不具有典型的民工特征,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在他们的形象中,感受到更多的是生活的艰辛和获得食物的满足感。忻东旺把握了街边饭摊食客们的心理:不愿意别人看到他们内心的切望之态,但又不得不忍受路人无意的窥视。早餐在此时只是满足身体需求的必需品,因此每个人都在专注于自己的食物,彼此之间没有交流。作品中人物神情、姿态自然,表现手法上更加纯熟,艺术地再现了最为平民化的生活瞬间。忻东旺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庞大的、被都市社会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形象。在忻东旺寄予了他们深刻理解的同时,对其生活处境也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与不满。对人物形象如此真实、生动的挖掘与再现,源于忻东旺对艺术真理的探寻和追问,正如他所说“一切真理的内容都是隐含在事物的内里,只有通过‘神性’的发掘才能提炼‘天机般的真实’。那么所谓‘神性’就是我们的感受与敏质以及思考和判断,所谓‘天机般的真实’即是艺术的真实”。对艺术真实的探寻让忻东旺的作品形成了有别于他人的独特审美感受,也许表现的视觉形象是丑陋、委琐、靡顿的,但却让人感受到长期传统现实主义美术创作中所缺失的真实美。
随着农民工问题被关注和讨论得越发深入,对这一群体的艺术表现在美术界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群体性。借助这样的表现题材,艺术家体现更多的是对人的生存状态、人性和社会等级差异的精神关照与价值批判。这种关照与批判在徐唯辛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当代现实生活的思考和关注使徐唯辛的作品体现出一种人性关怀和时代价值。近些年,由于社会问题的增多以及问题矛盾的逐步激化,导致人们对诸多社会问题和现象不满,这在艺术表现语言中被极端化地呈现,各种对现实生活反讽、嘲弄的表现形式成为艺术表达的风尚。而在徐唯辛的作品中,很少表达激烈的情节性冲突,简单到近乎直白的叙事表达让徐唯辛的作品有着异于常人的面貌特征。纵观徐唯辛的艺术历程,他总是不断变换着艺术表现的主体,这种变换一方面源于生活经验所给予他的创作冲动,而另一方面则体现出社会价值判断的转变所形成的主观性选择。从他早期具有浓郁少数民族风情特色的《馕房》《酥油茶馆》《圣地拉萨》,到现实主义创作的转折性作品《酸雨》,直至为其带来巨大声誉的农民工题材的系列作品,能够清晰地看出徐唯辛艺术创作的发展路线。对人物形象内在精神性的表达是徐唯辛艺术创作所追寻的目标,也是促使其艰难探索和转变的重要诱因。1998年的“过道”系列作品便已经明显倾向于对绘画本体语言的实验性探索,将关注的视点定位在具有特定时空意义的当下生存环境中,冷漠、空旷、静谧的意境营造凸显出整个社会所具有的焦虑和躁动。徐唯辛也是较早关注民工形象、民工生活的艺术家之一,他敏感地观察到这一重要社会人群在城市环境中的尴尬处境。虽然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和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时常没有保障,他们是一个值得同情和关注的群体。在以往很多艺术家的作品中,农民工都是被怜悯、同情的对象,而徐唯辛又给予了他们必须的尊重与人性尊严,表现他们的自信、力量和美感。
《工棚》就是这样一件代表作,在第十届全国美展展出后获得极大反响,掀起了一次对农民工生存状况关注和讨论的热潮。《工棚》表现了一群在艰苦环境中生存的农民工形象。破败的环境、粗糙的食物、简易的设施衬托出农民工们生活的凄凉和艰辛。在人物塑造上,徐唯辛扎实的写实技巧在画中得以充分体现。人物在共性基础上的个性化塑造是成功的,虽然没有更多的故事情节,但其传达的精神内涵隐喻于一个个饱经岁月和生活磨砺的人物形象之中。画面人物经过审慎的构思和细致的表现营造出和谐而统一的情调氛围。在徐唯辛的民工题材作品中,大多对人物造型都采用正面表现的形式,并尝试将自身融入到这一群体之中,平民化的表述语言,平视的表现视角,给予了这一群体缺失许久的尊重与理解。他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有着一份淡定与从容,不论是在人物较少的“打工”系列还是人物众多的《工棚》中,这种情绪的宣张都表现得尤为明显。这里的人物既不是美的,也不是丑的,他们只是生存在我们身边真实的个人,是我们社会组成的重要元素。然而正是这份艰苦环境下的平淡体现了更为突出的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批判社会等级、贫富的差距以及人性的冷漠和贪婪。这正是徐唯辛想要表现的与传统现实主义高扬真善美不同的,具有“批判性”、“真实”、“社会良知和人文关怀”的新现实主义创作的精神品格。正如徐唯辛为自己订立的艺术创作“四项基本原则”所追求的“人文情怀,贴近现实;题材当下,明确清晰;不断突破,讲究形式;精湛技艺,具像写实”一样,正是在对社会的介入与批判过程中,新现实主义美术才凸显了存在的价值并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