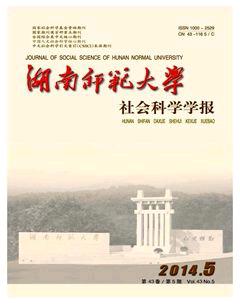儒家文化与明清两代湖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
摘 要: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在治理湖南少数民族地区时,逐渐调整控制与管理方式。到清中期,开始强化儒学教育、鼓励少数民族参与科举考试,有效地增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融合与政治认同。以花瑶地区为例,从明清史志资料以及实地调研所收集到的诸多一手资料中可以看到,随着明清两代中央政府治理花瑶地区的策略转变,使得儒家文化极为深远地影响到了花瑶民族的政治、族群与文化。
关键词:社会治理;儒家文化;花瑶
作者简介:黄勇军,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湖南 长沙 410081)
历史上,在湖南省中西部的雪峰山脉,聚居着大量瑶、苗、土家等少数民族,花瑶{1}就是其中之一。据花瑶内部流传的手抄本历史资料《雪峰瑶族诏文》的记载,花瑶先民于(元末徐寿辉)天启元年(即元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从江西出发,几经流转,逐步迁入隆回县北部雪峰山脉。{2}其所经历的不断迁徙的历程,不仅体现出“性喜迁徙”{3}、“富有移动性”{4}的山地民族特征,更体现出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极其艰难,与外部政权、不同族群之间又处于接连不断的冲突与战争之中,导致他们的生存空间不断萎缩,从而被迫迁徙。{5}面对这一地区的复杂情况,明清两代的中央政权在进行治理与管控时,采取了许多并不相同的策略,并通过不断强化儒家文化的渗透与示范效应,有效地增强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与社会稳定。
一、武力攻伐与文化融和:明清两代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方略
在我们所收集到的与隆回县花瑶地区直接相关的史料中,明隆庆年间所编撰的《宝庆府志》是较早出现的文献资料之一。不过,在这部《府志》中尚未出现专门介绍花瑶的篇章,仅在“卷四·风俗”中援引历代史志中的相关记载,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武冈志云:‘地僻万山,民徭团聚,杂处寡信。……城步志云:‘县民有三,一曰居民,敦礼明伦,信巫勤织。二曰徭民,性尚慓悍,好武少文。三曰苗民,椎鬟跣足,佩刀挟弩,语言侏离,辄习击刺。”
从明代史志中较为简单的关于“民”与“瑶”,以及“居民”、“瑶民”、“苗民”的分类中可以看出,对于居于主流与强势地位的汉族人而言,史志所要记述的重点就在于“民”(居民)的生存状况,尤其是“民”之中所出现的那些具备史料价值的人物与事件。而对于与“民”杂处,或是远离“民”独处的其他少数民族,无论是“瑶”还是“苗”,都被潜意识地视为“非我族类”,被一笔带过。或许,在当时撰写史志的汉族儒生的内心深处,其实无论瑶、苗,都是一个更为宽泛的群体,以“蛮”,或是“蛮獠”予以统称之,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清同治《武冈州志》所设立的关于瑶苗历史与风俗的“峒蛮志”这一条目名称之中看出来。换言之,除非被统称为“峒蛮”的少数民族的存在,直接影响到了周边汉族人的秩序感与安全感,或是需要进行带有猎奇性质的对于那些不同于汉族人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的考察与比较之时,作为“非我族类”的瑶苗,才具备最为直接的记载价值与述说意义。以汉族为中心编撰而成的历代史志,关于瑶苗等少数民族的记述,除了风俗、习惯上的不同之外,更多的笔墨,都被集中于少数民族与政府之间所发生的绵延不断的战争与攻伐。
从明隆庆《宝庆府志》中还可以看到,明代宝庆府地方防御体系,主要以瑶苗二族为重点防范的对象,“卷一”中关于城步县的记述中就强调了这一问题:“城步县本古巫黔中地,唐为镇,元为武冈路儒林书院,历代处蛮峒阨口。国初废书院设武冈州城步巡检司摄土款以控苗瑶。弘治十七年,洞苗李再万僭号作乱,寻讨平之。”并在“卷四·武备”中对驻军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守备司在武冈州城南关,正统二年平峒苗之乱,奏设。”而该府志中所涉及的诸多武将的简单传记,其功勋卓著者往往与弹压苗瑶之间的战争相关。
明代以来所形成的这样一种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相对抗的状态,也集中地体现在了花瑶所居住的地区,如清同治年间编撰的《溆浦县志》“兵防”中,在列举了宋以来瑶族人的反叛,以及与外族人之间的诸多战争后,直接提出了如下论断:“《陶志》以瑶防、兵防分为二,以溆之宜防者莫如瑶也。”从而将“瑶防”的概念从兵防之中单独提出来,并将其作为主要的防卫对象。
不过,即使在双方对抗相当明显的明代,在这一更为宏大与明显的族群间的抗争史之外,依然存在着另外一条更为隐蔽也更为细微的族群间关系演进史,那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所发生的或民间、或官方的交往与互动。虽然明代湖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与对抗仍然时有发生,但中央政府对于这一地域的控制日渐强势、成熟,汉族人也从人数、地理范围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以此为背景,瑶汉民间的交往与互动,也开始出现了不一样的发展趋势与格局。
清道光《宝庆府志》“卷百二十四·任侠”就记载了这样一位在明代时就定居瑶地,并教化瑶民的奇人:“萧元辉,武冈人,豪迈有干略。……先是,小坪多瑶僮种类,鸟言卉服,斑斓侏离,自汉唐以来,更居化外,或劝元辉当择地而蹈。元辉曰:是亦人类也,乃不可共处耶?日率其弟元隆元喜,劝谕瑶人开垦种植树艺,兼为讲说礼义仁让,使知父子之亲,夫妇之别,睦姻任恤之谊。又使其子弟教瑶民子弟读书识字。瑶民乐之,渐知向化。”这是一篇很显然站在汉族人的立场所撰写的人物传记,将汉与瑶二者进行了明确的对立,一方面,从心态上强调汉地优于瑶地,故而当汉族人迁徙时,要“择地而蹈”,远离瑶地;另一方面,从种族上强调汉族人优于瑶族人,故而会有“是亦人类也,乃不可共处耶”的自我辩护,换言之,在当时很多汉族人的心里,瑶民与汉民并不是一类人;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强调汉文化优于瑶文化,故而当以汉文化教化瑶民时,“瑶民乐之,渐知向化”,这样一种强调从文化上教化并改造瑶族人的思路,事实上也是居于强势地位的汉族人一直期望做到的事情。在明代这位奇人或是与他类似的人这里,只是开了一个头而已。
除了萧元辉这样的奇人之外,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为了有效控制并同化瑶族人,同样采取了多种方式,也付出了诸多努力。其中,通过有效分化瑶民,在瑶民中培植更为亲近中央政府与汉族人的所谓“熟瑶”,以此来钳制甚至控制其他瑶民,从而形成新的被中央政府所掌控的瑶汉间关系的方式,无疑是所有策略的重中之重。明代中央政府的相关做法,在清道光《重辑新宁县志》“卷十五·苗瑶”中就有如下描述:“(明)景泰辛未,知县唐荣奏徙县治招抚城步瑶人,给田世住,分为八峒,把守各隘瑶路,号为熟瑶。择峒丁有能干者,县给帖,命为峒长,俾自约束。沿至皇清,相安无事,每年纳本色粮无差。”这样一种通过在瑶民中寻找并培养更为亲近汉文化与中央政权,并以此钳制甚至管辖其他瑶民的做法与努力,并不是明代君臣所创,而是从南宋时就已经开始实施了。从清同治《武冈州志》“卷五十三·峒蛮志”中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早在南宋嘉泰三年,前知潭州湖南安抚使赵彦励就在上书中提出了“以蛮民治蛮民,策之上也”的说法,其建议也获得了当时皇帝与朝廷的采纳。此后,这样一种通过给予更为现实的政治特权与经济好处等方式以培养更为亲近中央政权与汉族文化的“熟瑶”,实现钳制、管辖不服教化、远离汉族中心的“生瑶”的政治性努力,成为历代中央政府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策略之一。
除了上述“分而治之”的策略之外,到清代中期,中央政府还做出了更为务实与可行的制度性努力,通过鼓励少数民族学习儒家文化,参与科举考试,实现了将瑶族精英们吸纳到政府体制之中的目标,这样的做法无疑在更大的程度上增强了对中央政权的政治认同感。
清道光《重辑新宁县志》“卷十五·苗瑶”中称:“(清)瑶编能读书通文理者,应试岁科,取进二名,名瑶生。雍正十年更名新生。设义学两所,……声教日开,学额递增三名,应试者几百人。”此外,清同治《武冈州志》“卷五十三·峒蛮志”中也对这一状况进行了描述:“我朝声教四讫,瑶童得与考试,给衣衿,其岁考所取瑶生,仍与生监,一例乡试。”而关于瑶族学生的称谓问题,清同治《溆浦县志》中也进行了辨析,在清乾隆二十一年之前,有所谓“瑶生”、“瑶童”、“瑶学”等称谓,此后,依照黔(贵州)省的规矩分别改为“新生”、“新童”、“新学”。清初以来所进行的这样一种加强对瑶族地区的文化、教育的普及力度,鼓励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且单独为瑶族人留下功名名额的做法与努力,无疑为他们改变自身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机会与可能,也从更为长远的角度上重塑了瑶汉之间关系的整体格局。花瑶人逐渐进入到汉族人的政治体制、日常生活、思维方式之中,开始像汉族人一样处理日常事务,如乾隆五十年《续增城步县志》“卷一·民俗”中称:“苗瑶与里民易俗。今被王化渐靡,已染华风。……曩者跳月以婚配者,今则媒约相通矣。曩者抄戈以报复者,今则控诉待质矣。士彬雅,农克勤,讳蛮之名而处汉之实。其风俗不大径庭也。”
通过历代政府的不懈努力,到清中晚期,中央政府与汉族人对于瑶民的教化与同化努力,获得了全新的进展与成就,而此时的瑶汉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格局之中。清道光《重辑新宁县志》“卷十五·苗瑶”中,对这一新的瑶汉之间状况进行了如下描述:“新宁峒瑶属宁者为熟瑶,属他邑者为生瑶。……(至清中期)向之目为瑶者,群耻其号,人情风俗,悉与县同,所谓民瑶是也。”根据瑶民与汉民之间差异程度的递减,关于“瑶”的称谓,也被进一步区分成为了“生瑶”、“熟瑶”、“民瑶”,越往后,瑶汉之间的差异越少,汉族人对于瑶族人的教化与同化策略就越成功。类似的情况也见于武冈等地,清同治《武冈州志》“卷五十三·峒蛮志”中也对“瑶”进行了如下区分:“有山瑶、民瑶之分,民瑶与夏人杂居,服食居处冠婚丧祭,具与民同。……其山瑶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与巴渝同俗。”此处所谓“民瑶”与“山瑶”的区分,同样是建立在瑶民与汉民之间相似程度的基础之上的。
可见,到清代中晚期,“民瑶”已经不仅从语言、文字、习俗、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与汉民相差无几,此即《武冈州志》所谓“具于民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对待自我族群特征的心态上,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更是出现了《重辑新宁县志》所谓“向之目为瑶者,群耻其号”的奇特现象。换言之,此时的“民瑶”对于自己所属的“瑶”的族性,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厌恶与自我反感的心态。这也充分反映出清代通过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儒家教育、鼓励科举考试,在实现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效果。
二、科举与瑶官:花瑶地区治理模式的新变迁
自明初迁入雪峰山脉后,花瑶与外部政权之间,矛盾常发,争斗不断,在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天启元年(1621)、清顺治十五年(1658)、康熙五年(1666),都曾发生大规模战争,这些战争一方面导致花瑶人在历史上不断迁徙,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以“瑶界”为边界的独立存在。从清嘉庆年间所编撰的《嘉庆重修一统志》中的“湖南统部图”可以看到,直到清嘉庆年间,花瑶居住的位于雪峰山脉之中的地域,仍然以清晰的“瑶界”为界限,被划定在了一片具备独立地位与自治状态的地理范围之内,很有点“国中之国”的味道。不过,在清初康熙五年所发生的一场最终以和平的方式收场的战争,使得花瑶地区的政治与文化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关于这场战争,历代史志以及清末花瑶人根据本民族口述史编撰而成的《雪峰瑶族昭文》中都有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官修史志资料与花瑶《昭文》对于事件时间、地点等基本问题的记述上,有诸多不同,官修史志资料无疑更具备说服力与权威性。{6}
根据《昭文》记载,雍正元年(1723),花瑶举行大规模起义,通过艰苦卓绝的抵抗,最终迫使清政府以招安的方式对花瑶人予以安抚,而不是强硬地实施武力镇压,“恩蒙圣上急传收兵令,差委上山和好,到宝庆邵阳县之小沙江收兵。又转溆浦县之五里江,收兵处汉安瑶,其有溆邵古立瑶山十六峒,地业判为瑶民永远耕作、管理,不准汉民侵占。”对于同一历史事件,清代史志资料的记载略有差别,如清光绪《邵阳县志》“杂志”条目下有如下记载:“清康熙五年(1666),邵阳瑶作乱,黔阳知县张扶翼谕降之。”而清光绪《邵阳乡土志》“卷一·兵事”中,有更为详细地记述,“(康熙五年)三月,麻塘山瑶与武冈城步各瑶,相互煽惑,聚众数万,据险称兵。沅州总兵李逢茂,会营弁领兵往讨,驻营安江。黔阳知县张扶翼遣人入山招降,否则进兵。瑶闻,愿赴大陇投诚。扶翼单骑驰至,各瑶俱来见,禀受约束。(见道光府志)”可以看到,虽然花瑶《昭文》与清代史志所记述的内容、时间、地点等都有较大出入,但是,有一点是没有异议的,那就是:此次战役是以和平的方式结束的。此后,花瑶总体上归顺了朝廷,而中央政府也使用了新的行政区划与管理方式来加强对瑶族事务的管理与控制,以确保当地的政治安定与经济发展。其结果之一,就是让花瑶人“长期以来插标为记、耕山为业的游农经济生活更趋于稳定。”{7}花瑶人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和平安定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其文明程度也不断提升,“道光末年,风气渐开,中人产,始衣裘帛,宴客稍丰。”{8}
通过与汉族人的长时间的和平共处,他们之间的感情与友谊也在日益增加,文化之间的距离与排斥感在此程中渐渐消失,这极大地促进了花瑶人对儒家文化的吸收状况,进一步实现了社会稳定与区域治理。此外,清代中央政府从康熙时代开始,采取了极为务实的体制性努力,在花瑶地区设立学校,普及儒家教育,准许花瑶学生参与科举考试,赋予其参与到现有政权之中的全新机会,从而将花瑶人从文化与体制两个层面上纳入到中央王朝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文化体系之中。以此历史大背景为契机,花瑶民族也进入了自古未有的读书、写字、参加科举考试的新的生存状态之中。在清康熙年间,今邵阳市辖区范围内的瑶族人开始接受正规的儒家教育,全市当时共有6所学校,其中现隆回县花瑶聚居区的小沙江2所。{9}可以想象,花瑶人中间真正通过接受儒家教育、参与科举考试的方式获取功名的人并不多,也没有花瑶人获得过高于“秀才”这一层级之上的功名。不过,随着政府力量的不断推进,似乎清代中晚期花瑶地区的治理权力,逐渐转入到了那些具备功名的花瑶人的手中。
在我们实地调研所收集到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关于这类获取了功名并进一步掌握治理地方事务权力的花瑶人,主要有如下三个比较正式的称呼:秀才、邑庠生、瑶官。前者是民间所习惯的更为普遍的称谓,后两种均见于《奉氏族谱》,是更为书面的称谓。
关于清代花瑶“秀才”的情况,我们最初是于2004年8月在虎形山乡崇木凼村与沈诗永老人的访谈中获得的。他给我们讲述了清末所出现的一个很有权势的秀才的故事。据传祖籍隆回县金谭乡的清末重臣、两江总督、湘军将领魏光涛(系晚清思想家魏源的族人,被当地人称为魏午庄)为了给其小妾在今虎形山乡的虎口之地谋取一块墓地,魏光涛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直接任命当时拥有这片地的花瑶人奉学傲为“秀才”。在当时,所谓的秀才拥有很大的权力,既可以有效处理本族事务,而且一旦政府有事,也会首先找秀才,从而也具备了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常常被后人看作是当时的“瑶王”。此外,秀才的头衔还具备代代相传的世袭功效,在奉学傲死后,秀才一职由其子奉成安继承,奉成安之后,又由其侄子、民国年间在当地非常有名的保长奉才禄继承。
无论这个涉及魏光涛以“秀才”的头衔换取墓地的故事是否真实,不过,从我们所收集到的其他资料以及花瑶人的普遍记忆来看,沈诗永老人关于奉学傲获取“秀才”头衔的描述,以及关于当时的秀才与花瑶地区政治权力的构成与转移方式的如上记忆与讲述,大致是可信的。{10}
与奉学傲是通过一种交易而被封为“秀才”的情况不同,花瑶人中还有其他读书人,是真正通过自己的学习、考试,获得“秀才”功名,而且有一个相当正式的名字——邑庠生。如《奉氏族谱》的编撰者奉成美就是通过学习获得功名的花瑶人之一,在奉成美自己编修、其长子奉德芳手书的《奉氏族谱》中,对奉成美有如下记述:“成美,邑庠生,排难解纷,乡里倚其直谅,嘉庆八年闰二月初十寅时生,同治十年正月初日申时没,葬水洞坪老山水口。……子三:长德芳、次德藻、三德芹。”从这段极为简单的生平描述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奉成美无疑是一位通过学习儒家文化获取“邑庠生”(秀才)功名的人,他所编撰的《奉氏族谱》是我们在花瑶地区所收集到的唯一的一份族谱,可知他对儒家文化的掌握,及其在当时花瑶人中间所具备的地位;另一方面,奉成美既然能够做到“排难解纷,乡里倚其直谅”,无疑说明他同时还是一个具备管理地方事务、维持地方秩序能力的人物。奉成美的后代是否继承了他的秀才头衔,我们并不知晓,虽然他的长子奉德芳曾手书《奉氏族谱》,可见应当文化水平不错,不过,在当地花瑶人的讲述中,其后代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有影响力的人。
《奉氏族谱》中除了记载了作为“邑庠生”的奉成美的基本情况之外,还极为简略地记述了明代晚期徙居今小沙江镇江边村麻坑组的某一个支派的子嗣中,有人同样获得了“邑庠生”的功名,甚至被冠以“瑶官”的称号:“内有一房系麻坑峒瑶官正望子,邑庠生,开科之派,俱未详。”可知,在麻坑的奉姓家族中,曾经出过这样一位资料不详的秀才(邑庠生),而且还被直接称为“瑶官”,这也是我们首次看到的极为正式的、带有官府色彩的称谓。很可惜,我们关于这位瑶官的认知,止于《奉氏族谱》的如上记述,对他获取功名的年代,瑶官称谓的来源,是否有现实的作为都不清楚。
不过,同样在麻坑,光绪年间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与《奉氏族谱》的编撰者同名的“秀才”:奉成美。我们并不知道麻坑奉成美的秀才头衔是否与那位瑶官祖先有关系,但是,关于麻坑的奉成美,同样可以肯定如下两点,一是他的文化水平也很不错,我们曾在他的后代、现居麻坑的奉泽都家,看到过一本世代家传的、由奉成美编写于光绪年间的、关于花瑶法术的书籍——《教法案例》,内容很是艰涩难懂。{11}可知他应当也是通过接受儒家教育获取的功名;二是奉成美同样拥有治理地方的能力与声望,是当时麻坑政治权力的拥有者与捍卫者。更为重要的是,在奉成美去世后,其秀才名分获得了进一步的传承,他的大儿子奉德金后来是民国政府的保长,而三儿子奉德堂则是甲长。
可以看到,清中期以降,中央政府通过推过儒家文化、鼓励参与科举考试,并通过将“秀才”(邑庠生)的功名与地方治理的权力相结合,有效地促使了花瑶地区逐步融入帝国体制的进程。这一努力从花瑶民族与中央政府两个层面上,都获得了极大的历史成效。
对于花瑶民族而言,新的政策与民族关系所带来的,一方面是掌握了儒家文化的秀才的出现,从而彻底改变了《雪峰瑶族诏文》之中所说的如下状况:“原我瑶民历未开化,没有一个书生;你看百万军中没有一个当兵作官的瑶民。岂不是真情?”更为重要的,通过参加科举获取功名,无疑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正式得到了中央政权的认可与尊重,并拥有了进入外部政治—文化体制的新的身份。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是极为关键与重大的变迁,这或许也是同治《武冈州志》所谓“文明之盛,盖自开辟以来所未有也”这一论断的一个佐证。事实上,到奉成美于咸丰年间所编撰而成的《奉氏族谱》序言中,甚至提出了如下论述:“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应于木本水源,勿忘其所自耳。凡圣朝以孝治天下,所属满汉,原皆各有族谱,以序昭穆,使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独我瑶于此典而阙如,诚憾事也。因不揣谫陋,勤求遍访四阅,岁而谱成。”从中也可以看出,花瑶读书人已经开始真正掌握儒家文化,并从思维与意识上,都已经使用儒家文化的立场,重新定位花瑶的历史与文化,以及自身族群在整个国家体系之中所处的地位。
对于中央政权而言,随着花瑶人对于儒家文化的接受程度的日渐加深,二者之间在文化与心理上的隔阂自然有所减少,此外,一旦设立瑶学,就意味着瑶汉之间可以通过一起读书,一起参加科举考试等方式,加强双方之间较为正式的交往与互动,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两族之间由于相互隔阂、相互误会从而导致激烈的对立与冲突的几率自然会减少。这一状况无疑有利于中央政权实现维持社会秩序,促进地方发展,并最终获取花瑶人的归顺与臣服等政治目标。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中央政府逐步从整体上实现了教化、同化瑶族人的目标。因而,清光绪《邵阳县志》在“建置”条目的最后,在简要介绍了花瑶十六峒之后,进行了如下评价:“瑶地险而民悍愚,善抚之亦易用也。”而到民国年间所编修的《溆浦县志》“瑶俗”条目中,甚至出现了如下带有结论性意味的描述:“瑶民今已式微,……向之履起叛乱者,今皆变为纯良矣”。
三、儒家文化与花瑶民族的政治认同:关于几个实证资料的考察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与花瑶地区所经历的上述历史变迁,不仅仅从宏大的权力体系、区域治理、文化融合等层面,深远地影响到了花瑶民族与花瑶地区,而且在微观的层面上深远地影响到了花瑶人的自我认知、生活方式与意义世界。关于花瑶民族自身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我们可以从实地调研所收集到的辈份诗、奉氏族谱、石牌律等材料中,获得极为直接的观感。
1. 辈份诗
在以正式的文字方式确定自身家族系统中的辈份排名之前,花瑶先民都以“丫”(有时也写成“亚”字,花瑶语念作“阿”)为代称,如花瑶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沈丫乖、丁丫未{12},以及明嘉靖年间鼎鼎有名的起义者“沈亚当”(又名“沈丫当”){13}的名字,都是如此。此后,花瑶民族曾有一段时间实行“父子连名制”,即男子名字的第一个字来自父亲,后一个字则为自己儿子的名字所延续,如在我们所收集到的《奉氏族谱》中,就记载了这样三位父子的名字:也保、葵也、同葵。这是典型的父子联名制传统的体现。再后来,随着儒家教育在花瑶地区的逐步普及,父子连名制传统也最终被以诗歌形式所确定下来的辈份系统所取代。
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开始,花瑶之中学习儒家文化的人按照与汉族人相似的方式(即编写易于记诵的诗文)编出了辈份。以下是在实地考察期间我们所得到的几个花瑶大姓的辈份诗文:
奉姓:“五派”:光世成德泽,锡祚兆祯祥,忠厚传家久,文章华国长。
“三派”:兴学成才道,修文启进英,源江发光明,桂林有先锋。
沈姓:开明成道德,诗书玉后祥,洪鸡会说白,曰曙希世泽(雄鸡会叫白,日旭棉世泽)。
刘姓:佑开绍助长,笃庆永乐昌。
杨姓:岩儿塘:文开正元才,朝廷方显达,法宝尚金召,登堂喜佑悲。
白水洞:文开正元才,朝廷方显达,登台赐玉杯,发榜上金鑫。
辈份的出现无疑体现了儒家文化对花瑶人的深刻影响,因为排辈份、修族谱都需要读书人出面组织、设计和撰写。就目前的资料来看,这些辈份诗的出现大多在儒家教育充分推行之后的清嘉庆、道光年间。如我们从实地调研所抄录的沈、杨两姓先祖的墓碑中,可以对花瑶辈份诗的出现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沈姓先祖沈贵种(1793~1864)的墓碑表明,自他开始有了班辈;此外,从杨姓先祖杨正贤(1687~1739)的墓碑来看,杨姓从其曾孙辈始以班辈取名,如杨正海(1809~1868)、杨正河等。
此外,花瑶人在为自己的族姓确定辈份排名时所使用的文字以及这些文字所表现出来的意境,已经完全儒家化、政治化了。一方面,这些文字显示出极为明确的政治认同感以及对中央权力的向往与追求,如杨姓辈份诗中所出现的“朝廷方显达”一语所释放出来的极为明确的政治信号;另一方面,在辈份诗出现的时代里,儒家文化已经逐渐成为花瑶民族的表层意识形态的象征,各姓辈份诗的文字中,不断出现“道”、“德”、“忠”、“厚”、“文”等儒家道统意识极为强烈的文字,无疑体现出儒家文化在花瑶社会中所形成的教化效果与示范作用!换言之,到了辈份成型的清代中晚期,儒家文化与朝廷权威,已经逐步融入了花瑶人的思维与意识之中。
2. 奉氏族谱
除了上述简单的辈份诗之外,我们在实地调研中所收集到的更为成熟也更具备典型性的文本——《奉氏族谱》,成为我们研究花瑶人的历史、政治、宗族谱系、文化传统等问题的关键性文稿。关于这部《族谱》以及族谱编撰者奉成美的基本情况,上文中已经有了详细的介绍,在这里,我们将主要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入手,探讨《族谱》的“序”所表达的文化意蕴与政治态度。
《奉氏族谱》的“序”,出现在原谱的第二、三页,这篇序文极为明确地表达了作者对待儒家文化与外部政权的积极态度。全文如下:
“序。《文心雕龙》云:谱者普也。盖家之有谱,所以普叙世系。俾继起者,远追宗近述祖,历亿万年如一也。我始祖奉明公原籍江西吉安府,田庐坟墓均在鹅颈坪,子三。长,奉亨公迁广西;次,奉贯公迁云南;三,奉寅公迁贵州。洎明洪武元年始,徙湖南洪江,嗣是又家龙潭。前兹无谱记。间有前辈笔载可稽,亦属断简残篇,安能于世远年湮之下而叙次世,远年湮以上之履历。故尔数典难免忘祖,贻诮窃念。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应于木本水源,勿忘其所自耳。凡圣朝以孝治天下,所属满汉,原皆各有族谱,以序昭穆,使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独我瑶于此典而阙如,诚憾事也。因不揣谫陋,勤求遍访四阅,岁而谱成。肇自马世公,其间高曾矩矱,子孙箕裘,足以信今而传后第。前此,风微人往,见之固无闻知亦罕,奚能以未及填讳者告无辜于奕叶在天之灵。至若昭兹来许,绳其祖武,自分可诵下武之五章。谨序。
主修马世公十五代孙成美
大清咸丰元年春月榖旦马世公十六代孙徳芳顿首书”
就儒家文化而言,从作者起笔处征引《文心雕龙》开始,就体现出极其明确的儒家文化的气息。所谓“谱者普也。盖家之有谱,所以普叙世系。俾继起者,远追宗近述祖,历亿万年如一也。”这样一种关于自身血缘关系的寻根溯源,是自古以来讲求“天人合一”、“人鬼相通”、“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等观念的儒家文化所坚持、维系的,《奉氏族谱》的编撰,无疑有效地回应了儒家文化所提出的问题与要求。因此,如何按照儒家的观念与要求,实现本宗族“远追宗近述祖”目标,也就成为这部《族谱》的编撰者们最初的动力与追求所在,此即所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应于木本水源,勿忘其所自耳。”可见,一部族谱的编撰,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宗族谱系的记录、承接问题,更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读书人追求自身价值与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与途径。
就外部政权而言,从序文所谓“凡圣朝以孝治天下,所属满汉,原皆各有族谱,以序昭穆,使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清代中央政权通过推广儒家教育,大大地加强了自身政权在花瑶地区的影响力与感召力,这样一种强调清朝是“以孝治天下”的观点,不仅仅体现出作者对中央政权的认同感,更体现出对中央政权所展示出来的示范性的仿效与响应。这样一种政治上的情绪,也成为《族谱》编撰者的另外一种使命感所在,此即序文中所谓“独我瑶于此典而阙如,诚憾事也。因不揣谫陋,勤求遍访四阅,岁而谱成!”
3. 石牌律
石牌律是瑶族特有的确定乡规民约的形式,在实地调研中,我们主要收集到了三块石碑,其中位于隆回县小沙江镇江边村奉家院子的于光绪四年所立的“万古不朽”碑,已经无法辨认了。能够完整认出碑文的内容的只有两块。
一块是位于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崇木凼村“永远蓄禁碑”,立于光绪九年(1883)。有关这块石碑的来源,一直在沈姓花瑶人中广为流传。崇木凼的沈姓自古以来就有明确的族规规定,祖坟重地里的树木属于全族人共有,除了清明节集体祭祀完毕后可以捡些树枝用于为参加祭祀的人烧火做饭之外,不得捡拾祖坟重地里的树枝,更不得砍伐树木。光绪八年(1882)冬,大雪压断了祖坟重地的一些树枝,沈姓族内有人擅违此规定,在祖茔重地捡拾柴火,被人抓住。在第二年清明节的家族大会上,二人被处以重罚,大会还决定,在祖茔重地立石牌一块,以儆后世。同年腊月二十八,石牌立起,碑文如下:“祖茔重地,禁止开砍捡柴烧灰,此系大典,亦系仁人孝子之所亟严者也。倘有不遵者,一经拿获,送上究治,决不容情。”
作为花瑶习惯法中的“大典”,碑文中所强调的严禁在祖坟之地砍伐的规定,具有非常强大的制约力,而且一直到现在还被花瑶人所遵守。在“大炼钢铁”时期,甚至与前来砍树烧炭的政府人员之间激烈对抗,发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保树运动”,其影响波及整个花瑶地区。{14}
另一块是位于隆回县小沙江镇江边村麻坑组的“永远禁碑”,立于宣统元年(1909)。根据当地奉姓瑶族与黄姓汉族老人们的记忆,晚清时期,瑶汉开始杂居于此地,矛盾不断,再加上当时正逢社会动荡,匪盗四起,当地敢犯禁作乱的人也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麻坑地区的安宁。因此,两族长老都认为需要立此石碑,从而对瑶汉二族的人进行劝诫与警示。碑文如下:“盖闻朝廷有律例,乡党有禁条,不加团规,人心不一。且地界邵溆,徭汉同居,耕田种土,勤劳度日。迩来习俗伦薄,往来人等同顾地方,无端骚扰,侵削元气,良懦难安,是以阁团集议,互相劝戒,奉宁示谕,刊碑约禁于后小,公同重罚,大则鸣送上究治。” 在论述完立此石碑的过程以及处罚的标准后,石碑上还附有具体禁止的条文十款:“一禁打牌押宝,一禁行强等项,一禁窝贼窝赃,一禁纵放滋牲,一禁面生歹人,一禁勾役索诈,一禁逰食强丐,一禁田禾山播,一禁否匪游棍,一禁斗秤公平。”
可以看到,到清末时,花瑶人已经开始用石牌律的方式,以汉族文字将自己此前并不成文的宗族习惯法进行了成文化的处理。具体而言,花瑶的石牌律作为宗族法,主要体现出对于日常伦理与宗族制度的维护,如“禁砍拾祖茔重地林木碑”主要反映出对“孝道”的重视,正如碑文所言:“祖茔重地,禁止不许开砍捡柴烧灰,此系大典,亦系仁人孝子之所亟严者也。”而在“禁偷赌匪盗碑”里,可以发现诸如禁面生歹人、禁游食强丐、禁斗秤不公一类的规定,实际体现了对日常伦理与宗族制度的维护。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两块碑文中,都曾提到“送上究治”的纠纷解决方案,这也表明外部政治权力已经深度介入花瑶地区,如果说“永远禁碑”的内容主要用于社会规范,需要遵守政府法令的话,那么,第一块“永远蓄禁碑”所作出的关于严禁在祖坟之地砍伐的规定,更像是花瑶的内部宗族事务,与外人关系并不大,而其碑文中仍然强调要“送上究治”,无疑意味着当时的国家权力与国家法律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花瑶自己的习惯法与宗族法。换言之,此时的花瑶地区,已经被国家权力有效渗透,并最终形成了瑶汉杂处的大环境。
四、结 论
综上所述,明清两代中央政权在花瑶地区的治理上,通过不断强化儒家文化的渗透作用与示范作用,使得瑶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由此不断获得深入。清中期以后,通过推广儒家教育、开放科举制度,儒家文化更为深远地影响到了花瑶的政治认同、族群意识与文化观念。在这一过程中,花瑶人逐步完成了从整体上抵制外来政治权威向不断认同外来政治权威的自我转变,而作为中央政府意识形态与文化载体的儒家传统,无疑起到了缓冲矛盾与嫁接文化的双重作用。
注 释:
{1}本文作者曾于2003、2004、2005、2008、2011、2012年,分别带领由中国政法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与研究生组成的考察团,多次进入湖南省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对花瑶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实地调研。
②米莉、黄勇军等:《花瑶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1-42页、第554页、第556页。
{3}{7}{9}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邵阳市志》,长沙:湖南出版社,1997年,第552页。
{4}(日)竹村卓二:《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页。
{5}{11}黄勇军:《瑶山上的中国:花瑶民族的生存意境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62-191页,第116-182页。
{6}由于《雪峰瑶族昭文》是晚清瑶族秀才记述本民族口述史的文本,所以出现时间、地点等的误差,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此事件当以官修史志资料为准。
{8}(清)齐德五主修:《溆浦县志》(清同治十二年刻本),溆浦县档案馆2003年10月重印。
{10}{14}米莉:《国家、传统与性别——现代化进程中花瑶民族的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2-47页,第66-77页。
{12}根据花瑶人的传说,沈丫乖、丁丫未是花瑶远古文明的开创者。
{13}花瑶人沈亚当曾于明嘉靖三十八年叛乱,后被总兵石邦宪平息。相关事件在《明史》中有简单的记述:“湖广溆浦瑶沈亚当等为乱,总督石勇檄邦宪讨之,生擒亚当,斩获二百有奇。”(《明史·石邦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