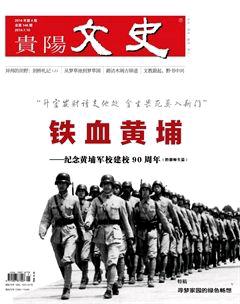汉语诗歌韵典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黄立元
编者按 在当代汉语中,由于没有在《汉语拼音方案》之后再出现如周有光先生所说的《文言拼音方案》,所以,当代人在阅读和欣赏中国古典诗歌时,常常会感到古人的作品似乎不那么合韵,却鲜有人对其中缘由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再者,当代人创作诗词,用普通话吟诵,却按《佩文韵府》取韵,也是一件十分别扭的事情。而当代的诗歌韵典又五花八门,莫衷一是,让人备感迷茫。本文作者有鉴于此,追本溯源,力求厘清古今诗韵变化。
2014年1月20日,笔者去到了位于北京北马寺附近的“中华诗词学会”。学会副会长赵京战(即《中华新韵》十四韵的编著者)和学会秘书长王德虎将我带进会议室。赵京战介绍说:“在推出《中华新韵》(十四韵)之前,学会曾經请来了许多专家,就在这间会议室里,多次讨论新韵的韵部划分问题,争论得很激烈……”
笔者能够想象得到那种激烈争论的程度。因为,翻开《中华新韵》(十四韵),笔者仿佛看到,争论的各方都自认为自己站在正确的台阶上,手中握着开启韵部大门的钥匙;仿佛看到汉语语音学的音位理论与汉语音韵学的韵部理论相互角力的情景,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新韵》主要是这两种理论不同观点相互妥协的结果。
为了不把艰深、枯燥的音位理论写进本文而又让读者明白这两种理论的不同,笔者简单介绍如下:汉语语音学把语音当做一种生理现象和物理现象来研究,汉语音韵学则把语音作为一种交际工具来研究。例如“根”和“观”两个字,语音学从实际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来研究,认为前者的发音部位在舌位的前部且不带圆唇;后者的发音部位在舌位的后部且帶圆唇。语音学家按韵尾对韵母进行分类,并且把鼻韵母en、in 、uen、 ün ,鼻韵母eng、ing、ueng 的韵腹都看作中元音/e/,因此,也就把带有这一特征的汉字划归在同一个韵部。
汉语音韵学则不是这样来确定韵部的。耿振生认为:“韵部的定义,来自于诗歌押韵的普遍规则——同韵基(即韵腹和韵尾相同)、同声调的字在一起押韵”(耿振生《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刘晓楠认为:“‘韵指字与字之间具有韵基(或加声调)相同的关系,而‘韵部则是指一组具有这种关系的可以押韵的字”(刘晓楠《汉语音韵研究教程》)。换句话说,在现当代,汉字是由汉语拼音来注音且每一个汉字的注音都是由声母、韵母和声调组成的。对于一个汉字与另一个汉字,我们只需要从该字的汉语拼音中(而不是从音位分析中)找出它们的韵基(不需要区分四声时)或者韵基和声调(需要区分四声时)是否相同,就能判定出他们属不属于同一个韵部。
客观地说,语音学和音韵学在它们各自的领域内,其方法和观点都是正确的。而且,这两种观点其实也不是对立的。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起草人之一,他在《汉语拼音方案基础知识》一书中就曾这样写道:“汉语拼音方案有三条基本原则:口语化、音素化和拉丁化,合称拼音三化。……音素化:按照音素(音位)拼写音节。”这就是说,汉语拼音并不是凭空而出,而是以音位为根据编写出来的。可为什么,一些新韵韵书的编著者却要硬生生地把音位等同于韵位?在他们看来,音位似乎比韵母更能反映汉字的韵部归属。汉语拼音可以对每一个汉字进行注音,却没有资格依据其韵母来确定韵部。这就好像有人去到蛋禽市场上买鸡,却非要让商家将鸡按鸡蛋的价格卖给他一样。因为鸡是由鸡蛋经过孵化后变成的。你说这理由够不够荒唐?
举一个例子来说:依照语音学的音位原理,认为更(geng)、英(ying)、雄(xiong)3个字韵母的韵腹实际上都是/e/,于是ing实际上等于ieng,iong实际上等于üeng。这样一来,ing就变为eng的齐齿呼,iong就变为eng的合口呼,把它们划归同一个韵部也就理所当然了。但是,从作诗押韵的角度看,却难以获得认同。因为同一个音位/e/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了变体,导致实际的语音发生了较大的变异,这种变异了的语音对于确认汉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已经在听觉上明显地感到它们并不相押。
因此,笔者以为,如果我们要进行语音本质的分析时,应该从音位的观点出发,认识它们的同一性,说们是一个音位。但是,当我们作诗押韵时,则大可不必对汉字语音作如此细微的辨析,因为这种“语音学的细微的辨析……对于音韵学来说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王力《汉语音韵》)。我们只需知道韵基相同必定押韵,韵基不同必不相押的道理就可以了。
此外,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还会看到,由于当今诗坛缺乏划分韵部的标准,在韵部的确定上,还存在着一些随意性和想当然。鉴于此,笔者对于新韵书中分韵已有共识的部分不再赘言,仅仅对有分歧的韵部逐一剖析之,期望能澄清诗坛新韵分韵的乱象,重建一个符合现实的、科学的分韵系统。
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参看在上一期的文章(《贵阳文史》2014年第2期,佩文韵府:中国古典诗韵的终结者——四谈平水韵兼论诗坛乱象)中已揭示出的从十三辙到二十韵的韵部划分的分歧,就容易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了。
关于十三辙“二波歌”韵部的分合。该韵部包含三个韵母“e、o、uo”。对应于前文(四谈)中 表1第三、第四两个横行;表2第二、第三两个横行。《汉语拼音方案》将“e、o、uo”3个韵母分列两行。这至少说明:这3个韵母不能划归在同一个韵部。
然而,《现代诗韵》(十三韵)的编著者秦似认为:“‘歌部分为‘歌‘波两韵。‘歌韵的韵母是e,‘波韵的韵母是o和uo,由于这两韵的常用字都较少,在现代语音中又比较接近,所以按宽韵的要求并在一部是可以的。但分用则和谐一些,如从严的话,也可以分用。”
笔者认为,根据韵部定义,一眼就可以看出“二波歌”韵所包含的三个韵母e、o、uo不相同,只有o、uo同韵。因为韵母uo去掉韵头之后,两个韵母的韵腹都是o,没有韵尾。所以应该将“二波歌”韵分为两个韵部。秦似也认识到“分用则和谐一些”,但因为“两韵的常用字都较少”,于是置韵部规定于不顾而将两韵归为一韵,这种做法无疑是当代新韵编撰者的通病。因为字少,把两个不同的韵强划在同一韵部,这样的理由带来的结果依旧是不押韵,不但如此,反而让使用者容易产生用韵的混淆和不便。
因此,“波歌(e、o、uo)”同韵,不符合汉语音韵学关于韵部规定的标准。强行把它们划为同韵,体现出了编撰者的想当然和随意而为。
平心而论,如果仅以“波(bo)、歌(ge)、多(duo)”3字而言,虽然主要元音两个是开口呼,一个是合口呼,发音不同,听起来却很相似。但相似只可以成为通押的理由,却不应该成为同韵的根据。而且,部分的相似不能推定为全部的相似。比如“波与得、歌与落、多与娥、特与摸”这些字,无论是读起来还是听起来,都没有押韵的和谐感。所以,除《现代诗韵》(十三韵)《中华新韵》(十四韵)外,其他的新诗韵典都是将“波歌”韵分为“波”“歌”两韵,这样做才与韵部的标准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