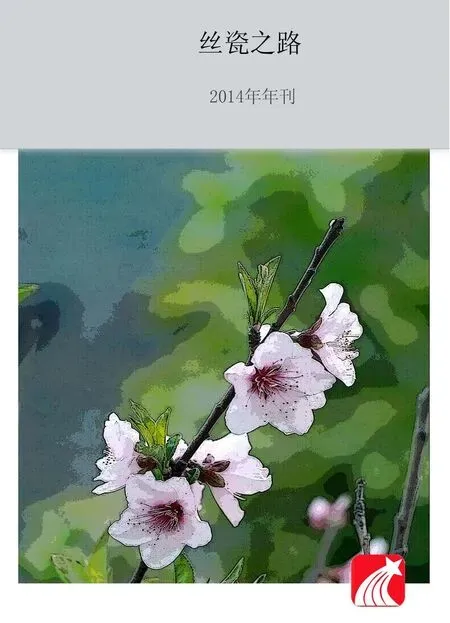古希臘羅馬文獻中的遠東
——賽里斯人(上)
萬翔
古希臘羅馬文獻中的遠東
——賽里斯人(上)
萬翔
一、文獻記載與研究回顧
(一)西方關於遠東的最早記錄
自巴比倫、亞述帝國時代之後,古希臘羅馬作家的作品成爲西方文化的淵源之一。在古希臘文明逐漸勃興的時代,遠東的商周文明也在黃河和長江流域發展起來。因此在西方作家的文獻中,留下了關於遠東的印記。
已知西方文獻中關於遠東的最早記錄出現在公元前7世紀古希臘作家阿里斯鐵(Aristeas of Proconnesus)的詩篇《獨目人》(Arimaspeia)[1]中。此書已佚失,保存在其他古典作家如品達(Pindar)[2]、希羅多德(Herodotus)[3]的著作中關於“北風以外的人”(Hyperboreans)的零星記載,無法讓人看到這一民族的全貌[4]。有學者指出,希羅多德記載的“北風以外的人”位於希臘世界已知地理的極限,客觀上可能指居住在遠東的古代中國人[5]。考慮到希羅多德常見的方向錯誤,“極北”可以不妨理解爲遠東[6],但對此目前尚沒有統一的結論[7]。
公元前5世紀末4世紀初希臘作家克泰夏斯(Ctesias of Cnidus)[8]的作品《波斯志》(Persika),是西方古典文獻中留存至今最早的關於遠東地區的記載。克泰夏斯記載了賽里斯人(Seres)身材高大和長壽的特徵。[9]
另一個關於遠東的早期記錄,是馬其頓征服者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36—323年在位)給其導師亞里士多德的通信。在公元前327—325年遠征印度期間,亞歷山大給亞里士多德寫了關於印度奇聞的通信(Epistola Alexandri ad Aristotelem de miraculis Indiae)。信中提到了賽里斯人。[10]信件裏對賽里斯和巴克特里亞的混淆表明,其成文的素材來自於希臘人征服巴克特里亞之前。其後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的記載則明顯區別了巴克特里亞和賽里斯人的土地。[11]
西方古典文獻對遠東的記錄,除了賽里斯這一名稱外,尚有“秦奈”(Thinae)的稱呼。秦奈一般認爲是通過印度洋海上貿易之路傳播的名稱。記載“秦奈”最早的現存文獻是《厄立特里亞海週航記》(Periplus maris erythraei)。[12]該作品的作者不詳,其成書時間約當公元1世紀下半葉。因此,與“賽里斯”相比,“秦奈”晚出且並不多見。除了《厄立特里亞海週航記》之外,衹有公元2世紀的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和公元5世紀的馬爾西安(Marcian of Heraclea)兩處文獻提到過“秦奈”。
“賽里斯”逐漸成爲了西方通過陸路交通所知的有人居住的地區東界的民族。相較於“北風以外的人”和“秦奈”的零星記載,“賽里斯”成爲西方古典文獻對遠東地區最重要的指稱,也因而是本文討論的主題所在。
(二)貫穿西方古典世界的賽里斯形象
現存文獻中的serica(其形式爲複數,單數爲sericum),即“賽里斯織物”這一名詞,首先出現在公元前1世紀抒情詩人普羅佩提烏斯(Propertius)的《哀歌》(Elegies)中。[13]自此以後,賽里斯這一名稱便與西方世界的絲綢供應者的身份聯繫起來。[14]古典世界以來,這種名貴織物的來歷成爲西方作家筆下的難解之謎。而賽里斯商人的形象,以及他們經商的誠實與奇特方式,也成爲希臘羅馬史家津津樂道的內容。
如果說絲綢是我們熟悉的內容,那麽關於賽里斯人的長壽、弓箭、戰車等等的記載,則爲賽里斯人確係中國人之說打下了問號。其中最大的疑問,還是來自希臘羅馬世界地理學家著作的記載。在古典地理學家中,斯特拉波首先提到了賽里斯。現存最早描述賽里斯地理位置的古典著作是梅拉(Pomponius Mela)的《世界志》(Chorography)和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又譯《自然志》),均成書於公元1世紀。兩者關於地理位置的描述同出一源[15],談到了沿里海和斯基泰洋航行的綫路,指出亞洲最東部居住著三個民族,並將賽里斯人正確地置於印度人和斯基泰人之間。
古典的地理學,到公元2世紀時集大成於羅馬埃及亞歷山大的托勒密。托勒密在《地理學》(Geography)中對世界每一個地區標定了經緯度。其中包括對賽里斯地區的詳細叙述。這一叙述引自推羅的地理學家馬里努斯轉述一位馬其頓商人梅斯的經歷。其不嚴密性在於,據馬里努斯所述,梅斯本人也沒有到過賽里斯,而是他的助手到達了賽里斯。[16]這一叙述的重要貢獻在於指出了“石塔”(lithinos pyrgos)[17]在通往賽里斯道路上的關鍵位置。
自古典時代以來,西方世界與中國的交往始終沒有中斷過。但從公元4世紀以後,西方文獻中關於賽里斯的形象基本上固定下來,後人的著作都可以在前人論著中找到根據。儘管6世紀以後拜占庭史家著作中出現了“秦尼扎(Tziniza)”與“桃花石(Taugast)”這兩個新的稱呼[18],由於文獻記載中沒有直接到達遠東的記錄,在西方作家的視野中,賽里斯這一形象的面紗一直沒有揭開。
13世紀蒙古帝國的建立打通了從中國到歐洲的交通綫,自古典時代以來,歐洲人第一次獲得了從西方直接到達中國的記錄。首先來到中國的歐洲使節之一魯布魯克(William of Rubruck)在其行紀中認爲,當時所稱的“大契丹國”,即中國北部,就是古典文獻中的賽里斯國。[19]
明清兩代鎖國之後,近代西方對賽里斯的討論始於在中亞和中國西部的探險活動。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中亞探險時就試圖考證古典文獻的記載。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從克什米爾初次踏上中國土地的第一站便是塔什庫爾干(Tashkurgan)。這個名字的意義“石頭城”恰如托勒密文字中的“石塔”的形象。[20]另一個重要的絲路城市塔什干(Tashkent)在探險者的筆下也成爲了“石塔”的候選者。[21]在第三次中亞探險之後,斯坦因最終將今天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達勞特—庫爾干(Daraut-Kurgan)比定爲“石塔”。儘管今天對於“石塔”的位置尚存巨大的爭議,塔什干、塔什庫爾干和達勞特—庫爾干都位於可以控制西域的中國所能達到的自然邊界上。這一點從托勒密、梅拉等人所在的東漢,到斯坦因的時代都沒有改變。
(三)近代學者研究下的賽里斯
相比於對遠東的實地探險考察,西方人在古典文獻中對遠東的研究很早就已經開始。這些研究的共同點是抓住古典文獻的叙述,一定程度上結合西方對中國的實地考察和地理文獻。《馬可波羅行記》本身及對它的研究就是這一方法的實例之一。最早涉及“賽里斯”問題的學者是法國的德經(Joseph de Guignes)和德國的克拉普洛特(Julius von Klaproth)。他們討論了“賽里斯”的語源,指出“絲”字與賽里斯的聯繫。[22]此後,關於賽里斯的論述屢屢出現在西方文獻學者和漢學家的著作中。[23]
衛維恩·德·聖馬丁(Vivien de Saint-Martin)較早運用東方文獻對希臘拉丁文獻中的遠東地理進行了考證。在1858—1860年間出版的作品《對希臘拉丁地理學文獻中關於印度記載的研究》中,聖馬丁對托勒密等西方主要地理學者記載的地名,使用梵語文獻進行全面的考證。由於其文獻來源單一,聖馬丁把很多爲後來學者認爲在中國境內的地名考證在印度次大陸。
洪堡之後最傑出的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其1877—1878年出版的巨著《中國》(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第一卷中對古代中國和印度、西方的交往路綫進行了考證。李希霍芬是第一個將對中亞的親身考察與中國、西方文獻進行綜合分析的學者。他的研究在很長時期內是西方對中國歷史地理學最詳盡的專著。李希霍芬還是最早提出“絲綢之路”這一概念的學者。[24]
英國學者裕爾(Henry Yule)所著的《東域紀程錄叢》(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從中國-歐洲交流史的角度對賽里斯問題進行了詳細的闡述。該作品原著出版於1866年,1915-1916年經法國學者考迪埃(Henri Cordier)修訂再版。與此前德經、克拉普洛特等人的論述偏重具體史料的考訂相比,《東域紀程錄叢》爲漢學學者提供了關於中國對外交流歷史的全景式介紹,並在附錄中翻譯和輯錄了重要的相關史料。經考迪埃修訂後的版本,成爲20世紀初研究中國對外關係史的集大成著作。
1910年法國學者戈岱司(Georges Cœdès)編輯出版了《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à l'Extrême-Orient)。戈岱司試圖窮盡西方古典文獻中關於古代遠東的記載,收集近九十位作家涉及古代遠東的著作片斷並譯爲法文,上起公元前5世紀末的克泰夏斯,下至公元14世紀拜占庭作家的作品,基本涵蓋了古典和中世紀西方作家的著述。戈岱司的輯錄長期以來一直是賽里斯問題研究最全面的史料集。同時戈岱司也在其導論中概括性地指出:“作爲一種妥善的辦法,人們不能夠僅僅根據這些資料就肯定,在公元前1世紀以前,地中海沿岸諸民族就開始瞭解和猜測遠東地區了。”[25]這一結論成爲後來著作反復爭辯的主題。有代表性的爭議是1931年赫德遜的《歐洲與中國》(Europe and China: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一書。赫德遜試圖以中國和歐洲作爲對等的兩個文明中心進行論述,上起遠古,下至1912年。他注意考古資料的收集與使用,認爲希羅多德以前東西方的交流就已經有顯著的證據,從而反對戈岱司的較保守的論述。[26]
德國學者黑爾曼(Albert Herrmann)出版於1910年的《漢代繒絹貿易路考》(Die alten Seidenstraß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beiträge zur alten geographie Asiens)和1938年的《古典之光下的絲綢之國與西藏》(Das Land der Seide und Tibet im Lichte der Antike)是作者長期研究絲路貿易的成果。黑爾曼大量運用中國和西方文獻對比的方法,對絲路貿易的路綫作出推定。在後一本書中,作者對賽里斯、秦奈等詞源的出處都進行了詳細的考察。他指出賽里斯這一名稱可能指所有從事絲綢貿易的遠東民族,而將賽里斯的首都賽拉城定於涼州的位置。黑爾曼的研究繼承了洪堡、李希霍芬以來德國對亞洲地理學研究的領先優勢,又適時參考了斯坦因、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同時代西方探險家在新疆和中亞的考察成果,其在二戰前出版的專著堪稱當時對西方文獻中遠東地理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同時代的祁利尼(G. E. Gerini)、貝爾特洛(Andre Berthelot)的著作[27]代表了英法兩國對中亞和遠東古地圖研究的重要成果。
在地理研究之外,對於賽里斯的詞源學研究,以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爲代表。他在20年代作了兩篇劄記,將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新出土的粟特語文獻、佛經梵漢對音與西方古典文獻的記載相結合,以其對歐亞諸多語言的精通,對賽里斯之名探源[28]。在其後出版的《馬可波羅注》(Notes on Marco Polo)中,伯希和對賽里斯詞源問題做出了迄今爲止最全面的總結。由於問題本身的複雜,他沒有就賽里斯的詞源給出確定的答案,但總結了從克拉普洛特以來包括馬夸特(Josef Marquart)、黑爾曼、勞弗(Berthold Laufer)等人對賽里斯的詞源的研究。後來美國學者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加拿大學者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也對此問題展開了進一步論述。[29]
二戰之前對賽里斯問題的研究幾乎都集中在歐洲學術界。唯一例外是日本學者白鳥庫吉1941年發表的《論托勒密所見葱嶺通過路》一文[30]。這篇文章指出了西方學者單方面重視西方古典文獻,而對中國古代史料重視嚴重不足的問題,就托勒密記載的通往“石塔”道路這一問題從中國古文獻記載的傳統出發,得出了與西方學者研究完全不同的結論。
二戰之前中國學者對西方文獻的利用主要是譯介工作。張星烺先生在其出版的《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一冊中輯錄了裕爾收集的西方史料。馮承鈞先生則在所著的《西域地名》中引用了裕爾和戈岱司輯錄的史料,結合漢文和多種西域語言資料,對西域地名進行考訂。
(四)二戰後以來對於賽里斯問題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身對歐洲學術界的摧殘自不待言,戰後出現的兩大陣營對立的局面,以及後來中蘇兩國關係的緊張和印巴危機、蘇聯入侵阿富汗等亞洲內陸政局的變化,使得除了60—70年代法國阿富汗考察隊等少數考古發掘之外,西方學者對中亞和新疆的考察幾近於停滯的局面。由於非學術的原因,中國的公共圖書館里一度中斷了從西方和蘇聯獲得資料的供給,因此提供給中國學者對上述問題討論的空間非常有限。
最早對中國文化產生濃厚興趣的法國此時走在了前面。法國學者布爾努瓦夫人(Luce Boulnois)1963年著的《絲綢之路》,以絲綢作爲中國和西方交流的綫索,刻畫了絲綢工藝的產生和傳播過程,以優雅的筆觸撰寫了從遠古傳說時代到20世紀中葉的中國對外交流史。《絲綢之路》超過了前人的著作[31]而成爲最詳盡的絲綢生產和傳播史方面的論著。
20世紀70—80年代,絲綢之路沿途古代語言的破譯推動了對包括賽里斯問題在內的中國-歐洲交流史的發展。研究者對以往的文獻史料進行進一步總結和討論,如1975、1980年芬蘭出版的兩卷本《東北歐亞大陸拉丁史料集》(Latin Sources on North-Eastern Eurasia)以及1979年瑞士出版的《希臘羅馬世界對西藏周邊的探索》(Griechische und römische Quellen zum peripheren Tibet)。
作爲在羅馬史的大框架下對史料的清理和羅馬史領域內問題的全面探索,1978年歐美各國學者聯合編寫的叢書《羅馬世界的興衰》(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第九卷收錄了弗格森(J. Ferguson)撰寫的《中國與羅馬》(China and Rome)和拉西克(Manfred G. Raschke)的《羅馬東方貿易新探》(New Studies in Roman Commerce with the East)兩篇專論,從東西方貿易的角度對中國和羅馬交往問題重新探討。
這一時期在文獻整理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是法國學者讓維埃(Ives Janvier)1984年發表的專論《羅馬與遠東》(Rome et l'Orient lointain:le problème des Sères. Réexamen d'une question de géographie antique)。讓維埃繼承了古典學家對古希臘羅馬文獻深入剖析的特點,對賽里斯問題進行了全面的再分析。他對史料的和近代學者研究的分類討論都具有獨創性。但是在具體考證中,讓維埃特別注重戈塞蘭(P. F. J. Gosselin)19世紀初提出的觀點,即把有關賽里斯的地名和民族放置在克什米爾(Kashmir)和西藏西部的拉達克(Ladakh)兩地。讓維埃試圖說明,最早的記載中的“賽里斯人”描述的是這一地區,然後賽里斯的形象逐漸向新疆和中國內地(包括西藏)擴展。[32]
同年,西德學者豪西克(H. W. Haussig)結合中文史料指出斯特拉波和老普林尼著作中的賽里斯人實際上是指遊牧的烏孫人。他們在中國和西方的貿易中起中間人的作用。他猜測賽里斯的語源來自錫爾河(Syr Darya)的名稱,由於口述轉譯,帕提亞語稱之爲Silis。[33]以上的說法與衆說相異,列出以資參考。
自20世紀60—70年代法國考古隊在阿富汗的考察和考古發掘爲進一步討論托勒密關於中亞的記載提供了可能。考古隊領導人貝爾納(Paul Bernard)曾就此撰文,成員之一拉平(Claude Rapin)指出托勒密地圖中關於東方部分的材料來源有相當部分來自希臘化時期的資料,並試圖還原托勒密記載中的通往賽里斯之路。[34]
在前蘇聯學者中,亦不乏對賽里斯問題的關注。由於筆者能力所限,對討論賽里斯問題的俄語文獻中,衹查找到前蘇聯科學院1988年出版的《古代和中古早期的新疆史》系列第一卷。[35]此著作系統地回述了西方古典著作中關於賽里斯的記載,並對比中亞和新疆的地理情況進行了勘定。此集體著作一卷中收集上千種研究材料作爲參考,體現了前蘇聯學者的研究成果。
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活躍的中國學術界也積極參與了對賽里斯問題的討論。1985年,莫任南指出《後漢書·和帝紀》記載的“西域蒙奇、兜勒遣使內附”與托勒密記載的馬其頓商人有關。[36]1991年,林梅村將托勒密記載的梅斯商團進入賽里斯境內與《後漢書·和帝本紀》記載的西域二國遣使內附相聯繫,並結合中亞古代語言的研究,考證了托勒密《地理學》記載的西域地名和民族。林文指出賽里斯一名起源於當時粟特人對中國首都的稱呼Srγ,並指出“石塔”的位置在塔什庫爾干。[37]
一時間學者針對林文展開了羅馬商團究竟是否到過中國的討論。楊共樂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爲林文所指的“石塔”位置和賽里斯稱謂均有誤,前者應在帕米爾西部地區,後者與中國首都長安(或洛陽)的稱謂無關。[38]臺灣學者邢義田對林文的叙述發起了全面的質疑,懷疑作爲托勒密材料來源的地理學家馬里努斯(Marinus of Tyre)的可靠性,並認爲梅斯商團沒有到達過洛陽。[39]張緒山則在討論了普林尼所說的賽里斯鐵[40]和羅馬帝國向東方探索路綫的基礎上[41],指出馬其頓商團很可能並未到達洛陽,但可能在西域都護得到了漢朝官員的接見;同時指出用托勒密轉述馬里努斯的記載確定塔里木以東的地理位置是相當困難的。[42]
目前對賽里斯的問題,各國學者仍然莫衷一是。筆者希望在本文的討論中,在回到文本的前提下,對一些最基本的問題進行探討,以期提起對賽里斯問題的關注。[43]這一問題需要不同領域的學者的共同研究,從古典學到東方學,從語言、歷史到地理,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才有希望獲得較圓滿的解決。
二、歷史的映像——文本的再檢討
(一)文本的時段選取與分類
回顧古希臘羅馬文獻中的賽里斯形象,首先要對文本進行重新清理。戈岱司的史料集收集了幾乎全部關於賽里斯問題的史據,包括大段古文引文。這一文集有些過時,對年代的推定也有錯誤。然而它仍是不可替代的基礎性文獻。此文集已於1987年由耿昇先生譯成中文,筆者討論的主要史料來自此文集中。
借鑒讓維埃的思路[44],筆者試圖將關於賽里斯的史料分爲四類。前兩類幾乎同時出現在羅馬共和國晚期和帝國早期,分別代表羅馬詩人和劇作家的傳統,以及繼承了希臘化時代遺產的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傳統。第三類是哲學與宗教思辨的傳統下的基督教和諾斯替教作家的傳統,此時正值羅馬帝國中期,基督教興起但還未成爲國教。第四類傳統則在晚期羅馬帝國與早期拜占庭時期,這一時期的文獻呈現出古典傳統與新興基督教傳統的碰撞與融合。
筆者沒有將較早的零星記錄如克泰夏斯和亞歷山大傳奇包括在考察範圍內。不僅因爲其可信度存疑,而且因爲它們所記載的時段在希臘化時代東西方交往擴展之前。而對於所載史料的下限,筆者以公元4世紀作家阿米安·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爲限。其時沙普爾二世(Šapur II, 公元309—379年在位)確立了薩珊波斯在亞洲西半部的霸權,羅馬-拜占庭世界與波斯以東諸民族的交通受到了自亞歷山大東征以來最大的阻礙。從此以迄6世紀科斯馬斯[45]遊歷印度和彌南德(Menander Protector)記載的拜占庭使節出使西突厥[46],西方沒有獲得更多關於遠東的知識。對於早期中古著作中散見的獨特記載如6世紀作家塞維利亞的伊西多爾(Isidore of Seville)對賽里斯的描述,筆者也將在下文中加以涉及。
(二)羅馬詩人和劇作家筆下的賽里斯
賽里斯的形象馳騁在羅馬“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詩人的筆下,其中尤以黃金時代詩人的作品爲重要。從公元前37年起:維吉爾(Virgil)、賀拉斯(Horace)、普羅佩提烏斯(Propertius)和奧維德(Ovid)的著名詩篇中,都出現了賽里斯的形象。
賽里斯人首先被描繪成珍稀紡織品提供者的形象:在維吉爾筆下“賽里斯人從他們的樹葉上采下來纖細的羊毛”[47];賀拉斯提到了“賽里斯人的坐墊”[48];奧維德則述及“賽里斯人的面紗”[49];普羅佩提烏斯直接使用“賽里卡”(serica)來命名這種紡織品。[50]作爲最早集中描寫賽里斯人的作家,四位用拉丁語寫作的詩人筆下都出現了賽里斯人的紡織品。這決非偶然的行爲,而是表現了當時羅馬對東方絲織品的巨大需求。普羅佩提烏斯的描述,正是西方文獻中對從遠東傳入的絲織品所使用的最早的專有名詞。
然而,黃金時代詩人對賽里斯的描寫並非僅僅局限在絲織品一個方面。在賀拉斯獻給皇帝屋大維(即奧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位)的頌詩(Odes)中,賽里斯人作爲未征服的東方民族之一,與帕提亞人(波斯人)、巴克特里亞人、印度人、蓋提人(Getae)[51]和塔奈斯人(Tanais)[52]並列 :
或者他(奧古斯都)能使威脅着拉丁地區的帕提亞人,
使他們遭受應得的慘敗,
也許東方海岸的臣民,
賽里斯人和印度人,
都將臣服於唯一的您對世界公正的統治。(Ι, 12, 53—57)
你爲小鎮而惴惴不安,
爲大城而憂心忡忡。[53]
怕引誘來賽里斯人、處在居魯士統治下的
巴克特里亞人或內亂中的塔奈斯人。(ΙΙΙ, 29, 25—28)
飲用深深的多瑙河水的人們,
不敢違抗愷撒的敕令,蓋提人、
賽里斯人、不忠的波斯人、
以同名之河流命名的塔奈斯人(都不敢)。(ΙV, 15, 21—24)
當時羅馬人已經熟知自己各個邊界上的民族。羅馬在東方的主要對手是控制波斯的帕提亞人。來自東北方的威脅則是色雷斯人和黑海沿岸民族。賀拉斯祝願屋大維能夠戰勝帕提亞人,從而使賽里斯人和印度人都成爲羅馬的附庸,在這裏賽里斯和巴克特里亞人、印度人一起成爲帕提亞以遠的東方的代名詞,但並沒有對其具體方位的說明。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賽里斯人作爲羅馬可能征服的對手之一,出現在賀拉斯的想像中。[54]
賀拉斯的記載中還提及了賽里斯人的利箭[55];而普羅佩提烏斯則記述了賽里斯人的戰車。[56]這條軍事的綫索始終貫穿在西方史料中。希臘作家查理同(Chariton)也記載了賽里斯的弓箭。[57]2至3世紀賀拉斯詩集的兩位注釋者:偽阿克倫(Pseudo-Acron)和波爾菲利昂(Porphyrion),在詮釋賽里斯人的箭時,都提到了帕提亞人的箭。對賀拉斯《頌詩》“善於射出賽里斯國的利箭……” (Odes,I, 29, 9)的注釋:
賽里斯國得名於同名的賽里斯人。賽里斯民族與帕提亞人相毗鄰,以他們善於造箭而廣負盛名,Sеriсum(這裏指賽里斯織物)一名也由此而來。(偽阿克倫)
此處賽里斯國的箭:就是帕提亞人(的箭),其箭名來自賽里斯民族的名稱,他們居住在東方世界的一隅。(波爾菲利昂)
羅馬克拉蘇軍團在公元前53年卡爾萊戰役中的全軍覆沒,使羅馬人領教了帕提亞弓箭的威力。後世的作家並未指出賽里斯和帕提亞弓箭的區別,說明賽里斯在黃金時代羅馬詩人與修辭家心目中衹是一個遠方神秘模糊的形象。帕提亞耀眼的絲質軍旗,給賽里斯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在白銀時代的羅馬詩人和修辭家筆下,賽里斯仍然以其距離的遙遠和奇妙的織物令羅馬人稱奇。在公元1世紀上半葉著名作家塞涅卡(Seneca)的悲劇作品中,尤其反映了這兩點。他使用“極遠的”(ultimi)一詞來形容賽里斯人[58],但同時承認不知道賽里斯的確切位置。[59]與維吉爾一樣,塞涅卡也認爲賽里斯的羊毛摘自樹上。在公元1世紀下半葉作家西流士·伊塔利庫斯(Silius Italicus)筆下,賽里斯人“往小樹林中去採集枝條上的羊毛”的形象躍然紙上[60],仿佛已成爲當時羅馬人對賽里斯人的常識。伊塔利庫斯還提到酒神巴庫斯(Bacchus)征服東方的故事,並把賽里斯人和印度人作爲他勝利凱旋的俘虜。巴庫斯即希臘神話中的狄奧尼索斯(Dionysus)征服印度,是希臘神話中的傳說之一,在希臘化時代作家的作品中常見。[61]
與黃金時代詩人的描寫相同,賽里斯人的形象也不是單一的。例如公元1世紀末作家斯塔提烏斯(Statius)首次從對錢財的態度描寫了賽里斯人。他記載“賽里斯人吝嗇已極,他們把聖樹枝葉剝摘殆盡,我對此深表惋惜。”[62]而後又將賽里斯人與印度人、阿拉伯人並列爲富裕的民族。[63]
這個時候的羅馬人不僅關注到了賽里斯人的富足,也深知賽里斯作爲羅馬遠方強大民族存在的政治意義。在公元2世紀初,馬提亞爾(Martial)記載了如下的內容:
帕提亞的貴族和賽里斯的首領,
色雷斯人、薩爾馬提亞人、蓋提人和不列顛人,
我能向你們指明真的愷撒[64]:來吧! (Eрigrаms, ХΙΙ, 8,8—10)
圖拉真皇帝(Trajan,公元98—117年在位)時代的羅馬帝國擴大到了其歷史上最大的版圖範圍。羅馬在色雷斯人和蓋提人居住的地區建立了色雷斯、梅西亞和達西亞行省,防備來自北面薩爾馬提亞人的進擊。不列顛人則處於羅馬不列顛行省的統治下。在東方,圖拉真的大軍在吞併亞美尼亞之後,於公元116年佔領了帕提亞的首都泰西封(Ctesiphon)。
馬提亞爾寫作這段詩篇的時間在公元100年至他去世的102年間,此時圖拉真正開始發動對北部邊界蓋提人的戰爭。在馬提亞爾筆下的世界圖景中,賽里斯人也是圖拉真時代盛極一時的羅馬將要征服的對手之一。
在2世紀初詩人玉外納(Juvenal)的諷刺詩中,好打聽的妻子被謔稱爲“通曉普天下所發生的一切:如賽里斯人所做、色雷斯人所爲……”[65]賽里斯再次成爲了遙遠地方的代名詞。
在戈岱司收集的白銀時代詩人的作品中,1世紀中葉詩人盧坎(Lucan)的《內戰記:法爾薩利亞》(Bellum Civile: Pharsalia)中描寫埃及的第十篇里,恰當與不恰當地出現了賽里斯人的名字:
白膩酥胸[66]透過西頓的羅襦閃閃發亮,
那是用尼羅河的織針將賽里斯人細密梳過的
絲綫撚開,織成寬鬆的薄紗。(Х, 141—143)
這一段生動描寫了西頓人將賽里斯織物重新紡織成輕紗的過程[67]。而在下一段里,盧坎卻錯誤地將賽里斯與尼羅河的源頭聯繫起來。
賽里斯人首先見到你(尼羅河),並探問你的源泉,
然後你又在埃塞俄比亞的田野掀起了巨浪。(Х, 292—293)
將賽里斯人與尼羅河錯誤聯繫在一起,是“受到某一地理學理論的錯誤影響(戈岱司語)”[68]。在阿里安的《亞歷山大遠征記》里,這一錯誤的影響早就可見。[69]將埃及、埃塞俄比亞與印度相聯繫是當時古典作家的普遍觀念,即認爲埃及以遠的南方,埃塞俄比亞的上游就是印度。盧坎這樣寫,無非是將賽里斯置於比埃塞俄比亞和印度更邊遠的“尼羅河源頭”而已。在他的同時代,也有一批學者認真考訂了地理知識,得出了更加準確的認識——有時甚至是驚人準確的。這些學者便是從古典作品中汲取營養,又受益於希臘化時代以來東西方交往,從而對東方世界更爲瞭解的歷史地理學家。
(三)希臘羅馬歷史地理學家記載中的賽里斯
幾乎在同時,與詩人傳統相呼應的,是希臘羅馬歷史地理學家的傳統——儘管在汗牛充棟的歷史地理著作中,賽里斯依然衹是寥寥數語,但他們的表達卻成最重要的歷史證據,也佔據了本文最多的篇幅。在目前的傳世著作中,保留下來的最早的歷史地理學著作是公元前後希臘作家斯特拉波(Strabo)的《地理志》(Geography),成書於公元7—18年。
斯特拉波參考阿波羅多魯斯(Apollodorus,生活於公元前2世紀中葉)的叙述,作了如下的記載:
(巴克特里亞國王們)始終不斷地向賽里斯人和富尼人[70](的地區)擴張自己的領土。(ХΙ, 11, 1)
羅馬詩人還完全不知道賽里斯人的準確位置,衹是拿他們和印度人、帕提亞人,甚至和黑海沿岸、多瑙河以北的歐洲“蠻族”相並列,與他們相比,斯特拉波的記載可謂頗爲確切了。公元前5世紀末,克泰夏斯的記載還衹是把賽里斯人和北印度人相提並論;到兩個世紀以後,阿波羅多魯斯的時代,巴克特里亞已納入希臘世界的東北邊境,賽里斯便與之聯繫起來。這一聯繫在後世歷史地理學家的記載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
克泰夏斯記載說賽里斯人長壽可達200歲。斯特拉波則兩次提到這一點:一處說他們比能活130歲的穆西卡尼亞人(Musicanians)[71]還要長壽(XV, 1, 34);另一處記載說有人說賽里斯人長壽可達200歲(XV, 1, 37),但斯特拉波本人認爲這種說法有所誇張。[72]與羅馬詩人一樣,斯特拉波提到了賽里斯人的織物:
賽里斯布(Sеriса)是一種從乾燥的樹皮中採集的麻布……[73](ХV, 1, 20)
據斯特拉波,這一說法來自公元前4世紀奧內西克里圖斯(Onesicritus)對亞歷山大東征的記載,叙述者則是亞歷山大的部將尼亞庫斯(Nearchus)。斯特拉波關於賽里斯人的全部記述中最重要的是他對地理學方面的細緻描述:
印度的地勢呈菱形 :其北端是從波斯之門(Аrеiаs)[74]開始一直延伸到東方邊緣的高加索山,這一山脈把北部的塞種人(Sаkаs)、斯基泰人(Sсhуthеs)和賽里斯人同南部的印度人分開了。(ХV, 1)
儘管沒有指明高加索山向東延伸的具體路綫,斯特拉波正確地指出了賽里斯人等民族和印度人在地理位置上的區別,但是他沒有區分塞種人、斯基泰人地區和賽里斯人地區之間的位置關係。被認爲是羅馬首位地理學家的梅拉(Pomponius Mela)在他成書於公元43年的《地志》(Chorography)里第一次將賽里斯人的準確位置記錄下來:
人們在東方遇到的第一批人是印度人、賽里斯人和斯基泰人。賽里斯人住在臨近東海岸的中部,而印度人和斯基泰人在邊緣地帶。(Ι, 11)
賽里斯人居中、印度人和斯基泰人在南北兩側的基本形狀,構成了當時希臘羅馬世界對歐亞大陸東部最詳細的描述。梅拉在下面的章節里(III, 59—70)對這一段地區的地理進行了描述,其中描寫賽里斯人的部分寫道:
(從大陸東北角的斯基泰海角向南航行)然後又是一片猛獸出沒的空曠地帶,一直到達俯瞰大海的塔比斯山(Tаbis)。(距離塔比斯山)很遙遠的地方聳立着陶魯斯山。賽里斯人居住在兩山之間,是充滿正義的民族,以其將商品放在無人的地方然後躲避起來等待成交的貿易方式而出名。
根據梅拉的描述,在東海之濱,由北部的塔比斯山和南部的陶魯斯山相夾的地帶,就是賽里斯人的土地。塔比斯山以北是斯基泰人和塞種人[75];之南則是印度人。梅拉提供了前代歷史地理學家沒有介紹的新內容,不僅包括地理的位置,還包括對賽里斯人高尚道德的評價。在後期羅馬宗教作家的筆下,這一點被抹上了濃墨重彩。
對賽里斯人貿易方式的描寫也十分耐人尋味。在此前羅馬詩人的筆下,賽里斯人被描繪爲服裝的提供者。[76]而對賽里斯人與西方進行的貿易形式,則是到了梅拉和其後一代人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時代才受到關注。
羅馬白銀時代文學的代表人物,同時又是博物學者的老普林尼所著《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對賽里斯的記載頗爲詳細,涵蓋的內容非常廣泛。特別是有兩處提到了賽里斯人的特徵:
首先遇到的一族人是賽里斯人,他們以其樹木中出產的羊毛而名聞遐邇。賽里斯人將樹葉上生長出來的白色絨毛用水弄濕,然後加以梳理,於是就爲我們的女人們提供了雙重任務:先是將羊毛織成綫,然後再將綫織成絲匹。它需要付出如此多的辛勞,而取回它則需要從地球的一端翻越到另一端:這就是一位羅馬貴婦人身著透明薄紗展示其魅力時需要人們付出的一切。賽里斯人舉止溫文敦厚,但就像其樹林中的動物一樣,不願與人交往,雖然樂於經商,但坐等生意上門而絕不求售。(VΙ, 54)[77]
賽里斯人居於伊莫都斯山(Hеmоdus)以外,(錫蘭的)人們曾經見過他們,以其商業而著名。(錫蘭使節)拉契亞斯(Rасhiаs)的父親曾經造訪過賽里斯國,而使節們自己也曾見過賽里斯人。他們描述說賽里斯人身材高大超乎常人,長着紅色頭髮、天藍色的眼睛,說話聲音很粗,交易時不說話。這一叙述與我們的商人所述相同:他們把運去的貨物放置在河對岸,與賽里斯人用來易貨的商品並列,如果賽里斯人滿意就取走貨物。(VΙ, 88)
與梅拉一樣,老普林尼的記載也非同尋常。他對賽里斯人貿易方式和外形的描述,在古典時代諸作家中是最詳細、最全面的。[78]而他對賽里斯織物如何生產的記載,則與前代作家大同小異。他認爲賽里斯人在樹叢里採摘羊毛,並多次提到“羊毛樹”(lanigeras)。[79]他還提到了賽里斯人出口鐵:
在各種鐵中,賽里斯鐵名列前茅。賽里斯人在出口服裝和皮貨[80]的同時也出口鐵。(ХХХΙV, 145)
賽里斯人出口鐵的說法,與普羅佩提烏斯談到的賽里斯戰車、賀拉斯記載的賽里斯弓箭一樣,證明了賽里斯這一民族在技術上的先進性,以及經濟和軍事實力。這也難怪老普林尼會在他的著作里驚呼:
以最低的估算,從我帝國每年流入印度、賽里斯和(阿拉伯)半島的財富,合計達一億塞斯特(羅馬銀幣單位)。(ХΙΙ, 84)[81]
老普林尼的書還介紹了遠東的地理。他對基本方位的描述和梅拉相似,但是記述了賽里斯人和印度人之間的很多民族[82],特別是包括富尼人(Phuni)和吐火羅人(Thocari)。可以看出那時羅馬作家已經知道賽里斯人和印度人之間有衆多民族,以及複雜的地形關係了。此外,梅拉和老普林尼都提到,在斯基泰人(以及塞種人)與賽里斯人居住的北界塔比斯山之間,都有一片野獸出沒的不毛之地。梅拉和老普林尼對東方地理細緻入微的描述表明,在羅馬黃金時代以後,拉丁作家對東方的瞭解已經極爲深入。
老普林尼的作品後來廣爲引用。例如3世紀初作家索林(Solin),戈岱司評論說,他的作品“衹不過是照抄多少有些刪節的普林尼著作罷了”[83]。然而,在對老普林尼的記載有所發揮的作家中,索林還是模棱兩可地提供了新的信息。與梅拉和老普林尼的記載有所不同的是,在索林筆下,翻過了塔比斯山之後,仍然要經過一段沙漠地帶才能到達賽里斯人的國家(LI)。索林還提到,錫蘭人可以從他們的山頂眺望到賽里斯的海岸(LII, 21),這一說法是對距離遠近不明的遠方民族的臆想。
哈德良皇帝(公元117—138年在位)統治時期的兩位作家弗洛魯斯(Florus)和德尼斯(Denys,即Dionysus Periegetes)都分別有不同於前人的新記載。在弗洛魯斯的《史綱》(Epitome,又譯《史鈔》)中,作家描寫了奧古斯都加冕禮上東方各國使節前來拜訪的情景:
斯基泰人和薩爾馬提亞人都遣使尋求與羅馬友好。同樣,賽里斯人和處於太陽垂直照射下的印度人也來了,他們帶來了寶石、珍珠和大象,他們考慮最多的就是這漫長的路程——他們說需要走將近四年始可到達。實際上衹要看一看他們的皮膚,就知道他們來自與我們不同的世界。(ΙΙ, 34)[84]在奧古斯都的紀念銘文(Res Gestae Divi Augusti)中,衹有印度人遣使的記載(§31)而沒有賽里斯人的名字。以作品的浮誇著名的弗洛魯斯發揮想像,把賽里斯和印度人相提並論,提及了他們與衆不同的膚色。這裏應當是指奧維德記載的“黝黑”膚色而不是老普林尼筆下的那種容貌。
同時代的德尼斯編寫的《百科書典》(Periegesis)的幾個不同版本里,都提到了賽里斯:
吐火羅人、富尼人和賽里斯國內的蒙昧部族,
都不重視肥壯的牛羊,
他們可以織出自己荒涼地區五彩繽紛的花朵,
還能以高度的技巧裁製貴重的服裝,
具有草原上綠草閃閃的光澤,
即使是蜘蛛的勞作成果也難以與之媲美。(752—757)
在4世紀阿維埃努斯(Avienus)和普里西安(Priscianus)編纂的拉丁文版本中,對以上記載的表述略有不同[85]——這又是一種對賽里斯人獲得織物的解釋。與老普林尼的記載相同,在德尼斯的筆下,吐火羅人和富尼人再次成爲賽里斯人的鄰居。
希臘地理學家中最重要的著作當屬托勒密的《地理志》(Geography)。托勒密對全世界地理的詳盡描述,主要借鑒了地理學家馬里努斯(Malinus of Tyre)的著作。此外,托勒密還很可能借鑒了《厄立特里亞海周航記》(Periplus Maris Erythraei)。[86]經過最近學者的詳細研究,托勒密《地理志》關於東方的部分主要來自兩部分原始資料,除了關於賽里斯的部分(VI, 16)主要來自馬里努斯的記載外,此前部分的叙述(VI, 10—15)中相當大的部分是來自賽琉古帝國所繪製地圖的史料。[87]而他所做的不過是修正馬里努斯的地理表——將世界的邊界縮小,並重新勘定了各個地點的經緯度。
托勒密在描述已知有人居住的世界(ecumene)的四至時,對賽里斯所處位置的基本描述如下:
大地上我們人類所居住的部分地域的東部邊界毗鄰未知的大地;未知大地內是居住在大亞細亞的東方民族秦奈人和居住在賽里斯國的諸民族……與北面的未知之地接壤的則是屬於大亞細亞的極北土地:薩爾馬提亞、斯基泰和賽里斯三國。(VΙ, 5, 2)
以上的描述即把賽里斯人置於有人居住的世界的東北邊界。就東部邊界來說,在所謂“大亞細亞”(Megale Asia)的北部,南面是位於正東的“秦奈”(托勒密使用Sinai而不是《厄立特里亞海周航記》中的Thinae);就北部邊界來說則在薩爾馬提亞和斯基泰(斯基泰人的土地)的東面。
此外,托勒密保留下來馬里努斯對當時馬其頓商人梅斯(Maes Titianos)的代理人行程的記載,提供了當時商人前往賽里斯進行貿易的路綫。在他的記載中出現了“石塔”或“石堡”(Lithinos pyrgos)這個關鍵地名。除去其中對經緯度的考訂和對路程遠近迂回的爭辯,重新整理托勒密的地理叙述後,對梅斯的代理人去往賽里斯國的行程可以作如下的概述:
代理人從幼發拉底河畔的希拉波利斯(Hiеrароlis)出發,經過美索不達米亞到達底格里斯河,然後經過亞述的加拉米亞人地區和米底亞到達埃克巴塔納和里海之門,再經帕提亞到達赫卡頓比勒……從赫卡頓比勒前往希爾卡尼亞首都,必須向北繞行……接下來是從希爾卡尼亞首都經阿里亞到達馬爾吉亞那的安條基亞的路程,這段路是先向南行……再向北……從這裏道路通向東方,直至巴克特拉,然後向北登上科梅多地區的山脈,再向南到達平原通向的山谷。這座山脈靠西北的部分,即(從巴克特拉出發後)登上的地方和拜占庭在同一緯綫上,而靠東南的部分則和赫勒斯滂(Hеllеsроnt)在同一緯綫上。因此他(馬里努斯)說儘管這條路是一直向東的,但是會略偏向南方。而接着從山谷上行直至石塔約五十雪尼的方向略偏向北,據說從山谷爬上去就到達了石塔,從此向東延伸的山脈與從帕林波特拉(Pаlimbоthrа)向北而來的伊麥奧斯山相接。(Ι, 12, 5-8)
……從石塔到賽里斯的都城賽拉的路程要經過七個月……(Ι, 11, 3)
……從石塔到賽拉途中要經受猛烈的風暴,因而必須在途中多次停留。(Ι, 11, 5)
這一段記載是目前唯一保留的從西方去往賽里斯的完整行程記錄(參見附錄地圖二)。可惜的是,自石塔以後到賽拉的路程,除了需要七個月時間和沿途風暴之外,沒有明確的地理記載。這也說明,當時西方作家對去往賽里斯的地理路綫瞭解的最遠處是石塔。
托勒密的著作中還以較大的篇幅叙述了賽里斯國的地理狀況(VI, 16)。他記述了包括賽里斯國的邊界、山川、民族和城市在內的詳細內容,對主要的地理特徵都標注了經緯度。作爲托勒密宏大地理著作的一部分,他對賽里斯國的概括爲後世提供了一串地名與民族名稱,其中大部分散見於此前諸作家的筆下。但是直至今日,對托勒密留下的地名的考證仍然未能令人滿意,就連托勒密所記載的賽里斯國的具體位置,也處在爭論不休的境地。蓋希臘羅馬世界與遠東路途遙遠,其記述的地理位置難以準確。托勒密又主要依據馬里努斯一人的作品爲材料寫成,卻將馬里努斯採用的經緯度盡數修改,因此很難通過最終記載在案的內容推定出真實的地理狀況。
在托勒密的另一部作品《占星四書》(Tetrabiblos)中,也記載了賽里斯人:
在四分大地的第三部分,其中包括大亞細亞的北半部,包括希爾卡尼亞、亞美尼亞、馬提亞納、巴克特里亞、卡斯佩里亞、賽里斯、薩爾馬提亞、奧克西亞那、粟特以及整個有人居住世界東北部分的其他地區……這些地區的居民崇拜木星與土星[88],財貨充盈、盛產黃金,其生活方式潔淨而文雅,睿智而善崇信神靈,生性公正而愛好自由,心靈寬廣而高尚,嫉惡如仇而又溫柔深情;若有善良與神聖的緣由,他們隨時願爲朋友勇敢赴死。他們的情愛關係嚴肅而純潔,著裝奢侈,和藹而有雅量……巴克特里亞、卡斯佩里亞和賽里斯地區屬於天秤宮和金星,因此這些地區的居民非常富有,喜愛藝術,而且更加奢華。(Ι, 3)
將占星應用在賽里斯人之上的作品,在托勒密之後也有論及,這就是叙利亞諾斯替教作家巴爾德薩納(Bardesanes)及其學生僞巴爾德薩納(Pseudo-Bardesane)等人的作品。這些作品將在下一節中專門展開討論。
在進入宗教作家的討論之前,最後一位需要著重提及的歷史地理學家是公元2世紀下半葉的保薩尼亞斯(Pausanias),他的作品《希臘道程》(Description of Greece)中記載了賽里斯人是如何獲得絲綫的(VI, 26, 6-8)。這一段描述已經反復爲歷代學者所論及,從而被看作是西方第一次知道中國人養蠶繅絲的大致手段。對於保薩尼亞斯記載的小蟲“賽兒”(Ser),有學者如克拉普洛特認爲就是“賽里斯”之詞源所在。詞源的問題且置後論,從保薩尼亞斯的生動描述來看,他已經完全脫離了前代作家“給樹葉澆水”和“梳理羊毛”的觀念,而是從一處不明的來源得知了近似實際的養蠶過程[89]。但是對於獲得蠶繭以後的處理,保薩尼亞斯沒有留下記載。
保薩尼亞斯接下來的叙述(VI, 26, 8—9)也是在西方文獻中首次出現。他指出,賽里亞島(Seria nesos)爲一條叫做賽兒(Sera)的江河和厄立特里亞海所包圍而成;而且,賽里斯人是埃塞俄比亞種[90];也有人說他們是“斯基泰人和印度人的混血種”。與其他作家的記載相比,保薩尼亞斯對“賽里亞島”的說法過於離奇;而他說賽里斯人是混血種的說法,似乎是對賽里斯人處在斯基泰人和印度人之間位置的一種延伸思考。
有趣的是,保薩尼亞斯對織物生產方法的比較準確的記載沒有在當時馬上流行開來。不必說前面提及的3世紀作家索林,即使到4世紀的著名作家阿米安·馬塞利努斯的筆下,維吉爾和老普林尼的“權威”說法依然記錄在紙上。直到6世紀拜占庭作家普羅可比(Procopius)的《哥特戰爭》中叙述了查士丁尼皇帝(Justinian, 公元527—565年在位)從印度僧侶(一說爲波斯人[91])的手杖中獲得蠶種,關於絲織品的秘密才漸漸被西方人掌握。難怪研究絲綢之路的學者布爾努瓦夫人會這樣激動地問道:
在保薩尼亞斯時代,是否無意中洩漏過絲綢的秘密呢?是否因爲偶然的機會使西方人得到了有關這方面的信息,後來由於遭到駁斥就又被永遠忘記了呢?雖然保薩尼亞斯所持之說最爲接近實情,但與他同時代的人是否會相信他呢?[92]
歷史中較爲真實的記載,或許總有一些是要遭受如此命運的吧。
(四)羅馬帝國宗教作家筆下的賽里斯
前文講到的叙利亞諾斯替教神學家巴爾德薩納(公元154—222年)及其門徒的作品,就屬於宗教作家的傳統。他們一再重複的一段話是:“賽里斯人嚴禁殺人、賣淫、盜竊和崇拜偶像”。巴爾德薩納的原著是叙利亞文,其英譯名爲《命運對話:世界各國的法律之書》(Dialogue on Fate: The Book of the Laws of the Countries),以對話體寫成,由巴爾德薩納講述。一般認爲,現存的叙利亞文作品是巴爾德薩納的叙利亞學生菲利浦(Philip)所作[93],因此戈岱司在他的譯文中稱其爲“僞巴爾德薩納”(Pseudo-Bardesane)。[94]在目前保留下來的希臘引文取自尤西比烏斯(Eusebius)的《宣講福音的準備》(Praeparatio evangelica)[95]和凱薩里烏斯(Caesarius of Nazianzus)的《對話》(Dialogue)[96]中。筆者下面節選的是尤西比烏斯的版本。現存的拉丁文引文則來自克力門傳奇(Pseudo-Clementine Romance)中的《認知》(Recognitions)。[97]
從大地的開端起(叙述)。在賽里斯人中,法律嚴禁殺人、賣淫、盜竊和崇拜偶像。在這遼闊的國度里,人們既看不到寺廟,也看不到妓女和通姦的婦女,看不到逍遙法外的盜賊,更看不到殺人犯和兇殺受害者。經過子午綫上空光輝的阿瑞斯戰神之星體不能違背人心而用武器殺人,與阿瑞斯相合的啟普里斯也不能強迫他們之中的任何人與別人的妻子私合。儘管在他們之中,阿瑞斯戰神每時每刻都在天中央巡視,賽里斯人每天、甚至每時每刻都在生育。(Prаераrаtiо еvаngеliса, Libеr VΙ, Х)[98]
下面一段出現在克力門傳奇的叙述則在內容上略有添加和差異:
所以賽里斯人是首先居住在大地盡頭的,他們擁有一整套法律,嚴禁兇殺、通姦、賣淫、盜竊和崇拜偶像。在這遼闊的國度里,既沒有寺廟也沒有偶像,既沒有妓女也沒有通姦的婦女,從沒有傳庭公審的盜賊,也沒有人記得那裏曾經有人被謀殺死。最後,燃燒的馬爾斯之星不像在你們之中一樣對他們的自由仲裁施加影響,不讓用武器殺死他們的同類。與馬爾斯相合的維納斯女神並沒有迫使他們去玷污別人的妻妾,儘管在他們之中,馬爾斯戰神整天佔據着天空的中央。但在賽里斯人中,對法律的畏懼比對人們在其之下降生的星辰的畏懼還要強烈。(Ps. Сlеmеnt, ΙХ, 19)[99]
巴爾德薩納稱,在賽里斯人廣袤的土地上,人們都遵循着嚴格的法律,還將金星(啟普里斯[100]或維納斯)和火星(阿瑞斯或馬爾斯)相合的影響考慮其中。[101]除了尤西比烏斯和克力門傳奇之外,巴爾德薩納的叙述在後來的拜占庭作家如9世紀的哈馬爾托爾的喬治(George Hamartolus)、11世紀的賽德雷努斯(Cedrenus)以至15世紀的弗蘭茨(Phrantzes)等人的作品中也全文引用。[102]基督教會史上的著名作家奧利金(Origen)在他的《反對塞爾蘇斯》(Contra Celsum)一文中也引用了巴爾德薩納叙述中關於偶像崇拜的問題。[103]戈岱司認爲,奧利金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基督教直到他生活的時代(3世紀上半葉)還未傳播到賽里斯人中間。[104]奧利金在反對信奉羅馬傳統宗教的塞爾蘇斯時明確指出,賽里斯人沒有任何的偶像或寺廟,是因爲他們並不信神,而是無神論者。奧利金對馬太福音的詮釋中也記載道:“無論在賽里斯人中還是(其他)東方民族中,至今尚未傳播基督教。”[105]裕爾曾經提到比奧利金稍晚的基督教作家阿爾諾比烏斯(Arnobius of Sicca)的著作。在後者爲反對異教徒而作,因而顯得誇張的記載中,到3世紀下半葉,基督教的福音已經傳播到了賽里斯人中間。[106]
巴爾德薩納以後描寫賽里斯人高尚道德的作家大都是基督徒——巴爾德薩納本人也是基督徒,衹是後來被正統教會宣佈爲諾斯替教異端。[107]作爲基督徒描寫並不信教的賽里斯人,還在其中引用異教的神靈和占星術的內容,這體現了在成爲羅馬國教之前基督教傳播早期的一個時代特徵。這些基督教作家仍然需要提到占星術這個時尚的話題,異教的諸神被賦予神化的星辰形象,從而成爲基督教作家筆下邪惡的源泉。在公元初思想活躍、各種知識流派百花齊放的羅馬帝國,基督教要與各種救世神學相鬥爭,而基督的降臨則成爲此後的時代與古典宇宙秩序的深刻決裂。因此,尚未取得思想上的權威地位的基督教作家要參與到對占星術的討論之中,而並不是像後世的正統基督教教義那樣對占星術採取一概排斥的態度。[108]
巴爾德薩納在他的對話中警告弟子,人的行爲並非由星辰所註定的命運所左右,世界各地的法律、風俗和禮教——從遙遠的賽里斯人開始——決定了一個地區人民的生活,這實際上是他反對羅馬傳統宗教和占星術決定人的命運的看法。雖然他後來被斥爲異端,但是叙利亞哲學家的傳統實際上是完全與古典羅馬作家追求“羅馬永恆”(Roma aeterna)和相信羅馬是(異教諸神的)“神意的代表”的史學傳統[109]相悖的。儘管在《命運對話》中巴爾德薩納試圖以人間的法律和習俗取代以占星術爲代表的命運,他的調和主義論調受到了以聖以法蓮(St. Ephrem)爲代表的正統派教徒的抨擊。[110]
這種把賽里斯人的種種傳聞和其風俗習慣聯繫的說法並非從3世紀開始。與保薩尼亞斯同時代的作家琉善(Lucian)爲賽里斯人的高夀陳述了理由。賽里斯人的壽齡達到了300歲,超過斯特拉波記述的200歲。琉善說,“有人把這種高夀歸之於氣候原因,還有人認爲是土質原因,甚至更有些人歸之於養生之道;確實有人說整個賽里斯民族以喝水爲生。”[111]這裏的闡釋帶有道德勸誡的意味。同在公元2世紀的著名醫學家蓋侖(Galen)對“賽里斯蘋果”的描寫也是對養生之道的議論。他告誡人們要趁鮮嫩時食用,而且不要吃得太飽。[112]
這一時期羅馬作家所作的虔誠描寫,將賽里斯人樹立爲理想中的民族、人類道德的楷模。這一形象並非單純出於想像,也是符合傳統的。在古希臘羅馬文獻中,描繪遠方幸福生活的烏托邦已然司空見慣。賽里斯人被描繪成“充滿正義的”高貴民族,通過潔身自好的生活來實現凡人難以企及的長壽。描寫賽里斯人的想像力,其實不過是對希羅多德記載的“北風以外的人”所處的文明而高潔的生活方式的一種延續——就像讓維埃指出的:“這不是發明,而是變形。”[113]不僅西方人有這樣的愛好,即使是我們古代中國人在記載到遠方的大秦國時,也說了如下的話語:
(大秦)其王日遊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114]
以上對羅馬共和國政體的速寫,流露的是由衷的欣賞。中國史官對周圍“蠻夷”民族多持輕蔑態度,但在他們筆下,遠方的大秦文明卻如此耀眼。
值得一提的是,在羅馬宗教作家傳統的同時期,還活躍着以出色的文學作品流傳于世的作家。3世紀作家赫利奧多魯斯(Heliodorus of Emesa)就是其中一位。[115]在其作品《埃塞俄比亞人》(Aethiopica)中,他沿襲了盧坎所堅持、爲保薩尼亞斯所提及的地理學理論,把賽里斯與埃塞俄比亞聯繫起來。
《埃塞俄比亞人》的第九章描寫道,在埃及南部邊境,遠征的波斯騎兵和來自其首都麥羅埃(Meroe)的埃塞俄比亞人交鋒。埃塞俄比亞人一方,由布蘭米耶人(Blemmyes)和賽里斯人組成的重裝步兵擔任先鋒。他們與大象隊一起大破波斯騎兵。[116]戰後,賽里斯人的使節向埃塞俄比亞國王希達斯佩斯(Hydaspes)[117]敬獻了“該國蜘蛛織成的絲綫和織物,以及染成紫紅色或素白色的服裝”[118]。有學者認爲,這裏出現的賽里斯使節意味着公元3世紀以前中國與非洲的遠洋貿易航路的存在,比15世紀的鄭和下西洋早了1200年。[119]但是如果回到文本細察,中國人並沒有將自己的絲織品染成地中海世界偏愛的紫紅色(代表尊貴)或素白色(中國喪服的顏色)的習慣,相反,如果要染成紫紅色,所需要的染料必須在地中海東岸的推羅、西頓等地獲取。[120]總之,赫利奧多魯斯生動表現的賽里斯使節,如果確有其人,也不過是爲了迎合地中海世界的審美而將買來的絲綢進行過加工染色和重新織造的中間商。然而即使如此,所謂“蜘蛛織成的”賽里斯絲綫和織物,則有可能是未經加工的中國絲織品。縱然不存在所謂中國與東非的直接聯繫,絲織品也早已通過發達的海路貿易到達了遙遠的東非海岸。
(五)晚期羅馬帝國與早期拜占庭時期作家的描述
4世紀初,伴隨着君士坦丁大帝遷都拜占庭,羅馬帝國進入了其晚期歷史階段。其時帝國的政治軍事重心已逐漸轉移到東方,而古典傳統在新的帝國宗教基督教的傳統面前,逐漸退居其後。崛起的薩珊波斯成爲羅馬的勁敵,曾經一度繁盛的東西方貿易受到波斯人的阻礙。作爲對波斯國王沙普爾二世長年戰爭的親身體驗,被稱爲最後一位古典作家的阿米安·馬塞利努斯提供了與前人不同的知識,這些知識大概來源於他在東方作戰期間。在阿米安的《歷史》(Res Gestae)中,賽里斯是波斯的衆多行省之一。
在記載前往賽里斯的道程時,阿米安叙述說:
(粟特地區)附近是野蠻的塞種人,居住在衹生長牲畜的不毛之地,因此他們沒有文明開化。阿斯卡米尼亞和科摩多山高聳於其上。在經過這些山腳下到達叫做石塔的村莊之後,伸展開一條通向賽里斯的長路,供商旅不斷往來。(ХХΙΙΙ, 6, 60)
在托勒密之後二百餘年,阿米安的記載中再次提到了“石塔”(Lithinos Pyrgos)。他明確指出“商人們便由此地前往賽里斯人中去”。他提供的綫索中,包括不毛之地和兩座山的位置,給尋找石塔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而下面的記載則詳細說明了賽里斯的位置:
在(伊麥奧斯山內外的)兩個斯基泰地區以遠、向東的位置,由高聳的壁壘頂端連結成的環形區域圍繞着賽里斯國,這裏豐饒多產、周遭廣闊,西接斯基泰地區,北面和東面則毗鄰荒蠻的雪原,而南部邊界則延伸到印度和恒河。(ХХΙΙΙ, 6, 64)
接下來,在叙述了一系列山的名字之後,阿米安特別提到了兩條河流,這兩條河流成爲後來學者爭議之一。
在四周爲斜坡和陡峭懸崖環繞的(賽里斯國)平原廣袤的土地上,相互分開的兩條著名河流奧伊哈爾德斯河(Oiсhаrdеs)與鮑提斯河(Ваutisоs)緩慢而蜿蜒地流過。平原上各地的自然環境各異:這裏寬闊而開放,那裏則帶有緩緩的坡度,如此的環境中農作物、畜群和果樹都欣欣向榮地生長着。(ХХΙΙΙ, 6, 65)
下面又提到了許多民族和城市的名字,其中最後一個城市是賽拉(Sera),即托勒密記載的賽里斯都城(Sera metropolis)。然後,阿米安再次進行了大段叙述(XXIII, 6, 67—68),儘管其中的相當一部分有抄襲前人(錯誤觀點)的嫌疑,例如老普林尼所述的向樹林噴水採集絨毛,以及賽里斯人奇特的交易方式;有一些地方明顯是穿鑿,比如由氣候宜人、森林茂密過渡到給樹林噴水、採摘絨毛;有的甚至是不合情理的,比如說賽里斯人不要求任何的進口物品作爲交換。但是應該承認,阿米安的全部描寫提供了寶貴的信息:圍繞着賽里斯國的高牆,以及對兩條河流的微妙描寫,是推斷賽里斯國地理的重要證據;他對賽里斯國人民喜愛寧靜和平、決不訴諸武力的描述,繼承了宗教作家們美好的幻想,而對立於早期羅馬詩人筆下那個強悍的形象。這種立場不僅表現了羅馬人自己心態的變化,也透露出當時所記載的商旅之路上的賽里斯,與早先羅馬黃金時代詩人筆下的形象亦有所不同。
晚期羅馬帝國的文學傳統分多個頭緒展開,其中古典派的代表人物除了阿米安之外,還包括當時的詩人。在古典風格的詩作中,縹緲的賽里斯人形象不時閃現。奧索尼烏斯(Ausonius)、克勞狄安(Claudian)等人依然如故地提到那個和紡織品相聯繫的賽里斯人:賽里斯人的長裝(vesti fl uus)、服裝(vestis)[121];賽里斯人的羊毛樹林(lanigerae)、羊毛(vellera)、紗綫(subtegmina)、帷幔(velamina)和絲綫(stamina)。[122]這些對紡織品的用詞都十分精細,不再像早期的詩人那樣使用模棱兩可的“賽里斯織物”等詞語。賽里斯人和紡織品的聯繫雖然變得更加深刻,但詩作中仍然堅持傳統的“羊毛樹”作爲賽里斯織物的出處。[123]
晚期羅馬帝國時期,基督教作家的傳統已經在帝國境內佔據了主要位置,這一傳統下的文學又與古典詩作大相徑庭,尤其是在對同一事物的關注重點上。與奧利金作品中的情形一樣,賽里斯作爲不信教的遠方民族,在基督教教父們與異教徒和異端的論戰中不斷被提起。前面說到的塞薩爾等人引用巴爾德薩納的作品就是一個例子。4世紀下半葉希臘教父埃彼法尼烏斯(Epiphanius)的《反對異端》中叙述了賽里斯人的習俗。他指出賽里斯人的男子結髮並使用香料和梳妝,以博得妻子的歡心;而女子則剪去長髮,著男裝從事農業勞動 。
4世紀的另一個延續前代的傳統是歷史地理作家的傳統。雖然由於蠻族入侵和波斯的崛起,新的歷史地理作品已經不可能達到帝國早期那樣的精確度,希臘羅馬作家還是試圖在基督教文獻和古典作品兩處汲取資源。帕拉迪烏斯(Palladius)是其中歷史作品的代表人物。在帕拉迪烏斯關於賽里斯國記載的兩個版本[124]中,有亞歷山大曾到達賽里斯國,並立下石柱的說法,還提到婆羅門(brachmanes)來自印度與賽里斯兩地。帕拉迪烏斯在記載中把埃塞俄比亞的阿克蘇姆王朝(Axum)和印度聯繫起來——印度商人“乘小舟自阿克蘇姆”順尼羅河而上,從而到埃及的底比斯進行貿易。[125]這裏的記載與前面討論的盧坎、赫利奧多魯斯等人的描述有相承關係。
這一階段地理志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則包括朱利烏斯·霍諾留斯(Julius Honorius)和奧羅修斯(Orosius)。戈岱司似乎極爲重視這一時期地理志的意義,他強調說:
霍諾留斯等人的著作……實際上和一項由愷撒大帝創始,而由奧古斯都完成的壯舉有關,這一壯舉目的在於對羅馬帝國各行省進行地形測量。他們所搜集的資料已被彙編成冊,形成一幅包括已知世界全部疆域的路綫圖。這一巨著成了後來一系列地理著作的基礎,令人遺憾的是原圖沒有流傳下來。……
霍諾留斯和奧羅修斯的作品反映的是同一傳說內容,而且是出於羅馬帝國的地圖繪製術。它們對於遠東的地形地貌的描繪與我們從普林尼和梅拉的著作中所看到的沒有什麽明顯的差異,這又一次證明他們著作反映的是一個古老傳統,而且無論如何比托勒密地圖要古老得多。[126]
戈岱司所謂羅馬帝國的地圖繪製術,從目前留存的波伊廷格爾地圖(Tabula Peutingeriana)中可以窺得其貌。[127]就此處所關心的文本而言,霍諾留斯等人的記載的確包括了不同於前人的內容。
奧羅修斯[128]都記載了從東洋(oceanus eous)中恒河河口的海路繼續東行偏北的地方有一個河口[129],自此以北就是賽里斯洋(oceanus Sericus)。這是賽里斯首次作爲海洋的名稱見載。奧羅修斯接下來叙述說,在恒河源頭與前面提到的那條偏北的河流的源頭之間有從陶魯斯山綿延而來的帕羅帕米薩達山區(montani Paropamisadae)。[130]奧羅修斯記錄了從此以北的山脈、河流和民族的名字,但是其中沒有賽里斯人,衹有賽里斯洋。
奧羅修斯還記載說,斯基泰人“因爲土地貧瘠而向遠方四散流浪”[131]。或許,前者對斯基泰人居地描述本是屬於賽里斯人的。
除了位於已知世界東北方的賽里斯洋之外,另一處記載說大賽里斯(Seres magnum)是著名的城市。這一說法見於霍諾留斯筆下。6世紀作家塞維利亞的伊西多爾(Isidore of Seville)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賽里斯人之名即得自同名的城市”[132]。這個說法在霍諾留斯的記載中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印證。他提到了東洋(oceanus orientalis)的大賽里斯和泰里奧德斯(Teriodes)兩座城市(I, 6),在下面的章節里又都記載了北洋(oceanus septentrionalis)的兩個民族:賽里斯人和泰里奧德斯人。這樣的對應記載看似有些滑稽和順序倒錯,即使是再粗心的讀者也會發現東洋和北洋的不對應性。然而,正是此處記載使讀者看到了一種模棱兩可的特性——無論是在東面還是北面都適用的賽里斯的位置。[133]
關於這裏出現的泰里奧德斯,有一條河流和它對應。泰里奧德斯河由位於斯基泰地區的三處源頭匯合,匯合之後的流程是942哩[134],最後流入里海。當時的作家還不能確知里海的大小,但對其相對位置是明確的。因此有理由認爲,泰里奧德斯人所在的地區比賽里斯人更靠近里海。[135]
從晚期羅馬帝國和拜占庭早期的文獻中可以看到的是一種從過去的傳統中尋找知識的熱情——無論是從古典作家、歷史地理學傳統或是基督教宗教作家的傳統中,當時的作品里體現了些許有價值的信息。但是總的來說,這時的西方世界已經逐漸與遠東隔離起來,對對方的信息也變得非常模糊。[136]絲綢之路上的陸路交通爲陸續崛起的薩珊波斯、寄多羅、嚈噠以及後來的突厥所阻斷。5世紀以後希臘作家如赫拉克利亞的馬爾西安(Marcian of Heraclea)、拜占庭的艾提拿(Etienna of Byzantine)和以親身造訪印度而著名的科斯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留下的大段歷史地理學記載都是關於海路航行到印度的內容。拉丁作家如6世紀的約爾達內斯(Jordanes)和塞維利亞的伊西多爾,則是將前人的著作重新整理和加工而著述。[137]除了普羅可比對蠶種西傳的記載外,這一時期的西方文獻對遠東的賽里斯人實在乏善可陳。
6世紀中葉突厥帝國的建立和在中亞的霸權深刻改變了東西方之間的交往,新的信息從此傳入西方。西方文獻中以“桃花石”(Taugast)稱呼陸路交通到達的遠東地區,但賽里斯之名並未被取代。傳播景教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叙利亞文碑文提到的Saraga,以及粟特文殘卷中的Srγ,都被學者認爲與賽里斯有關。而第一個親歷中國,並真的認爲當時的中國就是古典作家筆下賽里斯的,恰恰是以拉丁文寫作的方濟各會修士威廉·魯布魯克。[138]
如果說文本中的賽里斯衹是一個西方人眼中的映像,那麽它所反映的歷史真實則需要經過一番去僞存真來得到驗證。在本文的下半部分,筆者將試圖揭開賽里斯的真面目。
附:地圖

地圖一:公元2世紀的東西方世界:東漢、貴霜、帕提亞與羅馬

地圖二:托勒密記載的梅斯商團從希拉波利斯到石塔的行程
■注释
[1] 關於《獨目人》名稱之來歷參見Alemany i Vilamajó, Agustí, “Els «Cants arimaspeus»d’Arísteas de Proconnès i la caiguda dels Zhou occidentals”, Faventia, 21 (1999),p. 49, nt. 12.
[2] Pindar, Ol, 3, 16; Pyth, 10, 30; Isth, 6, 23; Pae, 8, 63.
[3] Herodotus, IV, 32—33.
[4] 參見張緒山:《三世紀以前希臘-羅馬世界與中國在歐亞草原之路上的交流》,《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第67頁。
[5] 如英國學者赫德遜(Geoffrey Francis Hudson)之觀點,參見(英)赫德遜:《歐洲與中國》,王遵仲、李申、張毅譯,何兆武校,中華書局1995版,第45—52頁。
[6] 此爲余太山先生之觀點,請參見余太山:《希羅多德關於草原之路的記載》,《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四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版,第22頁。
[7] 有學者試圖將阿里斯鐵記載的民族大遷移(Herodotus, IV, 13)與《史記·周本紀》中記載的犬戎(或獫狁?)攻陷西周鎬京相聯繫,參見Alemany, 注1所引文,pp. 50-55.
[8] 公元前404年—397年間,克泰夏斯作爲宮廷醫生,爲波斯君主阿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II Memnon,公元前404年—前358年在位)服務。
[9] Cœdès, Georges, Textes des 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a l’Extrême-Orient depuis le IVe siècle av. J.-C. jusqu’au XIVe siècle, Paris: Ernest Leroux, 1910, p. 1.
[10] Palladius et al., Kleine texte zum Alexanderroman, ed. by Friedrich Pfister,Heidelberg: C. Winter, 1910, p. 23.
[11] 斯特拉波就記載道,巴克特里亞國王在侵入賽里斯人的土地,見Strabo, TheGeography of Strabo,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orace Leonard Jones,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W. Heinemann, 1917-32, XI, 11, 1.
[12] 〔英〕裕爾撰,〔法〕考迪埃修訂:《東域紀程錄叢》,張緒山譯,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10頁。Cœdès, 注9所引文, pp. 22-26.
[13] 此前維吉爾的《田園詩》和賀拉斯的《希臘抒情詩集》分別提到了賽里斯人從樹上採羊毛和賽里斯國產的坐墊,參見Cœdès, 注9所引文, p. 2.
[14] 布爾努瓦引述老普林尼的論點,認爲西方古典時期的部分類似絲綢的織物實際上是愛琴海地區科斯島(Cos)的一種野蠶(Bombycine)提供的“野絲”,以及所謂“亞述蠶絲”(Bombyx Assyria)。參見〔法〕布爾努瓦:《絲綢之路》,耿昇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47—50頁。關於普林尼的論述,裕爾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包括對科斯和亞述蠶絲的考證,他指出普林尼著述引自亞里士多德,參見裕爾:注12所引文,165—167頁。
[15] 裕爾:注12所引文,165頁。
[16] 中國的班超在幾乎相同的時代向西出發,其副使甘英也到達了“西海”邊,卻最終沒有抵達大秦國(前97年,漢和帝永元九年),見《後漢書·西域傳》。對比梅斯和班超這位政府官員,可以看到商業利益的驅動更能夠提供足夠的動力完成使命,從而爲我們提供了更多的材料。
[17] 一作“石堡”,關於其稱呼的討論見楊共樂:《“絲綢之路”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與〈公元100年羅馬商團的中國之行〉一文作者商榷》,《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第109—110頁。
[18] 前者出自埃及的科斯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見Cœdès, 注9所引文, pp.132-135. 關於科斯馬斯及其著作請參見張緒山:《拜占庭作家科斯馬斯中國聞紀釋證》一文。後者出自塞奧菲拉克圖斯·西莫卡塔(Theophylactus Simocatta),見Cœdès, 注9所引文, pp. 138-141. 關於西莫卡塔及其著作請參見張緒山:《西摩卡塔所記中國歷史風俗事物考》,《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82—102頁。
[19] 《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第254頁。關於這一時期的中西交通問題,請參見Reichert, Folker E., Begegnungen mit China, Die Entdeckung Ostasiens im Mittelalter, Sigmaringen: Jan Thorbecke, 1992.
[20] 這一觀點由H.C.羅林森(Henry Rawlinson)提出,參見Rawlinson, H. C.,“Monograph on the Oxus”,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42 (1872),pp. 503-504. 在斯坦因第一次考古探險之後的著作《沙埋和闐廢墟記》中,他支持這一觀點(Stein, M. Aurel,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904, p. 71),但在其後的著作《古代和闐》(Ancient Khotan)中,他轉而接受“石塔”位於瓦赫什河谷的觀點,參見Yule, Henry,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rev. by Henri Cordier,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1915, vol I, Note II, p. 190, nt. 5。到第三次中亞探險之後,斯坦因最後確定達勞特-庫爾干作爲對“石塔”考察的最終結果,這在他的《亞洲腹地考古圖記》中得到了確切的表述,參見Stein, M. Aurel,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Carried Out and De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M. Indian Government, Oxford, Clarendon, 1928, vol II, pp.848-850.
[21] Stein, M. Aurel,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Vol. I, Oxford: Clarendon, 1907, p. 54.
[22] 裕爾:注12所引文,13、23頁。
[23] 1910年同時出版的戈岱司和黑爾曼的著作中分別綜述了此前的研究著作,请參 見 Cœdès, 注 9所 引 文 , VII-IX; Herrmann, Albert,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beiträge zur alten geographie Asiens, Berlin: Weidmann,1910, pp. 20-22.
[24] Richthofen, Ferdinand Freiherr vo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ol. I, 1877, p. 507。
[25] Cœdès, 注9所引文〔法〕X. 戈岱司編:《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耿昇譯,中華書局1987版,第12頁。
[26] 赫德遜,注5所引文,34—35頁。
[27] 分別見Gerini, G. E., Researches on Ptolemy's Geography of Eastern Asia (Further India and Indo-Malay Archipelago),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9與Berthelot,Andre, L'Asie ancienne centrale et sud-orientale d'après Ptolémée, Paris: Payot, 1930.
[28] Pelliot, Paul,“ « Šul » ou Sarag (?)”, Journal Asiatique, 211 (1927), pp. 138-141; 伯希和:《景教碑中敘利亞文之長安洛陽》,載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一卷一編,商務印書館1995版,第34—35頁;原載《通報》(T’oung Pao)1927—1928年合刊,第91-92頁。
[29] 卜弼德說見Boodberg, Peter A., “Sarag and Serica”, in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Boodberg, compiled by Alvin P. Coh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pp. 147-150;蒲立本說見Pulleyblank, Edwin G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Part II”, Asia Major, 9 (1973), pp. 206-265.
[30] 原文筆者未見:白鳥庫吉:『プトレマイオスに見えたる葱嶺通過路に就いて』,《蒙古學報》第二輯,昭和十六年(1941),第1—48頁。本文所援引之文章出自白鳥庫吉嗣後出版的《西域史研究》中:白鳥庫吉:『プトレマイオスに見えたる葱嶺通過路に就いて』,《西域史研究》下卷,岩波書店1981年版,第1-41頁。
[31] 在《絲綢之路》中提及的著作还包括:M. Ernest Pariset, Histoire de la soie,Paris, 1862; Tesnieres, Les noms de la soie, Alleche, 1942; A. Varron, The EarlyHistory of Silk, Les Cahiers Ciba, 1960。以上諸篇筆者均未引用。
[32] Janvier, Ives, “Rome et l’Orient lointain: le problème des Sères. Réexamen d’une question de géographie antique”, Ktema, 9 (1984), pp. 294-303.
[33] Haussig, H. W., “Die ältesten Nachrichten der griechischen und lateinischen Quellen über die Routen der Seidenstrasse nach Zentral- und Ostasien”, From Hecataeus to Al-Huwārizmi, ed. by J. Harmatta,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84,pp. 20-23. 與前面戈塞蘭的討論一樣,此處的解釋也不能接受。其原因在於,两人都試圖从居於絲綢之路中间的民族(印度人或北方遊牧民族)中尋找在絲綢之路東端的“賽里斯”词源,故不得其解。
[34] Rapin, Claude, “L’incompréhensible Asie centrale de la carte de Ptolémée.Propositions pour un décodag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2 (1998), p. 201-225.
[35] 關於其内容介紹請參見耿世民:《俄文新書多卷本〈古代和中古早期的新疆〉介紹》,引自歐亞學研究網: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890.html。
[36] 莫任南:《中國和歐洲的直接交往始於何時》,《中外關係史論叢》第一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版,第31頁。
[37] 林梅村:《公元100年羅馬商團的中國之行》,《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4期,第71—84頁。
[38] 楊共樂:注17所引文,第109—111頁。
[39] 邢義田:《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關係的再檢討》,《學術集林》第十二輯,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186頁。
[40]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XXXIV, 14.
[41] 張緒山:《三世紀以前希臘-羅馬世界與中國在歐亞草原之路上的交流》,《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第69—70頁;張緒山:《羅馬帝國沿海路向東方的探索》,《史學月刊》2001年第1期,第87—92頁。
[42] 張緒山:《關於“公元100年羅馬商團到達中國”問題的一點思考》,《世界歷史》2004年第2期,第111—114頁。
[43] 近年来有中國學者如華濤先生从新穎的角度討論此問题者,參見華濤:《“塞里絲誤解”的消除與葡萄牙人的歷史貢獻》,《文化雜誌》(澳門),49,2003年冬季刊,第1—18頁。
[44] Janvier, 注32所引文, pp. 261-262. 讓維埃採取了分以下四類傳統的方法,但在具體的材料選取上和筆者不同。
[45] 參見前注18。
[46] 關於彌南德的記載參見張緒山:《6—7世紀拜占庭帝國與西突厥汗國的交往》,《世界歷史》2002年第1期,第84—87頁。
[47] Virgil, Georgica, II, 121.
[48] Horace, Epodes, VIII, 15-16.
[49] Ovid, Amores, I, 14, 5-6.
[50] Propertius, Elegies, I, 14, 22.
[51] 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民族,與色雷斯人親緣較近。參見Herodotus, IV, pp. 93-97.
[52] 指黑海東北岸希臘化的博斯普魯斯王國。其主要城市是頓河河口的塔奈斯城(Tanais),是希臘世界最東北端的城市,在今烏克蘭羅斯托夫(Rostov)以西30公里。
[53] 此两句採戈岱司:注25所引文,第2—3頁。
[54] 利伯曼(Samuel Lieberman)考虑到這一問题,參見Lieberman, Samuel, “Who Were Pliny’s Blue-Eyed Chinese?”, Classical Philology, 52 (1957), pp. 174-175.
[55] Horace, Odes, I, 29, 7-10.
[56] Propertius, Elegies, IV, 8, 23.
[57] Chariton, De Chaerea et Callirrhoe, IV, 4. 據近年来考證,查理同的年代比賀拉斯稍晚,約爲公元2世紀初。
[58] Seneca, Phaedra, 389; Idem, Hercules Oetaeus, 414.
[59] Seneca, Thyestes, 378-379.
[60] Silius Italicus, Punica, VI, 1-4.
[61] 較典型的是公元前1世紀作家西西里的狄奥多魯斯(Diodorus Siculus)引用公元前3世紀初塞琉古王國駐印度大使麦加斯提尼(Megasthenes)的說法,參見Diodorus Siculus, Bibliotheca Historica, II, 2, 38.
[62] Statius, Silvae, I, 2, 122-123.
[63] Ibid, V, 1, 61.
[64] 指羅馬皇帝圖拉真(公元98—117年在位)。
[65] Juvenal, Satires, VI, 402-403.
[66] 這裏的“酥胸”是指克莉奥帕特拉。
[67] 與之相似的是,塞涅卡記載了推羅人的紫紅染料,見Seneca, Phaedra, pp. 387-389. 詳細的討論见布爾努瓦:注14所引文,第31—34頁。
[68] Cœdès, 注 9所引文 , XV.
[69] 據阿里安的記載,東征的亞歷山大見到印度的河流,覺得與尼羅河極爲相似,生長的植物也頗爲相似,於是便从神話中聯想到,尼羅河的源頭可能在印度,參見Arrian, Anabasis, VI, 1, 1-4.
[70] 富尼人(Phrynos或者Phrunos),可能是匈奴人的譯名。
[71] 其意義不詳。
[72] Janvier, 注32所引文, p. 265.
[73] 原文爲“Σηρικά ἔκ τινων φλοιῶν ξαινομένης βύςςου.” 此處採Richter, Gisela M. A.,“Silk in Greece”,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33 (1929), p. 30的英譯文譯出。對於βύςςου(byssus)的翻譯,洛布叢書的譯者認爲斯特拉波所指的就是蠶絲,祇是他把這種織物當作棉紗的一種,參見Strabo, Geography, VII, p. 34, nt. 23。此處不採耿昇先生的翻譯“足絲”,參見戈岱司:注25所引文,第6頁。
[74] 這一解釋来自 Hesychius, Γλῶςςαι: http://el.wikisource.org./wiki/Γλώςςαι/Α.
[75] Pomponius Mela, Chorography, III, 59.
[76] 例如Seneca, Letters to Lucilius, Ch. 15.
[77] 裕爾:注12所引文,第163頁。
[78] 除了上面两段之外,還包括對赛里斯人長壽可達140歲的記載,見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VII, 27. 根據老普林尼,這裏的說法来自伊西戈努斯(Isigonus of Nicaea,約生活在公元前1世紀,主要著作已遺失)。
[79]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XII, 17, 38; XIV, 22.
[80] 老普林尼提到了赛里斯人也出口皮貨,这一點在其他史料中没有提及。
[81] 裕爾:注12所引文,第164頁。此處可參考塔西佗《編年史》的記載:Tacitus,Annals, II, 33:“dесrеtumquе nе vаsа аurо sоlidа ministrаndis сibis fi еrеnt, ne vestis serica viros foedaret”. 賀嚴、高書文譯文作“(元老院)決定在私人的招待宴會上不许使用黄金製造的食具,男子的服装也不應該再用絲織品,因爲這會使他们墮落下去。”參見(古羅馬)塔西佗著:《羅馬帝國編年史》英漢對照全譯本,賀嚴、高書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版,第201頁。
[82]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VI, 53, 54.
[83] Cœdès, 注9所引文, XXVI. 戈岱司,注25所引文,第27頁。
[84] 裕爾:注12所引文,第22—23頁。
[85] Rufus Festus Avienus, Descriptio Orbis Terrarum, 769-771; 關於普里西安的版本請參見Cœdès, 注9所引文, pp. 72-73.
[86] Berggren, Lennart and Alexander Jones, Ptolemy's Geography: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hapt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p. 27.
[87] Rapin, 注34所引文, pp. 209-212.
[88] 這两個行星作爲希臘諸神是宙斯(Zeus)與克羅諾斯(Kronus),作爲羅馬諸神是朱庇特(Jupiter)與薩杜恩(Saturn)。
[89] 可能是从由海路訪問中國的羅馬商人處获得此消息,參見Yule, Henry,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rev. by Henri Cordier,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15, vol I, 18, p. 21. 張緒山:《羅馬帝國沿海路向東方的探索》,第90頁。
[90] 這與盧坎的說法,以及下面提到的赫利奥多魯斯和帕拉迪烏斯的記載一脈相承。
[91] 泰奥法内斯(Theophanes)的記載持此說法,參見Yule, 注89所引文, Note VII, p.204; Cœdès, 注 9所引文 , p. 152.
[92] 布爾努瓦:注14所引文,第72页。
[93] Moule, Arthur Christopher,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London: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30, p. 23. Denzey, Nicola ,“A new Star on the Horizon: Astral Christologies and Stellar Debates in Early Christian discourse”, in Scott Noegel, Joel Walker and Brannon Wheeler eds.,Prayer, Magic and the Stars in the Ancient and Late Antique World, 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09, nt. 3. 該文收入Spicilegium Syriacum. 這一版本中還收录了凱薩里烏斯的希臘文引文。
[94] 戈岱司的法譯文見Cœdès, 注9所引文, p. 79.
[95] 電子版本見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eusebius_pe_00_intro.htm/。
[96] 在法國教父米涅(Jacques-Paul Migne)編著的《希臘教父全集》(Patrologia Graeca)第38卷中收录,參見Cœdès, 注9所引文, pp. 89-90.
[97] 克力門傳奇是早期基督教著作中的一類布道與訓誡作品,記述的内容是作爲使徒保羅之友的克力門(教皇克力門一世)的成長經歷。其現存部分爲《克力門教諭》(Homilies)和《克力門認知》(Recognitions)两部分,二者的成書時間至今還是一個謎。但在現存的《認知》版本中,以4世紀下半葉魯菲努斯(Tyrannius Ru fi nus)的拉丁文譯本为最早。參見Clementines, in Catholic Encyclopedia of 1913.
[98] 戈岱司:注25所引文,第57頁,有改動。
[99] 戈岱司:注25所引文,第58頁,有改動。
[100] 希臘神話中代表金星的爱神阿芙羅蒂忒(Aphrodite)的別名叫啓普里斯(Cypris),得名於其傳說中的出生地塞浦路斯(Cyprus)。
[101] 據托勒密的說法,火星被賦予暴力衝突、戰爭、專制和殺死的意義(Ptolemy,Tetrabiblos, II. 8)。金星與火星相合即維納斯與瑪爾斯的結合,是羅馬宗教神話傳說中羅馬人繁衍生息的開始。
[102] Cœdès, 注 9所引文 , XXVI; pp. 89-91.
[103] Cœdès, 注 9所引文 , pp. 82-83.
[104] Cœdès, 注 9所引文 , XXVI, nt. 2.
[105] Cœdès, 注9所引文, p. 83: “nec apud Seras, nec apud Orientem audierunt Christianitatis sermonem”,中译文見戈岱司,注25所引文,第62頁。
[106] Yule, 注 89所引文 , 64, p. 102. Cœdès, 注9所引文 , pp.87-88.
[107] 正统基督教認爲,諾斯替教是“宣揚以知識而获拯救的異端”。參見Gnosticism,in Catholic Encyclopedia of 1913.
[108] Denzey, 注93所引文, pp. 209, 221.
[109] Rutilius Namatianus, De reditu suo, I, 68-88. 葉民認爲阿米安·馬爾塞林的思想與盧提利烏斯·那馬提安有相同之處,參見葉民:《最後的古典:阿米安和他筆下的晚期羅馬帝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99頁。
[110] Bardesanes and Bardesanites, in Catholic Encyclopedia of 1913.
[111] Cœdès, 注9所引文, p. 75. 戈岱司,注25所引文,第55頁。
[112]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 76。
[113] Janvier, 注32所引文, p. 274: “il y a eu deformation et non invention”。
[114] 《後漢書·西域傳》。
[115] 關於赫利奥多魯斯的年代,戈岱司將其定爲400年左右(Cœdès, 注9所引文, p.103);但晚近學者將其年代考訂爲3世紀中葉前後,參見Janvier, 注32所引文,p. 272。
[116] 赫利奧多魯斯还暗示,赛里斯人是養象的(Heliodorus, Aethiopica, IX, 17)。這又與弗洛魯斯的記載有聯繫。
[117] 希達斯佩斯是古典作品中一条印度河流的名稱,即流經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傑盧姆河(Jhelum)。亞歷山大遠征印度時最遠到達此河,在河岸边他認爲自己見到了尼羅河的源頭,參見前註71所引阿里安的記載。赫利奥多魯斯使用這個名字,顯示了他所引用的材料中印度和埃塞俄比亞的聯繫。
[118] Heliodorus, Aethiopica, X, 25.
[119] Janvier, 注32所引文, p. 273, nt. 60.
[120] 因此希臘文將紫紅色稱爲Phoinikobaphe,即“腓尼基人染的顏色”。推羅、西頓正是腓尼基人的城市。
[121] Ausonius, Technopaegnion, X, 24; XI, 6; XLV, 7. 值得一提的是,在XI, 6中,奥索尼烏斯描繪 :“穿長裝的賽里斯商人飞越了大海”(Jаm реlаgе vоlitаt mеrсаtоr vеsti fl uus Sеr),這是唯一的把賽里斯人和海路貿易聯繫起来的記載——虽然這很可能祇是詩人的想象而已。
[122] 轉引自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p. 102-103.
[123] 轉引自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 91.
[124] 其一爲僞卡利斯提尼(Pseudo-Callisthenes)的希臘文版本《論婆羅門》;另一个版本是聖安布羅斯(St. Ambrose)的拉丁文版本。參見Cœdès, 注9所引文,pp. 98-100.
[125] 僞卡利斯提尼版本如是記載。見Cœdès, 注9所引文, pp. 99-100。在聖安布羅斯的拉丁文版本中,同樣的商人被記錄爲“来自埃塞俄比亞和波斯的”,見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 101。
[126] Cœdès, 注9所引文, XXVII-XXVIII. 戈岱司,注25所引文,第28—29頁。
[127] 關於波伊廷格爾古地圖,請參見龔纓晏、鄔銀蘭、王知寒:《波伊廷格古地圖:條條大路通羅馬》,《地圖》2004年第2期,第37—40頁。
[128] Orosius, Historiarum adversus paganos, I, 2, 13-14.
[129] 奥羅修斯稱爲Ottorogorras,還記述說在其源頭有同名的城市。
[130] Orosius, Historiarum adversus paganos, I, 2, 44.
[131] Orosius, Historiarum adversus paganos, I, 2, 47.
[132] Isidore of Seville, Orig., IX, 2, 40.
[133] 奥羅修斯在此處的記載有所不同,在他的筆下,賽里斯人被置於希達斯佩斯河與印度河之间(相當于今天的巴基斯坦控制克什米爾與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請參看Orosius, Historiarum adversus paganos, III, 23, 11。
[134] 一種版本是842哩。在此筆者要感謝北京大學圖書館的無名讀者(一位相當嚴肃認真的先生)將戈岱司錯誤的譯文1442 milles上改出了一個9。戈岱司大概是出于粗心地將DCCCCXLII當作1442,而把下一頁另一版本的DCCCXLII當作1342。參見Cœdès, 注9所引文 , pp. 109-110。
[135] 然而在托勒密的著作中,泰里奥德斯是一个从恆河外印度航行到秦奈時所要經過的海灣的名字(VII, 3, 1-2)。可見托勒密所著與霍諾留斯的来源完全不同。
[136] 與之相似的是,漢文史料中對泰西的記載也在此時變得模糊和富於穿鑿附會起来。在3世紀魚豢所著的《魏略》(引自《三國志·魏志》裴松之註)之後,中國史書中關於“大秦”的記載便减少了許多,甚至不能獨立成爲单獨的章節。参见Leslie, D. D.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Roma: Bardi Editore, 1996, pp. 5-6。
[137] 例如,約爾達内斯《哥特人》(Getica)中對斯基泰一段的記載(其中包括對賽里斯的敘述,見於Cœdès, 注9所引文, p. 135),體現了對奥羅修斯的模仿和改編,參見Merrills, Andrew H.,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late antiqu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57-158。
[138] 貝凱、韓百詩、柔克義譯注:《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耿昇、何高濟譯,中華書局1985版,第254頁。參見華濤:注43所引文,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