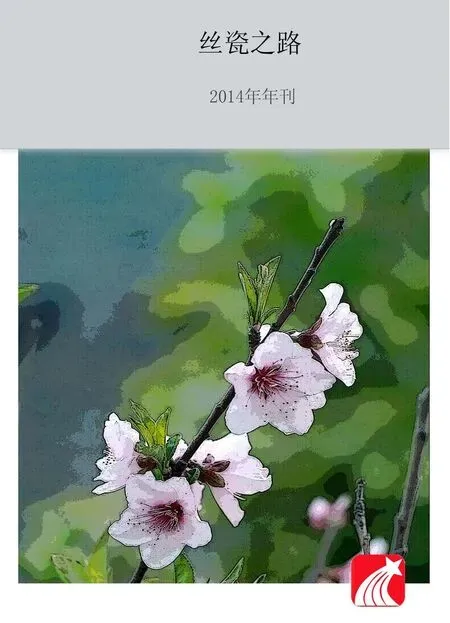附:迦膩色迦紀元諸說評介
附:迦膩色迦紀元諸說評介
在探討迦膩色迦年代問題、閱讀有關論文的過程中,我寫了一些劄記。這些劄記或長或短,有的還加上了按語。這裏發表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之所以考慮發表這些劄記,是因爲迦膩色迦年代這個問題比較特殊。有關的討論早就越出了迦膩色迦年代本身,甚至越出了貴霜史的範疇,涉及了古代中亞史和印度史的許多方面。可以說,一個多世紀關於迦膩色迦年代的討論極大地推動了古代中亞史和印度史的研究。因此,今日我們探討這個問題,似乎不應將視野局限於迦膩色迦年代本身,而應該盡可能廣泛地關注討論迦膩色迦年代涉及的各種問題。有鑒於此,同時也是爲了使有關迦膩色迦年代討論的內容更加充實,有必要逐一評介重要的年代說。遺憾的是我所見有限,祇能就手頭已有的材料進行這項工作,希望來日有機會繼續。
傳世的貴霜銘文表明,迦膩色迦及其繼承人曾連續使用某一紀元至少98年。一些學者認爲這一紀元由迦膩色迦所建,堪稱迦膩色迦紀元;該紀元之元年應即迦膩色迦即位之年。另一些學者則認爲,迦膩色迦及其繼承人採用了一個當時流行的紀元,也就是說該紀元的元年並不等於迦膩色迦即位之年。然而如果僅就迦膩色迦即位年代而言,諸說可大別爲公元前一世紀說、公元一世紀說,公元二世紀說和公元三世紀說四類。
屬於第一類的諸說中,以公元前58年說一度影響最大。屬於第二類的諸說中,以公元78年說擁有的支持者最多。屬於第三類的諸說中,值得推敲的主要是公元103年、110—115年、128年、135年、144年說,以及最新出現的公元127年說等。屬於第四類的則有248年說和278年說等。
在茲擬簡要評介諸說,諸說所引原始史料和各種論著的出處均見原文,不復加注。
一、公元前諸說
(一)公元前諸說
關於迦膩色迦紀元的絕對年代諸說中,公元前諸說是最早提出來的,可以說形形色色、林林總總。試舉幾種如下:
1. 公元前312年或公元前248年說
E. Thomas提出迦膩色迦紀元可能是始於公元前312年的塞琉古紀元(Seleucidian era),也可能是始於公元前248年的帕提亞紀元(Parthian era)說,祇是有關銘文的紀年分別省去了百位數3或2,實際上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應爲公元前9年或公元前45年。[1]
2. 公元前 57 年說
A. Cunningham主張迦膩色迦紀元爲始於公元前57年的超日紀元(Vikrama era)。[2]說者後來又改變看法,指爲塞琉古紀元。不過,有關銘文的紀年數省去了百位數4,故迦膩色迦即位之年已在公元一世紀。[3]
3. 公元前 50 年說
S. Lévi認爲迦膩色迦紀元應始於公元前50年。[4]
4. 公元前 322 年說
R. D. Banerji等人主張迦膩色迦紀元應爲始於公元前322年的孔雀紀元(Maurya era),當然也省去了紀年的百位數。[5]
5. 公元前 137—前 112 年說
G. Bühler主公元前 137—前 112 年之間說。[6]
6. 其他諸說
此外,尚有種種關於迦膩色迦紀元來歷的推測,如:J.Marshall以爲迦膩色迦紀元可能是由Taxila銅盤所見Moga創建的始於公元前95年的紀元。[7]R. D. Banerji以爲迦膩色迦紀元是Vonones創建的始於公元前100年的紀元。[8]K. P. Jayaswai以爲迦膩色迦紀元是一個大約始於公元前120年的紀元。[9]E. J. Rapson以爲迦膩色迦紀元是一個始於公元前150年的紀元。[10]W. W. Tarn以爲迦膩色迦紀元是一個大約始於公元前155年的紀元。[11]等等。
(二)對公元前58∕57年說的批評
在公元前諸說中,最有影響的是公元前58/57年說。自A.Cunningham提出迦膩色迦紀元爲始於公元前57年的超日紀元說以後,曾得到J. F. Fleet[12]、O. Franke[13]、H. Lüders[14]、J. Kennedy[15]、Barnett[16]等學者的支持。而隨着研究的進展,包括公元前58/57年說在內的公元前諸說業已無人信從,有關批評不少,茲介紹三種,以見一斑。
1. H. C. Raychaudhuri對公元前 58 年說的批評[17]
自J. Marshall在Taxila發掘以來,此說不復有人信從。銘文、錢幣以及玄奘的記載(《大唐西域記》卷一)都清楚地表明迦膩色迦的領土包括了乾陀羅,但按之《漢書·西域傳》,公元前一世紀後半葉佔領罽賓(ΚāрiŚа-Gаndhārа)的是陰末赴而不是貴霜。
迦膩色迦的金幣和羅馬的solidus的關係表明這位貴霜君主的治期不可能在Titus(公元79—81年在位)和Trajan(公元98—117年在位)之前。
2. D. C. Sircar對公元前58年說的批評[18]
(1)主公元前58年說者或置迦膩色迦組貴霜統治者於丘就卻、閻膏珍之前,這和中國史籍的記載是矛盾的。《後漢書·西域傳》明載,丘就卻是貴霜王朝的創始人,而閻膏珍則是第一個將其領土擴張到印度內地的貴霜統治者。
(2)幾乎沒有發現丘就卻的金幣,但閻膏珍和迦膩色迦發行了大量金幣。因此,如果置丘就卻於迦膩色迦和閻膏珍之間於理不合。
(3)早期印度的外族統治者,包括丘就卻和閻膏珍,頒行的錢幣是雙語銘文,正面用希臘文,反面用佉盧文。是迦膩色迦進行了貨幣改革──兩面都用希臘文,取代了較早的雙體錢。如果迦膩色迦在丘就卻和閻膏珍之前,則不符合貨幣發展的趨勢。
(4)迦膩色迦錢幣反面出現的神祗形形色色,而丘就卻、閻膏珍錢幣反面出現的神祗並無多樣性。這也表明丘就卻、閻膏珍在位時間早於迦膩色迦。Vasudeva與後者卻是一脈相承。
(5)Taxila的發掘也表明迦膩色迦組的貴霜統治者在位年代遲於丘就卻、閻膏珍,蓋前者的錢幣出土的地層較後者爲高。
(6)迦膩色迦金幣的式樣受到羅馬solidus的影響,可見他的年代不應早於Titus(公元79—81年在位)。
(7)年代爲41年的Ārā銘文所見迦膩色迦使用的稱號Kaïsara(Caesar)也表明迦膩色迦的年代大大遲於Augustus(死於公元14年)。
(8)晚期貴霜錢幣上所見得自薩珊的影響也表明迦膩色迦的即位不可能早到公元前58年。
3. B. Kumar對公元前58年說的批評[19]
Fleet公元前58年說的基本論據之一是玄奘關於迦膩色迦即位於佛涅盤後400年的記載。說者認爲佛滅於公元前483年,玄奘所謂400年不過約數,迦膩色迦其實即位於佛滅後425年即公元前58年。也就是說,迦膩色迦、Huvika和Vāsudevа的治期在丘就卻和閻膏珍之前。
Kennedy則根據他對古希臘文化的研究定迦膩色迦紀元在公元前一世紀。他也引用了若干中國記載支持其說。
(1)迦膩色迦的錢幣有希臘銘文,因此使用者一定懂希臘語。希臘語作爲一種日常生活用語在公元一世紀末以後不久在Euphrates以東(北美索不達米亞除外)地區部分消失,此後不可能單獨存在於旁遮普。因此,迦膩色迦的治期不可能在公元100年之後。
(2)迦膩色迦自波斯灣的商人處藉得希臘字母,他草書的商業手稿來源也相同。直到迦膩色迦的時代,安色爾(uncial)字體僅被用於希臘錢銘。迦膩色迦開始亦用安色爾字體,不久就變爲美麗的草體,而他的繼承者僅僅使用這一字體,則是由商業需要決定的。而公元一世紀的兩位Elam王恰好也做了迦膩色迦所做的事。因此,他的錢幣必定打鑄於公元前60年和公元40年之間。
(3)Sаmуuktаgāmа載公元五至六世紀時有四國同時統治:北方爲 Yаvаnаs(即喀布爾),南面爲аkа(即印度-斯基泰),西面爲 Pаhlаvа(即 Asia 和阿拉科西亞),東面是 Tusharas。因此,當公元前一世紀希臘人統治喀布爾時,在旁遮普和馬土臘必定有一個Tushara即貴霜王國。
(4)《後漢書》未提及迦膩色迦,說明其事蹟在公元25年和公元前100或前90年之間。而稱閻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意指貴霜第二次滅天竺(奪取旁遮普)。
然而,上說皆不可從。
一則,有關迦膩色迦治期去佛滅之年諸書所傳不同,不能以爲證據。例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和藏文《世親傳》(Vinaya)均作“涅槃後四百年”。漢文《婆藪槃豆法師傳》則作“五百年”。《大唐西域記》(卷二)亦作“五百年”。《洛陽伽藍記》(卷五)作“二百年”,一本作“三百年”。和闐文書作“一百年”。《雜寶藏經》卷七作“七百年”。
二則,貴霜錢銘用希臘文僅能表明貴霜諸王的愛好,不能說明什麽問題。Surkh Kotal銘文的發現表明,在阿富汗和貴霜帝國西北部確曾流行希臘文。由於該地區希臘人的存在,它必定在公元100年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流行。
三則,迦膩色迦使用的希臘文草體範圍太廣,不足以成爲判斷精確年代的依據。
四則,Samyuktagāma的作者並沒有對四個地區作出具體說明,也沒有提到這種形勢存在的時期,因而不足爲憑。
五則,閻膏珍是在天竺被外族如塞種之類征服之後再一次征服印度的,這是“復滅天竺”的真正意義。[20]
六則,Fleet、Franke輩置迦膩色迦組於Kadphises組之前的觀點業已爲考古發掘和錢幣的證據否定。Kadphises II和迦膩色迦的錢幣在許多處一起出土。兩者的錢幣上有相同的四叉花押,這種花押卻不見於丘就卻的錢幣;閻膏珍和迦膩色迦的錢幣重量一致,正面設計也顯示出有密切的關係。閻膏珍和迦膩色迦的聯繫尤其可以從Taxila的發掘看出。
J. Marshall在Taxila地區Chir萃堵波建築物中發現的錢幣有4個地層:最上層是Vāsudeva和後貴霜的錢幣,第二層是Kanika、Huvika和Vāsudeva的錢幣,第三層是丘就卻和閻膏珍的錢幣,第四層是akas和Pahlavas的錢幣。
在Sirkap城發現了同樣的分層現象,這主要就第三、四和最早的一層而言。不過,由於該城在第一和第二階段的建築物建立起來以前被廢棄,一層沒有迦膩色迦、Huvika、Vāsudeva的錢幣,祇有數千枚丘就卻、閻膏珍、塞種、Pahlava和希臘諸王的錢幣。
以上證據表明閻膏珍和迦膩色迦在時間上是非常接近的,後者直接繼承前者。既然《後漢書·西域傳》稱閻膏珍是丘就卻之子,如果迦膩色迦組在時間上早於丘就卻,則他們的錢幣應與丘就卻在一起發現,而閻膏珍的錢幣不應和迦膩色迦的一起發現,但事實正好相反。
七則,丘就卻幾乎沒有打鑄金幣,但閻膏珍和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有大量的金幣。這也說明丘就卻的治期早於閻膏珍和迦膩色迦。
八則,丘就卻是第一個貴霜王,而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屬於同一王朝,因爲他們在自己的錢幣上都稱“Koshano”。因此,後者必定在丘就卻、閻膏珍之後。
九則,印度早期外族統治者的錢銘使用兩種文字,正面希臘文,反面佉盧文,丘就卻、閻膏珍的錢銘便是如此,而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僅用希臘文。
二、公元一世紀諸說
公元一世紀諸說中最有影響的是公元78年說。此外,還有43年說[21]、80年說[22]、90年說[23]等等。[24]本文僅介紹公元78年說。
(一)公元78年說
最先提出78年說的是J. Fergusson[25]。較早的支持者有H.Oldenberg[26]等。當時佔有的資料有限,研究還停留在起步階段。H.Oldenberg後來改而支援A. M. Boyer說。[27]說者並沒有舉出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78年的絕對證據,無非是試圖說明公元78年說較公元前58年說合理而已。但此後,嚮應者日衆,特別是印度學者。[28]直至1960年倫敦召開的迦膩色迦年代專題討論會上,此說仍佔有很大優勢。[29]以下選擇若干78年說評介之。
1. H. C. Raychaudhuri的公元78年說[30]
說者扼要批判了公元前58年說,公元二世紀諸說(125年說和144年說)以及公元248年說等,以支持78年說。對於公元78年說,說者似未作正面論證,祇是反駁了Jouveau-Dubreuil對此說提出的若干責難。
(1)如果承認丘就卻公元50年在位,又承認迦膩色迦在公元78年即位建元,則丘就卻餘下的治期加上閻膏珍的全部治期總共不過28年,未免太短。
駁議:丘就卻去位時已八十餘歲,故閻膏珍即位時年紀必定不輕。即使公元50年丘就卻在位,由於閻膏珍在位時間不會太長,不能認爲28年的時間太短。
今案:駁議未安。丘就卻晚年得子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閻膏珍即位時年紀不輕未必在位時間便短。何況,事實上丘就卻之後,還有兩位貴霜君主。[31]
(2)年代136年的Taxila銀冊銘文,按所謂Vikrama紀元計算,實際年代爲公元78/79年。該銘文提到的貴霜君主可能便是丘就卻,卻絕無可能是迦膩色迦。
駁議:年代爲136年的Taxila銀冊銘文提到的貴霜君主採用稱號之一爲devaputra。這不是Kadphises組貴霜君主,而是迦膩色迦組貴霜君主的特徵。因而這一銘文的發現未必能動搖78年說。
今案:此說未安。一則,年代爲136年的Taxila銀冊銘文上提到的貴霜君主,由於姓名被省略,祇可能是丘就卻。丘就卻是貴霜王朝的創始人,他在位時是獨一無二的貴霜君主,省略姓名不致引起誤解。二則,devaputra一號即使不見於丘就卻和閻膏珍的其他銘文和錢幣,也不能因此斷定這一稱號與所謂“Kadphises組”貴霜君主無關。因爲丘就卻完全可能是在佔領Taxila以後纔自稱davaputra(這一稱號後來被迦膩色迦組的貴霜統治所者承襲)。至於閻膏珍不用這一稱號,則完全可以認爲是有關銘文或錢幣迄今尚未發現。何況在迦膩色迦以前,devaputra一號已見諸Kuyula Kara Kaphsa之錢幣。Kuyula Kara Kaphsa應即丘就卻。即使兩者並非一人,也不能否定前者屬於所謂“Kadphises組”,也就是說不能否定年代爲136年的Taxila銀冊銘文提到的貴霜君主屬於所謂“Kadphises組”。既然公元78/79年在位的貴霜君主屬於所謂“Kadphises組”,即使不提年代爲184(或187)年的Khalatse銘文,也不能認爲迦膩色迦即位建元於公元78年。更何況,事實上所謂“Kadphises組”和“迦膩色迦組”一脈相承,其稱號之間存在繼承關係不足爲奇。
(3)漢、藏有關文獻資料的研究表明,迦膩色迦於公元二世紀在位。
駁議:公元二世紀在位的迦膩色迦可以認爲是見諸年代爲41年的Ārā銘文的迦膩色迦。按照塞種紀元,他於公元119年在位。《三國志》所載公元230年朝魏的貴霜王波調則可以認爲是Vāsudeva二世。
今案 :藏文《于闐國授記》(Li yul lun-bstan-pa)[32]以及漢譯佛經有關記載均未涉及迦膩色迦的年代,很難據以作出推斷。但有一點似可肯定,這些資料提到的迦膩色迦是一世的可能性遠遠大於僅留下一篇Ārā銘文的二世,雖然後一種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至於《三國志·魏書·明帝紀》所見大月氏即貴霜王波調究竟是Vāsudeva一世還是二世亦無直接證據。事蹟大致截止明帝(公元227-239年)的《魏略·西戎傳》稱:“罽賓國(Gandhāra和Taxila)、大夏國(Tukharestan)、高附國(Paropamisadae)、天竺國(印度河流域)皆並屬大月氏。”這似乎表明當時貴霜國力尚屬強盛,因而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朝魏的波調是Vāsudeva二世的可能性不大。說者卻以爲“皆並屬大月氏”一句僅僅表示罽賓等地在名義上承認Vāsudeva二世的宗主權。質言之,《魏略·西戎傳》的這則記載未必表明明帝時貴霜尚能控制上述各地。然而,這種解釋顯然是頗爲勉強的。蓋《魏略·西戎傳》又稱,車離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今月氏役稅之”。“車離”應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東離”。該國臣服貴霜事既見諸《後漢書·西域傳》,可見其事最早可能發生在閻膏珍時期。《魏略》所謂“今月氏役稅之”應指明帝時的情況。貴霜既然能役稅其東南三千餘里的車離國,對罽賓、大夏等地的統治可見並不是名義上的。質言之,遣使曹魏明帝的貴霜王波調更可能是Vāsudeva一世而非二世。
(4)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的銘文和西印度州長用塞種紀元紀年的銘文表示日期的方式不同。
駁議:並非所有用迦膩色迦紀元紀年的銘文表示日期的方式都相同。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的佉盧銘文,表示日期的方式和安息-塞種人的銘文相同;但在他們的婆羅謎銘文中,常常採用古印度的方式。既然不能因此認爲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在他們的佉盧銘文和婆羅謎銘文中使用的不是同一个紀元,也就沒有理由否定他們在西印度的州長們因地制宜地採用第三種方式。
今案:雖然使用同一紀元時可能因各地習俗不同而採用不同的表示日期的方式,但這並不排斥表示日期的方式因所用紀元不同而不同的可能性。也就是說,表示日期的方式未必和採用的紀元完全無關。雖然不能僅僅因爲銘文表示日期的方式不同,斷定西印度塞種州長和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所用紀元不同,但在其他更積極的證據存在的前提下,表示日期方式的不同仍不失爲所用紀元不同的證據。
(5)如果迦膩色迦即位建元於公元78年,他應該就是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遣副王謝率軍七萬東逾葱嶺進攻班超的月氏王,也就是說他和班超是同時代人。果然如此,則中國史家不應該不提到他的名字。
駁議:如果與班超同時代的貴霜王是閻膏珍,《後漢書·班超傳》沒有提到他的名字纔真正不可思議,因爲從《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可以得知,當時中國人是知道閻膏珍的。又,據《付法藏因緣經》(卷五),迦膩色迦晚年曾自稱:“我征三海,悉已歸化,唯有北海,未來降服。”類似記載亦見諸《雜寶藏經》(卷六)。迦膩色迦未能降服的地區顯然是指葱嶺以東的塔里木盆地。迦膩色迦因未能征服塔里木盆地而遺憾,說明《後漢書·班超傳》所載,和帝永元二年(90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逾葱嶺東進、旋被班超擊退一事發生在迦膩色迦在位時期,派遣副王謝的月氏即貴霜王正是迦膩色迦。由此可見迦膩色迦是班超的同時代人。另一方面,《後漢書·西域傳》記載閻膏珍事蹟時未及遣副王謝一事,亦見公元90年在位者並非閻膏珍。
今案:其說非是。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後漢書》完全沒有提到迦膩色迦。不僅《班超傳》沒有提到,《西域傳》也沒有提到。而如所周知,《後漢書·西域傳》設有貴霜專條,敍述了丘就卻和閻膏珍的主要經歷,而該傳主要依據安帝末(公元125年)班勇所記。果然迦膩色迦即位建元於公元78年,其事蹟不應不見載於該傳。《後漢書·班超傳》沒有提到閻膏珍,是因爲該傳記述之重點是班超與貴霜副王謝之間的戰爭,未必意味着班超不知當時在位的貴霜王名。正因爲派遣副王謝的貴霜王名及其主要事迹已見載於《後漢書·西域傳》,《後漢書·班超傳》纔可以略而不提。同理,閻膏珍指遣其副王謝東犯一事既已詳述於《後漢書·班超傳》,《後漢書·西域傳》自無重復之必要。反之,如果公元90年在位的貴霜君主是迦膩色迦,其事迹既不見載於《後漢書·西域傳》,在《後漢書·班超傳》中敍述他求婚以及指遣其副王東犯諸事時不提他的名字纔是不可理解的。
2. S. Chattopadhyaya 的公元 78 年說[33]
年代爲134年的Kalawan銘文表明公元76年時Taxila不在貴霜治下,而年代爲136年的Taxila銀冊銘文表明公元78/79年時貴霜已經統治該地。後一篇銘文對貴霜統治者的稱呼爲maharajasa rajatirajasa devaputrasa Khusanasa。稱號 devaputra 是 Kanika 組貴霜統治者特有的,而不見用於Kadphise組。既然Wima的統治結束於公元78年以前,而Kanika在這一年即位建元,這一篇使用Vikrama紀元的銘文就不能歸屬於Kanika。既然使用Vikrama紀元表示Taxila銀冊銘文不屬於Kanika組統治者,而Devaputra的使用又表明這篇銘文不屬於Kadphises組,就祇能假定這篇銘文是屬於一位既不屬於Kanika組,又不屬於Kadphises組的貴霜王的。由此可見:
(1)正如Panjtar銘文所表明,公元64年前貴霜人征服了印度河以西地區。
(2)閻膏珍作爲儲君時可能已征服了Taxila,他繼承王位後又征服了印度內地,並任命副王統治各地。其治期結束於公元78年以前。由於丘就卻死時已八十餘歲,閻膏珍的治期必定很短。
(3)約公元76年,貴霜帝國發生了某種麻煩:Taxila獨立,其地不是在當地土著統治者治下,就是在閻膏珍的一位副王的治下。
(4)公元78/79年Taxila在一位既不屬於Kadphises組,又不屬於Kanika組的貴霜統治者治下。這位統治者顯然是閻膏珍的副王之一,他宣告獨立,但又不敢在記錄上提到自己的名字,也許就是頒發Soter Megas錢幣的無名王。在一枚金幣上,錢銘之爲Basileus Basilion Stoer Megas。據Taxila銀冊銘文類推,這位副王在獨立後同樣使用Soter Megas這一稱號而不著其名,這表明在公元79年閻膏珍可能還活着。否則這位副王可以在記錄上提到自己的名字。
今案:此說未安。即使Panjtar銘文[34]表明貴霜在公元64年征服了印度河以西地區,也不能推論公元64年以前貴霜已經統治了Taxila。所謂閻膏珍爲儲君時已征服Taxila云云純屬臆測。正因爲如此,Kalawan銘文[35]沒有提到貴霜也不表明這一年貴霜出現內亂、Taxila地區得而復失,而至多說明截止公元64年貴霜尚未征服Taxila。年代爲136年的Taxila銀冊銘文[36]則表明貴霜對Taxila的征服發生在公元64至公元76年之間。
年代爲136年的Taxila銘文不提統治者之名表明當時在位的統治者是丘就卻,因爲他是獨一無二的貴霜君主,不著姓名不至誤解。果如說者所言,該銘文提到的貴霜統治者是一位鬧獨立的副王,就很難解釋這位敢於使用最高級的稱號的前副王,何以不敢印上自己的名字。至於devaputra一號,顯然是丘就卻在晚年使用的,不見於以前的貴霜銘文未必表明使用這一稱號的貴霜統治者不屬所謂Kadphises組。銘文使用Vikrama紀元不僅表示該銘文提及的貴霜統治者不屬所謂Kanika組,而且表明Kanika不可能即位建元於公元78年。既然Taxila銀冊銘文表明丘就卻依舊在位,則公元78年應爲丘就卻去位年代的上限,這一年也是其子繼位年代的上限。僅僅根據銘文不著王名這一點就斷定該銘文所提到的貴霜統治者就是錢幣所見Soter Megas顯然未安。
閻膏珍的Kalatse銘文表明他去位年代的上限是公元129年。《後漢書·西域傳》沒有提到閻膏珍之死,也暗示公元125年他依舊在位。以往研究者懷疑他如此長的在位時期不無道理,但現在知道閻膏珍之前另有一位貴霜王,這個疑問就不存在了。
3. J. E. Van Lohuizen-de Leeuw的公元78年說[37]
(1) 中國證據
a.據中國正史,丘就卻和閻膏珍的治期不可能超過100年,既然丘就卻即位於公元前一世紀的最後25年之內,迦膩色迦繼閻膏珍即位必定在公元一世紀最後25年之內。
b.明帝遣使印度求法到使臣歸國應在公元61—75年間。時印度無疑在月氏治下,在位者不是迦膩色迦而是閻膏珍,否則佛教徒的文獻不會不提及這位護法之王。
c.《後漢書》所載公元90年班超擊退的月氏副王謝當係迦膩色迦所遣,蓋班超熟知丘就卻和閻膏珍,理應提及貴霜王名。另外,自玄奘《大唐西域記》等記載,可知迦膩色迦有東逾葱嶺未達目的之憾。
(2)銘文的證據:
在老紀元200年(Dewai銘文)和318年(Loriyan Tangai)之間,沒有發現用這一紀元紀年的銘文,而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的銘文所包涵的時期恰好填補了這一間隙。
(3)錢幣的證據
閻膏珍及其以後的貴霜諸王均打鑄了大量金幣。其重量標準與羅馬的aureus(124g)接近。後者是在奧古斯特(Augustus,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位)制定的。閻膏珍及其以後的貴霜諸王採取這一標準打鑄金幣,說明在此期間有羅馬的錢幣湧入。
(4)考古學證據
Marshall調查的Taxila萃堵波和Sirkap遺址的層次提供了充分的證據。Marshall根據風格和材料等判斷建築物的年代,不能沒有疑問。但他把迦膩色迦、Huvika和Vāsudeva看作丘就卻和閻膏珍的後裔是可以接受的,因爲還有其他事實支持。
(5)天文學的證據
(6)古文書學的證據
佉盧文字體可分爲四個時期:a.公元前四至前三世紀孔雀王朝時期;b.公元前二至前一世紀的變體,見於印度希臘諸王的錢幣;c.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一世紀,塞種時期的變體,見諸Patika的Taxila銅板和馬土臘州長āsa的獅柱,以及塞種和貴霜諸王的錢幣;d.公元一至二世紀的草體,以Gondopharnes的Takht-i-Bahi銘文開始,而在Vāsika和Huvika的銘文上得到充分發展。因此,迦膩色迦應被置於公元一世紀。而馬土臘州長銘文的字體和迦膩色迦早年銘文的字體驚人的相似表明兩者幾乎不可能相隔一個世紀以上。如果前者被置於公元前一世紀,迦膩色迦即位之年則在公元一世紀。
今案:說者對中國史料的理解是難以接受的。考古發現顯然無助於推斷精確的年代,錢幣和古文書學的證據均無絕對價值。至於所謂天文學證據,Wijk按照Siddhāntas計算,能夠滿足有關條件者不僅有公元79年,公元117年、公元128—129年或公元134年也一樣能夠滿足。[39]
此外,說者還提出新的證據[40]:
約公元180—200年,Āndhra派雕塑中突然出現佛像。既然Amarāvatī並不存在像馬土臘那樣就佛陀雕塑進行各種嘗試的階段,可見Āndhra派佛陀雕像係他處傳入。鑒於馬土臘作爲藝術中心産生的巨大影響,Āndhra派佛陀雕塑最可能是摹自馬土臘。
有趣的是,即使公元二世紀末最早的Āndhradeśa的佛雕,也已具有迦膩色迦紀元第110年以降馬土臘佛雕的風格特徵。因此,似難認爲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會落在公元二世紀某時或更遲。這就是說,祇有肯定迦膩色迦紀元之元年在公元一世紀後半葉,確切地說在公元80年左右,纔能與藝術史的事實相符。
今案:此說亦有未安。
一則,風格的影響是雙向的,未必馬土臘影響Amarāvatī。後者亦可能影響前者。因此,公元二世紀末Āndhradeśa佛雕具有與迦膩色迦紀元110年以降馬土臘佛雕相同之特徵,未必迦膩色迦紀元的110年早於公元二世紀末。
二則,Amarāvatī的佛雕與馬土臘的雕像的風格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其實很難說誰影響誰。Amarāvatī突然出現佛雕並不能說明它的佛雕一定來自别處,特別是來自馬土臘。另外,Amarāvatī並沒有一個像馬土臘那樣嘗試各種方式佛雕的階段,也不表明其佛雕一定摹自馬土臘,蓋其他題材的雕塑的成熟自可省去佛雕的嘗試階段。
三則,說者關於某些佛雕銘文的紀年數乃省去了百位數的假定尚未得到最後證實。
4. A. L. Basham的公元78年說[41]
(1)年代爲公元41年的Ārā銘文所見迦膩色迦的稱號Kaisar(Caesar),表明當時羅馬皇帝的聲譽在貴霜朝廷中非常強烈,這一稱號此後再未被貴霜王使用過。因此,不妨推斷,這一稱號被貴霜人採用之時,正值羅馬人對帕提亞作戰取得某次重大勝利。而且在這之後不久,羅馬在東方的勢力日益衰落,在貴霜朝廷的影響減弱。如果定迦膩色迦即位之年爲公元144年,則Kaisar這一稱號將會在Commodus治期被採用,Commodus是Marcus Aurelius的繼承人,他並無特別的治蹟可言。
若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78年、128年或144年,則Ārā銘文的年代爲119年、169年或185年。而在公元二世紀,羅馬與帕提亞的大戰有三次。第一次是在Trajan治期(公元113—117年),第二次是在Marcus Aurelius治期(公元162—165年),第三次是在Septimius Severus治期(公元195—202年)。第三次年代太遲,可置勿論。第一次的戰果是非常輝煌的,結果是羅馬征服了亞美尼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巴比侖。但是,這些地區很快就在Trajan的繼位者Hadrian手中丟失。第二次雖然略爲遜色,但其結果是吞併了西北美索不達米亞。因此,採用這一稱號最可能的年代是公元119年,亦即Trajan時代,而在Hadrian時代又放棄。公元128年之所以可能性較小,是因爲第二次的戰果既不如第一次輝煌又不如第一次短暫。質言之,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78年。
今案:此說未安。羅馬對印度的影響並非一事一時。貴霜君主採用Kaisar一號,和羅馬與帕提亞關係之變遷並無必然聯繫。
(2)元年爲公元78年的紀元曾在公元130年以降爲古吉拉特和馬爾瓦的“西部州長們”所採用。同一紀元亦曾被憍賞彌Kau āmbī,或 Kosabiya的Magha諸王所採用。而在尼泊爾使用的所謂Licchavi紀元其實也是這個元年爲78年的紀元。蘇聯考古學家在中亞發現的公元三世紀的文書,似乎也是按照這同一個紀元紀年的。因而,公元78年爲元年的這個紀元(後來被稱爲塞種紀元)早期的使用範圍十分巨大。這個範圍的中心在旁遮普的某處或當時稱爲乾陀羅的地區。但按照那些認爲迦膩色迦紀元並不是塞種紀元的學者的看法,並沒有證據表明古代旁遮普和乾陀羅使用過塞種紀元。該紀元的使用範圍自烏賈因經恒河流域、尼泊爾伸展至中亞,而在旁遮普完全不受影響似乎是極不可能的。明顯的結論應該是這個紀元是由一個強大的政權推廣的,這一政權於政治、文化兩方面發揮影響於上述較早使用這個紀元的地區。唯一能做到這一點的是貴霜政權。
今案:說者的意見不無合理性,祇是過於絕對。塞種紀元使用範圍廣大固然有可能是一個強權(譬如貴霜)推廣的結果,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可能性。質言之,塞種紀元使用範圍廣大也可能與塞種人的活動範圍廣大有關。在說者所描述的地域範圍內,無疑遍佈塞種的部落,而由於文化淵源的相同或接近,促使各地的塞人採用了同一個紀元。雖然貴霜人也與塞種有着難分難解的淵源,但貴霜一開始並未採用一個與塞種有關的紀元,因而即使迦膩色迦在公元78年即位,也未必創建一個與塞種有關的紀元。而已經站穩腳跟的迦膩色迦政權,不採用業已流行的塞種紀元,另創一個紀元或採用其他紀元的可能性同樣是存在的。
Nahapāna的兩篇年代分別爲41和46的銘文實際年代應爲公元56和公元61年。蓋Nahapāna和Andhra統治者Gautamīputra śrī Sātakari是同時代人,則不妨認爲公元61年是Gautamīputra第一年。提到Cana和Rudradāman的銘文年代爲塞種紀元第52年(公元130年)。
大州長śodāsa的年代爲72年的Āmohinī Tablet中也許採用了另一個紀元。從馬土臘獅柱銘文可知śoāsa無疑就是大州長Patika同時代人。雖然馬土臘獅柱銘文沒有年代,但是在年代爲78年的Taxila銅板銘文中,這同一個Patika被稱爲州長Liaka Kusulaka之
5. P. H. L. Eggermont的公元78年說之一[42]
說者根據印度宗教文獻,特別是中古耆那教歷史、往世書以及佛教傳說的片斷,得出結論:公元15年是塞種入侵印度之年。
既然Nahapāna在他的銘文上不採用塞種紀元,便應使用這一元年爲公元15年的紀元。在Kaharāta滅亡之後控制Mālwā、古吉拉特的Rudradāman和Kārdamaka家族的州長們纔使用元年爲78年的塞種紀元。子,他們都屬於Kaharāta家族。如果年代爲78年的Taxila銅板和年代爲72年的Āmohinī Tablet採用的紀元都是上述以公元15年爲元年紀元,則其年代分別爲公元93和公元87年。
值得注意的是Taxila銅板銘文提到的Liaka Kusulaka可與見諸迦膩色迦紀元第11年Zeda銘文的州長Liaka勘同。這說明Zeda銘文所用迦膩色迦紀元應即塞種紀元。因爲祇有迦膩色迦元年爲公元78年,因而銘文年代爲公元89年,纔與Taxila銘文的年代(公元93年)相符合。
另一種可能性是Āmohinī Tablet和Taxila銅板所採用的紀元都是Vikrama紀元(公元前58年)。這兩者的年代分別是公元15和公元21年。既然公元15年是塞種入侵印度之年,則Maga應是入侵者的領袖,而Kaharāta家族在印度佔優勢始於這次入侵。
今案:其說未安。且不說說者所依據的僅僅是宗教傳說,據以得出的結論可靠性不高,即使我們相信公元15年是塞種入侵印度之年,仍不可能據以證明迦膩色迦紀元便是78年的塞種紀元,蓋與其他已知事實相牴牾。
事實上,年代爲78年的Taxila銅板銘文早於馬土臘獅柱銘文,後者又早於年代爲 72年的 Āmohinī Tablet。[43]因此,Taxila銅板和Āmohinī Tablet採用的紀元絕不是同一個。迦膩色迦不可能是塞種紀元的創始人。
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必定比公元78年晚得多,甚至晚於年代爲199年的馬土臘銘文。塞钟在馬土臘至少存在至公元15年。最早提到Maharayasa Guaasa的是年代爲122年(即公元65年)的Panjtar銘文,這表明塞種在馬土臘的統治結束於此後不久。幸存的塞種最可能逃往古吉拉特,奠定了西部州長政權的基礎,於是開始了公元78年的塞種紀元。[44]
因此,可以認爲Āmohinī Tablet的紀元是公元前58年的超日紀元,其實際年份爲公元14/15年,而Taxila銅板銘文所見Liaka與Zeda銘文所見Liaka並不是同一個人。質言之,無從證明迦膩色迦紀元是塞種紀元。
6. P. H. L. Eggermont的公元78年說之二[45]
佛涅槃前40年預言佛法會持續500年,這意味着佛法結束於460 p. B. m.(post Buddham mortuum)。錫蘭的上座部(Theravādins)在他們的年代記 Dīpavasa和 Mahāvasa中說,在460 p. B. m.,僧伽(Sagha)中發生了糾紛,爲防止其教衰落,Theras將佛法寫在書中,而在此之前佛法一直是口頭流傳的。
北印度的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s)非常清楚這一傳說。據云:在迦膩色迦治世,僧伽中諸異議部執不同,以致該王試圖停止糾紛,舉行結集爲三藏作注。
說一切有部指佛滅之年爲公元前383年。如果說一切有部和上座部擁有這一共同的傳說,極可能說一切有部認爲佛法沒落於佛滅後460年,這一年便是僧伽中發生糾紛並寫定三藏之年。按天文學推算等於公元前382年。迦膩色迦結集之年爲460-382(即公元78年),這正是塞種紀元之元年。
由此可見,塞種紀元是真正的佛教徒和印度傳說,其根據是公元前383年的說一切有部紀元。按照這一老紀元,460 p. B. m.相當於公元78年。這是歷史的轉捩點,法輪轉動的最初五百年過去,一個新時期於是開始。
上述研究表明迦膩色迦的歷史與公元78年迦濕彌羅說一切有部的結集密切有關。可是這未必意味着迦膩色迦在78年即位。這結集也許是在他即位若干年以後舉行的。認爲迦膩色迦要等到460 p. B.m.說一切有部需要一個國王來停止宗教的衰落時纔挺身而,出似乎是相當荒唐的。儘管如此,這一看法表面上是唯一合乎邏輯的。因爲此傳說使結集發生在佛滅後460年而不是500年,這有力地說明迦膩色迦登基在公元78年。
蓋據最古老的佛教傳說,佛法將在佛的大無餘涅槃以後500年沒落,這意味着指稱同一事件發生於佛涅槃後460年乃是第二手的。若按說一切有部,佛陀大無餘涅槃(Mahāpariirvāa)在公元前383年,則佛法的沒落之年應爲公元118年(公元500—382年)。可是,在公元78年迦膩色迦即位,該王對於說一切有部的重要性不亞於阿育王之於古佛教。這使說一切有部不得不修改其教義中的年代說。也就是說,將原來關於佛法沒落將出現在佛滅後500年的傳說改爲佛滅後460年(佛陀被說成是在他死前40年發表了這樣的預言),使之符合迦膩色迦即位之年。迦膩色迦即位之年舉行的第四次結集——迦濕彌羅結集阻止了佛法的沒落,是年成了歷史的轉折點。
今案:其說未安。
一則,佛法沒落於佛滅後460年之說見於錫蘭上座部之年代記Dipavadins和Mahavamsa,不見於北印度說一切有部的記述。
二則,北印度說一切有部所述迦濕彌羅結集提及迦膩色迦王即位之年並不作佛滅後460年(《大唐西域記》卷三作“第四百年”;《大毘婆沙論》卷二〇〇同[46]),知說一切有部所傳與錫蘭上座部不盡相同,不可牽扯到一處。即使說一切有部確有修改舊說之事,亦未必與迦膩色迦即位或結集有關。佛陀畢竟祇是預言佛法沒落於佛滅後460年,並未說是年便是佛法轉盛之年。
三則,結集之年代未有定說,佛涅槃之年也是一樣。迦膩色迦即位之年未必就是結集之年。也就是說,即使能證明結集舉行於公元78年,也依然沒有解決迦膩色迦即位年代的問題。迦膩色迦即位、建元以及結集三者未必在同一年。
7. P. H. L. Eggermont的公元78年說之三[47]
Pompeius Trogus的Historiae Philippicae一書有殘簡稱,“Asiani(成了)Thocari之王,Saraucae則被殲滅”(XLII),可證丘就卻登上貴霜王位的時間下限爲公元前20/前19年,上限爲公元前29年。蓋Pompeius Trogus又述:Phraates四世發動與王位覬覦者Tiridates之戰爭,並求庇於斯基泰人,得後者之助,得以回國逐走其對手(XLII)。Phraates四世回國在公元前29年,其對手被逐在公元前26年。
Phraates和Tiridates之間的內戰似乎給了丘就卻很好的機會驅逐其他斯基泰部落,確立了貴霜部落之優勢。Phraates被迫逃往斯基泰在公元前29年以前,因而丘就卻戰勝其餘部族之年約爲公元前25年。由此可見,祇有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一世紀即公元78年,纔符合丘就卻即位和迦膩色迦即位之間的時間間隔。
今案:此說未安。並沒有證據表明Asiani便是Kushans。Asiani成爲吐火羅之王,與《後漢書·西域傳》所載丘就卻滅其餘四翖侯無從比附。Asiani成爲吐火羅王以及Sacarauli被殲的時間也未必如說者所指。Trogus書已散佚,現存僅若干片斷,無從得知Asiani成爲吐火羅王一事與Phraates四世、Tiridates之間的鬭爭有無聯繫,不能根據後者發生的時間推斷前者發生的時間。事實上,Asiani成爲吐火羅王以及Sacarauli被殲的時間當在公元前129年以前。[48]既然如此,Trogus的記載並沒有提供哪怕是間接的有關迦膩色迦於公元78年即位的證據。
8. D. D. Kosambi的公元 78 年說[49]
Tolstov關於花剌子模出土遺址的報告有力地支援了78年說。但是,錢幣學的證據,正如MacDowell和Göbl所提供的,表明迦膩色迦即位的年代應在公元二世紀,這與Barrett依據圖像和雕塑,以及Allchin依據巴基斯坦考古資料得出的結論也是一致的。這是一個矛盾。但是,祇要認爲塞種紀元是一位僅以Soter Megas的名義打鑄錢幣的迦膩色迦創建的,而在錢幣上自稱迦膩色迦的貴霜皇帝是迦膩色迦二世,矛盾就解決了。
今案:其說未安。
一則,花剌子模的發掘沒有提供迦膩色迦創始塞種紀元的任何證據。
二則,說者並未列出任何積極的證據說明Soter Megas應即迦膩色迦一世。
三則,說者認爲Soter Megas作爲一個州長發行的錢幣似乎太多了。但除一篇Ārа銘文外並沒有留下其他記錄的迦膩色迦二世發行的錢幣似乎也是太多了。事實上,Soter Megas錢幣並不是一個州長發行的,應是丘就卻和閻膏珍時期各地州長代表中央政府頒發的。[50]
四則,說者既然不否認錢幣學的證據表明這位迦膩色迦應於公元二世紀即位,又何故忽視銘文學的證據表明與迦膩色迦有關的銘文不可能是公元一世紀的産物?[51]
五則,如果說迦膩色迦一世在錢幣上僅稱Soter Megas是因爲他確信每一個人都知道他是誰,那末何故Soter Megas這一稱號不見於他的銘文,而在銘文上卻要寫上迦膩色迦這一名字?
此說之所以提出,似乎是爲了擺脫78年說的主要困境之一:錢幣學的研究表明,迦膩色迦錢幣的年代不可能早於公元二世紀。[52]遺憾的是,說者既未能證明Soter Megas錢幣的年代晚於閻膏珍,又未能解釋爲何迦膩色迦一世在錢銘上匿名,而在碑銘中並非如此。傳征服了以 Nahapāna 爲代表的Kaharātas族,證據如下 :
(1)據若干Nasik和Karli銘文,Nahapāna之婿名abhadatta(Uabhadata, Uavadata),而 Gautamīputra曾捐贈一片一度爲Uabhadata所有的土地。
(2)在Nasik的錢窖中,有若干爲Gautamīputra重新打鑄的
9. A. Maricq的公元78年說[53]
由此可見,Nahapāna和Gautamīputra同時代。後者於其在位第18年之前征服Nahapāna家族,而其治期至少有24年。
另據Rudradāman年代爲72年的Girnar銘文,Rudradāman曾兩次打敗Āndhra王但均因考慮到他們親密的家族關係而寬恕了他。而據Kanheri銘文,可知所謂親屬關係乃指曾娶 Rudradāman 之女爲妻。
(1)唯一一篇屬於他的年代爲52的Andhau銘文,將他和他的孫子Rudradāman並提,措辭含糊,不知是年是Rudradāman單獨統治,還是祖孫一起執政。因此從年代角度來看,很難排除Caana開創了一個紀元的可能性。但是,Caana和Gautamīputra的繼承者 Puumāvi之間,Gautamīputra和 Nahapāna之間的同時性,以及Caana在烏賈因接替了Nahapāna等都表明:從年代的觀點來看,不可能認爲Caana開創了一個紀元。
今案:其說未安。
(1)首先,Nahapāna採用塞種紀元紀年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Nahapāna既然採用塞種紀元,則不能排除他本人或其父輩創建這一紀元的可能性。Puumāvi和Caana同時代,很可能祇是首尾相銜,其實Caana應與Gautamīputra同時代。前者娶後者重孫女,既無血緣關係,有何不可,蓋政治婚姻無奇不有。再者,娶Rudradāman之女者亦未必是Puumāvi本人,或其異父兄弟(couterine brother)。[54]如一般認爲 Rudradāman 於公元 130—150 年在位,則塞種紀元第52年應爲Caana末年,時值Puumāvi在位第6年。
10. B. N. Mukherjee 的公元 78 年說[56]
據《後漢書·西域傳》,閻膏珍曾征服身毒。“身毒”得名於Sindhu,其地大致包括今西巴基斯坦(但Baluchistan不在其內),白沙瓦以南、印度河以西地區。
Mohenjo Daro的佛教萃堵波和寺院中至少出土了1438枚Vāsudeva一世的銅幣。如此大量的錢幣出現在一個宗教建築物而不是一個商業場所不能僅僅用貿易關係來說明,也就是說這些錢幣應在Mohenjo Daro地區正常流通。Vāsudeva一世的銅幣及其倣製品也發現於Mohenjo Daro以西僅20英里左右的Jhukar的一些世俗建築中,這也說明了這位貴霜王錢幣在該地流通。
Mohenjo Daro無疑是身毒國(Sindhu)的中心。因此,Vāsudeva一世的銅幣至少曾在身毒的部分地區流通過。雖然一個政權的錢幣在某地正式流通並不表明該政權實際管轄該地區,但既然身毒曾爲貴霜王閻膏珍征服,而且正如迦膩色迦一世的Sui Vihar銘文所表明的,貴霜統治至少存在於附近地區諸如Sui Vihar,則Vāsudeva一世的錢幣在身毒流通應該說明他統治過該地區。
因而,貴霜對身毒(Sindhu)的佔領似乎至少從閻膏珍的末年持續到Vāsudeva一世的第一年。已知Vāsudeva在位的最早年代爲迦膩色迦紀元的第64或67年。由於並不知道Huvika在迦膩色迦第60年以後是否在位,不能排除Vāsudeva就在這一年繼位的可能性。因此,似乎可以肯定,貴霜對身毒的統治至少從閻膏珍末年持續到閻膏珍的直接繼位者即迦膩色迦所建紀元的第60年。
另一方面,Rudradāman一世的Junāgadh銘文表明他在塞種紀元第72年(即公元149—150年)作爲一位獨立的統治者統治着身毒,因此貴霜對身毒的61年或更長的統治應結束於公元149—150年前後。
又據《後漢書·西域傳》,丘就卻“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稱:“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安息(即帕提亞)佔有高附(Kabul)祇可能在印度希臘人統治該地之後、貴霜人征服該地之前。既然喀布爾河上游至少在公元前一世紀某時屬於帕提亞勢力範圍,而帕提亞人對該地的控制結束於公元前1年或這一年之前,則丘就卻破安息、得高附也應該在公元前1年或稍前。既然《後漢書·西域傳》載丘就卻取高附僅在攻滅四翖侯、建立貴霜王國之後,他的統治生涯應開始於公元前1年前的某時。具體而言,可能是公元前5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話。
從丘就卻之子閻膏珍(Vīma Kadphises)征服身毒開始,貴霜人61年或更長的時間對身毒的統治必定結束於公元149—150年。因此,迦膩色迦紀元的第60年應在公元149—150年之前,該紀元的元年則不可能落在公元89—90年之後。如果考慮到已知Vāsudeva一世在位的最早年代是迦膩色迦紀元第64年或67年,而他可能在這一年之後的若干年內領有身毒,則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應不晚於公元一世紀的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另一方面,既然帕提亞君主Gotarzes二世即位於公元40—41年,他的某些錢幣反面的圖案(在祭台前獻祭的王)很可能就是閻膏珍很多錢幣正面圖案設計的原型(在祭台前獻祭的王),則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不可能早於公元40—41年。
如所周知,憍賞彌的Maghas採用塞種紀元。已知憍賞彌的Maghas獨立統治的最早年份是塞種紀元第81年(即公元158/159年)。如果一篇Bandhogarh銘文提到的Bhīmasena王是Magha家族的一位子孫,該銘文的51年(即公元128/129年)應爲該家族已知最早的統治年代。
沒有證據表明Magha人創建了塞種紀元,也沒有證據表明該紀元是Nahapāna或Caana創建的。另一方面,迦膩色迦治期有一紀元開始使用,而他至少在該紀元的第二年統治着憍賞彌。既然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落在公元40—41年和公元89—90年之間,那末他在憍賞彌的統治可能與塞種紀元元年(公元78年)不會相去太遠。
再者,憍賞彌的考古發掘表明,該地最高權力是從貴霜過渡到Magha家族的。因此,可以斷定Magha家族是熟知迦膩色迦紀元的。如果Magha人在迦膩色迦治下貴霜領土可能的界限之內或與之相去不遠的一個地區使用另外一個政權的紀元,那末合乎邏輯的結論是他們銘文年代是按照迦膩色迦紀元計算的。既然Magha人記錄中所用紀元的元年是公元78年,這一年便應該是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
今案:B. N. Mukhejee說未安。
一則,雖然僅僅根據漢文史料的記載不妨將丘就卻滅四翖侯,自號貴霜王的時間上限定在公元25年左右,但如果結合銘文和錢幣的證據,則不能認爲丘就卻在公元前已經領有高附(即Kabul河谷)。貝格拉姆(Begrām)出土了大量Gondphares的錢幣,但沒有他的繼承者的錢幣。這表明喀布爾河上游地區在Gondphares死後不復由其後人統治。[57]從貝格拉姆錢幣的出土情況來看,繼Gondphares之後統治該地的應是丘就卻,而年代爲103年的Takhti-Bahi銘文表明Gondphares即位於公元19年,去位年代的上限爲公元45年。因此,丘就卻攻佔喀布爾的年代不可能早於公元19年,更可能是在公元45年之後。《後漢書·西域傳》所謂“攻安息,取高附地”,乃指丘就卻攻取由安息人Gondphares家族統治的喀布爾河上游地區。丘就卻取高附的年代既不可能在公元之前,則說者以爲丘就卻於公元前5年開始其統治生涯的判斷就失去了根據。
二則,《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表明閻膏珍曾征服身毒,Mohenjo Daro等地佛教和世俗建築中發現的Vāsudeva的錢幣表明他也統治過身毒。但是,即使如說者所言,自閻膏珍至Vāsudeva,貴霜人統治身毒至少60年,並未間斷,與Rudradāman的統治並不矛盾。蓋後者役屬貴霜(迦膩色迦)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三則,閻膏珍的錢幣摹倣Gotarzes二世的錢幣未必說明兩者是同時代的,而年代爲134年的Kalatze銘文表明閻膏珍的末年不會遲於公元129年。這就是說,迦膩色迦即位之年不能早於此年。
四則,即使Magha人不是塞種紀元的創建者,Nahapāna和Caana也不是塞種紀元的創建者,仍不能排除在Nahapāna和Caana之前有一塞種統治者創建這一紀元。公元78年應是丘就卻去位年代的上限,其時閻膏珍無疑尚未征服身毒。正在這一年,一位塞種酋長創建了塞種紀元。雖然身毒一地不久便爲閻膏珍征服,但當地的塞種人仍有可能繼續使用自己的紀元。Nahapāna等因臣服於貴霜,不使用王號、帝號,而僅稱州長、大州長,閻膏珍則允許他們擁有某種程度的自治權,包括使用原來的紀元,僅置將“監領”。迦膩色迦繼位之後,很可能摹倣閻膏珍的統治方式,Rudradāman即迦膩色迦所置之“將”。Magha人統治憍賞彌最早的年代是公元128-129年,時值閻膏珍治期之末,很可能此時身毒一帶的塞種政權勢力日益強盛,乃至憍賞彌的Magha人也受其影響開始採用塞種紀元紀年,這也表明Magha人很可能一度臣服於身毒的塞種。後來,雖然憍賞彌落入貴霜的勢力範圍之內,但Magha人也有某種自主權,乃至塞種紀元沿用不變,直至獨立。質言之,考古學資料表明憍賞彌的最高權力是從貴霜向Magha人過渡的,並不表明Magha人一定採用貴霜人的紀元。
11. D. C. Sircar的公元78年說[58]
塞種、貴霜和笈多的馬土臘銘文資料的古文書學分析,連同其他銘文和錢幣的資料一起表明:貴霜(從迦膩色迦一世到Vāsudeva)統治馬土臘的一個世紀應該被安排在公元一世紀或二世紀。
馬土臘銘文(塞種、貴霜和笈多)共使用三個不同的紀元:a.Scytho-Parthia紀元:odāsa及其他;b.迦膩色迦紀元:迦膩色迦組統治者;c.元年爲公元319的笈多紀元。古代印度使用紀元的習慣是外來的。Scytho-Parthia紀元和迦膩色迦紀元均不例外。
(1)使用Scytho-Parthia紀元的一篇銘文年代是72年,而在馬土臘發現的若干迦膩色迦及其繼任人的銘文的年代數大於72年。
印度最早的紀元即Vikrama紀元(元年爲公元前57年)和塞種紀元(元年爲公元78年)正落在Scytho-Parthia和貴霜統治西北印度的時代。這兩個外來王朝創建在印度希臘王Demwtrius和Eucratides(前二世紀前半葉)及其繼承者之後,而貴霜王朝迦膩色迦一組統治者(其領土包括馬土臘)必須安排在公元380年(即旃陀羅笈多二世的馬土臘銘文的年代)之前很久,蓋據《往世書》的傳說(部分得到銘文和錢幣證據的支持),在馬土臘可能於公元四世紀中被沙摩陀羅笈多(約公元340—376年)幷入笈多帝國之前安排了七位Nāgas統治者。迦膩色迦紀元第28年Vasika的Sanchi銘文又肯定早於塞種酋長rīdharvarman的Sanchi銘文,後者的年代可能是公元279年,更早於笈多紀元第93年(公元412年)的旃陀羅笈多二世的Sanchi銘文。
考慮到早期印度土著統治者完全不用紀元,在公元前一世紀和公元三世紀之間統治西北印度的外來統治者使用兩個不同的紀元,這兩個紀元的元年之間相隔一個世紀又幾十年,而Vikarama紀元和塞種紀元的元年相隔135年,並且分別落在外來人統治西北印度的公元前一世紀和公元一世紀,就會很自然地認爲Vikrama紀元和塞種紀元分別就是見諸銘文的兩個外來紀元Scythio-Parthia紀元和迦膩色迦紀元。
今案:說者其實並未證明Scytho-Parthia紀元和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相差135年。事實上,公元199年的Mathurā銘文使用的是Scytho-Parthia紀元,而如說者所論,這一紀元的元年是公元前57年。迦膩色迦自創紀元取代舊紀元,則其元年應在公元二世紀前半葉。又,迦膩色迦即位無疑在閻膏珍之後,後者在位時使用說者所謂Scytho-Parthia紀元,其Khalatse銘文的年代爲184或187年,這也表明新老紀元相去不止135年。因爲提到的貴霜王名Vima正如多數學者承認的,顯然可以和閻膏珍勘同。閻膏珍無疑是早於迦膩色迦的貴霜王。
另外,年代爲136年的Taxila銘文無疑屬於迦膩色迦以前的貴霜銘文,其紀元應爲Scytho-Parthia紀元,實際年份爲公元78年(說者以爲該銘文的實際年份是公元79年,應屬無名王。據此,則迦膩色迦即位後舊紀元繼續爲貴霜王使用。這是矛盾之一。無論無名王是誰,既然公元79年在位,則似難認爲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78年)。如果公元78年爲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則不應有這種現象。應該指出:Taxila銘文上提到的貴霜“大王、王中之王、天子”,不可能是迦膩色迦,而應該是一位先迦膩色迦貴霜王。因此,銘文的年代136不能認爲是迦膩色迦在創建新紀元之前使用舊紀元的例證。而如果結合閻膏珍的Khalatse銘文,可見Taxila銘文的136年也不可能是這位先迦膩色迦王和迦膩色迦政權交替的一年。
年代爲103年的Takht-i-Bahi銘文提到了Gondophares。這篇銘文的紀元,如說者所指,應按Scytho-Parthia紀元計算。果然,則直至公元45年Taxial仍在Gondophares治下。這就是說即使認爲Gondophares去位於公元45年,而且不計其後繼者的治期,第一貴霜(包括丘就卻和閻膏珍兩者)的治期不過20年略多一些。丘就卻佔領罽賓(Gandhāra和Taxila)尚在佔領高附(Kabul)之後。而丘就卻取高附於“安息”(即Gondophares王朝)之手,這似乎祇有在Gondophares去世後纔有可能。這實在無法和《後漢書·西域傳》所載丘就卻之高齡以及兩位統治者的功業相協調。丘就卻和閻膏珍的錢幣業已大量發現也說明他們的治期不會太短。
說者以爲西印度塞種統治者Rudradāman年代爲72年的Junagarh銘文表明,在公元50年時Ākara(東馬爾瓦,連同在Vidiā的首都)都是Rudradāman的領土。但是Vāsudeva的年代爲迦膩色迦紀元第28年的Sanchi(Vidiā附近)銘文表明,在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治期貴霜佔領着東馬爾瓦。如果該銘文所用紀元爲125年,則Vasika與Rudradāman同時,這顯然是矛盾的。
其實,Rudradāman的上述銘文僅僅是宣稱對馬土臘地區的主權,未必實際佔有該地。何況,當時貴霜王是Rudradāman宗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至於在沙摩陀羅笈多征服之前,馬土臘地區存在七個Nāga統治者也不能作爲迦膩色迦紀元應該提前到公元78年的證據。不僅因爲這七個統治者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是《往世書》的傳說,具體在位年代不明,而且不能排除這七個統治者事實上是同時或差不多同時存在的可能性。
12. S. P. Tolstov 的公元 78 年說[59]
Toprak-kala遺址花剌子模王宮的檔案室中,出土了四件紀年皮革文書,其中三件的年代清晰可辨,分別爲某一不明紀元的第207、231和232年。出土資料表明,Toprak-kala遺址的年代在公元前一世紀末和公元四世紀之間,而宮殿的年代在公元三、四世紀之交。Toprak-kal宮殿的建築、雕塑和繪畫生動地表明,當時Khorezm藝術的發展和同時期的印度藝術有着密切聯繫。
Khorezm與印度的聯繫在雕塑中表現得最爲明顯。Toprak-kal宮一處宅第壁間所置武士雕像的人類學特徵完全不同於中亞居民。其像直髮、厚唇、鼻型特殊、身材短小,膚色自淺棕直至深黑,可視爲赤道種的南印度或達羅毗荼型變種。這種類型也見諸公元三、四世紀之交要塞Kalaly-gyr-I墓葬的人類學採集品中。
雖然Khorezm居民的南印度成分可追溯至公元前十三世紀,正如青銅時代晚期的墓葬Kokcha-Ⅲ的人類學資料所顯示的那樣,但Kokcha-Ⅲ所見已是南印度人種與Khorezm歐羅巴種的混合型。由於Khorezm所見和Toprak-kala雕像所示均係純南印度人種,這表明至遲在公元二世紀有一次新的移民浪潮,自南印度波及Khorezm。這應該是貴霜政府執行軍事移民的結果。
公元一世紀末,Khorezm成了貴霜帝國的一部分。錢幣學的證據證實了這一點。古代花剌子模的錢幣採集品中,貴霜銅幣佔有重要地位,共有60餘枚,其中包括閻膏珍6枚,迦膩色迦8枚,Huvika 9枚,Vāsudeva 18枚,餘者無從歸類。在 Toprak-kala城區及其附近共發現22枚,包括閻膏珍4枚,迦膩色迦3枚和Vāsudeva 6枚。而Vāsudeva的錢幣中可能有一些不是一世而是二世的。
花剌子模出土的貴霜錢幣,除閻膏珍的錢幣外,其餘兩邊都蓋有一個“S”形的戳記,這種戳記也出現在最早的後貴霜花剌子模錢幣上。
結合貴霜以前花剌子模錢幣進行研究,可知這“S”形戳記是花剌子模統治者在花剌子模本地收回對錢幣控制權的最早的表示。這以後出現了純粹花剌子模小銅幣,上面也有這種“S”形戳記。花剌子模發現的銀幣中包括兩枚最早的後貴霜銀幣,其上也有“S”戳記。這被稱爲Artamukh及其妻之錢幣。錢幣學的分析表明這兩枚銀幣的時間是公元三世紀第一個10年。
在Toprak-kala宮出土的兩枚銀幣,蓋有十字形戳記。這種蓋有類似戳記的錢幣大量發現於Toprak-kala城表面及其周圍。其年代應在有“S”形戳記的貴霜錢幣之後,而在“S”形戳記的花剌子模錢幣之前。後者恢復了Siyavushid特有的花押。花剌子模錢幣花押的這一變化說明曾發生過一次政變,一度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十字花押乃屢見於印度錢幣上的“+”字之變種,這表明某種印度傳統的復蘇,時在早期薩珊軍事活動啓動之際,甚或更早──三世紀中葉,在花剌子模一個印度王朝奪取了政權。當時既不可能有外來的征服,祇可能是內部的政變,這政變可能是上述黑膚武士發動的。這一王朝的第一位統治者是Wiramna。從錢幣可知這一王朝至少有三位(可能多達五位)統治者。
據比魯尼(公元973—1048年)記載,公元305年,Afrig建立了一個新的Khorezm紀元。此後,Afrig將都城自Toprak-kala遷往Fir (Fil)。Toprak-kala宮被廢棄無疑與這次遷都有關,時在公元四世紀之初。
假定出自Toprak-kala宮檔案室文書最遲的年代落在公元四世紀第一個10年,這未知紀元的元年應在公元68和78年之間,因而很可能是印度的塞種紀元。蓋據比魯尼,Afrig以前的花剌子模王按照自己在位年代紀年,人們已經不再記得有曾使用過200年以上的花剌子模土著紀元。這表明文書所用的紀元是一個外來紀元。印度是當時唯一能提供花剌子模一個紀元的地區,因爲Toprak-kala城在建成不久就成了貴霜帝國一部分,歷時近百年,深受印度文化之影響。而見用於中印度和南印度銘文的塞種紀元之所以見用於花剌子模──貴霜帝國的邊緣地區,說明該紀元正是貴霜的官方紀元即迦膩色迦紀元。
假定第二貴霜諸王在位時間持續100年,則在最後一位貴霜王(Vāsudeva一世或二世)和Toprak-kala宮放棄(相當於用塞種紀元紀年的文書完成之日)之間流通的錢幣材料的時間跨度也爲100年或略多。這段時間相當於有花剌子模“S”形戳記的貴霜錢幣在花剌子模流通的延長時期。一部分是所謂Artamukh及其妻之治期,一部分是另一位在採集品中由小銅幣代表的統治者的治期,這位統治者在他的錢幣的反面也加蓋一個“S”形花押。而上述政變以及一個新的Indo-Khorezmian王朝的建立(這個王朝的統治者打鑄一種有十字形花押和獨特的Siyavushid型花押的錢幣)的時間接近於沙普爾(Shapur)的遠征。
Indo-Khorezmian王朝有三至五位統治者。而在貴霜錢幣流行和Afrig即位之間至少有九位統治者。假定公元78年是迦膩色迦元年,第二貴霜諸王在位時間爲98年,則Vāsudeva二世於公元176年去位。考慮到Toprak-kala宮出土的Vāsudeva錢幣中可能包括二世,則蓋有“S”戳記的貴霜錢幣在花剌子模流通應在公元二世紀後期。
沒有戳記的貴霜錢幣在花剌子模開始流通和沙普爾一世(241年,這一年或稍後乃印度-花剌子模王朝出現之時)即位之間的時段,相當於花剌子模打鑄有戳記的貴霜錢幣和三位使用“S”形戳記的統治者的治期。換言之,這段時期持續30—40年。而Afrig以前至少六位王者的治期持續60—70年。
如果接受Ghirshman的144年說,那末貴霜以後花剌子模錢幣反映出來的複雜歷史進程祇能壓縮在半個世紀(即公元三世紀後半)之內,這顯然是不合情理的。
今案:此說未安。
一則,沒有充分的證據說明花剌子模曾經是貴霜帝國的一部分。建築、雕塑、繪畫等藝術風格接受印度同時期藝術風格的影響不足以證明這一點。至遲在公元二世紀末有一批南印度人遷入花剌子模也不足以說明這一點。既然早在公元前十三世紀已有同種的南印度人遷入花剌子模,則公元二世紀遷入未必是貴霜軍事移民政策的結果。花剌子模總共出土60枚貴霜銅幣似乎也表明該地未曾爲貴霜所幷。既然未能證明花剌子模曾是貴霜領土的一部分,即使能證明文書所用紀元爲塞種紀元,也不能認爲塞種紀元就是迦膩色迦紀元。既然印度的建築、雕塑、繪畫藝術可能影響同期的花剌子模,塞種紀元作爲一個印度地區流行的紀元輸入花剌子模也就不足爲奇了。
二則,即使花剌子模曾是貴霜帝國領土的一部分,也未必一直被貴霜人統治至第二貴霜王朝結束。質言之,公元二世紀末第一個在貴霜錢幣上打“S”形戳記的花剌子模統治者未必即位於Vāsudeva一世乃至二世之後。這位統治者完全有可能是Vāsudeva一世甚或Huvika的同時代人。既然如此,說者藉以反對144年說的理由便不能成立,依舊有至少一百年的時間來容納通過花剌子模錢幣分析得出的該地擺脫貴霜統治直至Afrig即位這一段頗爲複雜的歷史。
三則,文書的出土有偶然性,因此未必232是Afrig建元以前舊紀元的最大紀年數。揆情度理,Afrig遷都時應該將有用的文書帶走,而棄置在檔案室的多半是因年代久遠而價值跌落的那些文書。雖然Toprak-kala宮的年代在公元三、四世紀之交,但王家檔案室中藏有年代較早的文書不足爲奇。假定文書採用的印度紀元正是說者反對的始於公元144年的迦膩色迦紀元,則232年的實際年份爲公元176年。蓋232年應即迦膩色迦紀元第32年。質言之,文書檔案採用者其實是所謂Vikrama紀元(不過沒有省去百位數2而已),這並不妨礙以上有關花剌子模史年代的安排。
四則,Б. И. Вайнберг[60]認爲 :阿姆河下游 Toprak-kala 墓葬的骨殖罐上的紀年銘文表明,有一個花剌子模紀元至少存在了8個世紀。Toprak-kala的文書,若干刻有花剌子模銘文的銀盃和Toprak-kala骨殖罐都按該紀元紀年。遺憾的是,根據現有資料無法精確地判定該紀元的元年,因而無法確定Toprak-kala城堡的年代。Toprak-kala發現的錢幣也沒有提供任何證據支援S. Tostov關於該紀元應即78年的塞種紀元的觀點。Toprak-kala的有關材料祇能使我們相信該紀元始於公元一世紀40或50年代初,不會遲於公元54年。
按照佛教傳說(Sarvāstivādin, Vaibhāika),脅尊者(Pārva)和世友(Vasumitra II)是迦膩色迦贊助的一次佛教結集的領袖人物,Caraka(遮羅迦)是迦膩色迦的宮廷醫師,Mātcea是一封給一個叫Kanika的國王書信的作者。確定以上三人的大致年代有助於迦膩色迦的年代的判斷。
諸經所載佛滅後所謂傳燈系統表明,龍樹(Nāgārjuna,大乘Mādhyamaka派的創始人)在脅尊者之後。而據太羅那特(Tāranātha),世友是脅尊者的同時代人,在迦膩色迦去世時依然健在。又據太羅那特,龍樹在其晚年自那爛陀往赴南印度,其學生聖天(Āryadeva)曾使 Mācea皈依佛教。印度因明學發展史的研究表明Caraka和世友的年代均早於龍樹。由此可見,祇要知道龍樹的年代,便能推出其他三人的年代。
史詩和若干其他文學作品均稱龍樹和一位娑多婆訶王(Sātavāhana)同時代,而據太羅那特,龍樹和鄔闍衍那的arvavarman(薩爾瓦跋摩)是同時代人。因此,和龍樹同時代的娑多婆訶王可能是著名的Prakrit文學的提倡者和Sattasaī的編者Hāla。
13. A. K. Wardar的公元 78 年說[61]
由此可見,與世友同時代的迦膩色迦一世的年代也應該是公元97年(他可能在今後幾年內去世)。而另外一位迦膩色迦的年代應爲公元172年。如果考慮到迦膩色迦二世可能在一世死後18年即位,則 Mācea的信應該是寫給迦膩色迦三世的。這就是說,迦膩色迦一世祇可能即位於公元78年。
既然包括《大唐西域記》在內的佛教諸傳說均未言明於龍樹同時代的娑多婆訶王究竟是何人,則不妨如一般所認可的那樣,指Yajñaātakari(約公元 174—203 年),爲龍樹同時代人。[63]這位國王的錢幣發現於中央邦的Chandā,這表明他的勢力曾涉及這一地區,而《大唐西域記》的憍薩羅國很可能曾建都於該處。[64]
(二)對公元78年說的評論
以下簡單介紹兩種對公元78年說的評論。
1. A. H. Dani說[65]
古文書學的證據表明,Nahapāna不可能效忠於迦膩色迦。因爲前者銘文的書風見不到貴霜影響,甚至晚期西部州長的銘文也見不到這種影響。古吉拉特和馬爾瓦依然流行老風格,甚至在整個北印度已受貴霜風格影響時也是如此。因此,迦膩色迦不可能是塞種紀元的創始人。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必定比公元78年晚得多,甚至晚於199年的馬土臘銘文。塞種紀元最初僅在西印度流行,僅在後期纔傳播到其他地區,有關的傳說都表明了這一點。
塞種紀元也不可能歸諸閻膏珍,因爲閻膏珍的年代爲187年銘文使用的是一個老紀元,而沒有證據表明塞種紀元在閻膏珍的領土上使用過。但是,閻膏珍或另一些早期貴霜統治者可能與塞種紀元的起源問題間接有關。塞種在馬土臘至少存在至公元15年,這已由年代爲72年的odāsa銘文證明。此後,還有州長Ghaāka。再往後,這個地區的塞種似乎被貴霜人推翻,其年代必定晚於佉盧銘文提到貴霜之時。
2. A. K. Narain說[66]
說者認爲,如果接受78年說,就無法安排迦膩色迦之前的貴霜統治者。持78年說者,爲了避免困難,祇能試圖將丘就卻生涯的起點提前到公元前20年,而如果將丘就卻安置在公元一世紀的第一或第二個10年,就祇能試圖壓縮閻膏珍的治期,其根據僅僅是閻膏珍繼承的是一個八十多歲人的王位。但是,這兩種安排都不能解決問題。如果將丘就卻即位之年提前到公元前20年,他的年代就會與已知塞種和Pahlava諸王的年代重疊。如果壓縮閻膏珍的治期,則很難理解這位印度征服者留下的大量錢幣。
Philostratus的《地亞那的Apollonius傳》一書中可以找到一個確定的點:儘管Phraotes的比定有爭議,但不能否定公元43年統治Taxila的是一位Pahlava王。這和Taxila的發掘結果是相符的。祇要假定丘就卻治期的大部分在公元43年之後,即使他在位50年也不應死於公元75年之前。
公元78年說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印度史提出的要求,但不能滿足中國史和薩珊史提出的要求。不管波調是Vāsudeva一世還是二世,都不能使之與迦膩色迦元年爲公元78年說相一致。因爲比公元230年一個早50年,另一個早30年。且如J. Marshall所指出,公元78年說的一大問題是《後漢書》沒有提到迦膩色迦。同理,薩珊對貴霜的勝利不可能早於公元223年,雖然可能略遲一點,但祇要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78年便無法協調。
指迦膩色迦紀元元年爲公元78年的唯一原因,是將迦膩色迦與塞種紀元未知的創始人勘同的誘惑。但奇怪的是,所有與塞種起源有關的傳說均與一個貴霜政治勢力沒有進入的地區聯繫在一起。使用這一紀元的地區顯然有別於貴霜帝國。何況貴霜並非塞種,沒有證據表明迦膩色迦創建了塞種紀元。
如果接受公元78年說,則公元114—119年時接受臣磐的月氏王便是Huvika,但不僅沒有證據,甚至沒有傳說表明Huvika與中國新疆有關,在新疆發現的貴霜錢幣中祇有一枚屬於Huvika。
三、公元二世紀諸說
公元二世紀諸說中,公元144年說一度最受青睞,尤其在倚重漢文史料的研究者中信從者較多,故在此首先介紹之。
(一)公元144年說
1. R. Ghirshman的公元144年說[67]
這是最早的公元144年說,以下是其主要論據:
(1)公元230年遣使曹魏的大月氏王波調應即亞美尼亞編年史家Moses Khoren的提到的貴霜統治者Vehsadjan,他與亞美尼亞王Khosrov聯盟,和Ardashir一世作戰,時在公元227年,也就是Vāsudeva。因此,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143/144和154年之間,因爲迦膩色迦王朝是在公元241/242和252年之間被沙普爾一世摧毀的。
(2)據泰伯里,Ardashir(公元226—241)視貴霜爲威脅,征服了巴克特里亞。這一記載,似乎被Surkh Kotal的發掘所證實,那裏出土了貴霜諸王─迦膩色迦、Huvika的錢幣,但未發現Vāsudeva的。而在沙普爾一世(公元240—270年)的Naqsh-i Rustam銘文中,沙普爾一世宣稱他的軍隊佔領了“Pskbvr”即貴霜的冬都白沙瓦。可見由迦膩色迦創建的貴霜王朝被沙普爾一世摧毀,取而代之的是承認薩珊宗主權的另一系統的王公們。
貝格拉姆的發掘表明Vāsudeva是在公元241和252年間被沙普爾一世推翻的。那裏出土的最晚的錢幣是Vāsudeva一世的,這些錢幣出自第二層。從Kobadian IV, Tali-Barzu, Qala-i-Mir和Airtam-Termez的發掘也可以得到類似的結論。
(3)迦膩色迦對帕提亞的遠征可能發生在Vologases三世治期,這也許起因於帕提亞人試圖收回被貴霜人兼幷的某個省份。
(4)貴霜人都使用省去百位數的Vikrama紀元,迦膩色迦即位於Vikrama紀元第201年即公元144年。[68]
今案:與其他公元144年說一樣,此說具有內在的合理性。最主要的是,其結論建築在文獻和考古資料相結合的基礎之上。但確指迦膩色迦元年爲公元144年則證據顯然不足。貝格拉姆即使被沙普爾一世毀於242年,亦不等於這一年便是Vāsudeva的末日。更何況,Vāsudeva的統治未必結束於迦膩色迦紀元98年,銘文的發現有其偶然性,事實上也不見得Vāsudeva治期每年至少有一篇銘文問世。
其說誘人處還在於堅持迦膩色迦並未另創紀元,仍然沿用Vikrama紀元,這和其前任丘就卻、閻膏珍是一致的。但是,其說的弱點也在於此:迦膩色迦即位之年恰好是Vikrama紀元第三世紀第一年的可能性極小。由於迄今沒有可以指認爲屬於迦膩色迦的年代爲Vikrama紀元199年及其以前的銘文,實在難以首肯該王即位之年爲公元144年。當然,此說還有待與基本史料,特別是漢文和亞美尼亞文史料協調。
2. A. H. Dani的公元144年說[69]
古文書學的證據表明,西北次大陸的佉盧銘文可大別爲三組:
第一組是最早的紀年銘文,始自68年的Mansehra銘文,止於191年的Taxila銀瓶銘文。這一組又可細分爲A、B兩組。A組是最早的一組,自68年的Mansehra銘文直到113年,包括Kaldarra銘文,但Takht-i-Bahi銘文不在其內。B組是較晚的一組,年代爲122年以降,其中有若干提到Kuaa、Khuaa或Guaa這一名稱,還包括Takht-i-Bahi銘文。這一組銘文明顯地有別於那些更早的沒有年代的銘文,必定使用同一紀元。
第二組包括迦膩色迦組統治者的銘文,以及跟在這一系列銘文之後的銘文。這一組又可細分爲A、B兩組。A組包括11年的Zeda銘文、18年的Manikiala石銘文、40年的Shakardarra銘文、41年的Ārā銘文以及89年的Mamane Dheri基座銘文。A組刻在石上,刻畫清楚,形式古樸。B組包括11年的Sui Vihar銅板銘文,20年的Kurram casket銘文和51年的Wardak瓶銘。B組刻在金屬上,草體。B組書寫風格與新疆出土的佉盧文一致,雖然可以認出由於書寫工具和材料的改變而引起表面上的不同,但最明顯的事實仍然是書寫技巧的一致,以及新字母的使用所體現的語言方面的某種類似。
在迦膩色迦這一組貴霜統治者的時代,西北次大陸流行着兩種佉盧文書寫風格。(2)A是較老的傳統的繼承;(2)B是從中國西域輸入的風格,這可以從新字母的出現得到證明。這種輸入不是由於迦膩色迦組統治者來自中國西域(因而他們屬於不同於第一貴霜的支系),就是因爲他們在征服該地區後從彼處輸入了抄寫員。後一種可能性較小,因爲這種風格的變化從這種統治者最早的年代就開始出現了。因而,如果古文書學可信,必須認爲:迦膩色迦組統治者的來臨引起了西北次大陸歷史和文化明確的變化。這一組紀年銘文的年代遲於前一組。
第三組的年代爲303年至399年。其中最重要的是303年的Charsadda銘文、318年的Loriya Tangai銘文、359年的Jamālgarhi銘文、384年的Hashtnagar銘文和399年的Skārah Dherī銘文。所有這些銘文都是私人記錄,僅Skārah Dherī銘文中提到“大王的村長、總督Avakhajhada”,其語言表面環境回到了迦膩色迦統治者以前,在風格上幾乎沒有受到文書的影響。事實上其傳承得自(2)A,而不帶文書的影響。可能是由於這一原因,較早的古文書學家試圖把這一組銘文斷在迦膩色迦之前。但是,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些銘文的字母形式中能見到清楚的發展形式。因此,這第三組銘文的年代一定晚於第二大組(迦膩色迦組)。老風格的恢復和老紀元的使用是一致的。在古文書學上,迦膩色迦組的銘文是闖入者,它來自塔里木盆地,這和迦膩色迦引進一個新紀元表明其權威是完全一致的。這一組的年代正落在200和303年之間──第一組的最晚年代和第三組的最早年代之間。根據這一分析,第一組和第三組所用紀元是同一個紀元。
通過以上的分析,在西北地區祇有一個紀元(不管其起源如何)一直使用到399年,而迦膩色迦組統治者的記錄給予的紀年系統在這個地區是一個闖入者,它至多持續了99年。這一闖入的紀年系列,連同隨之而來的見諸書寫風格的影響一起,被完全從這個地區驅逐了出去。在回答這兩個紀元始於何時這個問題時,必須明白:第一個紀元一直流行至馬土臘,正如99年的馬土臘銘文所證明的。而這一紀元可能也流行於西印度其他地區。
在婆羅謎文書法的發展過程中,馬土臘州長的銘文引進了一種新的風格。最好的例子便是72年的odāsa 的馬土臘銘文。這篇銘文的書風和Nahapāna銘文的相類似,而有別於晚期Āndhra統治者的銘文。Nahapāna的銘文和晚期Āndhra的銘文之間的差別並不表明Nahapāna的年代早於後者,因爲兩者代表不同的傳統。
古文書學的分析表明,Nahapāna銘文的書風得自馬土臘州長的銘文,因而年代晚於後者。但Nahapāna銘文的年代爲41和46,而odāsa的馬土臘銘文的年代是72,這表明兩者的紀元並不是同一個。既然Nahapāna銘文採用塞種紀元,則其年代爲119—124年,odāsa的年代在119年之前。同樣根據古文書學的分析,Nahapāna銘文年代早於199年的一篇馬土臘銘文,也就是說該銘文的實際年代晚於公元119年。由於72年的odāsa的馬土臘銘文和199年的馬土臘銘文採用的是同一個紀元,則這一紀元的元年不可能早於公元前80年,也不可能遲於公元47年,不能不認爲這個紀元便是元年爲公元前57年的所謂Vikrama紀元。
迦膩色迦組統治者的婆羅謎銘文可以分爲兩組:A組是在馬土臘及其附近發現的。B組是在東部例如在薩爾那特、室羅伐悉底和憍賞彌附近發現的,特別是Magha統治者的銘文。兩組銘文的書風有着顯著的區別。B組保持着見諸馬土臘州長銘文的風格,雖然也能見到若干新的影響,而A組突然引進一種新的書風,這種趨勢令人想起見諸中國西域佉盧文書的書風,這種風格也見諸西北地區佉盧銘文(2)B組。由此可見,迦膩色迦組貴霜統治在佉盧文和婆羅謎銘文的書風中都引進了一種新的風格。這種貴霜風格顯然晚於199年的馬土臘銘文。蓋後者不見這種風格之端倪。因此,如果老系列始於公元前57年,則迦膩色迦組的插入應在199年即公元142年之後。
他們的年代系列延續至他們在馬土臘統治結束。而且這一年代很可能在薩爾那特被AŚvaghoa採用,AŚvaghoa的銘文年代爲40。也可能被憍賞彌的Magha諸王採用,他們的銘文紀年在52和139年之間。這些形式又必須追溯至手稿書法所見的同一種趨勢。這同一風格也見於14年的迦膩色迦銘文,它必須追溯至同一趨勢,並被視作一種來自KauŚāmbī的地區影響。沒有必要像Lohuizen那樣把這篇銘文說成144年。沒有證據表明後期貴霜人在馬土臘超過99年。Lohuizen的某些年代省略了第一位數之说不能同意,她的古文書學分析是經不起檢驗的。
Nahapāna和後期貴霜銘文書法風格的清晰對照,明確地表示塞種政權在古吉拉特和馬爾瓦的擴張並不能歸因於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如果Nahapāna效忠於迦膩色迦,那末在Nahapāna銘文中應有某些貴霜風格的影響。事實上看不到這種影響,甚至晚期西部州長的銘文的書法也看不到這種影響。甚至在整個北印度已受貴霜風格影響之時,古吉拉特和馬爾瓦依然繼續老風格。因此,迦膩色迦不可能是塞種紀元的創建者。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必定比公元78年晚得多,甚至晚於199年的馬土臘銘文。馬土臘從公元78年進入貴霜人的勢力範圍,先是Kadphises組,後來是迦膩色迦組。可是,貴霜在印度較晚的年代無妨他們在中亞較早的歷史,那必須取決於那裏的證據。印度證據是與貴霜的較晚的年代相一致的。接受這一推算廓清了其他不必要的混亂,進一步說明了笈多帝國從俱賞彌的Magha統治者那裏學會了他們的書法,而紀元的思想及錢幣的類型都來自後貴霜。
今案:此說的問題在於
(1)無法證明迦膩色迦組統治者來自中國新疆地區,有別於之前的貴霜統治者。新發現的銘文可以證明他們是一脈相承的。
(2)書風的轉變祇能有助於大致年代的推斷,不可能精確到具體的年份。
(3)儘管說者不承認其銘文省略百位數之說,但祇要指迦膩色迦紀元之元年爲公元144年,實際上等於承認迦膩色迦和其前任一樣,還是採用了超日紀元。這不免自相矛盾。
3. P. L. Gupta的公元144年說[70]
迦膩色迦組貴霜統治的100年無疑在孔雀王朝衰落(約公元前215年)之後,而在笈多王朝興起(約公元315年)之前。
貴霜王國的心臟部分諸多遺址發現的錢幣表明,在馬土臘、俱賞彌、Ayodhyā和Ahicchatrā孔雀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四個邦國,而這四個邦國都有一個長而太平的統治期。因此,貴霜在上述四個地區的統治必定在這四個邦國的統治之後。貴霜很可能促使了這四個邦國的衰落。
在馬土臘及其鄰近地區出土的土著統治者錢幣表明,孔雀王朝衰落後,在馬土臘興起的王國有不下二十位統治者:Gomitra、S ū ryamitra、Brahmamitra、Dhruvamitra……有關錢幣學的分析表明,這二十位統治者相繼統治馬土臘,並無中斷。如果假定每位統治者有18年的在位時間,他們的治期就有360年。Gomitra錢銘的書法表明它們是這個王國最早的錢幣,其時間接近公元前三世紀末。如果馬土臘王國興起於公元前215年,緊接在孔雀王朝衰落之後,那末這二十位統治者至少統治到公元145年,這是貴霜人可能統治馬土臘的最早年代。
在憍賞彌──古代Vatsa的都城,發現了一個有迦膩色迦早年紀年銘文的佛像。這些銘文表明了貴霜對該地的統治。憍賞彌出土的錢幣表明,孔雀王朝以後,最早統治該地的是Mitra王朝(統治者的名字以Mitra結尾)。在出土Mitra統治者錢幣的地層中也出土了貴霜的錢幣,但似乎僅出現在最早的地層中。
在憍賞彌發現了不少於19位前Magha時期的Mitra統治者的錢幣。這 些 統 治 者 是 :Vavaghoa、AŚvaghoa、Paravata、Indradeva、Sudeva……此外,還從銘文中知道另一位Mitra統治者ivamitra。不妨認爲,這二十位統治者統治憍賞彌360年左右。
迄今知道的Magha統治者共有11位:Bhadramagha、Vairavaa……他們一共統治198年。發掘表明,此後是Gaapati Nāga,即沙摩陀羅笈多,在350年左右擴張時征服的統治者之一。因此,不妨認爲Magha統治者對憍賞彌的統治約開始於公元152年。而憍賞彌的貴霜錢幣的年代可大致斷在公元145—152年之間。
屬於十五位當地統治者的錢幣已在阿逾陀發現,這十五位統治者是 M ū ladeva、Vāyudeva、ViŚākhadeva、Dhanadeva、Pāthadeva、ivadatta、Naradatta……
在阿逾陀發現的一篇銘文中提到一個國王Dhanadeva(很可能就是錢幣所見Dhanadeva),Phalgudeva之子。他聲稱從總司令Puyamitra算起是“第六”,後者是阿逾陀王,進行過二次馬祭。據《大疏》和《摩羅維迦和火友王》,senāpati(總司令)是Puyamitraunga的稱號。因此,銘文提到的Puyamitra無疑是Puyamitraunga。既然Dhanadeva之名並未出現在往世書的ungas表中,似乎他僅僅是該王朝的某一旁支。如果銘文中“第六”一詞意指“第六代”,這可以認爲他在Dhanadeva之前五代,他的家族與unga王族有某種關係。據《戒日王傳》,M ū ladeva(可能就是錢幣所見 M ūladeva)殺死了 Sumitra(Vasumitra),Agnimitra之子。所有這一切表明阿逾陀的unga 領土是被 M ū ladeva 在約公元前130年侵佔的。
約公元前130年以降,阿逾陀16位統治者(包括Phalgudeva,他的錢幣沒有發現)統治約188年,也就是直到公元158年左右。貴霜人祇可能在這個年代以後到達喬薩羅。
般遮羅王國及其都城Ahicchatrā亦興起於孔雀王朝以後,從其錢幣可以得知至少有21位統治者連續不斷地統治。這些統治者是Rudradāman、Jayagupta……
雖然古文書學的證據似乎表明沒有錢幣早於公元前200年,仍不妨假定般遮羅王國興起於公元前215年(孔雀帝國衰落之年)稍前。這21位統治者統治378年,直到公元163年左右。
Ahicchatrā的錢幣出土情況還表明當地統治者之後便是貴霜人。貴霜之後便是公元350年被沙摩陀羅笈多征服的Acyuta。Acyuta之前是貴霜和仿貴霜錢幣。一般相信貴霜之後仿貴霜錢幣在印度流行約一個世紀。這意味着貴霜開始於公元350年以前約200年,即公元150年左右,這說明貴霜錢幣也許出現在163年稍前,即公元150年左右。
綜上所述,貴霜進入恒河-耶木那河流域的近似年代,根據馬土臘的資料是公元145年,根據憍賞彌的資料是145—152年,根據阿逾陀的資料是158年,根據Ahicchatrā的資料是150—163年。這些年代雖不精確,但清楚地表明不可能早於公元二世紀中葉。因而Ghirshman的144年的結論是可取的。
今案:有關年代的推算大致是可信的,足以證明迦膩色迦的治期開始於公元二世紀上半葉,祇是難以落實爲144年。
4. E. G. Pulleyblank 的公元 144 年說[71]
(1)《後漢書·西域傳》不載迦膩色迦,表明他不可能即位於公元125年以前。
(2)《後漢書·西域傳》斥《漢書·西域傳》關於五翖侯記載有誤,以爲高附不在五翖侯數內,直至丘就卻破安息,月氏始得高附。事實上,《漢書·西域傳》關於五翖侯的一段是在《漢書·西域傳》完成之後纔加到“大月氏條”中去的。有關情報乃於公元74—75年得諸班超,時丘就卻尚未一統其餘四翖侯,但已南向擴張其勢力至喀布爾。證據是傳文所載五翖侯的位置不像其餘諸國那樣用去長安的里數表示,而是用去陽關和去都護的距離來表示,同傳類似的里數標誌法也見諸康居五小王和縣度。也有理由認為這兩處是公元一世紀後半加進去的。由此可知迦膩色迦實無可能即位於公元78年。
(3)有關迦膩色迦和于闐關係、該王曾征服中國西陲的傳說,以及羅布淖爾地區在公元三世紀時使用佉盧文作爲官方語言的事實,均爲貴霜勢力曾進入塔里木盆地提供了有力的旁證。尤其是佉盧文(以及使用佉盧文書寫的印度西北俗語)被鄯善地區用來處理行政事務,表明該地區可能確實有一段時期被貴霜佔領。甚至可以設想,在貴霜勢力撤出之後,鄯善王國的行政管理由貴霜職員操縱。與佉盧文書一起出土的漢語文書中提到“支”姓戰士,也說明可能有貴霜軍事人員留在該地區。
中國史籍對貴霜佔領西域保持沈默,有關的記載也表明公元175年之前貴霜似乎沒有可能佔領塔里木盆地。此後,由於黃巾起義,中國人自顧不暇,以致公元184年以降沒有留下關於西域的記錄。因此,如果貴霜確曾佔領過塔里木盆地,最可能在公元175—202年這一段中國史料對西域事情保持沈默的時期之內。正是在這段時期,有月氏佛教僧侶到達中國的消息第一次見諸記載。
再者,公元184年在甘肅和青海爆發了一次嚴重的小月氏叛亂,直到公元221年纔完全平定。其原因中國史籍並無明確記載。如果考慮到貴霜勢力可能在這時對塔里木盆地入侵,則這種入侵可能導致其遠親起兵。
已知迦膩色迦最後一個紀年銘文的年代是41年,如果迦膩色迦即位於144年,則其實際年代爲公元184年。如果他在這十年或此後不久去世,則他在一生中的最後幾年(即公元175年以後某時)還有時間入侵塔里木盆地。至於于闐在公元202年朝漢不妨認爲是通知于闐恢復獨立,這就可以解釋爲何祇有迦膩色迦和Huvika的銅幣在于闐發現,而沒有Huvika以後貴霜統治者的錢幣在那裏發現。
(4)如果接受公元144年說,公元230年朝魏的波調應該是Vāsudeva。這和銘文所見Vāsudeva的年代是一致的─迦膩色迦紀元的61—98年,即公元204—241年。再者,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實際存在Vāsudeva二世或三世。那些被歸屬於Vāsudeva二世或三世的錢幣,很可能祇是Vāsudeva錢幣的拙劣仿製品。
要之,將迦膩色迦插入丘就卻和閻膏珍與大貴霜的繼承者之間,將迦膩色迦紀元與已知的元年爲公元前58年的Vikrama紀元勘同,完成了一個巨大的簡化過程。由此形成的假說不僅毫無困難地適合全部中國證據,而且也是唯一能做到這一點的假說。它似乎也符合錢幣學的和古文書學的證據。
今案:此說多有未安。
(1)《漢書·西域傳》關於五翖侯之記載絕無可能得自班超。質言之,不能以此證明迦膩色迦不可能即位於公元78年。說者對《漢書》和《後漢書》關於翖侯記載矛盾之解釋不足取。有關里數標誌的解釋也十分牽強,均不可從。
(2)貴霜僧侶入華時期爲靈帝時期(168—189年)。當時中亞居民,不僅貴霜人,還包括康居人、安息人以及一部分北天竺人,陸續不斷地移居中國境內。他們來華的路綫分海、陸兩道。取海道者經印度航海來到交趾,一些人留居交趾,一些人繼續北上,到達洛陽。由此可見,貴霜僧侶之入華,與貴霜當時是否佔領了塔里木盆地並無直接關係。
(3)年代爲41年的Ārā銘文提到的迦膩色迦,顯然不是迦膩色迦一世。已知屬於迦膩色迦紀年的銘文最晚年代是23年,但他很可能在位27年,因爲已知Huvika紀年銘文最早的年代爲28年。迦膩色迦果如說者所言,於公元144年即位,則他的在位時期爲公元144—170年。公元175年之後入侵塔里木盆地云云,無從談起。
(4)迦膩色迦可能在位的時期內,東漢的勢力雖未完全退出塔里木盆地,但已成強弩之末。如果說迦膩色迦確如玄奘所載,曾一度“治兵廣地,至葱嶺東”,以至“河西蕃維,畏威送質”,則應該發生在順帝以後。雖然中國史籍隻字未及貴霜在這段時期對塔里木盆地的佔領,相反有不少文獻和實物的證據表明,漢對西域的統治至少維持到靈帝後期。但是,必須看到,順帝以後,漢對西域的影響日益減弱,而國力正處於上升時期的貴霜,將其勢力伸向塔里木盆地是完全可能的。中國史料對此保持沈默,並不等於事情沒有發生。何況,塔里木盆地諸綠洲國因積威所在,對漢繼續稱臣,同時又役屬貴霜也是完全可能的。所謂“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原是西域綠洲小國一貫的立國之道。有關這一時期的記載十分短缺,默證的作用就顯得薄弱。客觀上,貴霜勢力完全可能在迦膩色迦在位時期一度入侵塔里木盆地。祇有如此假設,纔能解釋佉盧文書、于闐馬錢和新疆發現的貴霜銅幣等等。
(5)如前所述,公元144年說和Vikrama紀元的聯繫是該說最有魅力的地方,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裏。指Vikrama紀元301年爲迦膩色迦即位元年似乎過於巧合。
(二)對公元144年說的異見
1. B. Kumar對公元144年說的批評[72]
(1)Ghirshman未能使泰伯里的記載和Kaba-i-Zardusht銘文相協調──究竟是Ardashir一世還是沙普爾一世摧毀了貴霜。
今案:這正是Ghirshman說疏漏處。
(2)貝格拉姆和其他貴霜遺址的發掘情況僅表明這些地區是在Vāsudeva一世末年被放棄的,並不表明他們是被沙普爾一世摧毀的,也不能證明Vāsudeva是在公元241年被沙普爾一世趕下臺的。Mashall根據Taxila的發掘情況,力主貴霜王朝是被Ardashir一世推翻的;Schlumberger則在考察Surkh Kotal的貴霜神殿後,指出該建築是由Ardashir一世在Huvika治期結束時被毀的。
今案:遺址的證據孤立起來就顯得非常單薄。
(3)沒有證據表明迦膩色迦遠征帕提亞一事發生在Vologases治期,而可能是在Pacorus在位之時,蓋後者的治期並不太平。
雖然“波調”和Vehsadjan無疑是Vāsudeva的異譯,且薩珊諸王曾征服了原在貴霜治下的領土。但是,錢幣學的證據也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Vāsudeva一世死後,貴霜統治者繼續統治了喀布爾河谷很久,發行自己的錢幣,其中若干刻有Vāsudeva的名字。既然Ghirshman承認Vāsudeva二世和三世的存在,就沒有理由認爲沙普爾一世征服白沙瓦意味着是Vāsudeva一世、而不是Vāsudeva二世統治之結束。因此,公元230年遣使曹魏,227年與Ardashir鬬爭的也許是Vāsudeva二世而非一世。
今案:波調不可能是Vāsudeva二世,說見前文。
(4)銘文紀年省略百位數之說已被不同的學者用來支持不同的年代說,不足憑信。
(5)迦膩色迦紀元11年的Sui Vihāra銘文清楚地表明當時印度河下游的Bahawalpur地區包括在他的領土之中。而如果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144年,其年代爲公元155年。另外,在閻膏珍時期,Gujarat(Saurashtra)已經在貴霜控制之下。而Rudradāman的Junagarh銘文清楚地表明,他作爲事實上獨立的統治者在公元150年統治着Saurashtra和Sauvira,並完全征服了尤德亞人(Yaudheyas)。Sauvira包括印度河沿河地區,Multan周圍,而尤德亞人居住在Bahawalpur附近的Rajasthan。如果迦膩色迦在144年即位,Rudradāman是不可能宣稱佔領上述各地的。
今案:其說未諦,說見前文。
(6)Ghirshman認爲,Rudradāman應視作貴霜諸王的藩臣,他謙卑的稱號 rājā mahākatrapa說明了這一點。但是 Ghirshman並沒有解釋爲什麽Rudradāman能發行自己的錢幣,使用自己的紀元,而且自傲地宣稱征服了貴霜疆域內各地。Rudradāman的繼承人使用了同樣謙卑的稱號,但他們無疑擁有主權。顯然迦膩色迦和Rudradāman不可能是同時代人。
今案:此說未必然。Rudradāman使用自己的紀元、發行自己的錢幣,幷不足以否認他與迦膩色迦同時代。這與使用謙卑的稱號並無矛盾之處。
(7)沒有一個著名的紀元之元年始於公元二世紀,但銘文證據表明迦膩色迦確實開創了一個紀元,且由他的繼承者連續使用,祇能是後來“塞種”紀元。
今案:此說未安,說見前文。
(8)Ghirshman認爲,迦膩色迦紀元41年的Ārā銘文提到迦膩色迦僅僅表明該銘文用來紀年的紀元是由迦膩色迦創建的,而迦膩色迦本人在當時已經不在人世。這一假說不能成立,因爲銘文所見捐贈者不可能不怕麻煩把完整的皇帝稱號賦予一位去世的王,而且加上一個當時僅此一見的稱號Kaisar,也不可能提到迦膩色迦父親之名,而不提在位國王的名號。毫無疑義,Ārā銘文的迦膩色迦是迦膩色迦二世,於公元119年統治着貴霜帝國西北部。
今案:Ārā銘文中的迦膩色迦是迦膩色迦二世,但銘文的絕對年代不是公元119年。
(9)據S. Konow,祇有以公元128—129年,而不是公元144年爲迦膩色迦即位之年,纔能符合11年的Zeda銘文和61年的Und所提供的天文學資料。
今案:此說未安,說見前文。
2. A. K. Narain對公元144年說的批評[73]
(1)Girshman的公元144年說和中國史籍有關月氏早期活動以及丘就卻崛起的記載無法協調一致,因爲找不到一位統治者填補閻膏珍和迦膩色迦之間一段很長的間隙,有人試圖將Soter Megas的錢幣來填補這段空隙,但並不成功。錢幣學的研究表明,Soter Megas不是和閻膏珍同時代,便是早於閻膏珍,幾乎不可能在閻膏珍之後。如果Soter Megas與閻膏珍同時代,則間隙依舊存在;如果早於閻膏珍,那末他不是與丘就卻同時代,就是在丘就卻與閻膏珍之間;由於沒有蹟像表明他介乎丘就卻與閻膏珍之間,Soter Megas祇能是丘就卻本人,這顯然不利於Girshman說成立。
今案:此說未安。由於新銘文的發現,這已經不是問題。[74]
(2)Ghirshman將貴霜諸王歸入三個王朝並無正當理由,沒有支援這一方案的證據。而Ghirshman發表的銀十德拉克瑪,其正面爲閻膏珍之名,反面有迦膩色迦之名;閻膏珍的雕像發現於Māt,而那裏也有迦膩色迦的雕像;都說明了同樣的問題。至於說Vāsudeva屬於一個不同於Vāsudeva二世的家族,則與歷史時期中慣用的命名法是相抵觸的。錢幣學的證據清楚地反對任何將貴霜諸王分屬三個王朝的做法。
今案:其說甚是。
(3)貴霜在西部的政權究竟是在Ardeshir還是在沙普爾一世時代被摧毀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即使摧毀貴霜西部政權的是沙普爾一世,事實依然是Kaba-i-Zardusht銘文並沒有提到導致貴霜併入薩珊的這一次戰爭發生的日期。銘文甚至並沒有提到征服貴霜領土的是沙普爾一世,僅僅說沙普爾一世的領土中包括了貴霜帝國的一部分,這既可能是Ardeshir,也可能是沙普爾一次征服的結果,這次征服可能發生在公元223和262年之間。
今案:此說甚是。
(4)貝格拉姆II的年代是建築在兩個尚未證實的假說基礎之上的。其一是貝格拉姆 II毀於Vāsudeva一世時代,因爲據說發現了8枚屬於Vāsudeva一世的保存很差的錢幣。其二是這次毀滅發生在沙普爾一世即位(公元241年)和他向羅馬進軍之間的某時。
這兩個假說被重重困難包圍。據Ghirshman,貝格拉姆 III出土了Vāsudeva一世以後貴霜諸王的錢幣。在貴霜王國被征服之後,原貴霜王朝的若干成員繼續統治並發行錢幣是難以想像的。他們的錢幣,無論在風格、主題和銘文上都沒有絲毫蹟像表明他們役屬於薩珊。而且最後的Vāsudeva和非Vāsudeva一世的錢幣被用作所謂貴霜-薩珊錢幣的模型。所謂貴霜-薩珊(Kuāo-Sassanian)錢幣是在貴霜帝國被征服和并入薩珊以後、由統治原來貴霜領土的新的統治者頒行的。這些統治者均由薩珊王任命,他們有波斯名字和KuāŚāh 和 KuāaŚāhānuŚāhī的稱號。這意味着沙普爾一世或Ardeshir摧毀貴霜這一事件一定發生在Vāsudeva一世以後至少二代人的時間。Ghirshman從未發表那8枚保存得很差的Vāsudeva的錢幣,以致無法作進一步鑒定。考慮到以Vāsudeva名義打鑄的錢幣大不相同,進一步鑒定顯然是必要的。再者,很難同意貝格拉姆 II的火災是沙普爾一世發動的戰爭引起的。Ghirshman在貝格拉姆 II或II和III之間任何一個中間層中都沒有找到沙普爾一世或任何其他薩珊王的錢幣。而在Begrām III發現的迦膩色迦三世和Vāsudeva二世的錢幣,似乎表明該城繼續由貴霜人統治,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反證。確實有一層薄薄的灰燼將貝格拉姆 II和貝格拉姆 III隔開,這表明曾經發生過火災,但沒有足夠的證據推斷這場火災是由戰爭引起的。Ghirshman有關貝格拉姆發掘記錄中沒有關於戰爭的清楚蹟像。沒有理由認爲Vāsudeva以後有一個新的貴霜王朝建立。同樣,也沒有根據認爲貝格拉姆 III毀於一場入侵者的佔領引起的火災。火災更可能是其他事件引起的。畢竟貝格拉姆被發掘的祇是一個小區域,且祇找到8枚保存得很差的Vāsudeva一世的錢幣。
今案:這是實物證據的局限性。
(5)佛教傳說中提到迦膩色迦與安息的戰爭。如果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144年,他便是Vologases二世的同時代人。Vologases二世治世的早期,使Arsacid復興,並在西方戰勝了羅馬,迦膩色迦不可能戰勝Vologases。
今案:此說未安。一則傳說不可盡信。二則Vologases在西方取得之成功未必能在東方複製。
3. A. Maricq對Ghirshman144年說的批判[75]
據Ghirshman,貝格拉姆II城在某時毀於一場戰火。此後,在廢墟上建立了一個新城(貝格拉姆III)。在貝格拉姆II中,J.Hackin曾發現一個窖藏,藏品的年代估計從公元一世紀至四世紀。而在與這一窖藏相同的考古層中發現的年代最晚的錢幣是Vāsudeva一世的,其年代一般認爲是公元200—230年。而薩珊王沙普爾一世的Naqsh-i Rustam銘文提到沙普爾一世在對貴霜作戰中征服諸郡的名稱。由此可見,貝格拉姆II是沙普爾一世在公元241和250年間征服的,Vāsudeva一世的統治於是結束。Vāsudeva一世最晚的銘文是迦膩色迦紀元的98年;因此,這一紀元的元年應在公元143年和152年之間。而據Bhandarkar,貴霜人使用迦膩色迦紀元的一個世紀是某一紀元的第三世紀。該紀元一直使用至第220年,然後在第四世紀又被使用。如果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落在公元143和152年之間,且應爲老紀元的201年,則老紀元的元年應在公元前58年和公元前49年之間,老紀元應即所謂Vikrama紀元無疑。
但是,沙普爾一世的Naqsh-i Rustam銘文並沒有提到他曾發動對貴霜的戰爭,因而指貝格拉姆毀於沙普爾一世之手並無資料依據。
Ghirshman又認爲,上述銘文所列Ardashir一世的顯貴表,表中提到一位Margiana王、一位Carmania和一位塞種王。這清楚地表明Ardashir征服了Margiana、Carmania和塞斯坦(郡名表第17、20和21),而沒有征服排列在塞斯坦以後的諸郡,即Turan、Mukran、Paradan、Sind 和“ 貴 霜 人 之 地 ”( 直 到 Paškibur、Kashgar、Sogdiana和塔什幹的邊境)─郡名表第22至26,Turan以下均係沙普爾一世所征服。各郡在表上臚列的次序表明了波斯軍隊進軍的路綫,貝格拉姆正在這條路綫上。
但是,同一篇銘文中所見沙普爾一世的顯貴表及家族人員表同樣沒有提到Turan以下諸郡,按照Ghirshman的邏輯,豈不是也表明Turan以下諸郡不是沙普爾一世所征服的?沙普爾一世時代,塞種王是其子Narses,因而當時塞種王是Sind、塞斯坦、Turan之王,而在Ardashir時代,塞種王肯定沒有統治Turan。但是,這一差別未必表明Turan是沙普爾一世征服的。至於郡名表所列諸郡的次序,除Persis和Parthia兩郡列在表首外,其餘大致按照其實際地理位置臚列,亦似乎不能據以指實沙普爾一世進軍貴霜的路綫。
另外,進一步的鑒定表明,J. Hackin發現的窖藏品實際年代應爲公元50—75年,而不是最初估計的公元一世紀至三世紀乃至四世紀。既然全部窖藏品的年代不晚於公元一世紀,就很難認爲這些物品會收藏於公元三世紀。較合理的看法應該是隱藏地點約築成於公元一世紀末,而貝格拉姆被毀於公元一世紀末而不是三世紀中,其毀滅與沙普爾一世可能發動的戰爭無關。
Ghirshman在珍寶室的外面找到8枚Vāsudeva一世的錢幣。但它們被發現的一切細節都不知道,它們究竟是屬於貝格拉姆II還是III是有疑問的。既然窖藏品的製造年代是公元50—75年,加上若干不可知因素,例如製造和發送之間的延誤、旅途花費的時間以及它們在城市毀滅之前留在貝格拉姆的時間等等,將貝格拉姆II毀滅的時間定於公元141年以後是比較合理的。這就是說,該城毀於Vāsudeva一世即位之初,而非即位之末。而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爲公元78年。
此外,Ghirshman認爲,除貝格拉姆外,還有5個遺址可以認爲是薩珊進攻貴霜期間被毀的。其中,Surkh Kotal(Baghlān)毀於Ardashir,其餘則毀於沙普爾一世之手。
(1)撒馬爾罕附近的Tali Barzu遺址。Ghirshman所據乃Grigoriev的年代說,但Grigoriev的年代說已由Ternozhkin作了相當大的修正,Tali Bazu IV的年代其實屬嚈噠時期,而Tali Barzu V的年代爲公元6—8世紀。Ghirshman認爲它們分別與貝格拉姆I和III相當,非是。
(2)Airtam-Termez。Ghirshman指出,標誌着該城被棄的地層中發現年代最晚的錢幣是Vāsudeva一世的。但據Masson的報告,該城自Vāsudeva一世以降從未被放棄過,故不應在放棄之列。
(3)Kalai-Mir。
(4)Key-Kobad-Shah(Kobadian)。
1950和1953年對Kalai-Mir和Key-Kobad-Shah的發掘表明,前一世紀以降,居民區縮小,可能僅僅是由於居民的遷徙,但不清楚是否是由於一支軍隊引起的破壞。
總之,事實並不如Ghirshman所說,有一支薩珊軍隊在沙普爾一世率領下毀滅了以上4座城市。
今案:說者對Ghirshman的批判不無是處,祇是由於站在公元78年說的立場上,看不到Ghirshman說的合理內核。結合其他證據,Ardashir一世在Vasudeva一世治期進攻貴霜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三)其他公元二世紀說
除公元144年說外,還有其他各種公元二世紀說,擇要介紹如下。
1. J. Harmatt的公元 135 年說[76]
薩珊對貴霜的入侵十之八九發生在Vāsudeva二世即位之初,確切地說是在老塞種紀元299年。這應該就是Surkh Kotal銘文沒有完工的原因。薩珊軍隊毀壞了Surkh Kotal聖地,打斷了銘文的鐫刻。
Ardaχšahr對東伊朗的戰爭發生在兩次羅馬戰爭之間,亦即公元232年與238年之間。而他對Bactria的戰爭必定發生在233年。結合Surkh Kotal未完成銘文,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該銘文的鐫刻始於Vāsudeva二世之元年,但這一工作被薩珊波斯的進攻打斷。薩珊軍隊毀壞了Surkh Kotal聖地。既然薩珊的入侵發生於233年,無疑老塞種紀元的299年相當於公元233年。於是就有了一個關於老塞種紀元、迦膩色迦紀元以及貴霜統治者絕對年代的堅實基礎。
具體而言,老塞種紀元299年始於公元232年10月終於233年10月。由此可以推斷迦膩色迦紀元始於公元134/135年,而老塞種紀元始於公元前67/66年。
據此,Vāsudeva一世可能死於公元232年秋季之前,而Vāsudeva二世可能就在這一年即位,自公元232年10月他再次引進老塞種紀元。這一歷史事件的重構和漢文史料的記載完全一致。
據《魏略》,魏明帝(公元227—239年)時,貴霜帝國包括以下地區:Kashmir、Bactria、Kabul和印度。這清楚地表明,公元230年,貴霜帝國並沒有失去Bactria,也就是說其時Ardaχšahr的進攻尚未發生。這則有關貴霜帝國疆域信息的來源,顯然就是貴霜使團。這使團便是《三國志》所載公元230年1月5日,由波調(大月氏王)派遣的使團。“波調”應該就是Vāsudeva一世。貴霜統治者此時遣使朝魏很可能與受到Ardaχšahr的威脅有關。
貴霜使團被派遣到曹魏表明Ardaχšahr對貴霜帝國發動戰爭的年代是公元233年。可是,這時的貴霜統治者已經不是Vāsudeva一世,而是剛即位的Vāsudeva二世了。如果考察一下Parthia和薩珊統治者發動戰爭的日期,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情況:他們喜歡乘被入侵的國家王位變動或內部擾亂的時機發動侵略:羅馬帝國被攻擊便是在王位更易之際。很可能Ardaχšahr也乘貴霜王位更易之際發動入侵。
今案:此說雖有若干難以落實的地方,但不失爲公元二世紀說的一個有力支柱,儘管涉及的若干具體年代,譬如老塞種紀元之元年等,難以一一指實。
2. F. R. Allchin的公元二世紀說[77]
說者重新檢查了Marshall在Taxila有關錢幣的發掘結果,試圖建立錢幣次序和建築時期的對應關係。他分析了Bhir土墩、Sirkap和Sirsukh以及Dharmarajika萃堵波周圍的發掘成果,得出結論: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在公元二世紀。
據云:Manikyala大塔中發現被迦膩色迦18年石板銘文覆蓋的佛骨盒(relic chamber)是最初入藏的,其年代與萃堵波相同。其中有迦膩色迦和Huvika的若干銅幣和一枚金幣。這表明它們的入藏時間在迦膩色迦在位的晚期,其時Huvika作爲嗣子已開始以自己的名義發行錢幣。而在Ahin Posh萃堵波中出土10枚閻膏珍、6枚迦膩色迦和1枚Huvika的錢幣。同時入藏的還有Trajan、Domitian和Sabina的錢幣。由於閻膏珍的錢幣業已磨損,Huvika的一枚是新造的,可見這些錢幣入藏於迦膩色迦在位期間。既然迦膩色迦在位第18年時,Huvika已經以自己名義發行錢幣,則不妨認爲這些錢幣入藏於迦膩色迦在位第18—23年。既然Sabina的金幣打鑄於公元128—136年間,則迦膩色迦紀元的18—23年相當於公元128—136年,加上Sabina錢幣流入印度所需10—25年,可見迦膩色迦即位之年應落在115—143年。這一年不可能早於105年,最可能在130—140年間。
今案:此說與其他證據不悖,不失爲迦膩色迦元年在公元二世紀的證據。既然所藏Sabina金幣流入印度的時間不可能準確,則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144年左右亦是完全可能的。又,說者因一枚Augustus的銀幣與一枚Azilises的銀幣同時出土於Dharmarajika萃堵波Ⅳ之中,而指二者同時,則不妥,因與其他證據不符。蓋不能排除Azilises錢幣直至Augustus錢幣流入印度時尚未於流通中絕迹的可能性。
3. R. Gbl的公元二世紀說[78]
錢幣學的證據表明,貴霜錢幣多以羅馬帝國錢幣爲原型。其中閻膏珍、迦膩色迦和Huvika的錢幣分別以Trajan(公元98—117年)、Hadrian(公元117—138年)和Antonius Pius(公元138—161年)的錢幣爲原型。考慮到羅馬帝國的錢幣自羅馬或亞歷山大流入印度且成爲原型需要一段時間,以上對應關係表明閻膏珍的在位時間相當於Trajan之末,且跨入Hadrian時代,迦膩色迦的在位時期大致相當於Hadrian之末,且已跨入Antobius Pius時代,而Huvika的在位時間大致相當於Antonius Pius之末,並跨入Marcus(公元161—180年)和Severus(公元193—211年)家族早期成員統治時代。由此可見,迦膩色迦的年代應以J. Marshall和R. Ghirshman所說爲是。
Vāsudeva二世的錢幣可以與一世的區別開來,他的錢幣領先於薩珊波斯王Hormizd二世(公元302—309年)。如果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78年,Vāsudeva的治期結束於公元176年,則Vāsudeva二世的錢幣應該屬於從公元176年至Hormizd二世這130年的時期。果然,則錢幣一定在一個以上國王的統治期間流通。這與已經到手的錢幣數量是矛盾的。而如果定迦膩色迦的元年爲公元144年,Vāsudeva一世的治期結束於公元242年,則Vāsudeva二世的錢幣應屬於公元242年至Hormizd二世的治期約60年的時間內,符合祇有一個貴霜統治者的情況,且沙普爾一世的對手就會是Vāsudeva一世。
今案:錢幣風格雖不能作爲判斷年代的絕對證據,但精確、全面的比較研究無疑有助於迦膩色迦年代的推斷。
4. D. W. MacDowall的公元128/129年說[79]
說者認爲錢幣學的證據表明迦膩色迦應即位於公元128/129年,但並不排除公元144年或公元110年的可能性。
(1)Taxila萃堵波IV出土一枚公元11—13年在Lugdunum打鑄的Augustus的銀第納爾,同時出土有1枚Dioscuri類型的Azilises銀德拉克瑪。出土情況表明,這兩枚錢幣必定是同時有意入藏的。兩枚錢幣均未磨損。這表明,上述Azilises的銀幣不可能流通很久。而由於Azilises的銀幣不可能在Azes二世中年以後繼續流通(蓋當時銀幣急劇貶值,且被billon幣取代),上述Azilises銀幣的入藏時間不會晚於公元20—30年,也就是說Azilises約在公元11—13年在位。
今案:其說未安。一則,Azilises的銀幣未被磨損,未必表明它不可能流通很久,雖然一般說來表明它的入藏時間離開打製時間不久,但並不絕對。換言之,不能排除這枚錢幣甚至完全沒有進入流通的可能性。這枚錢幣和Augustus的銀幣同時出土,Augustus的銀幣打鑄於公元11—13年,這僅能表明Azilises的這枚銀幣入藏於公元11—13年之後,不能表明Azilises於公元11—13年在位。Azilises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烏頭勞,其子即Azes二世死於元帝時,其時間不會晚於公元前33年。[80]因此,他的銀幣應打鑄於Augustus即位之前。另外,如果承認Azes一世即位於公元前58年,則Azilises亦似乎不可能在公元11—13年時依然在位。
(2)Manikyala Court的佛塔有兩處出土貴霜錢幣:一處有4枚銅德拉克瑪,1枚是閻膏珍的,3枚是迦膩色迦的。另一處有8枚銅幣,能夠作出鑒定的有6枚,全係四德拉克瑪:1枚是Hermaeus和丘就卻聯名的,1枚是閻膏珍的,4枚是迦膩色迦的。這8枚銅幣存放在一個銅壇中,銅壇中有一小銀壇,其中有7枚羅馬共和國時期的銀第納爾,均已磨損,表明它們已經流通很久。與這7枚銀幣在一起的有一個小金盒,盒中有4枚迦膩色迦金第納爾。發掘的情況表明,這些金、銀和銅幣是一次性入藏的。由於沒有發現迦膩色迦的繼承人Huvika和Vāsudeva的錢幣,不妨認爲上述錢幣是在迦膩色迦治世入藏的。考慮到羅馬共和國的銀幣一直流通到羅馬帝國Trajan時代,而在Hadrian時代(公元117—138)尚被輸出,則不妨認爲迦膩色迦與Hadrian同時代。
今案:這些均可視作公元二世紀說之佐證。
(3)在Jalalabad的Ahin Posh佛塔共出土3枚羅馬金幣(aurei)和17枚貴霜第納爾,其中包括10枚閻膏珍的、6枚迦膩色迦的和1枚Huvika的。閻膏珍的已經磨損,迦膩色迦的略新,而Huvika的錢幣實際上是新鑄的;沒有後貴霜的錢幣。這清楚地表明這些錢幣入藏於Huvika早期。羅馬金幣是Domitian、Trajan和Hadrian之妻Sabina的。Sabina的金幣必定打鑄於公元128年之後、137年以前。因此,上述錢幣入藏時間的上限是公元128年。考慮到這一枚金幣在輸出前一定流通了一些時間(因爲已經磨損),入藏時間不會遲於公元160年。
(4)閻膏珍引進的標準金第納爾的概念無疑受羅馬金幣的啓發。一般說來,它的標準重量和大小可能受其原型影響。過去認爲,閻膏珍的金第納爾的重量標準直接摹倣羅馬金幣,而且必定在Nero(公元37—68年)使這一標準降低之前──否則,這不會符合西方商人的標準。但對大量羅馬和貴霜金幣重量的測定否定了這種看法。貴霜第納爾的重量是8克,在整個大貴霜時期一直保持不變,雖然所用黃金的純度有所降低。可是羅馬金幣的重量標準從它採用的時代起一直在有規則地、逐步地降低,但黃金的純度保持不變。Nero改革的結果之一是重量明顯地減少;但即使在Nero改革以前,金幣的標準重量也祇有7.6克,而祇有Augustus治期(公元前19—前12年)纔重達8克,這正是閻膏珍採用的標準。
今案:據此,不能僅按閻膏珍金第納爾的標準重量和羅馬金幣之間的關係來判斷閻膏珍及其他貴霜王的年代。
(5)如所周知,有一組丘就卻銅幣的頭像有羅馬式的桂冠,雖然倣自羅馬錢幣的正面頭像幾乎可以肯定得自Augustus或Tiberius的頭像,而不是Gaius、Claudius、Nero或任何其他羅馬皇帝的頭像。J. Allan認爲其反面圖案幾乎可以肯定是藉自Claudius的錢幣—Constantia坐在一張顯貴椅上,蓋Augustus錢幣反面沒有這樣的圖案。但是,丘就卻銅幣反面圖案與任何一種羅馬錢幣原型其實不太相似,其坐像顯然是東方式的,在顯貴椅上的坐姿也和羅馬或希臘人的坐姿不同。見諸丘就卻銅幣的顯貴椅與印度本地的明顯不同,無疑來自西方。這一圖案在丘就卻錢幣上出現不能作爲判斷年代的依據,因爲在Azes二世的一組銅幣的反面已經出現類似的圖案。丘就卻模仿Azes二世錢幣的可能性無法排除。
可是,這些丘就卻銅幣更類似於其羅馬原型。它們的設計和大小相同,甚至其重量也接近於羅馬銀第納爾。丘就卻的Augustus頭像銅幣的重量標準不是Augustus在位時首次發行的重量標準,而是在Flavia時期,羅馬帝國內部依然流通的已經磨損的Augustus第納爾的重量標準。也就是說,Augustus頭像很可能是丘就卻在Flavia時期摹倣的,當時Augustus和Tiberius的第納爾又一次變爲最適合流通的銀幣,因而成爲當時輸出的主要第納爾。
(6)一種巴勒維錢銘的引進:Gondphares的直接繼承者Abdagases的安息型錢幣有巴勒維銘文,這顯然是在摹倣Volagases一世(公元50—78年)。而Soter Megas在Taxila發行的錢幣緊跟在Abdagases之後,因而其年代一定遲於Volagases一世使用巴勒維錢銘的年代(公元58—70年)。
(7)漢佉兩體錢的重量標準有二:一爲15克,一爲3.5—4克,這與迦膩色迦的四德拉克瑪銅幣相一致,和Huvika早期銅四德拉克瑪的重量標準也相一致。由於迦膩色迦和Huvika的銅幣業已從和闐出土,這表明貴霜對於于闐的政治影響始於迦膩色迦,結束於Huvika早期。既然《後漢書·西域傳》稱:西域反叛,與漢絕交直至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這159年應該落在Huvika早期。
今案:僅僅據出土銅幣很難說明貴霜對于闐產生政治影響的程度和時間等情況。又,《後漢書·西域傳》原文是:“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這段話的主詞是天竺,既非貴霜,亦非于闐,也不是說整個西域。說者所引譯文有誤,其說不確。
(8)在Vāsudeva治期的某時,其金幣分爲兩種類型,其一類發展成貴霜-薩珊貨幣,另一類發展爲早期笈多王朝的錢幣。貴霜錢幣在Vsudeva之後分道揚鑣,說明貴霜是在Vāsudeva之後不太久被薩珊王朝推翻的。
Göbl對貴霜錢幣類型的分析表明,若干貴霜錢幣反面的類型乃派生自羅馬和亞歷山大原型,而迦膩色迦的錢幣類型主要派生自Hadrian治世打鑄的錢幣,Huvika的錢幣主要派生自Antonius Pius (公元138—161)治世打鑄的錢幣。由此可見迦膩色迦的即位應在公元二世紀前半葉。
今案:凡此皆有利於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二世紀上半葉說之證據。
5. A. K. Narain的公元103年說[81]
據《後漢書·西域傳》,疏勒王子臣磐在公元114—119年間曾爲質月氏,而當安國在公元119年去世時,月氏王出兵助他登上了疏勒王位。這位月氏王祇可能是迦膩色迦。臣磐應即《大唐西域記》卷一所記“質子”。《慈恩傳》卷二亦載:“有一小乘寺名沙落迦……我寺本漢天子兒作……”“沙落迦”即“疏勒”之異譯。在新疆發現的貴霜錢幣中屬於迦膩色迦者爲數最多,亦堪佐證。
《後漢書》沒有提到迦膩色迦之名不足爲怪,此書畢竟不是一部印度史,因而祇是在叙述疏勒歷史時附帶提及月氏王。班超死後,漢在西域的勢力迅速衰落。這一過程始於安帝,迦膩色迦的極盛時期正值東漢的混亂時期,故疏於記載。
既然公元114年(元初元年)迦膩色迦在位,銘文的證據又表明他的治期至少有23年,則不妨設公元114年爲他治期的中點,也就是說迦膩色迦的在位年代大約爲公元103—125年。《後漢書·西域傳》載:“順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臣磐遣使奉獻。”這表明臣磐於是年轉而效忠於漢,很可能是此前不久迦膩色迦去世。考慮到消息自貴霜傳至疏勒需要一段時間,因而不妨將迦膩色迦去位之年定在公元125年。
同樣,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103年也可以考定。蓋屬於閻膏珍時期的年代爲187年(或184年)的Khalatse銘文,應按元年始於公元前88年的Pahlava紀元計算,實際年代爲公元99年或公元96年,這一年未必是閻膏珍去位的年代,但由此可見將迦膩色迦即位之年定在公元103年左右是完全合理的。
據《後漢書·西域傳》等記載斷定大月氏征服大夏本土在公元前100年以後,丘就卻統一五翖侯開創貴霜王朝在公元25年以後,去世於公元80年左右。由於貴霜統治者的平均在位年數約22年,閻膏珍的統治應該結束於公元102—103年。也就是說,漢文史料也表明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103年說是可以接受的。
至於《三國志·魏書·明帝紀》所載太和三年(公元230年)十二月癸卯朝魏的貴霜王波調應是Vāsudeva二世而非一世。因爲前者發行錢幣上的銘文是豎寫的,而不像他之前諸王的婆羅謎錢銘那樣自左至右橫寫。這顯然是Vāsudeva二世受到中國書寫方式影響的緣故。這也說明公元103年說是正確的。因爲根據公元103年說,公元230年在位的不可能是Vāsudeva一世。
今案:以上是此說的核心判據,很遺憾難以成立。[82]在此基礎上,說者試圖對有關的銘文、錢幣、考古學資料涉及的問題作出解釋。其說多牽強處,茲不一一。
說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對上述年代說作了補充。[83]
說者強調《後漢書·西域傳》所記諸事均發生於公元100年之前。蓋傳文所據資料雖由班勇於公元125年編纂,但班勇所據均得自班超,後者於公元100年東歸。
今案:此說未安。即使在班超東歸洛陽(公元102年)至班勇西出柳中(公元123年)這一段時間內,東漢與西域完全斷絕關係(其實並非如此),也不能認爲班勇於安帝末所記全是班超時代西域事情。《後漢書·西域傳》有關貴霜諸事(例如丘就卻的情況)就包括許多班超以前的情況,班勇所記其實很可能包括公元100年以後所得者。說者之所以強調這一點,無非是因爲《後漢書·西域傳》中沒有提到迦膩色迦,而強調《後漢書》不載迦膩色迦表明他即位於公元100年以後。這對於他的公元103年說不能不說是一個障礙。班勇不可能不記錄他同時代發生的事情而記錄較遠的事件。[84]
說者以爲,班超死後,東漢在西域勢力迅速衰落,故有關記事疏漏甚多,因而記臣磐事情而不載迦膩色迦之名。
今案:《後漢書·西域傳》不載迦膩色迦事蹟,可知該王即位於公元125年之後。既然臣磐事情係班勇所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則不能認爲不載月氏王之名乃因疏漏。
說者又以爲有關臣磐的一則記載並非班勇所記,而是范曄所採用的較後資料。若係班勇所記,則有關月氏王名必定會提及。而由於班超以後一段時間東漢和西域斷絕了聯繫,因此范曄所用資料中不見有關月氏王的姓名。
今案:此說未安。一則完全沒有證據認爲有關臣磐的記載不是“班勇所記”。“班勇所記”亦未必提及月氏王之名。又,月氏遣兵立臣磐爲疏勒王,《資治通鑒·漢紀四二》繫於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事在班勇出屯柳中前四年,故沒有理由認爲其事不在“班勇所記”之中。又,《後漢書·班勇傳》稱:“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知班勇在延光末曾與疏勒直接發生關係。臣磐之事,不可能不知道。又,《後漢書·西域傳》稱“班勇所記”在“安帝末”(公元125年),可能是指其主要部分的完成時間,未必此後別無追補。這就是說,即使臣磐之事直到順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臣磐來朝始爲東漢所知,也完全有可能包括在“班勇所記”之中。
6. J. M. Rosenfield 的公元 110 - 115 年說[85]
馬土臘無疑一直是貴霜在恒河流域的主要統治中心。通過對馬土臘派雕塑的類型學和肖像學研究,以及對作爲捐款人的貴霜名流及其許願銘文序列的研究,證實Vāsudeva一世的治期結束以後在馬土臘曾使用了第二個貴霜紀元。這表明迦膩色迦的治期大約開始於公元110—115年。
Vāsudeva一世最後一篇銘文(迦膩色迦紀元98年)之後不久,開始了一個新的年代系列。馬土臘流派的作品至少延續至這一紀元的第57年。這些作品類型表現出一種清楚的朝公元五世紀笈多模式發展的趨勢。
繼Vāsudeva一世即位的迦膩色迦王的歷史真實性業已進一步得到證明。根據類型學和肖像學的證據,大量的雕刻(其中若干刻有承認迦膩色迦王權威的銘文)不可能被斷在公元二世紀。他們是直接從那些承認Vāsudeva權威、而年代爲迦膩色迦紀元的80—90年代的作品發展而來。這後一位迦膩色迦的名字出現在年代爲5—17年的銘文上。有關他的錢幣證據很久以前就被離析出來。
在Doāb和中印度的印度斯基泰政權延續到第57年。此後,紀年記錄似乎結束了。這位迦膩色迦以後,祇有零散的王號出現。
根據錢幣和往世書的證據,在Padmāvatī、馬土臘和VidiŚā土著的Nāga王朝興起,取代了在這地區的印度斯基泰人,産生了七個或更多的國王,直到他們自己被笈多征服,如沙摩陀羅笈多的阿拉哈巴德銘文所載。這也許是紀年銘文序列中斷的原因。
同樣,據Bijāyagadh銘文,和後期貴霜時期的Bayānā一樣,Yaudheya人似乎長驅進入了恒河上游平原。
結合《魏略》的記載,印度斯基泰霸權的殘餘在恒河上游平原似乎一直保持到三世紀後半葉。笈多帝國興起以前三個世紀這一地區歷史的大輪廓可以勾勒出來,而印度本土的貴霜史可概括如下:
約公元50年,征服Taxila和旁遮普。
約公元100年,Doāb的貴霜政權鞏固,並南向擴張至Sārnāth。
約公元110—115年,迦膩色迦即位。
約公元130—150年,王朝受到外來壓力,處於困難時期。
約公元210—215年,在Vāsudeva治期之末,王朝分裂爲兩部,統治中心一在Balkh,一在KapiŚā甚或白沙瓦。
約公元220—260年,薩珊入侵。
約公元250年,失去東旁遮普和Delhi周圍直至Yaudheyas地區。
約公元275年,失去恒河上游地區,包括馬土臘,直至Padmāvatī的 Nāgas。
約公元300年,薩珊佔領Bactria、Badaskhān、KapiŚā和喀布爾上游。
約公元358年,沙普爾二世征服喀布爾河下游、乾陀羅、Taxila。
公元350年,印度-斯基泰政權的全部痕跡在北、中印度消失。
公元400年,在西印度(馬爾瓦和GurjaradeŚa)消失。
既然Vāsudeva一世治期結束後第二個貴霜紀元中止於57年(等於迦膩色迦紀元157年),貴霜丟失恒河上游在公元275年左右,則迦膩色迦紀元之元年應該落在公元110—115年之間。
今案:此說的主要依據是馬土臘貴霜時期神殿的雕塑作品,但無論類型學還是肖像學的證據對於斷代均有較大的誤差。
7. E. Zürcher的公元二世紀四十年代說[86]
據《僧伽羅刹所集經》,《道地經》(Yogācārabh ūmi),僧伽羅刹(Sangharaka)所集也。“僧伽羅刹者,須賴國人也,佛去世後七百年生此國。出家學道,遊教諸邦至揵陀越土,甄陀罽貳王師焉。”而據《高僧傳》,《道地經》係安世高所譯。世高自公元148年入華,死於公元170年左右。如果考慮到他赴華之前可能在中亞逗留若干年,則不管怎樣《道地經》可能纂成於公元140年前,蓋此經可能由世高自西域攜入中國譯出(也可能是他在離開時已經熟記)。更重要的是,《道地經》屬於Kashmir的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而說一切有部的鼻祖中,僧伽羅刹緊接在Vasumitra(世友)之後,而Vasumitra又與迦膩色迦治期舉行的Kashmir結集有關。這一切都使“甄陀罽貳王師”僧伽羅刹的年代在二世紀上半葉。
今案:據考證,安世高離開安息在公元135年左右,入華之年爲公元148年,在西域遊歷十餘年。[87]果然,僧伽羅刹集《道地經》當在公元135年之前。而迦膩色迦師事僧伽羅刹即使是事實,也難以據此推斷其即位年代。蓋不能排除事在迦膩色迦即位之前。至於世友之年代,衆說紛紜,亦難落實。
8. H. Falk的127年說[88]
印度人Sphujiddhuaja於公元269年所撰《希臘聖誕節》(Yavanajataka)一書中稱:“當時計算塞種紀元的年代可在貴霜紀元(Kushan Era)的年代上加149年得出。”說者據以爲:貴霜紀元應始於塞種紀元(其元年爲公元78年)之後149年,具體而言爲公元227年。但這一特定年代必定屬於貴霜紀元的第二世紀,既然貴霜紀元在銘文上出現時,往往省略掉百位數,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無疑是公元127年。
今案:此說的基礎在於以迦膩色迦紀元紀年的貴霜銘文分佈於2個世紀,而屬於第二世紀的銘文的紀年省去了百位數。但並沒有證據表明迦膩色迦創建了一個新的紀元,其人繼承父祖紀元的可能性無法排除。更何況,沒有理由認爲這227年屬於迦膩色迦紀元的第2世紀,甚至沒有理由指此處所謂“貴霜紀元”便是迦膩色迦紀元。
(四)對公元二世紀說的幾種不同意見
1. H. C. Raychaudhuri對公元二世紀說的異議[89]
(1)迦膩色迦及其繼承人銘文所見紀年數表明迦膩色迦創建了一個紀元。但是,我們並不知道西北印度曾經流行過一個元年落在公元二世紀的紀元。
今案:迦膩色迦沿用了其父祖使用過的紀元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2)Sui Vihar銘文表明迦膩色迦的領土至少包括印度河下游的一部分。但是,Rudradāman的Junāgadh銘文表明這位大州長的征服範圍達到Sindhu-Sauvīra(據往世書和比魯尼,包括木爾坦),甚至沿Sutlej河抵達Yaudheyas的居地。Rudradāman無疑於公元130—150年在位,他的大州長也不是受封於任何人的。如果迦膩色迦在位於第二世紀中葉,那末他對印度河下游Sui Vihar地區的統治和Rudradāman在同一時期的統治顯然是矛盾的。
今案:Rudradāman可能是役屬貴霜的印度土著統治者,承認迦膩色迦的宗主權。反過來,迦膩色迦給予Rudradāman較大的自主權。換言之,Rudradāman和迦膩色迦之間並不存在說者所謂不可調和的矛盾。
2. S. Chattopadhyaya 對公元二世紀說的異議[90]
Ghirshman的公元144年說立足於貝格拉姆的發掘。他指出貴霜遺物中年代最晚者屬於迦膩色迦組最後一位統治者Vāsudeva,並假定這座城市在公元241和250年間毀於薩珊王沙普爾一世之手,而Vāsudeva之末年落在這段時間內。Vāsudeva在位年代爲迦膩色迦紀元第74—98年,因而迦膩色迦紀元之元年可能是公元144年。其說未安。
一則,貝格拉姆出土的錢幣並不屬於Vāsudeva一世。因爲Vāsudeva一世銘文的出處表明他的領土限於北方邦,而以馬土臘爲中心,而Ghirshman歸屬於他的錢幣並不是在北方邦發現的。貝格拉姆出土的錢幣無疑是另一位Vāsudeva,他就是公元230年遣使曹魏的波調。他這次朝魏顯然是爲了求得援助以對抗薩珊人的入侵。
二則,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貝格拉姆是毀於沙普爾一世之手。因此任何立足於這一點的Vāsudeva和沙普爾一世同時代說都是經不起推敲的。
多數西方學者認爲迦膩色迦並不是即位於公元78年而是在公元120至134年之間,Mashall說堪爲代表:丘就卻在公元50年左右將帕提亞人逐出喀布爾河谷,當時他約50—60歲。其子閻膏珍征服了乾陀羅、旁遮普和信德,在公元78年左右繼父位,其治期也許持續至公元二世紀之初。此後,直至迦膩色迦即位有一段約20年的間隙。這段時間內貴霜似乎有某種分裂跡象,可能有一個以上副王以Soter Megas名義爲貴霜君主繼續統治印度。此外,尚有若干重要證據表明迦膩色迦不是塞種紀元的創建者:
(1)公元73年至102年正是班超在西域活動的時期,東漢勢力強盛,因此不可能出現如玄奘所說河西諸國“畏威送質”的局面。
(2)《後漢書·西域傳》祇提到丘就卻和閻膏珍,但未及迦膩色迦。由此可見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125年左右。然而其說可議:公元90年,月氏遣使求漢公主,這位月氏王應該是迦膩色迦。蓋丘就卻死時年已八十餘,其子閻膏珍即位時年紀必然不小,不可能有求婚之舉。再者,閻膏珍在公元一世紀80年代已不可能在位。因此,求婚的月氏王必定是迦膩色迦,否則便是閻膏珍的副王之一。正如年代爲136年的Taxila銘文所表明的那樣。
玄奘所載“河西蕃維,畏威送質”,據《慈恩傳》可知質子其實祇有一人,並非許多。《大唐西域記》所謂“諸質子”,恐怕是一種疏忽。可是,迦膩色迦在中亞的統治是短暫的,有關迦膩色迦之死的傳說可以證明這一點。顯然他是被班超打敗的。但這次失敗發生在公元90年以後,這似乎直接證實了玄奘關於迦膩色迦在乾陀羅的統治開始之後向中亞擴張的記述。
迦膩色迦即位第2年的銘文發現於Kosam,第三年的發現於Sārnāth。而Zeda和Sui Vihar這兩篇最早表示迦膩色迦與西北印度關係的銘文的年代都是11年,這可能表示迦膩色迦在這一年或稍前征服了旁遮普和信德。又,他的年代爲21年的Kurram銘文是表明他統治印度河以西地區的最早證據。這些銘文證明迦膩色迦在北方邦即位,後來纔征服旁遮普和西北邊陲諸省。顯然他原來是閻膏珍的總督,在公元78年宣告獨立。而正如根據年代爲136年的Taxila銀冊銘文所推知的。當時有另一總督在Taxila宣告獨立,並發行Soter Megas錢幣。既然迦膩色迦統治乾陀羅之年不可能比公元99年早太多,中國史籍關於班超與貴霜之間鬭爭和玄奘的有關記載並非不可能調和。
迦膩色迦組統治者的銘文表明迦膩色迦是一個紀元的創建者,但是並沒有證據表明有什麽紀元開始於公元120年和134年之間。但也許會有人說,確實迦膩色迦曾在公元120—134年間某時建元,祇是這一紀元後來廢棄了,因此必須找出一些其他證據來確定迦膩色迦的年代。Rudradāman的Junāgadh銘文提供了這樣的證據:公元130年的Andhau銘文表明當時Rudradāman與其祖Caana聯合統治,而Junāgadh銘文表明他在公元150年之前征服了北印度和南印度。值得注意的是這篇銘文並未提到貴霜,祇是說他征服了Sindhu-Sauvīra地區(Multan和Jharavar)和尤德亞人。尤德亞人居住在Sutlej河畔的Johiyabar之地。這些地區都是貴霜的領土,因而銘文不提及貴霜的唯一解釋是,當時貴霜人的權力已經喪失,Rudradāman並沒有從貴霜人那裏奪得任何土地。
據悉,有6年時間沒有貴霜銘文,即從迦膩色迦紀元61至66年。換言之,在這段時間內貴霜已一定程度喪失權力。這61—66年必定落在公元130—150年之間,當時Rudradāman征服了北印度,這與公元120—134年說顯然不符,而公元78年說正堪接受。
如前所述,公元79在位的貴霜統治者既不屬於丘就卻組也不屬於迦膩色迦,這表明當時出現貴霜權力的窺伺者。而粉碎這些窺伺者後,迦膩色迦成了最高統治者。
要之,如果假定迦膩色迦於公元125年以後即位,Rudradāman對Sindhu-Sauvīra的統治與迦膩色迦的Mohenjo Daro和Sui Vihar銘文的記載就不可調和,蓋後者表明迦膩色迦控制着同一地區。另外,Rudradāman征服北印度時,必定是貴霜政權衰落之際和尤德亞人再次宣告獨立之時。最後,迦膩色迦是一個紀元的創建者,但並不知道有什麽紀元開始於公元二世紀。
今案:說者以爲貝格拉姆未必毀於沙普爾一世之手,該處出土時代最晚的貴霜的錢幣未必是Vāsudeva一世的云云,無非是出諸構建公元78年說的需要,並未舉出有力的反證。
說者對包括《大唐西域記》在內漢文史料的理解和詮釋是不可接受的,建立於其上的觀點因而也是是站不住的。尤其應該指出:西域諸國同時役屬東西方強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就是所謂“兩屬”現象。[91]
說者認爲Rudradāman和迦膩色迦不可能同時代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
至於說者關於不存在一個開始於公元二世紀的紀元的看法是則是正確的。但是,迦膩色迦沒有開創一個始於公元二世紀的紀元,並不等於迦膩色迦不可能即位於公元二世紀。
3. A. K. Narain對其他公元二世紀說的批判[92]
如果認爲迦膩色迦一世的元年在公元二世紀的三十或五十年代,那末Vāsudeva一世應於公元244(或公元220—238年)在位,而Vāsudeva二世在公元275年依然在位,即使給迦膩色迦三世的治期留出最小的餘地。其時笈多人已經在華氏城和阿逾陀開始他們的統治生涯。即使無視笈多人早期的征服直抵鉢羅耶伽,在公元350年左右,沙摩陀羅笈多已經統治着包括馬土臘在內的北印度則毋庸置疑。這意味着在最後一位貴霜王(當然,按某些學者的意見,存在一位Vāsudeva三世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和沙摩陀羅笈多之間至多間隔75年。在這段間隙裏,必須安排北方邦的Magdhas人。從沙摩陀羅笈多的Allahabad銘文可以知道,他不僅打敗了北方邦的那伽人和其他家族,而且還打敗了在貴霜之後獨立過一段時間的尤德亞人、馬臘婆人、Ārjunāyanas人、Kuindas人和Madras等。其中大多數的存在可以從《往世書》、銘文和錢幣得到證實。他們的年代最晚在貴霜和沙摩陀羅笈多之間是毋庸置疑的。同時也無法否認在貴霜帝國的東部,貴霜人的繼承者甚至早就被旃陀羅笈多一世摧毀。如果一定要認爲Vāsudeva二世在公元275年在位,這一切簡直無從安排,這正是多數古代印度史學者相信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爲公元78年的緣故。
公元120—128或公元144年說的另一問題是不能與Rudradāman的年代調和。沒有證據表明Rudradāman曾役屬於貴霜人。
今案:貴霜帝國崩潰開始以後,在原帝國版圖內本來役屬於貴霜的各族紛紛獨立,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政權,這些政權在不長的時期內被沙摩陀羅笈多逐個擊滅是完全可能的。一則,以上各種人建立的政權可能同時並存而不是相繼疊興。《往世書》乃至錢銘等所見同一政權不同名字的統治者也可能是各據一方,互不統屬的,因而並不存在前後繼承關係。當然,也可能是篡亂疊生以至治期短促。笈多人能一舉摧毀之,正說明這些小政權極不鞏固。
4. D. C. Sircar對公元二世紀說(公元 125 年說)的批判[93]
(1)西印度的塞種大州長Rudradāman是一個獨立的統治者,他的Junāgadh銘文表明Ākara於公元150年成爲他的一部分領土,而VidiŚā附近的Sanchi銘文(屬於Vasika,年代爲迦膩色迦紀元第28年)表明在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的治期貴霜人擁有東馬爾瓦。如果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爲公元125年,那末迦膩色迦、Vasika和Rudradāman同時代。akarīdharavarman的Sanchi和Eran銘文,以及沙摩陀羅笈多的錢幣與Eran和Allahabad銘文,旃陀羅笈多二世的Sanchi和Udayagiri銘文,都表明塞種人在二世紀中葉以後一直統治着東馬爾瓦。因而公元125年說不能成立。
(2)統治東Uttar Pradesh的KauŚāmbī諸王之年代肯定在迦膩色迦一世之後、笈多之前,其年代在某個紀元的51年和139年之間,這個紀元祇可能是迦膩色迦紀元。既然這一地區按照任何紀元紀年的最早記錄都是迦膩色迦一世的,而在公元最初的幾個世紀該地區沒有使用任何其他紀元的國王進行統治,那就沒有理由認爲在上述時期內這個地區使用過其他紀元。最近發現的Kailvan銘文,得自Bihar的Patna區,年代爲108年,雖然也是同一個紀元,但其若干婆羅門字母的形式早於odāsa和迦膩色迦一世。因而即使接受上述古文書證據,也很難將Kailvan銘文安排在公元二世紀以後,因而迦膩色迦紀元(年代爲108年的銘文必定按此紀年)應始於公元一世紀。
今案:其說未安。KauŚāmbī諸王記錄所用紀元應爲塞種紀元。諸王臣屬於貴霜,但仍有使用其紀元之自由。至於Rudradāman的問題,已見前述。
5. E. Zürcher對A. K. Narain公元103年說的批判[94]
據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可見質子住處並不是僅沙落迦一處。臣磐居住在Jālandhara附近某處不是不可能的。雖然《後漢書·西域傳》談到他與月氏王的友誼,因而寧可認爲他居住在Puruapura的宮廷中,但沒有理由假定他是像迦膩色迦的質子們一樣,“東居印度諸國,夏還伽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其餘住處的名稱不知,沙落迦僅僅由慧立提到,而非玄奘本人提到。慧立所述應該是可信的,但他同時還載沙落迦“相傳云是昔漢天子質於此時作也”(卷二)。玄奘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河西”不應包括疏勒,知亦以爲質子來自中國。玄奘的故事可能是由“至那僕底”這一地名引申而得。至於臣磐於公元127年朝漢,非不親貴霜,實畏漢也。與班勇在西域取勝有關云云。
今案:公元103年說是有問題,但說者的論證亦有可議之處。例如此處《大唐西域記》所謂“河西”當指西域無疑。“沙落迦”一名顯與疏勒無關,等等。
6. B. Kumar對公元128-129年說批判[95]
S. Konow斷定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125年以後,蓋其名不見載於《後漢書·西域傳》,而結合Van Wijk根據Zeda和Und銘文進行天文學計算,可知迦膩色迦的元年應在公元128-129年。然其說未安。一則不能因爲中國史籍不提到迦膩色迦的名字而認爲他即位於公元125年以後,因爲中國史籍在記述月氏人在西域活動時從未特別提到月氏王名。
另外,年代爲11年的Sui Vihar銘文清楚地表明:在公元139—140年,印度河下游Bahawalpur在迦膩色迦治下。若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128-129年,則該地直至公元156-157年仍然在貴霜治下,因爲迦膩色迦之後Vasika和Huvika治下的貴霜王國並無衰落的蹟像。但是,Junāgadh銘文所記Rudradāman作爲一個實際上獨立的統治者在150年左右統治着Sauvira(包括Multan在內),並征服了居住在Bahawalpur附近Rajasthan的尤德亞人。這與Sui Vihar銘文的記載是矛盾的。
同樣,貴霜對Sanchi的統治與Junāgadh銘文所見Rudradāman對Ākara(東馬爾瓦)和Avanti(西馬爾瓦)的統治也是不可調和的。再者,公元二世紀並不存在著名的紀元,但銘文表明迦膩色迦確實創造了一個紀元。
今案:既然迦膩色迦繼承了閻膏珍的王位,貴霜又在迦膩色迦治期臻於極盛,《後漢書·西域傳》記載了迦膩色迦之前的丘就卻、閻膏珍,而沒有記載迦膩色迦本人,又有證據表明該傳所依據的資料年代在公元125年之前,迦膩色迦即位於這一年之後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
Rudradāman和迦膩色迦的關係,如前所述,祇要明白貴霜統治中亞和印度的方式就不難理解。
四、公元三世紀諸說
公元三世紀諸說中,以R. G. & D. R. Bhandarkar的公元278年說最早[96],此後遂有R. C. Majumdar的公元248年說。[97]後說幾乎沒有支持者,茲略而不論。[98]至於前說,在此祇介紹R. G. & D.R. Bhandarkar之後的一些說法。蓋說者認爲首創者的結論是正確的,但論述業已過時。
(一)公元278年說
1. V. Lukonin的公元278年說[99]
此說本質上也是塞種紀元說:迦膩色迦紀元其實是省略了百位數2的塞種紀元。
至於沙普爾一世的Kaba-i-Zardusht銘文(公元262年)在臚列沙普爾一世統治的地區時提到“直至白沙瓦的Kuāāhr”,不過表明沙普爾對以前曾役屬貴霜的地區提出的要求。既然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沙普爾一世在位時使用過“貴霜王”以及類似稱號,就不能認爲貴霜帝國亡於公元262年以前。
沙普爾一世在東方戰役(公元245和248年之間)之後,設置了“Sakastene、Turestan和Indus直至海岸”的攝政官。這一職位一直存在至四世紀後半葉。不管沙普爾一世的戰士是否到達白沙瓦,上述攝政官所轄的土地界定了當時薩珊波斯的東境。
Vāsudeva末年,即迦膩色迦紀元第98年(公元376年),應是貴霜-薩珊錢幣發行年代之上限。
今案:其說未安。一則,即使直至公元262年貴霜祇是臣服而非亡於薩珊,KuāŚāhr不是薩珊人所置,而是指臣服薩珊的貴霜王,迦膩色迦紀元也不可能始於公元278年。
二則,貴霜-薩珊錢幣的絕對年代尚未確定,但其上限肯定不在公元四世紀七十年代末。退一步說,即使貴霜-薩珊錢幣最初發行的時間爲公元四世紀七十年代,也無助於公元278年說成立。因爲發行這種錢幣不過表明薩珊對原貴霜領土統治的強化,不能認爲只有發行錢幣纔表明薩珊對貴霜的征服。
要之,此說旨在說明薩珊滅亡貴霜的時間與278年說不悖,如此而已。
2. E. Zeymal的公元 278 年說[100]
(1)貴霜帝國被薩珊征服,最可靠的證據是貴霜-薩珊錢幣。這種錢幣最早發行的年代與公元278年說並不矛盾。
(2)貴霜帝國的部分領土被笈多征服,唯一直接的證據是按笈多紀元紀年的笈多銘文,如旃陀羅笈多二世的馬土臘銘文(笈多紀元第6年 =公元380/381年)、Udayagiri銘文(笈多紀元第82年 =公元401/402年)、Sanchi銘文(笈多紀元第93年 = 412/413年)。有關記載均可與公元278年說協調。
旃陀羅笈多二世時代撰寫的Allahabad銘文,詳細記錄了沙摩陀羅笈多的功蹟(約公元350年),也在臚列邊境地區諸民族和統治者時提到了貴霜王的稱號devaputraāhi。
(3)前貴霜事件的年代無助亦無妨於公元278年說成立,因爲這些事件的年代均取決於貴霜的絕對年代。
(4)不能認爲公元3—4世紀在貴霜領土上存在的若干小國或小王朝是公元278年說的反證,因爲這些統治者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臣服貴霜中央政權。例如:閻膏珍的州長Zeionises-Jihonika(塞種紀元第191年 = 公元269年)也發行自己的銀幣和銅幣。
(5)如果迦膩色迦紀元之元年爲公元278年,則可以說明爲何塞種紀元196和211年之間(公元274—289年)和218—270年之間(公元296—348年)的西部州長不使用“大州長”這一稱號。這正是因爲這兩個時間內貴霜王權力臻於極盛。當然,這與其看作公元278年說的證據,不如認爲是該說的推論。
今案:其說未安。
一則,貴霜-薩珊錢幣的發行年代不能看作貴霜王朝滅亡的年代。
二則,笈多王朝的銘文提到原貴霜王朝的部分領土被幷入笈多帝國並不表明貴霜王朝一直存在至旃陀羅笈多二世即位之時。
三則,沙摩陀羅笈多的Allahabad銘文提到貴霜人的稱號並不表明公元350年左右貴霜王朝依舊存在。即使這一稱號在當時依舊爲貴霜人使用,也至多表明貴霜人的殘餘勢力依舊存在,與迦膩色迦的年代毫不相干。
四則,說者定丘就卻的年代爲公元178—238年,閻膏珍的年代爲公元238—278年,完全無視中國史籍關於貴霜起源和建國的記載。
五則,在公元三至四世紀,原貴霜領土上小國林立,表明統一的貴霜已經不復存在。這些小國是否役屬貴霜無法證明。
六則,在塞種紀元196—211年以及218—270年之間,西部州長不使用“大州長”這一稱號與貴霜無關。
(二)D. C. Sircar對公元三世紀說的批判[101]
(1)Vāsudeva統治馬土臘直至迦膩色迦紀元第98年,如果該紀元即公元248年的Traikūakas紀元,則Vāsudeva統治馬土臘至公元346年,而馬土臘最早的笈多銘文是旃陀羅笈多二世的年代爲笈多紀元第61年的銘文,該銘文的實際年代爲公元380年。雖然馬土臘是旃陀羅笈多二世之父沙摩陀羅笈多征服該處的Nāga統治者後奪取的。往世書的記載表明在貴霜與笈多之間,馬土臘的Nāga統治者不少於七位。
(2)笈多征服之前Nāga朝在馬土臘地區相當長的治期可能表明Vāsudeva的年代大大早於公元四世紀中葉。對此,應該注意到,沙摩陀羅笈多的Allahabad石柱銘文稱Āryāvartta的若干Nāga王爲被笈多君主消滅的敵人,而僅稱同時的貴霜王即Daivaputra-Shāhī-Shāhānushāhī爲他的盟友。
(3)據《于闐國授記》,迦膩色迦是于闐王Vijayakīrti(公元二世紀)的同時代人。而其繼承人Huvika是佛教徒哲學家Nāgārjuna的同時代人,因而與 Sātavāhana王亦同時代,這位Sātavāhana在位年代不可能遲於公元二世紀。
(4)《高僧傳》載安世高譯僧伽羅刹所集《道地經》,而迦膩色迦曾師事羅刹,這位迦膩色迦必定在位於公元170年以前很久。
(5)如果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248年,就很難找到波調的位置。據《三國志·明帝紀》,波調應即Vāsudeva在公元230年遣使朝魏。
(6)後貴霜最遲在公元三世紀臣服於薩珊,也和三世紀中葉迦膩色迦即位是無法協調的。
今案:公元248年說尚且不能成立,更無論公元278年說。
五、後記
迦膩色迦年代經過一個多世紀不間斷的研究,可能性已經臚列殆盡。由於自忖很難再有與衆不同的見解,我一開始就決定就這一問題作一綜述,於是閱讀有關論文,逐篇摘要。
忽一日,我覺得自己似乎明白迦膩色迦年代是怎麽一回事了,閱讀旨趣隨即轉移,原來的計劃也就停頓下來。當自己的論文《迦膩色迦的年代》完成後,不知何故,再也提不起寫綜述的勁頭了。
已有七八萬字,本來打算一刪了之,後來考慮到這雖然祇是一個半成品,但關於迦膩色迦年代之我見可以說脫胎於這一組綜述。這似乎說明這些帶有隨機性的摘要有着某種內在聯繫,將他們放在一起發表,也就有了某種合理性,至少可以作爲我的迦膩色迦年代說的背景讀。
我在各段摘要之後,加上了一些按語。當時對於迦膩色迦的年代尚胸無定見,這些按語不免和《迦膩色迦的年代》一文不盡符合。之所以沒有在最後加以統一,是覺得保留一些自己認識這個問題過程的印迹也是很有趣的。
縮略語表
ABORI. 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AIU. R. C. Majumdar, ed., The Age of Imperial Unity, Bombay,1953.
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CHI. E. J. Rapso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Delhi,1922.
EHNI. S. Chattopadhyaya, Early History of North India, Calcatta,1958.
EI. Epigraphia India.
IA. The Indian Antiquary.
IHQ.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JA. Journal Asiatique.
JBBRAS. Journal of the Bombay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BORS. Journal of the Bihar and Orissa Research Society.
JIH.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C. Numismatic Chronicle.
OZ. Ostasiatische Zeitschaft.
PDK. A. L. Basham, ed.,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ka, Leiden,1968.
PHAI. H. C. Raychaudhuri, Politic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23, 1953.
SRAA.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 Kamakura.
WZKM.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Wien).
[1] E. Thomas,“Bactrian Coins and Indian Dales”, The Academy 26 (1874), pp.686-687.
[2] A. Cunningham,“Indo-Scythians”, Archea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Four Reportsmade during the Years 1862-63-64-65, vol. II. Simla: Printed at the Government Central Press, 1871, 43-82, esp. 68, note.
[3] A. Cunningham,“Coins of the Kushâns, or Great Yue-ti”, NC Series 3, 12 (1892),40-82, esp. 44.
[4] S. Lévi, “Notes sur les Indo-Scythes, I. Les contes”, JA 9e série, tome VIII,Paris 1896, pp. 444-484; “II. Les textes historiques”, Journal Asiatique 9e série,tome IX, 1897, pp. 5-26; “III. Saint Thomas, Gondopharès et Mazdeo”, JA 9e série, tome IX, 1897, pp. 27-42, esp. p. 42.
[5] 注5所引R. D. Banerji文, esp. 67.
[7] J. Marshall, “The Date of Kanishka”, JRAS (1914), pp. 973-986.
[8] 注5所引文, esp. 67.
[9] K. P. Jayaswai, “The Statue of Wema Kadphises and Kushan Chronology”,JBORS, vol. 6 (1920), pp. 12-22, esp. 21; “Problems of Saka-Satavahana History”, JBORS, vol. 16 (1930), pp. 227-316, esp. 240.
[10] CHI, p. 570.
[11]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 1933, pp. 494-502.
[12] J. F. Fleet, “A hitherto unrecognised Kushan king”, JRAS (1903), pp. 325-334; “St. Thomas and Gondophernes”, JRAS (1905), pp. 223-236; “The Date in the Takht-i-Bahi Inscription”, JRAS (1906), pp. 706-711; “The Traditional Date of Kanishka”, JRAS (1906), pp. 979-992; “The Early Use of the Era of B.C.58”, JRAS (1907), pp. 169-172; “Moga, Maues and Vonones”, JRAS (1907), pp.1013-1040;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reek Uncial and Cursive Characters intoIndia”, JRAS (1908), pp. 177-186; “The Question of Kanishka”, JRAS (1913),pp. 95-107; “The Date of Kanishka”, JRAS (1913), pp. 913-920 and 965-1011;“Review of E. J. Rapson’s Ancient Indi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First Century A.D”, JRAS (1914), pp. 795-799; “The Date of Kanishka”, JRAS (1914), pp. 987-992; “The Taxila Inscription of the Year 136”, JRAS (1914), pp. 992-999; “The Taxila Scroll of the Year 136”, JRAS 1915, pp. 314-318.
[13] O. Franke, Beiträge aus chinesischen Quellen zur Kenntnis der Türk-völker und Skythen Zentralasiens, Abhandlungen Kön. Prenss, Akad. d. Wissenschaften,Berlin 1904, Phil.-hist. Abhandl. I, p. 99.
[14] H. Lüders, 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 Kön. Preuss, Turfan-Expeditionen,Kleinere Sanskrit Texte, Heft I. Berlin 1911, p. 11.
[15] J. Kennedy, “The Date of Kanishka”, JRAS (1913), pp. 920-939.
[16] Barnett, “The Date of Kanishka”, JRAS (1913), pp. 942-945.
[17] PHAI (1953), pp. 465-467.
[18] D. C. Sircar, “The Kushāas”, In AIU, pp. 136-153, esp. 144.
[20] 今案:此說未安,見余太山《關於“閻膏珍”》,《絲瓷之路——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III,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3—31頁。
[21] E. J. Rapson, Indian Coins, Strassbueg, 1898, p. 18; E. J. Rapson, “Gandhara Sculptures (Some Recent Acquisitions), by J. Burgess, C. I. E., etc”, JRAS 1900, pp.388-390. 此說認爲迦膩色迦組貴霜統治者所用紀元可能是Vikrama紀元,祇是所見紀年數省去了百位數1。
[22] 主要有A. Cunningham, Book of Indian Eras with Tables for Calculating Indian Dates(Calcutta, 1883, p. 42)的80年說。他主張的迦膩色迦紀元實卽塞琉古紀元說也屬於這一類,此說主要依據漢文史料。
[23] A. M. Boyer, “Lʼépoque de Kanika”, JA 9e srie, tome 15, Paris, 1900, pp. 526-579, esp. 578-579.
[25] J. Fergusson, “On the Saka, Samvat and Gupta Evas”, JRAS, New Series, vol,XII, 1880, pp. 259-285.
[27] H. Oldenberg, “Zwei Aufsätze zur altindischen Chronologie und Literaturgeschichte, 1. Zur Frage nach der Aera des Kaika”, Nachrichten von der Kön. Ger.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Phil.-hist Klasse, 1911, pp. 427-441,esp. 441.
[28] 以下諸家堪爲代表:注5所引R. D. Banerji文; F. W. Thomas, “The Date of Kanika”, JRAS 1913, pp. 627-650, 1011-1042; C. Waddell, “The Date of Kanika.” JRAS 1913, pp. 945-952; CHI, pp. 582-585; H. C. Ghosh, “The Date of Kanika”, IHQ 4 (1928), pp. 760-764; IHQ 5 (1929), pp. 49-80; L. Bachhofer, “Die Ära Kanishkas”, OZ, Neue Folge 4 (1927-28), pp. 21-43; “Zurra Kanika”,OZ 1930, pp. 10-15; PHAI (1953), pp. 458-479. (PHAI (1923), pp. 245-256); J.E. Van Lohuizen-de Leeuw, The “Scythian” Period, Leiden: E. J. Brill, 1949, pp.1-65, 381-382, 387; 注18所引D. C. Sircar文, esp. 141-149; A. L. Basham, “The Succession of the Line of Kanika”, BSOAS 20 (1957), pp. 77-88; EHNI, pp. 74-81, esp. 80-81, 等等。其中,H. C. Raychaudhuri, J. E. Van Lohuizen-de Leeuw, D.C. Sircar等人的假說,A. K. Narain, “The Date of Kanika”, In PDK, pp. 206-239, 有批評,可參看。
[29] 詳見 PDK。
[30] PHAI (1953), 1953, pp. 458-479.
[31] 注20所引余太山文。
[32] R. E. Emmerick, 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 London, 1967, pp. 46-47.
[33] EHNI, pp. 74-81, esp. 80-81.
[34] S. Shrava, The Dated Kushāa Inscriptions, Pranava Prakashan, New Delhi, 1993,No. 211. 案:一說Panjtar銘文按迦膩色迦紀元紀年。
[35] S. Konow, “Kalawan Copper-plate Inscription of the Year 134”, JRAS 1932, pp.949-965.
[36] S. Konow, “Taxila Inscription of the Year 136”, EI 14 (1917-18), pp. 284-295.
[37] 注28所引J. E. Van Lohuizen-de Leeuw書, pp. 1-65, 361-387.
[38] W. E. van Wijk, “The Eras in the Indian Kharohī Inscriptions, Calculation of the Kharohī Dates”, Acta Orientalia 3 (1925), pp. 79-91.
[39] 注38所引W. E. van Wijk文。
[40] J. E. Van Lohuizen, “The Date of Kanika and Some Recently Published Images”, In PDK, pp. 126-133.
[41] 注28所引A. L. Basham文, esp. 85-87; A. L. Basham, “Introduction”, In PDK,pp. ix-xiv, esp. xi-xii.
[42] P. H. L. Eggermont, “The Purāa Source of Merutunga’s List of Kings and the Arrival of the Śakas in India”, In PDK, pp. 67-86.
[43]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 163頁,注 47。
[44] A. H. Dani, “The Date of Kanika (Palaeographical Evidence)”, In PDK, pp.57-66.
[45] P. H. L. Eggermont, “The Śaka Era and the Kanika Era”, In PDK, pp. 87-93.
[46] 《大正新脩大藏經》T27, No. 1545, 第1004頁。
[47] P. H. L. Eggermont, “The History Philippica of Pompeius Trogus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Scythian Empire”, In PDK, pp. 97-102.
[48] 注43所引余太山書,第144-167頁。
[50] 注20所引余太山文。
[51] 注44所引A. H. Dani文。
[52] R. Göbl, “Numismatic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Date of Kanika”, In PDK, pp.103-113; D. W. MacDowall, “Numismatic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Kanika”,In PDK, pp. 134-149.
[53] A. Maricq, “The Date of Kanika. Two Contributions in Favour of A. D. 78”, In PDK, pp. 179-199.
[54] D. C. Sircar, “The Saka Satraps of Wetern India”, In AIU, pp.178-190, esp. 183.
[55] 注 54所引D. C. Sircar文 , esp. 180-182.
[56] B. N. Mukherjee,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Date of Kanika I”, In PDK, pp.200-205.
[57] R. Ghirshman, “Fouilles de Bégram (Afghanistan)”, JA (1943-1945), pp. 59-71;R. Ghirshman, Bégram,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les Kouchans,Le Caire, Imperimerie d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46, pp.105-108; EHNI, p. 70.
[58] D. C. Sircar, “Palaeographical and Epigraphical Evidence of Kaniska’s Date”,In PDK, pp. 278-292; 注18所引D. C. Sircar文, esp. 141-149; D. C. Sircar, “The Kanishka Era”, JIH 38 (1960), pp. 185-188. 本文之介紹以第一篇爲主。
[59] S. P. Tolstov, “Dated Documents from the Toprak-kala Palace, and the Problem of the ‘Śaka Era’ and the ‘Kanika Era’”, In PDK, pp. 304-326.
[60] Б. И. Вайнберг,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Хорезма В Связи С Проблемой Кушанской Хронологии», In B. G. Gafurov; G. M. Bongard-Levin; E. A.Grantovsky; L. I. Miroshnikov; B. Y. Stavisky, ed., Central Asia in the Kushan Reriod I, Mockva, 1974, pp. 275-282.
[61] A. K. Warder, “The Possible Dates of PārŚva, Vasumitra (II), Caraka and Mātcea”, In PDK, pp. 327-336.
[62] F. Wilhelm, “Kanika and Kanika – AŚvaghosa and Mātcea”, In PDK, pp.337-345.
[63] D. C. Sircar, “The Sātavāhanas and the Chedis”, In AIU, pp. 191-216, esp. 206-210.
[64] 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23-824頁。
[65] 注44所引A. H. Dani文。
[66] 注28所引A. K. Narain文。
[67] 注57所引R. Ghirshman書,出處同。
[68] S. K. Dikshit, “The Problem of the Kuāa and the Origin of the Vikrama Samvat”, ABORI 33 (1952), pp. 114-170; 34(1953), pp. 70-112; 37(1956), pp. 27-54; 38 (1957), pp. 93-114.
[69] 注44所引A. H. Dani文。
[70] P. L. Gupta, “The Coinage of the Local Kings of Northern India and the Date of Kanika”, In PDK, pp. 114-120.
[71]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Kanika”, In PDK, pp.247-258.
[72] 注19所引B. Kumar書(Appendix II),pp. 277-283. B. Kumar的批評對象主要是R. Ghirshman。
[73] 注28所引A. K. Narain文。
[74] 參看注20所引余太山文。
[75] 注53所引A. Maricq文。
[76] J. Harmatt, “Minor Bactrian Inscription”,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3 (1965), pp. 149-205, esp. 186-195.
[77] F. R. Allchin, “Archaeology and the Date of Kaniska: the Taxila Evidence”, In PDK, pp. 4-34.
[78] 注 52 所引 R. Göbl文。
[79] 注52所引D. W. MacDowall文。
[80] 注43所引余太山書,第168-181頁。
[81] 注28所引A. K. Narain文。
[82] 說見注20所引余太山文。
[83] A. K. Narain, “A Postscript on the Date of Kanika”, In PDK, pp. 240-243.
[84] 參看注71所引E. G. Pulleyblank文。
[85] J. M. Rosen fi eld, “The Mathura School of Sculpture; Two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Kushan Chronology”, In PDK, pp. 259-277.
[86] E. Zürcher, “The Yüeh-Chih and Kanika in the Chinese Sources”, In PDK, pp.346-390, esp. 356-357.
[87] 說見馬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46—59頁。此文指出:世高以漢靈帝末年關洛擾亂纔南遊豫章、廣州,而最後死於會稽,其卒年必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以後,並非說者所指公元170年左右。
[88] H. Falk, “The yuga of Sphuijiddhvaja and the Era of the Kuâas”, SRAA 7(2001), 121-136.
[89] PHAI, pp. 467-468; H. C. Raychaudhuri, “A Note on the Chrological Relation of Kanika and Rudradāman I”, IHQ 6 (1930), 149-152.
[90] EHNI, pp. 74-81.
[91]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西域南北道綠洲諸國的兩屬現象——兼說貴霜史的一個問題》,《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486-494頁。
[92] 注28所引A. K. Narain文。
[93] 注58所引D. C. Sircar文。
[94] 注 86 所引 E. Zürcher文 , esp. 354-356.
[95] 注 19所引B. Kumar書, pp. 64-65。
[96] R. G. and D. R. Bhandarkar, “A Peep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Maurya Dynasty to the Downfall of the Imperial Gupta Dynasty, B.C. 322 - circa 500 A.D”, JBBRAS, vol. XX, Bombay 1902, pp. 356-408, esp. p. 386.
[97] R. C. Majumdar, “The Date of Kanishka”, IA 46 (1917), pp. 261-271; R. C.Majumdar, “The Kushan Chronology”,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Letters,University of Culcatta 1 (1920), pp. 65-112.
[98] PHAI,pp. 468-469,對R. C. Majumdar的公元248年說有批評,可參看。
[99] V. Lukonin, “Sassanian Conquests in the East of Iran and the Problem of Kushan Chronology”, In D. Y. Stavisky,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Culture of Central Asia in the Kushan Period (Dushanbe 1968), Abstracts of Papers by Soviet Scholars, Moscow, 1968, pp.37-39.
[100] E. Zeymal, “278 A.D. – The Date of Kanishka”, 見注99所引D. Y. Stavisky書,pp. 22-27.
[101] 注18所引D. C. Sircar文, esp. 145。